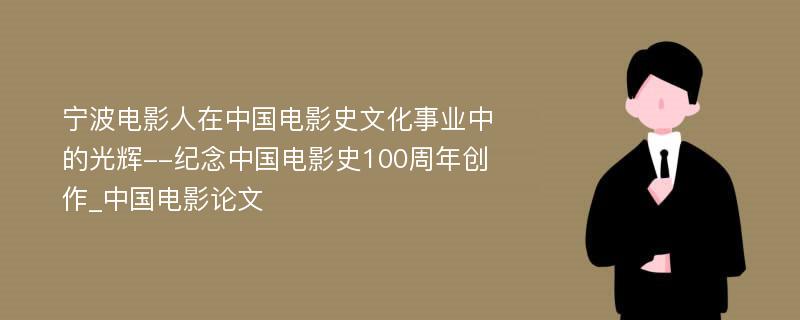
宁波籍电影家彪炳于中国电影史的文化成因——写在中国电影10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宁波论文,成因论文,写在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开一部中国电影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偏于东南海隅的古城宁波,似乎与电影有前定的情缘,在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和转型时期,宁波籍电影家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开拓性作用,引人注目地创造了中国电影十几个“第一”。其中有电影编导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林杉、桑弧、干学伟、张鑫炎、张子恩,电影事业家邵氏兄弟、徐桑楚,电影技术家郑崇兰、林圣清,还有一大批名演员如乔奇、韩非、张翼、舒适、白穆、陈思思、王丹凤、王志文、张小磊、陈肖依、洪金宝、周星驰……,总共有120多位宁波籍电影名人,这些电影家,有的出生于宁波,家乡将他们哺育长大;有的原籍为宁波,与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际,电影界评出任景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五位影坛领袖人物,其中宁波人袁牧之也榜上赫然有名。看来,像宁波这样与中国电影有着如此深厚情缘的城市,恐怕在全国找不出几个,如将他们与著名的“宁波商帮”一样,戏称为“电影宁波帮”也不为过。这个现象,自2001年在宁波举行第1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以后,就引起了电影界的广泛注意,以至成为研究的课题。原中央电影局局长、已故的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长陈播老前辈,在参加了2001年的金鸡百花节之后,曾建议宁波当地能成立研究宁波籍电影人历史功绩的小组,以宣传宁波电影人对中国电影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确实,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上,“电影宁波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有现象。
那么,宁波籍电影家为何能以独具的文化品质,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从而形成了一股冲击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呢?追根溯源,浙东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渊源关系应该是其内源性的文化动因,其主要特点表现在敢于领先天下、勇于流动开放、善于把握机遇三个方面。
浙东文化为宁波籍电影家提供了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元素,也造就了他们勇于创造、敢为天下先的独特文化性格。
浙东文化以其“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开拓创新”的文化精髓,对生活在这个区域中的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浙东重镇,具有7000年河姆渡文化深厚底蕴的宁波,其文化更是独具气质:既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历史的批判性,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宁波自宋明以来,可谓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学术文化至少有三次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心学大师王阳明、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曾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潮流,其影响遍及海内外。王阳明、黄宗羲都是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理论大师,他们的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总体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而且在近现代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和“无君之君”的体制构想,不仅适应新的生产关系,而且对维新改良甚至“五四运动”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思想更是对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宁波先贤的思想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宁波人,形成了宁波人“开拓、开放、开明”的文化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东文化精神,给宁波人提供了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元素,他们骨子里具有一种冒险精神,耻为人后,敢为天下先。宁波籍电影家汲取了浙东文化的精髓,对新文化有敏锐的感知力。当20世纪初,电影这一来自西方的最新艺术形式舶进上海之时,他们不仅接纳了这一新潮艺术,同时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率先抢滩,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当以张石川、应云卫、袁牧之最为突出。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拓荒者的张石川(1890—1953),这个14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闯荡的宁波人,首先打破了中国电影蛮荒时代的沉寂,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拓荒时代,他创办的“明星”公司促使中国电影走进了默片时代的黄金岁月。他导演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成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与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一样永远被载入电影的史册。1923年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拍摄了《孤儿救祖记》,使中国电影实现了从短故事片向长故事片的过渡;这部影片的另一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大大刺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发展,它的问世使国产片获得了足够的市场和舆论信誉,中国电影进入了第一个高潮,1926年在上海一地有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过影片,电影界生机勃勃、热闹非凡。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在中国电影处于探索并重大转型时期,又有两位宁波人应云卫(1904—1967)、袁牧之(1909—1978)脱颖而出,使中国电影有了重大突破。应云卫导演、袁牧之编剧并主演的《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用有声电影手法拍摄的影片,音响第一次成为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如主人公陶建平在工厂做工时的机器声响,他抱着婴儿送到育婴堂去时的狂风暴雨声及婴儿啼哭声,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图解作用,增加了特定情景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在片尾,当陶建平被执行枪决时,沉重的脚步声和铁链声,行刑时的枪声,以及画外的《毕业歌》声,通过音响、歌唱和画面的结合,影片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因此《桃李劫》称得上是中国有声电影的里程碑,从此有声电影走向成熟。而袁牧之编、导、演的《都市风光》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讽刺喜剧故事片,对讽刺喜剧电影作了全面的探索和尝试,它对中国电影的意义主要在于音乐第一次在影片中成为艺术表现手段,音乐与画面的完美结合,不仅使情绪和节奏完全一致,而且在揭示思想含义方面也起到了互为补充的作用,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更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最高典范,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享誉海内外。影片表现的是上海底层平民的生存状态,以喜剧手法处理穷苦人民不幸生活的悲剧性内容,既饱含着眼泪与辛酸,又充满了欢乐和嘲笑,整部影片明快、诙谐、隽永、充满了对生活的信心,其悲喜交集的情境及其整体的表现风格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路天使》电影语言的运用,也堪称一流,流畅生动,摄影机运动活泼,画面镜头鲜活可感。影片中的主题歌《四季歌》、《天涯歌女》早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歌曲。《马路天使》受到了世界一些著名电影史学家和影评家的高度赞赏,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不无惊叹地赞道:“中国影片《马路天使》堪称是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竟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想见,30年代中国的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影响该有多么巨大。”
上述电影家身上所显示出的正是宁波人对于开启新文化所独具的智慧和眼光,以及积极探索、勇于创造的文化品质。因此说,浙东文化的影响,是宁波电影人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化动因之一。
浙东面海文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宁波籍电影家在吸收了故乡母体文化的乳汁以后,又以自己独特的“基因”,按照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在异地发育壮大。
宁波背靠内陆,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在文化的生成方面需要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运行机制,为生存开拓新的疆域,包括精神疆域,以使自身成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登陆点和接纳点。加之,宁波域内河道密布,内外交通便捷,宁波人历来又有不重儒业而重商贾的习俗,必造成其好动善变的性格和乐于向外拓展的文化氛围,因此,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养成了宁波文化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独特品性。宁波人从东海之滨出发,汇入到开放的文化潮流中去,正是他们面向大海、走出封闭的文化心态的展露。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也使得宁波人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时,往往能形成为自觉性行为,也只有这样的自觉的文化接受需求,才使宁波人在历史提供某种机缘时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表现欲和冲击力,这就是宁波电影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居于全国上乘的深层内因。
在流动性、开放性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宁波人十几岁就要离家出去闯天下,否则会被人嘲笑,甚至连媳妇都娶不上。宁波籍电影家几乎也都是十几岁甚至更小就离开家乡,到异地寻求发展的。而上海是宁波人走向天下的首选目标,宁波籍电影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在上海成长壮大的,这绝非偶然。宁波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曾对全国的学术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自19世纪末上海迅速崛起后,宁波对全国的影响就大不如以前了,逐渐萎缩成一个地方区域性城市,再要恢复昔日地位已非常困难,致使耻为人后、勇于进取的宁波人作出要成才非要到上海去不可的文化选择。正因为上海成为了文化中心,所以西方的电影进入中国后,首先在上海落脚,使上海成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基地,这就给“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生”而云集到上海的宁波电影人提供了历史机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不同途径先后选择了电影作为终身奋斗的职业,并以其创造性的努力和骄人的成就迅速占据了中国电影的各路要津,或成为开创者、奠基人,或成为一种电影片种、一个电影流派的开拓者或代表人物。
当然,宁波籍电影家的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如出生在宁波市区的袁牧之,在已经成为一流电影明星的情况下,他仍然以文化行走者的姿态,毅然离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沿着武汉,延安、苏联、蒙古、中国的东北,最后到北京这样一条漫长的路线一路走下去,从南疆到北国,处处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广泛的流动性成为他事业成功的前提。而出生于宁波镇海的邵醉翁(1896—1979)、邵村人(1899—1973)、邵仁枚(1901—1985)、邵逸夫(1907—)四兄弟,更是把这种文化性格展露得淋漓尽致。1925年他们筹集资金一万元、在上海创办“天一公司”后不久,便把中国电影企业推向了海外,率先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了中国电影放映网,刮起了一股商业电影的飓风。后来邵氏兄弟干脆把“天一”迁往香港,于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创建了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影机构,拥有大型摄影棚10座,集彩色洗印、配音车间、办公楼、宿舍楼、外景街道、皇宫庭园建筑于一体的邵氏影城,可年产影片50部,邵氏兄弟一跃成为称霸于东南亚地区的电影商业巨擘,邵逸夫则被誉为“亚洲娱乐大王”。
宁波籍电影家继承了浙东文化启蒙思想的历史传统,面对历史的呼唤,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把握历史机遇,从而做出创造性的努力。
浙东文化中有深厚的启蒙文化思潮的历史积累,处在引领全国文化新潮的位置。有着对于优秀传统自觉接受意识并具有叛逆传统精神的宁波电影人,面对历史呼唤,对自明代以来的启蒙文化思潮,总是怀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怀恋和心理认同,产生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得以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邵氏兄弟为代表的宁波电影人善于审时度势,当中国电影每进入到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他们便紧紧抓住历史机运,挺立潮头,勇攀潮流,作无所畏惧的搏击,并以其先导性的艺术创作思想给中国电影发展以深层影响,并显示出开拓新路的潜能,起到了切切实实的引领作用。
在人民电影创业的重大转型时期,又是宁波籍电影家率先迈出了第一步,其中袁牧之是最突出的一位。在抗日烽火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折点,袁牧之投奔延安,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参加创建延安电影团,并担任电影团总编导,拍摄了大型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它虽没有最后完成,却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奠基石,开创了中国新闻纪录片的新纪元。1946年,以袁牧之为代表的党的电影工作者,抓住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机遇,克服重重困难,在长春一举接管了日寇留下来的伪满映,大大扩展了人民电影事业的实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任厂长。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作为中央电影局首任局长,直接领导了新中国电影事业初创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三年里,迅速恢复和重建了电影生产能力,拍出了一大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除袁牧之以外,还有一大批宁波人在编、导、演各个领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成为所属领域的开拓性的领军人物,创造了中国电影的多个“第一”。如出生在宁波市区的干学伟(1917—),1950年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内蒙人民的胜利》,为此后的同类题材电影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宁波籍导演桑弧(1916—2004)则完成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的重大转折,使中国电影终于赶上了世界电影的脚步,1954年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6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1962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另一位出生于宁波江北区庄桥镇的编导林杉(1914—1992),其代表作《上甘岭》、《党的女儿》虽然不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第一”,但这两部影片影响了几代人,将它们视作“红色电影”成熟的代表作,是当之无愧的。宁波鄞县人电影录音师林圣清(1927—),继另一位鄞县同乡摄影师郑崇兰(1893—1974)于1947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35毫米有声电影摄影机之后,于1957年主持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电影磁性录音机,填补了中国电影技术上的一项空白。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呈现出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当时香港长城影片公司向主创人员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出些好电影,让世界了解“文化革命”后中国电影的特色。宁波籍的香港导演张鑫炎(1934—)一向热爱体育,他受乒乓外交成功的启发,想到中国的武术也是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喜爱的中国传统文化,便以一部《少林寺》开了新时期中国新武侠电影之先河,在影坛上掀起了风格新颖的武术电影热潮,也使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造诣传遍了海内外,为新时期电影创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都是“电影宁波帮”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极好例证。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宁波电影论文; 上海电影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宁波拓展论文; 马路天使论文; 袁牧之论文; 张石川论文; 应云卫论文; 剧情片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