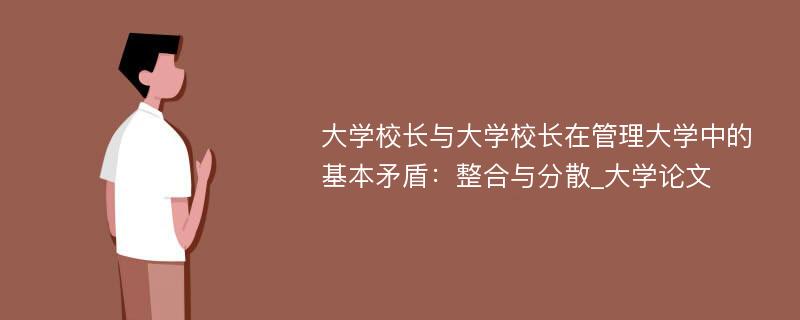
大学校长治校的基本矛盾:整合与分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分散论文,大学校长论文,治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18(2007)05-0001-05
乍一看去,大学这块土地,与别的组织并没有什么两样,成员整天忙碌地献身于共同追求的目标——真理——而成为一个整体。然而,深入大学内部,才发现大学这个组织又是那么的不同,人员分散在各自独立而互不相同的学科领域,似乎相互没有关系地、独立地我行我素,教师对自己学科的忠诚超过自己效劳的组织,大学组织似乎只是他们暂时栖身之地而已。高等学校是具有学科和事业单位双重权力的矩阵结构。在这个矩阵结构中,教学、科研人员处于双重权威之下,同时从属于一个学科和一个学校。高等学校管理始终交织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几乎在所有的高等学校中,在需要共同管理和要求理性自由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作为大学校长,虽然是组织的领导人,对于组织成员的工作似乎并不具有直接命令之权力,不少决策权普遍分散于整个组织,掌握在学富五车的教授手中。重要的学术政策“都是起源于工作台、实验室和午餐漫谈,然后向上向外渗透的”[1],而不像其它组织那样,由最高决策部门做出决定,自上而下地层层予以执行。所以,Cohen等的研究结论认为,大学是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和“松散联结的”组织,其“目标是模糊的、人员是流动的、技术是不明晰的”[2]。在这样的组织当中,达成组织目标的共识既没必要也不可行,正式的权力不但很少影响大学发展方向和组织个体选择,而且大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组织,存在自我分散的内在倾向。
再从管理学组织学的角度来考察大学组织的发展,也可以看到现代大学的这种分散倾向。促进组织分权的最主要因素包括:“组织的规模、活动的分散性、培训管理人员的需要”[3]。权力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管理层次的增加而与职责一起逐层分解;组织人员的活动越分散,要求权力分散的程度就越强烈。为了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水平,提高组织的整体适应能力,分散领导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大学成员活动的高度分散性导致权力弥漫和共享。
现代大学与其“祖先”相比,已经发生并还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学规模扩大,不仅表现在成员数量剧增,也表现在学科门类的延伸。大学复杂性增加,不仅表现在成员成分上和需求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识领域的急剧交互与急速发展,也表现在大学自身职能拓展的无限性趋势,以及内外关系结构的交融作用。大学不但是科尔(Clark Kerr)描述的“巨型大学”,而且也是博克刻画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规模扩大和复杂性增加,使得大学变成一个十足的科层式机构,再靠大学校长事必躬亲地领导已经没有可能。因此,为了使大学有效运行,必须实行分散化领导。更重要的是,由于学科以及附着于众多学科上的学术权威的增加,他们各自强调自己领域的优先权,形成一个又一个学术“小山头”,成为一个又一个“成本核算中心”,而加剧了大学自组织的这种分散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越综合、学术“明星”越多,对于大学校长治校中实施利益整合就越不利。正因为这种分散性传统与现实性存在,为了增强大学的快速应变能力,培养众多的次级和次次级领导者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分散,把责、权、利一起弥漫于整个组织,锻炼全体成员的领导管理能力。
任何事情总是在一定限度内发生和发展。适度分散虽然有益于学术自由与自治,增强成员使命感和组织适应性,但是,过度分散不但使得大学统一的政策形同虚设,而且降低了越来越有限资源的使用效力,可能危及大学整体利益。大学组织的这种神奇特性——内在分散需要和扩展中的强烈分散倾向——给大学校长强调整合的需要带来严重挑战。
大学校长作为领导者,其作用就是从全局利益和未来发展需要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限制权力分散,适当整合权力,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大学适应性与竞争力。所以,对于大学校长治校,分散与整合构成一对基本矛盾。
在这对矛盾关系处理之中,体现出大学校长的治校智慧。正是有了这样的空间,大学校长能够发挥其内外关系的纽带作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汇作用,各种资源的综合调配作用,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维护整个大学的利益,推动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获得新发展。大学校长治校中发挥整合作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避免大学因为膨胀而出现被撕裂的危险。大学越是巨大,越是复杂,利益以及权力的分散倾向就越是剧烈。这种“可怕的”分散倾向,恰恰给大学校长发挥有效而及时的整合作用提供了可能和契机。
第二,占领学术自由与自治的“无人地带”。即使是最权威的教授,对于浩瀚的现代学术领域也只能熟知自己似乎越来越狭窄的学科“冰山”之一角。学科演绎的高速化和高度复杂化,已经使得教授们成为真实的“专家”,而无暇顾及别的学科和学术以外的行政管理事务。这种“漠视”使得他们对于自己学术专长以外的领导和管理领域不具备专业权威。相反,大学领导与大学管理变得越来越专业,大学校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所具有的职能,恰恰填补教授学科领域之空白,占领各个学科之间、各位教授之间的“无人地带”。
第三,快速应对飞速变化环境的需要。现代大学所面对的时代动荡而多变,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且这个时代要求大学予以及时回应。完成这样的任务不能仅仅依靠分散的学术利益团体和象牙塔中的学术权威,还要有特殊的行政机制。大学校长的这种纽带作用就愈发凸显。
组织集权整合倾向,主要与组织历史和领导者的个性相关,还与组织领导与管理的要求相联。如果大学是历史较短并在较小规模、较低层次上逐步壮大起来的,那么大部分决策权就会习惯性地集中于大学校长手中,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组织习惯,形成一种组织文化。即使当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层次逐渐增加,大学校长也更加习惯地保留本应分散的权力,强调集中整合的重要作用。我们所看到的有所作为的首任大学领导者一般都是“铁腕人物”,特别强调集中整合作用,就是这个道理。朱九思先生是这样,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吉尔曼先生、英国沃威克(Warwick)大学的巴特沃斯先生(Jack Butterworth)(任职时间为1965 -1985年),他们都是学校的创始功臣,也都是强权领导者。
同时,大学校长治校又是高度个人化的领导行为,直接与大学校长的个性紧密相关。如果个性突出,自信果断,强调效率优先,那么,他就比较喜欢对下属实行严格的控制,不自觉地通过集中权力的形式,来保证自己的意志内化为组织行为。强调通过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较快地创造出治校业绩,从而提高和巩固自己在大学中的领导地位,强化校长之领导权威。朱九思就是一个多谋善断,强调“领导就是要敢于负责”的校长,所以他治校就比较强调集中整合作用。
另外,当大学所处的内外环境突然恶化,靠个体或个别部门不能应对的时候,大学校长的整合作用所体现出来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行动效率,就会被前所未有地得以强调。当大学面临恶劣的环境,处于转型期、快速发展和拓展时期,大学运转就会形成对集中领导的集体呼唤,运行更加注重行政效率,集体要求组织目标的加速实现,需要建立强权领导集体。这时,大学校长的整合作用往往显得必不可少。哈佛大学的艾略奥特校长、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校长(Harper)、加州大学的科尔校长(Clark Kerr)等,在特殊的环境下,为了学校发展,更多强调的是大学校长的领导作用。朱九思为了华中理工大学的快速转型和水平提升,也是采取“集中优先,兼顾分散”的领导方式。
最后,集中力量的形成还与大学校长任期有关。一般来讲,任职时间较短、任期较短的大学校长,往往以巩固“阵地”为权宜选择,能“大度”地容忍部属蚕食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不愿担当得罪教授和重要资深管理者的风险。相反,任职时间长、任期长的大学校长,他们不但对于大学的情况熟悉,拥有发言的“专业”权力,而且还在过去的岁月中已经凝结起自己的光辉,凭着“资格”和“老本”,逻辑地拥有较多权力。
集中整合至少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保证大学组织利益和政策的统一性。在一个大学生存环境急剧恶劣、竞争十分激烈、学科由分解走向综合与协作的时代,各类成员之间、各个学科之间、各种职能之间、各种内外关系之间、各种需求之间,都需要高度的协调一致,毕竟小利益可以很多,整体利益却只能有一个。因此,通过整合可以防止政出多门和相互矛盾,便于统一认识和集中力量。大学校长的整合作用就有力地彰显出来了。
第二,能够提高大学组织运行效率。大学组织是一个复合的复杂组织。如果继续任由各位教授治校的能量无节制地释放,那么大学必将分崩离析。为了防止组织机能瘫痪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当今大学的运行效率和资源运用效益已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大学校长的领导作用有了史无前例的发挥空间。大学校长正是因为可以依靠集中指挥的行政体系,把治校决策与意志有效而迅速地变成组织行为逐步成为现实,提升着大学应变速度与能力。像“1933年以前,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一直没有专职校长,由教授利用业余时间管理大学工作。那种轻松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了”[4]。就是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级老牌大学,第27届校长萨门尔斯在2001年10月12日上任的就职演说中,也特别强调集体的整合作用。他说:“尽管我们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但是因为共同的坚定信仰和共同的目标,作为一个大学整体——学者和学生的共同体——我们需要走在一起。可能我们各自饮取各自的溪流,但是我们各自的小溪却来自哈佛知识与传统的水库。每一个人的水平与声誉来自我们集体的实力。我们将不会牺牲自治赐予的灵活与创见,但是我们保证,哈佛——作为一个大学整体——比以往任何时期——集体力量将超过所有个体之和。”[5] 同样,以上两方面在朱九思治校过程中表现都很明显。他强调集中整合不但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之下迅速统一了全校意志,而且通过多年苦心经营的行政指挥体系把这种意志迅速地转化为行动和成果,充分体现出大学校长整合的强大力量和明显好处。
尽管大学校长实施集中整合的领导策略越来越需要,但过度整合又会导致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过度整合的决策质量可能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增加而下降。原因是现代大学校长与其说是一个学者,倒不如说更像一位官员,他们被官僚科层阻隔而越来越远离基层,获得的信息不再是一手的真实情况,而是经过层层传递与过滤、可能被严重扭曲的汇报、报告。依据非实时而又非真实的信息决策,不但速度迟缓,而且质量受到极大怀疑。
第二,过度整合使得大学适应能力下降。由于现代社会环境复杂、快速、多变,而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又是那么紧密和多元,因而大学的适应也应该是灵敏而多样的。这种敏捷而多样的反应,需要形成既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全局的,既可能是微观的也可能是宏观的多元自动调节机制,缓解利益冲突和环境压力。所以,仅依靠大学高层的有限力量来适应所有环境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同变量,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几乎没有可能。过度的集中,导致组织对领导者的过度依赖,可能使得各个小团体丧失自适应和自我调整能力。
第三,过度整合导致大学组织的学习能力下降。过度整合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以大学校长为中心的领导层面,下属就变成依赖上司被动地、机械地执行命令的组织人。这不但不利于培养他们的自我领导能力,而且将使他们失去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上述三种情况在大学转型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是由于大学机体固有的惰性,习惯热恋于过去的领导管理模式造成的,而在转型时期,新的结构和新的机制尚待形成。
朱九思治校总体上是比较强调集中领导,他认为:“发扬民主还有个集中的问题。只民主不集中,人人各行其是,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是对立的统一,失掉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了。”但是,到了他治校的后期,由于学校教师和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学科综合化的逐渐生成,科研活动强度的明显加大,学校处于全面扩张时期,大学变得不再像初期那样容易驾驭。由于管理和整合任务的迫切,朱九思也不可能再像他过去习惯一样经常性地深入一线了解情况,直接指挥,获得的决策信息主要是职能部门,更多是来自于他新设置的诸如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庞大的教研科、高教研究室等信息挖掘和智囊咨询机构的中转,以及各种内部简报、情况反映等二手材料。尽管他还经常获得教师来信反馈的直接信息,但总体上说,他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能主动地控制信息的流动,决策信息丢失、失真甚至扭曲的情况是难免的。同时,集中的结果还导致管理机构职能和人员的增加,机构职能出现重叠,政策相互矛盾的情况也就难免。所以,在决策的灵敏性和质量上受到一定影响。所以,1985年他的继任者为了缓解人力、财力的紧张,减少了招生的人数;同时,为了避免过度集中,调整了领导体制,“实行分级管理,做到层层负责”[6],扩大系一级和教研室的自主权,不越级指挥。这次调整实际上是一次整合与分散这对基本矛盾的重新平衡。
从以上分析看来,整合也好,分散也罢,都是相对的,各自都有自己的位置,都不能因为一方的优越性而否认另外一方的好处,搞绝对化和走极端。正确的态度是,实现这对矛盾的动态平衡和对立统一。大学校长处理整合与分散这对矛盾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与国家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相契合。体制的决定性影响比较复杂。对于一个实行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国家来说,可能大学校长容易受到体制影响,潜移默化地更加倾向于实行集中整合,强调全局利益而不是局部好处。我国的总体情况就是如此。大学校长就是国家政治统治链条上的一位执行官员,“我就是领导”的观念就强化了“我要领导”的行为。同时,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正是因为国家的高度集中,大学领导层可能被虚化,其领导的力量可能被高度弱化,采取“无为而治”的放任态度,甘当革命的一块砖,听从上级的指挥和调遣,以致于失去对大学集中整合的“兴趣”和能力。比如,日本国立和公立大学以及法国大学校长的作用就非常不突出。
实行民主和权力分离的政体,大学管理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比如,美国大学外部没有联邦政府的统一领导,来自州政府的行政干预也较少,实行高度大学自治和高度竞争;内部实行由学术“外行”组成的董事会集体领导,这些“外行”们忙于自己的事务而把权力全权委托给他们聘用的大学校长。欧洲由于学术传统力量的巨大作用以及国家对大学的领导,大多数国家的大学校长权力较小,对于整个大学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并不彰显。所以,美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有充分的保证,集中的力量超过欧洲任何一位大学校长[7]。
第二,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来自文化传统的影响总是潜在而深远的。有着封建专制传统的东方国家,长官意志容易获得认可,总是习惯于自己领导、自己指挥和支配,即使领导的客体是大学教授也不例外。相反,有着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对于被领导和被管理总是有一种习惯性的抵制,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更加讲求平等、自由和法制。
同时,还表现在与大学形成的传统有密切关系。有着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传统的国家,往往教授享有的权力较大,而大学校长的整合力量经常受到遮蔽。欧洲大学源自于行会组织,有遵循学术专家自治的古老行规性传统,大学校长通过内部选举产生,行使有限的协调和整合作用。相反,美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行会力量的约束,也没有学术权威形成的巨大学术权力的制约,治校之权当然地掌握在董事会和大学校长手中,整合力量被习惯地沿袭。在我国,尽管经过蔡元培先生等效仿德国模式,倡导教授治校,但并没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契合而凝固成为一种强大的大学组织文化传统;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从一开始就是用国家意志举办,突出大学的政治功能,按照政府行政机构的配属和领导方式行事,权力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状。
第三,与大学组织文化相契合。“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8] 大学组织文化是经过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的结晶,是大学精神、价值观、行为、制度的综合体现,直接影响大学校长在处理整合与分散矛盾中所采取的治校策略。在那些具有强有力学术控制制度和观念的大学,大学校长整合的力量可能会受到威胁。相反,在那些有着强大行政领导习惯的大学,大学校长实行分散领导策略可能还会被视为软弱和无能。
第四,与时宜相契合。实施大学领导的条件,不仅取决于领导者,而且也取决于被领导者和具体领导环境。权变理论告诉我们,不存在一种适合一切情况的最好的领导模式。影响领导活动成效的变量,并不像建立数学模型那样清楚并能用数字区分其权重。领导活动中的因素不但不简单而且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轻易略去,也没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一劳永逸的答案或者惯例。领导不能靠手册、用规范来完成,而常常可能是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的一种概率性直观判断。“敢于担当风险”——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大学校长治校策略必须适应变化着的情况,对不同领导对象、不同任务、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应采取不同整合或分散模式。否则,把本该授予或分散的权力还不合时宜地抓住,把本该整合集中的事项又不合时宜地分散,那么,治校活动一定会出现不必要的紊乱。
一般说,尽管大学校长应该整合的是大学发展方向、政策制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建立、资源配置、人力配属、责权划定与考核等重大事项,而把重大事项之外的“细小”事项分散,同时把学术的决定权委托给专家及其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但是,重大与细小事项之间的区分似乎只在理论上可以人为地划界,在实践中却非常灵活,界线常常模糊不清,全靠大学校长个人对于具体事情的态度和处置方式。也许一件看似并不影响全局的“小事”,处理不当,可能就演变成影响全局的“重大”事情。在大学中,就是学术与行政这两大权力的行使也并不是在学理研究中那样有清晰之分野,实际上往往也是模糊而交织互动的。即使是所谓“纯粹”的学术问题,往往发展的结果也需要大学校长以“学术自由”的名义,采用行政领导的方式予以处理。谁叫大学校长既是行政力量的中心,又是学术力量的平衡点呢?大学校长治校策略必须具有某种灵活性,适时符合时宜地调整,而不能僵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大学校长的领导艺术就体现在此。
所以,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是分散还是整合,要与一个国家的体制和文化传统因素,大学组织文化,以及具体的时机权变地兼容,否则,分散或者整合都不会取得好效果。
最后,用阿什比的话作为辩证处理整合与分散这对矛盾关系的结束语是比较合适的:“(大学的)决策权普遍分散在整个组织里,而且如果要保持组织的统一,必须使这些决策相互协调,使每个成员只感到最小的限制或压抑。”[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