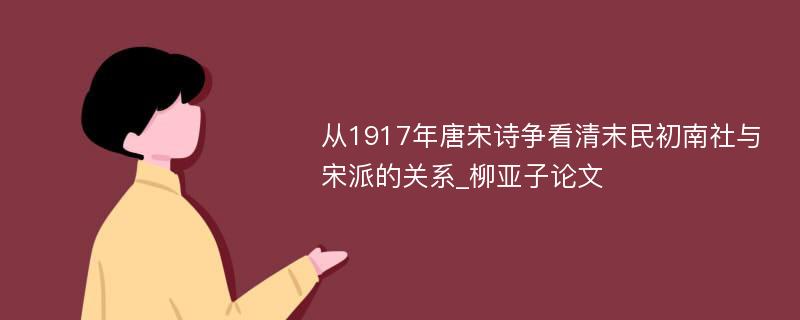
从1917年唐宋诗之争看南社与晚清民初宋诗派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晚清论文,唐宋论文,之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3-0136-04
晚清民初宋诗派和南社同为20世纪初期重要的文学流派,这两个流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长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中,南社始终占据光辉的一面,宋诗派则被冠以落后腐朽之名。人们往往从政治观念出发来评论这两个文学流派,南社的影响被有意无意放大,宋诗派则成为被压抑的存在。本文试图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来重新评价宋诗派的历史地位。本文所说的“晚清民初宋诗派”,指出现于清代光绪年间、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宗宋诗派,其理论家有陈衍,创作上的代表有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主张诗歌变风变雅,以杜韩苏黄为师法对象。文章中也以“近代宋诗派”简略称之。
南社唐宋诗之争从1914年初显端倪,至1917年达到高潮。先来回顾一下这场论争的始末。
南社在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宗唐和宗宋的分歧,但这种内在矛盾一直处于潜在状态,并未公开化。直到1914年,柳亚子发表《论诗六绝句》,批评宋诗派与其他学古诗派,矛盾才开始激化:“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柳亚子对宋诗派的激烈抨击埋下了几年后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的伏笔。[1]
1916年1月26日,姚鹓雏(锡钧)开始在《民国日报》连载诗话,盛赞同光体中的闽派诗人郑孝胥、陈衍、陈宝琛以及赣派诗人陈三立:“同光而后,北宋之说昌,健者多为闽士,如海藏、石遗、听水诸家,以及义宁陈散原。其人生平可以勿论,独论其诗,则皆不失为一代作者矣!”[2] 文中海藏、石遗、听水分别指近代宋诗运动代表人物郑孝胥、陈衍和陈宝琛。年轻的南社诗人姚鹓雏表达了对宋诗派人物的仰慕之情。
同年8月8日,傅專① 在《长沙日报》连续发表诗话,分析陈三立诗的艺术特点,认为“七律莫盛于唐,宋代继之,遂开新响。山谷,其一大宗也,近人惟陈散原能为之。”[3] 由此可见,柳亚子的申唐黜宋引起了南社内部宗宋诗人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原本潜伏于南社内的唐宋诗之争。之后双方论战逐渐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8月23日,姚大慈发表诗叙,自述由学唐而学宋的经过,称誉陈三立的七律源于江西诗派,而又自成一家。[4] 傅專和姚大慈的文章足以说明民初宋诗派影响之广泛,这也是柳亚子等南社宗唐派诗人所不能容忍的。
1916年11月17日,吴虞发表文章声援柳亚子:“前读《南社》集,见有友人谢无量诗,后读《民国日报》,见有亚子《论诗绝句》,‘郑陈枯寂无生趣’云云,大为神契。……上海诗流,几为陈、郑一派所垄断,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5] 吴虞是时并非南社中人,却率先响应柳亚子对宋诗派的批评,使得此时孤立无援的柳亚子欣喜若狂,极力要拉其入社,以壮大社内宗唐派的力量。“上海诗流,几为陈、郑一派所垄断,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道出了柳亚子等部分南社诗人的心声,声势日隆的宋诗派无疑是以诗坛主流自居的南社的最有力的对手,这是柳亚子等向宋诗派发难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南社内部的宗宋派诗人继续发表文章,表达对宋诗派成员的敬慕之情。11月,与宋诗派核心人物陈三立、郑孝胥、陈衍、陈曾寿等交谊颇深的南社诗人诸贞壮② 在其诗作中表达了对宋诗派领袖郑孝胥的倾慕之情,其《夜过海藏楼,归纪所语,简太夷并示拔可》中“主人论诗得真理,近称米氏椎欧阳。上规韩白许永叔,出以简淡非寻常。老颠落笔不局曲,意境往往齐苏黄。前闻沈侯语夏五,文字不可轻其乡。”[6] 在诗中高度评价了郑孝胥的诗歌主张,“沈侯”即沈曾植,“夏五”是夏敬观,都是宋诗派的重要成员,诸贞壮高度认可了宋诗派创作理论。
12月9日,姚鹓雏继续发表诗话,驳斥吴虞对陈三立诗的批评。[7] 此时的论争尚属于诗学旨趣的争论,双方均能平心静气地进行理论上地探讨。宗宋派诗人既赞颂了陈三立等人的创作,也指出了其创作上的缺憾。
进入1917年,矛盾骤然激化,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的诗学论争。
1917年1月19日,柳亚子致函吴虞,陈述提倡唐音,反对同光体的一贯主张,引吴虞为同调,动员他加入南社:“今读先生所言,知于囊时持论,若合符节。窃情吾道不孤,私以入道为请,甚以先生不弃鄙陋,惠然肯来,则拔帜树帜,可以助我张目,万幸万幸!”[8] 以上足见:南社内部宗宋势头强劲,柳亚子也感到了压力并试图振衰起弊。这是他拉吴虞入社,以壮大声势的主要意图。吴虞诗歌宗唐,被柳亚子引为同调。随着吴虞1917年3月5日加盟,南社内部宗唐派势力得到加强,沉默已久的柳亚子开始反击。以此为界,南社内部的宗唐宗宋之争渐趋白热化。
1917年3月11日,社员胡先骕写信给柳亚子,恭维同光体。本日,柳亚子在《民国日报》新辟的《文坛艺薮》栏发表胡先骕诗作二首,尖锐地指责以黄庭坚为鼻祖的江西诗派:“诗派江西宁足道,妄持燕石砥琼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儿问毁誉。分宁茶客黄山谷,能解诗家三昧无?千古知言冯定远,比他嫠妇与驴夫。”[9] 以胡先骕的信为导火索,矛盾迅速激化,隐忍已久的柳亚子以近乎谩骂的口吻严厉斥责宋诗派及其追随者。③ 4月23日,柳亚子致书社员杨铨(杏佛),告诉他曾以两诗回报胡先骕,表示不同意胡适对南社的批评,讥笑胡所作白话诗为“笑话”。他认为“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盛赞吴虞的诗“风格学盛唐,而学术则宗卢(梭)、孟(德斯鸠)”,推为“诗界革命”的“健者”:“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又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又诗文本同源异流,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殆不可少;第亦宜简洁,毋伤支离。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10] 柳亚子文中所指,是1916年10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的留学生胡适的文章。在文章中胡适同时批评了南社和宋诗派,但认为南社创作不如宋诗派。同时,胡适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6月27日,胡适自美归国,舟中,记述了对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的看法,认为“理想宜新”是正确的,但“形式宜旧”则错:“(柳亚子寄杏佛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11] 至此,1917年左右文学场域中三股力量激烈碰撞。南社中的宗唐势力既反宋诗派也反文学革命,宋诗派追随者对宗唐势力进行了反驳,胡适等白话诗倡导者激烈批评南社,附带提出对宋诗派的意见。
同年6月28、29日,柳亚子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了闻野鹤等人对宋诗派的鼓吹,指出:“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反对吾言者,皆所谓乡愿也。”[12] 柳亚子此文,标志着唐宋诗之争的升级。将同光体斥为“亡国之音”、“妖孽”,表明论争已超出一般意义的诗学论争而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
柳亚子文章发表后,激起了宋诗派追随者的强烈反应。7月6日,姚鹓雏发表论诗四首,认为郑孝胥等自成风气,属闽派,和江西诗派无关;作诗不必“主唐奴宋”。并以钱谦益和张溥为例,说明作家的节操和文采是两回事:“闽派年来数郑陈,豫章风气不相邻。无端拦入西江社,双井还应笑后人。诗家风气不相师,春兰秋菊自一时。何事操戈及同室,主唐奴宋我终疑。虞山投笔终降虏,草莽蹉跎有太仓。奇文高节原两事,论才怀古总茫茫。十年京洛忆风尘,偶把枯禅入论文。黎里先生劳寄语,谈诗磨剑太纷纷。”[13]“主唐奴宋我终疑”无疑是针对柳亚子、吴虞等人分唐界宋的论断。而“奇文高节原两事”则针对柳亚子从政治立场上来评判人物,将矛头直指柳亚子。
自7月6日起,《民国日报》陆续发表柳亚子的长文《再质野鹤》,全面反驳闻宥的观点,劝他不要作陈三立、郑孝胥的“驯奴”,放弃宋诗和清人学宋之作,“别创新声”。[14] 有趣的是,柳亚子的矛头既指向闻野鹤、姚鹓雏等宋诗派的拥护者,也针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至其数当代作者,则亦曰郑、陈、樊、易而已”,可见胡适对宋诗派等人的推崇相当刺痛柳亚子。柳亚子还以“诗文与气运相关,盛衰消长之理原于自然”的论断对宋诗派领袖郑孝胥、陈三立的文风人品进行尖锐的批评。柳亚子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闻野鹤等人进行了反诘。将文学上的“宋诗派”与政治上的复辟势力捆绑在一起,视其为“亡国之音”,是柳亚子的核心论点。其实,宋诗派中只有少数人趟进了复辟的浑水,而如陈三立、陈衍等宋诗派领袖则远离政治的风波。再者,让宋诗派为清室覆亡“买单”的做法确实有点高估了文学的作用而忽略了历史变迁的复杂性。
7月10日,柳亚子发表《论诗五首》,回答姚锡钧,继续鼓吹唐音。7月19日,南社另一重要成员陈去病发表文章声援柳亚子。[15] 而柳亚子则在《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斥朱鸳雏》,批评其《评诗》一文,认为“亡国大夫”与“共和国民的性情”,“天然不同”,鼓吹同光体乃是“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士大夫之性情”。文章充分肯定吴虞的反孔言论,也充分肯定他的诗作。[16] 7月31日朱玺在《中华新报》发表《论诗斥柳亚子》,赞誉郑孝胥、陈三立诗,嘲笑柳亚子不识诗坛派别,并进行谩骂、攻击。朱玺《论诗斥柳亚子》:“当年派别未分明,扪烛原来是一盲。如此厚颜廉耻丧,居然庸妄窃诗盟。海藏翛游自俊流,散原诙怪亦无俦。竖儿枉自矜蛮性,螳臂当车不解羞。”[17] 宗唐宗宋之争渐成意气之争,敌对双方极尽谩骂之词。“如此厚颜廉耻丧,居然庸妄窃诗盟”,恐怕是最能激怒柳亚子的语言。年少气盛的柳亚子本以诗坛盟主自许,鹓雏的讽刺激怒了柳亚子。柳亚子盛怒之下作出了驱逐鹓雏出社的决定。唐宋诗之争达到了高潮。8月1日,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布告驱逐朱鸳雏出社,8月9日柳亚子又宣布逐成舍我出社。
驱逐朱鸳雏和成舍我标志着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达到了高潮。
姚鹓雏对这场纠纷的严重性始料未及,有懊悔之意,也想给这场纷争降一下温。8月19日,鹓雏发表短文,申述酷好江西派的原因,批评后学者走得过远,[18] 但此时的论争已溢出了正常的文学论争范围,姚鹓雏难以控制局势的发展。
8月19日,成舍我继续发表《答客问》,声言“人人有天赋之权”,“诗宗何派,任人自由,干涉之者必反对之。”[19] 论争逐渐变成了对南社领导权的争夺。8月23日柳亚子发表短文,对姚锡钧表示谅解。[20] 姚鹓雏的“幡然悔过”,柳欣然接受,与之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但由姚所打开的“潘多拉匣子”一时却难以合上。姚想要控制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主观愿望未能奏效。8月24日,王德钟发表文章,分析唐宋诗在艺术上的异同,批评宋诗和清人学宋的弊病,认为陈三立完全不能与龚自珍相提并论。同日,姚光《南社通信》:“若论诗,则弟亦终斥陈、郑为枯寂而尚唐音也。夫有以人存文者,有以文存人者,陈、郑则两无可取。彼辈宗宋诗,则奉一宋人可矣,何视卑鄙之徒为神圣不可侵犯哉?识者有以知气类之相感也。”[21] 8月31日,郑千里认为:“今之阅时人诗至词旨肤浅者,辄曰此南社诗耳。此已成为流行语,其价值已可想见。此非社员尽无佳诗,乃选诗者之识力不足。此又一说也。”[22] 双方各以《民国日报》和《中华新报》为阵地展开激烈交锋。
10月2日,南社另一重要人物高吹万发表文章,批评柳亚子。高吹万《与蔡哲夫书》:“昨由石子寄来二片,知近以亚子事,致动贵处同人公愤,殊见公谊。亚子文才激宕,其对于南社亦具热心,惟有时傲慢自是,专尚意气。弟昔年曾以婉辞规之,彼非特不受,且辱骂之,弟由是深知其人。彼尝为人言,南社即亚子,亚子即南社。今日之肆然以主任名义驱逐朱、成,乃实行其昔之专横狂妄之意耳。朱、成二君,弟亦不相识。其论诗容有稍偏,要之亚子所论,尤属无当。矛盾之处,不可枚举。哓哓不休,徒见其陋。此间一二诗学具有根祗之人,如天梅、了公皆窃笑之。弟亦早有以窥其谬,然不欲牵人是非漩涡者,盖文章之事,得失心知,论定千秋,岂在口舌耶!尊处同人对于亚子妄举,至不承认其主任,确是!确是!惟选举将及不佞,则定有不克担任者,其理由若何,已详于复石子信中,当嘱转达左右矣。弟心中所欲举者,有黄晦闻,傅钝根二人,想为同社所公认。抑南社旧章,诗、文、词举三人分选,此章甚好,后为亚子破坏,今仍复之,俾得和衷共济,成一完全正大之东南文学渊薮,则幸甚。”[23] 高吹万是南社的核心人物,其言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之前的反柳言论均来自一些不太重要的南社成员,而此时高的表态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其观点也标志着南社核心层的分裂。本是源自于“宗唐/宗宋”诗学趣味的分歧却激起了层层波澜,最终导致了南社的解体。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站出来表态的高吹万也是宗宋的诗人。④ 再者,他提议来做南社领袖的黄节和傅钝根也都是宗宋派诗人。这表明在上述看似偶然和琐屑的诗歌旨趣之争的背后,是民初宋诗运动的巨大影响。柳亚子等人深恶痛绝并欲除之而后快的,也正是宋诗派的潜在威胁。站在台前的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王无为和不愿露面的高吹万、黄节、诸贞壮等宗宋派势力,充分说明了“宋诗”并没有在陈三立、郑孝胥这里成为绝学,随着一批年轻诗人相继加入宋诗派的队伍,声势浩大、绵延甚久的清代宋诗运动在民国初年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柳亚子等宗唐诗人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股力量。
之后虽有人还断断续续发表见解,已引不起人们太大的兴趣。
这场论争始于南社内部宗唐派主将柳亚子对宋诗派和其他学古诗派的贬斥。南社内部宋诗派追随者驳斥柳亚子而强调宋诗派的艺术成就,愈发激起柳亚子等宗唐派诗人的不满,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学论争。论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南社走向分裂,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而宋诗派经此打击,亦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恶名。柳亚子将宋诗派与满清遗老相提并论、斥之为妖孽的论断也长期左右着文学史书写。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胡适等白话诗倡导者的出现,新的诗学范式取代了传统范式,人们在新的文学标准下衡量宋诗派,声势浩大的清末民初宋诗运动就此淹没于文学史中。
作为士大夫精英文学的宋诗派,绵延有清一代,在20世纪初期依然有着较大影响。不仅昔日“诗界革命”的健将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后受到宋诗派的影响而日趋宗宋,和宋诗派人物互相唱和,以年轻诗人为主的南社同样有大批宋诗派的追随者。上述论争中提到的南社内部的宗宋诗人就有:黄节、林庚白、诸贞壮、姚鹓雏、胡先骕、刘季平、林亮奇、傅钝根等。南社著名领袖高燮(吹万)在1916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散原卓拔海藏雄,并世诗人数两公。”“白日放歌嗟老大,黄钟振响起疲癃。撑肠郁勃干宵上,敛手江湖变态中。赠与故人千遍诵,天涯襟抱问谁同。”(《以陈伯严、郑苏堪诗集赠马适斋,媵以一律》)表达了对宋诗派健将陈三立与郑孝胥的仰慕之情。宋诗派并未像柳亚子所希望的那样在民国的新生世界里销声匿迹,相反,倒是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著名诗人、词学家龙榆生谈到:“晚清诗坛,鲜不受陈、郑影响,俨然江西、福建二派;江西主山谷、宛陵;福建主后山、简斋、放翁诸家……。”[24]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真读过宋诗派的作品,他评价道:“在鲁迅之前时期承担文学之责的,当数以陈三立为顶峰的一群诗人”。[25] 也就是说,民国初年的诗坛上存在着两股重要力量:以柳亚子为领袖的南社和以陈三立、郑孝胥为代表的宋诗派,双反各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近代宋诗派是一个以创作来标明宗旨的流派,并没有多少互相的标榜与鼓吹。因此,柳亚子等南社成员向宗宋派诗人发难的背后,是民初诗坛依然笼罩于宋诗派的影响之下。论争折射出了柳亚子等文学新生势力的焦虑:宋诗派这个晚清最大的古典诗派为何在民初依然发挥着如此大的影响力?1945年的柳亚子回忆道:“辛亥革命总算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到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为诗坛的正统。”[26] 诗界革命并未打倒宋诗派,南社何尝打倒宋诗派?
南社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宗唐宗宋的矛盾,何以在1917年左右酿成规模浩大的一场论争呢?早在1909年的南社第一次雅集中,柳亚子就和庞檗子、蔡哲夫就唐宋诗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之后断断续续地,南社内部不断有人发表对于宗唐或宗宋的意见。这些争论都被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属于正常的文学观念的分歧。1917年的这场论争却掀起了层层波澜。
重新梳理这场论争,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等文学革命者的介入。1917年4月23日,柳亚子在致书杨杏佛时说:“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柳亚子所指,是《新青年》杂志1916年10月1日发表的胡适致陈独秀书信:“尝谓今日文学已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龛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27] 在胡适看来,宋诗派的水平要高于南社。胡适当时是留学美国的年轻学生,柳亚子想不到自己竟和宋诗派这些遗老被相提并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留学生眼中南社要逊色于宋诗派。“如樊樊山、沉伯严、郑苏龛之流,视南社为高矣”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年少气盛的柳亚子。同年7月6日,他再次提及胡适的话:“至其数当代作者,则亦曰郑、陈、樊、易而已。故仆尝诮为名为革命,实则随俗无特识。”直到20年后,在一封信中他再次提到:“然而,象胡适之博士论南社,以‘淫滥’两字一笔抹杀,反而推崇海藏(郑孝胥)之流,我自然也不大心服。”[28] 可见他对胡适的论断是耿耿于怀的,由此他也还以颜色,激烈抨击胡适。1917年,是中国诗歌转型的重要时期,持续已久的宋诗派、盛极而衰的南社、崭露头角的白话诗派在文学场域展开角逐。
值得玩味的是,宋诗派核心人物并未将这场争论放在眼里。1917年的《郑孝胥日记》中,可以见到两条关于南社的记载:“上海有南社者,以论诗不合,社长曰柳弃疾,字亚子,逐其友朱鹓雏。众皆不平,成舍我以书斥柳。又有王无为《与太素论诗》一书,言柳贬陈、郑之诗,乃不知诗也”[29];“南社社友登报,举高吹万者为社长;柳弃疾以逐朱玺、成舍我事被放。”[30] 沸沸扬扬的唐宋诗之争,在郑孝胥这里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且是以宋诗派的大获全胜而收场。柳亚子等人在郑孝胥这位诗坛宿将看来不值一驳。而在这则日记的前几天,他连篇累牍地记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的战况,此时的郑孝胥,关心的是天下大事,自不屑与后生晚辈一争长短。再者,“诗为余事”的观念也使得宋诗派诗人无意与人在口舌上争短长。作为传统诗学流派的宋诗派始终视诗为余事,“余事作诗人”的观念根深蒂固。近代宋诗派承继的是韩愈“多情杯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和黄庭坚“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答洪驹父书》)的传统。陈三立在谈到另一位宋诗派重要成员俞明震⑤ 时所言:“然而生世无所就,贼不得杀,瑰意畸行无足以显天壤,仅区区投命于治其所谓诗者,朝营暮索,敝精尽气,以是取给为养生送死之具。其生也藉之而为业,其死也附之而猎名,亦天下之之悲也”[31]。在陈三立看来,以诗为生命寄托的背后满是凄凉和无奈,“其生也藉之而为业,其死也附之而猎名”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南社则是一个以诗为宣传工具和革命武器的团体,十分强调诗的功利性,是一个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学团体,而宋诗派则是一个坚守传统壁垒的团体。两者在诗歌的性质、功用、审美品格上都存在着“代沟”。以承继传统、守先待后自居的宋诗派和以发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的南社自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在传统中求变,是近代宋诗派的突出特点。面对近世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身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空间,心存守先待后志向的宋诗派诗人们充满了忧虑,他们以诗为“写忧之具”(陈三立),在诗歌中传达内心的感伤。在艺术风格上,他们强调融化几千年优秀的诗歌传统(三元说、三关说),破除门户之见,展现诗人个性,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宋诗派诗人同样充满了艺术追求的真诚。近代宋诗派的艺术追求某种程度上启迪了五四以后新诗的思路。⑥
南社与晚清民国宋诗派的冲突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幕,超越以往的以“进步”的南社为主流的叙述视角,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窥见近代诗歌嬗变的复杂性。
注释:
①傅專(1884-1931):初名德巍,字声煥,后更名增湘,字君剑,号钝根。湖南醴陵人。光绪二十三年(1906)与同乡宁调元赴上海,共创《洞庭波》杂志,又办《竞业旬刊》,抨击清廷,鼓吹革命。次年返湘,任教中学。为南社早期成员。辛亥革命后,在湘主办《长沙日报》,兼执教师范学校。1916年任《长沙日报》主编。1920年后,任湖南省长署秘书,省议员。1924年,因与柳亚子所发起的新南社宗旨有异,另组“南社湘集”,任社长,主编《南社湘集》五期,均以五言为主。才富学赡,一生于新闻、教育、文学均声迹颇著,胡适、阳翰笙皆曾为其学生。
②诸宗元(1875-1932),字贞壮,别号大至居士,浙江绍兴人。曾与黄节、刘师培、邓实、陈去病等于上海设立国学保存会及藏书楼。南社成立,入社。1910年前后入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端澂幕,对南社社友的革命活动有所掩护。1923年浙江军务善后督办为卢永祥幕僚。1929年后供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生困顿于僚属之间,身后颇萧条。诗宗江西诗派,与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郑孝胥、沈瑜庆、李宣龚等均有交往。胡朴安《南社诗话》:“社员之诗,略有缙绅文学气味者二人,一潘兰史,一诸贞壮。”
③诗中提到的冯定远即冯舒是清初宗唐诗人,十分憎恶江西诗派,曾言:“江西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强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恼人,而曰孤高……山谷再起,我必远避,否则别寻生活,永不作有韵语耳。”(《钝吟杂录》卷四)
④1917年12月9日,高燮之侄高基发表诗话,指出高燮诗风受陈三立影响。高君定《致爽轩诗话》:“叔父吹万先生于古文学最深,所著《吹万楼文存》,兼有湘乡、柏枧之长,诗似甘亭,尤似梅村,近乃稍为伯严。有《吊庞蘖子即题其诗词遗稿》云:沈吟郁处笺愁地,历劫频年厌世人。自吐孤怀入绵邈,独携奇泪动凄辛。低回每觉情无尽,俯仰淮怜迹已陈。欲向灵岩问樵唱,残阳莽莽下城闉。其《散原精舍集》中语也。”)(《民国日报》,1917年12月9日)
⑤俞明震:1860-1918,号觚斋,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宣统二年(1910)署甘肃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寓杭州。他曾任南京矿务学堂总办,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在北京其间曾去拜访过他,俞去世时鲁迅送有挽联。
⑥杨扬:“新文学在批判宋诗运动局限性的同时,仍然接受了宋诗运动的观点、主张的影响。……宋诗派的观点、主张已经作为一种文学资源融入了中国文学传统之中,他是一种客观存在。”(《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本土化资源关系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庞中柱:“(晚清宋诗运动)不仅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了完善的总结,同时也为新文学运动兴起后,如何取法前贤,继承传统,作了良性的示范。”(《晚清宋诗运动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