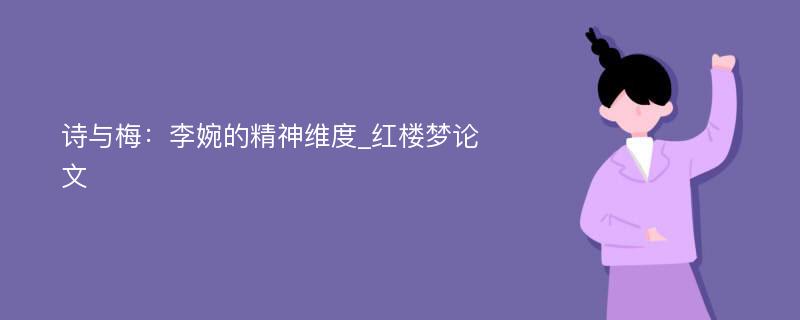
诗与梅:李纨的精神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李纨形象的两种论析
如果说凤姐、探春等人是被严重误读的红楼人物的话,那么,我以为李纨则是一个尚未被认识的红楼人物。概而言之,对她的评说大致有相反的两类,向两极伸延。较早的姑且不谈,仅列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论述如下:
1990年紫禁城出版社版《红楼梦诗词鉴赏词典》353页:李纨是个“禁欲主义的典型”,“一个节妇的典型”,“李纨的禁欲主义是以程朱理学的贞操观念为核心”(薛祥生、王少华撰稿)。
1991年三联书店版《红楼启示录》(王蒙著)23页:“槁木死灰式的李纨”。
1992年《红楼梦学刊》第一辑谭宇宏《女性传统价值的失落和裂变》:李纨“能做到古井无波”,“园外的李纨是一具活的遵守三从四德的标本”。
199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版《漫步大观园》(曾扬华著)163页:李纨是“真正符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要求的”样板,“李纨确象‘死灰槁木’一般,她的心完全死了。”
1993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张锦池《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凤姐和李纨……一个欲壑难填,一个心如槁木。”
199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红楼全咏》(张燮南著,周汝昌评)55页、92页评语:“她一生‘三从四德’”,“李纨评诗是旗帜鲜明维护封建妇德”。
1995年学林出版社版《红楼梦哲学精神》(梅新林著)207页:李纨“如死灰槁木一般”。
1995年东方出版社版《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李劼著)108页、231页:“李纨显示的是其精神和情感上的僵死……”,李纨“道德的吸毒导致身如槁木,心如死灰。”
1995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杜奋嘉《深埋于心理底层的情愫》:“她从小便形成了一套节操观念”,“恒定的心理趋向”,“对恶劣的环境她只好采取顺应的态度”。
1996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李希凡《金陵十二钗续论》:“李纨在大观园的生活,确是谨遵父训,身体力行,清心寡欲”。“她成了大观园中寡妇的‘标准户’”。
1996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四期章必功《红楼诗话》:“李纨论诗,依孔门诗教,主张温柔敦厚。”
以上著述可谓众口一词,是李纨论的主流派。谭宇宏、杜奋嘉二文虽有所分析,有些新意,但终究未能摆脱“槁木死灰”说,有些解构批评的倾向,解剖了不少现象,却没有触及最关键的问题。直到1997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刊出胡文炜的《李纨的命运和地位》一文(注:1995年12月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胡文炜论文集《贾宝玉与大观园》中收有此文。),才有了全褒李纨的观点。胡文首先指出:李纨是个“避免了悲剧结局”的“重要人物”,继而称:曹雪芹“充分肯定李纨的命运”是与“贾府里极大多数青年男女惑于情、误于情”根本不同的。作者反复申述:“李纨始终以理自守”,“与‘情’毫无关系”,因而其命运与贾宝玉、林黛玉、司棋等众人不同,得以“‘善终’于荣华富贵”。
二、上述两种论析的由来
上述两种论析,从根本方面看,都是和李纨的形象相距很远的,远离《红楼梦》本文的。
具体一点说,大致不外两种情况:
(一)以偏概全,以“想当然”代替具体的全面的分析。
在120回书,李纨在70多回中出现了180多次。在这70多回书中,小说家最着力谋构的李纨的故事在哪里?最倾注心血的最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在哪里?李纨的性格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有何发展变化?这些是研究者必须认真地深入地加以考察的。但是,上文提到的论者却大都没有这样做,大多只是把小说家在第四回开始时对李纨的家世出身的概略的介绍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立论依据;实际上,仅仅抓住了那段简介中的四个字“槁木死灰”,加以一般性的形式逻辑的推衍,再参照一点宋元以降寡妇们的一般的遭遇加以比附,而没有“顾及全人”“知人论世”(鲁迅语)。这样来写李纨论,李纨自然就成了“槁木死灰”。因为是“槁木死灰”,自然也可以说她是“死水枯木”,说她的“心完全死了”;再进一步,自然就可以说她“是以程朱理学的贞操观念为核心”的“典型的寡妇”了。有些论者则是从其家世出身进行推导的:因为她父亲是个封建知识分子,是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李纨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当然就不得不顺应这种名教纲常的准则,恪守妇道”,“从小便形成了一套节操观念”,当然也就“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心理积淀”,而且是“无法超越”的。由家庭出身决定论一路推导过来,内证的材料则是没有的。小说家的几句真真假假的议论,是不能作为评论小说人物的依据。否则,贾宝玉岂不成了草包、祸胎,王夫人岂不成了慈厚善人,贾政岂不成了品格端方的严父。
(二)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前人的论述出发,是认同性的演绎,而不是开拓性的研究,有不少观点仅仅是重复前人的话。
谨录前辈对李纨的两段论述如下:
王昆仑:李纨“在太太奶奶中能古井无波,杜绝尘垢”,“她秉承着自己父家的家训和适应着贾府的环境,要有意识地做一个标准寡妇。”(注:《红楼梦人物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页。)
李希凡、蓝翎:“李纨的生活是枯死了的,毫无生气……痛苦的积累变成了感情的麻木,只是以生物的意义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而灵魂却被吃人的礼教观念禁锢在僵死的躯壳里。”(注:《新建设》1955年四月号,后收入《红楼梦评论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27页。)
姑且不论几十年前的这些论述本身如何,只将上文所引的文字和这些论述对照一下,便会发现:几十年前的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重复着。是不约而同吗?就算是吧,但与几十年前并不确当的观点不约而同,又说明了什么呢?恐怕只能说有些研究者是裹足不前的,学风是浮躁的。新时期以来,文艺科学在迅速发展,思想在不断解放,红学研究也在深化,我们是站在前人构建的人梯上攀登新高峰呢,还是在前人的摊前拣点旧货搞个拼盘呢?是另辟蹊径,进入新领域呢,还是围着前人的旧著兜圈子呢?问题的要害恐怕就在这里。
胡文炜一文则两者兼而有之。他援引了甲戌本第四回开头的两条脂批:“妙,盖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为情所陷哉!”“此时此处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实罕见者。”胡文未加分析,即以其为圭臬,一再强调是曹雪芹“让与众不同的李纨出于‘守理’之家,让李纨始终以理自守”,从而“避免了悲惨的结局”。不但李纨“能以理自守,不萌情心”,终于得以享尽荣华富贵而终,而且认为:“李纫跟大观园中其他人不同的命运结局,充分体现了《红楼梦》这部书的创作思想。”这个“创作思想”是什么呢?作者说:是“警戒世人不要妄动‘风月之情’,试看《红楼梦》里结局可悲的人,大都与‘情’有关,从贾宝玉、林黛玉……金钏、司棋等无不如此。”曹雪芹写李纨就是为了与贾宝玉、林黛玉等少男少女们作对比,“特地写了她不动情的一面”,“从正面导引世人不要妄动风月之情。”这无异于说曹雪芹是个“以理自守”的作家,他让李纨“在《红楼梦》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展示了她的善和美”,从而展示“作者的憎爱态度和思想倾向”。把李纨以及通过李纨而完成的《红楼梦》的教化作用和警世意义发挥到如此地步,实属罕见。这样,《红楼梦》岂不成了十足的宋明理学教材!此其一。其二,他做了十二钗判词的文章,主要是对李纨判词的后两句作了特有的解释。众所周知,小说的实际情节已和判词所透露的小说家的最初构思大不相同,有些重要情节已完全改变(不只后四十回)。这种变化的最大可能是:小说家在塑造李纨形象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了“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的原则(第1回)。他没有按自己原来的构思来左右李纨,而是按李纨性格发展的主客观依据和内在逻辑超越自我,推倒了当初的设计,让李纨走自己的路。我们在评论李纨的时候,是按判词中透露的原始设计去作揣测做结论呢,还是按小说实有的情节来分析呢?是起初的设想还是实有的文本更能体现李纨的真实性格呢?答案是显然的。
三、我的李纨观
我的李纨观如下,谨以此与各位李纨论者会文。
在《红楼梦》中,李纨不是重要人物,但并非没有典型意义和评论价值的人物,她被列于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是贾府四大少妇之一,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向度,人们研讨她,是有其美学依据的。
李纨的生存环境是极恶劣的:她生于宋明理学最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女子已极难做人;其父是笃信理学的迂儒,婆家是没落贵族,婚后不久丈夫又死了,她陷入最可悲的人生境地。自然,这只是李纨人生处境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必须看到的,那就是自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已受到猛然抨击,李贽、归有光、张岱等人都已提出了反对卑视、压迫妇女的某些进步思想。至明末清初,民主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学生郑梁更提出了“男女皆人也”这一重大命题,指出:男女不平等,“此固天地间不平之甚也!”(注:郑梁:《寒村诗文选·文选·翏友张氏诗稿序》。)中国历史进入了“夷之初旦,明而末融”(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题辞》,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的大转型前夕。从小环境看,李纨已有一子,又与一群小姐妹生活在一起,这又使她有了一些精神依托,而未象李清照那样陷入孤寂凄凉的绝境。
以往,对李纨生存环境的分析是有片面性的,有的滑到绝对化的边缘。“古井无波”之类论断即由此而来。
十分清楚,小说家是将李纨的故事分为三大段来写的:进大观园前——进大观园后——迁出大观园后。这是李纨性格发展史的三大里程碑。其中,以园内生活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共有54回135次写到李纨,占李纨出场数三分之二以上。李纨性格的主导方面,主要是通过其园内生活展现的。进园前,有10回书20来处写到李纨,只是对其起始阶段的生存状况作简略介绍,基本上没有正面描写,在整个故事中,其意义主要在结构方面,是对后两阶段性格发展、变化的铺垫,用的是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其本身并无重要意义。
若以“古井”为喻,李纨的娘家和婆家均是“古井”。李纨是被宋明理学推入古井的,但是李纨的心并没有变成古井,她的精神并没有僵死。父训是十足理学的,但是有何根据说李纨是“恪守”它的呢?贾府的“规矩”的确很大(注:《红楼梦》六十五回兴儿对尤二姐等人说:“……我们家的规矩又大,寡妇奶奶不管事,只宜清静守节。”),但是,有何材料证明李纨对它只有“顺应”,并已形成了“恒定的心理趋向”呢?小说中什么地方描写了她遵从家长之命,专心陪侍小姑工于针黹纺织之事呢?都没有。
庄子说:“形固有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注:《庄子·齐物论》。)封建纲常名教可以把李纨推入“古井”,但是,在“古井”中李纨却保持了一颗鲜活的心。有了这颗心,她的青春之火就有复燃的可能。
大观园是曹雪芹的天才创造,是其理想主义的结晶。
大观园是女儿们的精神家园。
在那“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好季节里,贾府的女儿们离开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的荒谬乱世,进入了理想的生活境界。
由于封建家长们完全错误的认识和任用,李纨也和少女们一起进入了大观园。对于李纨这是改天换地。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过,她还有可能离开贾府的高墙深院!离开了那“牢坑”(龄官对贾府的概括语),就意味着她被意外地从“古井”中释放出来,并且意外地和封建贵族之家的逆子叛女们一起进入了“世外仙源”(林黛玉题大观匾额)。这对于李纨的心灵震撼,恐怕是远甚于宝黛等人的。小说家正以此为起点,开始正面地具体地揭示李纨的精神世界,真正开始抒写李纨的性格发展史。
进园之后的李纨积极主动地适应了这一全新的生活环境,她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前后判若两人。她点燃了自己心房中封闭多年的青春之火,虽然并非熊熊烈焰,但却洋溢着鲜明的青春的光和热,显示了一个少妇的生命的活力、生命的美丽。她是那么大胆而又谨慎地利用了封建家长们给予她的合法身分,积极地参加、有效地支持、掩护了一个又一个严重违反封建礼法的活动,几番领着妹妹们大闹大观园。她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为少男少女们营造往日难以想象的宽松、自由、开放的生活天地。与此同时,她也热忱地寻求、开拓了自己的新的生活空间、精神空间。虽然这一切开创性活动完全是按照她的个性、修养、气质进行的,但其心路历程是十分鲜明的。进园不久,她就进入了性格发展的第一高峰:参与创建大观园诗社。
不说李纨是创立大观园诗社的第一人,至少也应该说她是最早产生这一想法的人。探春提出创办诗社是八月,而李纨说:“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她们是二月二十二日进园的。这就是说,一入大观园,李纨就萌发了这一创造性思想。所以,一经探春提议,她便立刻赶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说:“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掌坛!”并自荐以自己的稻香村作为诗社社址。其支持诗社的真诚和热烈程度,可以说一下子便达到了顶点。从以后诗社有关的多项事宜到以后诗社的多次活动中,均可看出对于创办诗社,李纨是十分自觉的,是全身心地投入诗社事业中来的,并且往往达到忘我的程度。
我们仿佛看到,李纨正以崭新的风姿向我们大步走来。
李纨为什么会如此热忱呢?这是由诗社的重要性决定的。
贾宝玉对此举的第一反应是:“早该起个社!”他阐发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他要求大家鼓舞起来,群策群力。叔嫂二人,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心总是相通的。接着,黛玉提出:既入诗社,便不要再用姐妹叔嫂这些俗称。又是李纨首先热烈表态:“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并且,她第一个为自己起了号,还热心地为别人起号。其后,诗社的分工、社约的建立等等,几乎都是由她提出的,甚至第一社的诗题:即景咏白海棠,也是她提出的。在诗社中,她多么活跃,多么朝气蓬勃,多么富有开创精神!至此,怎么还能把“槁木死灰”、“惟知侍亲养子”、余事“一概无见无闻”和李纨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呢?
在她的支持和带动下,所有诗社成员无不兴会无前,诗情澎湃。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那位自觉而真诚地恪守封建道德纲常和女儿“本分”的薛宝钗,也被卷入了这股诗潮。诗社的“寄兴寓情”的写作宗旨,就出自这位封建淑女之口。王蒙曾认为:大观园诗歌创作,“反映了这些公子小姐们生活的空虚和烦恼”,“活着无所事事。”(注: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134页。)事实似乎恰恰相反,大观园的诗歌创作,不但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而且是反映了这些诗人们的新的精神向度的,是他们主动向封闭、塞息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的纲常名教发起的挑战;他们的结社吟诗,也是当时女性先觉者开始结社酬唱活动的典型反映。如果按照封建家长们的指示,李纨只带着小姐妹们“学规矩、针线”,念念《女四书》之类,那才是“空虚和烦闷”呢,而建社写诗正显示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向。对于李纨,其走出“古井”,青春之火复燃的意义是尤为显豁的。
写了诗,就要评诗。评诗,是曹雪芹塑造这个诗社社长的青春形象的又一精彩之笔。且看首次评诗:
对于诗情勃发一挥而就的潇湘之作,众人不禁叫好:“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都道当以这首为上”。但李纨却没有随大流,她自有评论:“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此评确实不同凡响,意义深远,所以敏探春首先拥护。当怡红公子提出商榷意见时,李纨不容分说,道:都听我的,“再多说者必罚!”
我们怎能不为之叫绝:这才是李社长之评!
作为社长,李纨对于第一次诗会是必须予以全方位地考虑、谨慎安排的。这一次诗会对于诗社的发展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社长,她必须让诗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使诗人们的热情能得以保持、发扬。而关键的人物显然不是宝、黛、探等,而是宝钗。评定钗为第一,应当说是最有思想最正确的评论。黛玉虽屈居第二,但在这个诗意横溢的场合中,这位极富诗人气质的少女,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在诗的海洋中去了,对于名次问题,她是并不在意的(以后的历次诗会中一贯如此)。何况她已得到众人的高度赞许,她的自尊心已完全得到满足,李纨对她和蘅稿的评语又是极为确切的,所以她是绝不致于耍小心眼儿的。而宝钗则不但没有得到众人热烈的喝彩,而且成了宝玉“商榷”的对象,如果李社长处理不当,宝钗一旦返回固有的心路上去,那是很可能给诗社带来消极影响的。李纨如此一评,她的目的便达到了:宝钗的积极参与心理保持住了,她不但为憨湘云设计出最佳的做东方案,还发表了一篇颇为通达的诗论。可以说,在大观园诗论中,她的那番论述是不失为上乘诗论之一的(但同时,她又贬低了女性诗歌创作的价值,她并没有忘记她的女儿“本分论”。可见她的心虽然一时被大家的诗情热浪激活了,随着姐妹们一起涌进了诗的浪潮,但其立足点并未改变)。湘云说要作菊花诗,她热心地为之策划,又提出了“只出题,不限韵”,不限数量,人人能作,不作亦可的灵活主张。这些,显然都是开明而积极的。这颗复苏起来的少女的诗心,在李纨和众人的护持和影响下,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直到林黛玉在酒令中接连说出《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唱词时她才“清醒”起来,拷问了黛玉;到薛宝琴新编怀古诗中再次出现《西厢记》、《牡丹亭》的内容时,她才警觉起来,再也不愿继续“同流合污”,于是开始发难,进而设置障碍,提出她要作东邀一社:既限题又限韵还限数,不但用韵要求甚严,而且要咏《太极图》,与前所论完全相反。诚如宝琴所说:“可知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这分明是难人!”
通过评诗,小说家深沉地展现了李纨的思想性格之丰厚内蕴。当宝钗对宝琴的两首怀古诗公然发难要求抹掉时,黛玉忙拦住,尖锐批评她“芯胶柱鼓瑟,矫揉造作”,探春也立刻表态支持黛玉。论争相当尖锐地展开了,趋向表面化了。在这种情势之下,李纨又一次表现出社长之才能:她没有让黛玉引发的火药味进一步增浓,适时出面,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平缓态度发表了长篇议论:纵论文史,品藻人物,连“关圣帝”的虚伪老底都被她不紧不慢地兜了出来。十首怀古诗的写作和论争表明:大观园的诗歌活动已不再是与当时社会和时代不相关涉的游戏,宝琴如同一支亮丽的华尔兹在大观园中奏响了,她使园里的人们知道: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她们动心了,诗社空前兴旺了。连神圣化的关夫子的画皮都敢于去扯,其历史的厚重度岂可忽视?对关夫子都可以说长道短了,何况乎《西厢记》、《牡丹亭》?自然,李纨并没有简单化,她不但有论据,有论证,而且滴水不漏,不留把柄;最终的结论也是平实而有力的:“这竟无妨,只管留着。”宝钗无可反驳,只得作罢。这场文艺思想的冲突,经李纨的处理,既分清了是非,又没有导致矛盾的表面化,可以说结局是理想的。至此,我们已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位年青寡妇,她相当充分地体现了长嫂兼社长的那种非权力权威的风范。贾宝玉说她:“是不善作(诗),却善看,又最公道。”确是知人的评。章必功说:“李纨论诗,依孔门诗教,主张温柔敦厚。”我认为章先生是论错了。单就咏海棠而言,此说或许尚可通过,但是对咏菊诗呢?对怀古诗呢?虽然李纨仍不失其长嫂之厚道,但与“孔门诗教”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是无法得出“李纨评诗是旗帜鲜明维护封建妇德”之类结论来的。恰恰相反,从评诗中,我们发现李纨是一个知识相当广博、内蕴相当丰富的少妇,是一个相当有社会活动潜在能量的女子。通过评诗,李纨的性格丰富起来了。
诗社建成了,为了使诗社巩固、发展,除了增强内部凝聚力之外,是绕不过经费这一重要问题的。于是曹雪芹又安排了一场李纨智斗内务总理王熙凤的好戏,将进园后李纨性格的发展引向第二个高峰。
向凤姐要资助,开始是探春出面的,凤姐采取了推与躲的手法,于是李纨出马。李纨一出马,凤姐便改变了手法:以攻为守,气势咄咄逼人。李纨则毫不示弱,立即大举反攻,势若暴风骤雨,唇枪舌剑,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什么“无赖泥腿市侩”、“诗书大官名门”、“下作贫嘴恶舌”这类短平快的特殊句式都用上了,什么“黄汤灌狗肚”、“狗长尾巴尖”之类语言都倾泻而出,而且新账老账一起抖了出来,立刻形成一种英雄与英雄交手、强女人与强女人对话的阵势。结果,向来以“辣”出名的王熙凤当众甘拜下风,连声叫着“好嫂子”,装小讨宠,只有求饶之力,没有招架之功。李纨却毫不心慈手软,而是步步紧逼:“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把凤辣子直逼到南墙上。但王熙凤毕竟是王熙凤,她竟能绝处求生,作出了最漂亮的反应:“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赞助多少、何时交钱,说得一清二楚。于是众人大笑。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原来纨凤都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人们既欣赏凤姐的绝顶聪明、狡黠,又欣赏李纨的柔中有刚,刚时直如狮子搏兔,雄风飚起,势不可挡。李纨性格中显现出了奇光异彩。
读者是否会感到李纨的这股雄风难以置信呢?看来不会。因为入园之后,李纨已多次偶露峥嵘,小试芒锋。就是说,小说家在此之前已为她的性格的这一侧面作了多次铺垫。比如,第97回凤姐在稻香村夸谈小红时,李纨就曾笑称凤姐是“泼辣货”(亦作“破落户”)。第39回螃蟹宴中,凤姐派平儿来取螃蟹,李纨偏不让平儿回去,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第42回黛玉故意向她发难:“叫你带着我们作针线,教道理呢,你反招我们大玩大笑的!”李纨当即伶牙俐齿地回敬她一通,使这位素以嘴巴尖刻的林姑娘脸红语塞,败下阵来。这就是说,李纨的这些行为都是有其必然性和可然性的。
更令人赞叹的是,曹雪芹还发掘了李纨性格中另一种奇光异彩: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激活了李纨不可抑制的创造活力、人生价值追求和青春生命力的荡漾。这集中在第49-50回中。曹雪芹大笔淋漓地描绘了雪中赏梅、诗兴勃发的场景,以此作为李纨和少女诗人们的中心意象。在展现这一中心意象前,我们注意到,小说家早已为此蓄势了。其显著者为稻香村的红杏。关于稻香村,贾宝玉已有令人信服的论断:稻香村是个违背天然之理、天然之趣的拙劣的人工造作。它的象征意义是:杀伐人性的宋明理学把青年寡妇李纨从“古井”推向枯寂的竹篱茅舍。然而,在那黄泥墙院中却“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这和稻香村多么不协调啊!而这种不协调正好构成一个极为奇妙的意象:“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注:宋诗人叶绍翁:《游小园不值》。)而这枝关不住的红杏,就是稻香村的女主人李纨!
蓄势已足,于是小说家安排了一场芦雪庵即景联诗。这次赛诗会,不啻是一曲最美丽最欢快动人的青春圆舞曲。有雪无梅不精神,有梅无诗俗了人,在芦雪庵三者连翩而至: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即景联诗;雪和梅融为一体,以梅为中心,构成诗的意境。
除了诗人们在诗中以火一样的热情咏雪咏梅之外,在故事中又多次用如诗如画的语言描绘了梅和雪:李纨一见下雪即起诗兴,提议到芦雪庵赏雪联句;宝玉踏雪赶往芦雪庵时,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的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宝玉从妙玉那里乞得一枝红梅,纵横而出,摇曳多姿,“花吐胭脂,香欺兰蕙”,老太太一见便赞道:“好俊梅花!”宝琴站在雪山坡上,身后有一瓶红梅,老太太以为这画面比仇英的《艳雪图》更美……把雪中红梅写到了绝处,令人心向往之。而最令人玩味不已的则是宝玉在联句中再次落第后,李纨竟罚他去栊翠庵乞红梅。这一罚当即引起众人兴趣,都道:“这罚得又雅又有趣。”
其趣何在?
其主要意蕴在于:它最充分地反映了李纨那雪中红梅一般的内心世界。它再一次无可辨驳地证明:李纨的内心,绝非“古井无波”,而是强烈地涌动着一股少妇的心潮,“其精神和情感”绝未“僵死”。她不但有性意识,而且主动大胆地表现了性意识。她采取的是东方式的可以意会不可语达的诗一般空灵的方式。这是李纨式的“意淫”。怎么能说她“与情毫不相干”“不动风月”之情呢?在她的内心深处,爱情之火正旺,只不过她是以她特有的方式渲泄它,使自己从中得到爱情饥渴的某种补偿而已。由己及人,对妙玉她是理解的、同情的(虽然她对她有独特的个人看法);对宝玉也是理解的,她采取了调侃和戏谑的微妙态度对待了他。她对正处于恋爱季节的少男少女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当她命人跟宝玉去栊翠庵时,黛玉忙拦道:“不必,有人反不得了。”李纨立刻意会,点头说:“是。”在这中间,她如此会意地分享了少男少女们的爱的欢乐。在这里,李纨内心活动的美妙和幽远,恐怕并不亚于妙玉和黛玉。在这里她显得多么幽默,潇洒,开放!这样一个女子,怎么会成为寡妇主义的典型呢?
那么,李纨是否会走得太远,以至滑出正道呢?我认为,曹雪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纨是一个有相当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成熟女性,她总是把自己的行为调控在确当的范围之内和形式之中的。寿怡红的狂欢之夜(63回)便是明证:由于家长不在府中,众少女们便蒙住管家婆,借宝玉生日之机在怡红院大开酒宴,夜以继日,开怀畅饮,猜拳行令,唱曲掣签,红飞翠舞,玉动珠摇,成为大观园中空前绝后的一次青年联欢会,将其视作青年们要求自由、平等、解放的实践性演习,大概是不会过分的。就是说,在狂欢的形式下面,是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内容的。李纨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她当然十分明白:背着管家婆,年青的寡嫂跑到小叔子的院子里去饮酒作乐,从封建传统观念和宋明理学的立场上看,其性质多么严重;而且,她又是带着上上下下一群少女一起参与狂欢的,其性质的严重程度,更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李纨却毫未推托地应邀参与了。一方面,她和少女少男们一起欢乐,很活跃、很尽兴;另一方面,她也起了她应起的引导作用。宴席上,黛玉故意向其发难说:“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李纨笑着回答了她:“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表态显然是很积极又很稳健的。她首先表明此事无妨,大家只管尽情地玩乐。这是基本态度。但她又表明,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有节制地在适当时节举行的,如果是这样就不用怕什么了。在这样一位长嫂的这样周详的指导之下,活动自然会顺利稳妥地进行而不至有大失误的。结果果然如此,所有参加者既皆大欢喜又十分安全。
在这个活动中,小说家还安排一处点睛之笔:抽花签。在抽花签中,李纨掣出的花签上画着一枝老梅,写着“霜晓寒姿”四字。对于此签,李纨十分喜欢,一看便笑道:“好极!你们瞧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她是以梅自况的,她是一枝老梅,始终处于霜雪苦寒环境之中,这在它身上是留下了独特的生活烙印的。但是它甘心充当这报春之花,它将引来百花齐放的大好春色。这样,就明确点出了梅花是李纨的中心意象。
李纨性格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是在迁出大观园之后。
群芳开夜宴之后,大观园事端日繁,贾府更大故迭起,特别是抄检大观园之后,少女们风流云散,玉殒香消,诗社也陷于停歇。于是,这个女儿乐园日益沦为荒园。作为姐妹们的领班,李纨承受的有形无形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主客观形势迫使她不得不迁出大观园。
迁出大观园,就是失去理想的生活境界,就等于复归“古井”。其意象性是显而易见的:女子尚无法走出历史的宿命,她们的解放还要经过可怕的反复、曲折的历程。认为李纨的命运完全不同于其他少女少妇,“她完全避免了悲惨的结局”,甚至是“善终于荣华富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臆语。后四十回对李纨的描写虽然屡见弱笔拙笔,但是,小说家并未改变李纨的悲剧性质。虽然入园之后,她曾点燃自己的青春之火,但历史决定了她是不可能长住这理想园的。一旦失乐园,她那青春之火就必将重归于凄风苦雨之中。
但是,李纨毕竟在理想国中生活了那么一段时间,青春的生命火种既然已复燃,她是不会让它熄灭的。如果我们把进园前和出园后的李纨作一番具体比较,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出园后,李纨在11回书中出现过25次。不但比入园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而且往往是主动参与那些份外之事的,在不少举足轻重的活动中她都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贾府被抄,众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凤姐也吓得栽倒昏死过去了,但李纨却并未失态,而在再三宽慰老太太;老太太对这种面临大事有静气的气度是很赏识的:“倒是珠儿媳妇还好,她有的时候是这么着,没的时候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地过日子,倒难为她!”对于贾兰,她并没有为了给自己争得一份凤冠霞帔而象贾政那样死逼儿子读书应试。贾兰晚上要补习功课,她还劝他“歇歇”。那真挚的母爱,使人为之心头一亮。宝玉“打出樊笼第一关”时有三别:一别母亲,二别大嫂,三别“宝姐姐”(直至此时,他只认宝钗作姐姐,而不承认她是妻子或情人)。这时,宝玉已完全进入狂人和哲人境界,王夫人、宝钗面对他的“疯傻”都陷入困惑和涕泪之中,而李纨却无惊无泪,表现出难得的平静和清醒。令人瞩目的是:老太太去世后,凤姐失恃,陷入困境,上上下下,事事处处与之作难,但李纨在这种情势下却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小说中这样写道:“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她“可怜”她同情她帮助她,不但吩咐身边的人不要学那些小人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而且要她们主动出力帮凤姐一把。这里,再次显现了红楼脂粉英雄们惺惺相惜的品格。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她自始至终全心全意地为悲剧女主人公林黛玉“送行”。当“苦绛珠魂归离恨天”时,正是“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之时,小说家让喜事丧事同时办理,不管人们作怎样的分析,这一妙构的巨大悲剧意义和价值,是无法抹杀的。主持喜事的有一大群家长,主办丧事的主要只有李纨。但是孰为丧?孰为喜?那些操办喜事的人无不陷于尬尴之中,她们都参与了骗局,都不得不为这场喜事可能产生的悲剧结果而提心吊胆,因而整个喜事不得不处处设防,人人都是愚蠢的虚弱的卑怯的。而丧事的主持人李纨则不然,自听到黛玉病危的消息起,便怀着挚情,悉心为之料理了一切。正当黛玉即将永诀人世时,主办喜事的人们却派来大管家婆到潇湘馆,要带紫鹃去参与那个骗局。紫鹃愤然拒绝,李纨也明确表明:紫鹃离不开。管家婆于是悻悻地说:“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面对这种威胁,李纨没有退缩,而是愤怒了,她说:“是了!你这么大年纪,连这么点小事还不耽呢!”李纨的潜台词就是:“天大的事儿我承担!”这种把大事看小,敢于当机立断,敢于自作主张的气魄,不正是一种智勇的体现吗?李纨的这种智勇,不是颇能启发人们想到古代那些敢于刑场抚尸,大恸叛徒的大勇者吗?虽然表象上李纨没有那么激昂慷慨,大哭大骂,依然是按她的个性和气质行事的,但是那种气度中所包含的力量,不是比大哭大骂更为震撼人心、令人肃然起敬吗?而为了强化这种勇智者的精神境界,小说家把死者和送行者一起加以诗化:“大家痛哭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这不啻是一曲响彻千古的安魂绝唱。在如此良辰美景之中,一曲仙乐迎去了一个少女的灵魂。小说中多次点出:这是仙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它是为黛玉的精神涅槃而奏响的,它是为死者的灵魂升入仙境而奏响的;而送行者正翘首星空,目送黛玉飘然飞升,她分享了这尘世俗人难以享受到的仙乐,她的精神也随之而上升了。
至此,我们仿佛才真正看清了李纨的全貌。
对于这个始终生活于封建时代没落贵族家庭中的女子身上的历史的、阶级的、传统文化的种种局限性,我们和当今的广大读者一样,是清楚的看到了的,我们不拟费言论证它。
标签:红楼梦论文; 大观园论文; 曹雪芹论文; 李纨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红楼梦学刊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西厢记论文; 牡丹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