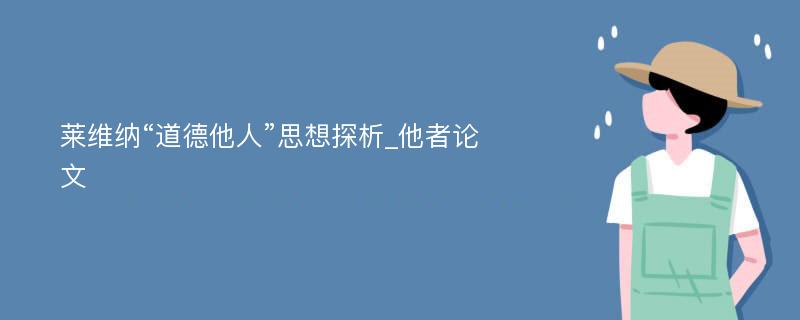
列维纳斯的“道德他者”思想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斯论文,道德论文,思想论文,列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裔法籍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①著述中的“他者”思想非常丰富。1948年出版的《时间与他者》一书是迄今为止少有的关于他者的理论专著。②在列维纳斯的著述中,对他者理论的阐释与道德哲学的内涵紧密相连。这一点,可以借助其在《生存与生存者》(1946年)[1]、《塔木德四讲》(1963年)中所论述的“面向他人”的问题③,在《上帝·死亡和时间》(1975年)中所论述的“他人之死与我之死”的问题[2](P12-19),还有在1984年所论述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道德”[3](P75-87)等问题,而得以进一步的认识。
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无论是逻辑起点还是理论目标,抑或价值立场,都指向道德。如果结合主体的自我反思以及主体超越自身的理论观念来说,该理论可谓从主体之“为道德”的角度,超越了主体独语的局限,深化了对话主义的主体内涵,在一定意义上还显示了主体自我反思的深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列维纳斯借助于道德他者理论的阐释,切入到对生存以及生存者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而且把伦理道德带向了“第一哲学”的理论境界。基于此,本文将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他者称为“道德他者”。
那么,列维纳斯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否定自我与他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又是如何阐释道德他者的理论内涵的呢?本文从列维纳斯对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之“我—你”关系的理论解读、对生存与死亡问题的现实思考,以及对主体同一性问题的逻辑延伸等三个层面,具体阐释列维纳斯道德他者的理论内涵。
一、对马丁·布伯哲学的理论解读
马丁·布伯有关原初词“我—你”关系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主体反思的深入,即主体的思维由原来的主体本位走向关系本位。然而,布伯的上述观念,在列维纳斯的理论视野下,不仅具有主体反思之深入的理论内涵,而且还具有道德他者的理论要素。
(一)相遇是一种责任
在《马丁·布伯与知识理论》一文中,列维纳斯说道:“‘我—你’关系拓展了自性的疆域,尽管布伯从未对‘我’进行过区分和限定……‘我—你’关系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本体论的,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本质联系。……‘我—你’关系是一种真知的关系,因为它保持了‘你’之他者的整体性,而不是对匿名之‘它’而提出‘你’。”[4](P64、66)在列维纳斯看来,布伯的“我—你”关系开拓了主体性的疆域,即将自性的范围由单纯的主体独语拓展成双向的对话交流。④这一点可谓显示了主体反思的理论成果,这是其一;其二,他将布伯的“我—你”关系中的“你之国度”⑤描述为一种包容了“你”的他者状态,即作为他者的“你”并不以“我”之存在为转移,“你”的存在状态是与“我”相面对的。换句话说,“我—你”关系代表的是“我”与他者的面对。
列维纳斯认为,“思索‘你’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之实存,依赖于对我称述的‘人言’。同时,还必须强调,对另一存在担负起责任,则能进入到与之对话。责任,从术语的词源学意义来讲,它不仅仅是言语的交流,它还有‘对话’的含义,它仅仅是前述例证意义上的相遇。”[5](P66-67)在笔者看来,列维纳斯对布伯的解读,不仅继承了布伯的“我”与他者的面对,而且还将“我—你”关系拓展到“面对”之实现方式的语言表述的层面上,而这一点,为列维纳斯从布伯的“我—你”关系的论述中引出道德问题,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二)允诺是一种真理的实现方式
列维纳斯说:“真理并不是那些对现实进行思考、且毫不动情的主体所能把握的东西,而是借助于允诺的方式才能把握的东西。在允诺中,他者保持在主体的他性中……对于布伯而言,允诺就是接近他性,因为,只有他性才能探出责任的行为。布伯试图在‘你’的关系中维持‘你’之本质的他者,而‘我’不是误将客体视为‘你’,也不是欣喜若狂地将自身认同为‘你’,因为‘你’一直保持独立,尽管我们进入了与之的关系。”[6](P67)在这里,列维纳斯进一步将真理也纳入了主体间的关系范围,即他把真理的实现方式,视为“我—你”关系基础上的“允诺”。而这种关系型的“允诺”,为主体接近他者提供了条件或可能。列维纳斯说:“允诺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关系。真理并不是由对上述允诺的反映而构成,而是其本身就是允诺……知识通过允诺而与存在契合。为了知晓痛苦,心灵必须将自身投入到对痛苦的深层体验中去,而不是像思辨者那样进行沉思;同样,一切灵魂的事件会同于神秘而不是思辨……但是,痛苦有着一种特权的地位,它预设了一种与存在的契合。对于痛苦,布伯要求有着一种不同的关系,基本上的对话关系,与‘世界中的痛苦’进行沟通交流的关系。”[7](P67)在这里,列维纳斯所言的真理的“允诺”,它造就的是与存在的相遇或契合,而灵魂借助于痛苦所实现的与存在的相遇或契合,与真理借助于“允诺”所实现的与他者的相遇或契合,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见,通过考察真理的“允诺”问题,列维纳斯链接了真理与道德的相遇或契合,而这一点,为他进一步阐释道德他者的内涵提供了前提。
(三)责任感是相遇他者的前提
那么,作为主体的“我”,在列维纳斯那里是如何与他者相遇而实现道德内涵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维纳斯引入了“责任感”、“内括性”、“忘却”等概念。他说:“对话或者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借助于责任感而被暗示为互惠互利的,对话的最终本质表现为布伯所谓的内括性,它是布伯哲学的一种最基本的概念。在‘我—你’关系中,互惠互利能直接地被体验到,且不仅仅是处于‘我’与‘你’的关系之中,它借助于‘你’而与自身更进一步关联,如同‘我’同反过来关联‘我’的那些人相关联一样,即通过‘你’之外表而与自身紧密关联。因此,通过‘你’的方式,它返回自身。这种关系应该与心理现象学的Einfühlung(内括性)区别开来。在心理现象学的内括性之中,主体完全将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由此而忘却自身。”[8](P67-68)在这里,列维纳斯主要阐述了主体与他者相遇的作用机制。在他看来,责任感对于实现“我—你”关系基础上的道德内涵,不可或缺,因为对话状态下的“我—你”关系,是一种责任感作用下的彼此都能体会到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它不是心理现象学中的自我忘却的心理效果,而是一种与他者相遇或与存在契合的原初关系。
总之,列维纳斯在阐释布伯的“我—你”关系中,不仅发现了他者的成分,而且还在对他者的分析中,找到了蕴藏在他者背后的道德根源。
二、对生存与死亡问题的现实沉思
列维纳斯在谈及为什么写作《生存与生存者》一书时说道:“这些研究从战争以前开始的,就是在监禁中也继续进行,并且写下了绝大部分的内容。在集中营里之所以有兴趣写这些东西,并非为了表现自己的深奥和沉湎于学术以保护自己,而是想对1940年到1945年间发表的那些具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不被人们注意这一点作一解释。”[9](前言)那么,在列维纳斯那里,什么是已经发表但未能被人们所注意的内容呢?他重新阐释那些问题的意图或目标又是什么呢?
(一)向善是存在的本性
列维纳斯说:“把生存者引向善的那种运动并非生存者把自己提升到较高的生存的那种超越,而只是从存在以及描述这种存在的范畴那里启程:‘一种离开存在’(an ex-cendence)。但是,离开存在以及善在存在者(being)那里必定有一个立足点,这就是存在比非存在者(non-being)要好一些的原因……生存这个动词只有在其分词形式下才变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只是在那生存着的生存者那里才变得可以理解。”[10](P1)原来,列维纳斯之所以要重新阐述生存与生存者的问题,原因在于:现实中存有存在与存在者相混淆的现象,将向善运动的动力源误认为是来自存在者。而他所要做的就是澄清生存与生存者的界限,并找出向善运动的起点或立足点。实际上,列维纳斯所谓的向善运动,其动力源来自于存在,而不是来自于存在者,且这种来自于存在的向善冲动,本身就具有诸如责任感的道德内涵。而倘若向善运动的原动力来自于存在者,则会引起向善行为的摇摆不定。在列维纳斯那里,向善运动本质地存在或先天地存在,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念,由此,他肯定不会将向善运动的动力源归结为存在者,而将它限定在存在这一本体的层面。实际上,正是列维纳斯将向善行为归结为存在的本性,从而为他的道德他者的理论设定了牢固的逻辑起点。
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在列维纳斯那里,除了具有本体意义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以及列维纳斯自身作为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在一定意义上也促使列维纳斯思考诸如生存与生存者、死亡、时间和上帝等问题。⑥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形而上的拷问,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归根到底还是复归于他的道德他者的哲学理想。
(二)死亡彰显主体的局限
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一书中说:“对死亡的无知,并不是直接的虚无,而是与体验虚无的不可能性相关联。它并不表明死亡是无人自那返回之域,因而作为一种事实而被保持不可知;对死亡的无知表明,同死亡的关系不能在光亮下发生;还表明,主体是处于那种并非来自自身的关系之中。我们能说,它是一种神秘的关系。”[11](P40)在这里,列维纳斯之所以引入死亡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进一步考究主体的局限性。在列维纳斯看来,死亡问题不仅是主体自身范围内难以解决的认识问题,而且对死亡问题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生出一种崭新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且这种关系不是来自于主体自身,而是来自于对于主体而言的某种神秘性。
列维纳斯说:“我甚至惊奇,我们同死亡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地被哲学家的眼光所回避。同死亡的关系并不是同虚无的关系,因为在死亡状态下我们一无所知,它主要借助于情景而让绝对不可知的事物呈现。绝对不可知性意味着,它远离一切光亮,它展示一切不可能的可能性之假设,但是,在这种情景中,我们自身又被牢牢地捕获……这就是死亡为什么不在场的原因,它也是不言而喻的。”[12](P41)在列维纳斯看来,死亡并不等同于虚无,也不是与虚无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因为死亡具有超越主体感知或认识的特性。死亡问题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是借助于死亡这样的情景,进一步考察某些绝对不可知的事物,而这种考察在本质上又是对主体极限的挑战,或者说是对主体局限的超越。正因为如此,列维纳斯借助于死亡问题的追问,实现了他对超越主体问题的思考,并最终借助于超越主体而全面阐述了他的道德他者的哲学理想。
(三)死亡隐喻主体的终结
列维纳斯在具体阐述主体与死亡的关系时,尤其是阐述死亡的功能表现时说道:“死亡远离一切在场……它标志了主体性机能和英雄主义的终结。现时是一种这样的事实:我是主人,可能性的主人,把握可能性的主人。死亡从来就不是现时。死亡在处则我将不在,这不是因为我是虚无,而是由于我不能把握虚无。作为主体的我的主人地位,我的性机能,我的英雄主义,既不能成为与死亡相关的性机能,也不能成为与死亡相关的英雄主义……死亡之永恒地无处不在。”[13](P41、42)可见,列维纳斯所论述的死亡主题,是相对于主体问题而言的。它从死亡之功能表现的角度论述了死亡与主体的本质区别。在列维纳斯那里,主体与“性机能”、“英雄主义”、“在场的现时”以及“主人地位”等,形成一定的隐喻关系;而死亡则被隐喻为“性机能与英雄主义的终结”、“无法把握的虚无”以及“永恒的无处不在”等。借助于上述双向的隐喻,列维纳斯在主体与死亡主题之间,建立了相对应的逻辑联系,从而为他借助于死亡问题的考察实现超越主体的哲学理想打下了基础。
在阐述死亡的基本特征时,列维纳斯说:“在死亡事件的可能性中,主体不再是事件的主人,而在对象的可能性中,主体总是主人,并且它总是唯一的主人。我视这种死亡事件的特征是神秘的,更确切地说,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即无可把握的,它如同那些不能驶入的事件一样,不能驶入或进入在场。”[14](P45)可见,列维纳斯所谓的死亡之特征,主要包括“神秘性”、“不可预测性”、“无法把握性”以及“缺场性”。上述特征都是相对于主体意识中的“真实性”(或“真理性”)、“必然性”、“整体性”(或“同一性”)以及“现实性”(或“在场性”)而言的。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在死亡的特征与主体的特征之间,建立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采取的言说策略,它并不意味着死亡与主体之间是某种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
三、道德他者的凸现
《列维纳斯读本》的英文编者西恩·汉德(Seán Hand)曾说:“他者的优先性构成了列维纳斯哲学的基础。”[15](P38)在汉德看来,列维纳斯哲学的最终理论目标是指向他者的。下面,从列维纳斯为主体与他者相遇而设置的情景这一问题出发,进一步阐释道德他者的理论内涵。
(一)死亡隐喻着他者的神秘
列维纳斯在解决了死亡问题与主体的逻辑联系以及内在差异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列维纳斯说:“接近死亡暗示了我们与被视为绝对他者之物的关系……同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田园诗般的、充满和谐的、圣餐仪式般的、或慈祥的关系,借助于这些关系,我们能将自身置于其他的地方;而他者则会同于我们,外在于我们;同他者间的关系就是同神秘间的关系。他者的彻底存在是由他者的外在性或他异性所构成的,因为外在性是一种空间的属性,它通过光将主体折回自身。”[16](P43)在这里,列维纳斯借助于“我们”(即主体)与他者关系的阐述,进一步论述了死亡与主体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主体与他者之面对的道德含义和超越主体的哲学内涵。在列维纳斯看来,主体与死亡的关系,并不是我们在主体意识下的那种主体间的关系,它实际上是指主体与绝对他者之间的关系。⑦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我们是不能以主体间的某种关系而揣测它或演绎它,甚至这种揣测或演绎本身就是一种误区,因为列维纳斯之所以提出主体与死亡、主体与绝对他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的最终目标不在于让我们认识或演绎该关系中的具体的理论内涵,而在于上述关系之提出的理论策略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列维纳斯提出主体与死亡的关系问题,目的在于借助于对死亡和他者问题的形而上的考察,揭示死亡或他者对于主体之超越;同时在这种超越之下,保持对死亡神秘性的尊重和对他者道德性的强调。
(二)情景或事件中介着与他者的相遇
列维纳斯说:“同他者之关系,与他者面面相对,相遇一张面孔,且这张面孔能立即地给予或隐藏他者,以上都是那种情景。在该情境中。事件发生在主体身上,而主体又不能设想事件,最终,没有任何东西能以确切的方式呈现在主体面前。他者仅能被设想为他者……在同他者的关系中,主体趋向于认同他者,通过以一种集体性的表象去吞并他者,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17](P45、53)在这里,列维纳斯为主体与他者之相遇提出一种“情景说”的理论,即主体借助于“情景”的中介而实现与他者的相遇,或者构成发生在主体身上的“事件”。他者的“神秘性”、“无可预测性”以及“缺场性”等特征,尽管为主体与他者的相遇设置了种种障碍,或者说,他者不可能直接地为主体所认识、描述或理论化;但是,他者可以借助于某种“情景”而实现与主体的相遇,从而间接地影响主体,或者说为主体超越自身而提供内在动力。
不仅如此,在列维纳斯那里,上述情景的建构还表现为“事件”,即由主体、他者和情景共同构成的一种运动着的、变化着的事件。它不同于主体话语所建构的同一性的、必然性的、真理性的历史事实或历史发展过程。在上述情景中,主体与他者相遇,他者在主体面前并不是为某种主体所意识化了的确切的存在,而仅仅是他者,即他者就是他者。在这里,借助于情景而实现与主体相遇的他者,已经不同于形而上意义上的“绝对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它有点类似于拉康所言的“小写他者”,即处于潜意识阶段的、与话语或语言无涉的镜像阶段的他者,与感性的他人形象相关的他者。[18](P36-37)列维纳斯所阐述的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桥梁或纽带的作用,即在本体世界的“绝对他者”与现象世界的主体之间建立了桥梁或纽带。没有上述意义上的“小写他者”,也就根本谈不上主体的自我超越,因为如果没有了作为超越参照的“小写他者”,也就没有主体自身,也就谈不上主体的自我超越问题。而“小写他者”也不是直接地与“主体”发生联系,它也要借助于“情景”的中介,或者说借助于“事件”的营构而得以实现。这样,“绝对他者”经由“小写他者”和“情景”的双重中介,实现与主体的相遇,并最终服务于主体的自我超越。或许有人会问:主体与他者相遇有什么现实意义?列维纳斯引入了“未来”等概念,借助于对死亡与未来的论述,推演出他者的道德内涵,进一步彰显了主体与他者相面对的道德内涵。
(三)他者界定着未来
列维纳斯说:“我不是借助于未来而界定他者,而是用他者去界定未来,因为死亡之未来构成了死亡之整体他者……同死亡的关系,就文明的层面来讲,它是一种原初性的复杂关系,它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复杂,而是它本身就被发现了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辩证。”[19](P47)在列维纳斯看来,用他者界定未来,体现的是一种文明的原初性关系,换句话说,他者的本体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明的原初性含义,而这表面上似乎显示了列维纳斯的观点回归了马丁·布伯的“原初词”的学说。但是,列维纳斯所阐述的“以他者界定未来”的观点,在实质上已经超越了马丁·布伯的学说,因为他在指向未来的道德关怀的理论旨趣中,显示出观点的独创性和论证的独特性。
列维纳斯说:“他者仅为其自身,其间没有为主体预留额外的存身之处。他者借助于同情感而为人所熟知,正如又一个自我和变化了的自我一样……假如某人能拥有、把握和知晓他者,则它将不是他者。拥有、知晓和把握是权力的同义词。”[20](P47、51)在列维纳斯看来,他者自身的“纯然性”不为主体所“玷污”,他者就是他者,而不是主体的另一版本,他者的纯然状态是借助于“同情感”而为人们所熟知的。显然,列维纳斯所谓的他者内涵,最终指向的还是道德伦理,即上面所说的“同情感”。不仅如此,列维纳斯之所以竭力倡导“同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与他反权力、反权威的理论主张密切有关,即对主体之权利或权威的颠覆,对道德之“同情感”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回归他者,回归他者的纯然状态。最后,列维纳斯发出了“爱一切人”[21](P31)的呼声。
总之,列维纳斯“道德他者”的思想给我们以许多启示。
注释:
①关于Emmanuel Levinas的译名以及国籍的认定,有着不同的说法。译名有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伊曼纽尔·里维纳斯、埃玛纽埃尔·勒维纳斯、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伊曼纽尔·利维纳斯、伊曼纽尔·莱维纳斯等,本文采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就国籍而言,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有人说是法国人,实际上,他是德裔法籍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人大逃亡时期来到法国,并加入法国籍。本文采用德裔法籍的说法。
②该书原文为法文版,首次出版于1948年,据英译者Richard A.Cohen的译注,《时间与他者》一书源自列维纳斯应Jean Wahl所创立的巴黎哲学学会的邀请,在1946-1947年间所做的系列演讲,1948年结集出版,1979年又重版。参见Emmanuel Levinas.Time and the Other(and additional essays).Translation by Richard A.Cohen,Pittsburgh,Pennsylvania: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7。目前国内尚未出现中译本。英译本还有节选本:Seán Hand(ed.).The Levinas Reader.Basil Blackwell,1989,pp.37~58。
③埃玛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该书是列维纳斯于1963年到1966年在巴黎的犹太学者研究会年会上发表演讲的论文集。
④在这里,所谓的双向对话交流,无论是在布伯看来还是在列维纳斯看来,都不是一种现实性和必然性,而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或话语策略,其最终的实现还有途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问题。为此,布伯和列维纳斯开出了道德这剂良药。在布伯看来,“关系”体现的就是一种道德;而列维纳斯则把道德更推进了一步,认为道德是第一哲学。在列维纳斯看来,科学知识的真理本质是一种主体化作用下的现实效果,其在现实中仍存有它所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道德的出场。列维纳斯关于“作为第一哲学的道德”这一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如康德所谓的本体界和现象界的划分之上,因为有了上述划分,科学、道德、艺术,它们就有了各自的领域和任务,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道德”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
⑤关于布伯的“你之国度”的阐述,详见马丁·布伯:《我与你》,17~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笔者认为,布伯意义上的“你之国度”是相对于另一个“它之国度”而言的,它相当于本文所说的“他者”状态,即与主体相对却又不为主体所同化或整体化的“全然他者”的状态。其中,主体相遇上述意义上的他者,则是借助于“关系”的中介,具体过程则表现为:布伯意义上的“我—你”原初词的提出,构建了一种列维纳斯所谓的“情势”(Situation),借助于情势,最终得以言说自我,并相遇他者。而布伯意义上的“它之国度”,则表现为我所言的“主体独语”的状态,“他者”经由主体的同化,而成为主体的对象,成为主体的另一个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他者”被主体所排斥。
⑥根据《塔木德四讲》的译者关宝艳的介绍,列维纳斯是一名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法军而被俘,在纳粹集中营里艰难地渡过了五年的时光,其家人,除妻子被法国的朋友收留而幸免于难之外,其他亲属全被纳粹杀害。参见关宝艳:《伦理哲学的丰碑——写在〈塔木德四讲〉汉译本付梓之际》,载埃玛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⑦在这里,“绝对他者”与“大写的他者”、“彻底的他者”,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关于“大写他者”的内涵,参见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从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载《哲学动态》,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