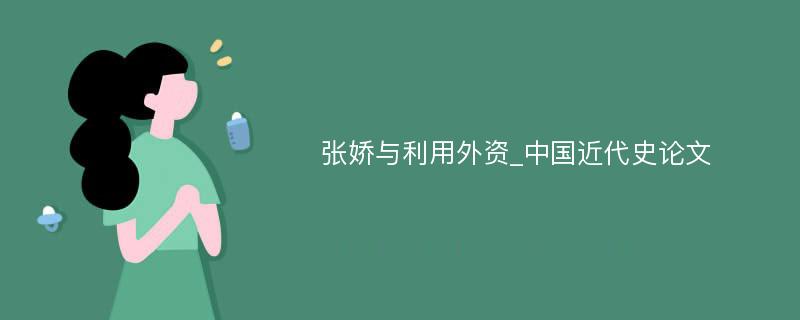
张嘉璈与利用外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张嘉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嘉璈,又名张公权。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民族金融家,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从事银行金融工作,出任过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和总裁职务,并于1935年至1943年担任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负责抗日战争前夕及战时的铁路建设事业。他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在中国利用外资修筑大规模铁路的设想,并为此身体力行,不仅遵循孙中山的遗训,推行利用外资,努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而且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阐发,著有《中国铁道建设》一书。
一
张嘉璈对铁路建设事业的关注早于其就任铁道部长之前,当他在中国银行总经理任内,就“竭力提倡中国银行界投资铁路”〔1〕。在任铁道部长期间,他更是以铁路建设为己任,提出了“铁道建设论”。
1.论述“铁道建设”和“开发矿产”的积极性
张嘉璈指出,“大规模之铁道建设,对于政治及经济需要之迫切已不言而喻。”比如,“在农业方面,能增设铁路……则所费人力,已非数字所能形容”;对于“工业建设,尤其各种国防工业,例如钢铁厂,兵工厂,化学工厂,机车厂,以及卡车厂等……必须建立一广大之铁路系统,以利运输。”尤其那些“甘肃新疆之石油,四川云南之钢铁,以及西康四川之煤矿,若非铁道达到,焉能有开发之望?”〔2〕他又从维护国家统一,从促进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高度论述铁路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本部与边省之间,以及经边省而达邻邦,亟需有大规模之铁道,沟通其间。”“如果各边疆区域均有铁路可通,不特边省问题可以消除,而与各邻邦之隔阂纠纷亦可避免,其有裨于中国政治之安定,非浅鲜焉。”因此,他强调,“沟通边省之路线,尤其有重大之政治意义。”〔3〕张嘉璈更认为建设铁路“最重要者尤在促进全国之真实团结统一。”〔4〕他说, “中国铁道事业奋斗之目标在于争取中国之独立与自由发展,今后铁道之增加建设,更在于促进与维持民族之统一,国家之自由独立。”〔5〕
张嘉璈认识到铁路建设不仅有助于“物质之流通,旅行之便利,军队运输之迅速”,且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我国幅员广大,人口及财力之分布,至不平衡,铁道建设之后,人民自由流动,则人口分布,地方繁荣,可渐臻平衡。”又说,“我国如欲以大量原材料,供给于世界市场,必先具有价廉之运输工具。换言之,有完备之铁道系统不可。”〔6〕
他特别强调铁路建设对沿线资源开发的积极意义,指出,“惟国内大部分资源,迄今尚未开发,则属公认之事实,将来铁道发达,运输便利,各地已知未知矿藏,自必能逐渐探见开发”。反过来,他认识到沿线资源开发对铁路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指出“开发铁路沿线之矿产,以期增加出口,取得外汇来源”,这样能直接促进铁路建设事业的开展。正如他所说,“我国欲完成建设计划,亦唯有出此一途”。这就指出了铁路建设和沿线资源开发相辅相存的密切关系。
张嘉璈还指出了工业建设、矿产开发和铁路建设的连锁关系,认为矿业开发是工业建设的“先锋”,而铁路建设又是矿业开发的“先行”。他分析说,“中国如欲开始工业建设,其基本条件,必先发展电力设备,有发电机始可推动工业,有煤始可推动发电机,故矿业之开发,尤其煤矿之开发实为轻工业之先锋。”同时,他又认识到工业建设的发展对于铁路建设事业的促进作用,他指出,“一俟工业发达之后,”“铁路收入亦随以俱增”〔7〕。 张嘉璈这一见识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的见解,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作出了新的具体阐发。
此外,张嘉璈还看到铁路建设对于引起社会风气改变,吸引西洋文明,推进近代中国文化进步的积极意义。他说:“西洋思想,输入我国,对于固有文化,鼓荡刺激,尤以沿海各省,与新文化接触较多,影响所及,甚于内地,因此全国各地文化水准之轩轻,日见显著。唯有运输与交通逐渐改进,使新文化之发展,迅速普及全国。即如铁道若逐渐伸张,内地人民得见向所未见之机车引擎,即与近代机械文化相接触。故为保存发扬我国固有文化,消除各地区文化水准之不同,并为吸引西洋文明之优点,唯有从事大规模铁路建设一途。”〔8〕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2.阐述“吸引外资”发展铁路和“中外合作投资”工矿事业的重要性
张嘉璈认识到铁路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但他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国“生产资金之枯竭”〔9〕, 因此,他提倡“吾国铁路吸引外资”,“工矿事业之发展,有赖于外资之援助”,“鼓励中外合作投资,从事测勘与开发,以期早日开发”〔10〕。他主张,铁路建设采用举借外债的方式,而工矿事业则采用“中外合作投资”的方式,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种“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方法。他说,利用外资,应当“包涵铁路与矿产并行开发之原则”,“工矿事业之发展,有赖于外资之援助,正与铁路相同,唯形式则有不同”,因为“铁路外资之利用,……唯有藉重各国政府之协助,直接在国外市场发生债票,或利用各国政府所设置之出口担保,供给资金。至于矿产与电力之开发,宜尽量采用合资投资经营方式。”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良以利用发行债票方式,或出口信用,则仅有国与国之资本关系”,而无在合资中“技术上或技术人员关系之发生,更无私人或私人企业团体间利害情感之发生。”所以,他指出,“工矿事业,如能提倡合资投资经营,则不特资金易于招致,而铁路投资方式所缺乏之国民间之个人关系,可由工矿业投资中补救之。”〔11〕这就是说,铁路借债采用“发行债票”或“出口信用”的方式,只产生“资本关系”,而工矿事业采用中外“合资投资经营”会产生“资本”、“人才”和“技术”一揽子关系。正如他所说,“中国尤所盼者,为各友邦技术人员之供给,如外国各大实业,能以最新技术及优秀技术人员供给我国,则有助于我国工矿事业之发展”。如果与我国优秀人才及其“技术之心得,两者同时并进”,那么“中国工业技术之进步,必可一日千里”。所以,张嘉璈竭力主张“中外合作投资”这种一揽子引进外国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方式。
为了确保引进外资中的国家主权,张嘉璈强调指出,“铁路外资之利用,须打破以往势力范围之旧观念,以免除今后再发生以往政治上之外力压迫”,“使吾国铁道吸引外资,而不至再丧失主权。”他“对于我国铁道资金问题,认为理想中之办法应以外资筹购铁路材料,其余建筑费用以本国资金担任。”所以,“根据上述原则”,他一方面“提倡中国银行界投资铁路”,另一方面要求“我国信用机构能以公正立场,审慎态度,对于本国及外国投资者或为保证者,或为信托人,则即可进而劝导外国投资家放弃其旧时侵犯主权之苛刻条件。”〔12〕据此,他制订了“铁道投资之方针”,指导其担任铁道部长期间的“借款筑路”活动。而对于“中外合作投资”,他强调“外资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九,董事长及总经理必须为中国人。”〔13〕
张嘉璈认识到利用外资,发展铁路建设和生产建设是“债权与债务国互助互利之举”,一方面中国引进外资进行“铁道建设,足以增进生产,增加出口,以大宗原料品,供给于各工业国家。”而另一方面“工业国家,以其过剩之制造品,协助吾国建设铁道,同时辅助我国增进生产,以生产品之出口,偿还铁道债务本息”。总之,“不特国际经济合作可以增进,即世界和平亦以维持,不亦一举两得。”〔14〕这就体现了在“互助互利”基础上开展利用外资活动的思想,也揭示了这种“互助互利”的引进外资对于增进国际经济合作,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
3.阐明“整理旧债”和“废除旧制”的必要性
张嘉璈认识到“吾国举借外债之最大障碍,厥由于过去大部分铁路借款本息之愆期未付”,因此,“中国欲在外国市场发行新债票实不可能,即欲举借小额之材料借款亦属不易”〔15〕。对于这种“信用低落”的状况,他认为“若欲完成铁路建设计划,必须恢复铁路债信,使铁路债票价格回涨,至可在国外市场发行新债之程度,庶使巨额外资可以招致。”〔16〕出于“恢复铁路债信的动机,由国民党政府成立了铁路债务整理委员会”,并制订一系列“铁路债务整理原则”。张嘉璈主持这一整理工作后,指出“全国铁路收入,悉数充作公债担保,旧日合同内有以关盐收入担保者,亦一并代以铁路收入,以期划一,倘铁路收入不足时,应由国家总收入中拨补充。”〔17〕这一观点与“铁路债务整理原则”是一致的。
在有关“整理旧债”、“整理旧路”的论述中,他坚持了维护主权的思想。他指出“整理恢复偿付本息后,对于债信,已有显著之进步”;但是,“以往办法,尚有种种缺点,若不修改,恐中国铁路之自然充分发展,仍无达到”,因此,“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必大加改变,不至再恢复旧日势力范围观念。”他强调:“以往足以妨碍我独立自由者,必使根本消除,深盼各友邦能予以深切之同情,自动放弃过去所获得之筑路特权,不论已筑或得而未筑之路权,以及特许管理经营之路权,一概放弃。”〔18〕因为“旧制一日不除,势力范围之观念,终难于根本消除,势力范围一日存在,即不能消除过去流弊”〔19〕。所以,他希望在整理旧债、恢复债信的同时,废除外国以往凭借债权所获得的“势力范围”之特权,为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他说,“我国铁路投资之旧办法,以各铁路为个别对象者,应速予修正,而代以我国整个全国铁路为对象,所发债票,由政府负责担保,如此办法,其对于投资者之保障,敢信不特不见削减,必且优于以往也。”〔20〕他进一步说,“债权国间之分配,当按债权多寡,以及每一材料供给能力之多寡为比例,务使各债权国与中国之贸易,因此日见增进,各国得自由平等投资通商之实益,中国可一扫七十五年来势力范围之束缚,树植今后长久和平基础”。〔21〕由此可见,张嘉璈“整理旧债”的出发点,不仅在于“恢复债信”,而且还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开创“利用外资”的新局面。
二
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后,大力推行“整理旧债”和“吸引外资”的两大主张,并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条件下,部分实现了铁路建设计划。
1.“整理旧债”活动
张嘉璈于1935年就职铁道部长,莅任之初,深感我国铁路事业虽有七十余年之历史,而始终未获一真正之发展机会,“设列强于过去数十年间,能采取贤明之态度,则中国之铁路史与远东政治史当另具一色彩,何至有今日之局势。”“同时反诸吾国本身,连年政局不安,全国不能统一,铁路当局为应付政治起见,不以常轨处理路务,路款收入往往移用于铁路以外,因此铁道本身之需要,反感不敷,路政日就衰颓,到期债款愆期偿付,更使外国投资者对于我国铁路事业裹足不前,吾国人不能不任铁路落后之责也。”〔22〕可见,他上台伊始,面对“路政衰颓”、“旧债愆期”这一铁路形势发出一片苦叹声。
在感叹之余,张嘉璈首先着手“旧债整理”,他后来回忆说,“至于旧债之整理,进行亦极顺利”。“先后整理各债,计有津浦债票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开始恢复偿付本息,道清借款于同年五月恢复,广九借款于同年八月恢复。此外,美比荷兰各国之借款,亦经陆续整理,计陇海借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八月整理,湖广借款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整理,综计整理各借款数额达英金四千零三十六万九千七百十四镑或美金一万九千八百十二万二千五百零七元之巨。”〔23〕由于“旧债整理”顺利进行,恢复了我国的债信,出现了“新资本络绎而至”,“各债票在国外市场行市随而好转”,“外国投资者之眼光逐渐移转,视中国为一优良之投资市场”的大好局面,所以,张嘉璈对此兴奋不已,称“数十年来铁路之厄运,一旦否极泰来,国人欢忻鼓舞之情,固非言语所能形容也。”〔24〕
2.“整理旧路”活动
“整理铁路旧债”之后,张嘉璈便着手“整理旧路”,他认识到,“建筑新路固属必要,而改进旧路尤为急切。”〔25〕所以,“作者于整理旧债之后,继以开始整理旧路”,其要点在于撙节开支,提高效率,俾各路收益改善,而有余力应付新旧债款之本息负担。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整理旧路“主要者为整理平汉借款,改善京沪设备借款,浙赣换轨借款”。“其实施步骤”是,“首先,规定开支预算,裁减冗员,节用材料”;“其次,补充机车辆设备,改进列车速率,以期增加营业进款”;“最后进而统一各路之会计材料,以及人事行政,俾铁道部对于各路之财政,可从多方面加以统制”。由于采取上述的步骤,“各铁路之营业进款”大增。比如,1936年上半年收入为8757.7万元国币,到1937年上半年达到9185.2万元国币,一年内就增加了几百万元,“在此时期,所有到期债款无不照付本息,于是吾国管理铁路之能力,以及维持债信之决心,为世界共见矣。”〔26〕这就为举借新债,发展铁路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吸引外资”活动
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当时有人认为在战时发展铁路已不合时宜,但他认定,铁路建设“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均有兴筑之价值。”〔27〕根据这一宗旨,他从1935年开始拟定实施3年内修筑3700英里新路的计划。并“于抗战爆发前十八个月中, 将利用外资建设铁路之途径重打开”,“新路方面,国外借款共计四万万七千一百零二万七千五百十一元”;加上“旧路方面,国外借款共计五千八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五十五元”,“总计国外借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元,约合美金一万万五千七百二十六万零五百三十五元,或英金三千一百九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镑。”〔28〕他主张“外资筹购铁路材料”,内资承担“其余建筑费用”,采用内外资结合建设铁路的办法。1936年1月, 他主持的铁道部采用这一新举措“修筑了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2月,修筑了湘黔路株州至贵阳线。 ”他还与外资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并拟定了1937—1941年修筑铁路5000英里的计划。由于抗战的爆发,这一计划告吹了。不过,张嘉璈仍制订了战时的铁路建设计划。他在当时说,“抗战中计划建设之新路,有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滇缅铁路、叙昆铁路、西北铁路。”尽管“各路之建设,遭遇无穷困难,一面随军事形势之转移,进行计划,一面敌人封锁,着着加紧,材料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输入,影响及于工程进展”,但“迄今尚能稍有成就,亦云幸矣”。〔29〕在他的主持下,利用外资先后修筑了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黔桂路贵州至柳州段;宝天路宝鸡至天水段等。此外,他又打算修筑西北铁路经新疆到达苏联,还打算修筑滇缅铁路与缅甸接轨,等等。这些计划终因战时的种种困难,有的只进行了勘探工作,有的则完成部分计划,也有的因战事进一步扩大而中止。尽管如此,在抗日战争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张嘉璈于1937—1942年间还是领导完成了1000英里的新建铁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
张嘉璈推行“利用外资”进行“中国铁道建设”的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
1.推行“整理旧债”政策,“恢复铁路债信”
张嘉璈根据制定的“铁路债务整理原则”,即:“(1 )凡各铁路自能负担之债务,应由各铁路自行清还之。(2 )凡向来由盐款还各铁路债务,应仍由盐款支付之。(3)凡用铁路名义各政治借款, 应由财政部负责清理。(4)凡铁路债务,铁道部无力单独担负者, 应由财政部尽力协助之”,分别对各款旧路债务进行整理工作。据史载,关于旧有铁路的外债整理,大致可分为三类:(1)履行原订合同, 照旧偿付的外债;(2)对已发行债票或未发行债票的铁路借款及垫款,延期偿清,甚至从关盐两税和增加铁路运费等方面偿付旧欠;(3 )因无特殊担保或外国根本未照原订合同履行而无法整理或尚未整理的各债。经过整理,其中第一类有4款,第二类有11款(其中7款是发行债票的,4款是未发行债票或垫款的),均被一一整理, 而第三类已囊括在无必要整理的69笔外债之中。
整理结果表明,截至张嘉璈上任铁道部长第一年,即1935年底,国有铁路积欠的外债共计5382万余英镑,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三,均一一加以整理,并开始还本付息。仅在1935年,偿付已整理的外债本息和指定某项收入偿付的借款本息,共达2500万元以上,占国有铁路营业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30〕可见,张嘉璈整理旧债工作的成绩出色。到1937年,国民政府已将1928年以前拖欠的大部分债务清偿了,使其在国际上的债信得到提高, 外国投资者开始恢复对中国铁路的投资,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先后商订之新款或已订合同,或仅订草约,除材料借款之外,共计英金三千一百九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镑,或美金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六万零五百三十五元之巨”〔31〕。此外,原已发行的旧路债票纷纷上扬,如“津浦债票涨至七一·五镑,湖广债票涨至七一镑,道清债票涨至八八镑,陇海债票涨至四二镑,京沪债票涨至九○镑,均属空前未有之最高价格”〔32〕。这一切都表明,“在此一年又半”,张嘉璈整理旧债的工作已使我国的债信大大得以恢复,于是,中外“新资本络绎而至”,人们“对于铁路建设重复恢复过去热烈之信心,新路工程因获迈进之机会”〔33〕。
2.筹措铁路建设资金创造内外资结合的新举措
早在1928年,张嘉璈主管中国银行后,就对铁路投资发生兴趣,以中国银行为首的杭州银行团为帮助建筑杭江路(杭州至江山的铁路),将其因发行法币的数量增加且各地工商业萧条而过剩的资金共计670万元放贷于浙江省政府。 该省政府又借用了各列强转拨的庚子赔款,以购买国内不能生产的铁路材料,用于杭江路的建筑,这就初创了“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借债筑路”的新路子, 终于使杭江路于1934年1月竣工。这一收获使张嘉璈得到很大的启发。于是, 他在担任铁道部长后就提出,“外资采购铁路材料”,内资承担“其余建筑费用”的主张。当玉萍路兴建时,在张嘉璈的主持下,一方面以“铁路建设公债”为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用铁路建筑的款项,另一方面通过中国银行向德奥托华尔夫公司担保,借用材料款项。在内资和外资的合作下,玉萍路段终于1937年筑成并通车,不久将路段接通已成的株萍线,与粤汉铁路相连,完成了共长950公里的浙赣铁路的建设。 这一铁路的修筑,开创了内资与外资参合的“铁路借款”新途径。它成为此后国民政府筹集铁路建设资金的主要方式。
1936年,湘黔铁路建筑和平汉铁路黄河大桥重建的两笔数目更大的借款,是由西门子电子电气公司出面,又由奥托华尔夫公司参加,并与以中国银行为首的上海银行团合作贷放的,只不过抗日战争爆发,仅贷放了其中的一部分。
此后,张嘉璈主持的铁道部先后与英、法、比等国签订了由宋子文主持的中建银公司合作参与投资的一些铁路借款合同,如与英国签订的沪杭甬铁路与钱塘江大桥建筑,以及京(南京)、赣(贵溪)、贵(溪)梅(县)、广(州)梅(县)、浦(口)襄(阳)、三(水)梧(州)等借款合同;与法国签订成渝线以及贵(阳)昆(明)、湘桂铁路南(宁)镇(南关)段、叙(州)、昆(明)铁路等借款合同;与比利时签订了宝(鸡)成(都)铁路等购料借款合同。所有这些合同都采用了“中外合作投资”的新路子。不过,这些签订合同的铁路工程,除极少数开工实施之外,到抗战爆发后均告中止,尽管如此,这一举债途径是遵循了孙中山所提倡的“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同时实行”的方针,为改变以前列强通过贷款而监督和攫夺路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方式而创造了一种“中外合作”的新模式。正如张嘉璈所说,“今日以后宜采用中外合作之新精神,只替代以往之监督条件。以此各项新借款契约中已充分表现,足为战后利用外资之规范。此无形收获非炮火所能毁灭,是作者努力固未尽掷诸虚牝,虽失犹得,所可引以自慰者也。”〔34〕
3.建筑新铁路,“大俾于抗战”和战后经济复兴
张嘉璈就任铁道部长数年,在任上,他共领导完成新的铁道建筑“二千二百六十三英里”,据史载,1928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共建筑铁路也仅有2153公里。在1937~1942年在他直接领导下又完成了1000余英里的新路建筑,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所新建的铁路很大部分是在张嘉璈任内完成的。而一部分铁路是在抗战极困难的条件下,建筑于西南地区,即抗战的后方地区。这些铁路的建成,对于促进内地的经济建设,支援前方的抗日战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正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王云五副院长在为张嘉璈所著《中国铁道建设》一书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公权先生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迄三十一年(1942年),总管铁道交通行政,此时期内对于铁道事业之贡献,早为国人所共闻共见。”对他利用外资建设铁路事业的成绩,王云五称赞道,“于久经涸塞之外资财源,竟于一年有半之短期内,排除一切障碍,而使其畅流,复于七年中完成新路二千二百六十三英里,约等于过去七十年总里程百分之二十三强,其成就诚不容蔑视。至于抗战期中,铁道运输供应之困难,后方新路工程推动之艰苦,尤非丰于素养,老成谋国之士,易能应付”。〔35〕这一席话并非言过其实,比较准确地肯定了张嘉璈一定的历史功绩,对于利用外资铁路建设的积极意义,用张嘉璈自己的话来说,“在战时将大俾于抗战”,在战后将促进“经济复兴”,推动“百业待举”。所以,他不仅在抗战中拟定并实施了利用外资进行铁路建设的计划,而且还拟定了战后利用外资进行铁路建设的十年计划。
张嘉璈在《铁道十年计划》中提出设想:“战后十年之内,应计划完成一万四千三百英里之路线”,具体分为两个阶段加以实施,“第一期建设,兴筑铁路七千一百五十五英里”,“第二期建设,兴筑铁路七千一百四十五英里。”〔36〕并强调“吾国铁道”,在“不至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吸引外资”,“鼓励中外合作投资”,“借重各国政府协助”。这一设想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遗憾的是,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一样,张嘉璈的《铁道十年计划》在当时半殖民地半主权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得以实现。
注释:
〔1〕《中国铁道建设·绪论》,第4页。
〔2〕〔3〕〔5〕《中国铁道建设》,第222—224页。
〔4〕《中国铁道建设》,第209页。
〔6〕《中日铁道建设》,第208页。
〔7〕《中国铁道建设》,第222—224页。
〔8〕《中国铁道建设》,第224页。
〔9〕《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
〔10〕《中国铁道建设》,第222页。
〔11〕《中国铁道建设》,第222—223页。
〔12〕《中国铁道建设·绪论》,第4页。
〔13〕〔14〕《中国铁道建设》,第223、211页。
〔15〕〔16〕〔17〕分别见《中国铁道建设》,第49、99、214页。
〔18〕〔19〕〔20〕均见《中国铁道建设》,第214—215页。
〔21〕《中国铁道建设》,第215页。
〔22〕《中国铁道建设·绪言》,第5页。
〔23〕〔24〕均见《中国铁道建设·绪言》,第9页。
〔25〕《中国铁道建设》,第88页。
〔26〕〔27〕《中国铁路建设·绪言》,第10、11页。
〔28〕〔29〕《中国铁道建设》,第93、165页。
〔30〕拙作:《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第314页。
〔31〕《中国铁道建设·绪言》,第9页。
〔32〕〔33〕〔34〕《中国铁道建设·绪言》,第9、10页。
〔35〕《中国铁道建设·绪言》,第1页。
〔36〕《中国铁道建设》,第211—2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