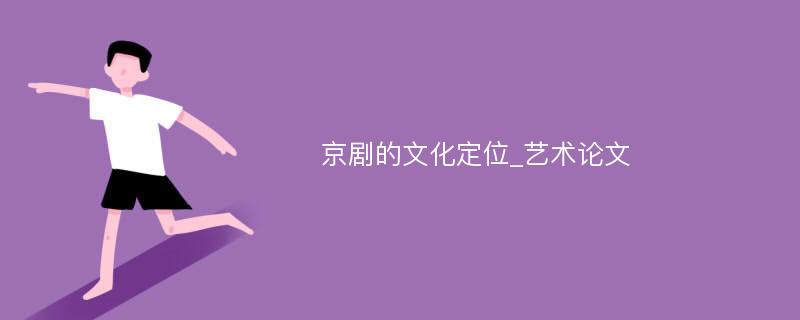
京剧的文化定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剧形成以后,约有百年光景,既是民族艺术,又是流行艺术,令朝野倾倒,南北风靡,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后渐起变化。如今文化格局大变,京剧面临重新选择位置的问题。如定位得当,它虽不能恢复当年的主流地位,但仍可作为民族戏曲的首席代表,参加现代文化新格局的建构,发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如选择失误,也可能更趋萎缩、衰落。所谓定位,不是一种主观愿望,也不是单靠政策和行政力量的托举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不断地以相当数量的高质量、受欢迎的艺术作品加以维系的一种局面,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在京剧的定位问题上,有颇多意见值得讨论。蒋锡武同志发表在1996年第6期《上海戏剧》上的《作为古典京剧的现代存在价值》一文认为,京剧应当作为古典艺术加以保存。文章就现代人需要古典艺术、古典艺术也有现代价值做了动人阐述。这些意见如能取得社会认同,对于京剧传统艺术的抢救、保存无疑是有利的。但对蒋文把京剧定位为只可保存、不能发展的古典艺术这个基本论点我有怀疑。像京剧这样一个蕴藏着极大艺术能量的全国性大剧种,是否仅仅作为古典艺术加以保存就够了?眼下常见的那些传统剧目是否都能作为古典艺术长期保存下去?蒋文引了《国语·郑语》中史伯的两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然后说,古典加古典或现代加现代是“同”,现代加古典是“和”,“只有‘和’,才能健康发展;‘同’就难免要走入穷途了”。这说得很对,问题是,这条原理除了适合社会文化整体外,是否也适合于京剧自身呢?换句话说,对于京剧,究竟是古典加古典,还是古典加现代更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呢?对京剧作某种程度的现代转换即在若干剧目中进行有现代意义的新创造,是否就是“一味新潮”,要把京剧弄成像西方夜总会、酒吧、红灯区中的玩艺儿呢?上海京剧院如果只是拿传统艺术去“走向青年”和“万里行”,能有现在这样的社会效应吗?这类问题,确实关系到京剧的发展战略,关系到京剧在新世纪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回避。
我以为,传统艺术不等于古典艺术。何谓古典?最浅白的解释是“古”而且“典”。传统艺术由历史遗留下来,占一“古”字,“典”则未必尽然。在我看来,具有典范意义的传统艺术才是真正的古典艺术。传统艺术与古典艺术既相通又非同一,它们之间会有无穷过渡。而典范性这个标准,并非一把固定的尺子,它实质上乃是一种“与世迁移”的对传统艺术的高品位追求,合则受到珍视而流传,不合者终归淘汰。京剧是古典形式的戏剧,泛泛说,也可称之谓古典艺术,其实它是一种驳杂的存在,精粗美恶都有。作为传统艺术的京剧,要提高为古典艺术,需要依靠艺术家——不光是演员,还包括编、导、音、美各方面专家——进行审慎的必要的整理与加工。有些与传统风格接近的新作也可成为新的古典艺术。过去艺术家们这样做过,今后仍要这样做。“三并举”政策中对传统剧目就有这方面的要求。前不久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把传统剧目加工到当代最好水平作为范本流传下去。其精神也是不让传统艺术停滞不前,只有稳步地把它推向典范化,才会有久远的生命力。《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在“音”上作了挑选,在“像”上得其仿佛,具有艺术欣赏和资料保存的双重价值。但其中的传统剧目要作为古典艺术参与新世纪文化建构,不是只在荧屏上播放,而是要在剧场里、在群众中长久地存活,就有许多工作等待艺术家们去做,而且未见得都能如愿以偿。
蒋文主张京剧艺术只能古典加古典,不能古典加现代,而且断言,京剧的现代转换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话说得如此之绝,令人遗憾。“无必要”是一种见解,不必勉强求同;“无可能”则是对京剧改革新成果一概视而不见。像《曹操与杨修》这样的作品,虽非完美无缺,但算不算得上京剧现代转换的一个成功例子呢?它如无现代文化品格,又怎能使如许老中青知识分子观众激动不已?它有没有因为现代转换而丧失了作为京剧的资格?我们应当痛苦地承认一个事实:京剧界的新创作存活率实在太低,这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可惜至今未加正视,但亦不应由此灰心丧气,以为京剧只能传统加传统、古典加古典了。京剧改革应当建立古典加现代的张力结构,这种结构目前也有,只因古典化与现代化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而显得疲弱。形成古典加现代的张力结构,既有利于京剧的现代化,也有利于京剧的古典化。古典化使京剧的本体特征得到质朴、纯正的艺术展现,不仅其高度技巧和民族戏曲的美学特色可供现代观众反复欣赏,反复品味,而且对于京剧的新创造将不断输送本原性信息而使其不至于离本体太远,对可能出现的过分异化倾向起制约作用(中介是观众和专家的批评)。反过来,成功的现代化作品既是传统艺术的竞争对手,又是传统艺术经过现代转换可以获得新品质、新生命的有力证据,从而激发人们更加珍视民族艺术传统,又会“逼迫”传统艺术从疲疲沓沓的被动延续状态中走出来,精益求精,变成真正的古典艺术。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会构造一个广阔的空间,使京剧的风格、形态多样化,增加其活力和生机。
反对古典加现代的同志,还与他们对京剧审美功能的理解过于偏狭有关。蒋文认定欣赏京剧应是一种“怀旧”性消费,人们在被现代文明异化之后,京剧就是“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徐城北同志则说,现在听戏、看戏都不济了,已进入“品戏”的新境界,既要品出“梨园行中的所谓‘义气和修养’”,“更要品出那些似乎在戏外的更深层的文化味”。实例之一:某女演员“一次练舞绸,五丈长的绸子她这么轻轻一抖,无意中踩在另一头的男演员就胳膊脱臼”,这里要品出其“气功”;例二:“为什么男旦总比女旦走红?女花脸总比男花脸叫座?”这里要品出“一直伴随着京剧的畸形的性心理”,等等(《京剧的文化背景——访徐城北》,198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谈到这儿,还不能忘了《死与美》一文的作者——曾宣布古典戏曲早该寿终正寝,谁要延长它的寿命谁就是存心把它弄成丑八怪,因而最好向死去的古典戏曲“致最后的注目礼”的李洁非同志。他新近又在《艺坛》199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漂亮文章,题为《戏缘——回忆和杂想》。其中宣布,京剧的美是一种“纯粹的美”,是一种把“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道德的”“一切附庸的价值剥落已尽之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不朽的东西”。类此说法,当属理论“新潮”,大概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京剧的美不在内容只在形式,不在戏内只在戏外,或者说,这种美的欣赏,不仅非功利、非实用(这是对的),也无意味、无意蕴,完全是与人生、与心灵的旨趣无关的纯形式的把玩。而且,在洁非同志看来,感受、判断这种“纯粹美”的能力也难以培育,因而它之“陷于四面楚歌式的困境”是难以挽回的。说来说去,“美”还得“死”,又何来“不朽”?我以为,在京剧审美中,对形式因素的品味、愉悦固然占有很大比重,尤其在欣赏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艺术时,会出现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说的那种“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的审美状态,但只要细细咀嚼,“沉没”不等于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本质上还是康德说的“依存美”;积淀在形式美里的社会心理、伦理内容,还会不知不觉地浸染欣赏者。黄裳先生在风雪弥漫的征途上忽然哼起“蟒袍玉带不愿挂,弟兄们双双走天涯”来(手头无《黄裳论剧杂文》,不知记忆确否),为什么不哼“龙凤阁内把衣换”呢?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里有个住在阁楼上的年老孤苦的报贩,常常酗酒,总爱哼“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为什么不哼“孤王酒醉桃花宫”呢?心境不同嘛!即使非关心境的“玩票”,唱得够味不够味的深层标准,仍在于音色、音调、音韵后面的意和情。在审美功能问题上,我们既要防止由来已久的“左”的夸大,也不能苟同那些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论调。京剧应当是民众的艺术,应当关注人生。京剧不仅可供提笼架鸟溜弯儿的老人们哼着消遣,也要争取能够弹拨青年人的心弦。有位青年朋友看了《曹操与杨修》之后,在首都高校学生“心目中的京剧”大型座谈会上发表感想说:“这出戏所以能打动科技界、学术界,打动将来或正在逐步成为国家栋梁的青年人,很重要的是与人的解放结合起来了。京剧若能对此作出贡献,启迪人的心灵,使人从自身的弱点和疏忽中解放出来,就不是危机的问题,而是对人类文化的高级贡献。”(《京剧——现代启示录》,1996年第1期《中国戏剧》)京剧有高超的技艺、精美的形式,还必须在文化内涵上有新的丰富,这样才能为现代人的心灵建设提供多层次的“文化保健”。这当是解决京剧文化定位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