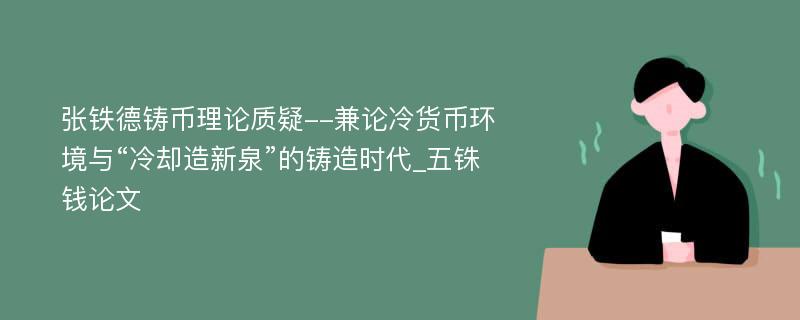
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环境论文,时代论文,张轨铸钱说论文,兼论前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5)02-0062-0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分裂割据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带来了经济上的混乱,经济上的混乱不仅造成北方许多地方“钱货无所周流”(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也使一些割据者为昭示自己的王者名份而自行铸钱,出现了一些区域性钱货。被一些古钱币专家和史学家认定由张轨铸造标有“凉造新泉”字样的钱币便是其一。这种认定从清光绪年间“凉造新泉”发现时开始,至今仍有人沿袭其说。如朱活《古钱新典》在提到1970年发现于西安的“凉造新泉”时,征引了李竹朋《古泉汇》所云:“刘青园有三枚,惧得于凉州,断为轨所铸”(注: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这里的凉州指今武威市,轨指张轨。
笔者不仅质疑张轨铸“凉造新泉”的说法,也怀疑张轨还铸造过“五铢钱”的说法。搞清张轨曾否铸钱,以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代和铸造主体,不仅只是为张轨的政治身份正名,也是为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格局补缺拾遗。
一
张轨,安定乌氏(今平凉市西北)人。史称其为“西晋名臣”(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其父张温身居西晋太官令之职。早在汉魏时期,张氏家族就是陇东的名门望族,“家世孝廉,以儒学显”(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西晋讲名教治国,晋武帝司马炎就自称自己的家族“传礼来久”(注:《晋书》卷20《礼志中》。)。凡晋初名臣,大抵都用忠孝二字磨砺自己。张轨不仅出身“家世孝廉”,而且自幼随其同乡皇甫谧学习《孝经》。长成后“好学明经,有器望,姿仪典则”(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是个行不逾规,动不越矩之人。他于晋怀帝永于元年(301年)自愿请缨,到河西去做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解决了朝廷揪心的问题,使晋武帝不再“为之旰食”(注: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一·秃发乌孤》,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国学丛书本下册,第613页。),不再继续“减膳”(注:《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张轨在凉州13年,始终以晋臣自居,临死还遗令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这时已是匈奴兵破洛阳后的晋怀帝永嘉七年(313年)。
有关张轨曾否铸钱的争论源于《晋书》中的一段记载:
愍帝即位,进位司空,固让。大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
根据这段记载,加上武威发现了“凉造新泉”等古钱币,有人就断言包括“凉造新泉”在内旁及一些“五铢钱”是张轨所铸。这未免失于偏颇。其实,这段记载中的索辅进言也好,张轨纳言也罢,从头至尾不及一个与“铸造”有关的文字。它讲的只是在河西恢复不恢复使用钱币以及使用何种钱币的问题。这在那时已够振聋发聩、移风易俗的了。
前文说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地区正处于“钱货无所周流”的时代,史家称其为“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这个时代早从两汉之交就开始。自王莽变汉制,废五铢钱,至汉光武建武十六年(40年),“始行五铢钱”,中间20多年,社会现象是“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光武帝以后,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有人提议干脆封存钱币,国家租税统统以布帛征纳。到汉桓帝时,国家“竟不铸钱”(注:《后汉书》卷57《刘陶传》,中华书局,1965年。)。东汉末期董卓擅权,“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注:《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虽然后来曹操再废小钱,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货币经济在北方并未由此复苏和活跃起来。史书所载魏晋时期食货及其决策总体情况是:
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注:《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65年。)
汉魏晋之际这些钱币与谷帛之间的行与废,争与斗,说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时代统治者的无奈。在无奈之余,我们还可以窥视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以正统自居的汉魏晋统治者在恢复钱币流通上的勉为其难和对五铢钱的情有独钟。出于这点,他们试图恢复钱币流通的办法大都不像王莽或董卓那些“僭伪国贼”者变更币制,以求一逞,而是因循传统,恪守成规。除魏明帝以外,都不再铸五铢或什么新泉,只是想把散在社会和存在府库里的五铢钱调动起来。《晋书》作者说西晋也是如此。既如此,作为西晋名臣的张轨又怎会去改创呢?笔者认为,索辅身为凉州太府,他清楚河西民间和凉州府库中五铢钱的多少,他依据凉州社会秩序转安和社会经济恢复的实事,向张轨提出合乎时宜的建议;而张轨则审时度势地接受建议,“立制准布用钱”,上下互动,从而在凉州实现了五铢钱的再流通。张轨与索辅的举措之所以有振聋发聩和移风易俗的意义,正是由于他们在河西走廊率先结束了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其实,张轨尊崇晋室,不会在钱币上去做“改创”之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考虑,如五铢钱那样多,又有信用价值,还有无必要铸新钱,如铸,能否行用?还有铸钱需要的铜料来自何处等等。其中,更值得张轨考虑的是操守,因为汉魏晋国家不仅不准许“盗铸”,也不准许偷取钱币铜料以作它用。这方面直到东晋时,还有严格的禁令: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注:《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65年。)
当然,僭伪者不会理会正统王朝有关钱币的法令,也不会顾忌铜料方面的科律。董卓不仅坏五铢钱,而且又铸小钱,“恶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注:《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在张轨恢复五铢钱稍后的219年,石勒称赵王。称王前针对刘曜对他的封赠说:“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1965年。)他称王后除设置太医、尚方、御府等官署外,“又置絜壶署,铸丰货钱”。(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1965年。)他不讲正统,也不管所铸钱币有无信用,当然也不管铜料从哪里来。当他发现百姓不乐意使用丰货钱后,借口发现了王莽时的权石和大钱,采取了强迫民间使用的措施,结果弄巧成拙。
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注:《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新铸的钱既无信用,又强制人们去使用。结果扰乱了经济秩序不说,又徒增犯罪人数。在这点上,张轨与石勒,一个是“正统”,一个是“僭伪”,身份不同,政治行为也不同。张轨不铸新钱,既毋需敛聚铜材,又毋需立什么“科条”,搞什么“限令”,他只通过发扬五铢钱久经考验的信用价值,就使百姓感到了便利,也合乎规律地拉动了河西商品货币经济。
二
张轨有无铸造新钱的必要性?
石勒所铸丰货钱难推行,不光因人们怀疑新钱的信用价值,还因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社会上的闲散货币本来就很多,这种情况下,连原本信用度很高的五铢钱都缺乏购买力,因此才有了“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的现象。即使在非自然经济社会里,货币过量也会造成通货膨胀问题。何况石勒铸币之前,襄国一带也有大量五铢钱的散在,并且还流通着白银等贵金属货币。有记载说,石勒初占襄国时,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两,肉一斤直银一两”(注:《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这说明通货膨胀固已存在。石勒为了表现王者之尊不去整顿经济环境,却违背规律增铸新钱,碰壁是当然的。张轨不铸造新钱,而是按缣布与五铢钱的比价,“立制准布用钱”,其作法与石勒钱帛折算如出一辙,但原理却大相径庭。他巧妙地利用了河西货币环境方面的优势,避免了来自通货膨胀方面的困扰,也因此实现了“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河西的货币环境大致有两方面,一是自西汉中叶起,这里一直是北方通西域的主要商道。在汉武帝设立四郡后,只要无兵乱,常有西域胡商通过敦煌穿河西到内地贸易。鉴于“胡商贩客,日款塞下”的丰厚关税和利润,任何对河西走廊拥有主权的朝代或地方守宰,都尽力维护河西商道的通畅。曹魏的敦煌太守仓慈和凉州刺史徐邈在这方面做得就很突出。仓慈积极招商西域,清除通商障碍,将敦煌变成国际贸易的陆港:
又常西域杂胡欲来,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阳)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其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注:《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中华书局,1959年。)
徐邈则是投资招商:
乃度支州界年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注:《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
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之勋也。(注:《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
河西商道晋初一度断绝。这是因为发生了鲜卑的反晋战事。鲜卑曾一度“尽有凉州”(注:《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域胡商入内地或就在凉州交易,其方式不排除以物易物,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现钱买卖。西域多使用金银钱币,罽宾、安息、大月氏乃至遥远的波斯帝国都如此(注:杜佑《通典》卷9《食货典·钱币下》,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河西也因此获取了大量西域金银钱币,并用于流通。直到北朝末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钱”(注:杜佑《通典》卷9《食货典·钱币下》,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这从高昌古城发现波斯银币可以映证。要市西域的“金帛犬马”,也不能不支付为西域诸国认可的中国货币。而为西域诸国认可的中国货币只有五铢钱。西域人钟爱五铢钱,这在考古中得考古工作者在古龟兹(今库车)以及焉耆、和田等地发现过西域小铜钱,这些小铜钱原型就是五铢钱。
张轨恢复五铢钱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实现河西走廊在东西货币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他不铸新币,也基于五铢钱本来就是居优势地位的货币。史载,张轨下令使用五铢钱后,很快招来了西域胡商,“西胡致金胡瓶,皆作拂蒜奇状,并人高二枚”(注: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民国26年版,第486页。)。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将张轨恢复五铢与从西胡那里得到金瓶连缀在一起,意在说明金瓶是西域生产的珍异商品,只能是五铢钱才买得到的。
张轨能恢复五铢钱流通的另一个货币环境是五铢钱和多种金属货币在河西的藏量。
汉武帝开始设置河西四郡是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是年秋,匈奴昆邪王杀掉休屠王降汉,汉武帝“以其地为武威郡、酒泉郡”(注:《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又《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与此有歧异,兹不论。)。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二郡之地置为张掖郡和敦煌郡。而上林三官初铸五铢钱是在元狩五年(前118年)。就这点说,河西置郡的时间恰与开始总一货币为五铢钱的时间相吻合。这个时间与张轨任凉之间相隔四个多世纪。这四个多世纪正是五铢钱流通和贮藏两大功能呈现阶段性发展的时期。史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云”(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下》。)。这多达280亿万的五铢钱无论流通于诸市和贮藏于公私的数量成什么样的比例,其数量在长时期内部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王莽改币制,“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下》。),很显然是在罢除刘汉的正统地位,而“罢”只是禁止流通,并没有也做不到把二百多亿万的五铢钱全部收缴销毁。相反,由于他改制后的新币缺乏信用和购买力,适促使五铢钱在民间现出巨大的贮藏功能,私下流通也不会中止。王莽颁新币,“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贾”(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下》。),这是明证。而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衰落,又会带来五铢钱贮藏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从董卓废五铢,到后来复五铢的议论不绝于耳,这是最好的说明。
西汉之世,五铢钱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河西走廊更是重要流通地区。这不仅由于河西走廊是国际商道,也不仅由于五铢钱是西域认可的货币,更重要的还由于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当初汉武帝总一货币的目的一在遏制富商大贾“滞财役贫”的无道,制裁富商大贾们在国家有难时“不佐国家之急”的奸利行为;二是为增强边备和与匈奴作战的需要。这第二点更为重要。所谓富商大贾“不佐国家”,就是指国家为徙民实边和反击匈奴,“费以亿计,县官大空”(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下》。),而那些富商们却不为所动,坐视不救。当时的河西走廊是实边和击胡的重点地区,花费的钱财也更多。仅举《史记》所载其移民规模便可知其概: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立田之。(注:《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
《居延汉简》中也不乏移民方面的记载:
□ 迫秋月,有徙民□来关。
居延移民,以物供□门□□(下缺)。(注:分见《居延汉简释文》卷1,第15页、第40页。转引自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西汉政府给戍边和实边的兵士、费民的补偿是“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下》。)。这实际是招募政策。当然,既是招募,受募者都会因资助携带一定数量的货币。
另外,无论是击胡还是戍边,西汉政府对将领实行重金赏赐政策,对战士实行军俸政策。如卫青、霍去病第一次率军击胡时,获“赏赐五十万金”(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下》。)。后来霍去病入河西击胡,亦当如此。这种赏金和军俸制也会将大量钱币留在河西土地上。
总之,由于河西走廊是西汉重要的军事、边防、商贸地区,西汉所铸五铢钱会大量流向这里。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多次发现数量众多的五铢钱说明了这一点。魏晋时期,河西政治、军事、商贸重地的地位并未改变,五铢钱在河西的藏量也不会改变。如改变只会有增无减。因此徐邈才能取凉州每年经费的节余部分为曹魏国家购置西域商品。
除汉武帝移民实边外,从西汉末到西晋初,河西移民又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一是王莽代汉时,一些反对王莽的西汉官僚为避难跑到河西。西州大姓的令狐家族就是其中之一。二是张轨时期,因中原战乱,“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这种势头到张轨死后,尚在延续。如刘曜攻陇右,上邽一带军民“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注:《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寔传》。)。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西晋官僚和中原豪望。他们为避乱举族迁徙,不可能将其庄园带到河西,而只能将积累起的大量财富带到河西。其中,钱币是主要财产。如氾腾,他避乱辞官归敦煌故里,带回五十万资产“以施宗族”(注:《晋书》卷94《氾腾传》,中华书局,1965年。)。当然,这五十万是以五铢钱折算的。
总之,自西汉以来,河西走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货币市场。除潜在的五铢钱外,金银等贵重金属存量也极为丰富,所以当376年前秦攻灭前凉后,能够一下子“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65年。)。
处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之中,张轨既不会熟视无睹,也无必要选择铸钱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当他任地方豪族中的索、氾、宋、阴等家族作为“股肱谋主”时,他还要照顾到这些家族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家家都“丰于钱货”。因此而论,索辅认为“宜复五铢”和张轨立制复五铢后“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里的“人”指的首先是地方豪族。
三
那么,究竟是何人在何时铸造了“凉造新泉”?“凉造新泉”的流通情况又如何呢?这是所有古钱收藏家、研究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首先,“凉造新泉”是五凉时期的一种钱币,这毋庸置疑。因为“凉”指的是凉政权,而不是指凉州。自汉及晋,凉州地方政府是无铸币权的。张轨作为西晋凉州刺史亦不例外。
诸凉政权出现在十六国时期,它们依次指张轨以后的前凉,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鲜卑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和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这五个凉政权中,前凉和北凉历时最长,完全拥有河西走廊。而后凉、南凉、西凉部历时短暂,只占有河西局部土地,并且经历着战争和内乱。它们铸钱的可能性不大,史书上也没有关于它们铸钱的记载,故可将它们排除在“凉造新泉”铸造者的行列之外。
前凉成为割据政权在317年西晋亡国以后,时去张轨病死已有四年。它成为割据政权,是因为西晋灭亡使它丧失了原为西晋凉州刺史部的名分和实质。尽管如此,张轨的儿子张塞、张茂等仍称凉州牧。由于“官非王命”,《晋书》以外的诸史,都称其为“私署”。既是“私署”,就可能私铸。然而张寔初期,西晋在长安的政权虽岌岌可危,却还存在。张寔也为“赴国难”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张茂时期,关中立国的前赵不断西侵,地方豪强又伺机捣乱,张茂忙于应付外忧内患。因此寔、茂弟兄同样以晋臣自居,也不可能铸钱。
前凉政权中最有可能铸钱的是张骏。张骏时,“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东)晋,而不行中兴之朔,舞六佾,置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焉耆、前部、于阗并遣使贡方物”(注:《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另外,张骏“性又贪惏”(注:《魏书》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传附张骏传》。),平生喜好西域宝货。后凉时期,有胡人安据盗发他的墓葬,“得真珠簏、琉璃梳、白玉樽、赤玉萧、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珍奇不可胜记。”(注:《晋书》卷122《吕光载记附吕纂载记》。)虽则如此,仍不能断言“凉造新泉”是张骏所铸。因为他毕竟尚未称王,另外史书中仍不见他铸钱的蛛丝马迹。有人认为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的“太元货泉”“殆张骏造”(注:朱活《古钱新典》第229页。),只是一家之言。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太元为年号的三位统治者,一是吴大帝孙权,二是前凉张骏,三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其中只有张骏未冠以“帝”或“王”字样。既非帝又非王,何来年号。张骏的“太元元年”当是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324年)。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死于此前一年。这时张骏仍用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太宁元年,骏犹称建兴十二年”(注:《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是时,张骏又开始建立与东晋的君臣关系。“寻,承元帝崩问,骏大临三日”(注:《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长史氾祎当时以黄龙见于揟次嘉泉之兆劝他改年号,被他拒绝。这事在《晋书》、《资治通鉴》中记载得清清楚楚。惟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在东晋太宁二年条上为张骏系上一个太元元年。而仅据太元这一年号就说出土于内蒙的“太元货泉”是张骏所铸,太难使人认可。与此相类,说有一种叫“太清丰乐”的钱是前凉最后一个统治者张天锡所铸,也系妄下断语。
舍去前凉来说,“凉造新泉”极有可能是北凉所铸。
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族属是匈奴卢水胡,他与石勒同属于胡羯,并且都是胡羯中的雄略之主。412年,沮渠蒙逊灭南凉,建都于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玄始十年,他相继攻破酒泉和敦煌,灭掉西凉,统一了河西走廊。他称王33年,将王位传给其子沮渠牧健。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政通人和,经济稳定,与西域关系密切。他对外实行权变政策,先后权变性地称藩于后秦、北魏、刘宋。他不像前凉张氏是从晋王朝官僚体系中派生出来的那样,不敢越雷池一步。从理论上说他极有可能是“凉造新泉”的铸造者。此前,已有出版物将“凉造新泉”断为北凉沮渠蒙逊永安年间造(注: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编,刘巨成主编《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但未论述其根据。笔者同意沮渠蒙逊是“凉造新泉”主人的说法,但对具体事类要略作补充。
补充之一是关于沮渠蒙逊铸钱所需铜料来源:
先,酒泉南有铜鉈出,言虏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卷2《天部下·雪》,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23页。又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民国26年版,第665页。)文中“铜鉈”在《初学记》和《太平御览》中写作“铜駞”。以意忖之,“铜鉈”或“铜駞”当是驼状的自然铜。酒泉南是祁连山脉。今天,这里仍是矿产资源很丰富的地段。一千五百多年前能开采出自然铜,似不应怀疑。
补充之二是蒙逊玄始二年与钱币有关之事:
蒙逊母车氏疾笃,蒙逊升南景门,散钱以赐百姓。(注:《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
蒙逊散钱,一为其母祈福,二来因此前发生了旱灾。他散的钱是否就是新铸造的“凉造新泉”?如果是,则“凉造新泉”可能成钱于玄始初,即公元412年左右。另外还可能是蒙逊为其母车氏祈福或为禳旱所铸。如果这样,那它不是实用钱币,是用于厌胜驱邪的钱币。但是已发现的“凉造新泉”有两种币面,一种直径1.8厘米,重1.5克,一种直径2.06厘米,重2.3克。这又不好解释。就这两种钱的重量而言都达不到汉武帝时五铢钱的重量标准,即3.5克。(注:“凉造新泉”的两种币面及汉武五铢钱的标准重量之说分别见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和第228页。)即使它真是用于流通的钱,它的信用程度也不会高。信用既不高,流通起来就困难。迄今为止现身的“凉造新泉”为数不多,并且除西安一枚外,其余都出土于古姑臧所在的今武威市。甚至在河西走廊其他地方也杳无踪迹。当然,这除说明它发行量小,流通不广之外,反过来又说明它具有的古币收藏价值。
综上所论,此前古钱币专家和一些史学家主张的张轨铸钱说存有讹误。将张轨“复五铢”的举措与发现“凉造新泉”联系起来,更缺乏根据。张轨时期的凉州,仍是西晋的天下,作为“西晋名臣”,他不可能僭越到石勒那样的地步。所以张轨与“凉造新泉”沾不上边。张轨之所以能在河西恢复货币经济,一是他注意到了汉以来五铢钱具有的信用价值,二是他适应了河西走廊潜在的货币环境。他的举措仅限于恢复五铢钱流通。这里的“复”是相对于此前的“罢”和“不行”而言。这一“复”既启动了货币市场,又改变了“货滞物留”的现象,同时又避免了石勒那样新的通货膨胀。正是这样,张轨复五铢的举措才对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内外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外,“凉造新泉”很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它发行量不大,流通范围不广,却很有收藏价值。
[收稿日期]2004-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