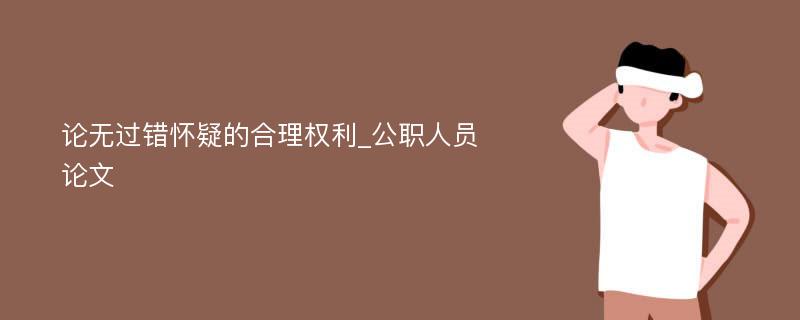
也谈无过错的合理怀疑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无过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底,深圳市有关部门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的一个条文引起了学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该条文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此我就媒体的怀疑权也来谈谈粗浅的看法,并求教于各位同仁专家。
一、怀疑权的内涵及意义
《条例》没有规定怀疑权的涵义,依据笔者的理解,怀疑权是媒体享有的对公职人员或者社会知名人士的行为(《条例》特指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不信任表达的权利,其实质是一种监督权。怀疑权在各国的新闻立法中鲜有表述,但西方传统的新闻自由价值体系通常包括,或者说隐含了这个权利,如媒体的“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在我国,怀疑权也有若干法律上的渊源,如《宪法》第35条所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第41条赋予公民的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等。可以说,怀疑权就是这些宪法性权利的具体化或者说落实。
此前,虽然我们都认同媒体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但是另一方面也认为,媒体只有在获得“事实”后才可以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报道和评价,否则会引来侵权诉讼。而怀疑权支持媒体预先介入未明确的事实,甚能提升媒体监督的信心和力度。同时,怀疑权的社会意义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怀疑权是促进政务公开的具体措施之一。在政府运行和活动的范围有了巨大扩张的情况下,政府有能力掩盖其本身的某些犯罪和渎职行为,而媒体的发展及其灵活性、主观能动性能够发现和报道行政部门的某些秘密的不法行为。(注: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刘丽君译:《自由的法》第2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在媒体获得怀疑权的条件下,公务人员的不公开行为会备受媒体的责问和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及官员工作的透明度,促使政府和官员接受更广泛的群众监督和社会评价。因此,怀疑权对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促进依法行政、民主政治建设及政府廉政建设有重要意义。
其次,怀疑权也是权力监督体制的创新。“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已经在起作用,但是还未获得人们所期望的以及她本身应达到的效果,具体的表现为监督滞后、监督虚设和监督乏力”(注:李交发等:《法治建设论》第1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在公权力监督系统强化的同时,也要在创新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媒体对权力监督的能量,对此赋予媒体怀疑权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美国,除去其媒体热衷煽情的成分,我们得肯定一个事实:即媒体监督是维护现代民主不可或缺的力量,或者说其就是在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之外的第四种力量。我国也很重视媒体的监督作用,党和政府的文件,都要求强化对政府及官员的舆论监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十六大辅导读本》第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为便于人民群众知情和监督,要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怀疑权既是现有监督体制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一种创新,使它能进一步发挥媒体监督政务及官员的作用。
二、怀疑权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条例》确定媒体的合理怀疑权,确实是一个突破。但就总体而言,在作用范围及操作性方面,《条例》上的怀疑权还存在诸多的欠缺。这种作用范围的有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一方面,怀疑权的对象范围有限。《条例》仅仅是待通过的一个地方性法律文件,即使通过,也只在特定地域发挥作用。同时依据《条例》,合理怀疑权行使的环境是预防公职职务犯罪,即这种媒体的合理怀疑权只能发生在公职人员身上。这对加强公职人员的监督有一定作用。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媒体应当更广泛地对民众知情权负责。注意到民众感兴趣的监督对象范围很广泛(除了公职人员以外,还包括非公职人员,如明星、其他知名的社会人士等),笔者认为,为了满足民众知情权的需要,立法机关应进一步扩展怀疑权的适用对象范围。
另一方面,怀疑权适用的事实范围也受到了限制。根据《条例》,赋予媒体怀疑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预防职务犯罪,加强媒体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但是,媒体报道目的更多的情况下是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其不是在预防犯罪时才合理地出现在监督位置上。这种信息所包容的目的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承认预防犯罪过程中的合理怀疑权,那么对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达到犯罪、可能是一般性的违法事实或者工作失误是否可以怀疑?同时,特别注意到媒体不是司法机关,其如何判断公职人员是否涉嫌犯罪?当然,由于立法权限的规定,对上述的分析,我们无法求全责备于深圳市有关立法部门,关键是相关国家立法部门要认识到这种立法的紧迫性,以出台适用于全国的统一的更具操作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使这种“阳光”不仅仅是照耀在深圳市的上空。
其二,囿于现有制度,即使是对公职人员,合理怀疑权的监督作用也可能有限。在我国,新闻出版管理的基本制度包括出版许可制度(即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经过国家的出版管理行政机关的批准才可进行出版活动,包括创办活动、出版中的变更事项等)、主管主办单位制(每一个媒体都有其主管的部门)、属地管理制度(即由媒体所在地的新闻出版部门对其实行监督管理)等制度。根据上述制度,对媒体主管部门,媒体的监督作用能够发挥到何种程度值得考虑。更重要的是,国有性质的媒体除了受到归口管理外,其还接受当地的其他方面如党委、政府部门的管理。如根据媒体发布新闻的惯例,在报道涉及政府部门的新闻时,存在党政领导审稿这一个程序;很多情况下,媒体的报道是在得到相关部门或领导的支持后才能进行。这使得媒体与被监督对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体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不得不考虑这种无法割断的联系。根据上述分析,在获得合理怀疑权以后,媒体能否有力地对《条例》里所提及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以预防犯罪,这是值得怀疑的。在上述制度的条件下,媒体在无确切证据时,是难以大胆行使合理怀疑权的,相反只会选择回避。
由此看来,合理怀疑权的设置并不能保证媒体监督适时地到位,这种缺位不仅仅是媒体的失职,其与现行媒体的管理制度有很大的联系。对此,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理顺媒体和主管部门的关系,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重新配置媒体监督的权利和当地政府主管权力。这不是说媒体不需要来自政府的监管,实际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媒体都受到来自政府的监督。笔者想说明的是,媒体肩负着舆论监督、传递真实信息的社会责任,理应具备一种超然于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力量。媒体负责的对象是拥有知情权的民众,而非主管部门等职能机关。因此,须进一步强化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以满足民众知情权为价值导向来构建主管部门与媒体关系。在媒体行使合理怀疑权时,其应当被视为对民众知情权的负责,而不是其他。唯有如此,媒体怀疑权才可以起到更实在的作用。
三、怀疑权具体适用的条件
怀疑权和其他权利一样,也是相对的,即适用是有条件的。明确条件是怀疑权获得可操作性的前提。条件的确定必须建立在调和承载个人利益的官员名誉权和承载社会大众利益的媒体采访权(这里特指怀疑权)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只有这样,在操作过程中才可避免由于媒体主观认识的差异性而带来的权利滥用的可能性,也可以解决怀疑权行使后所带来的纠纷问题。但是,注意到怀疑权出现在公共领域,为公共利益服务,因此对其限制的定位不宜太严。依据《条例》规定,媒体怀疑权行使的前提有两个。
1.合理问题
《条例》规定怀疑权行使必须合理。至于“合理”的衡量标准,《条例》相关条文并没有确定。这降低了怀疑权的可操作性。“法律规则都具有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则它难以被反复适用,没有确定性就难以保障法的稳定与安全”,虽然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是相对的,但是,“立法者不得依此为由追求法律的不确定、追求‘粗’,立法者应当追求法律规则的最大限度的确定性”。(注: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71页、第9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是对媒体,还是基于立法者监督公职人员的目的,“合理”的标准应当是在条文基础上可以判断的。标准没有确定,媒体无法利用这种权利去监督官员,《条例》的美好设想也难以实现。
“合理”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媒体基于公正的立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收集大量资料而形成的报道可视为达到了合理的标准。应明确的是,这个标准不是绝对的。因为这种怀疑权本身就是对未明确事实的一种怀疑,其内容应当允许与客观事实有偏差。绝不可将与事实有差距的报道定性为不合理。新闻的时效性、记者调查手段的有限性决定了新闻上的事实只是接近客观真实的事实。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梅里尔(John·C·Merril)说,“客观报道应该在实际上符合现实,它应该揭示事实——全的事实、纯粹的事实。我们找得到这样的报道吗?没有记者知道真相,没有记者可以写出符合事实的报道。……换句话说,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事实本身,事实总比字面所描述的广阔得多”(注:(美)埃弗利特·E·丹尼斯等著、王伟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第10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另一个方面,基于怀疑产生的报道很有可能与事实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也即媒体怀疑权客观上确有可能给官员个人声誉带来影响甚至损害等。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是否允许新闻相对人以诽谤为由诉请赔偿呢?这涉及怀疑权行使有无过错的问题。
2.过错问题
根据现代侵权的问责规则,在一般性的领域,追究责任不但要参考损害事实,还要考虑过错。对此,《条例》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即媒体的怀疑权应当在无过错的条件下进行,媒体主观上无过错的,受到怀疑的相对人不可提出这种赔偿请求。那么,又如何判断媒体的过错呢?根据一般的法理原则,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和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失实侵权,下同),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这种结果能发生的心理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无过错怀疑权应当在无故意和无过失的状态下进行呢?
笔者认为,行使怀疑权监督公职人物,不但要适用过错归责的原则,而且这种过错应当视为不包括过失。其理由如下:
其一,怀疑权是社会性权利,其作用的领域具有公共利益的关联性。怀疑权的价值目标非个体利益,而是公共利益,即满足民众对公共领域事务及相关人士活动知情权的需要。现代社会里,虽然存在很多监督机制,但民众更相信自由竞争下的媒体监督,且媒体传达的消息更及时、易得。故将怀疑权视为媒体的权利,不如说是媒体利用这种权利或自由对社会负责,对民众在行使告知的义务。其二,如果对媒体责备求全,要求怀疑权的行使不可存在过失,一律要求发现“真实”后才可以报道,媒体的监督不但会来得很迟,而且更可能产生“寒蝉效应”,即媒体会惧于对私人(此主要指公职人员)承担责任的成本,进而惧于发表言论,使媒体沉默。这不但有损于社会信息的自由流通,也会给社会民主带来伤害。其三,公职人员的行为应当更具有透明性,允许民众和媒体进行无恶意的评价。因为政务透明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标志之一,政务官员的活动及行为理应接受来自各方面更多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其四,在媒体报道被证实与客观有较大的差距以后,公职人员还可以行使更正请求权、答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确,“过失”不可以成为官员索赔的理由。那么,是否可以推断“故意”可成为官员索赔的理由呢?有些学者认为,权利滥用的主观要件之一就是权利人存在损人利己的故意。(注: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71页、第9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里我们还是要借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沙利文诉纽约时报”判例确立“确有恶意”的规则。该规则认为:出于宪法保障的自由,法律不允许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行为受到诽谤而得到赔偿,除非他能够证明言论的发表者“确有恶意”。“确有恶意”是明知所述情况虚假而根本不问事情是否属实。承办本案的大法官布伦南认为,因为疏忽而未能发现与事实不符的报道,并不可代表媒体根本不问事实。判决(指“沙利文诉纽约时报”一案的判决)媒体胜诉的原因是因为新闻相对人是公职人员,如果对政府非恶意的批评有可能受到惩罚,则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精髓会受到冲击。引进美国判例法上的“确有恶意”规则作为过错认定标准,我国媒体才可以真正行使怀疑权,获得监督公职人员的“尚方宝剑”。因为证明媒体有主观上的真实恶意,是很难做到的事。也就是说,官员对事关自己的媒体怀疑权的行使有异议,其必须要举证证明媒体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即明知情况虚假而进行报道,或者证明媒体的报道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如打击报复),而不是为了监督的目的。
除了“实际恶意”规则外,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应推定媒体无过错。如媒体根据社会民众的反映就某件涉及职务犯罪的情况进行采访,而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被当事人或当事机关拒绝。在此种情况下,媒体的任何怀疑或预测应当被视为合理,无过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采访的当事机关本有责任对事情作出澄清而其没有履行职责。
怀疑权作为新闻自由价值中的含义之一,其有效的适用将有助于我国的廉政建设,并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但是,基于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可操作性,怀疑权还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我国相关的配套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