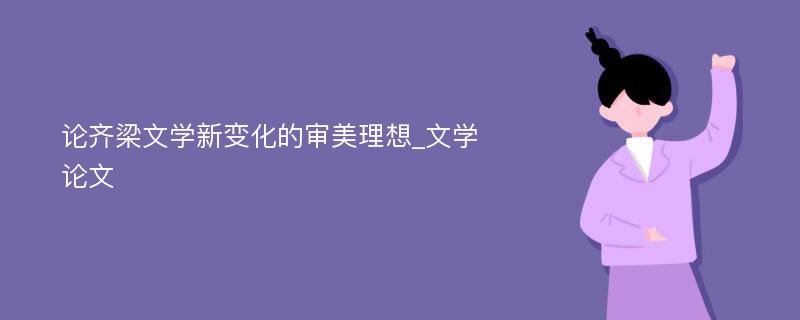
论齐梁文学新变的审美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梁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齐文论家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感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
显然,萧子显是将“不相祖述”作为文学新变的基本条件。结合前后文的论述来看,萧子显之所以提出“不相祖述”的说法,其直接目的就在于要扬弃上一阶段的文学——刘宋文学,来实现当时文学的新变。因此,尽管萧子显于对刘宋文学也不无称赏,但接下又对刘宋文学的“三体”做了一番不无贬意的分析: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萧子显的评析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谢灵运的诗歌,虽然颇有闲逸清丽的风致,但其铺写风物,“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白居易《读谢灵运诗》),确实也造成了“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钟嵘《诗品》上)的毛病。由于他是为了“避世”而遨游山水,以及借山水描写来阐发玄理,因此,其山水诗中,便往往体现出自鸣清高、超群脱俗的雅兴。这就是“典正可采,酷不入情”的缘由。“缉事比类,非对不发”的第二体,当是指颜延之诗。颜诗的用典对偶,虽然也对诗歌的发展有所贡献,但典事过繁,偶对过拘,确实也“颇失清采”、了无生气;而这种表现多见于其廊庙体诗,虽称典雅,亦显板滞。第三体即“发唱惊挺”的鲍照诗,鲍诗多写世事俗情,与复杂的情感相配合,且多用险词浓彩。在齐梁文人看来,这又显得“险急”“淫艳”,以致趋向“险俗”一途而“伤清雅之调”(《诗品》中)。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萧子显又提出了他要求扬弃“三体”而新变的诗歌理想模式:
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即是要求革除用典过繁、文藻过缛的风气,作到易读易懂;“吐石含金,滋润婉切”,则是强调诗歌声律婉转的美感,这也正是齐梁文人所一致重视的;“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即溶合民歌风谣的创作特点,以加强诗歌音调的轻快流利。做到这几方面,便可达到“不雅不俗”的目的。可以说,“不雅不俗”,就是萧子显对新的诗歌模式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新变”的审美理想。这里的“雅”,既指谢、颜诗“酷不入情”、“顿失清采”的“典正”之雅,也可指文人诗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博奥典雅诗风。这种诗风,在刘宋诗,尤其是颜延之的廊庙体诗中表现最为充分。萧子显主张“不雅”,就是要求突破传统雅文学的规范以求新变。这里的“俗”,既指鲍诗的“险俗”,也可指民歌风谣的土俗。所谓“不俗”,就是要求避免流于过分的俗气,以致“伤清雅之调”。萧子显主张“不俗”,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排斥“雅”。从更深一层理解,就是萧子显的新变审美理想,并没有截然割断和“雅文学”的联系。
本来,文学艺术由粗糙到精巧的演变,就是一个不断“雅化”的发展过程。虽然过于求雅会产生“板滞”的流弊,但是雅文学的成就——尤其是艺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因此,尽管萧子显宣称“不相祖述”,但在文末的“赞曰”中也说:“学亚生知,多识前仁。文成笔下,芬藻丽春。”所谓“多识前仁”,就是要求继承、学习前人雅文学中的优良传统(尤其是艺术精华),这样才能创作出“芬藻丽春”的作品。照此看来,“不相祖述”的意思,应理解为反对亦步亦趋和食古不化。是呼应上文“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新变思想而说的。也就是在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上,要求突破前人的框框而创新求变。“不相祖述”与“多识前仁”并不矛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前者,文学就不能发展;而没有后者,文学的发展便成无源之流。这就是“不雅不俗”审美理想的更深一层含义。
这种“不雅不俗”的文学主张,在以往的文论中似乎未曾见过,齐梁文人却频频有此说。除萧子显外,刘勰便认为“通变”要达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萧统则认为理想的文学作品要“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群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丽”趋俗,“典”近雅;“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即不雅不俗,适得其中。范云对何逊的评价,也体现出“不雅不俗”的主张:“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梁书·何逊传》引)
齐梁文人之所以反复强调“不雅不俗”,就因为齐梁文学正处于“雅俗沿革之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的重要关头。尚“俗”,在当时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是一股势头愈来愈猛的风气。这股风气,对当时文坛以及文学新变,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与论述。
南朝的许多帝王都出自寒门,他们为了巩固其新政权,不断加强与提高寒士阶级的政治地位。唐长孺曾论述当时的情形:“宋齐时期,大量寒门地主挤入士族行列,‘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在底层形成‘士庶不分’的情况(《通典》卷三《乡党》载沈约上言)。这是自宋以来几十年寒门地主长期斗争包括流血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尽管在社会上、政治上他们仍受到高门甲族的歧视,但无论如何,在地方上他们取得士族身分,特别是取得了免役特权,这是真正的胜利。”(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7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然而,这些寒门新贵们的文化素养毕竟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有一定的差距,其生活情趣以至审美情趣也并不如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么“高雅”。齐郁林王就居然认为做“天王”“不如作市井屠沽富儿百倍矣”(《建安实录》卷十五),并在“丹屏之北,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开桑中之肆”(《南齐书·郁林王纪》),在宫苑中干起屠沽酒肆的勾当以为乐。不少南朝帝王公侯亦有此举,如宋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宋书·少帝纪》),齐东昏侯“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南史·齐废帝东错侯纪》)。宫廷御苑之中,充斥着市井俗侩的气息。正是由于上层统治者有这样的尚俗情趣,吴歌、西曲等表现市井风情的民歌,也在刘宋之后大量地涌入了宫廷贵族的生活圈子。
南朝时,长江流域的建康、扬州、江陵、襄阳等城市,凭藉着水上交通的便利条件,促成了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由此而产生了全新的市井文学——南朝民歌:“《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那呵滩》)多叙江陵及扬州事。”(皆见于《古今乐录》)“南朝文物为最盛,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南朝的帝王在尚未发迹时,就已十分熟悉并喜爱这些民歌风谣,登基后更亲为拟作。例如,《古今乐录》载:“(齐武)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即《估客乐》)。”又如,梁武帝(萧衍)在齐时代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但他的文学趣味与竟陵王(萧子良)并非完全一致,竟陵王兴趣主要在文学的规范化方面,梁武帝则对南方时尚的乐府民歌尤其钟情。据《隋书·乐志》中的记载,梁武帝早年在襄阳,便很欣赏当地的童谣《襄阳白铜蹄》,“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
在正统文人眼中,南朝民歌“多淫哇不典正”(《宋书·乐志》)。但在帝王们的倡导下,南朝诗坛兴起了拟作“淫哇”民歌的热潮,以致“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史·萧惠基传》)。“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南齐书·王僧虔传》)。尚俗,成为当时诗坛上引人注目的创作倾向。这些“谣俗”之作(包括民歌及文人拟作),内容多是儿女私情,形式上则“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这与传统的雅文学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因此被时人视为“新声”。可见,尚俗的创作风气,也是当时文坛新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故清代纪昀说,齐梁诗文是“求新于俗尚之中”(评《文心雕龙·通变》语)。
萧子显排斥颜、谢的言论,正是“尚俗”时风的产物。“险俗”的鲍诗虽然也颇受齐梁人非议,但在诗歌创作实际中,鲍诗之“俗”,却对齐梁文人影响很大。齐梁文坛的著名领袖,也是永明新变的主要倡导人沈约,就在其诗歌创作中表现出“宪章鲍明远”的倾向。钟嵘在《诗品》中评沈约云“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所谓“不闲于经纶”,即不熟习经纶典正之作;“长于清怨”,即擅长抒写清怨俗情。说沈约“不闲于经纶”,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说沈诗“长于清怨”,倒很恰当。沈约曾称许鲍照“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宋书·鲍照传》)。清人贺贻孙也说:“明远与颜、谢同时,而能独运灵腕,尽脱颜、谢之板滞之习。”(《诗筏》)鲍照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诗创作方面,而鲍照的乐府诗,正是以世情的抒发、灵变的手法、险俗的风貌尽脱典正的“板滞之习”。沈约也写过不少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其他不少诗作,也主要是在清怨世情的抒发与流丽灵变的笔法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鲍诗之“俗”。
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四、五言体的消长,以及人们的评价,也体现出六朝文学雅俗观的演变。自建安“王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以来,五言体诗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流。但在两晋时期,又重新兴起一股推崇四言体的风气。四言体是被作为“雅音”而受到推崇的:“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文章流别论》)四言为《诗经》的主要体裁,其节奏持平舒缓,颇有典正之风。汉儒奉《诗经》为经典之一,四言也就被视为高雅典正之体了。汉武帝时,用于帝王祭祀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八首为纯正的四言体,由此可见尊崇四言的倾向;但另有六首为三言体,三首为五七杂言体,二首为四、七杂言体,也显示四言体并未占绝对的优势。建安时的朝庙类歌辞,除了王粲的《太庙颂》为纯四言外,其他如《俞儿舞歌五首》(王粲)、《魏鼓吹曲十二首》(缪袭)多有杂言,曹植的《鼙舞歌五首》则为五言体,可见四言体的地位,在“王言腾踊”的建安文坛已大受冲击。西晋时期,奉名教为正统的司马氏重倡儒学。与之相适应,晋初傅玄、荀勖、张华等受诏撰写的正典朝会所用的郊庙歌辞与燕射歌辞,绝大多数是采用四言体。这些歌辞,皆以“雅”见称:“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雅音之韵,四言为正”的思想,正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虽然五言是西晋诗的主流,但四言体的创作却较之建安大为增长。除了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之外,西晋文坛流行的应诏、应令一类诗,也大多是四言。有人还刻意模仿《诗经》作《补亡诗》(束皙)、《周诗》(夏侯湛)等。其他内容的诗,也常用四言诗。陆云的现存诗,大多是四言。挚虞存诗五首,全是四言。可见,尽管五言在西晋诗坛已占优势,但四言仍作为雅音正体而得到并行不悖地发展。刘宋颜延之、王韶之等人的廊庙体诗,便是晋代四言雅音的嗣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刘勰称四言诗为“正体”而五言诗为“流调”,显然是继承了挚虞“四言为正”的说法。但从后面的论述看,刘勰对四、五言的地位是不分轩轾的。“流调”即变调。变体,这是相对“四言正体”而言的;从历史根源看,五言体则是从民歌俗谣流变而来。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就深受汉乐府中的五言体影响。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文人大量拟作乐府民歌(这些拟作也大多为五言体),民间歌谣之俗风再次深刻影响了文人的诗歌创作(其影响更集中在五言诗)。因此可以说,所谓“流调”,也就是俗风的流衍。刘勰将这种跟民歌俗风关系密切的五言流调,提到与四言正体平等的地位,其实就表明他对尚俗风气的肯定态度。刘勰虽然曾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将典雅与宗经联系起来:“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但《明诗》中的“雅润”,却是具有审美的意义的。“雅润”即典雅而有文采润饰。刘勰以张衡(平子)和嵇康(叔夜)的诗为例证:“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张衡现存诗有《怨篇》(四言)、《同声歌》(五言)和《四愁诗》(七言)。刘勰称张衡四言诗“雅”,当是指《怨篇》。在《明诗》中,刘勰也恰好提到:“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清典可味”,显然是审美意义上的评语。嵇康诗以四言为主,而嵇康的四言诗,更是以文采润饰为著。可见,刘勰所说的四言正体之“雅润”,是从审美角度而言,与宗经无关。
晋人对“雅”与“丽”是有区别的。《晋书·傅咸传》云:“(咸)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颖川庚纯常叹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诗人之作”即是雅正之作,尽管“绮丽不足”,只要“言成规鉴”,便可因其雅正而受赞赏。陆机《文赋》称“雅而不艳”为一病,也是将雅与艳(丽)分论,但已表现出要求雅丽兼融的倾向。刘勰将四言正体之“雅润”与五言流调之“清丽”并举,虽然也有雅、丽区别之义,但“兼善则子建、仲宣”的例证,则体现出他要求雅、丽兼善——即“不雅不俗”的审美理想。
与刘勰相比,钟嵘明显表现出抑四言而扬五言的倾向。他在《诗品》中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钟嵘的评述,倒也道出了当时诗坛的实情。齐梁之时,四言诗的创作大为消减,而五言诗的声势愈为壮大,并“会于流俗”——深受世人的喜爱。而南朝文人向民歌学习的热潮,又使五言诗的创作更具“尚俗”的倾向。钟嵘将“会于流俗”的五言诗奉为“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在评价诗人时,也屡屡称誉“(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鲍行卿)甚擅风谣之美”,足见其对“俗”风的肯定态度。当然,五言诗创作也有“雅”的表现,而钟嵘也并不排斥“雅”。其《诗品》论诗人,就常常涉及“雅”。如:
(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应璩)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颜延之)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
(鲍照)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
(曹彪、徐干)亦能闲雅矣。
(谢庄)气候清雅。
(张欣泰、范缜)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
从上面评论中,可概括出钟嵘的雅俗观:一、赞许“雅”,反对过份的“峻切”、“危仄”和“俗制”,以免“伤雅”、“失雅”。二、钟嵘所赞许的“雅”的内涵,主要是“情兼雅怨”、“体裁绮密,情喻渊深”、“赏心流亮”等具有艺术、审美意义的“雅”。三、纯以“雅”入品的诗人,除应璩、颜延之在中品外,其余皆在下品。而嵇康、鲍照“伤雅”,仍可居中品。反观上品诗人,则多以“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陆机)、“烂若舒锦,无处不佳”(潘岳)、“调彩葱菁,音韵铿锵”(张协)的流调清丽本色而入品。可见,钟嵘虽然给“雅”保留了一席地位,但“雅正”的品位,远不如“俗丽”的品位。四、钟嵘称曹植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正是雅俗兼善的表现。钟嵘对此评价甚高:“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雅俗兼善——即不雅不俗的诗风,也正是钟嵘的诗美理想。
总的来说,自刘宋到齐梁,是南朝文坛由雅趋俗、雅俗沿革的重要阶段。齐梁文人主张“不雅”,表明他们对“趋俗”“尚俗”风气的认可;但他们又主张“不俗”,则表明他们不希望溺俗而不返。即要求“俗”而有度,“趋俗”而又要有所制约。说到底就是在“趋俗”时,又要保留“雅”的地位,以“雅”制“俗”,雅俗兼融。
那么,齐梁文人又是如何以“雅”制“俗”的呢?依我之见,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以儒学礼教的典正来制约俗情的泛滥;其二,以艺术审美的文雅来要求形式的表现。
魏晋以来,儒学虽然没有完全消歇,但它对社会(包括文坛)的影响,一直是很微弱的。到了南朝,儒学才又重新得到重视。刘宋时期,儒学与文学等同时被立为官学,显示了儒学思想的再次抬头。在齐代,辅助齐高帝萧道成受禅登基的,就是一代儒宗王俭。在王俭等人的力倡下,儒学进一步兴盛起来。在整个南朝,儒学最兴盛的时期是在梁代。最积极的儒学提倡者,便是著名的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经学》云:“《陈书·儒林传序》亦谓梁武开五馆、建国学、置博士,以五经教授。帝每临幸,亲自试胄,故极一时之盛……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此南朝经学之极盛也。”佞佛的梁武帝,在统治思想上却以儒学为宗,其《立学诏》便明确地将儒学奉为建国立身的根本。天监四年(505), 梁武帝在下诏置五经博士时更宣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附,抑此之由。”(《梁书·儒林传序》)梁武帝严厉批评“魏晋浮荡,儒教沦歇”,这是魏晋以来少见的论调。他推崇汉儒“服膺雅道”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理论与创作。裴子野就径直把“服膺雅道”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准则。他在《雕虫论》中,主张为诗应“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基于这个准则,他严厉地抨击了当时弃雅尚俗的文坛风气:“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裴子野在梁武帝时任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史书称他“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梁书·裴子野传》)。可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裴子野都是一个极端的崇雅斥俗派。裴子野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的利益,但在文学本身发展早已突破了诗教樊篱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助于文学的进步与繁荣。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则采取折衷的方法。刘勰虽然也提出“原道”、“宗经”等“服膺雅道”的原则,但同时也极为重视“情采”、“声律”等艺术形式美。折衷的思想方法,也体现于刘勰的“通变”观,而在“通变”观中,也正体现出他对雅俗的态度。在《通变》篇中,刘勰分析了文坛“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趋俗风气。对这种风气,刘勰是不满的。因此他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也就是以“还宗经诰”(即“服膺雅道”)来矫正“讹”“浅”(即“俗”)的时风。正如他在《定势》篇中所说的“执正以驭奇”。同时,也要求从雅文学中汲取营养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创发“新意”,雕饰“奇辞”:“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可见,刘勰并没有象裴子野那样极端地返雅弃俗,而是主张“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通变》)。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通变”。萧统的观点跟刘勰相似。他既推许“风雅之道”,又欣赏“为入耳之娱”、“为悦目之玩”的美文(《文选序》)。在“雅”与“俗”的关系上,萧统则认为“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远兼邃右,傍暨典坟;旁以聚益,居焉可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这无疑就是以雅制俗、雅俗兼美的主张。梁简文帝萧纲与其弟湘东王萧绎,既是皇族,又是诗人及文论家。他们对儒学与文学关系的看法,较之梁武帝萧衍、刘勰及萧统等人,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萧纲的思想显然也深受儒学的影响,其《幽絷题壁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非欺暗室,岂沉三光。”颇有儒家推崇的君子慎独之气概。然而,在“立身”与“为文”的问题上,他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便是他惊世骇俗的宣言。立身谨重,颇见服膺雅道之心;文章放荡,又足显尚好俗风之趣了。二者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更清楚地表述了将儒学与文学区别对待的用意:
若夫六典之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慕《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在此,萧纲明确地将儒学与文学区别开来,首先,他认为儒家经典法则的施行和运用有一定的场所和范围,文学不应该包括在内;其次,认为文学创作不必模拟儒家经典;再者,认为文学的本质不是宗经述圣,而是有其“吟咏情性”、“操笔写志”的特性。萧纲所谓的情与志,恰恰又是与诗教大相径庭的俗情逸志:“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玩飞花之入户,看斜晖之广寮,虽复玉觞浮碗,赵瑟含娇,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长谣。”(《闲愁赋》)当然,萧纲也并没有完全弃雅,他曾说:“又若为诗,则多须见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详其去取,然后丽辞方吐,逸韵乃生。”(《劝医论》)所谓“或古或今,或雅或俗”,便是亦雅亦俗。这就给“雅”保留了一席地位。但这种保留,只不过是存雅趋俗的表现,他所强调的仍是丽辞逸韵的俗尚诗风。他认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的裴子野“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与湘东王书》),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也是将儒学与文学分而论之。文中说:“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即认为文学家不必以儒学名家,只须在“文”的方面穷究奥妙便可;其对“文”的界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也正是齐梁尚俗文学的典型表现特征。萧纲、萧绎兄弟将儒学与文学区分开来。进一步强调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的怡情审美特征。这么一来,雅道与文学的关系也进一步疏远了。刘勰等人的“以雅制俗”,到了萧纲兄弟那里,已潜变成为“存雅趋俗”,这个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宫体诗的产生。这正是史书所说的:“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隋书·文学传序》)
在齐梁文坛的雅俗沿革演变中,无论“以雅制俗”派(暂且以“派”称之),或“存雅趋俗”派,有几个方面的表现却是基本相似。其一,在思想上,他们都可以说是服膺雅道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这种思想使他们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多少会有一定的制约或自我制约表现,以使文学创作不致于完全脱离雅道的规范,而沦入批评者所说的荒淫放荡、俗不可耐的地步。如梁武帝萧衍虽然拟作过不少风情民歌,但一旦得知宫体诗流行,却大为动怒,以五经大义严斥徐摛(见《梁书·徐摛传》);昭明太子萧统尽管欣赏“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诗文,却认为陶渊明唯一的“艳情”之作《闲情赋》为“白璧微瑕”(见《陶渊明集序》);即使后来的萧纲等宫体诗人,在宫体诗的创作中,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制能力,使宫体诗基本上能做到艳而不淫荡。其二,齐梁诗人虽然基本上都有服膺雅道的思想,但在诗歌创作中,却极少儒家学说的直接表述。如号称一代儒宗的王俭,在其现存诗中,仅《侍皇太子释奠宴诗》有儒学思想;而极端崇雅道斥俗风的裴子野,今存诗三首,也仅《答张贞成皋诗》有儒家的建功意识,其余两首(《咏雪》、《上朝值雪》)却是嘲风雪、弄花草的咏物诗。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给诗人们留下了更大、更自由的艺术创作空间。其三,虽然齐梁文人大都有拟仿民歌风谣之作,在创作手法与风格上受民歌的影响,但他们却能发挥其本身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优势,在语言、修辞、声律等艺术形式上对民歌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从而形成比民歌更为工巧雅丽的文人诗歌创作风貌。齐梁新体诗的“不俗”,很大程度就体现于这种工巧雅丽的诗歌艺术风貌。
概言之,齐梁文人在思想上服膺雅道,但在文学创作中,却与雅道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形成不即不离的状况;齐梁文人热衷于民歌风谣的欣赏与拟作,但同时也在艺术形式上自觉而积极的追求“雅文”。这些因素的综合,便构成了“不雅不俗”的文学新变审美理想,以及盛极一时的新体诗创作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