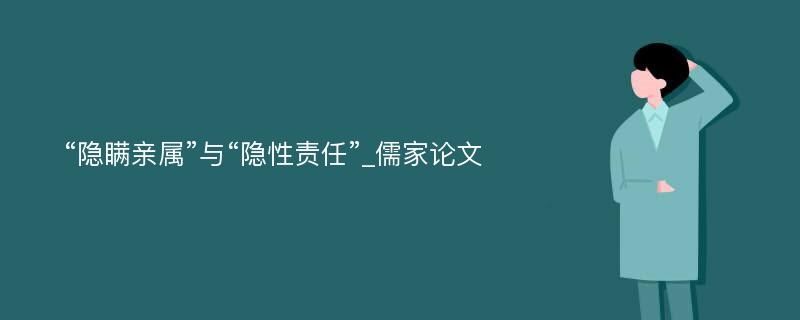
“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评价儒家伦理的讨论,涉及如何看待血缘亲情,以及孔孟等儒者是如何处理血缘亲情与仁义普遍原则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参见郭齐勇主编,2004年;2011年)对此,学者已发表了不少高见,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该次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其实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涉及与“亲亲相隐”相关的内容,为我们理解这一学术公案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拟结合新出土材料以及前人的讨论,对“亲亲相隐”尤其是儒家对于血缘亲情的态度和认识,作一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梳理。
一、《论语》的“直”与“直在其中”
有关“亲亲相隐”的一段文字见于《论语·子路》篇,其原文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面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尴尬局面,孔子的态度如何,其实是一个需要分析和说明的问题,这涉及对“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直”的理解。在《论语》中,“直”凡二十二见,是一个不为人重视但相对较为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也较为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微妙的差异。大致而言,“直”有直率、率真之意,也指公正、正直。前者是发于情,指情感的真实、真诚;后者是入于理,指社会的道义和原则。《论语》有时也称“直道”,而“直”就代表了这样一种由情及理的活动与过程。“直”与《论语》中仁、义等其他概念一样,是一个过程性、功能性概念,而非实体性概念。
在《论语》中,“直”有时是指直率、真实之意,如《论语·公冶长》说: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邻而与之。
邻人前来借醋,或如实相告家中没有,或向别人家借来以应乞者之求,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但后一种做法未免委曲做作,不够直率、坦诚,有沽名钓誉之嫌,故孔子认为不能算是“直”。这里的“直”主要不是指公正、正直,不涉及品质,而是涉及性情的流露,指坦率、实在。与此相对的是“狂而不直”(《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钱穆说:“狂者多爽直,狂是其病,爽直是其可取。凡人德性未醇,有其病,但同时亦有其可取。今则徒有病而更无可取,则其天性之美已丧,而徒成其恶。”(钱穆,第227页)又,《论语·阳货》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愚也直”的“直”指质朴、耿直,古代的人愚笨而纯朴、耿直,远胜于今人的愚蠢而狡诈。不过“愚也直”虽然有其质朴、真实的一面,但并非理想状态。所以仅仅有质朴、率直是不够的,还需经过学习的提升、礼乐的节文,使德性、行为上达、符合于义,否则便会有偏激、刻薄之嫌。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阳货》),又说“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绞”,急切、偏激之意。邢邴疏:“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学,则失于讥刺太切。”如果一味地率性而为,不注意性情的陶冶,难免会伤及他人,招人厌恶。故说“恶讦以为直者”(《阳货》)。“讦”,“攻人之阴私也”。(《玉篇·言部》)当面揭露别人的短处、阴私,似乎是率直、敢为的表现,其实是粗鲁、无礼,根本不能算是“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质直而好义”(《颜渊》),既有率真、真实的本性,又重视义道的节制,发乎情,止乎礼,这才是“达者”所应具有的品质。所以《论语》中的“直”也常常指恪守原则,公正、正直,实际是对“质直”的“直”(率真、率直)与“好义”的“义”(原则、道义)的结合,指“直道”。在《论语》中,“直道”凡二见: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
前一章中,“直道”与“枉道”相对,直道即公正、正直之道,也就是义道。浊乱之世,不容正直,以直道事人,自然见黜;以枉道事人,又非心之所愿。夫子以柳下惠为喻而感慨系之。后一章中,“斯民”指孔子所赞誉之民,也就是有仁德之民。以往学者释“斯民”为“三代之民” (刘宝楠:《论语正义》),或“今此之人也”(朱熹:《论语集注》),“即今世与吾同生之民”(钱穆,第441页),均不准确。其实《论语》中有一段文字,可与本章对读: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人”读为“仁”,指仁者;“罔”读为“妄”,指妄者,与仁者相对。①仁者生存于世,是因为公正、正直;狂妄者生存于世,则是因为侥幸而获免。所以,三代之所以“直道”流行,就是因为有这些以“直道”立身的“斯民”的缘故,正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综上所论,《论语》中的“直”在不同语境下,具体内涵有所不同,既指率真、率直,也指公正、正直,兼及情与理。而“直”作为一个德目,代表了由情及理的实践过程,亦称“直道”。“直”的这一特点,与早期儒家重视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密切相关。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云:“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第50简)如果是发自真情,即使有了过错也不可恶;如果没有真情,做到了难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可贵。可见情的重要!既然只讲情可能会导致过错,那么,正确的方式应是“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既发于情,又止于义(理)。“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第3、4简),做到情理的统一,这一过程就是道,故又说“道始于情”。《性自命出》反映的是孔子、早期儒家的思想,《论语》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孔子的“仁”既指“亲亲”,也指“泛爱众”(《学而》),仁道就代表了由孝亲到爱人的实践超越过程。“仁”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直”也是如此。
搞清了“直”的特点及其含义的微妙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亲亲相隐”章作出更为准确的解读。本章三次提到“直”——“直躬”、“吾党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但具体内涵有所不同。“直躬”之“直”主要是公正、正直,但“直躬”只讲理不讲情,故为孔子所不满。“吾党之直者”代表了孔子理想的“直”,兼及情与理,其“直”是指“直道”。关键在于“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的“直”,一般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公正、正直,于是,此句就是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是公正、正直的,或体现了一种正直。
笔者认为上述理解是不合适的。其实,这里的“直”是“直道”的具体表现,是率真、率直,而不是公正、正直。孔子的意思是说,面对亲人的过错,子女或父母本能、自然的反应往往是为其隐匿,而不是控告、揭发,这一率直、真实的感情就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相互隐匿中。故从人情出发,自然应亲亲相隐。孔子的这一表述,只是其对直躬“证父”的回应,而不是对“其父攘羊”整个事件的态度,不等于默认了“其父攘羊”的合理性,或对其有意回避,视而不见。因此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该章中虽然出现了三个“直”,但叶公、孔子所说的“直”的内涵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叶公是立足于“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来说“直”(庄耀郎),而孔子则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直”“不是法律是非、社会正义的含义”,而“与情感的真诚性有关”(李泽厚,第315页),是一种发诸情感,未经礼乐规范的率真、真实。这种“直”虽然为孔子所珍视,但并非最高理想,不是“直道”,还有待学习的陶冶、礼乐的节文进一步提升之,由情及理,上达“直道”。孔子对“直躬”的不满,主要在于其只讲理不讲情,而孔子则希望兼顾情感、理性两个方面。从率真、真实的情感出发,孔子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理性;但从公正、正义的理性出发,则必须要对“其父攘羊”作出回应。盖因自私有财产确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将禁止盗窃列入其道德律令之中,勿偷盗几乎是一种共识,孔子自然也不会例外。只不过由于情景化的表述形式,孔子点到即止,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出说明,结果留给后人一个谜团,引起种种争议。
二、“直道”的实现:“隐而任之”
幸运的是,孔子没有谈到的问题却在近年来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献中被涉及,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从维护公正的角度,孔子、早期儒家将会对“其父攘羊”之类的问题作出何种回应。2004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基本相同。据学者研究,《内礼》应是孔门嫡传曾子一派的作品,其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内礼》说:
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第6、8简)
面对父母的“不善”之行,《内礼》主张“止之”,具体讲,就是要谏诤。由此类推,对于“其父攘羊”,孔子一定也是主张谏诤的。如果说“隐”是一种率然而发的性情之真,是对亲情的保护的话,那么,“谏”则是审慎的理性思考,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在孔子、早期儒家看来,这二者实际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儒家虽然主张“事亲有隐而无犯”(《礼记·檀弓》),却一直把进谏作为事亲的一项重要内容。“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因此,我们不宜简单地说,儒家错误地夸大了血缘亲情的地位,为了血缘亲情就无原则地放弃了普遍准则。在重视血缘亲情的同时,儒家对于是非、原则依然予以关注,依然主张通过谏诤来维护社会正义。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对于谏诤的态度呈不断强化的趋势。在《论语》中,只说“几谏”,“几”,微也。“微谏”,即微言讽谏。在成书于曾子一派的《孝经》中,则说“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争”,读为“诤”,谏诤之意。到了《荀子》,则明确提出“从义不从父”。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义”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谏诤的作用也不断被强调。但问题是,当子女的谏诤不被父母接受时,又该如何实现“直道”?如何兼顾情理两个方面呢?《内礼》的回答是“隐而任之”,“任”,当也,即为父母隐匿而自己将责任担当下来。故根据儒家的观点,“直躬”的根本错误在于当发现父亲攘羊后,不是为其隐瞒而是主动告发;正确的态度则应是,替父亲隐瞒而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样情理就能得到兼顾,亲情与道义得以并存,这才是真正的“直”,是率真、率直与公正、正直的统一,是“直道”。
“亲亲相隐”是对亲情的保护,是率真、率直;“隐而任之”则是对社会道义的维护,是公正、正直,由于兼顾了情与理,故是“直道”。二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地反映孔子、早期儒家对待“其父攘羊”之类行为的态度。以往学者在讨论该章文字时,由于没有对“直”字作细致的分疏,不了解孔子情景化的表述方式,以偏概全,反而在“亲亲相隐”的是非对错上争论不休,控辩双方恐怕都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没有把握住孔子对于“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整个事件的真实态度。
那么,“亲亲相隐”是否有一定的范围、条件呢?是否只要是亲人的过错都一概可以“隐而任之”,由己代过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儒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派别态度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而言,早期儒家主张“亲亲相隐”是有一定范围和条件的,主流儒家是情理主义,而不是亲情主义,更不是亲情至上论。如简帛《五行》篇就认为,虽然为亲人隐匿是合理、必要的,但并非没有条件的。其文云:
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显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隐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第38-41简)
《五行》提出了处理罪行的两条原则:简和匿。其中“简之为言犹练也”,“练”,指白色熟绢,引申为实情。因此,简是从实情出发,秉公而断,是处理重大而明显罪行的原则,故又说“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匿匿”的前一个“匿”是动词,指隐匿。后一个“匿”应读为“昵”,指亲近。所以匿是从情感出发,隐匿亲近者的过失,是处理轻微不容易被注意的罪行的原则,故又说“有小罪而赦之,匿也”。《五行》简、匿并举,是典型的情理主义。在其看来,论罪定罚的界限不仅在于人之亲疏,还在于罪之大小,不明乎此便不懂得仁义之道。对于小罪,可以赦免;对于大罪,则必须惩处。据邢昺疏,“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论语注疏·子路第十三》)可见,“其父攘羊”乃顺手牵羊,而非主动偷羊,显然是属于“小罪”,故是可以赦免的,孝子的“隐而任之”也值得鼓励。只不过前者是法律的规定,后者是伦理的要求。但对于“其父杀人”之类的“大罪”,则应依法惩办,孝子自然也无法“隐而任之”,替父代过了。《五行》的作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故子思一派显然并不认为亲人的过错都是应该隐匿的,可隐匿的只限于“小而隐者”,即轻微、不容易被觉察的罪行。其强调“不简,不行”,就是认为如果不从事实出发,秉公执法,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正义。又说“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第34-35简),《五行·说》的解释是:“不以小爱害大爱,不以小义害大义也。”“小爱”,可理解为亲亲之爱;“大爱”,则可指仁民爱物之爱。“小义”、“大义”意与此相近,前者指对父母亲人的义,后者指对民众国家的义。故子思虽然简、匿并举,但更重视的是简:当小爱与大爱发生冲突时,当小义与大义不能统一时,则反对将小爱、小义凌驾于大爱、大义之上,反对为小爱、小义而牺牲大爱、大义。也就是说,子思虽然也认可“隐而任之”的原则,但又对“亲亲相隐”作了限制,“其父杀人”之类的大罪并不在隐的范围之中。子思的这一主张显然与孟子有所不同,而代表了一种更值得关注的思想传统。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中饱受争议的舜“窃负而逃”的故事,就能发现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可以从“隐而任之”来理解的,只不过其立论的角度较为特殊而已。据《孟子·尽心上》: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诉然,乐而忘天下。”
当面对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的难题时,舜作出了两个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命令司法官皋陶逮捕了杀人的父亲,另一方面又毅然放弃天子之位,背起父亲跑到一个王法管不到的海滨之处,“终身诉然,乐而忘天下”。可以看出,孟子与子思的最大不同是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范围,将“其父杀人”也包括在其中。当小爱与大爱、小义与大义发生冲突时,不是像子思那样坚持“不以小道害大道”,而是折中、调和,力图在小爱与大爱、小义与大义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维持平衡的关键,则是舜的“弃天下”,由天子降为普通百姓,使自己的身份、角色发生变化。郭店竹简《六德》曰:“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依此原则,当舜作为天子时,其面对的是“门外之治”,自然应该“义斩恩”,秉公执法,为道义牺牲亲情;但是当舜回到家庭,成为一名普通的儿子时,其面对的又是“门内之治”,则应该“恩掩义”,视亲情重于道义,故面对身陷囹圄的父亲,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而必须有所作为。另外,舜放弃天子之位,或许在孟子看来,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为父抵过,为其承担责任了。这样,孟子便以“隐而任之”的方式帮助舜化解了情与理、小爱与大爱之间的冲突。这里的“隐”是隐避之隐,而“任之”则是通过舜弃天子位来实现。
三、亲亲相隐:范围、理据和评价
由上可见,早期儒家内部对于“亲亲相隐”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子思简、匿并举,匿仅限于“小而隐者”,而孟子则将“其父杀人”也纳入隐或匿的范围之中。那么,如何看待子思、孟子二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呢?
首先,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子思《五行》所说的是处理案狱的现实的、可操作的一般原则,而《孟子》则是特殊情境下的答问,盖有桃应之问,故有孟子之答,它是文学的、想象的,是以一种极端、夸张的形式,将情理无法兼顾、忠孝不能两全的内在紧张和冲突展现出来,给人心灵以冲击和震荡。它具有审美的价值,但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故只可以“虚看”,而不可以“实看”。因为现实中不可能要求“其父杀人”的天子“窃负而逃”,若果真如此,那又置生民于何地?这样的天子是否太过轻率和浪漫?生活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例。所以舜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学虚构,只能是审美性的而非现实性的,与子思《五行》“有小罪而赦之,匿也”属于不同的层面,应该区别看待。批评者斥责舜“窃负而逃”乃是腐败的根源,予以激烈抨击;而反批评者又极力想将其合理化,给予种种辩护,恐怕都在解读上出了问题,以一种“实”的眼光去看待《孟子》文学性的文字和记载。
其次,在情与理、亲亲与道义的关系上,子思、孟子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前面说过,儒家主流是情理主义,而不是亲情主义,更不是亲情至上论。孔子、子思虽对亲亲之情有一定的关注,但反对将其置于社会道义之上,表现在仁、孝的关系上,是以孝为仁的起始和开端,所谓“为仁自孝悌始”,而以仁为孝的最终实现和目标,仁不仅高于孝,内容上也丰富于孝;孝是亲亲,是血缘亲情,是德之始,仁则是“泛爱众”(《学而》),是对天下人的责任与关爱,是德之终。因其都突出、重视仁的地位和作用,故也可称为儒家内部的重仁派。那么,儒家内部是否存在着亲情主义,存在着将亲亲之情置于社会道义之上、将孝置于仁之上的思想和主张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以乐正子春为代表的重孝派。笔者曾经指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在儒家内部发展出一个重孝派,他们以孝为最高的德:孝是“天之经,地之义”,孝无所不包,“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孝广大而抽象,体现为“全身”、“尊亲”和“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而仁不过是服务于孝的一个德目而已,“夫仁者,仁此者也”(同上),扭转了孔子开创的以仁为主导的思想方向,在先秦儒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恰恰一度受到重孝派的影响,故思想中有大量宣扬血缘亲情的内容,如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同上)甚至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这些都是受重孝派影响的表现,有些表述就是直接来自乐正子春派,笔者对此有过详细考证,此不赘述。(参见梁涛)故孟子在先秦儒学史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其早期较多地受到重孝派的影响,保留有浓厚的宗法血亲的思想;另一方面随着“四端说”的提出,孟子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宗法血亲的束缚,改变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的看法,把仁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完成了一次思想的飞跃,将儒家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前面说他在小爱与大爱之间折中、调和,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本来血缘家族是人类最早的组织,每个人都生活、隶属于不同的家族,故当时人们只有小爱,没有大爱,家族之外的人不仅不在其关爱范围之内,杀死了对方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而被杀者的家族往往又以怨报怨,血亲复仇,这便是“亲亲为大”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交往的扩大、文化的融合、地缘组织的形成,逐渐形成了族类意识甚至人类意识,人们开始超越种族、血缘的界限去看待、关爱所有的人,这便是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同上)的社会背景。儒家仁爱的提出,某种意义上也是生命权利意识的觉醒。从肯定的方面讲,这是强调人的生命至为珍贵,不可随意剥夺、伤害。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认为人的生命比外在的“天下”更为重要。从否定的方面讲,这是要求“杀人偿命”,维持法律、道义的公正。因此,在“亲亲为大”和“仁者,爱人”之间,实际是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冲突的。是以孝悌、亲亲为大,还是以仁义为最高的理想,在儒家内部也是有不同认识的。孔子、子思等重仁派都是以仁为最高原则,以孝悌为培养仁爱的起点、根基:当孝悌与仁爱、亲情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他们主张“亲亲相隐”、“隐而任之”,但隐匿的范围仅限于“小而隐者”,要求“不以小道害大道”。而孟子的情况则比较复杂,由于其一度受到重孝派的影响,故试图在“亲亲为大”和“仁者,爱人”之间折中、调和,表现出守旧、落后的一面。表面上看,舜“窃负而逃”似乎是做到了忠孝两全,但在这一“执”一“逃”中,死者恰恰被忽略了:站在死者的立场,谁又为其尽义呢?如果用“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衡量的话,显然是不合理、不符合仁道的。所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孟子的思想中,真正害怕的是旧的‘亲亲为大’的伦理原则的坍塌,而不是其‘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新人道原则的坍塌。”(吴根友,第554页)
孟子的这种折中、调和的态度,在另一段引起争议的文字中也同样表现了出来。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象是一个非常坏的人,舜却封给他有庳。为什么对别人就严加惩处,对弟弟却封为诸侯?孟子的回答是:仁者对于弟弟,“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为了使有庳的百姓不受到伤害,孟子又想出让舜派官吏代象治理国家,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公正。(见《孟子·万章上》)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反对“无故而富贵”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不仅墨家、法家有此主张,即使在儒家内部,荀子也提出“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如果说孟子质疑“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是维护亲情的话,那么,荀子主张将王公、士大夫的子孙降为庶民岂不是寡恩薄义了?两者相较,哪个更为合理,更为进步?如果不是立足于“亲亲为大”,而是从仁道原则出发的话,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一问题上,荀子的主张是合理、进步的,而孟子是保守、落后的。
另外,《孟子》舜“窃负而逃”的故事虽然是文学性的,但由于后来《孟子》成为经书,上升为意识形态,“窃负而逃”便被赋予了法律的效力。从实际的影响来看,它往往成为当权者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的理据和借口。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刺杀大臣袁盎,事发后其母窦太后拒绝进食,日夜哭泣,景帝于是派精通儒经的田叔、吕季主去查办。田叔回京后,将孝王谋反的证据全部烧掉,空手去见景帝,把全部责任推给孝王的手下羊胜、公孙诡,让二人做了孝王的替罪羊。景帝闻后喜悦。值得注意的是,景帝处理弟弟杀人时,大臣曾建议“遣经术吏往治之”,而田叔、吕季主“皆通经术”。据赵岐《孟子题辞》,《孟子》在文帝时曾立于学宫,为置博士,故田叔所通的经术中应该就有《孟子》,他之所以敢坦然地销毁证据,为犯了杀人大罪的孝王隐匿,其背后的理据恐怕就在于《孟子》。既然舜可以隐匿杀人的父亲,那么景帝为何不能隐匿自己杀人的弟弟呢?结果只能是转移罪责,以无辜者的生命来实现景帝的“亲亲相隐”。孟子的答问恰恰成为田叔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的理据,这恐怕是孟子所始料不及的。
又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周家人传》,周世宗柴荣的生父柴守礼居于洛阳,“颇恣横,尝杀人于市,有司有闻,世宗不问。”对于世宗的“亲亲相隐”,欧阳修以《孟子》的“窃负而逃”为之辩护:“以谓天下可无舜,不可无至公,舜可弃天下,不可刑其父,此为世立言之说也。”欧阳修所说的“至公”是“亲亲为大”也就是重孝派的至公,从“亲亲为大”来看,自然是父母为大,天下为轻了。“故宁受屈法之过,以申父子之道”,“君子之于事,择其轻重而处之耳。失刑轻,不孝重也。”
对于欧阳修的说法,清代学者袁枚给予针锋相对的批驳:“柴守礼杀人,世宗知而不问,欧公以为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误之也。”他认为,孟子让舜“窃负而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使自己陷入矛盾之中。对于世宗而言,即使没能制止父亲杀人,事后也当脱去上服,避开正寝;减少肴馔,撤除乐器;不断哭泣进谏,使父亲知道悔改,以后有所戒惧,“不宜以不问二字博孝名而轻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后,皋陶少矣。凡纵其父以杀人者,彼被杀者,独无子耶?”(袁枚,第1653、1655页)显然,袁枚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来立论的。如果世宗纵父行凶为孝,那么被杀者难道没有子女?谁去考虑他们的感受?他们又如何为父母尽孝?如果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原则来衡量的话,世宗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能称为孝,反而是不仁不义之举。袁枚将孟子的“窃负而逃”落到实处,未必符合孟子的本意,但他批评世宗非孝,则是十分恰当的。这也说明,是从“亲亲为大”还是从“推己及人”来看待“亲亲相隐”,观点和态度是有很大不同的。孟子的“窃负而逃”本来是要表达亲情与道义的紧张与冲突,是文学性的而非现实性的,但在权大于法、法沦为权力的工具的帝制社会中,却被扭曲成为法律的通例。由于“窃负而逃”涉及的是天子之父,而非普通人之父,故其在法律上的指向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实际是为王父而非普通人之父免于法律惩处提供了理论根据,使“刑不上王父”成为合理、合法的。中国古代法律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优良传统,却始终没有“王父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主张,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但是另一方面,孟子也具有丰富的仁道、民本思想,他主张“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认为“民为贵”、“君为轻”,均体现了对民众生命权利的尊重;他的性善论则包含了人格平等的思想,从这些思想出发,又可以发展出批判封建特权的观点与主张。袁枚的批判思想,其实也间接受到孟子的影响,是对后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现象看似吊诡,却是历史事实。
综上所论,围绕“亲亲相隐”的争论,其核心并不在于亲情是否珍贵,“亲亲相隐”是否合理,而在于儒家是如何看待、处理孝悌亲情的,儒家又是在何种意义、条件下谈论“亲亲相隐”的,尤其是如何看待、理解“窃负而逃”故事中孟子对亲情与道义的抉择和取舍。这些都是较为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根据前面的讨论,围绕“仁”与“孝”,儒家内部实际是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的:重孝派以孝为最高原则,通过孝的泛化实现对社会的控制;重仁派则视孝为仁的起点和根基,主张孝要超越、提升为更高、更为普遍的仁。孔子虽然也提倡孝,视孝为人类真实、美好的情感,但又主张孝要上升为仁,强调的是“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面对亲情与道义的冲突时,并不主张为亲情去牺牲道义。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说的“直”是率真、率直之直,而不是公正、正直之直。为了维护社会的道义、公正,曾子一派又提出“隐而任之,如从己起”,要求子女不是告发,而是代父受过以维护情与理、亲亲与道义的统一。子思一派的《五行》篇则将隐匿的范围限定在“小而隐者”,即小的过错,并强调“不以小道害大道”,“不以小爱害大爱”。孟子的情况虽较为复杂,在亲亲与道义间表现出一定的折中、调和,但其“窃负而逃”的情节设计,主要还是展示亲情与道义间的冲突与紧张,似更应从文学、审美的眼光看待之,而不可落在实处,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或辩护。况且,孟子也不是为了父子亲情便完全置社会道义于不顾,他让舜下令逮捕父亲瞽叟,让舜“弃天下”,便是对道义、法律的尊重,试图维持情与理之间的紧张、冲突,是“隐而任之”的表现。只不过孟子的这一设计不仅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从实际的后果看为“刑不上王父”提供了法理的依据,成为帝王将相转移罪责、徇私枉法的根据。从这一点看,子思强调“有小罪而赦之”,“不以小道害大道”,可能更值得关注,更有着时代进步的意义。
注释:
①此采用廖名春先生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的说法。
标签:儒家论文; 亲亲相隐论文; 论语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任之论文; 天下父母论文; 五行论文; 亲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