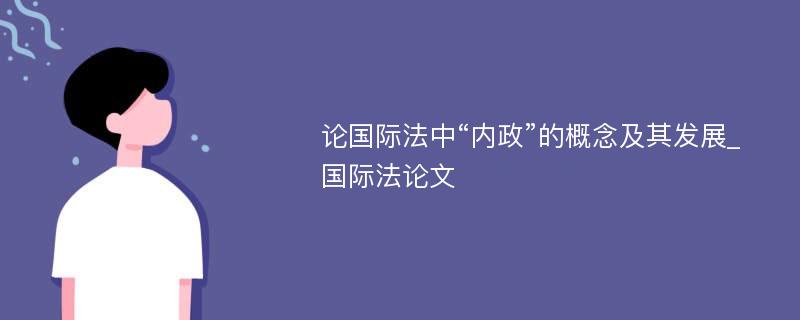
论国际法上“内政”的概念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内政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内政”这个概念往往与国家主权、国际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内政”这个词具有政治性、法律性和伦理性等多重性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内政在国际法上就变成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范畴,对之在国际法上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国际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该原则突出反映在“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国际法原则之中,这些与管辖权规则相关的国际法规范提供了这样一个指南:什么是或不是一个国家内部权限范围内的事务。①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当我们谈及“内政”一词时,实际将不可避免地论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对此,凯尔森就认为,国际法决定着不同国家国内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并从而划定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②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它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国家凭借这一权力可以处理所有国内事务。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它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而国家主权本来是国内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在法律上,国家通常的全部权利,即法律能力的典型情况被描述为“主权”;特殊的权利或数量上少于规范权利的累积被认为是“管辖权”。因此,“主权”或“主权权利”通常是指包括国家领土之上立法权限在内的管辖权。③因此,内政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直接集中体现在国家的管辖权问题上;但另一方面,内政往往又与干涉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国际法上的内政概念显得异常复杂。
二、“内政”的概念
1.“内政”一词在国际法上的名称及其意义
在汉语里,“内政”这个用词主要是指“国家的内部政治事务”,④在中文习惯里,往往将“内政”(Internal Affairs)与“外交”(Foreign Affairs)相对应来使用。实际上,外交仍然是各国内政的延续,因此,汉语的这种习惯用法显然太过于狭隘,不符合内政在国际法上的科学含义。而在英语里,有关“内政”的不同表述形式就有很多,诸如“Internal or Domestic Affairs”、⑤“Domestic Matters”、“Domestic Question”、“Matters of Domestic Jurisdiction”、“Reserved Domain of Domestic Jurisdiction of State”、“Exclusive Domain of State Jurisdiction”等。然而,有学者声称,这种认为总有那么一些专属于一个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的观点具有某种“误导”作用,因为如果这种事项由一项国际条约所调整的话,那么该国的所有国内事务都可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只有当不存在与国内事务相关的国际规范或没有产生国际影响的话,纯粹的国家内部事务才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⑥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如此,仍然有些事项关涉到国家的专属管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国家能行使这种权利,例如领土国家的“执行管辖权”。这就是为什么联大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提到“内部或外部事务”的原因,因为这里强调的不是行动或决定发生等行为的范围,而是这种决定是否由主权国家在以下两层意义上来行使:(1)国家做出决定或行为的专属管辖;或者(2)自由选择采取这种行动或决定的权利。⑦在以上几种有关内政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内政的概念历来有其他诸如“国内问题”、“国内事项”、“国内管辖事项”、“国家管辖权的专属管辖领域”等不同的表述形式,而其中“国内管辖事项”这个术语可能是用得最多的一个。事实上,对于内政这个概念的探讨将涉及国家的主权问题,也关系到国际法所调整的具体领域。问题的本质在于:它是否乃应该由国际法来规定的问题,或者是否为已经由国际法加以规定了的问题,或者是否为在国际法上根本还没有得到确切地规定,进而需要对其具体范围进行界定的问题等等。
2.国际法上对内政概念的界定
国际法学者对于内政这个概念在实在国际法上是否有规定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论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认为国际法没有规定国内管辖事项的“无规定论”和认为作了规定的“有规定论”。“无规定论”又可以分为以下各种主张:“国内管辖事项本来就属于国内法领域”、“纯属没有规定的领域”以及“国内管辖事项不属于国际法领域,也不属于国内法领域,而属于‘第三领域’等。“规定论”又分为“有限的规定论”、“不完全的规定论”以及“完全的规定论”。⑧事实上,上述学者对于内政在国际法上有无规定的不同观点突出反映了内政概念的法律与政治属性的复杂性。在一般国际法上,要对国家的内政或内部管辖事项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内政”这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不过,国家拥有管辖权是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这是国际法上明文规定并已确立了的原则,即国家有权排他地自行决定和处理国际法上规定系属于一国管辖的全部事项,对此,他国不得进行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内政这个概念在国际法上也应该是有所规定的。因此,对于内政这个概念在国际法上不能单纯地下结论说没有作出规定,或者单纯地判断已经作出规定。
一般认为,内政这个概念在国际社会于1919年订立《国际联盟盟约》之前在实在国际法上并没有作出规定,主要是限于学术上的讨论。⑨
而在近代国际法上,内政一词往往是和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是与“领土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的。早期国际法向政治理论借用主权概念时,强调“绝对领土主权”(Absolut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认为国家权威非但在其领土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不存在有其他更高的权威或国际法律可以约束其主权行为。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领土意味着该国内政管辖事项的范围,而领土边界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确立其主权管辖范围的分界线,并且是保证一个民族国家政治独立、领土完整的最基本条件。在边界内,主权国家或政府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独特的政治制度而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边界的任何变动必须在严格遵守国际法的秩序下进行,国家在自己边界范围内制订和实施自己的法律制度。因此,一般认为,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其政治地理意义就是不要干涉他国领土边界范围内的事情。⑩此后,国家主权开始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而国家主权平等的一个必然逻辑结果是不干涉内政义务。然而,在整个近代国际法上,内政的概念始终是不明确的,在实在国际法上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不过,从当时的实践及有关学者的论述来看,作为不干涉对象的“内政概念”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出现的,而且也主要是主权国家在抵制外来干涉的过程中确立起来,从这方面讲,内政这个概念在当时主要涉及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国家对其他两国间关系的干涉(外部干涉);二是国家对一国的内部争端的干涉(内部干涉);三是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某种救济的手段,国家因一国触犯了国际法而通过发动战争而对一国所进行的干涉(惩罚性干涉)。(11)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内政概念主要限于国家内部的争端及与他国的外部政治或军事关系。另外,对于一国对另一国因触犯国际法而对该国内政的限制主要是依靠“自助”(如惩罚性干涉)来完成的。
而实在国际法上第一次提出内政这个概念是1919年的《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第8款的规定:“如果争执各方任何一方对于争议自行声明并为行政院所承认,按诸国际法纯属该方国内管辖之事件,则行政院应据情报告,而不作解决争议之建议。”该条款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因当事国主张排他性管辖权而认为该事项属于其内部事务,是否属于其内政问题,由国联行政院自己判断审查一次争议以及对一个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纠纷通过一次报告。然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于其内部事务的一次公然的干涉。(12)尽管如此,这至少可以说明,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国际组织来确定,而不再纯粹由国家自己单独来判断并采取“自助”措施,并且,联盟行政院上述判断的做出须得到行政院的全体一致通过,从而防止发生主观的判断和滥用的情况,这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二是使用了“按照国际法纯属国内管辖之事件”的措辞。这说明什么是当事国的国内事件,判断的标准是国际法。然而,“按照国际法”这个修饰词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有鉴于此,在1923年的“突尼斯—摩洛哥国籍法令案”中,国际常设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第一次对国内管辖事项做出了界定:“纯属国内管辖”一词是指某些事项虽然和一个以上的国家的利害密切相关,但原则上不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关于某一事项是否纯属国内管辖事项,原则上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它依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13)这种界定也没有取得很大的效果,事实上,国内管辖事项这个概念暗示一个国家有自由选择其存在的目的和手段的自由。尽管这个概念在不断发展,一个彻底或完全确定的国内管辖事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并不存在,在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解释往往基于不同的案例而被不断重新解释。(14)
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该条款较之于盟约第15条第8款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联合国吸取了国际联盟的教训,鉴于“国际法”一词的模糊性,宪章第2条第7款并没有提到“国际法”,这实际将“哪些事项是一国国内管辖事项的决定权”完全留给了主权国家自己。其次,盟约第15条第8款仅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事项纳入国内管辖事件范围之内,而宪章第2条第7款却除了将涉及《联合国宪章》第7章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排除以外,还将联合国的几乎所有职能范围内的事项都纳入到了国内管辖事件范围之内,这实际极大地扩大了内政概念的具体适用范围。再次,“本质上”较之于“纯属于”的措辞更为模糊和广泛,由于“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的表述不是很清楚,这很容易导致针对该条款的各种不同解释,并且使得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范围与国际法所调整的事项范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确,因为许多国内管辖事项可能兼具有国际法上的含义。最后,宪章第2条第7款禁止联合国所有机构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而《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第8款只将国联行政院排除在实施干涉的主体之外,这实际也强化了国家对其国内管辖事项的管辖权。对于一个事项是否是一国的国内管辖事项,盟约第15条第8款规定只能由当事国和国联行政院加以判断,而宪章第2条第7款却没有明确规定是否由联合国各个机构或国际法院来决定,根据推定应该由当事国自己来进行判断。但如果两国发生争端,一方将其提交到联合国,则联合国的各个机关都有权进行判断。尽管如此,宪章第2条第7款较之于盟约第15条第8款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其但书的规定,“……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就给联合国在宪章第7章的规定下干涉各国的国内管辖事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内政概念的法律与政治属性
主权自产生的那刻起,它既是为排除来自其他权力主体的支配或干涉的反抗性概念,同时受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上的国际法的约束,与国家拥有主权并不矛盾。(15)因此,一方面,内政作为国家主权的具体运用的概念是与不干涉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内政概念是与国内法和国际法联系在一起。从而,内政这个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同样地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两种属性。作为政治概念的“内政”往往是主权国家在抵制来自外部干涉行为、维护国家独立权的斗争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的,换句话说,作为政治概念的内政是与主权国家的独立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权利”。(16)实际上,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可适用标准问题的内政范围是可以变化的,这就赋予了内政以极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某些国家,尤其是大国往往利用干涉他国内政的方式来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强权政治与大国霸权的客观存在也就注定了干涉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可避免性,因为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统一的国际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国家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理解或解释内政的具体含义的。而干涉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经常发生且政治性很强的现象通常在国际法上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遇到“非强制性”干预的场合,就更难判定内政与干涉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不过,对于那些强制性干涉,尤其是武力干涉来说,内政与干涉之间的联系就很明显了。例如人道主义干涉本身作为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它不但涉及法律和政治问题,而且还涉及国际伦理问题,因此,大多数观点认为,如果将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看待,人道主义干涉自始至终都没有、也不能构成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一个例外,现行国际法上也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因为它严重侵犯和干涉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三、内政概念在国际法上的“扩展”与“收缩”趋势
内政这个概念在国际法上是否存在具体的范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从国家积极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或维护国家主权性权利的角度来思考其内政适用的具体范围;二是从国家消极承担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义务中思考内政的保护范围。有学者就概括得比较中肯,即“询问不干涉原则对国家所保护的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等于在询问处于一个国家国内管辖权范围内的事项是什么的问题”。(17)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思考,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要比较确切地掌握内政概念在国际法上的具体内涵及其适用范围是非常困难的,从追求界定概念的准确性这点来看,国际法上内政的概念确实是落后于现行国际关系的发展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内政概念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它随着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这样看来,内政本身就是一个弹性很强的动态性概念,而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相关实践来看,内政概念在国际法上越来越呈现一种既“扩展”又“收缩”的矛盾发展态势。
1.内政概念在国际法上的“扩展”趋势
实际上,内政概念的产生、发展是与民族(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为了抵制外来的干涉以及权力斗争的需要,各国一般倾向于强化国家内政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这突出反映在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体制下制定的相关国际文件对国家内部管辖事项或内政的重申或强调,最典型的如《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如第2条第7款)、联大相关决议、国际法院的相关判决以及众多区域性国际文件等。传统国际法上一般只强调内政问题为国内问题,但随着国际间相互关系和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干涉义务不仅限于国内事务,还涉及对外事务,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49年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3条规定:“各国对任何他国之内政外交,有不加干涉之义务。”后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等都强调了这一点。(18)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内政概念实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内政与国家的管辖权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国际法的触角日益倾向于伸向原本“纯属”或“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的事项的领域范围,内政概念看起来好像是“缩小”了,但这种缩小实际仅仅只是一种“相对地缩小”。这主要是因为,其一,科技的发展确实使得现行国际法将其触角伸向了传统国际法上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领域,但同时也使得国家将自己的管辖触角伸向了原本在传统国际法上不可能涉及的领域。其二,国家的地域管辖权这条规则实际只适用于执行管辖权,现行国际法并没有一项实在规则禁止一个国家对于发生在本国领域范围外的行为行使实体性的权利。(19)国际常设法院曾经在1921年的“荷花号案”中主张,一个国家不可以在他国领土范围行使任何形式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管辖权当然是领土性的;一个国家不能在其领土范围外行使自己的权力,除非依据来自国际习惯或一项公约的允许性规则。一方面,由于国家根据条约、国际惯例等国际法上的义务从而使管辖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国家也可能根据条约、国际习惯等国际法的规定从而使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超出自己本国领土的范围。(20)这也就是说,一国随时有可能在与他国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国际法途径将自己的国内管辖权的触角延伸到本国领土范围之外,同时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或“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的概念不是一个“领土性的”(Territorial)概念。(21)其三,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与其用“内政”这个政治性很强的概念,还不如用法律性很强的“国内管辖事件”这个概念更为恰当。相对于国内社会来说,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因此,在目前国际社会的条件下,不大可能存在所谓真正法律意义上有关“国际管辖权”的概念。正如凯尔森所说,国际法没有规定使国内法无效的程序。(22)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随时都有可能运用针对国际法院管辖其内部事务的“可抗辩性”(Opposilitité)程序。即使是目前唯一带有普遍性的国际法院所确立的国际管辖权也是一种任意而非强制性管辖,尽管目前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国际专门法院,如国际军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庭、WTO争端解决机构等等,但接受这些国际法庭强制性管辖的国家经常援引不干涉国内管辖事件的原则作为一项保留条款。因此,总的来说,严格意义上的由国际法院所确立的“国际管辖权”概念尚未出现,大部分由国际法所设定给主权国家的义务都只是由国际法来进行调整,并不直接受国际法的管辖。国际法的调整事项与国际管辖事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国际法调整事项范围的扩大,只是意味着国家针对其内部事务的管辖权受到了国际法的限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法上的内政概念呈现出日益扩展的趋势。
2.内政概念在国际法上的“收缩”趋势
内政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说明其与国际法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而国际司法机关的相关实践表明国家不能利用国内法来改变国际法,如1932年国际常设法院关于“在但泽的波兰国民待遇问题”一案所出具的咨询意见中认为,一国不能以国内法来规避依据国际法或有效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后来,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也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因此,如果一项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成为国际条约调整的对象,那它就成为了当事国之间的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强行法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对其内政任意决定的保留范围。因而,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强化”,一国的内政将越来越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和限制。内政概念的这种“收缩”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国家间关系的相互依赖的增强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使得影响一国内政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多,许多原本纯属于一国管辖的事项越来越由两国或多国或国际社会共同来管辖,如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传染病问题等,从而使得一国的国内管辖事项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色彩。从实体来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国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越来越多,许多原本由国内法调整的事项越来越同时由国际法来进行共同调整,国家内部管辖事项范围呈现缩小的趋势。而从程序来看,国家实际可以就任何本国国内管辖的事项通过缔结条约的技术性手段而成为一个国际法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的范围也随时都有缩小的可能。因此,如果一项事项与国际争端有关,而该国继续主张该事项为国内管辖事项的话,有两种途径可能使得该事项不再纯粹为国内管辖事项,一是如果存在与该事项相关的国际条约或习惯,二是即使该条约或习惯的适用存在问题,国际机构的判决必须解决这种问题。(23)但值得指出的是,即使这些事项受有关国际法律规则的支配,也并不意味着这种事项就完全排除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只是国家的管辖权不再是无拘无束的,它必须受到国际法的限制。(24)
(2)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进程的加快,主权国家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一方面其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对其内部管辖事项的某种主动让渡,另一方面,国家基于国际合作的需要以及国际组织为了切实履行其宗旨的考虑,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倾向于主动介入成员国内部管辖事项的范围,作为普遍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就是一个典型。联合国对于宪章第2条第7款的相关实践尤其是值得关注的。宪章第2条第7款一向被认为是国内管辖事件的实践重述和强化,其自第一次被阐述的几十年以来一直被经常得到重新阐述,当然,这并不阻止联合国讨论或采纳有关成员国的内部政策的相关决议,实际上,联合国60多年来的相关实践已经进一步限制和侵蚀着一国的国内管辖事件。(25)《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表面上是扩大了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但必须结合宪章其它条款来进行理解,人权的保护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26)从联合国的政治机构(大会以及安理会)的相关实践来看,这些政治性机构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克服“国内管辖事件”的抗辩,其中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以国内管辖事件演变成为“国际关切事项”为由通过相关决议。另外,安理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开展的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行动越来越多地突破宪章第2条第7款的限制。近年来,安理会在授权开展维和行动时,也越来越多地援引《宪章》第7章下的强制性规定,这表明,安理会的维和行动日益倾向于介入一国内部事务。但联合国安理会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宪章第7章下的规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被合理地认为是排除在宪章第2条第7款所规定的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之外的,只要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或破坏(即使是因国内情势所引起的),联合国安理会都可以不受宪章第2条第7款的限制,而“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包含任何关涉第2条第7款的实施程序的条款”。(27)这清楚地说明,自冷战结束以来,安理会的相关实践已经对于国内管辖事项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28)尤其是当一国国内发生人权侵犯事件时,安理会日益倾向于将其视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威胁”,从而大大增加了安理会介入一国国内事务的机会。例如1970年安理会通过了有关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第282号决议,认为这种状况已经“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2005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首脑峰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其中规定,当一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而政府不能、不愿或纵容该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就有权对其内部事务进行介入。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内政这个概念尽管与国家管辖权这个概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其在国际法上仍然不大可能得到明确的界定,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曾经对于内政这个概念试图进行编撰,但由于分歧太大,内政问题始终未能被列入该委员会进行法律编纂的主题名单上。一个国家行使其管辖权的权利以国家主权为依据,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有在它所选择的任何情况下行使管辖权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的行使可能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利益。而一个国家所认为它的管辖权的主权权利的行使,而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认为是对它自己的属地或属人权威的主权权利的侵犯。(29)尽管任何一个在国际间得到认可的政权国家都享有“主权”,也享有国际间的法律正当性。但是,政权国家在国际间的法律正当性(对外主权)与它在国内的政治权力正当性(对内主权)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在国际关系中,受到重视的是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对内主权,国家被想当然地当作为了一个统一和同一的行为主体。然而在国内社会现实中,国家并非是这样一个主体,国内社会一直就是一个充满分裂与冲突的非统一体,它由各种各样的利益分裂和联盟的关系网所构成。(30)这种情况的存在就极有可能使得原本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演变成为“国际关切事项”。而且,内政这个概念本身既意味着国家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义务,这说明“绝对主权”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国家主权即使存在豁免,也只是意味着国家在外国法院享有审判管辖豁免(司法程序方面),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国际实体法上有免除其责任或义务的权利。而且,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抛弃了“绝对豁免主义”,奉行“限制豁免主义”。这种情况的存在将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现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没有什么事项可以被认为仅仅只是“纯属于”或者“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或内部管辖事项。另外,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那些自然“溢出”(Spill-Over)一国国内边界的国内管辖事项很有可能随时演变成为国际关切事项,而这种事项或者有可能为强权政治所“掌控”,或者也有可能为国际法或国际组织所“关切”。因此,在实在国际法上,内政的适用范围尽管原则上规定得是很广泛的,但同时却是极其模糊的。而在实践中,作为“‘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管辖事件’的国际法律概念的实质性变化也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而变化。”(31)
注释:
①See Tim Hillier,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②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③参见[英]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第320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20页。
⑤该词据说最早出现在1655年英法两国所缔结的友好同盟条约中,该条约首次确立了“以宪法和国家的形式为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原则。参见邹今骏:《关于“国内管辖事件”的范围问题》,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⑥See Kofi Darko Asante,Election Monitoring' s Impact on the Law:Can it Be Reconciled with Sovereignty and Nonintervention? in HeinOnline-26 N.Y.U.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1993-1994,p.261.
⑦See Georges Abi-Saab,Some Thoughts on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in Karel Wellens ed.,International Law:Theory and Practice,Essays in Honour of Eric Su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8,pp.230-231.
⑧参见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词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75-476页。
⑨参见[韩]柳炳华:《国际法》(上卷),朴国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⑩参见胡启生:《海洋秩序与民族国家—海洋政治地理视角中的民族国家构建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11)See P.H.Winfield,The History of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HeinOnline-3 Brit.Y.B.of Iht' L.132 (1922-1923),p.131.
(12)Voir N.Ouchakov,La Compétence Interne des Etats et la Non-Intervention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Recueil Des Cours,1974 (I) ,Tome 141 de la Collection,p.26.
(13)Voit Décrets de Nationalité Promulgués en Tunisie et Moroc,7 Févrie 1923,PCIJ,Recueil Des Avis Consultatifs (Série B) ,n.4 (1923),pp.23-24.
(14)See Veronika gartosch,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in Politische Wissenschaften,5,pp.14-15.
(15)参见[日]松井芳郎:《国际法》,辛崇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16)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100页。
(17)See Vincent,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29.Quoted in 'If Sovereignty,then Nonintervention' ,this article served a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author' 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Norwegian Military Chaplain Corps Symposium on Military Ethics -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 Oslo 14 September 1999.at http://www.pacem,no/2000/1/intervensjozv/neumamt/.
(18)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19)See Tim Hillier,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20)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7页。
(21)See G.I.Tunkin ed.,International Law,A Textbook,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6,p.139.
(22)参见[奥]凯尔森:《法的纯理论》,转引自[英]斯塔克:《国际法导论》,赵维田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注释3。
(23)See Kofi Darko Asante,Election Monitoring' s Impact on the Law:Can it Be Reconciled with Sovereignty and Nonintervention? in HeinOnline-26 N.Y.U.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1993-1994,p.261.
(24)See Georges Abi-Saab,Some Thoughts on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this paper is in Karel Wellens ed.,International Law:Theory and Practice,Essays in Honour of Eric Su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8,p.230.
(25)See 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Fifth edition,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575.
(26)See Amy Eckert,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in Hein-Online-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Volume 7,No.1,pp.55-56.
(27)A.Trindade: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of Stat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25,Oct.1976,p.761.
(28)See Dr.Mohamed Kadry,Evolution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From 'Non-Intervention' to ' Pre-emption',in IISS Intervention in the Gulf Workshop,Dubai,26-27 May,2003 Arab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o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Draft Report,Part-1.
(29)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第1卷第1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30)See Michael Mann,Neither Nation-State Nor Globalism,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8 (1996),p.1960.
(31)See G.I.Tunkin ed.,International Law,A Textbook,Moscow Progress Publishem,1986,p.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