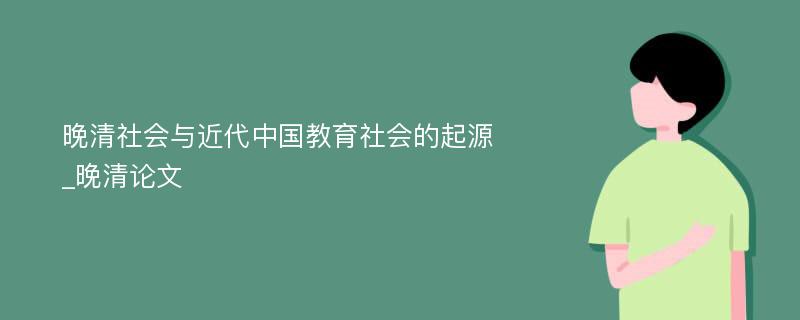
晚清社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发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16(2010)08-0014-04
集会结社,中国古已有之。据研究者的考察,“会社的活动,发轫于先秦,自汉迄清,一直延续,其间虽有盛衰,但其活动却并无停歇。”[1]13-14不过,近代学会并非传统会社的自然延续。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的《教育大辞书》中诠释“学会”为“系一种学术团体,而以交换智识、研究学术为宗旨”[2]1510。显然,学会建基于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乃学术之“会”,或学科之“会”,为近代以来学人开展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而“传统士人之结社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道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3],其组织结构与活动方式也“与近代学会的民主性、学术性、群众性和组织上的科学性不可同日而语”[4]。由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即不论是六艺、诸子百家,还是经史子集,都未能确立起教育学术的独立地位,教育不过是政治与哲学的附属,故而,中国古代乃至戊戌维新之前,成立教育学会的时机并不成熟。作为近代学会类型之一的中国近代教育学会,承戊戌时期维新志士掀起国人创始近代学会的高潮而发轫,折射着晚清以降“救亡图存”的教育诉求,表征着新式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专门化趋势。
一
近代意义上的国人集会结社,肇始于戊戌时期,首当其冲为救亡图存之激荡。甲午战败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又一次无情而现实地摆在国人面前,康有为述及当前中国的处境,忧心如焚,“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5]384-385。不过,事变本身也惊醒了国人,诚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维新志士一方面反思洋务运动“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亦无几矣”[5]484的缺失,一方面认真分析时局,形成了这样的变革思路:“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十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效尤速,转移尤钜也。”[5]385康有为还辅以当时巨创于日本的教训,明确表示“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上”[5]389。显见,造就“学之群”担当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成为他们的共识。于是,兴学堂、办报纸、开学会的呼声与行动,有如雨后春笋,交相辉映。其中,开学会在造就“学之群”方面的功能尤为维新志士所睹目,因为学会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汇聚士人,讲求学术,开通风气,培养人才。梁启超展望学会的功效道:“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学会将为各行各业培养“不可胜用”的人才,如此“以雪雠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修?”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5]375甚至断言:“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5]377“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梁等人将创兴学会之举付诸实践,于是有了强学会的率先降生。尽管因此触发了守旧势力的恐慌,强学会不久便遭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5]395。一时间,学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毋庸置疑,戊戌时期的学会,离不开中国传统集会结社的浸润,它们与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传统会、社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不过,在中西文化汇冲的大背景下,其近代性更为凸显。论者指出:“这些学会从中国古代士人结社传统中吸收了三方面因素——以文会友、聚会讲习的因素,书院讲学的因素,政治集会的因素;同时亦从西方近代学会移植来三大新因素——会员间之地位平等,定期聚会之民主管理制度,及创办期刊、藏书、印书、讲演等新式事业”[3],从而使其别于传统集会结社。换句话说,戊戌时期的学会乃西学东渐之产物。揆诸史实其实不难发现,戊戌时期的学会从实践范式到理论基础,主要来自鸦片战争后开始新一轮东渐历程的“西学”。正是通过西方“学会”这面镜子,维新志士逐渐知晓了近代学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尤其意识到学会与学术发达、国富民强之间的关联,进而从观念上突破了西人之强在于“坚船利炮”、“工商实业”的窠臼,而直指“学以致强”的事实,为创兴学会奠定理论基础。康有为声称:“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5]386《湖南龙南致用学会章程序》中一语道破天机:“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5]465
在戊戌时期中国近代新式学会创始与勃兴的氛围中,作为其类型之一的教育学会亦蒙其惠而萌发。闵杰在考述戊戌学会时指出,戊戌时期的社会团体,可以明确定性为学会组织的,主要有三类:政治性团体、社会风俗改良团体、学术团体,“此外,还有一种教育团体,今人已经很难严格区别其性质究竟是学会抑或学堂”[6]。因为其时,“学堂者,主也;学会者,辅也。始之创兴学会者,所以为学堂之基础也;继之扩充学会者,所以补学堂之不及也”[7]。20世纪初期,学堂与学会之间相互转换的情形仍屡见不鲜。其实,学会、学堂、报纸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构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8]。换句话说,学堂也好,学会也好,首要为应对时艰。但不论如何,至少表明国人已意识到参照西方近代学会的建制组织教育学会的问题,尽管已有的研究似不足以说明此时教育学会的具体情况,因为明确以“教育”命名者尚未见诸相关研究成果中,然时人诸如“根本救济,端在教育”[9]474、“舍教育改良无他法矣”[9]281等言论,又足以说明:戊戌时期,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急速放大,救亡图存的教育诉求甚嚣尘上。由此,推测其时有教育学会的活动足迹并非武断。事实上,与晚清以降“救亡图存”这一社会基调相对应,“振兴国势、挽救民族危亡,成为绝大多数教育家提出自己的教育理论、学说、主张的立论依据,成为贯穿于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的主旋律”[10]。应该说,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发轫,是与这一主旋律相伴而生、相辅而成的。
二
除了“救亡图存”之激荡,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发轫自有其内在逻辑:新式教育的发展。肇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新式教育,乃出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威慑,“师夷长技”之必然。步入20世纪初,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发展新式教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时论描述道:“不欲为我中国计则已,欲为我中国计,舍教育无自。斯言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古考孔孟之法,新徵欧美之说,虽有百喙,无异一词。是以庚子以后,上有各府州县官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惹心教友,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游学之徒,数以千计,足迹遍东西强国,岁资费千百万以上,时有增加,未有已日,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专心致志,出全力以经营者也。”[11]诚然,晚清政府在其间的作用毋庸置疑,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式教育的蓬勃景象正是其政策导向与积极鼓励的结果。
不过,事情远不如想象得那般乐观。比如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所需的经费,对于晚清政府来说便是难隐之痛。以1908年为例,当年入库金银铜三项总数为21370173两,而支出金银二项总数便高达45415528两。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大量银两外流,致使国库空虚。“按是年中国金银,泄诸外国者,总计合规平银两千四百余万两。”[12]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已有教育的正常运作,已是勉为其难。不仅如此,像创兴学堂与毁学风潮之间的尴尬,废除科举与奖励出身的悖论等,更是彰显着制度设计的缺陷与体制自身的惰性等深层次的囹圄。总之,在发展新式教育问题上,正如时论所言,晚清政府已是力不从心。“朝廷之罢贡举而兴学校,于今几十年矣。然一问其所以为教育之目的者,于国民一方面固未尝丝毫为增进国民之智识能力计也。其敷衍粉饰,今日下一令,明日颁一谕,而以教育著之敕令者,仍唯在于造成官吏之材而已,他非其所计及也。故教育之欲普及而责望诸政府,是犹以驽骀而追駃騠,终觉瞠焉在后耳。”[13]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地方、社会与民间力量逐步走向新式教育发展的中心。显然,这既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其向前推进的客观需要。事实上,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以及留学教育的兴起,在传统士大夫阵营里,已逐渐形成一批趋新知识分子,广泛分布在乡间、社会,关注、投身“教育”与“实业”,成为他们思考挽救民族危亡的基点,以“集会结社”的方式增厚群体力量,成为他们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的选择。据研究者的统计,1901-1904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不计分会),其中有教育会21个[14]275。清末“新政”的实施,特别是教育变革的“仓促”发动,为他们创造了更为广泛与“合法”的活动空间。论者指出:“由于新旧思想斗争激烈,政府在行政层面并没有为变革做好准备,无论是机构设置、官员结构还是管理方式等各方面都不能适应变革的需要。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情绪急躁,虚实不辨,改革未能符合中国的实际。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民间士绅的力量得以伸展,各种教育团体特别是教育会组织,才有了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空间。”[15]165这些教育团体在地方学务方面的“客观”作用,则不能不使清廷为之所动。例如,1905年由张謇、恽祖祈、王同愈等士绅发起组织的江苏学务总会,在缓和、平息当时江苏各地因新旧思想导致的学务纠纷方面便较好地履行了职能。他们推定调查干事,“实地调查,具一书面报告,根据理论和事实,判明曲直,解开症结,恢复和平”,以“取得双方当事者接受,使学潮得以平息”[16]75。此举深得晚清政府地方大员的赞许。1906年该会遵晚清政府部章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时,江苏巡抚便作了这样的评价:“诸绅上年设立学务总会以来,于本省教育,担任义务、倡导维持、辅官力所不逮,实已成效昭然。”[17]1906年晚清政府准学部所奏的《各省教育会章程》中,充分肯定了此前地方士人兴学的积极性,并明确表示:“势必上下相维,官绅相通,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地方学务乃能发达。”[18]255这为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随后,各地兴起创设教育会的高潮。至1909年底,全国公开成立的教育会已有723个。至1911年,除了新疆、甘肃等个别地方尚未曾设立教育会外,全国其他的省区均已设立教育总会及分会。诚如论者所言,“晚清时期新式教育迅速发展,清政府教育主管机关不可能独立解决新式教育的各种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教育会社得以发轫的重要机制之一”[19]24。
三
晚清政府对于新式教育发展的力不从心,无疑也突出地表现在缺失教育学术的研究上。时论曾对清末以来的兴学状况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按之近今之教育界,究皆可忧多于可喜,可危甚于可安,可以为者难于可以勿为。推厥弊端,要可一言蔽之曰:盲行而已。”[20]之所以“盲行”,除了政治、社会的原因,就教育自身而论,诚然是乏于学理的指导。主持中国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编辑事宜的王国维曾言:“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之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21]16事实上,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教育逐渐摆脱政治与哲学的附属,成为社会中相对独立的一项社会事业后,其进程中累积的问题,诸如教育宗旨的颁定、教育制度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等等,均不是凭借主观愿望或已有经验以及一纸政令或指令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须集专业人员的研究方能成事。只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如经、史、子、集,显然不具学科意义,更没能确立起教育的相对独立地位,专门化的教育学术也就无从谈起。学科的引进乃至体制化,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论者指出:“自清末推行教育改革以来,清廷便不时派员出访考察国外教育制度,也有不少朝臣士子于戊戌之前便已开始介绍西方学制与学科分类系统,但是能获采行的方案终究有限,直至《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教育制度才明显出现了向西方学科体制转化的痕迹。……学堂章程的颁定,实可视为官学系统对西方教育体制的妥协,当然,它同时也代表着近代学科体制正式确立的一份声言。”[22]38-40学科化的教育理论,在“救亡图存-兴学育才-创办师范”的逻辑中,因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兴起,借道日本导入并藉现代学制的颁定从而步上制度化轨道。
甲午战败后,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声浪中,教育又一次被赋予不堪之重,兴办师范随之成为时代的激樾之音。“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即就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急务矣。”[23]607从东西洋的经验来看,作为培养师资的机构,“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材教法”等课程的设置,是师范学校“师范性”的标志所在。因此,导入教育学科势所必然。据现有资料及已有研究,《教育世界》第9、10、11号(1901年9-10月)上连载的由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为近代西方教育学科导入中国之始。尽管此时导入教育学科主要是基于课程开设之需,学科著作多为师范教育课程用书,因而“不是处于一种研究教育、服务实际的状态,而是以传授国外教育学科知识为主”[21]62,但从其后时人所译介以及编撰的教育学科讲义、著作来看,结合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的良好愿望一以贯之,由此也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发展的历程。随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将西方的现代学科体制纳入学校教育系统,教育学科遂借此步入制度化轨道。从《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规定来看,教育学科是初级师范学堂区别于中学堂的主要标志,授课时数仅略少于经学,其修习内容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教育法规、学校管理、教育实习等[24]405-409。而在优级师范学堂,不论主修哪个门类,“教育学”、“心理学”均是必修科目,包括普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理论及应用教育史、教育史、各科教授法、学校卫生、教授实事练习、教育法令等课程内容的修习。作为提高程度的“加习科”,则几为教育学科课程[24]421-428。教育学科的制度化,为教育学会这一教育专业人员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依据。论者有言:“学科建制的形成是学术制度得以建构的基础,学科体现了知识内部的分化逻辑,因为分化才有分工,进而形成学术人各有所属的共同体(或无形学院),譬如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大小圈子、学术社团等。”[25]江苏学务总会因“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不涉学外事”而设;清末的中央教育会,尽管受到当时日本高等教育会议的启示,但其起因实在于“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益繁重,非决一二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非“汇集教育名家,开议教育事项”不可[18]177。《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确认了清末新式教育的专门化走向及设立教育会的必然:“现在学堂教育方见萌芽,深明教育理法之人殆不数觏,是非互相切劘、互相研究,不足尽劝导之责,备顾问之选。”[18]255
综上所述,晚清以降“救亡图存”的历史境遇,激荡着包括教育学会在内的中国近代新式学会的产生,而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学术共同体”的教育学会,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则来自新式教育变革的客观需要以及教育的专门化趋势。
收稿日期:2010-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