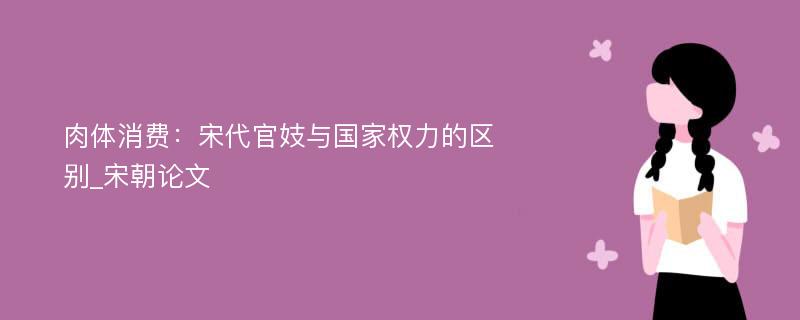
身体的消费:宋代官妓的差排、祗应与国家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应与论文,国家权力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妓包括教坊妓、地方各级官署的歌妓。宋代教坊反复置废,南宋最终废除教坊后,乐人后多隶临安府。“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辈。”①最终被地方衙前乐人所取代,故此处讨论以地方乐妓为主,暂不涉及教坊妓。 一、官妓的差排 庞德新先生以宋代市肆工匠要应付官府差使,及营妓之活动推论营妓也应该“籍其姓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②,应官府差使。庞先生还用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六中所记:“(二曲)所居之妓,系名官籍者,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如遇并番,一月止一二日也。”③《新编醉翁谈录》的出版说明指出,金盈之《醉翁谈录》全书凡八卷,清朝阮元在搜辑时全书只有五卷,缺后三卷。“也可能是因为后三卷中之《平康巷陌记》是后人将《北里志》篡改而成的。”④但排印本还是收入后三卷成全璧。庞先生所举例即是文集后三卷的内容。笔者以《北里志》与之对照后发现,庞先生所举“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一句为《北里志》不存。《醉翁谈录》也记同样史料,撰者为罗烨,生平不可考。⑤罗氏著《醉翁谈录》记风月之事,在丁集卷一《花衢记录》中四条内容与《北里志》相似,仍存此句,不知是错漏,还是后人篡改抄袭。此句话中“并番”与《梦粱录》中记“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对照,“设法卖酒”也是宋代之事,但终因此句与《北里志》之篡改相连,故不为确证。⑥ 所幸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例可以说明妓女应官府差使的情况。以话本《月明和尚度翠柳》为例,所记宋时“当日府堂公宴。承应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娇媚,唱韵悠扬。府尹听罢,大喜”,问妓者何名,答言:“贱人姓吴,小字红莲,专一在上厅祗应”。“柳府尹赏红莲钱五百贯,免他一年官唱”⑦,确是官府安排官妓祗应的例子,综合上文所述,可知府尹有权力免去官妓相应的差使。 黄庭坚《满庭芳》词: 初绾云鬟,才胜罗绮,便嫌柳陌花街。占春才子,容易托行媒。其奈风情债负,烟花部、不免差排。刘郎恨,桃花片片,随水染尘埃。 风流,贤太守,能笼翠羽,宜醉金钗。且留取垂柳,掩映厅阶。直待朱轓去后,从伊便、窄袜弓鞋。知恩否,朝云暮雨,还向梦中来。⑧ 描述了妓女的生活状态。妓女稍长成人,便知身处妓院,需要向“烟花部”尽义务,“不免差排”,“刘郎”代指痴情人也不能阻止妓女因烟花部的安排而被他人染指。太守因权力在握,便是常常染指之人。只有太守离去后,妓女方可从便。以此看来,官妓需要应对官府的差使。⑨有时活动颇为频繁,如温琬“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日不得在家”⑩。叶适所见妓女也说“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11)。祗应时还需及时赶到,否则会被长官责怪。《西湖游览志馀》记载苏轼在杭州任职时,与府僚会集于湖上: 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坐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据,但低首垂泪而已。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12) 点唤了众多妓女到场助兴,营妓秀兰在乐营将的屡次催促之下才到场。府僚因为怀疑秀兰与他人有私,借口秀兰迟到而责备不已。 显然府僚并不对妓女平日的生活了如指掌,所以才会怀疑秀兰的行为。可见,有些官妓的生活不全在官员掌握之中。不在官府点集时妓女可与其他人往来吗?话本《月明和尚度翠柳》中红莲所说为“专一”在上厅祗应,又是何种意思呢? 唐代时,营妓就有在外居住、官府宴饮时再召集妓女到场的情况。“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13)《北里志》中所载官妓居北里亦可招呼他人。 宋代营妓也有自己的住所,朱熹、唐仲友案中涉及的妓女王静、沈玉、张婵、朱秒、沈芳、许韵都有个人住处(14),如“张将仕、韩天与往弟子许韵家饮酒”(15),还在所住处与他人发生争执。 妓女冯妍的故事较完整地呈现了官妓入籍、脱籍、居住在外的境况: 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四,姿貌出于辈流,且善于歌舞。本谢氏女也。其母诣郡陈状云:“卖此女时才五岁,立券以七年为限。今逾约二年矣,乞取归养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终身风尘中。”郡守张定呼问妍曰:“汝离家时尚小,能认母乎?”曰:“能认。”于是引谢媪至前示之,摇首曰:“非也。”张判所诉云:“既非真母,难以强取。免勘虚妄,逐。”谢便衔恨涕泣而出。妍还冯居,才入门,忽迷不识路。娼母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把手遮我。更不能晓解。”暨至房,便觉内障。告于郡,以疾求假。张不之信。因会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碍。与之酒,亦不知盏所在。犹以为诈,曰:“汝且归,只从当中去。”妍迂枉信足,遂堕砌下。始验其被疾,听除籍。遂竟失明。孙鼎臣为判官日尝见之,眸子宛然而其盲自若也。(16) 冯妍自幼被母卖入官府,成为官妓,略长大后,母亲依券讨女儿归。冯妍辨识后不认母亲,母亲未得带回女儿,独自离去。冯妍回到住所后突发眼疾,向郡守请假休息,郡守据平日宴会时见冯妍状况进行比较,才准冯妍脱籍。其中,冯妍有自己的居住处,并与假母即“娼母”同住。 在话本《单飞英》中,杨玉亦为官妓,且有娼母住处等。(17)此外,还有众多同列,以姊妹相称,落籍后仍付金帛与娼母。(18)名妓温琬为市妓,才华过人,同列亦有众人,郡将知道后,想将“欲呼琬入官籍,而辞以不笙歌,不足以备尊俎欢。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乃辍之”。温琬所遇多“当世豪迈之士”,郡将欲纳其入籍,并不为其住处之类所限,其中有女弟已在籍中,也同住一处。后来温琬终“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日不得在家,颇废书”(19)。可见官妓除官府点集外,可在家居住,并有娼母经营。文彦博晚年“既罢遣声妓,取营籍十余人,月赋以金,每行必命之”(20)。可见,官妓应官府点集外,有其他营生。所以上文所说府僚并不知道平日官妓的营生,营妓秀兰如有其他生活来源,也属于较为普通的情况,所以府僚才会对秀兰的迟到备加怀疑。 有些妓女则没有娼母管制: 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僧限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妓丧夫,家极贫。念欲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求舍随缘,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钱,号泣藏前掷钱拜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矣。(21) 该营妓婚配有偶,丧夫后家庭贫困。应是除差排外,不曾招呼他人。且念再嫁,远不同由娼母管制之妓女,活动较为自由,婚配限制较小。 综上可知,“专一祗应”是指一部分官妓,如红莲之类,只应官府点集,在家时并不再招呼他人谋取营生,故可婚配,也可以有自己的家庭。还有一部分官妓,除应官府点集外,亦招呼他人,推测此部分活动应与市妓无异。另一方面,市妓也可因官府籍入,温琬就是先为市妓,后成为官妓,故衙前乐人也可以“多是市井歧路辈”(22)。 二、祗应:迎送宴会、圣节 地方官妓籍入府衙后,所祗应活动包括迎送、宴会、节日活动等。 (一)迎送 官员上任、离任、途经某地,当地官员可差使妓女迎送。如“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此妓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博得欢心,“安国为之嗟赏竟日,赏以万钱”。(23)又淳熙年间(1174-1189),雷州太守“舟过城下”,在乐营将的带领下,“群妓迎谒”。(24)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诸番国”使节到达时,当地妓乐司也需要承应。政和五年(1115)八月八日,礼部根据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状,市舶司兴复以来,已去国外招使通贸易,然后“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俟相见罢,赴客位上马”,“并乞依蕃蛮入贡条例施行”,礼部准之。(25) (二)宴会 宴会中级别高的是皇帝赐宴,使两京府前妓乐祗应。一种是皇帝亦参与,如雍熙元年(984)宋太宗“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士庶同观。(26)还有一些规模较小,是皇帝与近臣之赐宴。太宗“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三馆之职皆预。中书、枢密院、节度使出使赴镇,宰相还朝,咸赐宴于外苑。以亲王或枢密宣徽使主其席,掌兵观察以上有特赐者,皆开封府乐营支应”(27)。另一些是皇帝敕设赐宴后,给予特别的礼遇,使官妓祗应。京师百官上任时,“惟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至陈和叔,仁宗嘉祐六年(1061)进士,除学士时,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土院敕设不用女优”。(28) 地方官妓在府衙宴会时多有点集。实际上地方性的公务、宴饮、聚会,都会点集官妓。如多景楼竣工,当地官妓以齐聚助兴。不仅在地方性事务中,官员以地方之名召集的宴会也会命官妓陪同,如前文所说秀兰等,此处不再赘言。 (三)节日 圣节为帝、后的生日,一般会有庆祝活动。妓乐是表演内容之一。此外,臣僚也可以在此日公筵招妓乐,如“天申节及人使往来之处,守臣休务之日,许用妓乐于公筵”(29)。其余上元节、乞巧节等节日,官府也会组织妓乐演出。正月十五时,开封府绞缚山棚,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30)。三月一日,东京仙桥“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31)。其他地区如成都等情况也相似。 也有较为特殊时候使用妓乐,以示庆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因降祥瑞,“雨露之恩徧加率土,应天下悉赐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枢密直学士任中正于,遵旨于“衙南楼前盛张妓乐杂戏”。(32) 迎送宴会、节日时的活动,从制度规定来看:其一,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享受妓乐。《庆元条法事类》中记监官之类,和职掌相类的官员,如发运监司、察访司、按察司官员到州县时,甚至常平官亦“依监司法”,州县教授、州县学职事等都不可预妓乐筵会。(33) 其二,不是所有场合、场所都可以用妓乐。如劝农时不得用妓乐。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时,应翰林学士苏绅所请,诏“沿边臣僚筵会,自今并不得以妓女祗应”(34)。即便是用妓乐时,妓女活动也要注意场所,“燕会之时,非得台旨,妓女不许辄入宅堂”(35)。 其三,不是所有时间都可以用妓乐。至少到南宋时便有规定“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州郡遇使命经过应管待者非”(36)。公私忌日也需要避讳。如与叶适相遇的妓女在“太守私忌”日,才可以得暇出行。(37) 但是,上述限制并没有很好遵守。如温琬为官妓时,要应不同级别人员的召唤,“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38);叶适所见妓女也说宴会频繁“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39)。所以官箴中才会提醒官员“若旬休公暇,欲与寮寀士友会聚,只为文字清饮,彼当不以我为简也。剖决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间”(40)。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侍御史汤鹏举言:“近年州县许用妓乐,遂有达旦之会,监司、郡守或戒约之,则哄然生谤。此风起于通判,行于司理,至于盗用官钱、官酒,苦刻牙人、铺户,恣纵市买,以至县官筵会之费尽科配于公吏。”不得不“乞于天申节及人使往来之处,守臣休务之日,许用妓乐于公筵,其余自总管、谋议官、通判以下,并不许擅用借用,违者委监司、郡守实时具奏”(41)。 三、售酒:妓女、文官体系与国家权力 官妓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差使——卖酒。宋代酒的销售对国家经济有较重要的意义。(42) (一)售酒 宋代酒楼无疑有妓女侑酒之事,但官府何时于酒库设置官妓售酒实不易考。至迟仁宗朝,已有官妓卖酒。例如李觏、陈烈有一天同往蔡襄处赴宴,“时正春时,营妓皆在后圃卖酒,相与至筵前声喏”(43)。已是由官妓为官府卖酒。 到南宋时,官库多用官妓售酒。《梦粱录》说:“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44)即使官妓在酒库卖酒,但真要见到还是要费一点周折,只有花钱打点其“家人”才可以点到花牌。“太平楼、丰乐楼、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45)参考前文所说,官妓之差排,祗直者应是指当值者数人,从府衙到酒楼向下轮值。 (二)官私妓女的合流 在售酒的过程中有两件大事:开煮和开清。南宋“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46)。《梦粱录》记时间略早,是在“中秋前,诸酒库中申明点检所,择日排办迎新”,“往蒲桥教场教阅,都人观睹,尤盛于春季也”。(47)在此之前“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官私妓女在迎煮之前,都会做好准备,其中妓女无论籍属何处,无论档次,“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而再办”。(48)等待迎新时,“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49)。“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袴,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着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妆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值。”(50)《武林旧事》中也载有相似的场景,都人对此都是习以为常,并不为怪。(51) 宋代官库“迎新”,妓女是这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迎新”中的一个标志,整个“迎新”活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民俗活动。活动中妓女不再是由籍属何处进行区分,而是以声名等分等级。美化的同丑化的身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走,妓女的身体超越了审美形象,超越了社会道德,对抗日常生活规范,与利益结合形成了一种民俗现象。再一次强化、也统一了官私妓女共通的身体的消费性。从根本上来讲,她们是一个时代的消费符号,官府通过酒的销售与展示,显现出对妓女身体的控制。 (三)妓女、文官体系与国家 国家身体(52)在根本上对于妓女是警惕的。其中皇帝代表国家时,因为雅乐“所以飨宗庙、格神衹、法阴阳、来福祉者,盖雅正之音与天地同和也”(53),此中的妓女是国家仪式中的符号表现,其性别特征与身份都不同于世俗妓女。在这些场合中,代表国家的皇帝是抵制世俗妓乐的。仁宗自言“不好乐,至于内外宴设,不可阙者,勉强耳。居常多恬然默坐,至于声妓荡心之物,固不屑意”(54)。当皇帝代表臣子、代表民众的意愿时,妓女表现出的是一种天下祥和、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场面,皇帝可以同臣、民同乐无妨,如节庆时,皇帝坐于楼上与民众共同观看妓乐表演。 监官、州县学职事等官员也是需要抵制拒绝声色诱惑的,不能参加妓乐筵会。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延边地区的官僚不预妓乐,正是为了使国家身体安全,才要克制妓乐的诱惑。在这个体系中妓女的形象是危险的。一旦这些官员有所越轨,“每赴宴集,亵狎娼妓”,其行为便是“有玷国体”。(55) 国家身体对于这种危险以两种方式传递给他者。一方面,以同乐为名义,在文官体系边上,保留庞大的妓乐体系。文官体系之身体在保证国家身体运作后,妓乐作为一种特权,一种礼遇,使文人之情怀仍是有所寄托,而且官员并不需要像百姓一样为此支付财物。但是官员与官妓的肉体关系被排除在外,国家需要防止妓女对文官体系的侵害。妓女可能与官员发生关系,尽管对文官体系存在潜在的危险与危害,但仍在国家的控制之中,妓女与官员的暧昧关系成为国家身体可以接受的风险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售酒,国家身体将这种已经被文官体系作为一种特权的妓女,转化为了一种经济利益,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盈利方式。国家在明知“今之乐则不然,荡情性,惑视听,开嗜欲之源,萌祸乱之本,无益于至治也”(56)的时候,将欲望转变为利润。 在这个层次中,国家身体正大通透,官员身体是有污点的,百姓纠缠于欲望,妓女的身体就像工具被其他身体消费利用。官员与百姓都成为妓女、甚至是官妓的消费者,而妓女身体远离了礼制,再到售酒等各种商业经营中展示,身体的欲望成了最重要的消费内容之一,妓女的身体转换着表现价值,从国家、官员的特权到大众的普遍消费。这个过程中,不变的是男性以绝对优势掌控着对妓女的权力。 随着文官系统的壮大,妓女身体的消费遍及各地,妓女与官员的关系越来越难控制,当这种特权逐渐侵害到官员乃至整个官僚体系本身的形象、利益与地位时,这个集团内部就会产生不同的声音,反省滥用国家给予官僚享受妓乐特权所带来的后果:对于自身形象、权力影响力的贬抑。南宋官箴中,越来越警惕妓乐造成的越轨行为。南宋晚期颇具声名的学者杨简在任职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罢妓籍,俾之从良”。 何谓罢妓籍,俾之从良。坏乱人心莫此为甚。盛妆丽色,群目所瞩,少年血气未定之时,风俗久坏,其能寂然不动者有几?至于名卿才士,亦沉浸其中不知愧耻。每每发诸歌咏,举世一律不以为怪,人心蠹坏,邪僻悖乱,何所不至?前代乱亡之祸皆基于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艺之俗成而绵祚八百,后世君臣胡得无惧,而官僚士夫中怀大欲袭循流俗重于罢去,致国家受末流之祸,呜呼痛哉!(57) 此处的罢妓籍绝不是为了使妓女转变生活方式,而是再一次重申了妓女身体的危险性,要求名卿才士、官僚士夫远离盛装丽色的欲望,并将这种群体的诫惧联系到国家安危,对官僚群体地位进行巩固与提升,而妓女的身体成为败坏风俗、人心蠹坏的表现。妓女的身体又一次遭遇贬抑。 ①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1《教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②岳珂:《愧郯录》卷13《京师木工》,知不足斋丛书本。 ③庞德新:《从话本及拟话本所见之宋代两京市民生活》第五章,龙门书店1974年版,第163页。 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出版说明”,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⑤罗氏之书现流传版本中因含有元代个别人名,被疑是宋人书之元刻本。本文所引《醉翁谈录》史料,根据地方行政制度判别,应是宋代之事。 ⑥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孙棨撰,曹中孚校点:《北里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吴自牧:《梦粱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⑦[明]冯梦龙辑:《古今小说》卷29,明天许斋刻本。 ⑧黄庭坚著,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⑨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记元人徐大焯《烬余录》载,宋代时,“每年选官伎十人,并给身价十千,五年期满……轮值之岁,各人值一月”。多为他人引用。盖据庞德新等先生考《烬余录》为伪书可能性较大,故不可证。[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9《宋时官妓》,《笔记小说大观》(第34册)影印上海进步书局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451页。 ⑩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之7《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11)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丁卷第12《西津亭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639页。 (12)[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馀》卷16《香奁艳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第616页。 (14)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页、第854页。 (15)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4页。 (16)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丁卷第四《娼女冯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6页。 (17)王明清:《摭青杂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龙威秘书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10页。 (18)王明清:《摭青杂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龙威秘书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10页。 (19)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七《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74页。 (20)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第740页。 (21)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丛书集成初编据稗海本排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页。 (22)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1《教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23)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乙卷6《合生诗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24)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辛卷8《横州婆婆庙》,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7页。 (2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3,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7750页。 (26)《宋史》卷113《赐脯》,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第2700页。 (2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0《王礼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0页。 (28)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2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3,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572页。 (30)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6《元宵》,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页。 (31)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1页。 (32)黄休復撰,赵维国整理:《茅亭客话》卷1,《全宋笔记》第二编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3)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迎送宴会》,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2页。 (3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2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508页;并参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等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癸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95页。 (35)胡太初:《昼帘绪论》“远嫌篇”第一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2册,第726页。 (36)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迎送宴会》,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37)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7《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38)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7《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39)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丁卷第十二《西津亭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639页。 (40)胡太初:《昼帘绪论》“远嫌篇”第一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2册,第726页。 (4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3,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572页。 (42)设法卖酒其中一说是由王安石所定,主要依靠资料为《燕翼诒谋录》所载“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王栐、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后世多引此材料说明,无其他佐证。据李华瑞所考,天圣年间即有“设法”之说。故此说待考(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3)不著撰人,赵维国整理:《道山清话》,《全宋笔记》第二编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44)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10《点检所酒库》,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4页。 (45)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武林旧事》卷6《酒楼》,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46)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武林旧事》卷3《迎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页。 (47)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3《八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 (48)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49)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50)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51)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武林旧事》卷3《迎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379页。 (52)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认为世界身体是以“拟人说”为基础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美]约翰,奥尼尔著,张旭春译:《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具体到一个国家时,便是将一个国家构想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包含了国家精神、国家凝聚力的整体。 (5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4之1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29页。 (5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4之1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29页。 (5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70之31,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960页。 (5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4之1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29页。 (57)杨简:《慈湖遗书》卷16《论治务》,四明丛书约园刊本(宁波),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