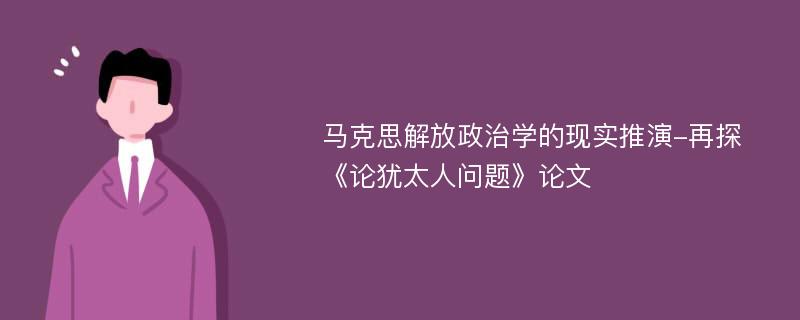
马克思解放政治学的现实推演
——再探《论犹太人问题》
徐博雅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 作为马克思阐析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经典文本,《论犹太人问题》被认为是马克思解放政治学的理论起点。从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过渡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从政治的解放到社会的解放;从抽象的个人的解放到现实的个人的解放,从观念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这三个维度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但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理论侧面,为理解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关键词: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政治解放;人类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深刻阐述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其所形成的基本政治观念贯穿于马克思之后所有的思维轨迹之中。作为马克思详细谈论人的解放问题及其历史过程的重要文本,《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蕴含的共产主义思想萌芽已初现,尤其是他主张“只有对政治解放 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1]167,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政治国家远不是历史的尽头,现实的矛盾和社会历史的未来必然性指向了更高的阶段。本文从马克思解放政治学的三个维度对《论犹太人问题》重新解读,继续说明他关于人类解放的推演逻辑,从而证明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一、从政治的解放到社会的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关键主角——犹太人——在当时的德国受到双重打击压迫。一方面,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其宗教身份必然受到“特殊的”压迫,这使得犹太人虽在形式上立足于普遍的基督教秩序之中,而实质上却被排除在体系之外,是一个“非部分的部分”;另一方面,在德国,不论是谁,在政治上都没有得到解放,也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秩序本身对于全体德国人而言形成了“普遍的”压迫。由此,犹太人遭遇了双重打击,成为了政治权力链中最底端的一个群体。也正是因此,犹太人的解放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布鲁诺·鲍威尔在这里出场,他对犹太人要求政治解放的呼喊给出了一个看似革命的答案——消灭宗教本身。在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才是人类及其世界追寻的终极答案,宗教作为自我意识发展的阻碍,必须被超越,甚至被消灭。费尔巴哈说神学之真正意义是人本学,“在属神的本质之宾词跟属人的本质之宾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从而在神的主词(主体)或本质跟属人的主词(主体)或本质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2]15。鲍威尔更进一步提出,不仅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而且这种外化最终反过来成了不受人支配甚至支配人的东西:人性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动物教”。[3]114宗教在本质上是狭隘的神灵崇拜,只不过各宗教之间都以普遍、绝对的真理自居,互相排斥,所以都未能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狭隘性。所以鲍威尔比费尔巴哈更为激进,他并不是将异化的上帝的本质重新归还于人,以此让宗教神学自行消解,而是主张要从外部铲除和消灭宗教,让普遍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得以实现。不仅如此,鲍威尔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认识并不笼统,他对犹太民族有更多的宗教偏见。鲍威尔特别认为,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特权,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特权(这种特权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单单要求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而不放弃犹太人的社会特权是毫无道理的,这实质上有利于维护德国当局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另外,鲍威尔说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前提,但是他要求的普遍的宗教解放首先就是没有前提的解放;他也没有发现政治解放本身的局限性。
相比于鲍威尔,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从虚幻的天国引入尘世。他指出,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犹太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德国它是神学问题,因为在德国真正的国家还没有产生,犹太人问题表现为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对立问题;在法国它“是立宪政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 的问题”[1]168,因为在立宪制的法国,“这里还保存着国教的外观 ”[1]168,犹太人与国家的关系还有着对立的外观;只有在新生的美利坚,国教被废除,民主共和制已经建立,宗教信仰从此成为个人的信仰,政治解放得以真正完成。但是,政治解放的完成也同时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抱有不同信仰的宗教信众同国家的关系才真正以最纯粹的形式得到解放,而鲍威尔却在这里停下了。
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 摆脱某种限制,国家 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 ,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 。”[1]170也就是说,“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 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 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1]171,宗教不再作为国家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它逃遁到社会领域,与个人直接相对。归根到底,宗教和国家都是“异己的他者”,当然他们也有明显差别,政治国家取代基督教国家明显具有进步意义,它是社会解放历程的必然阶段,但是政治国家是通过将自身作为中介来联结和统一相互分离的个人的。因此,国家对于个人来说依然是异己的存在物,是对现实矛盾和分裂的遮羞布,它表面上是在组织社会力量,而事实上却是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具体来说,政治解放的局限就在于它未能触碰到市民社会,没有深入到人类社会的现实维度。虽然在法律层面上,等级制已被政治解放废除,私有财产的限制也已破解,每个人在名义上都拥有了象征解放的政治权利,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市民社会的深处,就会发现财产的等级差别依然无法撼动,私有财产作为现实权利的表征仍然稳固。伴随着基督教国家瓦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变成了分散的、利己的单子,一切受到压抑的欲求得到充分释放,而政治国家直接把这种人的自然性当做理所当然的前提,并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一方面,个人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和财产差别。因此问题在于市民社会必须发生改变,这个中介——政治国家必须追问自己的根源,而不是用法律的保证去解决问题,因为法律不过是私有制的表象罢了。归根结底,只有当人与人的关系取代了人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个人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他人和由这些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承认。
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 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189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已经获得了政治解放的社会里仍然受到奴役和控制,国家从宗教中获得的独立性最终以自己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从外观上消灭了宗教,自己却成为了现实的宗教,而宗教本身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进入了私人的领域。这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万万想象不到的,因为人的解放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自我意识对宗教意识形态的超越本身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它们不是在同一个空间中对接,必然会发生错位。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只有社会本身获得了解放,人类解放才能最终完成,两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从政治的解放到社会的解放,这个关键概念的转换意义是重大的。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从传统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他不再执着于黑格尔式的理性国家观,甚至对政治国家本身也不再迷恋。社会成为承接国家的真正自由的场所,政治也开始从国家内部走出来,从马基雅维利迈向了卢梭。另一方面,这种转变的现实意义或说历史意义,则更为深远。政治的解放仅仅停留在国家意义上,它只是一种“治理”的、“管理艺术”的政治解放,它从本质上只能属于一部分人,即拥有管理权力的那部分人;而社会的解放是要从根本性质上改变前一种政治,它要求所有人的自由。马克思在这个转变中为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特别是后现代的激进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合法性。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是由市场原则定下基点的管理型社会,形式的自由永远由社会的例外来做补充,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现存的被管理者,甚至游荡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浪汉、难民、黑人、女性等特殊群体,他们构成政治解放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是生成性的,一般而言往往只是被意识形态遮掩了,而资本主义真正的意识形态就是犹太人问题,就是私有财产。政治的解放是这种意识形态被隐蔽地承认,而社会的解放才能将它彻底破除。因为社会的解放是个人从私有财产中得到解放,是国家把权力交还给它的主人——全体人民。
根据快线的功能定位,分析深圳湾口岸站—松山湖北站的线路条件,13号线车站分布呈中心城密集、外围稀疏的特征。南山组团平均站间距为0.9 km,外围光明组团平均站间距为2.06 km,跨境段松大组团平均站间距为4.56 km。通过对列车运行速度分别为80 km/h、100 km/h与120 km/h情况下的运营时间进行对比分析(见表2)得知,当速度目标值为100 km/h时,全线运营时间较80 km/h可缩短5.8 min,节时效果明显;且较120 km/h的速度目标值,列车全线运营时间仅增加2.2 min,相差不大。故推荐13号线采用100 km/h的速度目标值。
政治解放又可以看作是观念的解放。作为类存在的国家公民已经摆脱了宗教的束缚,犹太教、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都不再以普遍性的必然遵守的权威对个人造成压抑,它成为了每个人自己的私务,个人可以自主选择信教与否。宗教的本质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共同性 的本质,而是差别 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 、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 的表现——它最初 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特殊的颠倒、私人的奇想 和任意行为的抽象教义。”[1]174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彻底消灭宗教,但至少它使得宗教私人化,而不再作为国家意志强加于人。但是,这种私人化依然是一次必须被认可的进步,这一方面在于政治解放是对宗教的批判,揭露了宗教的异化本质;另一方面,宗教进入人们的个人生活,其神学的精神统治力不再是必然的,而首先需要得到个人的认可。这样,政治解放,至少是部分地,具有了观念解放的意义,或者说极大地促进了观念的解放。
野村谷有酒堡,酒堡底下是酒窖,酒堡城头高张酒幌子,“酌道酒庄”四个字赫然入目。酒庄专事藏酒,这等营生远近恐独一无二。藏酒名码标价,论斤论坛,纯粮固态发酵的各标号高度酒,每坛分量不等,藏家选定即编号定格,记录姓名年份,在恒温恒湿的地窖密封久藏,直至预定的出窖开封日。
二、从抽象个人的解放到现实个人的解放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解放政治学的第二个维度是从抽象个人的解放到现实个人的解放。他指出,政治解放只是对个人解放的抽象表达。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国家从宗教压迫的枷锁中挣脱,每个人都拥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公共事务成为了个人的普遍事务;另一方面,宗教观念并没有因为政治解放的完成而消失,个人依然可以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财产资格被取缔也没有影响私有财产现实地发挥作用。
在“现代国家”中,人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环节得到政治解放、获得自由的;人摆脱宗教的控制是以国家的名义来宣布的。因此,在政治解放完成后,个人的解放依然只具有抽象的形式。首先,政治国家表现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共同体。在国家中,人被看作是类的存在物,他的现实的个人生活被掩盖起来,因而形成了虚伪的普遍性。其次,个人政治权利保障得到官方的承诺。国家以法律确认和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信仰自由、保护私人财产、保证平等和安全等权利,而这些权利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能理解的限度内出现的,而并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最后,公人和私人的二重化。“人分解为 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宗教教徒和公民”[1]175,原来封建社会中被反对的一切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政治国家驱赶到私人的领域。
那么应到哪里去寻找现实的个人呢?答案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市民社会中,人才把自己和他人看作现实的个人,而非类的存在物:“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 中得到解放。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 ,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 。”[1]187在这里,天然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并把这种天然性当作不需要再加以阐述的前提接受下来,把信仰自由、私有财产、平等、安全等个人利益变成崇高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公民生活、政治共同体等要素对致力于实现政治解放的人来说,就成了固守利益的武器。私利成了公义,公民为自利的个人做嫁衣,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的身份屈从于私人个体的身份。因而,不是公民,不是政治人,不是人为的、寓言的、抽象的人,不是法人,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个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这个人的解放必须通过对政治国家本身的批判才能实现,而因为政治国家出生与成长的秘密源自市民社会,因此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实现人的解放,也即现实的人的解放。
鲍威尔对政治国家的崇拜实质上是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他把现代政治国家当作人类自由可以充分实现的共同体。在他看来,人的自我意识源于他者的认可与承认,然而在基督教国家,人的自我同一性被认为是一个伪命题,“他者”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超验形象,神对自我的承认只在梦幻的天国中才有意义。因此自我意识在本质上还是同自己——尽管是异化的自己——发生关系,人由此接纳了异己力量对自我的支配。鲍威尔马上得出结论:只要宗教被政治解放废除,自我意识便能够在国家之中成长,构建起自由联合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承认,人的自由确实是一个关系范畴,但这个关系不是同异己他者的关系,而是个人同自己的他者之间的关系。鲍威尔对政治国家的崇拜,同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国家崇拜并无二致,前者只是对后者的哲学抽象。换言之,个人并非真正获得了解放,而是抽象的个人获得了解放。因为政治国家和宗教一样,依然独立于个人之外,并与之相对立,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然是抽象的个人,因为他们在其之中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虽然这个公民身份是由现实的个人支撑的,但仅是一小部分的个人。
观念的彻底解放,即宗教神学的彻底消除,不是在观念中完成的,而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现实地得到解放。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4]134为此,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基础。犹太人政治上的被歧视由其社会权力得到平衡,“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1]194犹太教能够与基督教同时存在,不是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社会稳定需要一个绝对被排除在秩序之外的他者来承担社会全部的恶,而仅仅在于实际的犹太精神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体现——“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政治解放就是市民社会的解放,它让实际的犹太精神得以自由驰骋。“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1]194,犹太教在现代国家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它不再需要过多的理论和思辨来证明自己的真理,实践成了它最雄辩的证明。正是以这种方式,犹太教实现了最普遍的统治,把整个人类、甚至整个自然界变成屈膝在利己主义需要面前的奴仆,变成已经异化的、没有思想的动物,他们唯一的意识就是去交换、去买卖。
现实的解放必然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 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1]198,这也就是马克思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喊出的“消灭私有制”。在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为实现这种解放寻找到了物质力量。“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 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 ,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 ,而是一般的不公正 ,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 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 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 ,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 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 这个特殊等级。”[1]213
三、从观念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
马克思的这个转变是惊人的,整个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都或多或少来源于此。在政治解放的结尾,马克思敏锐地找到了人类解放需要迈出的下一步,这几乎中断了传统政治哲学漫长的理论历史,也让十九世纪之后的世界政治运动有了新的主题。
从抽象个人到现实个人,这是人的主体性第一次被普遍地承认。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有近乎严苛的要求,他不同意鲍威尔,也反对费尔巴哈,认为前者沉迷在自我意识里,而后者也仅仅触摸到人的一个类身份,他们两人没有把“人”解释完全,至多只提到了某个片面。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35而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是属于市民社会的,这就规定了现实的人的解放必须摆脱政治身份,去市民社会、现实生活中寻找。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曾经做了非常深刻的延伸,“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5]666,这正是马克思当初未能言尽的后续。
更为重要的是,抽象的个人,即政治国家赋予的公民身份,与现实的个人——处在社会关系利益纠结中的独立个体,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在过去两个世纪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今日呈现出新的形态。自由民主制确保了每个人拥有的抽象政治权利,这已经为世界范围内的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霸权所承认,这种纯粹形式的自由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历史阶段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主导价值观。但正是在这种纯粹口号的自由宣言下,却有一大堆糜烂的社会灾难作为补充:第三世界的经济凋敝,社会紊乱;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的局部热战;叙利亚奔向欧洲的难民冲击……在这种抽象的解放背后,最真实可触的反而是连基本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的个人命运。这并不是什么人的解放,哪怕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把犬儒精神发挥到极致的那些安分守己分子,也要面对私有财产和市场规则的暴力。由此可见,现实的人寻找解放的使命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状态。全球化的资本狂潮为陷入其中的世界公民们建造了一个天堂般的幻想空间,却又在另一边汲取着这个世界最本源的能量——人本身,它空空许诺了一个自由的身份,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剥削和奴役众人。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尤其需要重提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观点,把现实的人的解放当做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从观念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初步显现;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为这种崭新的哲学找到了物质载体——无产阶级,他也由此开启了自己探寻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征程。从观念到现实的回归是马克思突破德国哲学思维惯性的一次伟大尝试,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精神、这种指向实践的理论精神塑造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从康德开始,德国的哲学就是一场思维的漫长旅行,康德把真理留在了现象界,这种强横的设定是意识首先涉险建构世界的尝试。黑格尔批判康德“把某些东西预设为真理”,而忽略了这些预设的东西“本身是应该先行审查的。”[6]49但是,黑格尔却并没有借此否认思维的第一性,而是主张精神可以自在自为地发展自己,而不依赖人的主观的干涉。到了后来,这种精神崩解为形形色色的碎片,有的取名为“自我意识”,有的取名叫“唯一者”……甚至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也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在哲学家们沸反盈天的争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朝现实瞥一眼。唯有马克思,在德国人民的苦难中才发现了这个弥天大谎,进而开始向德国的现实宣战。
渝黔边界地区主要包括:重庆的黔江区、江津区、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南川区、武隆区、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等“五区四县”(总面积2.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75.49万人,分别占全市的34.47%、18.7%),贵州省遵义市的习水县、桐梓县、道真县、务川县、正安县,铜仁市的沿河县、松桃县等“两市七县”(总面积3.5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42.83万人,分别占贵州省的20%、26.3%)。
2007—2017年世界刨花板进口额排名前5位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俄罗斯和伊朗,2007年依次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比利时,2017年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美国进口额始终位列第1,其世界占比虽存在波动,但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为42%,2017年为19%;德国始终位居第2,世界占比总体变动不大,在10%上下波动;排名第3至第5位的国家则变动较大,且各国世界占比总体差距较小。
在资本设定的全球秩序里,今天大多数西方人所获得的也不过是一种观念解放罢了。他们陷于对自由的疯狂追逐当中,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狂热的信徒,甚至高呼“历史的终结”这样荒谬的结论。但被他们忽略的是,这种自由、这种解放只是由意识形态所保证的罢了,至多加上法律的承认。意识形态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法律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法律,只有针对阶级统治本身的解放才可谓之为真正的解放。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强烈信念正是从这里寻找到哲学起源,而他开辟的这条道路至今还吸引无数人朝前迈步。
多胎之一葡萄胎主要指一个或多个正常胎儿合并完全性葡萄胎(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 CHM)或部分性葡萄胎(partial hydatidiform mole, PHM),其发病少见。近些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明显增高,多胎之一葡萄胎的发病率也随着增高。与单纯的葡萄胎相比,其产前诊断的时间相对延迟,并发症更多,发生恶变的几率也更高[1,2]。本文通过分析3例双胎之一葡萄胎的临床资料与妊娠结局,以期对临床诊断及处理做出指导。
四、结语
通过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至此,马克思已经找到了从观念解放到现实解放的现实路径和所需要的阶级力量,但是这种认识仍然还是哲学推演的结果。为了进一步从经验的事实中解释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他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最终提出了“劳动异化”概念和剩余价值论。哲学的批判起到了先锋作用,促使他后来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进而确立了新的世界观,而政治经济学则实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正是得到了这两者的支撑。
在1848年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转入低潮,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迟迟没有到来,这一度令人们感到悲观失望。马克思的哲学是不是被历史证明为谬论了,这个问题萦绕在无数理论家、革命家的脑海中。市民社会一再展示出自己的强大能量,它总是能在那些最危险的历史关卡中存活下来,并随着时代变迁调整自己的生存形态,同时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犹太精神”,“只有作为市民社会革命的政治解放才能真正结束专制权力或专制统治的历史”[7]。直到俄国的革命终结了这一切,但这种终结并不是依靠摧毁强大的资本主义,而是摧毁了较为弱小的资本主义。至于今日,资本已经完成了全球化,实现了自己的最终进化。我们发现,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资本肆意妄为,生生镶嵌到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里,把“不自由”的基因植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现实的解放必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宣战,这不仅是200年前马克思的结论,更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我们也不应放松对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的警惕,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我们努力奋斗的根本信念。唯有如此,社会主义的旗帜才能继往开来,更加自信地飘扬在这颗星球上。
A组30例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分别为(24.95±2.46)min、(20.76±3.62)ml、(3.86±1.41)d。B组22例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分别为(52.01±7.13)min、(60.03±7.08)ml、(4.39±2.39)d。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的t值分别为19.696、27.078、2.107,P=0.000,差异有显著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
[3] 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杨晓东.政治解放的不可逾越性及其当代价值[J].岭南学刊,2008,(4).
收稿日期: 2019—06—04
作者简介: 徐博雅(1993—),女,安徽淮南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6-0041-06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6.006
责任编辑:武晟
标签:马克思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政治解放论文; 人类解放论文;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