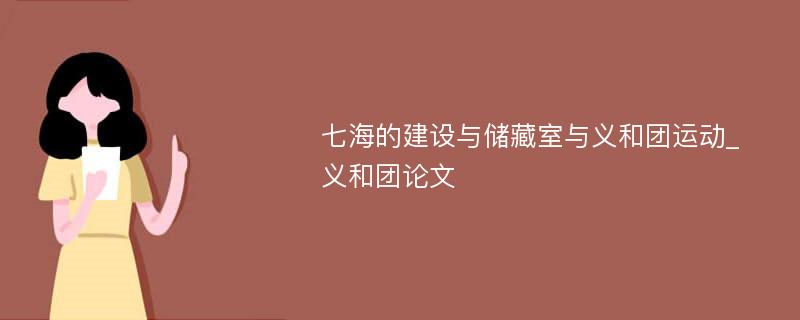
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8587(2000)04—0008—10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将永远被人们所纪念。但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确沉碴泛起,鱼龙混杂,使得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酿成严重恶果,不免引起种种非议。如果我们深入探讨19、20两个世纪之交的清廷政局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造成义和团之在京畿地区的“轰轰烈烈”,最终惨遭八国联军和清军的联合镇压,与一个在戊戌政变以后崛起的新的政治集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的疯狂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废立”阴谋的挫折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六君子”被杀,康梁出逃,光绪帝被囚禁瀛台。但是,建立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体制上的顽固派当权是十分不稳固的。慈禧太后年已六十有四,行将就木,而光绪帝刚及“而立之年”,“一旦山陵崩”,光绪帝马上可以重揽大权。面对这样一张时间表,难免使参与鼓噪太后垂帘听政的大小官吏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忧心忡忡。慈禧太后于光绪帝成年之后重新垂帘听政,也不合传统封建专制的“家法”,必须寻找新的理由以巩固她垂帘听政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1898年9 月的政变只是整个政治格局变动的开始。政变发生之后,围绕着光绪帝的存废,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面临重新再分配的形势。
废立阴谋在“百日维新”期间即已风传,有所谓天津阅兵即行废立之说,但系无稽之谈,不足深论。但废立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甚嚣尘上,则并非空穴来风。9月23日,京师即传出消息,“皇上病势沉重, 恐致不起。”“不起”,则不需废立,径选后嗣继大统即可。因此,外界最担心的是谋害光绪帝。于是即有“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18—419页。),又有疆臣反对之奏。废立之意,出自慈禧:
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注: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阻挠废立,英国的态度最为积极。戊戌政变之后,英国兵舰就开到大沽口外,《字林西报》则发布种种消息,怀疑光绪帝已经被谋害,认为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注:《北京之谜》,《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月6日,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489页。)这种否定慈禧太后统治合法性、 为列强瓜分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的言论引起了清政府的担忧。10月16日,庆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正式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光绪帝还健在,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538页。)清政府立即照办,于18 日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548页。)。 19日,太后召集宗室亲信大臣开会,“某亲王已预遣其子入宫,以便陟位,后有大臣谓恐外人干预,遂止。”(注:《知新报》载《路透电音》,1898年10月20日,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6页;《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446页。)显然,要实现“废立”,必须排除列强的干扰。
在废立光绪以后,入嗣大统的人选几乎是非端王载漪之子溥儁莫属。光绪帝即位之时,清廷曾一度发生“礼仪”之争。同治死后无嗣,慈禧太后定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但光绪帝无子嗣,废立之后,必须在近支王公溥字辈中物色后嗣。道光帝遗子九,四子即位为咸丰帝外,长子奕纬有孙溥伦、溥侗。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殇,均无子嗣,五子奕誴子载濂(注:1899年6月19 日《清议报》引日本《时事新报》消息:“翰林院学士某曾谓人言:顷者西后迎贝勒载濂子溥某于宫中,待以太子之礼。某年甫十一。”(《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383页)不确。载濂无子,当为载漪之子溥儁,时年正好十一岁。)、载漪、载澜、载瀛、载津,仅载漪有子溥僎、溥儁,载津有子溥修。六子奕訢有子四,载澂、载滢、载濬、载潢,仅载澂有子溥伟。七子奕譞,子载湉过继咸丰外,载洸无嗣,载沣尚无子嗣。八子奕詥子载涛,尚无子嗣。九子奕譓有子载沛、载澍,沛子溥伒,因此,在道光后代中,当时有嗣皇帝资格的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溥侗;五子奕誴之孙溥僎、溥儁、溥修;六子奕訢之孙溥伟;九子奕譓之孙溥伒。在此七人之中,溥伦、溥侗父载治至郡王,早于光绪六年卒;溥伒父载沛仅至贝勒,早于光绪四年卒,且三人均已成年,无论谁即位,太后即不能听政。因此,实际上只能在道光五子奕誴、六子奕訢孙辈中选择后嗣。奕誴一系载津已于光绪二十年卒,爵仅至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其子溥修自然不可能入选。奕訢去世不久,孙溥伟年届十八,已届婚龄,如入嗣大统,慈禧太后即不久于听政之位。因此,在慈禧看来,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注:“其时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依伦次皆可当璧,而载漪平时得太后欢心,故立其子”(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 第478页)。)9月25日,逃亡到上海的康有为向英国驻沪领事班德瑞叙述了有关“废立”的宫廷阴谋:“关于废立之议已经酝酿了一年了,西太后常威胁皇上,说如果他不顺从她的意思,她便废掉他……将来的局势是,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按:指大阿哥溥儁)将要继皇上登基,西太后将成为真正执掌实权的皇上,而她却是沙俄的走狗。恭王的孙子,一位十八岁的孩子,拒绝继承皇位。”(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527页。)据莫理循在10 月得到的消息:“选定的继承人是端王的年方十岁的孙子。”(注: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昭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按, 此处“孙子”应为“儿子”之误。)
溥儁这种明显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班薰心富贵之徒”(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第479页。),使得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以端王载漪为中心的“大阿哥党”。
二、“大阿哥党”与“己亥建储”
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琮次子,咸丰十年袭贝勒,光绪十四年加郡王衔,至二十年晋端郡王。光绪十六年、二十四年叔辈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相继去世,载漪的地位仍然无法与光绪帝之弟、袭醇亲王衔的载沣相比,因此在政治上很少有所建言或行动。戊戌政变之后的“废立”,把他推到了前台,而他为了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便以百倍的疯狂竭力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宝座。而外国的阻挠“废立”,成了他的心头之病。
“大阿哥党”的核心人物是刚毅。戊戌政变以后,荣禄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并掌武卫军,入值军机处,权倾一时。协办大学士刚毅在朝中地位仅次于荣禄,与荣禄积不相能。“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注:罗惇曧:《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35页。)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均投靠刚毅(注:刑部尚书赵舒翘后被处死,不少文献把他列入刚毅一党,其实不然。慈禧太后后来说,“上年载勋、载澜诸人,自夸系近支,说大清国不能送与鬼子,其情形横暴已极,几将御案掀倒,惟赵舒翘,我看他尚不是他们一派,死得甚为可怜。”(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载《庚子国变记》第187页。),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庆亲王奕劻虽不属“大阿哥党”,但也一度依附载漪。庆亲王奕劻控京师神机营,为荣禄所忌,颇受压抑,乃投靠端王,力主“废立”。“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注:《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 5日,转引自《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409页。)。
在“大阿哥党”的积极活动下,1899年冬,“废立”之议复起。而在此前,清廷突然颁布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
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38页。)
这里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显然与“废立”有着直接关系,暴露了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们不惜与列强开战而“废立”的决心。但临到出笼,却是定溥儁为“大阿哥”。其中曲折,恽毓鼎是这样叙述的:
己亥(1899),上春秋二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
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惧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
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第477—478页。)
在徐、崇、启三人造访荣禄和荣禄与慈禧独对之先,荣禄就拜访了李鸿章。
合肥李文忠公方以大学士入阁办事。入阁办事者,犹言不办事也。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门外骑从喧赫,有宾客过访,则荣文忠也。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督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无理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而端、庄、刚毅辈仇洋之说,由此起矣,遂有庚子之变。(注:章华:《语林》,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四册,第321—322页。)
据说,当时荣禄告知废立阴谋后,李鸿章“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即以此言密陈于太后,“幸回天聪”(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载《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第479页。)。因此,由“废立”而变为“建储”, 是西太后权衡利害后采取的缓冲之策。因为只是“建储”,大阿哥党只能是大阿哥党,而无法蜕变为新“帝党”(注:“惟谋立大阿哥一事由荣禄主之,刚[毅]不与闻。盖刚性最急,固在速行大事,不欲多此一折也。”(佚名:《综论义和团》,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决心不惜一战以实现“废立”,反映了“大阿哥党”的狂妄;由“废立”而退至“立大阿哥”,又暴露了慈禧太后对现实危险的恐惧和“大阿哥党”的无奈。时势造“英雄”,也能造“小人”。1900年春天北方形势陡然变化,使得这批宵小之徒又突然变成了顺应民意、抗拒外辱“英雄”。
三、从涿州事件到“宣战”
1899—1900年之交的废立阴谋再度为列强所挫,“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为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注:惇曧:《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41页。)“适义和拳起,诩其术谓枪炮不入,乃大喜,以为天助,欲倚之尽杀使侨,以促行废立。”(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一,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向直隶发展,利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外国势力,成为“大阿哥党”的基本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发动存在着鲜明的互动关系。
涿州事件的处理,是整个局势发展的枢纽。1900年5月27日, 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了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当地政府陷于瘫痪,近畿形势陡然紧张。29日,列强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派兵进京保护使馆。从 5月31日到6月6日,列强增援驻京使馆的兵力约有450人。在义和团运动进一步高涨、列强入侵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清廷进退维谷,如何防止侵略战争的爆发,成为清廷应付局势的关键。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请增兵弹压,同时认为义和团“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约束不令滋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0页。 赵舒翘奉命前往涿州宣慰后,“刚毅虑赵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惇曧《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第35页)。)。这个政策,具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避免清政府与义和团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通过招抚义和团以维系民心,加强清政府的力量;一是抵制列强要求严厉惩办义和团的要求,同时又避免义和团的失控而遭致列强的大举侵略。因此,清廷在决定派赵舒翘等前往涿州时,并未丧失理智。但到 6月6 日晚的御前会议以后,安抚义和团政策的立意已明显发生了变化。(注:李文海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130—131页。)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定议时,衹荣相[禄]、礼王[世铎]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奕劻]、端王[载漪]、刚相[毅]、启[秀]、赵[舒翘]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文韶]则默然无语。(注:《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24页。按:赵舒翘时在涿州,不可能参加此会。)
御前会议之后,刚毅等前往涿州,“一意主抚”,直隶总督裕禄“初非袒拳者……知朝贵主用拳,遂纵拳以自固矣。”(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一,载《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7页。)山西巡抚毓贤则“日与端、刚通密函”(注:许指严:《十叶野闻》,载《义和团史料》下册,第760页。)。关于御前会议前后的变化,袁昶写道:
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罔。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复命。(注:袁昶、许景澄:《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义和团》资料丛刊(四),第167页。)
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对策,在“1900年5月20日以前, 列强虽然叫嚣武装镇压义和团,但主要还是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威逼清政府取缔义和团。”(注: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5月20日以后, 列强大量陈兵大沽口外,增兵天津,并陆续派兵进驻使馆,一是继续威逼清政府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二是防止使馆受到义和团的直接攻击,三是应付形势的突变,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清政府的希望。但自刚毅前赴涿州“安抚”以后,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京师局面日益失控。列强也已看清非直接干涉已无法保证驻京使团的安全,作出了向北京大举增兵的决定。6月6日御前会议召开的同时和以后不久,英、德、俄、美等国相继授权本国驻华公使和军队司令官可以与其他国家协同便宜行事。而到6月9日,英、俄等国公使都得到情报,清政府非但不能保证驻京使馆的安全,而且将派军队进攻使馆,根据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紧急请求,当天晚上,各国在津部队指挥官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以西摩尔为首的联军,于第二天清晨由大沽口赶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进京,由此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
需要注意的是,西摩尔联军之进京,固然侵犯了清政府的行政主权,但并非是直接针对清政府的宣战。而是什么原因促使清军直接参与与西摩尔联军的作战的呢?
在西摩尔联军出发的当天,清政府任命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个直接与外国公使馆打交道的衙门为“大阿哥党”所控制了。第二、三天,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并发生了董福祥甘军士兵刺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一面派员至使馆劝阻联军进军,并下令聂士成等布防禁阻联军入京。另一方面下令严惩为匪作乱的拳民。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禁阻联军入京的命令,是严格执行的——6月18日, 聂士成的军队与义和团民一起在廊坊成功地狙击了西摩尔联军;而惩办义和团民,却徒具虚文。这种对于谕旨有选择地执行,反映了“大阿哥党”对于政局的实际控制。
论者谓,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的巨大力量,已经使清政府无法加以镇压。其实,在6月10日以前,义和团在京师虽然已有活动, 但其大举进入北京城内,还是在6月11、12日以后。入城之时,并无阻拦, “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注: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页。)京师重地,听任大批团民武装进入,“终日任其街市往来,砍杀不绝。地面官兵,不敢阻止”(注:洪寿山:《时事志略》,《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90页。),这在列强已经增派援军进京的情况下,其严重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而“大阿哥党”就是要把事态引向与列强的直接军事冲突。
[刚毅自涿州]回朝,极言团民义勇可恃,并带团首晋谒端邸,甘言诱餂,端邸信尤深,日与团首计议,以为杀教民、毁教堂,洋人决不甘休,从此将洋人一网打尽,何难之有?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端王等决计惟团首之言是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注: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记事》,第80页。)
团民在北京的“滔滔而行”,为“大阿哥党”所利用和控制,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而且使“废立”和列强干涉的危机空前地增加了。
北京城内,并不像华北乡村地区那样存在着尖锐的民教冲突,团民入京之后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不仅偏离了斗争的方向,而且累及北京普通市民,引起了人们的疑惧。一位迷信而又排外的士大夫写道: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注:仲芳氏:《庚子记事》,载《庚子记事》,第15页。)
与义和团大举入城的同时,在京城还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王团”、“公主团”等,与义和团混合生长,在政治上逐渐受“大阿哥党”的控制。端王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等“赴端王府议话。”(注: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载《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188页。)在他们的鼓动之下,“两宫诸邸左右, 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注:《荣禄集》,《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 )李莲英甚至“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注:高树:《金銮琐记》,载《义和团史料》下册,第 729页。)与此同时,对于义和团“神术”的迷信,也迅速地在京城蔓延开来。
攻打使馆之议,早在戊戌政变以后不久就有风传。1898年10月6 日熙礼尔报告英国公使窦纳乐:“我的买办[吴懋鼎]告诉我:昨晚街谈巷议中有某些值得注意的说法,据说是军机处的一个成员讲的,要趁这留住北京的外国人为数很少的时际,将他们全部根除,烧毁各国使馆。我的部下昨晚是尾随在一群总理衙门属员身后,听到了这种十分令人担心的交谈。”(注: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因此,在1900年6月21日对外宣战之前,清政府首先向各国驻京使馆攻击并不是偶然的。
孝钦纳荣文忠言,已命护送使侨出京,勿任攻杀。荣预调旗兵二千以待,且言必先解直督裕禄任,乃免生他变。孝钦亦许之。其与克使商洽者即是事。端邸知之,乃潜使章京连某伪造使团照会,请归政于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万人入卫。偕启秀入宫奏进。孝钦果为所中,盛怒曰:“吾前此违众遏拳,皆为彼等安全计,乃以此报我耶!吾誓亦必报之,虽死不受其侮。”于是幡然主战,虽荣亦莫能进言矣。(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一据《景茀亭日记》,与恽毓鼎所述江苏粮道罗某叩荣禄递假照会之说比较后,认为“以端邸伪造为近”。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45页。)
因此,17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便呈一边倒的态势,“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注:《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338页。)至19 日,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决定进攻使馆,并于21日正式向列强宣战。虽然在进攻使馆和对外宣战的动机方面,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之间可能存在着区别(注:根据林华国先生的分析,慈禧太后企图挟持使馆人员为人质,以迫使列强停战议和(见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但是,此种意图只是见于个别奏折,而没有见诸任何外交文献之中。慈禧太后果真有此意图,那么,在列强向大沽口炮台发出最后通牒后,清政府不必采取宣战的措施,而向列强发出摧毁使馆的威胁,岂非更加有效?),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合力”,“大阿哥党”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进攻使馆、对外宣战与废立阴谋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废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本无需外国支持。西太后之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看外国使臣的脸色,是因为她怕影响同洋人的关系。如果西太后为了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不惜与外国决裂,那么,她尽可以对外国使臣的态度置之不理,径自实行废立。为什么一定要攻打使馆?为什么一定要等‘夷平使馆’后才能实行废立?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注: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第116页。)从形式上看, 问题的确是这样,但是,“废帝立储”不仅受到列强的干涉,事实是即使作为一个内政问题,慈禧太后也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不可能一意孤行。光绪皇帝反对对外宣战。在御前会议上和战两派的激烈争论,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强烈反对宣战的奏折,都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光绪帝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径行废立,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点,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应该十分清楚。宣战而不废帝,以争取京外官僚对于朝廷的政治支持,恰恰是慈禧太后政治上老练的表现。“使馆朝夷,皇位夕易”,只是“大阿哥党”的一厢情愿,而这个一厢情愿也是当时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的政治现实。在列强大举入侵之时,慈禧太后如果马上向列强妥协,与列强联手镇压义和团,那么已经成为京城义和团实际领导的“大阿哥党”骑虎难下,挺而走险亦并非不可能。由此看来,宣战而不废帝,又是慈禧太后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一段“钢丝”。6月30日,朝廷这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之由来:
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文中虽然不免有推卸责任之意,但特别提到“王公府第”,其中“祸起肘腋”一语的含义,治史者需深察焉。
四、“大阿哥党”的覆灭
从6月21日宣战到8月15日凌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两宫仓皇出逃北京,这五十多天,既是“大阿哥党”政治上的又一高峰,又是他们末路的开始。
与对外宣战的同时,清政府又颁布了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的诏令。“自载漪倡剿夷之说,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抚拳匪为团民,恐诸团游散无归,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注: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487页。 )不在注册之列的义和团皆为“伪团”,照土匪严拿惩办,其目的在于完全将在京城的义和团控制起来,供其驱使,并派往各衙门把守站岗。
宣战之后,“大阿哥党”又迫不急待地企图实现废立,甚至公然与慈禧太后争吵起来。慈禧太后后来回忆说,“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义和团)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载澜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扛,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载《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436页。 被视为伪作的《景善日记》记载6月25日载漪等人率义和团六十余人进入大内, “大有弑君之意”,被太后呵止,似乎并非毫无根据(见《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74页)。)
7月14日, 天津为联军攻破,庚申(1860)之役的惨剧即将重演,京城局势更趋紧张。不堪因战败而见笑于臣下的慈禧太后开始对主和派官僚大开杀戒(注:五大臣之被杀于清军败局已定之时,原因何在?无史料证明。袁绍在官渡之战失败后,对于事前谏阻决战的田丰的态度或可参考,《三国志·袁绍传》载:“绍之南也,田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且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慈禧太后于京城沦陷之前的心态可能也与袁绍相似。)。7月27日,吏部左侍郎许景澄、 太常寺卿袁昶以“莠言乱政”、“语多离间”下狱,于次日被处死。8月6日,联军攻杨村,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11日,联军突破张家湾防线,主帅李秉衡自杀,北京沦陷在即,慈禧太后又令逮捕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与先期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一并处死,徐桐之子徐承煜得意洋洋地到刑场监斩,并且拒绝按照大臣处死的规格行刑。五大臣或反对废立,或反对宣战,与“大阿哥党”的矛盾很深,他们在被处死之前,几乎都未经过审讯。“大阿哥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恽毓鼎言:“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义和团》资料丛刊(一),第51页。公元369年桓温北伐,于枋头兵败,回朝后废帝。 )把诛戮大臣与“大阿哥党”的废帝阴谋联系了起来,并非毫无根据。
8月15日,联军攻入北京,两宫出逃, “大阿哥党”开始走上了他们的末路。大学士徐桐悬梁自尽,其子徐承煜、启秀被联军捕获。崇绮逃至保定莲池书院,闻子葆初全家及老妻在京活埋自杀,悲痛自尽。
但随两宫西行的“大阿哥党”还在朝中具有相当的影响。随行的军机大臣有荣禄、王文韶、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后载漪补军机大臣,留出的御前大臣一缺由载澜递补(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46页。)。8月18日,两宫狼狈地逃到怀来,怀来知县吴永接驾,才勉强得到供应,稍后甘肃藩司岑春煊率二千兵丁前来扈驾,刚毅等人以岑违旨擅行,还极表不满。但行在的政治关系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日,光绪皇帝下“罪己诏”,但是,只敢将罪责推诸“大小臣工”,不敢涉及尚在左右的“王大臣”,但毕竟开始否定朝廷已定的政策。接着,清廷又下诏求言并决定前往西安,于是,吴永上奏十条,包括下罪己诏、派王大臣留京善后、镇压义和团和选拔通达时务人才,尤其是留洋学生(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资料丛刊(三),第417页。)等内容,预示着清廷政策将发生重大的变化。9月7日, 清政府正式下令剿灭义和团,认为义和团“为致祸之由”,把罪责推到了义和团身上。9月15日, 为响应列强的“惩凶”要求,奉旨来京“议和”的李鸿章在上海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上奏,要求惩办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王大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91页。)。
9月25日,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分别轻重”, 革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议处(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2页。)。 这样的“惩处”列强自然不能满意,经过反复讨价还价,1901年2月, 根据列强的要求,清政府被迫“惩凶”: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端郡王载漪及载澜改为降辅国公,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山西巡抚毓贤处死。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左都御史英年革职、斩监候;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斩监候,嗣改为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处斩立决。刚毅、李秉衡、徐桐均追夺原职,撤去恤典。(注:《辛丑条约》附件四、六,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9—1011页。刚毅已于1900年10月21日在侯马镇病死。)
在这场“废立”、“建储”的闹剧中的主角“大阿哥”溥儁,在两宫到西安不久,即“斥退出宫”(注:罗惇曧:《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第41页。)。他并不是一个“呆且鄙,知者知其不称”(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一,载《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7页。)的角色,虽“不喜读书,所好者,音乐、骑马、拳棒三者而已”,“音乐学问极佳”(注: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载《庚子国变记》,第219页。),如果没有己亥建储的闹剧, 他或许也会像红豆主人溥侗一样闻名于世。无论如何,“大阿哥党”的政治前途随着这位十几岁的少年走出禁宫,终于划上了句号。
五、在“义民”和“乱民”面前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起来以后,统治者对于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首先必须权衡政治上的利弊得失。用群众运动自身的诉求来衡量或评价执政者的对策,往往会背离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引出十分荒谬的结论。
当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几乎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吏都认识到,这是以往地方官“袒教抑民”的恶果。即使到赵舒翘赴涿州安抚义和团之前,仍持这一看法:
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9—110页。)
因此,此前的清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这是对以往“袒教抑民”对策的一种否定,是在对社会矛盾激化原因准确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政策犹豫。如果由此而逐步形成严格控制义和团对于教民、教会的盲目报复,坚持在民教冲突案件中政府应有的公正立场,以避免列强的直接武装干涉,造成国家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害,仍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政治选择。但是,废立问题已经造成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重大的分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政策选择,已经分裂的各个政治派系只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权衡利弊,提出各自的对策。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尖锐矛盾、并在戊戌政变以后在中央政府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大阿哥党”最终选择支持义和团,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失误。当时就有人评论道,庚子事变,“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注:《乱原二》,《中外日报》1900年 12月8月,载《义和团》资料从刊(四),第226页。), 这是对于清政府应负政治责任的比较准确的看法。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深重,华北千千万万的民众奋勇而起,凭借民间既存的组织、信仰等武器,走上反帝斗争的前线,无疑具有正义性。但是,正义的斗争一旦失去控制,演变成不加区别、不计后果地屠杀教民、教士,破坏铁路电线乃至一切涉洋之物,使他们融“义民”和“乱民”于一身,折射到清政府,发生“剿抚不定”的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6月30日赵舒翘上奏请兵弹压, 重点在于防范而不是镇压,所提出的将义和团编入行伍,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义和团,防止事态的扩大。根据这份奏折,清政府马上命令赵舒翘前往涿州,说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赵舒翘的主张,即以宣慰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用现在的话语来说,这样做,既能保护义和团的爱国热情,又能防止义和团运动越轨而酿成恶果。而一旦越轨,必须“弹压”。这仍不失为一个理智的对策。但6月6日“大阿哥党”在御前会议的大闹以及刚毅亲自前往涿州之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他们把义和团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褒奖为“义举”,无疑大大张扬了民众运动中的落后面,并且企图利用来抵抗外侮、达到废立。这使得京畿地区义和团表面上走向新的高潮的同时,也种下了走向失败的恶果。因此,对于义和团运动最终的失败,“大阿哥党”无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的政治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她与“大阿哥党”同取废立的主张,但她的“训政”地位只是受到封建专制体制道义上的压力,而没有受到现实的政治挑战,因此,“废立”对她来说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大阿哥党”则迫切需要凭借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把“废立”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虽然有自己的特定的政治利益,但不能不受最高统治利益所左右,而“大阿哥党”以还未获得最高统治权之前,则更多地是为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所驱动。在义和团向京畿地区日益发展的同时,在中央政府内,以光绪帝为代表的主剿派力量日益减弱,“大阿哥党”的政治能量得到扩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的政策选择多少会滑向“大阿哥党”一边,但是东南督抚的态度仍然明显地制约着慈禧太后对“大阿哥党”的倾斜态度。这位精于权术而缺乏政治主见的老太太自始至终不能承担起政治家的责任。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爆发的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越轨行为,帝国主义国家动辄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如何妥善处理和引导民众的反帝正义斗争,防止列强的武装干涉,避免民族灾难的发生,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应付的重大政策问题。“大阿哥党”出于本派系的私利,慈禧太后玩弄政治权术,纵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百年前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惨剧,清晰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统治者的“失误”,总是由统治者们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
[收稿日期]2000—08—10
标签:义和团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代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庚子国变记论文; 光绪论文; 庚子记事论文; 慈禧论文; 涿州论文; 瓜尔佳·荣禄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