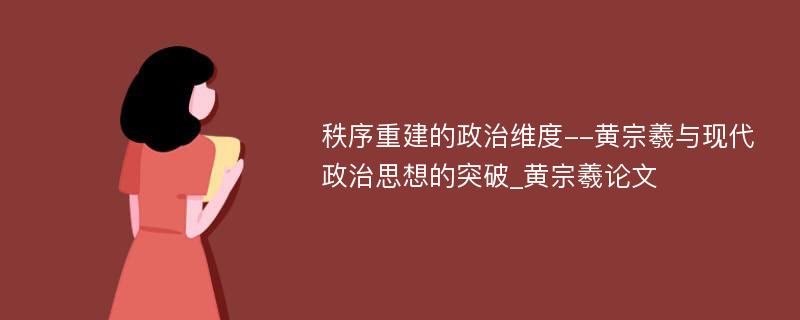
秩序重建的政治之维——黄宗羲与近世政治思维的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近世论文,秩序论文,思维论文,黄宗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明新儒学是近世道德和政治思潮的主流。就宋代而言,由朱、陆集其大成的理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代表的浙东学术确立了此后数百年新儒学政治思维的基本构架。宋明两代儒学的发展具有其内在连续性。宋代诸子为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确立了基调,相比之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儒者身处华夏陆沉、天崩地解之变局,故而对政治体的精神根基、根本法度以及政制构造进行了较之前贤更加深入的思考,以期基于儒家精神而对权威、权力主体予以合理的安顿与规约。这一基于华夏文明秩序重建之整体考量而展开的政治思考,无疑意味着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的进一步展开。本文拟从以下诸方面梳理黄宗羲立足于政治维度的秩序重建论题,以期在勾勒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之连续性的同时,发掘其自我更新之蕴含与潜能。
一、精神秩序:道德事功之辨
对于明末士人而言,明朝覆亡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与思想冲击无疑是至为深刻的。在众多清初学者看来,阳明心学风行天下导致的操守荡然、空言心性之世道与学风,实为明亡之祸根。政治秩序的崩溃源于伦理精神的解体,在这一点上,黄宗羲的认识与清初诸老并无二致,①然而不同于顾亭林、颜习斋放弃心性之学而转向实践实用主义,②他依然立足于心学传统而对秩序重建抱持更为宏通高远之理解,正如钱穆所论:“梨洲所谓儒之大全,将以经世植其体,事功白其用,实践以淑之身,文章以扬之世。其意趣之宏大,规模之恢伟,固足以掩顾、颜而上之矣。”③
诚如学者指出的,如何在社会观念与秩序日趋齐整的情形下为个体的价值确认保留必要的多元化空间,乃是南宋以来社会发展自然生长出的问题。王学的崛起,使这一问题以相反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在价值主体挺立、多元化明显的环境中,如何追求共同的社会观念与秩序。④明亡的政治历史背景,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对于王学的批判与修正,构成了明清之际思想的主流。作为广义上的王学传人,黄宗羲在思想上立足王学而力图修正之。基于心学立场,他批评那种认为“本原性命”无关乎“修齐治平”的观点。⑤可见其重塑心性之学的首要向度,正在于塑造一种作为政治秩序之根基的精神秩序。
在王门后学中,黄宗羲对于泰州派的批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在他看来,泰州末流与禅门的合流,乃是将王学精神引入歧途的罪魁。因此,黄宗羲修正王学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上述二者的纠谬与批判。儒释之判本是宋明儒学史上的老问题,然而在黄宗羲那里,辟佛的角度却与先儒有所不同。在他看来,释氏之弊不在偏于内不足以经世,而在汲汲经世却不以正道。在晚明禅门中,黄宗羲认为为害之大者并非遁隐出世之如来禅,而在纵横功利之祖师禅。⑥对于祖师禅之横行,黄宗羲有如下批评:
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咐,聚群不逞之徒,教之以机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宁止于洪水猛兽哉!⑦
显然,在这里辟佛已远非个体修为层面之事,而是一个“关乎治乱之数”的秩序问题了。⑧至于泰州末流之颜钧、何心隐等辈,皆与祖师禅授受甚深。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明确指出了二者的学术关联。其对泰州的指摘,亦与上述释氏批判一脉相通。⑨
泰州与禅门合流,根源在于二者之学皆以空为底蕴,从而消解了儒家治道之本原。“空”是对宋明新儒学之道德形上本体的消解,“夫释氏以作用为性,其所恶言者体也”。⑩体之存否,意味着社会政治秩序是否需要根据儒家道德伦理精神展开。黄宗羲指出,释氏但求放纵无碍,其实质乃在鼓吹一种迥异于儒家气质的“散漫无纪”的精神理念:
今观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无纪?何以万殊而一本,主宰历然?释氏更不深造,则其流行者亦归之野马尘埃之聚散而已。(11)
但求流行无碍,则不能不将是非善恶一扫而空,“其流之弊,则重富贵而轻名节”,(12)瓦解整个社会精神秩序,而人心之失范,正是政治秩序崩塌的根源。
禅门与泰州之病,根本上在于功利意识脱离了道德精神之规范。因之对治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树立道德本原,并使之能够发用于经世实践。以朱熹、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论争为标志,近世政治观念中呈现出两条脉络的分化,一边是个体修为本位的道德主义,一边是客观功效为主的事功主义。(13)某种意义上,明末政治秩序之崩溃,正是以上两条路径终未绾合一致、甚至渐行渐远的结果。从黄宗羲对于明亡的反思中,亦能看出这一点:一方面,空谈道德性命者“析之愈精,逃之愈巧”,至于危难,则“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14)另一方面,功利之说脱离了道德规范,则一转而为“机械变诈、皇皇求利”之人心世风。黄宗羲指出,明亡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数十年来,人心以机械变诈为事”(15)。因此,如何在道德事功之间开出新局,就是秩序重建的首要问题。
对于黄宗羲而言,重新收拾世道人心,首先自然需要贞定儒家道德之体,而贞定道体,又在于确认其与天道的关联:
盖心体即天体也。……天无一息不运,至其枢纽处,实万古常止,要不可不归之静。故心之主宰,虽不可以动静言,而惟静乃能存之。(16)
心体本乎天体,天体之枢万古常止,为人间秩序确立根本。黄宗羲将心体连属于天体,其意义在于为个体精神乃至人间秩序确立起恒常不易的天道本原。
其次,道体并非空悬,必于经世实践中呈现:
夫道一而已,修于身则为道德,行于言则为艺文,见于用则为事功名节。(17)
在他看来,先儒各执道体一偏,使道德事功判然分途,不免误入歧途。事实上,道德事功理应统一于道体之全。由此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融合心性与事功之学的道体观。一方面,深广之事功必本诸道德:
人唯志在事功,则学无原本,苟可以得天下,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亦且为之矣,其成就甚浅。(18)
另一方面,道德亦必于事功中获其真正之实现:
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19)
离仁义而言事功,则事功必定浅陋;废事功而谈仁义,则仁义必成空言,就此而言,“古今无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20)。由此,经由天体贞定道体,进而将道德事功涵摄于道体之全,黄宗羲完成了对于道德事功之辨的理论回应,前者重在重树道体之本原,而后者则意味着道体的经世实践之展开,意在将事功内化于道德之中。
道德事功之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性重于理论性的问题,因此除了理论融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以具体的方式呈现道德对于事功的指引。在此问题上,黄宗羲的努力主要在于如下方面。
首先,道德发而为事功,必须经由政治世界的转化。透过与潘平格的辩难,黄宗羲批评了后者将经世治平视为良知扩展的思路。(21)在他看来,“治心”与“经世”固不可判然二分,然而其间的距离亦不容抹煞:精神修养必“合外于内,归用于体”,重内在之收摄;至于经世事业,则必须在客观的“时位”中展开,需要外在法度之介入,但凭世人良知,并不足以塑造良好政治:
使举一世之人,舍其时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为事,又何异于中风狂走?即充其愿力,亦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之事也。(22)
由此,客观的法度政制构成了融通道德事功、治心经世的关键要素,而政治世界亦获得了相对于精神世界的独立价值:后者之于前者,毋宁是“规矩之于方圆”的体用关系,而非一线贯通打并为一。(23)此种对于“政治之客观意识”的体察,显示出与同出浙东的南宋事功经制之学的授受之迹。(24)
其次,黄宗羲从天下公私的角度着眼,对三代—汉唐之事功作出了进一步辨析:
三代以上之事功,与汉、唐之事功迥乎不同。当汉、唐极盛之时,海内兵刑之气,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礼乐之风不能常浑同。胜残去杀,三代之事功也,汉、唐而有此乎?其所谓“功有适成,事有偶济”者,亦只汉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统天下而言之,固未见其成且济也。(25)
此段论述直承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辩而来。在他看来,朱陈之辩的一大问题在于二者皆将道德、事功截然二分,而未就三代、汉唐事功中蕴含的不同道德属性作出辨析,结果自然难分高下,“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26)。倘若将三代、汉唐之事功置于天下公私的角度进行辨析对照,那么三代事功意义在于成济天下;至于汉唐,家天下格局既定,政体皆出一姓之私,其事功只在帝王身家,无论从道德凝聚力还是事功之正当性而言,二者均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对道德事功的辨析已经与对家天下的批判相合辙。因之,若欲真正熔道德事功于一炉,那么一套体现天下公义的客观政制法度的建立就是势所必需。
二、重建法原:“天下之法”与秩序意向
秩序重建的努力自然离不开一定的秩序意向作为支撑。(27)在黄宗羲那里,秩序意向的塑造主要表现为对于法原,亦即法治精神的重构。通过三代“天下之法”与后世“一家之法”的对勘,黄宗羲试图扭转秦汉以来以君主私利为取向的法度原则,转而建立一套以天下公义为旨归的根本法度。
在《原法》开篇,黄宗羲即指出了“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根本区别: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28)
三代立法的用心在于天下公义,后世之法则着眼于一姓祚命。法度之正当性源于其公共性,三代良法意在保障民财民命、教化风俗,体现天下公义,所谓“藏天下于天下”,故法虽疏而乱不作;后世法制精神败坏,法度堕落为君主把持天下、攫取利欲之具,“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故虽文网周密,亦难免勾起天下人之觊觎,故法虽密而乱愈生,是为“非法之法”。(29)
至此,黄宗羲的批判视野业已深入到秦以来君主视天下为私产,进而以力把持的基本秩序格局:君主凭借统治权力维护私利,故而法度规则并不具备完整的公共属性,政权亦始终无法成为一种恒常不易之公共存在。此种“家产国家—集权政治”(30)的秩序结构的内核是一种私利与强力二者相互扭结而成的秩序意向:在上者欲以力保其私利,在下者则欲以力夺之,所谓“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31)因此政治秩序之重建,必然要求秩序意向的扭转,此即以公天下理念还原三代法治精神,以具有宪制意义的根本法度体现公平正义,保障民财民命,使之成为共同体安全、秩序与伦理的保证。
三代之治与后世政治的对比,构成了近世新儒学政治论说的经脉。如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世经制儒学的政治思维中,三代之法所标举的乃是客观法度的超越意义。(32)如果说南宋浙东诸子在三代之法与宋代祖宗之法所表征的当世立国精神之间尚能采取一种兼收融合的态度,承认后者所体现的国家宪制意义,那么黄宗羲回向三代的批判意识显然更加彻底。这种彻底性,一方面由于其与现实政治权力的疏离,另一方面,亦缘自家国亡痛所激发的更加深入的反思。在黄宗羲眼中,后世所谓祖宗之法,皆出于开国之君的利欲之私,空有宪章之余名,而并不具备真正的宪制意涵,(33)惟有以六经所表征的礼乐秩序为根底,并因时损益,方能塑造共同体的根本宪制:
六经皆先王之法也。其垂世者,非一圣人之心思,亦非一圣人之竭也。……后王第因而损益之而已,奈何后世以为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汉世以杂霸自名,晋人以宽和为本,唐任人,宋任法。所谓先王之法,皆废而不用,人徒见其享国苟安,遂谓无所事此,幸而保守一家之富贵,其四海之穷困,虽当极盛之世,未之能免也。岂不忍人之政者?故曰:不以三代之治为治者,皆苟且而已。(34)
因此,优良政治秩序的确立,关键不在于杂霸还是宽和、任人抑或任法之类治术层面的小小更革,而在于必以六经为根底确立起根本法度。由此,以法度之公共性为核心的法原精神对于后世私利与强力相扭结的家产制秩序意向的取代,无疑意味着一种由“家产国家”向“宪制国家”的转变。(35)就此而言,根本大法(治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石,其相对于政治领袖(治人)的首出意义是确然无疑的。《原法》篇末“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点睛之论,(36)其意义正在确立共同体根本宪制相对于执政者个体意志的优先性。
三、政制重构:混合政体与共治共和
以天下公义为悬鹄的法原精神一经确立,那么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无疑源自对它的循守与契合。正如天下之法不为一姓而设,政治权力同样不应集中于一人。宋代以降的政治发展凸显出两种内含紧张的力量:一方面是君主集权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政治兴起,形成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格局。黄宗羲的政制重构设想,既是对君主集权趋势的反拨救正,也是对共治格局的新生转进。通过天子—宰相二元君主制的确立,以及朝廷—学校二元权威的建构,他试图塑造一种权力、权威各自得到平衡制约与妥善安顿的混合均衡政体,而贤能之治与公议精神,则构成了维系其运作的基本原则。
较之传统中国的制度实践,黄宗羲的政制设想其实更加明显地体现了混合均衡政体的特征。由于中西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以及近世以降世族式微,平民社会兴起的特征,在以混合均衡政体描述黄宗羲的政制构想时,笔者将着重分析透过朝廷、太学、郡县学等不同政治机关而分别体现的政治领袖(君相)、知识精英(太学儒生群体)以及普通士庶之作用,而非着眼于一种固化的社会各阶层政治作用的考察。
黄宗羲的政制设计依然保留了君主制的成分。不过,新体制中的君主制因素已经不同于传统集权政治结构中的世袭皇权。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世袭君主性质与作用的重新定位,其次是对宰相地位与权力的大幅提升。其中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君、相二元君主制结构。
具体而言,首先,世袭君主不再具有绝对权力与神圣地位。在黄宗羲看来,天下既非君主一姓之私产,那么君臣之间绝非主仆关系,自不应有悬绝的位势之别。他援引孟子“天子一位”之说,指出君臣之别只在于治权意义上的层级高低。君臣作为共治者,其政治身份一致,所谓“名异而实同”,(37)君主并不拥有超出共治者身份之外的绝对权力与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就君权之神圣性而言,宋明儒者多注重君主道德化人格的养成,认为君主理应体现圣王人格。(38)而在黄宗羲看来,这种圣化君主的做法并不可取。借由朱熹、陈亮三代汉唐之辩,他批评二者之失在于“必以天理全然付于汉唐之君”。在他看来,天理原本是公共之物,即便君主不贤,那么历代名臣贤相,如诸葛亮、陆挚、范仲淹、方孝孺等人,同样可以成为天理在人间的至高担当者,是为“以天理把捉天地”。(39)如此,则从以天理衡量君统转变为以天理自身来把握历史。此一转折,无疑意味着新儒学政治思维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对于“圣”、“王”之分的明确指认,从而剥落了世袭君主身上的神圣性位格。
其次,宰相分有君主之最高决策权,世袭君主不再具有独断专行之能力。在黄宗羲设计的决策机制中,天子、宰相、六卿每日便殿议政,各类章奏均由天子、宰相同议可否,然后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40)如此便消解了君主宸纲独断的程序空间,宰相不但有与天子同议之权,甚至可以在天子缺席的情形下通过与六卿的会商而独立决策,其权力更是提升到了极致。宰相所起到的,已经是类似君主的政治领袖作用,正所谓“分身之君”。(41)由此,君、相二者共同执掌最高统治权,构成了混合政制中的君主制因素。
有必要指出的是,黄宗羲设计的天子、宰相二元君主结构,一方面包含了分割、平衡最高统治权的用意;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政治体制之决断能力的重视。这种重视,源于其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反思。黄宗羲指出,明代政治的病根固然在于“君骄臣谄,上下隔绝”,(42)需要限制君权以矫枉,然而士大夫政治亦有其弊端。明人杨锵曾作《过臣》一文,批评宋代士大夫之文弱无断、迂徐寡效,“急于分黑白而缓于课功能,怯于当事机而重于畏清议”。(43)黄宗羲将该文收入《明文海》,并指出其说“深中弱宋之病”。(44)由此亦可看出,黄宗羲之所以保留世袭君主在政治决断中的作用,并在恢复宰相制的问题上采取唐宋以前的独相制设计,其用意亦在确保混合政体拥有必要之政治决断能力,避免书生政治、舆论政治所可能导致的效率与决断力上的弊病。
混合政体中的贵族因素,主要体现在学校制度之中,尤其是中央太学。在他的设计中,太学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更是重要的政治机构。首先,从其成员构成来看,太学以祭酒为首脑。祭酒由当世大儒担任,或以致仕宰相为之,朝廷无权委派。(45)至于太学之生员,一方面来自每年从各地郡县学中选拔而出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也包括天子之子以及三品以上大臣之子。(46)可见,太学成员的组成具有相当浓厚的精英意味。如果说致仕宰相以及贵胄之子代表了政治元老、政治世家的政治经验之传承,(47)那么,当世名儒以及郡县秀异无疑体现了德行与智慧,扮演着自然贵族的角色。(48)
就太学之政治功能而言,除了培养政治人才之外,其职责首先在于根本宪制之议定,所谓“出治天下之具”。(49)如前所述,黄宗羲认为国家的根本宪制在于对六经所蕴涵的“三代之法”的因时损益,那么在太学这一最高学术机构之中,以祭酒为代表的儒生群体显然掌握着解释经典,进而损益宪制,更革法度之权。其次,作为众论汇集之地以及是非判断的最终场所,太学对朝廷起着舆论监督作用,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其非是于学校”。(50)就学校与政府之关系而论,太学对于朝廷、地方学校对于地方政府均具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祭酒、学官人选的确定方式(公议推举而非朝廷任命)以及学校生员的考绩升黜之上。同时,学校与朝廷的关系乃在师道伦理的框架中展开:君相六卿以及郡县长官每月定期前往太学、郡县学,就弟子列听祭酒、学官南面讲学,接受其对政事的批评建议。(51)
祭酒对于君相、郡县学官对于郡县长官的指导,凸显了权威在政治中的指导作用,而有别于权力之间的分割制衡关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权威的产生源自罗马的政治经验。在罗马政制中,权威存诸元老院,其作用大于咨询、小于指令,它并非政治权力,但负责公众事务的人们不会忽视它的作用。(52)汉娜·阿伦特对权威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在她看来,权威指一种“不令而行”的能力,其成立必以等级秩序为前提,且等级秩序中的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至于权威的来源,则必定是某种超越性的存在,如自然法、上帝、祖先等。(53)以此衡诸黄宗羲的学校理论,不难看出在太学与朝廷的关系中非常清晰地体现了政治权威的作用。就等级关系而言,君主以弟子礼师事祭酒,意味着对师道高于君道的等级确认;就权威来源论之,太学之权威显然源自儒生群体对儒家道统、天理之担当,因而具有其超越内涵。正如张灏所指出的,在黄宗羲那里,学校是传承与维持天道的地方,是人极秩序的中心。(54)
君、师二元权威的确立,实乃黄宗羲政制建构中的核心理念。学校制度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政治体系。郡县学校同样具有教化、议政之职能,其与郡县官的关系亦同于太学一朝廷之关系。由此,道势、君师的分立以及道高于势、师尊于君的理念,已经作为政治结构的基本原则获得了制度性确认。儒家传统中,道势、德位之二元区分源自孟子,(55)而在宋明儒学中,理势、君师在理念上的二元分立,在朱熹、陆九渊以至明代王学那里皆有展现。(56)至此,由黄宗羲最终全竟其功的政教制度化二元分立,实为儒家近世政治思维中酝酿已久的一个重要突破。
最后,平民因素亦在黄宗羲的政制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57)首先,郡县学校每月朔望均有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皆参与其中,其内容除切磋学术之外,还包括对郡县官政事之评论。倘其政有缺失,小则于会中予以绳纠,大则“伐鼓号于众”,动员郡邑庶民群起攻之。其次,行乡饮酒礼之时,缙绅士子尽皆到场,凡年龄70以上、生平无玷清议之士人,以及年龄80以上、未曾犯过之庶民,学官、郡县官皆北面尊事之,向其乞求善言以供效法。(58)
经由以上描述,大体可以看出黄宗羲所设计的混合政体中君主(朝廷君相)、贵族(太学儒生群体)、平民(郡县士庶)三种因素各自发挥的作用。就以上三种因素的关系而言,朝廷君相主要处理中央日常政务,所谓“章奏进呈,便殿议政”。太学儒生群体的职责则在根本法度之议定,并在重大问题上对朝廷起到权威指导与监察作用。与上述两个层面相比,平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方治理层面,从郡县学集会的频繁程度(每月朔望两会)以及“小则绳纠,大则伐鼓号于众”的政治参与形式上看,普通士庶的意志对于地方政事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就此而言,地方治理中的平民参与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某种直接民主的意味。可见混合政体中的三种因素既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亦各有其侧重:太学儒生负责立制与清议,朝廷君相主司中央政务,普通士庶则在切近己身的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
就政制运作的原则而言,“贤能”与“公议”构成了其中的两个基本要素。(59)首先,以士人为主体的政制构造蕴含了贤能政治的内在要求。所谓贤能,包含了德行与能力两方面的要求。在黄宗羲那里,士人之德主要体现为一种“至公血诚,任天下之重”,(60)勇于为共同体事业献身而成就伟大功业的品质:
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后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61)
因此,德行与成就事功之能力,实为一体之两面。在这里,黄宗羲所强调的德行,着重于政治领域的担当、审慎、节制之品质,而不同于以往理学家注重的那种个体化、内在化的心性修养。这种转变,同样源自其对近世士大夫政治所呈现的舆论化、朋党化特质的反思,尤其是晚明党争的历史教训。在《黄氏家录》中,黄宗羲委婉批评了以魏大中为代表的部分东林士人在政治行动中徒逞意气,求名之心重于社稷之念,认为天启党祸之成,东林诸君子实难辞其咎。相反,他赞扬其父黄尊素在政治行动中能够“弥缝其间,先事绸缪”具有审慎节制之品质,指出后人不应仅仅表彰其刚直之气,更应借鉴其在政治实践中展现的成熟审慎与责任伦理。(62)
其次,公议精神构成了混合政体运转的另一基本原则。在黄宗羲的设计中,公开的讨论、辩难、说服,构成了学校议政的基本方式,以及产生祭酒、学官的主要途径。(63)如前所述,学校是政治权威之载体,然而此种权威性格主要体现在“学”对于“政”的制衡关系中。至于学校内部之讲学研讨,则遵循辩难会商、理性说服之原则,所谓“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64)祭酒、学官之权威,亦由此证成。公议之风影响所及,庶民亦不再是政治过程中的旁观者,在郡县官执政出现重大缺失的时刻,学官可以“伐鼓号于众”,(65)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中的宣示来取得庶民的支持,迫使其改过。此种公议精神,很大程度上源自晚明泰州、东林士人讲学集会之实践。通过学校这一平台,公议精神从一种学术风气演进为政治规则,并获得了制度化的保障,成为维系混合政制良性运作的重要原则。
经由上述政制结构与运作原则的梳理,不难看出,一方面,黄宗羲的政制构想脱胎于近世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既有格局,另一方面,通过由君相二元君主制以及朝廷一学校的政教分立而确立的混合政体,以及将公议纳入维系政制运作的基本原则,其气象显然已非共治格局所能范围,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而演进为某种共和政治之雏形。(66)
对于“共治”和“共和”的差异,笔者尝试从以下诸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共治理念侧重治权的分享,对于政道层面的公私之分则较少致意。而共和政治则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属性。其次,就政治身份而言,共治体制中的君臣关系未尝不可以主仆定义。(67)而在共和政治之中,基于公天下之理念,共治者之间理应保持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正如传统语境中“共和”一词的原初指向。(68)最后,共治理念比较缺乏明确的制度化保障,且更多出自士大夫对于皇权的诉求。(69)相比之下,共和政治则必具备一套混合均衡政体的客观制度架构,并且能够对公民之间以及政治家之间的公共辩论予以制度化的容纳,以之作为共和政体的重要基础。(70)
因此,共和政治相对于共治格局,无疑存在着某种跃迁。从共治到共和的转变,需要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跃迁做出回应。在黄宗羲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寻绎出这种演进的迹象。首先,“天下之法”所标举的法原精神的重构,意味着政道层面的公天下理念的确立。其次,对于君主性质以及君臣关系的重新界定,体现了共治者政治身份的平等化趋向。最后,以二元君主制以及政府—学校二元结构为核心的新型政体,容纳了君、士、庶等多种政治因素,并为公议政治提供了系统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近世政治思想从共治到共和的演进,某种意义上亦是对三代古典政治理念的回归。如论者所言,“君子共和”实为封建时代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基本机制。(71)因此就政治传统而言,黄宗羲的新制度论绝非无源之水,而应视做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成为基本秩序格局、科举士大夫取代世袭贵族成为政治主体的近世背景下,试图通过政体的改进而接续古典政治理念的一种尝试。由此,宋明儒者回向三代的政治蕲向,可以说得到了至为完整的展现。(72)
四、余论:黄宗羲研究的视角转换
至此,经由以上精神、法原、政制三个层面的论述,庶几可以在明末秩序重建的整全视野中勾勒出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纵深向度。不难看出,无论就思想渊源还是思维方式而言,黄宗羲均受到近世新儒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如道德事功的交汇融通,三代后世的批判对比,师道君道的高下分合。同时,由于其身处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历史环境之中,故而比较能够摆脱现实政治权力的束缚,以一种更加深入的批判意识对近世思维进行集成性总结与进一步展开,从而提出某些极具突破性的新见,诸如对以天下公义为中心的法原重构、以朝廷—学校为核心的混合政体塑造,以及在政体运作中对于公议精神的强调。就此而言,黄宗羲政治思想中的种种创见,实乃基于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传统的“调适上遂”,而非“另开歧出”。(73)
因此,就以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政治思想研究而言,—种研究视角上的调整或许是必要的。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往往着眼于黄宗羲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比照,抑或其对晚清变革运动的影响,而较少从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的发展脉络本身来理解黄宗羲思想的渊源与新变。事实上,无论从问题意识还是论说方式上看,在黄宗羲那里都体现出了近世儒学政治思维在宋明两代数百年的时势变迁中保有的相对连续性。无论是法原的重构、根本法度宪制的确立,还是混合政制的构筑,都是因应近世政治中的新问题——诸如君主集权的强化、士大夫政治效能的缺弱、政治舆论的合理安顿——而给出的一种具有综合性深度的思考。在其秩序重建的整体视野中,精神、法原、政制三个层面的重建最终所指向的,乃在于从“家产国家—集权政治”转向“宪制国家—共和政治”这一根本目标。
另一方面,就西学资源的借鉴而言,西方政治学资源的引入无疑有助于我们将传统政治思想中一些潜在、隐性、分散的教诲凝聚为一种显豁、积极而充分的理论表达,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将比较的视野集中于启蒙视野中的自由、民主等西方现代思想,而忽略了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或许更为切近的共和主义、宪政主义等西方古典资源。其结果是难以从一种最恰当的视角来观照传统政治思想,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掘其潜在价值。同时,将自由民主理念奉为评判传统思想价值的唯一标准,亦限制了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各种思想资源的交相资引中塑造未来中国政治文明的可能性。
诚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儒家向来是一“内圣外王连续体”。(74)对于善治理想的追求,乃是不同时代儒者共同致力的目标。在近世新儒学的政治思维中,这样的努力是一以贯之的。(75)而黄宗羲的思想史地位,正在于以一种批判吸收的双重视野将近世儒家政治思维予以充分展开,从而在儒家传统的同一性、延续性中展现出时代的鲜活感。因此,就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而言,基于现代政治的后视视角与着眼于儒学政治传统的前视视角或许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前者有助于确认儒家政治传统经受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理念之充分洗礼的可能与必要,后者的意义则在于将“开新”建立在“返本”的坚实基础之上。就前视视角而言,黄宗羲无疑是宋明儒学政治思维充分展开的高峰与终点;而就后视视角观之,那么他又是清末接引西方资源而引领政治改革运动的始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离不开传统资源的重新发掘与创造转化。就此而言,在上述两种研究视角的交汇融合中斟古酌今、借鉴中西,重新审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近世新儒学政治思想的价值,无疑是一项充满潜力而极富意义的工作。
①在《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中,黄宗羲指出,明亡之根本原因在于“数十年来,人心以机械变诈为事。士农工商,为业不同,而其主于赚人则一也。赚人之法,刚柔险易不同,而其主于取非其有则一也。故镆铘之藏于中者,今则流血千里矣”。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②“实践实用主义”为梁启超之概括,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页。
④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
⑤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九《诸儒学案三·何瑭传》,《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473页。
⑥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55-156页。
⑦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三《泰州学案二·赵贞吉传》,《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874页。
⑧“今人不识佛氏底蕴,将杨、墨置之不道,故其辟佛氏,亦无关治乱之数,但从门面起见耳。”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五《诸儒学案下三·郝敬传》,《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654页。
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820页。
⑩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聂豹传》,《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428页。
(1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罗汝芳传》,《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4页。
(1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陶望龄传》,《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130页。
(13)任锋:《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第60页。
(14)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46页。
(15)黄宗羲:《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第66页。
(1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聂豹传》,第427-428页。
(17)黄宗羲:《重修余姚县学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34页。
(18)黄宗羲:《孟子师说》,《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07页。
(19)黄宗羲:《姜定庵先生小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23-624页。
(20)黄宗羲:《国勋倪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98-499页。
(21)在黄宗羲看来,潘平格论学之旨在于以天地万物一体为性,以触物而物我一体为良知,以致其物我一体之知为工夫,故学者必从家国天下事上致其良知,如是则将致良知与经世打并为一事。参见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第150页。
(22)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第152页。
(23)“夫吾心之知,规矩也,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犹规矩以为方圆也,必欲从天下国家以致知,是犹以方圆求规矩也。”见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第151页。
(24)牟宗三指出,南宋叶适、陈亮之事功经制之学,体现了“政治之客观意识”。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25)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第225页。
(26)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第225页。
(27)此处“秩序意向”(ordering inclination)概念,借自姚中秋先生,指推动秩序之生成与维系的精神取向。详见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57-61页。
(2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页。
(2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第6页。
(30)“家产制”之概念出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支配者将政治权力当做其私有财产的有用附属品加以利用的制度。参见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黄宗羲对秦以降政体的诊断显然与韦伯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正因君主“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故而必惧其刑赏之权旁落。因此,笔者以“家产国家—集权政治”概括黄宗羲所描述的三代以后之君主政体。
(3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页。
(32)任锋:《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第22页。
(3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第7页。
(34)黄宗羲:《孟子师说》,第87页。
(35)此处“宪制国家”之提法,取自“宪章”与“经制”两个黄宗羲论著中固有之词汇,指建立在一套限制绝对权力、保障民产的基本法度之上的国家形态。
(3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第7页。
(3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第5、8页。
(38)如朱熹对“皇极”的解释:“皇,谓君也;极,如屋脊,阴阳造化之总会枢纽。极之为义,穷极极至,以上更无去处。”《朱子语类》,卷七九《尚书二·洪范》,中华书局,1986年,第2045-2046页。
(39)黄宗羲:《破邪论·从祀》,《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93页。
(4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9页。
(4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第8页。此外,《置相》篇云:“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可见在其眼中宰相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君主之职能。
(42)黄宗羲:《明文海评语汇辑》,《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109页。
(43)杨锵:《过臣》,收入黄宗羲编撰:《明文海》,卷一百,中华书局,1987年,第987页。
(44)黄宗羲:《明文海评语汇辑》,《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109页。
(4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2页。
(4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学校》、《取士》篇,《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2、18-19页。
(47)黄宗羲从政治经验的角度肯定了政治世家的作用,他指出:“六朝以门第相高,人物最为近古。盖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说,朝典国故,是非邪正,皆有成案具于胸中,犹如巫者,见证既多,至于医病,不至仓皇失措。单门寒士,所识不过朱墨几案间事,一当责任,网罗衣钵之下,不觉东西易置。”黄宗羲:《五军都督府都事佩于李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06页。
(48)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论述了“自然贵族”的概念,他把具有良好品行与才能的社会精英都称做“自然贵族”。真正的自然的贵族由一个具有一些合理预设的品质的阶层构成,如自我尊重、知书达礼、乐于接受公众的批评与监督、关注舆论、富于远见、审慎坚毅,等等。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9页。
(4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0页。
(5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0页。
(5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2页。
(52)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政治学》,龚人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53)陈伟:《阿伦特的权威理论》,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54)张灏:《政教一元还是政教二元?——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载《思想》第二十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月,第128页。
(55)《孟子·万章下》:“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尽心下》:“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56)如朱熹以天理为准绳而对三代、汉唐高下所作的明确指认,见朱熹:《与陈亮第八书》,载《陈亮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303-307页。陆九渊则指出理、势常处在对立之中,有道之世则必“势出于理”、“理为势主”,见陆九渊:《与刘伯协》,载《陆九渊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168页。王学对于师道的推尊与复兴,参见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9-310页。
(57)在黄宗羲那里,政治中的平民因素主要体现于下层士人以及一般庶民。在其定义中,士人大体指通过多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具备一定文化教养或专门技能的知识人群体。然而士人并非官员,由士人升为官员士大夫,仍须经过进一步的选拔。未通过选拔的下层士人,在身份上仍属平民。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取士》、《学校》诸篇,第10-19页。
(5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2-13页。
(59)“贤能”与“公议”均为《明夷待访录》之既有词汇。参见《取士下》篇,《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6页;《学校》篇,第11页。
(60)黄宗羲:《破邪论·从祀》,第193页。
(61)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2页。
(62)黄宗羲:《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416页。
(63)《学校》篇谓:“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1-12页。
(6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2页。
(6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2页。
(66)“共和”一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本指王位空缺之时公卿协作共同治理的状态。《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而就西方思想史上的共和政治而言,其特征大致在于混合政体的制度框架以及对公民美德、公共辩论等因素的强调。因此,笔者此处所使用的“共和”一词,既包含其在传统语境中的含义,也包括了部分西学语境中的意涵。
(67)如宋儒张载在《西铭》中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
(68)西方共和主义理念同样强调政治身份的平等,这种平等指向一种参与公共生活机会的平等,而不排斥君主、贵族、平民之间基于自然的等级区分。参见陈伟:《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9-24页。
(69)余英时指出,在宋代积极倡导“同治”或“共治”的,是士大夫而非皇权。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第230页。
(70)尼德尔曼(Cary J.Nederman)指出,这种公共辩论往往被视为共和政体的重要基础。见卡里·尼德尔曼:《修辞、理性与共和——古代、中世纪以及现代的共和主义》,收录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71)姚中秋指出,封建制下之“君子共和”,指共同体中包括国君、公卿在内的两个以上的君子,同时拥有决策之参与权,通过面对面协商、审议的方式寻求共识,对公共事务做出决策。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358-369页。
(72)黄宗羲《破邪论·题辞》云:“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治。”(《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92页)可见其对古典政治理念的传承当有自觉。
(73)“调适上遂”与“另开歧出”二词,借自牟宗三先生。所谓“调适上遂”,指顺本有者引申发展而为本有者之所涵;所谓“另开歧出”,指于基本处有相当之转向,歧出而另开出一套以为辅助。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74)余英时:《试论儒家的整体规划》,《朱熹的历史世界》附论三,三联书店,2004年,第918页。
(75)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参见任锋:《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第17-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