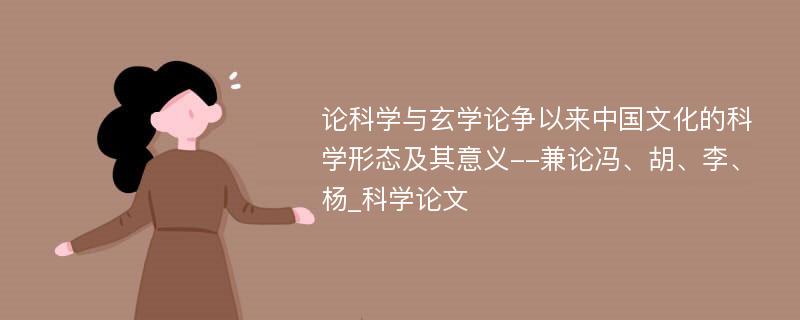
科玄论战以来关于中国文化之科学形态的研究及其意义——冯、胡、李、杨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形态论文,意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问题最早是由“科玄论战”引发的。20世纪19—20年代初,中国思想 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科学与玄学论战”。参加这 场论战的开始是两方。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任叔永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即所谓的 “玄学派”,他们力主科玄分疏,反对科学万能。另外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 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即所谓的“科学派”,他们虽然也认为科学的材料和结论都有其特 殊性,但认为科学方法却具有普适性,因此认为类似科学的人生观也是可能的。随后参加的 以陈独秀、范寿康、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派——唯物史观派就其内容上并没有出“西方 文 化派”之右。他们既不同意张君劢、梁启超的非实证的玄学,也不完全同意西方文化派表现 出来的经验主义倾向,具有某些科玄分疏的思想。同时,他们既认同了“西方文化派”的 科学因果观,也一定程度地认同了东方文化派的某些先验形式的理性思想。
针对“科学派”中许多人否认中国文化具有科学形态的思想,冯友兰先生通过专门和系统 的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冯先生晚年曾回忆说:
1919年我到美国后,和西方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触,上面所说文化矛盾的问题(指当时流行的 关于东方文化有无科学形态的见解—作者),对于我更加突出。那时正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胜利后的繁荣时期,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贫弱,更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我经常考虑的 问题是: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节节失败,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西方为什么富强?中 国为什么贫弱?西方同中国比较起来,究竟在哪些根本之点上比较优越?
我当时思考的结果,自以为是得到一个答案。西方的优点,在于其有了近代自然科学。这 是西方富强的根源。中国贫弱的根源是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冯友兰,《三松堂全集》 ,第一卷,1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但是,是否像当时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科学形态是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的呢?冯先生对此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可是问题又来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是为之而不能;或是能之而不为?当然 我认为是能之而不为。为什么不为呢?这应该在中国文化中寻找答案。
为了寻找这一答案,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文化之历史 及其结果之一解释》……这篇论文的大概意思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 国 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谋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如有人仅只是求幸福 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确切的知识。(同上,189~19 0页)
冯先生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他也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他并不 认为科学形态是中国文化中没有的。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主要 是中国人将科学的方法用于了对人的内在幸福的研究,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将之用于自然知识 和控制自然的研究。冯先生借此表明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并不像许多人 认为的那样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倾向于认为,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因此文化也不可能有 什么本质的差异,差别仅在于研究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因此,他特别反感当时流行的关 于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这种主流观点。他认为,东方哲学也有研究自然问题的, 西方哲学也有研究人的内心幸福的。这样,在西方也有精神文明,在东方也有物质文明。不 能说西方人的思维就是偏重自然的,东方人的思维就是偏重人文的。
根据冯先生的观点可以逻辑地推出,如果中国文化将其主要对人文的关注转向主要对自然 的关注,中国也会产生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也会产生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在这种 观点看来,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的体用之争就显得多余。而且,冯先生的观点还蕴含了这 样一个假设:如果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科学形态,那又怎么能在中国引入科学这种“洋玩 意”呢?即使引入了还不是会因为没有土壤而死亡吗?反过来,如果说可以引入,那不等于说 已经承认中国文化也有科学形态的土壤吗?
那么,如何看待冯先生的上述观点吗?我们需要对一般文化的科学形态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 。根据我的思考,一般文化的科学形态大致可有五方面的涵盖:其一是思维意义上的,主要 关涉思维是否合规律、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等内容;其二是工具理性意义 上的,主要关涉是否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语言、方法或逻辑体系,是否有实验条件以及实验水 平如何;其三是类似于自然科学发展史意义上的,主要关涉是否有史的传统,是否具有自生 的可持续性,是否具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梯性、层次性、有序性,是否具有某 些分叉和整合性;其四是具体的技术意义上的,主要关涉具体的科学的实物形态或工具形态 等。其五是抽象理论意义上的,主要关涉信息复杂性的涵盖程度。
以此观之,冯先生认中国文化具有科学形态主要是就第一层面而言的。值得注意的是,冯 先生自己曾反复谈过,他形成上述看法时,正值古老的中国文明被西方文化歧视之时,因此 ,冯先生的上述观点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辩的性质。
但是,一战后的若干年间,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特别是西方带 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西方人不得不开始痛苦地反思自己的文明与文化,特别是随着斯宾格 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影响的日益广泛,重新评价西方文明与文化成了当时热门的话题。在 这种情况下,“玄学派”的观点又开始占据上风,认中国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欲文明的流 俗又起,转眼间全无了先前的耻辱感,转而开始讥贬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 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不得不在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问题上再次重申和深化他反对“玄学 派”的观点。这也决定了胡适的观点为什么具有和冯先生完全不同的民族批判的性质。胡适 道: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 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古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 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 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 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 狂 ;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306页,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和冯先生一样,胡适也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分的,是一体的。胡适是从西方哲 学关于文化(胡称之为生活方式)与文明(胡称之为应付环境所得的总成绩)的区分谈起的,正 是基于这一点,他认为:“没有一种文明只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 ,都有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 。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 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cal Civilization)一个名词不应该有什么讥贬的涵 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文明,不是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车所代表 的人类的心思和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同上,307页)
由于胡适认为中西文化没有根本差别,那么他当然也和冯先生一样,不认为中国文化中没 有科学形态。不过,与冯先生不同的是,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仅具有科学思维意义上的 科学形态,而且与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差不多同期,类似的逻辑意义上的科学工具也在中国 文化中产生了。
那时正是傅(傅斯年)先生所谓顾亭林、阎百诗时代;在中国那时候做学问也走上了一条新 的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同上,469~470页)
当然,胡适这里所指的科学工具主要是指中国文化中的归纳逻辑思想。不过在胡适看来, 可惜的是,中国却将同样的科学方法用于了书本的诠释(不同于冯的人的内心幸福的研究)。
在十七世纪初……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 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新的宇宙出现了。(同上 ,470~471页)
但是,同样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又如何呢?
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在学者顾亭林阎百诗的领导下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材料是书本 。顾亭林研究古韵,他的确是用的新方法,不过他所用的材料也还是书本……结果,他们( 西方人)奠定了三百多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而我们在 这三百多年来在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亭林,阎百诗做引导……但是因为材料的 不同,弄来弄去离不开书本,结果,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三百年来的治学的成绩。 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不可以道理计。而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 说明傅先生的话:凡是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料,只能研 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同上,471~472页)
胡适不仅考察了中国文化中有科学思维,而且还认为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的逻辑工具,单就 这 方面看,胡对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的认识比冯先生视野略宽。
不过,胡与冯最大不同是,胡不但反对将东西方文明作“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样 的区分,反对那种认为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观点,而且也不认为东西方文明在物质和精 神方面有侧重不同。恰恰相反,他认为,西方文明就是在“精神文明”方面,也远远超过了 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胡在得出这一结论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 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东方的哲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后知礼节。这 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同上,306~307页)
由之,他认为: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的进 一 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 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同上,309页)
总的说来,无论是冯先生还是胡先生都大大超出了西方关于科学的特殊认定。在冯先生那 里,科学实际上被普遍地理解为一种中西方共有的智慧,似乎一切科学问题都是智慧问题, 似乎不需要另有一套科学逻辑而仅凭人类共有的具有智慧特性的科学思维就能从事科学研究 。也就是说,似乎只认识到了科学思维对科学发展的意义,而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分类和分门 别类的科学发展特别是专门的科学工具对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观点无疑仍然具 有中国文化非分析的综合性质。胡先生虽然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但他同时具有中国文化 的综合性质,因而也势必要大大拓展了它的涵盖,走向了另一极端,认科学是适用于包括社 会各个方面的通则,似乎一切问题包括科学问题最终都是自然科学问题,因而具有明显的科 学主义的性质。
如果说冯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观点主要是国内科玄论战的逻辑沿袭,那么,英国科学家李约 瑟博士的观点无疑具有更为普遍的性质。就事实来看,李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拓宽 了论域,也大大深化了冯、胡两位先生的观点。他在用大量篇幅证明中国文化是如何对近代 以前的科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对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作了缜密的研究。和冯、 胡二位先生一样,李约瑟也承认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的科学,但同样认为,这并不是由于中国 缺乏科学思维。比如,他用法国科学家雷缪萨1815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讲的话来证 明中国人早就经同样的科学思维发现了引力现象:
我曾在一本出版时期比发现引力还早得多的中文辞典中找到潮汐的原因,它非常恰当地被 称为‘月亮对地球的爱情’。即使这个民族的天文学理论有缺点,他们关于日月蚀和慧星的 编目还是很有意义的;即使人们坚持说中国人在计算中有错误,但必须承认他们的眼光和我 们一样好。(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5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第84页)
李约瑟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决不是中国文化所致,而是另有三个原因。一个 原因是,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 ” (同上,第42页)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自己极少写科学史”。此外,他完全同意胡适的观点 ,他援引胡适的话道:“两者所用的研究方法极端相似,可是所研究的领域却有很大的差异 。西方人研究星辰、球体、杠杆、斜面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文献考证。 ”
不过,李约瑟和胡适又有很大不同,他认为:
重要之点并不在于如胡适先生所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的只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 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重要之点乃是在于:不管我们今后能找到哪些在中国 社会中起过抑制作用的因素,在中国人过去的时代精神中,显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人们 去发展那些符合于最严格的考据原则、精确性和逻辑推理的知识。
有些中国人最初曾被欧洲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所迷惑,以致于认为造成这种优势的欧洲 科学技术传统似乎是无可匹敌的。真的,把科学称为‘西洋科学’,把它看成是中国难以理 解的、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根的这种倾向,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同上,第95页)
在李看来,只要条件允许,中国文化同样可以对近代科学产生巨大的贡献。李认为,历史 的发展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从现象上看,中国确实没有产生“像伽利略和凡萨里乌 斯等一类人物”,但是,中国文化与近代以来的科学仍然在逻辑线索上极其恰合。他指出,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和玻姆就曾反复说过,量子理论的基本思想,早体现在中国道家的思 想中。除此之外,中国文化至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近代以来的科学的贡献是“伟大的” 。(同上,第14页)因为,尽管“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 自然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的形式的解释,但 它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的 是 ,这些也正是今天最新的自然科学所要关注的内容。
在这里,李和冯、胡的异同就跃然纸上了。冯、胡二先生认中国文化具有科学思维,李也 认同,冯、胡二先生认中国文化没有产生技术形态的科学,李也认同,不过他承认这只是就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而言的,并认为近代以前的科学技术中国不但有甚至远远领先世界。胡 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也产生了科学逻辑和科学的工具理性,李也认同。但是,比胡更进一步的 是,李提出了“科学理论”的概念,根据李的理解,如果不能形成理论形态的科学,单靠科 学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这很有道理,许多人无疑也具有职业科学家的智慧(冯先生在这方面 看得很准),但许多人并不能通过智慧就能进行科学研究,他还必须要经过系统和专门的理 论学习。中国智慧中无疑具有许多科学思维(单说这方面,中国文化中蕴含的科学思维甚至 具有超前性,如李所言的有机生态观、和系统整体观、辩证统一观等),但若要形成近代自 然科学,非得要诉诸理论科学和发展不可。与之相连更进一步的是,李提出了“科学史”的 概念。李的深刻也正在于此,因为如果没有科学史,科学就不得不总是停留在具体的经验层 面上,就不得不进行大量的重复劳动,就不得不使人类的认识永远不能脱离起点。如此,只 会有经验性科学的不断重复而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理论产生,如此,近代以后的科学也就不 会产生。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科学史,中国许多具体形态的科学只能是人人传承的关系 ,因此,别说是像牛顿那样“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发展了,单是防止失传就是一件十分困难 的事情。
另一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与李约瑟博士一样,杨也是 职业科学家,而且同样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同的是杨原本就是大陆本土的中国人 ,且自幼就系统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近一、二十年间,杨教授对中国文化与科学的 关系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特别是,1999年12月3日杨教授在 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对其相关思想做了简要的总结。
与冯、胡、李的观点相似,杨教授也认为,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确实不是在中国文化基础 上自生的,而是在清末从西方引入的。杨教授也承认,中西文化有着形式的不同。即中国文 化是以身心为主的“内学”,而西方科学则是以自然为主的“外学”,也就是说,近代以来 的具体形态的科学和理论形态的科学都是从西方引入的。不过,与三人一致,杨教授也认为 ,就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而言,中国和西方确实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中国 的智慧才在接受和传播西方科学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杨教授回忆说:
在1900年,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微积分……到了1925年,少数的大学才开始筹办算学系 、物理系——那时候不叫数学系,叫作算学系。我去查了一下,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算学 系、物理系的名字,在1925年前还没有。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清华大学,就是在1926年到 1927年之间,才正式成立了算学系。到了1938年,我进大学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准已 经达到了世界级,这个是一个极快的现代化。到了1964年,中国成功地制造了原子弹,而制 造原子弹所需要的人数之多、知识的方向之广,是很难想像的。再到了1970年,中国成功发 射了人造卫星,到了1999年,前一些时候,大家知道,“神舟”成功地发射与收回了,你看 ,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快速的进步。(《光明日报》,2000年3月21日)
而且,杨教授也部分同意了胡、李二位认中国有逻辑和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科学的观点,这 工具理性便是归纳逻辑。杨教授认为,西方的科学归纳法是中国文化中本身具有的。
首先可以肯定:近代科学也是在追求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所讲的“理” ,这就是“自然规律”。所以,近代科学的“自然规律”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理”。那 么,近代的科学怎么来追求这个自然规律呢?其精神和方法之一,跟中国文化一样,是用归 纳法求得这些规律。(同上)
但是,与前面三位先生的观点不同,杨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有科学逻辑工具,那仅对归 纳法而言才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科学逻辑中不仅有归纳法,还有推演的方法。这是杨教授与 上 述三人不同的一个地方。
不过,近代科学跟传统的中国文化一个主要的分别,是前者还有一个方法,另外有一套思 维 的方法,这第二个方式是从上到下的,是推演,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而这是中国文化里 头没有的。……所以总结起来说,传统的中国文化跟十六世纪以后才发展出来的近代科学其 分别是什么呢?是传统中国文化要求“理”,近代科学要求“自然规律”。但传统中国文化 求理的方法,只有归纳法;而近代科学求规律的方法,则是推演法再加上归纳法。(同上)
由这种不同,杨教授进一步拓展了工具理性的范围,除了归纳逻辑外添加了演绎逻辑的要 求,还突出了实验工具理性的重要性。特别是,他第一次明确将西方自然哲学(Natural Phi losophy)也纳入了其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归纳逻辑对于近代 科学而言还是不够的。
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我们知道,有名的王阳明“格”竹子: 坐在那儿,看着竹子,脑子里转来转去,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理”是什么。这跟西 方的近代科学形态不一样。不错,后者也要思考,可是还要有实验。因此中国文化跟近代科 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几个分别就在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 一切为理。这个传统里头,缺少了推演,缺少了实验,缺少了西方发展出来的所谓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同上)
此外,杨教授还在科学思维中将目的性科学的概念突出了出来。他将西方的“自然规律” 概念同中国文化的“理”的概念等同起来。杨教授据此认为,中国文化处理“外学”时,就 会力求达到如朱熹所说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不过,如果真要将科学目的性纳入科学 思维的话,中西实际上差异还是很大的。就西方“自然规律”而言,所要力求达到的是规则 、规律或者定律,而要尽力与人的主观目的性剥离。但中国文化之“理”则不同,它的 外延要大得多。它大大涵盖了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只关涉主客观是否相符,中国文化之 “理”则力求使自然规律与人的合理性需求协调,它既关注主客观是否相符,同时也关注自 然规律的产物是作为有益的核能还是作为毁灭地球的核能。“自然规律”会自生无序和混沌 ,中国文化之“理”则力求环境的持续有序,甚至包含对自然要灭绝的生物的保护,“自然 规律”只关涉某一事件是否是“真”的,中国文化之“理”则力求达到这“真”是否是“真 理”,是一种的辩证整体观。
通过上述反思,我们不难对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有个大致的了解,并可由此得出中国文化 继承与重建之五个要点。这便是:立足中国文化之智慧基础,补之于推演、实验、自然哲学 等 工具理性,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而非古本诠释或经验附会之“史”脉,深化细化学业之专分, 丰富理论内涵之信息复杂性。
标签:科学论文; 胡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