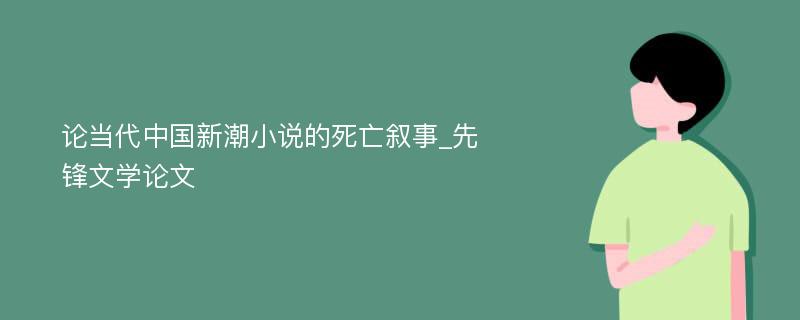
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死亡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4—0067—06
自称是“由外国文学抚养成人”的中国当代新潮作家对“死亡”的迷恋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外国老师,“中国文学中还从来没有像新潮文本这样充满了‘死亡’的气息”[1] (P51)这种如此气息浓重的死亡气息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背道相驰的。无论是庄老学派还是儒释两家都对死亡讳莫如深,视为畏途。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至今在中国农村仍有“红白喜事”说法,“红”指结婚,“白”则指死人,死和喜在许多方言中都是同一种发音,结婚时打锣敲鼓放鞭炮吹唢呐,死人时也同样如此。死亡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禁忌,轻易不说“死”字是童叟皆知的常识。这种对死的规避心态甚至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审美观念,以至于文学中每每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有人甚至说“中国无悲剧”。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悲剧,而是没有悲剧精神,以乐感文化为主导的华夏文明借着各种手段将死亡所带来的悲剧气息销蚀殆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作品不缺少对死亡的叙述和描写,“但死亡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情节手段,它或者是为了渲染悲剧气氛,或者是为了强化作品主题的感染性。也就是说,它呈现在作品中的只是认识论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意识。死亡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生命化的动态过程。”[2] (P52)涕泪涟涟的哭泣和义愤填膺的控诉完全抵消了作家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悲剧气氛。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许多作家越是书写死亡越是远离死亡。而新潮作家已经不再把死亡当作一种情节手段,不是为了渲染悲剧气氛或是为了强化作品主题的感染力而去描写死亡,死亡成为表现的目的。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新潮作家不仅获得一种对死亡的直观的体验,而且还从存在论的哲学维度认识到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重点关注:在西方先锋文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新潮作家对死亡的认识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呈现出哪些既不同于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新的质素,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审美变革?他们还存在哪些缺憾?
一、死亡叙述与现实生活的剥离
新潮作家一贯轻视反映重在表现,他们喜欢将眼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漠视当下,他们的死亡叙述往往与现实语境剥离,很少与现实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不仅使得新潮作家可以穿越生活表象迷津而直达生活的深处,把握生活的本质,而且还使得他们能够站在历史之外,从历史中超脱出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潜在的对话。例如,格非的长篇小说《敌人》一开头这样写道: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
如果将这句话和通常的叙事文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交待得一清二楚:“几十年前”、“村中”、“上了年纪的人”、“大火”,作为叙事文的几个要素一应俱全,下面就是等着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细细一想,却觉得什么也不是,虽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但现在是什么时间,文中并没有交待,这样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空洞的无所指的概念化时间。村中,哪个村?如果小说中人物所取的名字不是赵少忠,而是彼得或者汤姆,这样的村庄也许就在俄罗斯或者英国的某个乡下,同样,上了年纪的人多得是,也不知到底指谁。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将能指符码与所指符码割裂开来,造成一种所指的空缺,将叙事从具象性的特指层面提升之抽象性的泛指层面,从而达到叙事的哲理化。在此后的叙事中,猴子、赵少忠的女人、柳柳、赵龙、赵虎等相继死亡,赵家被死亡的阴影完全笼罩,凶手到底是谁,谁是赵家的敌人?由于小说抽离了现实语境,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答案的线索完全中断,生活经验对此无能为力,所以尽管赵少忠手中那份可疑人的名单在不断减少,但他心中的谜团反而越来越大,最后剩下的一个可疑人就只能是他自己。所谓的“敌人”就是本人。小说中的一次次死亡只不过是符号不断消失的过程,能指经过不断萎缩后,最终完全坍塌。格非这样的新潮作家之所以能够这样处理小说,固然是因为他们主动学习、借鉴欧美先锋文学表现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大胆地抛弃了传统作家赖以生存的生活现实,从机械的反映论走向表现论。这样就彻底打碎了文学必须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樊篱,完全解放了他们的想象力,使得他们得以集中精力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曾经有人说新潮小说的标志是由过去的“写什么”转向现在的“怎么写”,主要体现为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法论”革命。现在看来,这种归纳是不太客观实际的。其实,新潮作家的“新”不仅只限于写作方法的新,更主要的是文学观念的更新,如果光有方法的新,而没有内容的新,那么这样的变革还是表面的,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小说说到底是一种叙事文学,没有了“事”,“叙”也就成了无“皮”可附的“毛”,不复存在。其实,新潮作家没有一个不是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故事。由于剥离的现实语境,死亡在新潮作家那儿,不再是和“灾难”、“苦难”对等的概念,而是和“活着”、“吃喝”、“性爱”等处于同等地位,是指一种存在的状态。再如余华的《世事如烟》,既无具体背景,又无主体事件,人物竟用数字符号来指称,从其中感受不到任何生活气息,一切如过眼烟云,连死亡也不例外,这就是余华所理解的生活本相,生活(包括死亡)本无意义,如同山水草木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所谓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后来附加上去的。死只是生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别无他意。有时候,先锋作家也会出示死亡的背景,如格非《迷舟》的故事发生在北伐期间,余华《一个地主的死》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洪峰《极地之侧》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八七年二月,但这样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纯粹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保罗·利科认为,“历史时间是以三重叙事模拟的形式‘把生活时间(重新)刻印在宇宙时间之上’的产物:
模拟1——在人类行为结构及其日常阐释中,预塑(prefiguration)历史时间的叙事结构;
模拟2——通过叙事结构塑造(configuration)历史时间,这些叙事被‘放置’在与它共有的宇宙时间的那个年代学框架‘之上’;
模拟3——借助于它的叙事塑造的影响,在‘读者’经验的基础上重塑(refiguration)生活时间。”[3] (P83)
中国新潮作家的做法正好和利科的时间理论相反,由于消除了最基本的“生活时间”,新潮作家的文本无法获得“历史时间”新潮作家只能置身于历史之外,与历史和生活同时对话,新潮作家的这种做法与一向重视历史感的欧美先锋作家大相径庭。就连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卡尔维诺也是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我们的祖先》中的子爵、男爵、骑士一下子就让人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新潮作家这种敢于向历史挑战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学者赵毅衡对此有这样中肯的评价:“中国先锋小说近十年的成果之富,经得起细读苛评。”得意中他还援引了国外专家对中国当代新潮作家的评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真得忘掉我们心中关于中国文学的一切既成概念……这些早熟的青年作家正迫使全世界承认。”[4]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新潮作家脱离传统反映论的羁绊,不满足于通过死亡来展示、渲染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残酷。但是就他们本身的理论素养和生命体验来看,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存在观(死亡观),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体系。他们重在打碎、拆解,而忽略重建、再建。在关于死亡叙事时,新潮作家不仅借用了别人的理论,而且还借用了别人的体验。所以,尽管新潮作家将死亡与现实生活剥离,尽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便获得一种历史的视角从而穿透现实表面的迷雾,直达生活底端。但是他们获得的历史只是一种虚假的历史,“因为,如果没有先行到死中去这个生存有限性的标志,就不可能有“时间性的时间化”,因此,推广开来,没有先行到相同种类的历史“终结”中去,就不可能有历史时间的时间化,不可能有历史的时间性:没有先行到“历史的终结”中去,就没有历史。[5] (P93)① 更令人遗憾的是,新潮作家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一错再错,在随后的新历史主义浪潮中,新潮作家任意操纵历史,在历史的“真空”中完全“失重”。
二、死亡叙述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
新潮小说将死亡叙述与现实生活剥离除了想获得一种历史的视角外,它的另一个“阴谋”就是要实现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断裂。从事新潮小说写作的作家们,大多是一些年青新锐作家,他们一方面力图摆脱父辈“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受欧美先锋文学的影响,崇尚一种纯粹的写作,力图将文学从过去依附地位的尴尬处境中摆脱出来,捍卫文学应有的尊严。因此,将死亡从过去那种宏大叙事主要构成部分切割开来,是新潮作家实现死亡叙述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剥离的必要手段。过去,象《红日》、《红岩》、《林海雪原》等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死亡”往往担负着负载小说主题功能的重任,英雄的光荣献身和敌人的必然灭亡,不仅对比鲜明,而且构成一种因果关系,形成经典小说叙述一条不曾公开的协约,英雄之死和敌人的灭亡总是同时出现,而且英雄之死必然导致敌人的灭亡,否则就是违反叙事逻辑,小说的叙事意义就会受到侵犯,读者的审美期待就会受到挑战,不满、责备之声就会像潮水般扑来。同时,英雄之死还时时提醒读者要饮水思源,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昨日英雄之死之间的因果联系。总之,传统的死亡叙述(尤其是英雄受难和英雄之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学中的主要表达方式之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惧感被英雄之死所造成的壮烈感以及随后带来的胜利感取代,死亡成为一种英雄的纪念碑供后人凭吊,成为胜利狂欢前的三分钟的默哀。正是这种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态度致使我们的战争叙事很难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从这一点上说,新潮作家的死亡叙事将死亡从过去宏大叙事的规训下解脱出来还原死亡的本来意义,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不仅为将来的战争叙事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还将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悲剧意识,确定一种新的悲剧审美原则。
由于抛弃了宏大叙述的准则,新潮作家的死亡叙事只能和个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展现个体生存景观的必要手段。如格非《大年》里面的豹子和唐济尧,两个人一个是新四军,一个是新四军的联络员,惯偷出身的豹子参加新四军,既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为了替穷人翻身,而是因为乡绅丁伯高家漂亮的姨太太玫,作为联络员的唐济尧既不是豹子的革命引路人,也不是豹子的成长导师,他亲手将豹子杀死也不是为革命除害,而是为了方便和玫私奔。丁伯高和豹子的先后被杀,只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格非就这样将一个革命的故事化解为个人情欲的暴力行为。格非在小说的卷首还特地加了一个题记——“我想描述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情欲萌动和展开的过程,其中也包括外来因素的干扰所造成的情欲的突然中断。发生在大年前后的这一场死亡事故,原来只不过是情欲爆发和冲突的结果,死亡在格非笔下竟是这样的灰色和平淡。同样,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中的所有死亡也是那么平淡无奇,即使是王香火这样将日本兵引向绝境最后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杀的“壮举”,由于叙述者的不动声色而失去悲壮的效果:
那两个日本兵哇哇叫着冲向王香火,这一刻有几个日本兵回头望着他了。他看到两把闪亮的刺刀仿佛从日本兵下巴里长出来一样,冲向自己。随即刺入了胸口和腹部,他感到刺刀在体内转了一圈,然后又拔了出来。似乎是内脏被挖了出来,王香火沙哑地喊了一声:
“爹呀,疼死我了。”
他的身体贴着树木滑到地上,扭曲着死在血泊之中。
日本兵指挥官喊叫了一声,那些日本兵立刻集合在一起,排成两队。指挥官挥了一下手,他们“沙沙”地走了起来。中间一人用口哨吹起了那支小调,所有的人都低声唱了起来。这支即将要死去的队伍,在傍晚来到之时,唱着家乡的歌曲,走在异国的土地上。[6] (P209)
王香火用计将一队鬼子消灭掉,本该享受“民族英雄”的待遇,没想到却死得这样凄惨,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人之举,最后“扭曲着死在血泊中”。倒是日本兵临死前显得十分体面,他们是排着队唱着歌从容走向地狱之门的。抗日英雄竟然死得没有侵略者悲壮,这才是真正的惊人之举,原先的意义链条和叙事逻辑被余华彻底割断和扰乱。在洪峰那里我们还能看到对死亡的另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奔丧》中的“我”听到姐姐告诉父亲死亡消息时,不是悲伤,而是专注地欣赏姐姐丰满的乳房,奔丧中,“我”竟避开妻子去与过去的恋人约会,父亲的死与儿子“我”似乎毫无关系。从格非、余华、洪峰等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中,可以看出,死亡不但没有附加任何意识形态意义,甚至连伦理意义也取消了,剩下的只是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这样的叙述只能是一副冷冰冰面孔的寡情叙述。
三、死亡叙述与写作主体情感的剥离
为了进一步表现死亡的客观性,新潮作家必须保持在死亡面前的克制态度,尽量不让自己的感情渗入到叙述当中去。这种将主体感情从审美对象当中抽离出去的行为,其实是和西方经典美学家的观点相符合。康德认为:“构成鉴赏判断的规定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有对象表象的不带任何目的(不管是主观目的还是客观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因而只有在对象借以被给予我们的那个表象中的合目的性的单纯形式,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话。”[7] (P60-61)在康德那里,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和人类的共同感构成了美,而黑格尔则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8] (P142)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9] (P147)无论是康德或黑格尔,他们都强调审美的纯粹性,即非功利性。新潮作家最终从启蒙与救亡、自由与民主、独立与富强、科学与现代化等宏大话语模式中突围出来,转向对人性本身和人的深层意识的探索,从功利主义转向非功利主义,从话语模式和审美理念两个维度变革文学,使当代文学的面目焕然一新,为中国文学重新走向世界进而走在世界提供了可能。然而,如果新潮作家仅仅是回到康德、黑格尔那里,那么他们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甚至还没有到达冯至、李金发这样现代作家的地步。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经典美学在西方早已受到挑战,有人这样批评到:“黑格尔所投射出来的人的形象是经过美化的,但也是对我们真实的人类经验的歪曲,因此,最终是一种侮辱。”[10] (P284)这就是说自朗吉努斯以来以崇高、和谐为核心的传统美学观念受到挑战,因为他们都否认或忽视存在的非本真性和被遮蔽状态,尤其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大厦根本就没有正视人的真实的存在。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先锋派使得审美又回到感性层面,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审美关注的是人类最粗俗的,最可触知的方面……审美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激动——这种激动是肉体对理论专制的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11] (P1)关注人类最粗俗的,最可触知方面的审丑艺术成为先锋作家剖析人性恶、展示存在荒诞感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新潮作家正是从欧美先锋派那里获得灵感,他们很快地走向审美的反面——审丑,于是叶芝当初曾惊呼的“一种可怕的美”终于在新潮作家的文本中迷漫开来。死亡“作为一种可怕的美”成为新潮作家的新宠。莫言的《红高粱》和《檀香刑》对死亡过程的描写尤为动人心魄。《红高粱》中活剥罗汉大爷一段曾被无数论者反复引用,这里不妨再引一次:
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呲出来。……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的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丁东丁东响。
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不成形状的嘴里还呜噜呜噜地响着,一串串鲜红的小血珠从他酱紫色的头皮上往下流,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有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
正如有论者评述的那样:“莫言这种骇人的描写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亵渎,客观、冷漠、克制成为其展示人的躯体和人的行为之丑的情感基调。”[12] (P88)莫言的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曾经招来不少非议,但莫言没有丝毫让步,反而在《檀香刑》中更有发挥。
俺看到檀木橛子在俺的敲击下,一寸一寸地朝俺岳父的身体里钻进。……
随着檀木橛子逐渐深入,岳父的身体大抖起来。尽管他身体已经让牛皮绳子紧紧地捆住,但是他身上的所有的皮肉都在哆嗦,带动得那块沉重的松木板子都动了起来。……
俺看到岳父的脑袋在床子上剧烈地晃动着。他的脖子似乎被他自己拉长了许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想不出一个人的脖子还能这样子运动:猛子一下子抻出,往外抻——抻——抻——到了极点,像一根拉长了的皮绳儿,仿佛脑袋要脱离身体自己跑出去。然后,猛地一下子缩了回去,缩得看不到一点脖子,似乎俺岳父的头直接地生长在肩膀上。
终于,檀木橛子从孙丙的肩头冒了出来,把他肩上的衣服顶凸了。俺爹最早的设计是想让檀木橛子从孙丙的嘴巴里钻出来,但考虑到他生来爱唱戏,嘴里钻出根檀木橛子就唱不成了,所以就让檀木橛子从他的肩膀上钻出来。……檀木橛子就上下均匀地贯穿在孙丙的身体之中了。孙丙还在嗥叫,声音力道一点也没有减弱。爹仔细地观看了橛子的进口和出口,看到各有一缕细细的血贴着橛子流出来。满意的神情在爹爹脸上洋溢开来。[13] (P461-465)
如果说行刑的过程血腥得让人不忍卒读的话,那么下面的文字更是惨不忍睹:
余看到,眉娘不避污秽,站在孙丙的眼前,用一条白色的绸手绢,擦拭着苍蝇们用闪电般的速度下在孙丙身上的卵块。……那些卵块在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了蛆虫,蠢动在孙丙身上所有潮湿的地方。……
孙丙身上不但散发着扑鼻的恶臭,还散发着逼人的热量。……但他还没有死,他还在喘息,喘息的声音还很大,他的两肋大幅度地起伏,胸腔里发出呼隆呼隆的痰响。
成布衣……近前后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戳了戳从孙丙肩上探出来的木橛尖儿,然后又转到孙丙身后,俯身探看了木橛子的尾。在他细长的手指动摇了木橛子的首位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息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14] (P483 P486)
无独有偶,余华在《现实一种》和《一九八六年》等小说中对死亡的叙述也是令人触目惊心,前者对山岗尸体的分解写得那样漫不经心:医生们在玩乐和嬉笑中割取自己所需要的部位,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具刚刚死去还有余温的尸体,而仅仅是一堆肉。后者写疯子采用的五种古代刑罚(墨、宫、大辟)对自己进行的自残是那样细腻而富有耐心,砍膝盖、断手足、锯鼻子、斩双腿……尽管是血肉横飞,但周围的人却无动于衷,疯子死后,他的妻子和女儿竟然很优雅地走在大街上。
新潮作家将死亡叙述与主体情感剥离的做法不仅导致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审丑的确立,而且也是对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和零度写作等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回应。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潮作家这种冷漠的叙事态度和随后崛起的新写实主义是不同的,尽管两者都袭用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都是对过去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拨,但新潮作家更注重行而上层面的精神追求,而新写实主义作家则完全浮在生活的表层,专注于“一地鸡毛”、“几块豆腐”之类的芝麻小事。新写实主义作家中的许多人最后滑落到通俗、甚至庸俗的层面与其自身的美学态度不可分割。
四、新潮作家死亡叙述的再思考
死亡叙述经过三次剥离后,新潮作家们确实让我们对死亡有着一种全新的感受和认识。但新潮作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死亡叙述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将被迫陷入这样的悖论:既然死亡没有意义和价值,那么新潮作家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地书写死亡?难道仅仅是为了呈现死亡的无意义?这样做岂不是更无意义?先锋精神到底体现在哪里?让我们对西方先锋作家和中国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作一番比较后,再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西方先锋作家的死亡叙述缔造了自己的文化英雄,而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在嘲笑传统的英雄之死后,出现了意义的空白。有着深厚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方先锋作家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决定了西方先锋作家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极其尊重,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只要他是上帝的选民,在其死亡时都会受到祈祷,享受应有的仪式。无论是最后欣然走向刑场的K(卡夫卡《诉讼》),对饥饿表演爱得发狂将自己关进兽笼供人观赏的饥饿艺术家(卡夫卡《饥饿艺术家》),有自杀嫌疑的德·雷谢克(西蒙《弗兰德公路》),含笑、坦然而死的罗伯特·乔顿(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和凯瑟琳(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他们的死亡都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因而这种死亡不但没有给人带来恐惧和颤栗,相反却赢得尊重和敬仰。卡夫卡的许多人物都带有一种替人受难色彩,如《在流刑营》中的那位军官(行刑官),最后自己代替犯人受过,被杀人机器杀死。② 再如《饥饿艺术家》,如果把饥饿艺术家所呆的笼子换成十字架,他就是主动前往耶路撒冷受难的基督。军官和饥饿艺术家完全可以看作反抗现行秩序,维护信仰的文化英雄。在西方先锋作家那里,拯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启蒙者的振臂高呼,而是从自我开始,自我拯救和自我启蒙,他们不以精英分子自居,他们的表达始终是一种个体表达,注重叙述主体内心的各种经验和体验,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在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切,虽然上帝的地位已经动摇,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但他们心中的上帝永在。这个“上帝”在卡夫卡那里就是对绝望和荒谬的经典忍耐,在海明威那里就是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硬汉”精神。无论先锋作家表现怎样的物化的世界,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始终没有停止,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问也始终没有停止。因此,德·雷谢克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乔顿和凯瑟琳对自由的追求,都可以看作先锋作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与欧美先锋作家相比,中国当代新潮作家在死亡叙述时却没能塑造出自己的文化英雄,相反却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虚无主义。新潮作家在嘲弄、消解传统的“英雄之死”后,却一筹莫展,也有个别新潮作家,企图有所突破,但并不成功。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很显然,莫言想从余占鳌这个勇猛彪悍的土匪身上发掘一种失传已久的强力精神,寻找中华民族深处的蕴藏着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然而,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理念和信仰的土匪来承担,连莫言自己恐怕也没有信心。其他作家,像余华、格非、苏童等人,都没能展现死亡与永生之间的逻辑联系,他们在死亡叙述时将“英雄”置换成“常人”(包括“惯偷”、“草莽”甚至“疯子),这些常人之死虽然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此在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但没有赢得“人”的尊严。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将英雄“杀死”的同时,也将人“杀死”。③
其次,西方先锋作家的死亡叙述具有强烈的原罪意识和自我解剖、自我拷问的勇气,而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不乏对苦难的揭示,也具有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的功能,但始终缺乏自我拷问的精神,从而失去自我批判的价值。在罪感的认识上,中西文化相去甚远。由于《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的原罪,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罪感意识,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存在,要不断向神灵忏悔,以减轻自己的罪恶。而中国文化中虽也有“性恶论”一说,但终于敌不过“性善论”的绝对优势地位,只能始终沉默不语,作为“性善论”的陪衬品被偶尔提及。即使是“性恶论”与原罪意识还是两码事,“恶”如果不表现出来就不能称之为“罪”,“恶”还可以以伪善的面目出现,而原罪是与生俱来的,显而易见的不可隐瞒,活着的人必须进行赎救。性善论则是将人的罪恶归为后天形成的,尤其归结为外在环境的主动施为。这样必然导致对自己所犯罪恶的辩解甚至否认。由此可见,文化语境的差异最终导致先锋作家和新潮作家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绝少西方那种勇于自我解剖、对灵魂进行拷问的作家。作为波斯米亚式人物的知识分子,其主要职责在于批判。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15] (P25)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和集权主义压制,中国还缺少真正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多的是依附性知识分子(也就是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得到改善。叙事主体已经从政治批判、文化批判走向对批判本身的反省:“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把责任推向社会,推向他人,推向个别的决策者;所有社会历史的责任都由他人承担,而每个参与者均与历史事件无关;这种社会批判对个体的忽视,个人责任在社会历史中的遗忘,正是造成灾难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社会缺乏大批的责任个体和自由个体,暴政和专制才得以形成。”[16] (P15)但这种反省在新潮作家那里始终是作为一种精神背景而存在,也就是说新潮作家虽然具备了自我反省的意识,但并没有将其化作主体内在的精神需求和心理自律。所以这种反省仍是不自觉的,是将自己排除在外而直接指向他者的反省,骨子里有一种“举世皆醉余独醒”的优越感。所以,当福克纳的昆丁为妹妹凯蒂的堕落和心中的乱伦意识而悔恨不已举枪自杀时,洪峰的“我”却在专注地欣赏前来报丧的姐姐的丰满的乳房。当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了解救姐姐和索尼亚而将房东老太太砍杀并为此灵魂受到无尽的折磨时,格非的唐济尧却在算计着怎样将情敌豹子除掉。新潮作家死亡叙述中所表现的对主流话语的反叛和嘲弄的勇气令人可敬,对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阴暗面的批判让人拍手称快,但是缺少像鲁迅那样自我解剖的真诚,缺少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拷问灵魂的胆识和勇气。
最后,西方先锋文学的死亡叙述崇虚,而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尚实。西方先锋文学中的死亡叙述背后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存在与时间关系的探讨,并提出了“向死而在”的哲学理念,为先锋作家的死亡叙述提供了哲学依据。欧美先锋文学从来没有回避死亡,相反它表现出对死亡的迷恋。这种死亡意识是不能简单地用悲观主义哲学几个字眼来概括的。在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欧美先锋文学所表现的死亡意识是对生命形态的另一种表达,死亡固然可以引起恐惧和战栗,但死亡并不是灾难的演示,也不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怜悯之心,而恰恰相反,它表达的是一种悲壮的情绪。同时,在先锋作家那里“死亡”往往和“原罪”、“拯救”、“自赎”、“永生”这些哲学概念联系在一起,因而更具有行而上的意义。西方先锋文学的死亡叙述兼具隐喻功能,是虚指。如卡夫卡的《在流刑营》的那位军官,他之所以选择自杀,并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而是觉得无力维护旧有的司法程序,在绝望中和旧的法律机器一同毁灭。正因为是隐喻,所以它的所指也是不确定的,有人将它理解为“遗弃”,也有理解为“替人受难”、“自我放逐”、“最后审判”等等。正是由于虚写,使得西方先锋作家的死亡叙述具备丰富的意义,也为读者提供了多种阐释空间。相对于西方先锋作家,中国当代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特别强调死亡的逼真感和亲在性,好像写作者本身曾经经历过死亡的过程或者就在死亡的现场亲自聆听死亡者对他叙述死亡的感受:
她明显觉得脚趾头是最先死去的,然后是整双脚,接着又延伸到腿上。她感到脚的死去像冰雪一样无声无息。死亡在她腹部逗留片刻,然后像潮水一样漫过了腰际,漫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这时她感到双手离她远去了,脑袋仿佛被一条小狗一口一口咬去。最后只剩下心脏了,可死亡已包围了心脏,像是无数蚂蚁似地从四周爬向心脏……
——余华《现实一种》
医生出身的余华简直是从解剖学层面上展示了死亡的过程。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写法所具有的意义。在这种冷漠的背后我们依然感受到余华这样的新潮作家对个体的生存状况的强烈关注。在我看来新潮作家除了极个别的文本外(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马原的《叙事》等)大都是有所寄托之作,决不能因为新潮小说迷恋形式,讲究艺术突破,就将其看作是形式的巨人,精神的侏儒,所谓“老派小说读意义,新派小说读句式”的说法,将新潮小说家苦心经营的意义之域一笔取消。余华《现实一种》对人性恶的揭示不可谓不深刻。再如莫言的《檀香刑》对杀人文化的反讽也是空前的。④ 但由于新潮作家过分追求对死亡的精雕细刻式的描写,他们在获得死亡的本体性的同时,减少或丧失了死亡所指向的意义域。尽管余华、格非、苏童、北村等作家几乎用笔去拥抱死亡,但始终没能传达出对死亡的尊重和崇敬。新潮作家将死亡从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主体情感中剥离出来的目的,在于将死亡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加以关照,企图获得某种超验的价值或意义,但由于在死亡叙述中所采取的这种过分写实的态度,使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注释:
①这里的“历史的终结”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是同一个概念,它是指一种“历史视域”一种,“面向世界的总体性”。
②军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新任司令官将老司令官一套诉讼程序废置不用,在求助旅行者(司法专家)遭到拒绝后,愤而自杀。军官竭力维护自己的信仰,一旦当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无望时,他宁可自杀。小说结尾曾交待老司令官的墓志铭的内容:“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们为他挖了这个坟,立了这个碑,现在只好隐姓埋名,可以预言,司令官在若干年后又将复活,从这个屋里率领他的信徒重新占领这块营地。请你们相信并等着瞧吧!”从中可以看出,军官是把老司令官比作耶稣,自己比作耶稣的门徒。
③吴义勤先生在《极端的代价》一文中,深入地讨论了小说要不要人物进行这一小说诗学问题,也是对新潮小说死亡叙述这种虚无主义的反思。参见《花城》2004年第6期。
④当然也有不少读者由于理解力的障碍认为莫言把杀人技术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从而责备莫言的不人道和非理性。
标签:先锋文学论文; 死亡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红高粱论文; 作家论文; 余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