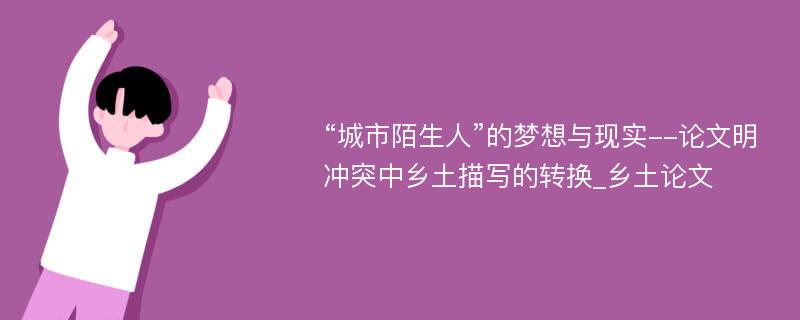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异乡论文,冲突论文,现实论文,梦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世界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中,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带着血腥味的掠夺:“城市与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合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更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在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大都市是这一时尚的先锋。”(注:劳伦斯·哈沃斯语,参见【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著,孟庆时译《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研究译丛”。154页。)这是西方从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它无疑是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远没有逾越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我们沿海的小部分地区同时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语境中了,但是,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而中国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正是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乡土存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变化,才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领域。
“农民工”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概念,它囊括了一切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定义似乎还不能概括那些走出黄土地的人们在城市空间工作的全部内涵,因为游荡在城市里的非城市户籍的农民身份者,还远不止那些从事“打工”这一职业的农民,他们中间还有从事其他非劳力职业的人,如小商小贩、中介销售商、自由职业者、代课教师、理发师、按摩师、妓女等许多不属于狭义“农民工”范畴,他们比那些真正的“打工仔”更有可能成为城里人。当然,在阶级身份层面的认同上他们仍旧是属于广义的“农民工”范畴的。因此,无论从身份认同上来确定这些“城市游牧者”阶层,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考察这些漂泊者的灵魂符码,我以为用“城市异乡者”这个书面名词更加合适一些。
“城市异乡者”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许多作家的关注,就是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二难命题。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他们出卖劳力,出卖肉体,甚至出卖灵魂,但是,城市给予他们的却是剩余价值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然而,比起在土里刨食、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生活来,他们又得到了最大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是个完全边缘化的“虫豸”,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是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但是,一旦他们返归乡土,就又会变成一个趾高气昂“Q爷”,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统治者”,一个乡村的“精神富足者”……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着悖反的现实生活图景与精神心理光谱。
毫无疑问,对“城市异乡者”的描写,随着日益澎湃的“农民工潮”和农民职业向工业技术的转换而迅速猛涨,对这一庞大群体的现实生活描写和灵魂历程的寻觅,就成为近几年来许多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而就作家们的价值观念来说,其中普遍的规律就是:凡是触及到这一题材,作家就会用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来掌控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这是“五四”积淀下来的“乡土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以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渐行渐远的、带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开始在这一描写领域复苏。在这里,作家们的思考不再是那些空灵的技巧问题,不再是那些工具层面的形式问题,因为生存的现实和悲剧的命运已经上升为创作的第一需要了。即使像残雪那样带有荒诞意味描写的作家,一俟接触到民工(《民工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这一题材的时候,也不得不在严酷的生活面前换上了现实主义的面孔,改变了以往那种艰涩的形式主义的叙述外壳,用更平实的叙述方式来介入现实生活,即便还是改变不了她那种絮絮叨叨式的精神病者梦呓的琐屑,但也毕竟清晰地描写和抒发出了城市给农民带来肉体痛苦和心灵异化。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在悲剧审美与喜剧审美之间,绝大多数作家站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用饱蘸情感的笔墨去抒写人性和人道的悲歌。其实,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新的文化背景需要我们不但对人性和人道作出回答,还需对时代和历史的发展作出评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需要克服人性的偏颇,客观地去描写戴着假丑恶面具的发展性事物的,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
专门关注乡土的女作家孙惠芬一旦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的乡土社会生活当中去,就痛切地体味到乡土现实世界的悲剧性命运:“与那些被外出民工的男人们撇在乡下空守着土地、老人、孩子和日子的女人们相遇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她们的男人如今与她们、土地、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常年在外,他们与城市难道真的打成了一片?而女人与土地、日子、丈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于是,在“2001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当我在我家东边的台阶上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民工扛着行李泪流满面地往车站走,一对回家奔丧的父与子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不一定是父与子,更不一定是回家奔丧,可是不知是为什么当时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他们一旦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便再也顾不上企图超越自己的妄想了,我一下子被他们牵进去,一下子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父与子的尊严和命运,我一旦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他们的尊严和命运,便不设防地走进了一条暂时的告别工地、告别城市、返回乡村、返回土地、返回家园的道路,在这条大路上展示他们与这一切的关系便成了我在劫难逃的选择。”(注:孙惠芬《心灵的道路无限长》,《小说选刊》2002年第4期,5页。)本着这样的初衷,孙惠芬创作了《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作品描写了鞠广大、鞠福生父子二人回乡奔丧的故事。无疑,小说的视点是在空间和时间的不断转换中,来完成人物的塑造的,空间是城市(实际上就是建筑工地)与乡村(歇马山庄)交替呈现的;时间是过去与现在叠印在一起的。就空间感来说,作品给人的感觉还是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和语境之中的。这不仅是选材的使然,多多少少还带有作者不灭的“歇马山庄”的乡土情结,因为作家的价值立场是与乡土和农民呈平行视角的:“歇马山庄,你离开了,却与它有着牵挂与联系,而工地,只要你离开,那里的一切就不再与你有什么联系。鞠广大已做了十八年的民工,他常年在外,他不到年根儿绝不离开工地,他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夏天里就回家呢?”那无疑是那个叫着“家乡”的地方遭遇到了天灾人祸。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比对之中,作家的价值取向虽然是呈悖论状态,但是,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欺压的农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几乎成为作家写作情感的宣泄。当鞠家父子离开喧嚣的城市工地,踏上火车看到窗外农田景色时,他们的心境就会好起来:“田野的感觉简直好极了,庄稼生长的气息灌在风里,香香的,浓浓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有被搂抱的感觉。鞠广大和鞠福生走在沟谷边的小道上,十分的陶醉,庄稼的叶子不时地碰撞着他们的脸庞。乡村的亲切往往就由田野拉开帏幕,即使是冬天,地里没有庄稼和蚊虫,那庄稼的枯秸,冻结在地垄上黑黑的洞穴,也会不时地晃进你的眼睛,向你报告着冬闲的消息。走在一处被苞米叶重围的窄窄的小道上,父与子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迷失了他们回家的初衷,他们想,他们走在这里为哪样,他们难道是在外的人衣锦还乡?”不错,城市是他者的,民工只是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一个“闯入者”、一个“城市的异乡客”、一个“陌生的侨寓者”、一个寄人篱下的栖居者,他们既是魂归乡里的游子,又是都市里的落魄者。但是,毕竟鞠广大们也有梦想:“他走进了一个幻觉的世界,眼前的世界在一片繁忙中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在这个工地上,他鞠广大再也不是民工,而是管着民工的工长,是欧亮,是管着欧亮的工头,是管着工头的甲方老板。”鞠广大们会成为工头,从而变成城里人吗?毫无疑问,这一梦想是每一个走进城市的淘金者的最终追求的人生目标。但是,这条道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这篇小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出许多作家清晰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文化批判立场,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从价值理念来看,许多作家过分迷恋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秩序,过多地揭露城市文明的丑恶,多多少少就削弱了作品更有可能进入深层历史内涵的可能性。
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山花》2005年第1期)几乎是用严酷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去抒写一个农民工的浪漫主义的理想——那个男主人公“我”是一个一心想做城里人的民工,他有于连式的野心,但是却没有于连那样的运气;而女主人公却是一个带着强烈传统伦理道德的民工,因此,在长安街接吻便成为两种文明矛盾冲突的焦点,一个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不是事件的事件,却成为一个重大悲剧,这就是文明转型中农民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作者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平淡寡味的故事铺衍成为一个跌宕起伏的中篇呢?其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就直接表现了主题:“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不要说北京是世界有数的大都市,就是我所在的云南富源这个小县城我也非常热爱……当我从报刊杂志上读到一些厌倦城市、厌倦城里的高楼大厦、厌倦水泥造就的建筑,想返朴归真,到农村去寻找牧歌似生活的文章时,我在心里就恨得牙痒痒的,真想有机会当面吐他一脸的唾沫。”是的,那些后现代文化心态对于仍然生活在农耕文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来说确实是奢侈一些了,他们只能发出“我厌倦这诗意的生活”的强音!因为,解脱贫困才是他们的最大生存渴望,你不可能让一个还没有尝到过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农耕者去享受后现代的精神面包,所以,对一切城市文明的渴求成为农民工阶层的理想:“我害怕被绑在家乡的小山村里,怕日出而作,日落而眠的生活,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融入这个城市便成为民工们的最高追求目标,他们不但要取得这个城市的肉体身份的确认,更重要的是还要取得这个城市的精神身份证,做一个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城里人。因此,“我”才别出心裁地用到长安街接吻来证明我在这个城市的存在!“我”的这个想法是蓄谋已久的,但是其目的性是非常清晰的:“想到长安街接吻这个念头于我太强烈了,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是空穴来风,多少年的城市情结使我想以城市的方式来生活。”毋庸置疑,“生活方式”对于农民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才是检验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试金石,“生活方式”可以改变人,同时也能改变他者对你的身份认同,要使民工不再受城市人的歧视,“我”才从那些城市女人的白眼和咒骂中读懂了这生活的真谛,才想出了到长安街去接吻的妙招。这是一个农民工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我”向城市宣战的大胆行动计划。否则“一个从农村来的人有什么必要跑到长安街去接吻?接了吻又有什么意义?接了吻又说明了什么?这是荒诞而无聊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对于这样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荒诞的想法,如果实施的对象是一个城市姑娘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喜剧的结局,然而,“我”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在农耕文明中长大,而在城市文明里又精神发育不全的村姑,那注定会是个悲剧。由于柳翠的拒绝,致使这个进军城市的计划一度落空,导致“我”成为残废。其实“在工棚里接吻和在广场上在大街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我就是渴望着在长安街上接吻。在长安街接吻对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的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为什么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富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获得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城市边缘人起码的精神权利!但是,悲剧的冲突和剥夺这个权利的动能不是城市的制约,而恰恰是来自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的压力,来自柳翠冥顽不化的封建固执:“来自她的封闭、缺乏自信和不把自己当个人的想法,她把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拉开,自觉地按乡村的做法一切自己约束自己。她极大地伤害了我,她在我走向城市的路途中猛的给我一闷棒,打得我趔趔趄趄几乎倒下。”这样的打击要比遭受城市的白眼和咒骂还要悲哀,它没有使“我”致命就算是幸运的了,当“我”从五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成为残废的时候,才意识到“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虽然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让柳翠配合“我”完成了在长安街接吻的壮举:“我和柳翠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车流奔驰之侧,在期待盼望之中,热烈而又真挚的亲吻起来了。掌声热烈地响起来,掌声不光来自簇拥我们来的民工,还来自所有围观的人。我的心被巨大的幸福所陶醉,我的灵魂轻轻地升到高空,在高空俯视北京。呵,北京真美。”这个浪漫主义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但是,我还是兴奋不起来,因为我还不相信城市有这样的包容性,我还不相信像柳翠这样代表着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秩序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而一步踏进城市文明的门坎。因为民族的劣根性也还残存在这个群体之中。永远的乡土和瞬间的城市,可能是农民难以进入城市的最后一道精神屏障,驱除这样一种前现代农耕文明精神形态中的积弊应该是乡土小说作家价值理念中必有的理性因素。
残雪的《民工团》所描写的民工生活也是悲惨的故事,但是,作家的落点仍然是对农民工群体中的那种相互告密的人性弱点进行揭露,不过,残雪从此也开始介入现实生活的描写,给出了农民工承受肉体的煎熬生活场景:那个工头三点过五分就叫醒他们去扛二百多斤的水泥包,简直就是个现代“周扒皮”的形象再生;民工掉进石灰池就回家等死;掉下脚手架就当场毙命……就像灰子叔叔一再赌咒发誓不再到城里来打工,而来年又回到了这个群体当中那样,生存决定了这条道路是他们的惟一选择:“我要养活老婆孩子,如果不外出赚钱,在家乡就只能常年过一种半饥不饱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他们还得承受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这一切是使他们成为“城市异乡者”异化的原因——他们想成为残废者!那样就不再受肉体和精神的煎熬了:“我现在成了残废人了,你们来羡慕我吧。我一天要晕过去好多次。”“我的话音刚一落,房里的四个人就都嚷嚷起来,说他们‘巴不得成残废人’、‘巴不得晕过去’,那样就可以躺下了,那是多么好的事啊。”不幸的事变成了幸福的事,这究竟是农民工的幸事呢,还是不幸呢?我们在泪中看见了笑呢,还是在笑中看见了泪呢?!作品给出的最后问号应该是:农民如果恪守土地、恪守农耕文明的精神秩序,会不会“异化”呢?
同样是描写农民工的“异化”,荆永鸣却是一个专写农民工进城后遭遇到文化尴尬的作家,他的系列作品所呈现的“尴尬中的坚守”正是作家对城市文化批判的折射,是对农民文化心理异化的深层揭示。他的《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更是体现了“进入都市中的外地人,总比城里人有着太多的阻隔,也有着太多的尴尬”。这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我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一个保姆精心侍侯一个瘫痪的男人,在终于‘养活了’男人的一只手时,这只手却要去摸她的羞处(《保姆》)——是尴尬;卖烧饼的小伙子用刀子吓跑了撒野的城里人,事后自己的手却老是抽筋儿(《抽筋儿》)——是尴尬;一个餐馆里的伙计在警察‘查证’时,被吓尿了裤子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证件俱全(《有病》)——是尴尬;本篇中(《北京候鸟》)的来泰在城市的雨夜中找不到自己赖以栖身的居所,也是尴尬……如此说来,‘尴尬’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我小说里的一种符号呢?”(注:荆永鸣《在尴尬中坚守》,《小说选刊》2003年第9期,5页。)不要指望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和新的生活,就会赢得城市和城市人的青睐,严酷的市场经济准则不是以农耕文明的道德法则行事的,如果荆永鸣的系列小说还停留在对文化尴尬的无奈和怨恨之中的话,那么,更多的小说则是用血和泪来控诉城市文明给这群候鸟带来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痛苦。
乡土的富裕是要农民付出沉重的肉体代价的,何况即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未必就能够富裕起来。正如陈应松在《归来·人瑞》(《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中描述的农民工工伤死后那样的情形:“摆脱贫困,总是要一代人作出牺牲的。”“桃花峪有二十几个妮子长梅疮,就是梅毒,没了生育,可人家楼房都做起来了,富裕村哪,哪像咱们这儿!后山樟树坪穷,可去年死了八个,挖煤的,瓦斯爆炸,一下子竟把全村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千多块,为啥,山西那边矿上赔的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种理念也正在渗透着一些过去沉湎于农耕文明而难以自拔的一些乡土小说作家当中,贾平凹也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牺牲有两辈人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农民永远是很辛苦的,是需要极大的关怀群体和阶层。”(注:《贾平凹答复旦学子问》,2005年3月31日《文学报》。)但是,如何处理好关怀与批判的关系,的确是每一个乡土小说作家值得深思的问题。
可以看出,对农民出走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已经成为作家们所关注的普遍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女青年在进入城市后的命运成为乡土小说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她们不仅是构筑故事的最佳方式,同时又是透视乡土与城市的最好视角。在吴玄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叙述:“我走进发廊街,就像回到了故乡。这感觉其实有问题。我的故乡西地,事实上,比发廊街差远了,它离这儿很远,在大山里面,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我的乡亲姐妹们在那个破巢里养到十四、十五岁,便飞到城市里觅食,她们就像候鸟,一年回家一次,就是过年那几天。本来,西地和发廊毫无关系,就我所知,西地世世代代只出产农夫、农妇、木匠、篾匠、石匠、铁匠、油漆匠,教师匠也有的,甚至有巫师和阴阳先生,但没有听说过发廊和按摩,西地成为一个发廊专业村,是从晓秋开始的,历史总喜欢把神圣的使命交给一些最卑贱的人,几年前,那个一点也不起眼的小姑娘晓秋,不经意间就完全改写了西地的历史。”“发廊改变了我妹妹的命运,乃至全村所有女性的命运。通过发廊,女人可以赚钱,而且比男人赚得多,我妹妹一个月寄回家的钱,就比我父亲一年劳作赚的还多。后来,村里凡有女儿的,日子过得大多不错。从此,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还有一个近乎笑话的真实故事,村里的一个妇女,突然伤心的痛哭,村人问她什么事这般伤心,那妇女伤心地说,她想起十五年前一生下来就被扔进尿桶淹死的女儿了,当时若不淹死,她现在也可以去发廊里当工人,替家里赚钱了。”是的,发廊生意不但改变了乡土的生存观念,而且改变了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依靠儿子传宗接代、延续农耕神话的生育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黄土地里走出去的一代青年妇女用她们的血肉之躯作代价,为中国乡土社会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如果从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来衡量她们的行为,无疑是不齿的。但是,从她们别无选择的人生选择来看,她们在无形中又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尽管它是以一种过激的、丑陋的方式呈现,但是,它的杀伤力却是巨大的。这是乡土的幸还是不幸呢?历史的进步往往是需要丑与恶作为杠杆的,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有其双重性的效应,这就是历史送给文明的礼物。所以,当农民工们在接受这份沉重的礼物时,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呢?这正是乡土小说作家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中美丽的姑娘樱桃就是用自己的色相为贫困的乡村之家建起了拔地而起的楼房,“这幢楼房算得上是全村最气派的房子了,村里在外面做事的人那么多,有几个像樱桃姐这样有本事寄钱回来,让家人住上楼房的呢?”可是,这贫困的乡村能够接纳她这个从都市里面走回来的游子吗?答案却是否定的。与其说她是死于假药的治疗,还不如说她是死于乡亲们的冷眼和闲言。她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尤其是那些随意开放的红花草,但是家乡爱她吗?她是在悲愤和郁郁中死去的。然而,樱桃姐最喜爱唱的那首著名的外国民歌《红河谷》的旋律却始终萦绕在乡间河畔,沁入人们干涸的心田。从这如诗的旋律中,我们不仅听到了樱桃姐们的哭泣,而且也看到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当樱桃姐们走出这片黄土地时,她们还能魂归故里吗?其实她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人们怀念的是樱桃姐们的微笑呢,还是怀念她们为家乡所增添的物质财富?难怪樱桃姐每每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满含热泪——那可是城市异乡者眷恋家乡而被抛弃的至痛至苦!这很能使人联想起那部曾在80年代初引起过巨大反响的日本影片《望乡》,在金钱与伦理道德的天平上,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而在淳朴的乡情亲情与伦理道德的天平上,人们又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与怪圈中完成利益和意识形态选择的,谁又能去体验这一出卖肉体和色相群体的内心世界呢?当然,她们内心世界的痛苦也并不仅仅就是伦理道德带来的压力,更多的还是她们不再被那块曾经养育过的乡土所认同,她们成为随风飘荡的无根浮萍,肉体毁灭的悲剧只是表层的,她们最在意的是灵魂的家园被毁灭!作家所展现出的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时的那种精神的阵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保姆题材是近些年来的热点,而项小米的《二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却是翘楚之作,这不仅体现在轻盈的文体中所透露出来的作家的厚重人文关怀,而且也体现于作家在城乡二元视角中穿行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的价值批判立场,读后令人感动不已。从表层结构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中篇当作一篇反抗压迫和人性觉醒的作品来看。但是,从那个不是主角的主角人物二的死魂灵中,我们看到的是保姆满目的心灵疮痍——对乡土性别歧视的反抗使她走进了城市,而城市的奸诈和隔膜又使她绝望。我们的主人公小白就是在这样的悖论循环中,从一个梦想成为一个城市的女主人而变成一个城市的流浪者的。小说描述小白的心灵历程是很清晰的:开始对主妇单自雪的歧视是“瞧不上就瞧不上,咱乡下人到城里就是来挣钱的,不指望你顺带还让你瞧上。咱出力,你给钱,就这么简单。但你不能侮辱咱,咱也是有人格的。”到后来“单自雪教会了她如何从一个村姑逐步成为一个都市人。小白进入城市生活的一切细节都是从这个家庭开始的,在这里得到改造,淬火,蜕皮”。再后来,“小白就渐渐看懂了城里人的表情。”但是,她很清楚她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这栋二百平米的复式跃层,这个有着沙拉娜大理石地面,有着钢琴、电脑、等离子电视的城里人的家,远远比不上她和二的共同嬉戏的那个山洼。在山洼里,小白是主人,而在这里,她不是。”但是,她难道就不想做城市的主人,做这个家庭的主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她和主人一家到三亚亚龙湾的凯莱大酒店旅游度假时,她的野心就是随着城乡和贫富的巨大落差而悄悄发生了变化:“睡上一个晚上的觉,就够一个乡下孩子交五年的学费了。小白突然感觉,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命运对自己是如此的不公平!”这也可以看作是她和男主人聂凯旋那段因缘最初的思想萌芽吧。作者没有简单地处理一个乡下小保姆与城里大律师之间的爱情孽缘,而是又一遍重温了一个“城市姑娘”的“鸳蝴梦”,抑或是“灰姑娘”的城市梦。我们不能把她和聂凯旋的做爱看成是《雷雨》里的保姆与主人始乱终弃的爱情模式,而把作品的意向简单地引向反封建和阶级论的主题。因为小白不仅仅在这个偷情的过程中品尝着乡土社会生活中从来不会出现过的“城市爱情”的甜蜜,虽然男主人聂凯旋还有些虚伪;更重要的是,小白天真地认为,通过聂凯旋死亡的婚姻,她看到做一个城里人的希望了。“小白曾经无数次想象过她将会以何种方式抵达这个时刻,那一定是漫长和奇妙无比的。她尽自己少女的经验幻想过无数可能,唯独没有想象过她未曾经历任何风景就进入了最后的驿站。”无疑,那种初次的性快感使她忘乎所以,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的命运也许从此就改变了。”“单自雪和聂凯旋的夫妻运明摆着到头了。……离婚后聂凯旋的再娶,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吗?自己从此就可以永远逃离没有暖气、没有热水的噩梦般的老家,永远不必违心地去和什么狗剩或者国豆搭帮过日子,去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生儿,而是鲤鱼跃龙门一样,从此过上体面的城里人的生活。关键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本来并不需要自己付出什么,不需要付出鲜血、生命、苦役,甚至,不需要付出尊严,便可以体体面面得到这一切。要知道,多少女孩子为了过上这种生活,只能去做二奶,为了几个钱像活在地洞里的耗子一样永无出头之日,可就这样的日子还被多少人羡慕哪!”但是,生活是无情的,当这个“城市姑娘”的美梦还没有做到一半时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聂凯旋对单自雪一句轻慢的解释就足以把小白爱情和“入城”的理想击倒:“我认为她不过是在抒发自己对都市生活的种种感受,就像报纸上常说的那样,一种‘都市症候群’,不过如此而已”。也正如单自雪所言:“一个结过婚的男人的诺言,基本等同于谎言:相信男人的谎言最后受尽伤害,那不是男人的问题,是女人的问题。”对于一个游走在都市里的边缘人,尤其是一个来自于乡下的女人,如果对生活和爱情的期望值太高,她的命运就会愈加悲惨。小白想走进那个爱情的“围城”,再通过婚姻的“入城”仪式,走进这个城市的红地毯,可是,她与单自雪较量的失败,正是她永远不能理解的奥秘——即使没有单自雪的存在,聂凯旋也不会娶她,因为他和她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人,在聂凯旋来说,那只是一场性游戏而已,可怜小白却没有意识到乡下的她与城里的他原本就不是生活在同一精神空间之中的,他们之间没有身份认同感,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作者在小说结尾虽然给小白的人性抹上了最后一道光彩,但还是遮掩不住一个幽灵游荡在这都市的上空而无所皈依的悲剧命运。就像鬼子在《瓦城上空的麦田》里所描写的那个游走在都市里的幽灵似的无名身份人物那样,他(她)们已然是既被乡村抛弃,又遭城市排斥的一群没有命名的孤魂野鬼!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又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却又不能给他们证明身份的“绿卡”。可是谁又能够发给他们一张“灵魂通行证”呢!(注:参见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这部小说是以批判农耕文明的男权意识开始,转而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城市文明的冷酷,无疑是很有深度的。然而,作家过分的美化小白的心灵,似乎缺少了一点文化批判的自省,阻碍了作品向更深层面的挖掘。
如果说小白没能够通过婚姻实现自己的城市之梦的话,那么,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十月》2004年第6期)中的明惠却是在成为一个城市主妇后遭到精神毁灭的典型人物。作品几乎是用略带淡淡惆怅的细腻笔调勾画出了一个“城市灰姑娘”似的人物。可是我们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肉体上已经成为城里人,而精神与灵魂还不能被城市文明所包容的悲剧下场!明惠自从走出乡土以后,就抱着做一个城里人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挣更多的金钱,她终于更名“圆圆”做了妓女,但是,她挣钱的目的却不是单纯为了寄回乡下炫耀,而是实现自己在乡间的自我人生的价值,她的理想是远大的,充满着高傲,也充满着野心:“圆圆想,我要比徐二翠更有出息,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要他们做城里人,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好一个“城里人的妈!”这正是每一个乡下少女进城以后的玫瑰之梦,当圆圆投入离了婚的副局长李羊群的怀抱中,整天过着奢侈悠闲、无所事事的生活,满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时,一场圣诞节聚会让这个真实的明惠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边缘地位,她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城市,并不属于这个文化圈中的人,而那些举止文雅的女人才是这个城市里的真正主人,这个城市客厅里并没有那个从乡下少女明惠(抑或城市别名为“圆圆”的妓女)的座位!这就使我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那个遭受贵族世界冷眼的妓女。同时,更使我想起了恩格斯在给《城市姑娘》作者玛·哈克奈斯的那封著名的信件,多少年来,我始终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是,恩格斯只提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问题,而为什么没有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那个“城市姑娘”美梦破灭的原由所在呢?同样,在《明惠的圣诞》中,明惠看到的图景和玛·哈克奈斯所描写的场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女士们是那么的优越、放肆而又尊贵。她们有胖有瘦,有高有低,有黑有白。但她们无一例外地充满自信,而自信让她们漂亮和霸道。她们开心恣肆地说笑,她们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啊!她圆圆哪里能与她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交道?圆圆是圆圆,圆圆永远都成不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像那个渴望做一个真正的“城市姑娘”的女主人公那样,当她一旦看到那个欺骗了她的感情的男人正和和睦睦与妻子孩儿欢笑之时,她的悲剧命运就来临了。同样,导致明惠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她的希望的破灭,这个破灭不是肉体的,而是属于精神的!它不是李羊群们所能拯救的,也不是明惠们可以自救的,更不是社会与道德,乃至于宗教可以救赎的人的灵魂归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给出的生活图景是有文化批判意味的。
寻觅精神的归属已经成为一批乡土小说作家自觉追求的主题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宁愿将王梓夫的《死谜》(《北京文学》2000年第12期)看成是一篇寻找灵魂故乡的诗章,也不把它当作一部“反腐题材”作品来看。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小毛通过机缘和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包括把未婚妻和师父接进了城里,俨然是一个城市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从骨子里都是一个用农耕文明的传统眼光来看一切事物的,正因为他的灵魂归属永远是乡土的,才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李小毛在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思维观念的冲突和两难中选择了死亡,就是因为一面是恩重如山的宁副县长以“重义轻利”的农耕文明理念赋予的施舍,一面是腐化堕落的城市文明现实。作为一个乡下人,他既不能违背的是礼教中的信义;又不能冒犯的是道德的天条。就像他既不能逃脱肉欲的海拉尔的性诱惑,又感到对不起未婚妻菊花一样,罪感是在伦理道德层面的两难境地中生成的。李小毛从乡下人成为城里人可谓质的变化,因为他知道:“在农民眼睛里,人只分两类:一类是城里人,一类是乡下人。乡下人生活在地上,城里人生活在天堂。乡下人看城里人,得伸着脖子仰着脸。要是能从乡下人熬上城里人,那可是屎壳郎变知了——一步登天了。为达到这个目的,有多少如花似玉的姑娘降价下嫁给城里的二流子懒汉?有多少人为了个农转非的指标倾家荡产低三下四?”那么,成为城里人的李小毛为什么没有进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中去呢?这是因为乡土的农耕文化印记已经渗透到了李小毛们的灵魂当中去了。就像李佩甫在《送你一朵苦楝花》里所形容的乡下男人永远洗不掉身上的特有气味那样:“他知道他洗不净,这气味来自养育他的乡村和田野,已深深地浸入血液之中。城市女人是城市的当然管理者,每一个从乡下走入城市的男人都必须服从城市女人的管理,服从意味着清洗,清洗意味着失去,彻底的清洗意味着彻底的失去。”但是,这种清洗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他(她)如果是从乡下进城的,那么,他(她)就必须背负着这个农民身份的沉重十字架。尽管“城里的月亮”给了农民无穷的想象空间:“城市在我们眼里就是堆满黄金的地方,城市在我们眼里就是美女如云的地方,城市就是金钱和美女伸手可及的地方。”(墨白:《事实真相》)但是,在绝大多数作家的笔下流露出来的却是无尽的苦难意识。从这些大量“进城”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家过多的同情和怜悯,而在寻觅灵魂的皈依中缺少了一些更深刻的思索。那么,当农民在无所皈依的情况下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壮举”呢?王祥夫的《管道》(《钟山》2005年第1期)似乎想回答这个问题,作品中的主人公“管道觉着自己总有那么一天也会住到城里来,娶一个城里姑娘在城里过安逸日子……管道他妈就说管道心太大,说一个乡下人有那么大的心思不会有什么好处。这简直就让管道痛苦,同时又让管道觉出了某种孤独”。带着这样的心境来到城市,“一没上过学,二又没个亲戚在城里。”管道能够干什么呢?他只能在这个城市里游荡,当他被妓女和鸡头欺骗殴打时,只会重复:“别惹我!谁也别惹我!”他把这个城市当作敌人,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那样,他以一个乡下人的逻辑去思考问题:“管道想过了,自己的钱既然是城里女人拿走的,那最好还是让这个城里的女人把钱退还给自己。”所以,他才铤而走险,不分对象地拿刀去对无辜的城市女人实施抢劫。他对城市的仇恨不是简单的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进城农民形象就可以诠释的,我们在这场抢劫的背后,更要看清楚的是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战中,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肉体和精神的夹缝中无所适从的失重心理状态,以及灵魂没有栖居的痛苦。
同样,在阿宁的《灾星》(《时代文学》2005年第2期)中,当农民工福亮因为在“非典”时期染上了肺炎后,既怕被政府抓走,又怕自己的病感染给家人,于是就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典型环境,给出了一个肉体和灵魂都无家可归的农民工的悲惨生活结局。老实无言的福亮满以为凭着自己一身的力气就可以混迹于城市,为自己构筑一个美丽的乡土田园之梦:“他看见在辽阔的坝上草原上,一座漂亮的住宅建了起来。六间大瓦房,东西一边两间厢房,一个大院子。院子是用土坯垒起来的,用麦秸和成的泥土抹得平平整整,院门高大、宽敞。草原的蓝天像透明似的,白云棉絮般铺展开,阳光下的红瓦屋顶发出漂亮的红光。”作为一个农民工的家园梦想,其实也并不难以实现,可是,上天不再给他机会了。整个故事的构成围绕着福亮的命运而展开,作家把这个人物劈成了两半,一半归属于城市,一半归属于乡村。就像他的两个女人一样:月饼象征着肉欲的城市;红菱象征着灵性的乡土。“如果红菱是他的爱,月饼就是他的欲望。”但是,欲望化的城市即使能够给福亮带来一些金钱,然而它对于农民工来说永远是有一道天然的心理屏障的,只有乡土才是他们惟一可以依靠的家园:“乡间的一切在他眼里是亲切的。土道上散落的马粪,草滩里突然窜出的野兔,都会勾起他的乡情。”“内地的空气里流淌着麦子生长的气息,这里是刚刚翻开的土壤的清香。田头的一两棵歪脖子树,才刚刚抽出绿色的嫩叶,在他看来却是更有春意了。”死也要死在家乡,叶落归根可能是农民工这一群体遵循农耕文明生死观的行为准则,可能也是人类共通的人性中归家情结的显现。福亮费了千辛万苦走近了家乡:“路边的树下有块石头,他顺着石头坐下靠在树上。毕竟是家乡的树,靠着就像靠在亲人怀里,不一会就似睡非睡了。”对于生他养他的乡土出生地而言,再贫穷再衰败,也是有亲和力的;而对于那个谋生的城市而言,再富足再豪华,也是陌生的。家乡是农民工的灵魂栖居地,如果失去了,那就是孤魂野鬼,这才是农民工们的真正悲剧。无疑,家和乡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个名词却带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因为农民的家是建立在乡土之上的,如今,农民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向着城市进军!也许这一两代农民魂归故里的文化遗传基因是难以消除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还有乡土情结呢?
就像美国的许多乡土文学是建立在移民文学之上一样,中国目前的乡土文学在很大一块被这些向城市进军的“乡土移民”的现实生存状况所占据,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和研究反映这一庞大“候鸟群”生活的文学存在。然而,从众多的反映这一群体生活的作品来看,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还缺乏那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那种欧洲18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更重要的还是需要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战中,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才不至于陷入文化悖论的两难选择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因此,强化作品思辨理性的钙质才是这类作品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要在提高作家人文意识的基础上加强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宏观理性认识。是的,仅仅批判是不够的,我们的乡土小说作家还缺乏那种对三种文明形态的辩证认知,所以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还罕见那种超越感性层面、具有人类社会进步意识的深刻之作。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