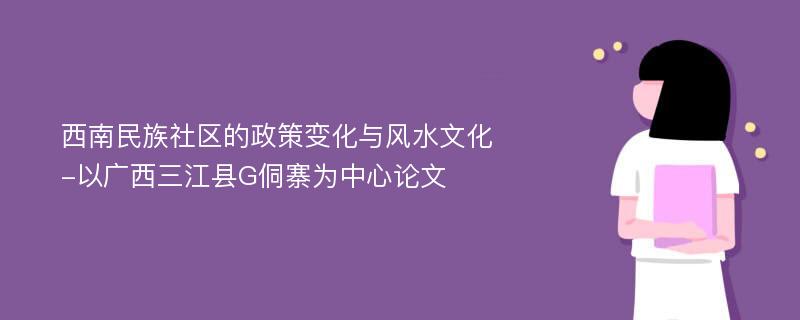
西南民族社区的政策变化与风水文化
——以广西三江县G侗寨为中心
黄洁
(日本京都大学 亚非地域研究科,日本京都府 京都市606-8501)
【摘 要】 近年来,由于移民和旅游政策为西南少数民族社区的村寨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关的人类学研究以人的移动为中心,探讨了移民迁徙、移民适应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课题,而往往忽略了同样作为被移动、被改造对象的自然空间、人文空间或设施等景观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为此,文章试图以位于广西北部的一个侗族社区为例,探讨当下的移民与旅游政策如何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性知识,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现象。考察发现,当地居民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自己身边展开的地方历史并不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社会运动所建构的,而是更为主观的、个体的关于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看法。对侗族而言,即是被表述为政策变化背景下的关于村落空间变革的“风水想象”。为此,通过考察围绕村寨空间展开的风水传说与实践,理解当下的政策性变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社区内部生活空间和知识结构的改变。
【关键词】 村落空间;风水实践;政策变化;社会变迁;侗族社区
本文是关于中国近现代村落空间的政策性移迁或变化的人类学研究。现代以后,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政府主导的农村、农业相关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在西南少数民族社区逐渐展开和日渐深化,民族村寨的迁移和居民的移居,以及自然和社会空间的移动、整顿等环境的变动频繁发生。以此为背景,通过实地考察,研究政策性变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并试图理解政策变动影响下的居民自身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再建构。具体而言,通过了解居民围绕村落空间变迁相关的一系列风水传说和实践,进一步考察和理解近现代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政策对当地居民产生的微妙影响。作为案例的是位于广西与湖南交接的坪坦河流域的侗族村寨,近年刚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群。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长期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决抛弃 “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的传统思维,把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保障移民长远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在工作目标上,必须更加重视移民收入翻番、农业现代化和移民新农村建设,重视移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三是在工作重点上,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在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移民增收、加强社会建设、建设移民美丽家园等方面工作取得新突破。四是在工作路径上,必须明确移民工作方向,找到破解移民工作难题的有效路径,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切实让广大移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一、“政策变化”与少数民族社会变迁
现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农业相关经济和文化政策,使少数民族村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比如,“大跃进”政策下,为了粮食增产而开垦山地、修建水利设施;为了支持钢铁生产,从农村地区砍伐大量的树木供应给城市。21世纪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展开,为了重点解决贫困问题而实行了农田水利、防火防灾等行政主导多项经济和文化政策。现在,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等政策背景下,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道路、水利设施实行移动和调整的情况非常频繁,由此带来的村落和居民的迁移和村落空间的规划调整等环境的变动也频繁发生。
人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研究,以人为中心,着重研究由政策变化带来的生态移民[1]、生态移民政策[2],移民的处境[3]、移民的适应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4],以及变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等。相比之下,其他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社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尤其带来的变迁则较少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以村落为单位的自然空间和设施的移动与改造,即移民的适应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变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最为频繁,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为深广。特别是作为当地居民所生存生活的公共空间,在移民、旅游开发政策作用下往往受到改造和整治,这些生活空间的变化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对居民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应对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方法论上,目前对围绕中国农村展开的政策变化乃至近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外部观点和宏观视野来讨论政策对各地区、各民族所产生的影响,倾向于农村经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化,讨论村落结构上与国家权力机关的互动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有的也注意到地方行政机关、地方经营等在村民社会治理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扶贫、移民、水利、土地、产业政策上的扶持”,诸如养鱼、暖棚、栽树、建房、改水、整土、修路、治河、移动、电视普及等工程,主要都是为了实现“改善百姓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功能目标[5]。尽管不少研究者也曾指出其不适用性,如黄树民“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少完全适合在其之下运作的人”[6],对“在其之下运作的人”的研究却很少。其实,考虑一系列政策改革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从内部的观点和微观的视野看,作为政策实施和操作的对象,当地居民对这些工程持怎样的态度,对这些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他们是如何考虑的[7]。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考察和理解移民和旅游开发等政策对村落生活环境的改造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针对这些事件的见解、评价和应对方法。
具体而言,本文以居住在中国西南的侗族村寨为例。侗族的居住空间特征较为明显,拥有鼓楼和风雨桥等传统公共建筑,历史上以河流经过的山间盆地为基础形成村落社会为主要特征。现在随着行政主导的经济文化政策的影响,侗族的村落空间和环境也产生激烈的变动,农村生活也产生了老龄化、文化传承断裂等多种问题。不过,另一方面,侗族的村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出现民间信仰和公益活动逐渐得到复兴和发展的现象。因此,对于考察政策变化在少数民族社区的生活空间产生的影响,以及民族地方的应对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二、风水信仰、变化与知识的传承
风水是起源于中国古代,影响了现代东亚及东南亚等其他周边地区(形成了所谓“风水文化圈”)独特的环境判断、环境影响评价、看地相宅的方法的总称[8],是关于环境的传统知识。关于风水的既有研究,倾向于以风水理论书所说明的风水原理为依据来理解风水思想,如三浦[9]、窪[10]、陳[11]、水口[12]等人的研究。 然而,除了这类关于单纯从风水原理所演绎的思想的解释以外,现住地民众之间还拥有自身的风水观念,即所谓的“主观的风水”[13]。具体而言,一般民众所拥有的风水知识和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性知识,不依赖于文字,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单从中国各地、各少数民族的情况来看,现代风水信仰的实际形态拥有多样性和多义性。因此,近年来对风水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视角和方法。一种是对风水的自然环境的判断和人文环境(都市、村落、家屋、墓地等)的改造等景观地理学的研究[14],或对现地民众的文化或社会文脉中风水的重要性加以考察[15];另一种则是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现地一般民众的风水知识,利用特定群体的关于风水的语言和行为的数据,来理解地方性的风水观念。本文对侗族村落风水的考察以后者为主。
以中国为代表的风水文化圈中,人(或村落)、自然和设施的移动一般都与风水有关。人们在讨论移动和风水的关系时,往往有“风水目的型”和“风水解释型”两种。前者指人为的移动是出于改善风水的目的。如琉球王朝时期《球阳》中的记载表明,琉球王国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王府主导了多次村落移动,他们向农民解释的原因是风水有关[16]。后者则是与风水无关的移动,事后当事人将其与风水相关联加以解释。所以,“风水”可以作为当下移民和旅游政策的移动研究的切入口。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包括“风水”在内的民间信仰一直被当作“迷信”长期处于被批判、受打击的弱势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关于风水知识的当下传承特点的研究,作为窥见中国社会现代以来的民间信仰变迁的窗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是出于此目的的一个尝试。
游客进入村落以后,“风水意义上会招致灾难的风雨桥”和“被视为民族特有景观的风雨桥”之间产生意义上的对立关系。
调查地G村村民将风水师称为“地理先生”“先生”或“千门土地”。地理先生通晓风水知识,能进行住宅、墓地、村落地形地理判断,选择吉日吉地,操办丧葬、禳灾等相关事宜。他们自称受到佛道两教的影响,使用的书本(如汉语的《三本侗书》《望月楼》)、道具、法事都与佛道两教相似。过去,长老作为侗族村落传统权威往往需要具备地理先生的能力,并主持村落仪式,“四清”和“文革”时期,成为“封建头”“迷信头”和被批判的对象。1954年后,村中长老制被废除,成立了村民委员会,主要管理村中行政,20世纪80年代的老年协会则延续了长老制的一部分功能,主要管理风水山林、婚丧嫁娶等民间事务。现在村中共有地理先生5名,全为男性。
1962年1月13日,G村遭受火灾,200间木结构住宅有160间被烧毁,鼓楼和庙宇也被烧毁,经历两年才完成村寨重建。
把生命交给党,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听从党的安排,这是方志敏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胡锦涛指出:“我们纪念和学习方志敏同志,就要像他那样,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2]方志敏36岁慷慨就义,其生命虽然短暂,但革命经历非常丰富,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他在革命斗争中曾担任过多种不同的工作。无论什么工作,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像胡锦涛所指出的“始终不渝、毫不动摇”。这里,我们可以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得到印证。
三、广西三江县的侗族村落的政策变化
就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而言,1950年以后围绕村落空间的移动很多。具体而言,特别是1958—1970年进行的“大跃进”“农业学大寨”、1964—1966年的“四清运动”和之后的“文革”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使县内各村落的自然空间、公共空间和设施受到破坏或改造,带来了诸多的社会变动。
从G村来看,根据村民的记忆,他们村落的传统结构,由河流和东南北三面的山为边界,建有2米高的城墙环绕构成的、靠山背水的生活空间。同时,各山道设置有四个寨门,夜晚关闭,以防备老虎、盗贼和官兵。这样的传统空间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中,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除了以上三方面研究,还有学者提出苏雪林作品有取材希腊神话的迹象,并受到伤感主义和西洋水彩画技法的影响。如朱双一的《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棘心〉〈天马集〉论》、祝宇红的《“老新党的后裔”——论苏雪林的〈天马集〉与曾虚白的〈魔窟〉对神话的重写》等。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笔者于2016年8月2日至10月31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进行了文献调查,并再次访问硕士阶段调查过的三江县G村,进行了田野调查。主要收集与村落风水相关的传说和言论,访谈当地地理先生(风水师),并获得了村落风水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根据入手的手写民间仪礼书的分析,2017年1月21日至2月17日再次调查风水传说的产生和传播,以及实践的动机,对侗族村落内部多样的观念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考察。为了对比民族内部和地域间的差异,3月22日至24日又短期考察了湖南省和贵州省交界处邻近的侗族村落。
2008年,三江县的民族村寨改造项目开始实行,为了防火在山上建储水池,木结构房屋的一二层改造为水泥结构,安装电话,设置饮用水,为了建设“整洁村容”,改善卫生环境,掀起了一场对厨房、厕所等设施进行改造的革命,也为村中生活样式带来了改变。
1964年,开辟了村东南面的“红星坡”,试图开垦百亩大田。采伐杉木卖给柳州市国营木材加工厂,并大量种植用于观赏的竹木。宗族祠堂和墓地所在山地被挖掘或只能变更场地。开垦后土地用于水稻和棉花种植。
1974年,根据林溪乡的政策,为了安全防火,在管辖区内各侗族村落设置防火线,主要是将房屋之间进行分离和搬迁。为此G村中一部分居民被移至周边山上居住。
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紧接着的“文革”期间,拆毁了村中飞山神、雷神和南通神等三座庙宇,鼓楼丧失宗族联系的功能,被改造为村的行政机关和生产队的仓库和开会场所。
对鸭坯进行统一前处理,之后进行烤制实验。具体为红外蒸汽烤制温度220℃,烤制时间30、35、40、45、50min,蒸汽喷射2次,分别为烤制的第10min和第30min,每次喷射时间为3s;最后红外干烤10min。
2.3 患者术后1年死亡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以随访1年后是否死亡作为因变量(否=0,是=1),以在前述单因素分析中呈现显著的指标/因素作为自变量(共10个),其中连续变量进行适当的分类变量转换(例如血清 Cr,1=异常,即≥133 mmol/L,0=正常),建立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采用逐步回归拟合,自变量进入和剔除水准分别是0.05和0.1。结果显示术前心功能4级、“罪犯”血管为左主干、术中发生无复流和术后TIMI血流<3级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伴严重心力衰竭患者术后1年死亡的危险因素。见表3。
G村2012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省其他7个侗族村落一起被列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从2013年起,广西区环境保护厅开始实行对村落的“生态村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景观整治、传统家户保护、道路和桥梁等公共空间的修葺和维护等。
近年来,出于防火、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目的,政府政策等外来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侗族居住的传统的干栏式建筑群所连接而成的空间。那么,当地居民对于村落空间的变动如何考虑和对应?下一节再加以考察。
5.按通配符(wildcard)查询。这是一种基于词的底层模糊查询,可结合正则查询使用,使用户快速定位自己感兴趣的语言信息。
四、以被移动公共空间为中心的村落风水传说
围绕被移动的村落公共空间、G村村民有多种说法。这些言说大致有一个相似的基调,即认为公共空间的移动发生以及发生的现象(特别是灾难),往往与风水相关联。总的而言,以政策性变化为背景的风水传说和相关表述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作为火灾原因的桥
以上言论主要认为,村落火灾和贫穷、灾难的原因与桥的建造位置不恰当有关。而解决方法是拆桥。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其实这座桥的拆去是“四清运动”时,在上级政府的命令下强制实行的,并非如村民所说,出于改善风水的目的而自发拆去。
建同样的桥给村落带来坏影响,代表了村民的普遍看法。不过,1961年大火灾的直接原因,是村民的过失引起的,很难说与桥有直接关系。然而,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桥的位置不仅与火灾有关,而且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我们土地很重视风水,从村落西北方位来看,我们这个地形像一只水獭,水獭喜欢吃鱼。村落四周的山环绕起来,到山脚下那座桥建造以后,就把水獭关起来了,它就来破坏我们村寨内部了。那以后,村民中小偷、强盗、赌徒都增加了,狡猾的就到外面偷,胆小的就在家里面偷,有的卖田卖地,都变贫穷了。到1961年大火,村落8成以上的房屋都烧了。村民就说要拆桥。后来2年后,村委会才带我们去拆桥,把木头分给各个生产队”。
2016年夏在G村进行调查,围绕上述风水传说相关联的景观,笔者发现村民中存在与地理先生的立场截然不同的言说。其差异主要在于,针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对象的移动或再造的时候,村民是经由地理先生的风水判断来考虑(即优先考虑风水的意义),或者考虑旅游开发的效果(即风水的意义让步于经济发展等其他方面的有利性)。下面通过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
宁夏贫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辅食及时添加率为55.9%,首次添加辅食最多的为谷类泥糊状食物占66.6%,远低于张玲等[7]研究的贵州地区(分别为91.1%、74.5%)。本次婴幼儿看护人儿童营养知识总知晓率仅为36.5%。可见婴幼儿看护人在喂养过程中存在辅食添加过早和过晚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因此,加大健康教育覆盖力度,是婴幼儿营养改善干预措施的重要环节,对于改善下一代营养健康状况具有长远意义[8]。
“四清运动”和“文革”期间被拆去的风雨桥与破坏风水的说法相关联。具体而言,调查地G村和附近的村落,经常发生火灾,有时村落的一部分甚至整体被烧掉的情况也有。村民则将这些火灾的原因归结于桥的位置被移动,导致破坏了村落的风水,给村民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引起了火灾。比如,G村的丁哨桥,1963年被撤去移到另外的位置。根据不少村民的记忆,是因为当时所主导的政治运动强制性撤去的。关于这座桥与村落风水的关系,村民有很多说法,如YYX氏(男、1942年生、G村)认为:“我们村落从地形看,刚好像一个瓮或袋,有一个开口。而那座桥就在那个开口处。因此,那座桥架在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盖子,把我们村落(像一只乌龟一样)关在这个袋子里了。所以那座桥修建以后,我们村落和村民多灾多难。好几次火灾,1961年那次最大。”
(二)为宗族带来厄运的鼓楼
提倡集体经济时,宗族鼓楼的破坏和改造,在风水的原因上为村落或宗族带来厄运的言说。比如G村中5层的杨姓家族的鼓楼被改造后,成员中出现小偷、强盗,家业荒废等。为此,他们集体集资重新修复破旧的鼓楼,至于为什么要重修鼓楼,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过去鼓楼遭受破坏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如YGZ(男,1945年生,G村)的讲述:“鼓楼象征了我们宗族的力量。我们从来到这里定居以后,从刚开始的3户发展到现在60多户500多人的大姓氏,并建造了一个5层的鼓楼。但那只是一时的繁荣。1960年末,集体农业在全村实施,我们的鼓楼成为居住区的会议所,鼓楼正中的大柱被切断,5层的鼓楼变成1层了。从此以后,我们的人口不怎么发展,外出找到好工作的人也没有,而且我们的宗族成员当中还出现了强盗、背叛者,风气败坏。”他们通过成员捐款,将旧鼓楼拆了,改建成7层的,理由主要是希望改善风水,宗族才能出更多人才。现在村中的大学生总共有6人,他们宗族成员占了一半。
(三)家运的没落与龙脉的关系
G村村民重视龙脉或风水,在埋葬亡者时请地理先生选择风水好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坟地与祖先的灵力和家运的亨通密不可分,为了家人健康,家运旺盛,必须保障坟地完好无损。然而,农业学大寨时,G村的生产大队大量使用山地,开垦周边的公共空间作为耕地使用,挖掘了“红星坡”。因此,开山挖坟之后,对家运发生不好影响传说。特别是挖了龙脉以后,导致家人病死、家运衰落等。
如YYJ(女,1973年生,G村)的讲述:“YSH(女,1976年生,G村)的丈夫之前是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拥有大量的土地。她不用外出打工生活都很富裕。但2015年末,她丈夫突然检查出右脚有肿瘤,做了手术以后6个月,左脚又发现有恶性肿瘤,就去世了。她现在一个人照顾两个女儿,而她丈夫的妈妈又有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地理先生说红星坡是个聚宝盆,他们挖了自己家的财库才导致厄运的。”根据YYJ的说法,地主家庭的YSH丈夫一家,挖了自家龙脉,因此才会家人生病、家运衰落。
(四)没有好报的破坏者
村中,砍伐树木(风水树)、破坏神庙等公共空间的个人受到神灵惩罚的相关传说很多。三江县及其周边的村落这类传承经常能听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对应国家政策的木材交易的采伐,古树被砍倒以后,砍树的人不是患病就是变成痴呆,甚至为全村带来灾难的讲述很常见。如LLH(女,1934年生,三江县富禄乡葛亮村农民)所述:“‘四清运动’时,村委会的干部将鼓楼正中的四个大柱撤走,破坏了鼓楼,‘文革’时,庙里的神像都被拿去河里丢掉,鼓楼的木头全部被烧掉。几年后,这些破坏者,两个得病很快就去世了,一个当时指挥的女性,丢了神像以后,得了奇怪的病,现在整日只能躺着。”
同时,村民担心受到神灵的惩罚,直到现在也仍不敢轻易使用鼓楼遗迹的空地,更不敢私自在附近建造房屋。另一则类似的传说,是在湖南省通道县调查时,SYB(男,1951年生,通道县陇城乡路塘村)的讲述:“根据地方规约,从来古树都是不能随便砍的。但还是有人去砍。1980—1990年,我们村有两个人这样做了。其中一个是干部。他砍了古树以后,很快就死了。还有一个人也去砍了古树,之后,他回到家中一直卧床不起,变成植物人。他的小孩也受到影响,得了原因不明的病,现在一直都痴痴呆呆的。”
总的而言,类似的传说在村落中流传很广,其实这些事情未必真的与风水有关,而是他们联系过去,将这些事情主观地与风水关联在一起,附加了风水的想象加以解释。这些可以称为新创造的风水传说。这些传说的发生和传播,作为村民的主张和想法,显然与他们地方性的风水信仰和地理知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他们关于风水的常识,也是这些言说得以在村落中共有、传播和传承的原因所在。同时,这些传承也应该理解为,只是他们对地方历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及其与此相关的历史记忆再建构的一种呈现方式。
五、现代村落风水的交涉与实践
(一)以游客为目的的移动和景观整备
由上述风水传说可见,风雨桥、鼓楼和古树等景观在侗族村落空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因为村民认为这些自然和公共设施与风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十年来,随着来访G村的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从政府获得资助,民族旅游开发也渐次展开。同时,村民也意识到,可以利用“风水”来吸引游客。为此,现在村民学习地理知识或风水知识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通常只有村落内部人员才能参加风水相关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外部的游客也能参加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关于村落空间的风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地理先生所拥有的专家知识,转变为村落中民众所共有,乃至于村落外部的游客所共有的知识。
W={w1,,wn,,wN}为N个评价指标权重,可结合应急目标、各指标的相对重要度和指标间的关联关系确定,
1.“风水招致灾难”VS.“民族特有的景观”
侗族主要居住在中国的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地带。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总共约288万人。在侗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要素中,鼓楼和风雨桥等公共建筑备受注目[17]。三江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对侗族而言,风水被当作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知识。虽然风水传入侗族地区的具体时间尚未明确,但根据史书记载,明代时,统治者就已经根据风水知识来决定县城的位置,县域中心的转移也与风水有关[18]。村落层面上,也留下许多记录村落风水的石碑碑文[19],村落的由来传说也多与风水相关。
风雨桥和鼓楼被当作侗民族文化的特征。最近,地方居民为了游客,开始对这些民族特有的景观加以移动、修理和整治。首先,因防火线的建设而搬到河流对岸的吴姓和杨姓两个宗族共同在2006年建设了一座新的鼓楼。在建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使用传统鼓楼的四角结构、八角结构,以达到“四平八稳”的风水原理。而是为了美观,学习汉族建造六角亭的观赏建筑方式,建造了六角形的阁楼。而且,他们声称是“侗族地区非常少见的美丽的六角楼”。
同时,对前面所述为村落带来极坏影响的丁梢桥,村民将其与闻名国内外的三江“程阳风雨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相比较,称丁梢桥比其更大更美,对其被拆毁表示可惜。如:“以前我们河下游那座桥如果没有拆,比程阳风雨桥还壮观。火灾发生后,有人说要拆桥,好大的桥木头分了好多到各家修建房屋和鼓楼。”对这座少数老人儿时见过的风雨桥,发出“很好的景观,被拆掉了很可惜”的感慨的言语时常听到。特别是20~45岁的村民,他们其实很多人没有亲身见过那座桥,他们对侗族村落旅游符号“程阳风雨桥”的引用,只是为了强化旅游的效应而已。同样,村民将自己村落西北方的一处山脉,与另一个国际旅游符号“桂林象鼻山”作比较,声称比“桂林象鼻山”更像象鼻,并希望笔者替他们为那座山写文章做宣传。
由于紧邻桩身的桩土界面处的土压力及孔隙水压力直接作用于桩身,比远离桩身处更重要,而目前的研究和应用中鲜有直接测试PHC管桩沉桩过程和静载过程桩土界面的土压力和孔隙水压力的报道.唐世栋等[30-31]、王育兴等[32]通过在钢管桩外壁安装土压力盒和孔隙水压力计,测试了钢管桩沉桩过程不同深度处桩侧土压力和超孔隙水压力变化,都没有针对静压PHC管桩.李杰[33]通过现场测试桩身应变值,将应变值转化为桩侧压力和摩擦力,但没有测出孔压,无法求出桩侧有效应力.因此,PHC管桩在现场贯入过程和静载过程桩土界面土压力及孔隙水压力的测试手段有待解决.
还有一个事例是G村附近的高团侗寨。2016年10月国庆节,为了吸引游客,高团村为一座新桥(2015年建成)举行了踩桥仪式。对侗族而言,新桥建成之后,必须请来风水先生,选择吉时举行踩桥仪式,以保证新桥通行的平安。村民认为,这样的踩新桥仪式是为了守护村落的安宁,有时候甚至需要“人柱”(特别是村外人员),非常危险。因此,当天笔者前往高团村考察时,村民对笔者加以制止,并警告不要靠近新桥。使笔者惊讶的是,该新桥其实修建于2015年,备受重视的新桥踩桥仪式早在建成之后很快就实行了。那时,包括游客在内的村外人员一律不能参加,实际上参加者只有本村村民。但是这一回,通道县政府为了吸引国内外游客,为县内每个民族村提供5万元,让每个村落自行组织一个本民族特色的活动。为此,高团村的老年人协会会长WXY(男,1948年生,高团村的风水师)选择了“踩桥”仪式作为吸引游客的活动。当时,前来参加仪式的人员,除了周边的侗族人,更多的是来自北京、贵州、河北、浙江、广东和美国等地的游客,总人数达300人以上。
目前,外泌体的提取方法主要有差速离心法、超速离心法、过滤离心法、密度梯度离心法、免疫磁珠法和色谱法,而鉴定方法则主要包括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颗粒跟踪分析技术、蛋白质印迹法和流式细胞术。外泌体的常规储存条件为-80℃,重复的冷冻和融化会影响囊泡的完整性[14]。外泌体分离鉴定后,可结合芯片和二代测序结果筛选与疾病相关的差异表达因子,并最终分析其可能参与的生物学功能及信号通路。近年来,调控外泌体释放和发挥生物学效应的信号通路仍不明确,考虑其与病毒在大小、密度、组成及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故可借鉴病毒的相关成果来开展外泌体的系列性创新研究[15]。
欧盟承诺2014—2020年,将至少投入政府预算的20%于气候行动,因此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补贴强度较高,有数个较大的明确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资助方案。比如,作为世界最大的低碳创新能源示范项目资助计划之一,NER 300以支持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为两大目的,其中与可再生能源研发相关的资金超过20亿欧元。而中国在减排初期更关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起步较晚,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且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因此研发补贴强度远低于欧盟。
2.“信仰物”VS.“受欢迎的东西”
随着游客进入村落,围绕自然环境的开发和改造,村民观念中的“信仰物”和“受游客欢迎的东西”之间发生了摇摆和矛盾。对于侗族人而言,风景树和山地具有风水信仰的意义。然而最近,当地居民开始考虑游客对景观的喜好,在周边山地的古树红豆杉、用于建造房屋和制作家具的杉树以外,又种植了桂花树、凤尾竹等观赏性植物。今年,村民更将一棵古树命名为“许愿树”。老年人协会的YCS解释是,他们到湖南的旅游景点考察,发现许愿树相当受年轻人欢迎。
如表1及图5所示,总体来说,教堂广场的视域整合度为7.009 170,相比中山路街区的平均整合度4.108 800要大得多.说明该区域视域整合度相对较高,空间的集散功能相对较强.但教堂广场的视域全局整合度核心位于广场西北角、曲阜路与浙江路交叉口以及肥城路与中山路交叉口3处,最高达到12.118 000,是视线聚集性较高的区域,相比之下,广场中心空间整合度反而相对较低,基本维持在平均值7.009 170附近,视线的聚集性较低.说明在外围建筑的遮挡下,教堂广场空间整体区域整合度分布不合理,部分区域整合度分布产生断层,限制了整体区域的视线聚集性.
同时,为了吸引游客,他们推出了“韭菜节”“红薯节”等新节日。在与游客接触中,他们发现,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游客,喜爱吃少数民族农村种植的蔬菜和鱼肉,因为他们的蔬菜和鱼肉是在自然中培育、没有使用农药等,这是他们在城市中吃不到的。为此,他们自2012年开始,每年一度或两年一度在“五一”“十一”或“八月十五”的黄金假期举办“韭菜文化节”“红薯文化节”。并为此开始在周边山地、田地大量种植韭菜、红薯、油菜花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将田地挖掘成水池养鱼的村民也有不少。
2016年上半年,村民为了举办“红薯文化节”,向政府申请资助修建了附近的停车场、维修公路,据他们的描述,其目的是为了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广泛传播侗族特色的文化。
(二)风水师与村民委员会
在旅游的背景下,风水师和村民委员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政策背景下的村落空间移动和改造实行时,村民为了守护村落的风水,采取了自发的对应措施。具体而言,通过制定民间传统习惯法,对自然环境相关的禁忌在全村实行。如砍伐风水树,要处以罚金,作为受到重视的山脉,严禁埋葬死者。同时,考虑到风水信仰和过去曾遭受批判的历史,在与政府进行交涉的时候,风水相关的实践往往是私底下进行。以G村为例,具体如下:第一,1974年为了防火防灾,应政府要求村中设置防火线,并在山顶设置两个储水池,但是村民具有饮用井水的习惯,出于风水说的考虑,他们认为有建设龙井的必要,特别是在火灾发生以后,他们通常都会修建龙井,祈求神灵守护,防止火灾再次发生。因此,他们私下修建了龙井。第二,2016年下半年,为了扶贫和旅游开发,乡政府向G村资助了数万元用以修建停车场,停车场的设计工程是依据乡政府的计划进行。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例如从停车场通向村落的道路,他们认为进入村落道路的方位会影响村落整体的繁荣和人们的发展,所以修建的时候,还是先通过风水师确定了方位。向政府作了说明之后,他们则以“为了村民行动方便”作为客观理由。
这类风水实践,一般都是通过地方干部的行政权力实现的。侗族村落内部的治理,主要包括由地方干部构成的村民委员会,利用现代制度和法律管理村中内部事务。此外,还有民主选举产生的老年人协会的民间组织。老年人协会继承了传统体制的一部分职能,依据风水山林、婚丧嫁娶的管理规约,管理民间事务。因此,风水是老年人协会的重要功能,而政策是村委会的工作。近年来,村民委员会和老年人协会,不仅在构成人员上有许多交叉,在关系村落空间的移动和改造等方面的政策上也形成了许多相互协助的关系。
六、结语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考察了移动和旅游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以及当地居民对这些政策的见解和应对。以“风水传说和实践”为切入口,发现近60年来发生在侗族社区的社会变动主要是村落内部的自然和社会空间的移动和改造。针对由此引起的诸多的社会变动和历史事件,村民们运用自身的风水知识加以解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风水传说,并有巧妙的应对策略。特别是在一系列的政策性改造和社会变动的背景下,原本自主自治的村落社会由于行政的逐渐渗透,从相对封闭的、排他的共同体逐渐被席卷入外部社会和关系中,伴随着这种社会状况的变化,地方性风水知识也从在民族村落内部传承和维系,逐渐转为面向村落外部、村民以外的人群共享。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意识也发生了转变。可以说,所有这些政策变化背后的思考,并不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改革运动所推动的,而是主导性很强的国家和外部社会的观点。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居民个体而言,则是国家行政的介入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之间频繁的互动产生的主观性回应。因此,社会变动带来了村民风水知识的多样性动态的发展。通过新造传说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地居民对社会政策带来的生活变迁的看法。
本文的考察发现,即使是当下在侗族的村落社会中传承的风水知识也仍然具有传统性,是他们自过去传承至今的地方性知识。正如渡边指出,传统性在于“民俗知识的整合,象征性的知识不断被正当化,与其他知识不相矛盾、互补的关系得以持续,即使承认了知识的抗衡性,公共知识也能不断取得胜利、得到支持,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可能”[19],因为“知识的传统性是当事人用以作为确认文化上的自我的相当好用的东西”[20]。风水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受到强烈的抵制,风水信仰作为“迷信”,一直处于不被公认的位置,风水师也曾作为“迷信头”被批判,其活动也受到抵制。然而,从G村的事例看来,围绕政策所移动和改造的村落内部的空间,村民自身利用集团内部自过去共享至今的风水知识,来解释由于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后果。例如,风水与对村落空间的破坏者所受到神灵惩罚的讲述,又如,即使是现在,关系到地方风水事件,也仍然以村落中的传统组织、习惯法为中心加以处理。究其原因,侗族村落社会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通过民间组织和民间规约实现民族自治,这种治理方式在当下社会中仍然有部分功能得以延续。
G村村民关于风水的传说和实践相关的风水信仰,是他们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实际上与政策的施行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强制性的政策发生以后,村民们利用他们所拥有的风水知识,对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加以解释,这些主观风水的解释,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对过去实际发生事件的“合理性”想象,属于主观的风水观念。当下居民共享和传承的风水知识,与过去的风水知识相比,原理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好的位置架桥、破坏宗族的鼓楼、开垦山地、挖掘龙脉、砍伐古树、破坏神庙等公共空间,会带来糟糕的影响,甚至带来灾难,而造成灾难的原因确实与风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他们自古以来传统的知识。他们之所以将实际上与政策的施行全然没有关系的村落风水与政策带来的后果联系起来,在面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和现代化进程中,更倾向于结合风水知识来解释和应对,这些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他们而言,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有效、有用的。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变迁时,有必要充分重视考察和研究他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空间的传统,特别是过去的地方性知识在当下的应用和延续。
正如日本自然景观改革进程的新近研究中发现的那样,长期以来关于环境未来型城市、污染处理等项目的解决方案的实践,促使政府的行政越来越倾向于与地方个体、机构的合作[21]。在中国农村,随着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逐渐深化,地方社区内在的文化和权力的结构,特别是村落层面的地方权威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村落权威机关的角色扮演和管理技能,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方式,都转变为指向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下当地民众的公共诉求[22]。可以说,近年来的政策移动在少数民族社区带来的最大影响,也集中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上。2000年以后,随着旅游化在村落中的逐渐发展,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接触逐渐增多,他们对经济的诉求也与日俱增。同时,地方政府以民族特色文化宣传为目的,对侗族村落中空间移动和景观整治的事例也很多,居民也由此获得地方政府资助。这些变化,促使当地居民在考虑村落空间的调整时,对村落风水的考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存在于是“倾向于优先考虑风水”,还是“优先考虑经济”的选择上。此外,村落中风水师和村干部之间关系的缓和,这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风水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中变化最大的地方。地方干部和风水师的相互作用和协调,也许存在许多利益上的矛盾,但在旅游开发和守护村落风水二者的协调上,都需要村民、地方干部和风水师来共同协调,这也是本来可能相互冲突的行政和居民之间的关系能够实现调和的原因所在。特别是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村落公共空间的移动和改造中,游客和居民、风水师和村干部、村落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这也对置身于现代文化之中的风水师、村落内部的知识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而言之,他们不仅需要像过去那样能够处理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需要能够解决当下村民与游客等外部者、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包智明.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7-31.
[2]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程瑜.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4]刘有安,张俊明.民族学视野下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以宁夏南部汉族移民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5):152-156.
[5]唐龙文.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82-84.
[6]HUANG S M.The spiral road: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M].Boulder,San Francisco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9.
[7]LIN J, XIX Y.A century of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The crisis of the countryside[M].Boston: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 Inc,2018.
[8]渡邊欣雄.風水の社会人類学——中国とその周辺比較[M].东京:風響社,2001:37.
[9]三浦国雄.中国人のトポス 洞窟·風水·壷中天[M].东京:平凡社選書,1988.
[10]窪徳忠.沖縄の風水[M].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
[11]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2]水口拓寿.中国風水思想史研究の回顧と展望[J].中国哲学研究,2015(28):161-190.
[13]兼重努.集落地形の風水判断:西南中国トン族の村落風水の事例から[J].滋賀医科大学基礎学研究,2007(13):19-44.
[14]渡邊欣雄.風水:気の景観地理学[M].京都:人文书院,1994:19.
[15]瀬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の家族·風水·移住[M].东京:風響社,1996.
[16]小熊誠.沖縄の村落移動と風水—村落史の記憶と歴史的事実—[J].歴史と民俗,2011,27:155-184.
[17]兼重努.エスニック·シンボルの創成—西南中国の少数民族トン族の事例から—[J].東南アジア研究,1998(4):132-152.
[18]三江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三江侗族自治县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19]渡邊欣雄.風水思想と東アジア[M].京都:人文書院,1990:41.
[20]川田順造.無文字社会の歴史—西アフリカ·モシ族の事例を中心に[M].東京:岩波書店,1976:183-184.
[21]INOUC K.Eco-city development in Japan[M]//LIU T S, JANKU A,PIETZ D.Landscape chang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East Asia:perspectives from environmental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18.
[22]RICHARD M.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216-218.
Policy Changes and Fengshui Culture in Southwest Ethnic Communities:A Case Study of Dong Village in Sanjiang County of Guangxi
HUANG Jie
(Graduate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Area Studies,Kyoto University,Kyoto 606-8501, Jap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immigration and tourism policies have brought tremendous changes to the living space and daily life of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The relevan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human mobility,the issues such as migration,immigration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ere discussed,while the natural space,human space or facilities,which were also the objects of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nd the social changes caused by them were often ignored.Therefore,taking a Dong community in northern Guangxi as an example,how the current immigration and tourism policies affect residents’daily life and local knowledge and how they cope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olicy changes were explored in the paper.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local residents’views on the local history unfolded around them after 1950s were not constructed by one social movement after another,but with more subjective and individual views o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For the Dong people,it is expressed as the “Fengshui imagination” about the spatial change of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cy changes.Therefore,by investigating the legends and practices of Fengshui around village space,the changes of living space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in the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policy changes can be understood.
Key words: village space;practice of Fengshui;policy changes;social changes;Dong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04(2019)03-0106-12
DOI: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9.03.013
收稿日期: 2018-09-30
作者简介: 黄洁(1987— ),女,广东澄海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罗清恋,穆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