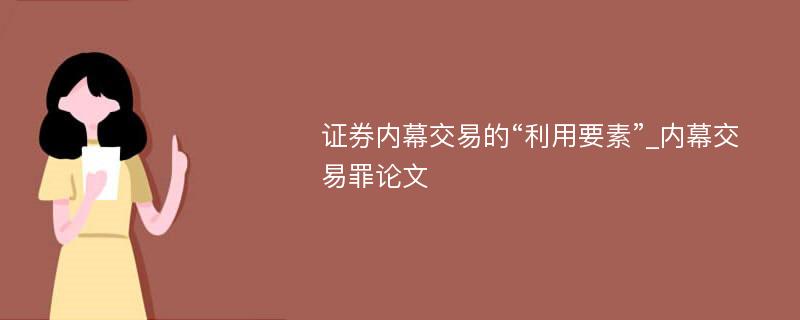
证券内幕交易的“利用要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件论文,内幕论文,证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明需以该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为基础,在法定构成要件科学设定的前提下,通过证据的采集以及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才能顺利实现对该行为法律形态的证明与认定。2008至2011四年间中国证监会共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154起,行政处罚31起、移送公安47起,打击内幕交易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内幕交易持“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①上述数据说明了内幕交易案件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高发态势,打击内幕交易任重道远。而且,由于内幕交易行为极具隐蔽性,其证明过程十分艰难,加上我国证券法和刑法对该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增加了证明的额外困难,两难叠加,使得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及证明问题在理论上混乱不清、在实践中困难重重。本文以内幕交易证明问题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行为人是否“利用内幕信息”为研究对象,提出并解析内幕交易的“利用要件”内涵,评析相关立法并提供修法建议。
一 我国相关法律规范的文义解读:冲突与问题
证券内幕交易已成为一种法律明确禁止的证券(广义的证券包括期货合约,②下同)交易行为,并已入刑,但不同法律对“知情人③是否利用内幕信息”之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一致。
第一,我国《证券法》第73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该条文含有“利用”字样,强调的是知情人进行交易时以内幕信息为投资决策依据这一行为的主观特征,故可称之为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利用标准”或主观标准,用公式表示就是:“知悉+利用=内幕交易”。
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层面,除了《证券法》第73条,其他涉及内幕交易的条文采用的均是“知悉+交易=内幕交易”的立法模式。例如,《证券法》第76条第1款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该规定直接列举了所禁止的行为,而无涉是否利用了所知悉的内幕消息;再如,该法第202条关于内幕交易行政责任的规定态度也如出一辙,其文句都没有明确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系法定构成要件,即将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设定为“知悉+交易”而非“知悉+利用”。我国《刑法》第180条关于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也是如此。④除《证券法》第73条外,内幕交易违法犯罪之构成可描述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只要从事了法律所规定的证券交易活动⑤即构成内幕交易,情节严重的,构成内幕交易罪。对此,在其它构成要件(如主体、内幕信息及其公开状态等)确定的情况下,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可用如下公式表示:“知悉+交易=内幕交易”,与前述“利用标准”之主观性相对应的是,该公式体现的是“知悉标准”,不考虑知情人的主观状态,亦称内幕交易构成及证明的客观标准。
第三,除基本法律层面外,内幕交易是否应具备“利用要件”的分歧还体现在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中:
1993年的两部相关行政法规中都明确规定了“利用要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2条规定:“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泄露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的建议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第4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内幕交易包括下列行为:(一)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三)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而2007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第13条(构成要件定义条款)则没有规定“利用要件”:“本指引所称的内幕交易行为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的证券交易活动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符合下列条件的证券交易活动,构成内幕交易:(一)行为的主体为内幕人;(二)存在买卖相关证券,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或者泄露相关信息的事实;(三)上述事实发生在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内。”该条规定用公式表达就是“知悉+(敏感期内)交易=内幕交易”,显然,采用的是知悉标准而非利用标准;但该《指引》又没有完全放弃“利用要件”,其第14条第(五)项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泄漏信息的人为内幕人,或者泄露的信息为内幕信息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该信息买卖相关证券”,文句外观显示的是因信息传递而知悉内幕信息的受密人之内幕交易的构成仍应具备“利用要件”,其内在原因反映的应当是规则制定者对“利用要件”的模糊认识。
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导向性作用的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11]225号)第5条也规定,“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显然,该《纪要》认可了“利用要件”,并明确了将法定情形下“未利用内幕信息”的证明责任转移至行政相对人(即知情人),但对“知情人”如何证明“未利用内幕信息”以及证券行政管理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采纳“知情人”“未利用内幕信息”的主张,并没有具体规定,但本文研究将表明,《纪要》的规范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上述多重文义解读表明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规定存在冲突,其中,“知悉内幕信息”是行为人能够从事内幕交易的前提、也是认定内幕交易过程中必须证明的事项,并无争议;但对于“利用内幕信息”是否也是内幕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存在冲突,学界亦无定论。⑥事实上,是否将“利用内幕信息”作为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之一,既反映了该构成要件之理论设定的科学性,也将改变相关违法犯罪定性时的证明规则,包括证明方法的运用、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的确定。那么,从其各自逻辑和实践应用来看,“知悉+利用”与“知悉+交易”之要件组合哪一个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呢?
二 “知悉+利用”还是“知悉+交易”:比较与选择
(一)“知悉+交易”——简单但有缺陷的要件组合
显然,从内幕交易的证明角度看,“知悉+交易”的要件运用是简单而且方便的。依照此要件,知悉内幕信息、并且进行了与该信息相关的公司股票的交易,即构成内幕交易,而不需要证明在该交易中“知情人利用了内幕信息”,如此一来,执法或司法机关的证明负担将大大减轻。从这个意义上看,“知悉+交易”要件组合既符合内幕交易的基本行为特点,又不需要艰难而繁琐的证明过程,似乎是简洁而完美的。然而,这只是一个表象,事实上,“知悉+交易”要件组合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
1.从理论上看,“知悉+交易”的法理基础十分脆弱
以“知悉+交易”认定内幕交易,意味着只要知悉并且交易即构成内幕交易,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而所谓“交易”,是公开市场的常态行为,例如甲和乙在公开市场买卖A公司的股票,甲一旦知悉涉及A公司的重大非公开信息,则依此可直接认定甲构成内幕交易。这表明,“知悉+交易”的法理基础等同于交易者“交易人知悉(内幕信息)即违法,情节严重者构成犯罪”,这显然有失正当性,因为交易者主观获悉某种特定信息,这本身并没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除非他以此为交易依据,在交易当事人内部,“如果一方交易者并不是利用了其知悉的内幕信息来交易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交易的对方并不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⑦回避“利用要件”的“知悉+交易”是脆弱的法律构架。
从比较法上来看,与“知悉+交易”采取同一法理基础的美国法内幕交易基本规则——“公开或戒绝交易(Disclose or Abstain Rule)”—现在也开始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解释修正。⑧该规则要求知悉公司内幕信息的人要么公开该内幕信息,要么不得从事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反言之,如知情人没有公开信息,反而买卖了涉及该信息的证券,即构成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及1942年SEC依据该条制定的10b-5规则所规定的欺诈,⑨将被追究内幕交易之责。故“公开或戒绝交易规则”的法理基础即在于“知悉即构成欺诈”,同样不考虑“利用要件”。但是,脆弱的理论基础之上不可能构建科学的规则体系,即便制定出来了规则也会始终面临质疑,在晚近的许多案例中,如United States v.Teicher等案中,被告就一审提出的“知悉即构成欺诈”向第二巡回法院提起上诉,第二巡回法院无法评价,只能无奈地解释说“要求SEC证明被告实际利用了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实在过于困难”。⑩
2.从实践上看,“知悉+交易”形成过宽的打击面,影响市场公平
公开市场上,的确有很多投资人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取不正当利益,但并不是所有的知情人都是如此,特别是随着市场金融工具的丰富,专业性和量化的长期操作不断增长,在现有法律规定和现实实践中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例外情形。此时,如只要行为人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交易就认定为内幕交易犯罪,不但打击过宽,也有失公平,会让投资者陷入惴惴不安的心理困境。兹列举目前市场环境下“知悉+交易”部分可能的例外情形:
(1)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我国《证券法》第76条第2款:“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法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表明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的上述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2)做市商参与的交易,一般不应被认定为内幕交易,除非有证据证明做市商背离了制度初衷。做市商制度(Market Makers,Market Dealers),也称造市商制度、双边报价制度、报价驱动交易制度,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符合法定条件的证券经营机构作为特许交易商,持续公布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双向报价并在该价位上接受投资者的买卖申报,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其中维持双向买卖交易的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即为做市商,以做市商为主导的证券交易即为做市商交易制度。(11)与证券公开集中竞价交易相比,“做市商”取代交易所成为证券交易的组织者,承担报价、接受申报、撮合成交及传递信息等职责,在调节市场方面具有主动性,既可以在市场低迷时通过适度报价和证券投放活跃市场,也可以在市场过度投机时平抑价格挤出泡沫。所以,以调节市场交易为己任的做市商交易,即便其知悉内幕信息,也不应被认定为内幕交易。当然,若其背离了制度初衷,利用内幕信息谋取私利,则为法律所不容。
(3)安定操作中的承销商交易,通常也不应当认定为从事内幕交易。安定操作又称为稳定操作,是指为了使有价证券的募集或卖出容易进行,防止或减缓证券价格在对公众发行时发生跌落或有跌落的可能性,在符合证券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证券市场连续买卖有价证券,或委托或受托买卖有价证券,以钉住、固定、或安定证券价格的行为。(12)安定操作中承销商进行的交易,系基于法律许可的稳定发行价格之目的,即便其知悉内幕信息,通常也不应被认为是内幕交易。当然,和前述做市商相同,安定操作的承销商也不能借此谋取私利。
(4)具有规范的信息隔离机制的委托交易,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概率较高。例如,甲和乙都是具有规范的内部控制机制的经营机构,甲长期委托乙进行证券交易,乙对所发生的交易具有充足的交易依据;后来,甲知悉相关内幕信息,但没有证据证明甲乙之间有该信息的传递,此时尽管乙交易的证券就是甲所知悉信息涉及的证券,仍不宜认定为内幕交易,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内幕信息在甲乙之间进行了传递,且乙是以该内幕消息为特定交易依据的。
(5)在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即已完成了相关证券交易的书面计划、合同或指令,该计划、合同或指令具有长期性而非临时性,且规定了买卖证券的数量、价格、日期,甚至包括书面公式、算法或计算机程序,且具有反复使用的适应性。基于此进行的证券交易通常亦不宜直接认定为内幕交易。
(6)其他特定交易情形,例如,基于对冲风险所进行的与股指期货等衍生证券进行套期保值而建立的股票现货头寸等。这类交易具有合理性,即便知悉内幕信息,一般也不应认定其为内幕交易。
以上除第一种外我国法律均没有相应的豁免规定,意味着知情人无论提出何种合理理由,都难以形成抗辩,而必须对其相关交易承担内幕交易之责,实在难言公正!事实上,上述列举还只是“知悉+交易”内幕交易认定中可能“误伤”的部分情形,随着证券市场的复杂化和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类似交易还将不断增多,如果不对此做出合理的法定要件构成分析并予以规制,将有违金融交易本身的发展规律。
(二)“知悉+利用”——“利用内幕信息”事实上为内幕交易构成不可或缺
故此,本文认为,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应当成为内幕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相比于“知悉+交易”,具备了“利用内幕信息”要件的“知悉+利用”要件组合更具有科学性。
1.“知悉+利用”包含了“利用内幕信息”的构成要件,在逻辑上方才完整
一般情况下,证券市场的交易者进行交易都是根据上市公司(或其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为交易依据,此时,假设某投资者知悉了某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并买卖了该公司的股票,通常来说,难道知情人会仅仅是依据该公司的公开信息而无视其所知悉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吗?“重要的信息是不会呆在人的大脑中无所事事的”。(13)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所从事的交易应该是有根据的,那么,一项重大、确定、真实、因未公开而具有私密性的内幕信息,其信赖价值显然高于公开信息,所谓投资“理性”中肯定应包含对此类他人不知晓信息的运用,作为一项交易决策的依据,内幕信息比其他公开信息具有优先性,亦是资本逐利性使然。因此可以说,内幕信息知情人做出的投资决策就是他“利用”了内幕信息的逻辑证据,如果在要件构成中缺少了此“利用要件”,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认知逻辑是断裂的、不完整的。
2.“知悉+利用”符合实践中的真实认知,案例中“利用内幕信息”更是被反复提及
虽然在立法层面,《刑法》第180条等采用了“知悉+交易”的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组合,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是否“利用内幕信息”的争议却仍十分普遍。例如,广发证券董正青(泄露内幕信息、建议内幕交易)、董德伟内幕交易案中,(14)一审裁判文书大量讨论了犯罪嫌疑人是否利用内幕信息的问题;再如深深房公司叶环保、顾健内幕交易案中,(15)顾健对自己直接的辩护就是提出,交易是“考虑到春节期间的市场行情和其他什么消息无关,而且这次炒股失败亏损了40多万元,这是没有利用内幕消息的最好证明。”法院则针对该抗辩指出:“相关供述表明‘已详细告知该事项具体信息,并帮助被告人顾健完成交易行为’,可认定其交易利用了内幕信息。”
除司法审判外,中国证监会数起关于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决定中也都提及了“利用要件”,例如2010年北孚集团案(16)、2009年四环药业案(17)、2007年陈建良内幕交易案(18)等。在陈建良案中,相对人提出“未利用内幕信息”抗辩:“系全权委托他人操作交易账户,代理人不知悉、未利用内幕信息,根据其自己的判断买卖,”执法机关则针对于此,以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明了“利用要件”的存在。(19)
不仅在我国,即使在证券监管最为发达的美国,也存在对内幕交易“利用要件”同样的纠结。如上所述,美国法遵循“公开或戒绝交易规则”,为此,司法判决中通常认为判断是否构成内幕交易应采“持有说”或“知悉测试”,而不是“利用测试”。(20)但在事实上,知情人是否“利用内幕信息”在案件审理中却仍被反复提及,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irks案判决中采用了“trading on inside information(依据内幕信息进行了交易)”字句;(21)在O'Hagan案的判决中也有类似表述:“trading on the basis of inside information(以内幕信息为基础进行了交易)”;(22)在SEC v.Texas Gulf Sulphur Co.案中,法院认为交易人的交易受到其所知悉的“内幕信息的影响基于重大非公开信息进行了内幕交易”;(23)在SEC v.Downe梨(24)、SEC v.Ginsburg案(25)等内幕交易判决也都是如此,虽然刻意避免“利用”一词,但文字表达却与“利用”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是否“利用内幕信息”,其实一直纠结于规范内幕交易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之中。(26)无论是“依据内幕信息”、“以内幕信息为基础”还是“基于重大非公开信息”等用语,其实都是“利用”内幕信息的同义表达。在法律规则明确规定不采用“利用要件”的情况下,现实案件裁判却仍被反复提及,正是清楚地表明了该要件的存在价值:内幕交易行为本身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利用要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逻辑节点。
(三)反思:放弃“利用要件”的唯一理由仅在于其“难以证明”
上述研究表明,内幕交易违法犯罪构成中是采用“知悉+交易”还是“知悉+利用”要件组合,核心在于知情人是否利用内幕信息作为交易之基础。显然,相比于“知悉+交易”要件组合,含有“利用要件”的“知悉+利用”要件组合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但事实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若干国家却多选择了简单的“知悉+交易”要件而舍弃合理的“知悉+利用”,原因何在呢?
对此,加拿大学者认为:“依据加拿大刑法典(Criminal Code of Canada,CCC)的规定,违法者不仅要掌握内部信息,还要故意使用这些信息。这一规定回归了各省证券法以前规定的内幕交易证明标准,即违法者‘利用’内幕信息但是现在各省的规定取消了‘利用’要求,因为这一构成要件太难证明了。”(27)同样,1996年加拿大通过《内幕交易法修正案》时放弃“利用要件”也是基于上述理由,从而可以便利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打击。
在澳大利亚,根据该国“公司和市场顾问委员会”报告,亦是基于上述观点在法律条文中放弃了“利用要件”,从而将其《公司法》和《内幕交易修正案》中关于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冲突修正为接近一致。(28)
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如果‘利用内幕信息’被设定为内幕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那么证券行政执法的执法者或者诉讼中的原告方或公诉人在执法或司法活动中就必须证明该要件的成立,从而被课以了沉重的举证责任,甚至因为内幕交易本身的隐蔽性以及‘利用内幕信息行为’的主观性,致使证据难以搜集”。(29)法官亦指出:“对使用‘知悉测试’最有力的支持在于‘利用测试’将课以SEC较重的举证负担”;(30)证券主管部门“不可能进入某人的大脑,找出他做出商业决定的直接原因”。(31)
可见,人们在观念上并不否认知情人进行交易是基于内幕信息,内心也认同内幕交易的构成需以知情人利用了相关内幕消息为基础,只是惮于证明之难而排斥“利用要件”,进而在面对知情人的“未利用抗辩”时,只能无可奈何地回避而不执一词,(32)或者直接通过判例提出“知悉即为欺诈”这样苍白的理由。但实际上,执法者自己对此都难以做到内心的确信,否则在已有明确立法规则的前提下怎会仍然出现上述那么多现实案例,继续纠结在“是否利用内幕信息”和“未利用抗辩”之上。
客观地看,“知悉+交易”要件组合的理论基础脆弱,实践中也会带来过宽打击面有失公平,而包含了“利用要件”的“知悉+利用”要件组合在逻辑上完整、连续,体现了内幕交易构成要件设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应当成为内幕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我们需要面对的,只是如何解决“利用要件”的证明难题,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一弃了之。
三 从事实推定走向法律推定:为“利用要件”正名
内幕交易“利用要件”虽难以证明却并非无法证明,其证明之难,难在证据的采集和运用,但随着证明方法之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尤其是推定证明方法的运用,为“利用要件”的证明开拓了新的空间。
在证据法研究领域,推定的应用已不断增多,逐渐成为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并列的证明方式。(33)推定“指由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34)它与一般证明方法的区别在于,一般证明方法都是证明事实,推定则是选择事实;(35)在当代两大法系中,比较一致性地将推定分类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36)
(一)“利用要件”的事实推定
近年来在我国,纠结于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这一具有逻辑应然性但却证明困难的问题,司法和执法机关已经开始在实践上运用“推定”的证明方法,事实上,文首所指《纪要》也已认可这一证明方式。例如,2010年中国证监会在李际滨、黄文峰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指出:“李际滨提出自己的交易行为没有利用内幕信息,买入粤富华股票是出于对公司全年业绩的判断,而不是受电力分红的影响;黄文峰也称其股票交易行为完全依据对公开信息的分析和对个股技术走势的判断做出。我会认为,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后从事了相关证券的买入或者卖出,就可以推断其买卖行为系‘利用’了内幕信息,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与证据排除这种推断。”(37)
除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晚近尝试外,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发达的美国,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事实推定的证明方法已经开始得到应用。1968年,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Texas Gulf Sulphur案中认为,知情人“之前从未购买过目标公司的股票,但知悉内幕信息后进行了交易,由此可成立‘这个内部人是受内幕信息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推论”。(38)此后,在1997年SEC v.Downe案、2004年SEC v.Ginsburg等案件的审理中,都采取了类似的推定证明方法。(39)而1998年SEC v.Adler案更是这方面的里程碑案例,确立了以事实推定方式证明内幕交易的利用要件。
1998年,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审理SEC v.Adler案,认为“案件真正的争议在于被告是否依据内幕信息作出交易决策”,该案没有回避“利用”问题,知情人是否“利用内幕信息”成为该案件审裁的核心,为解决利用要件难证明的问题,Anderson法官提出了“强烈推知规则(Strong Reference Rule)”,即“以交易者获知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可推定交易者利用了内幕信息,此种推断足以减除SEC在证明交易者进行了利用方面的困难”。(40)
Adler案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对“利用要件”进行“事实推定”之证明方法的大前提,而该大前提的科学性(41)在其后的判例中也得到了反复的检验,形成了美国法上的“Adler推定(Adler-type presumption)”(42),即由“知悉+交易”→(推定)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换言之,“知悉+利用”与“知悉+交易”并非对立的关系,在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和参与证券交易的情况下,知情人“利用了内幕信息”即成为一个可以推论的事实,依此推论,可论证认定“利用要件”已被满足,从而符合内幕交易的法定要件,构成了内幕交易,除非当事人能提出明确的、符合法定要求的反证证明自己并没有利用内幕消息。
事实上,在上述很多判例中,这种推定思维都隐隐地存在于各裁判文书之中或背后,只是一直没有被明确提出来罢了。但总是隐身其后并不是好的选择,现在是时候让“利用推定”拨云见日了,应让其从幕后走上前台,从“事实推定”走向“法律推定”。
(二)“利用要件”的法律推定
尽管“事实推定”之证明方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其推定之大前提的科学性,但从证据法理论上来看,要对其普遍应用还存在着三个障碍:
其一,“事实推定”本身的正当性可质疑。事实推定离不开经验法则,“言事实推定,必依经验法则”,(43)而所谓经验法则即为审理法官个人的生活经验,所以“事实推定”本质上是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由于不同法官生活经历、道德水平各异导致其经验法则的差异,运用事实推定就可能增加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几率。(44)证券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非常强,对其审理更是如此,在一个案件中是采用事实推定还是无视于它,全依凭于该法官自由裁量,此时要求法官所具备的,不仅是通常的生活经验,还需要对证券市场行为范式的深刻理解,一旦把握有所欠缺,就可能会放大自由裁量的弊端。
其二,“事实推定”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因为事实推定不是确定性认定而是或然性认定,故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例如上文提到的Adler推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同一年审理的Smith案中,法官就认为“这样一个推定在涉及认定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时是不能适用的”,(45)刑事案件要求“控诉方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承担的是‘反之构成要素’的说服责任,即必须一直证明到能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46)
其三,“事实推定”下被告提出的“未利用抗辩”将过于宽泛。因为既然法官可根据该案件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事实上的推定来认定被告(知情人)“利用了内幕消息”,那么知情人也可以反过来就此提出事实上“未利用抗辩”,并可能任意、宽泛地制造假象,从而实际上又使执法者陷入“必须证明却又难以证明”的尴尬境地。
为克服上述障碍,需要在事实推定的基础上走向法律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立法者根据事物问的常态联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推定。(47)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来源,法律推定是事实推定的合理发展。(48)就一项特定事实所产生的长期、大量的事实推定结论,终将反映到相关的法律规范当中,如上述美国法上多项判例、尤其是Adler案带来的“由‘知悉+交易’→(推定)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的事实推定结论,就在2000年带来了其内幕交易违法犯罪主要适用法源的修订,制定了SEC Rule 10b-5新规则,将“‘知悉+交易’→推定‘利用’”这一事实推定转化成为了法律推定。
SEC 10b5-1新规(49)分三款,(a)款规定:《证券交易法》第10(b)条10b-5规则所禁止的“操纵性和欺骗手段”,除其它事项外,包括违反对证券发行人或发行人股东、或作为重大非公开信息来源的其他人直接、间接或派生承担的信托或信任义务,依据与证券或其发行人有关的重大非公开信息买卖发行人的证券。
(b)款接着对其中的“依据”一词作出界定:除以下(c)款中的抗辩外,如果某人在购买或出售时知悉重大非公开信息,则其购买或出售发行人的证券就是在“依据”与发行人证券有关的重大非公开信息。
(c)款进一步规定了“只要购买或出售的人可以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则其购买或出售就不是‘依据’重大非公开信息”,并列举了三类肯定性抗辩:包括知悉前交易;知悉前指令他人交易、依据确定的书面合同、指令或计划进行交易;未改变原定数量、价格或买卖时机的证券交易等,并对所涉合同、指令、计划以及数量、价格等做了详细明确的界定。
考察及此可以发现,根据上述规则: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已成为内幕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并对其采取法律推定型描述,“知悉+交易”即可推定其“利用内幕信息”,从而可实现对该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证明问题;同时进一步规定知情人的法定抗辩理由,允许其在此范围内反证,避免了不公。
这样的规则设定符合以“信息公开”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证券市场中理性投资人的认识,从而使得人们对内幕交易的判定具备了逻辑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即通常,重大非公开信息的可信赖程度大于公开信息,所以,知悉内幕信息的理性投资人一般会以此为交易依据。与此同时,又通过法律明确的推定,使得“利用要件”的证明具备了确定性,避免了以“事实推定”方式证明时的种种弊端。该新规则在其后的案件审理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如2005年U.S.v.Causey案中即据此点明了Adler推定:“规则10b5-1创建了一个Adler推定:只要能证明被告于证券交易发生时知悉重大非公开信息,他或她就应承担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除非被告能够举出证据说明在其做出交易决定时,这些重大非公开信息并非其中的一个因素。”(50)
四 我国内幕交易构成要件中“利用要件”的完善
(一)理论研究小结
综上所述,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应当成为内幕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我国立法应当采用“知悉+利用”而不是“知悉+交易”之构成要件组合,使得内幕交易法定构成要件在逻辑上具备连贯性和完整性。对待“利用要件”会带来证明困难的问题,解决方法则是建立“可以反驳的法律推定”立法模式,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知悉+交易’→(推定)‘利用’”,并同时明确规定允许内幕信息知情人反证的主要事项。笔者将本文的研究结论归结为以下两个公式:
其一,“知悉+利用”之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组合公式,即在内幕交易其它事项(知情人、内幕信息等)确定的情况下,知情人只有“利用”了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方构成内幕交易,否则不构成,由此强调“利用要件”的适用。
其二,“知悉+交易”→(推定)“利用”公式,即如果知情人进行了(涉内幕信息的)证券交易,即可推定其证券的买卖系以该内幕信息为依据,在交易中“利用了内幕信息”。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并给出相应的法定抗辩事项,从而将事实推定产生的结论转化为法律推定。
(二)法律实施模式及相应立法建议
上述公式要求我们正确面对“利用要件”在内幕交易构成中的逻辑正当性,对此,文首的研究已指出,我国现有证券法律规则之间存在冲突,除《证券法》第73条明确规定了“利用要件”外,其它若干法律规范对此并不认同。而现有证券行政执法机构主要依据《证券法》第202条,(51)认为“认定内幕交易构成时可以不考虑‘利用要件’”。本文不同意这一观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证券法》第202条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法律规定,应当结合《证券法》第73条进行整体解释和适用。(52)事实上,不仅《证券法》第202条应该如此,《刑法》第180条等关于内幕交易刑事责任的规范解释和适用也应如此。换言之,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倡导“规范群”思维,与内幕交易相关的若干法律规范应被看作一个整体,从而保证对规范之解释和适用的制度化和体系化,而不能孤立地对待单个法律条文。就内幕交易的前述“规范群”而言,《证券法》第73条应作为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定义性条款,其条文对内幕交易法律制度整体具有基础性的立法价值,该条文中已经明确的事项,包括《刑法》第180条在内的其他各相关部门法可不再重复描述,直接应用,在此体系解释方法之下,“利用要件”一直都在、从未离去。
依此法律实施模式,《证券法》第73条作为定义性条款,必须对其进行恰当的立法描述并建立相应的配套规则,包括“利用要件”的确认以及证明等,否则设定了一项难以证明的构成要件,只会使该规则失去实践价值,事实上阻碍法律的公正实施。故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前述比较法上的经验,本文提出我国内幕交易的立法修改建议如下:
第一,对《证券法》第73条增加一款:“除非符合本法第76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在购买或出售证券时知悉内幕信息,则其购买或出售证券系‘利用’该内幕信息。”
该款系将前述法律推定公式“‘知悉+交易’→(推定)‘利用’”反映到立法中。
第二,删除《证券法》现第76条第二款(将其纳入下文提及的配套规则),重新制定该款:“如果证券交易者(知情人)有证据证明即使在完全不知道内幕信息的情况,仍应当进行同样的交易行为,则其购买或出售证券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的交易行为。”
该条款是在立法确立“知情人只要进行交易即视同利用内幕信息”这样一个法律推定的前提下,对知情人的特定抗辩事项进行的规定。本款具备如下特点:
其一,原则性。本款是知情人特定抗辩事项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抗辩事项需要配套规则——如国务院颁布相应的行政法规、或授权证监会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等,予以细致规定;
其二,抗辩事项范围法定且证明责任转移。本款及基于本款而具体规定的抗辩事项,由抗辩人承担证明责任,司法机构或证券行政执法机关负责审查抗辩事由及证据,并作出抗辩有效与否的结论。
其三,严格性。本款的严格性主要通过其所建立的可抗辩原则并在相关配套规则中体现,本款提出的可抗辩原则是“如果证券交易者有证据证明即使在完全不知道内幕信息的情况,仍应当进行同样的交易行为”(以下简称“仍应当交易原则”),与此对应的另一种描述是:“证券交易者有证据证明即使在完全不知道内幕信息的情况,也会进行同样的交易行为”(53)(以下简称“也会交易原则”),两相比较,可知前者严苛于后者。
在“仍应当交易原则”下,具体的抗辩事项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源于法律的规定可以进行的交易,这种情形下,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可能是收购人、或者做市商、承担安定操作责任的特定金融机构等,这些特定主体参与证券交易拥有法律的授权或许可,知悉内幕信息与否不影响交易,当然也不存在是否“利用”的问题。例如现行《证券法》第76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上市公司被收购”显属内幕信息,但不影响收购人(也仅限于收购人)依法买入该公司股份。此类涉内幕信息的交易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知情人只要提交相关证据,审裁者无须质疑。
另一类源于确定的或长期的交易计划、合同约定或特定交易方式下的交易,例如,知情人有长期的交易计划、或长期代理他人进行交易并接受了非知情人的交易指令、或者基于对冲风险而进行的交易等,但这类抗辩事项的可质疑性比上一类要大,(54)故对这类抗辩,要求知情人不能只是做单纯的“未利用抗辩”,而要求其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程度达到“不必利用抗辩”的程度,即要能让法庭(或证券行政执法机关)确信:无论利用或不利用内幕信息、知悉或不知悉内幕信息,交易都会进行。针对这类抗辩,可以建立专家意见征询机制,以解决法官自由心证方式可能产生的弊病。
和“仍应当交易原则”相比,“也会交易原则”下的抗辩事项范围要宽泛得多,包含了一些“知悉内幕信息即不应当交易”的情形,在我国证监会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中出现过一些类似抗辩情形,例如,“无意听说”(55)、“误操作”(56)、“巧合及独立判断”(57)、“全权委托他人交易”(58)等,这些抗辩无法排除对内幕信息的“利用”,不足以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不应纳入立法明确的法定抗辩事项中。
第三,国务院(或授权证监会)尽快制定颁布相应的行政法规或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内幕交易的构成、认定及其特定抗辩事项作出明确的列举。
2012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内幕交易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吸收了部分理论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做法,对内幕交易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量化标准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与本文研究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的是,《解释》所采认定内幕交易的标准为“知悉+(敏感期的异常)交易=内幕交易”,并列举了四项法定豁免情形。对该司法解释中对与本文相关的问题评述如下:
其一,总体来说,《解释》是《刑法》第180条的法律适用型解释,故在“利用要件”问题上与《刑法》第180条保持了一致,这也是法律解释的应有之意。但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产成冲突,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刑法解释的过程,(59)而如上文提出的,对内幕交易罪也应当注重体系化解释,不局限于刑事法律制度内部,而应与〈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相协调一致,例如美国法上无论规制内幕交易行为还是内幕交易罪,其主要法源不仅是《证券交易法》Section 10b,也包括SEC Rule 10b-5等规则。
在刑法理论上,内幕交易罪属于“情节犯”,即属于内幕交易违法行为中“情节严重”者,故其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之基本构成要件应当一致,对待“利用要件”的态度也不应存在本质差异。所以,本文认为,可以将“知悉+交易”→(推定)“利用”或者“知悉+(敏感期的异常)交易”→(推定)“利用”(60)在《证券法》第73条中予以明确规定,并在《刑法》第180条增加一款,在“利用要件”问题上,仿照第180条第二款(内幕信息的范围)和第三款(知情人员的范围)的立法方法,与《证券法》进行衔接,建立规范内幕交易的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二,《解释》第四条列举了内幕交易的法定豁免情形:(一)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购该上市公司股份的;(二)按照事先订立的书面合同、指令、计划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的;(三)依据已被他人披露的信息而交易的;(四)交易具有其他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61)从这些内幕交易法定豁免、即“知悉+(敏感期的异常)交易=内幕交易”推定例外的设定中,特别是从“交易具有其他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这一兜底项中,我们可以看出,《解释》本身的标准仍未统一,即如果它采取完全的“知悉+(敏感期的异常)交易:内幕交易”,那么,只要发生交易,就可认定内幕交易罪成立,而无论交易本身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不可能提出该项豁免了。故而实际上,《解释》也已隐含了“知悉+(敏感期的异常)交易”→(推定)“利用”这一“利用要件”的推定式认知,后续的立法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性来进行法定要件构成的设计,将其予以确认。
其三,在“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刑事立法原则下,推定需要慎重,但刑事法律制度并不完全排斥推定,在具体形态上,本文所指“利用要件”的推定模式属于立法型推定——将历经实践检验的结论上升为应予强制适用的法律,属于强制性推定并且属于可反驳的推定,(62)立法可以通过确定法定豁免事项的方式给予被告反驳的机会,以免当事人陷入无所适从的“自证清白”的窠臼。当然,在证明标准方面,不同的责任形态应当有所区分。
其四,《解释》对内幕交易法定豁免情形的规定,与前文研究基本一致,但涉及的具体范围要小并保留了兜底条款。事实上,内幕交易的法定抗辩情形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基础性研究,提出了法定抗辩的基本立法原则并对豁免范围作了研讨,在此基础上,具体的抗辩事项及其证明方法尚需进一步的细致制定,并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增加完善。
注释:
①参见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继续把打击内幕交易作为工作重点》,资料来源:http://www.cfi.net.cn/p20120111001712.html,访问时间:2013年9月8日。
②证券法上之证券界分为基础证券和衍生证券的类型化研究,可参见曾洋:《论证券法之“证券”——以《证券法》第2条为中心》,《江海学刊》2012年第2期,第217-218页。
③内幕交易主体在我国的法条用语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本文中统称“知情人”,即指知悉内幕信息的人。笔者将另撰文讨论内幕交易主体的理论基础和立法逻辑。
④2012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内幕交易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利用要件”延续了刑法的态度,后文将专门讨论。
⑤此处“从事了法律所规定的证券交易活动”即指法律条文中规定的“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为行文方便,下文均作如此表达,在相关公式中直接简称为“交易”。
⑥例如,马其家:《英美法系内幕交易的认定证明标准及启示》,《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10月号;彭冰:《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三卷(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6-130页;马其家:《我国证券内幕交易认定标准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54-157页;李建春、许昌清:《论内幕交易“利用”和“知悉”标准的再造——对美国经验的借鉴》,《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62-69页,等论文对该问题亦有一些讨论。
⑦See U.S.v Smith,155 F.3d 1051,1066-1069(9[th] Cir.1998),即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上诉法庭审理刑事上诉案件美国诉史密斯案的判决书认为,如果甲交易A公司股票并不是以其所知悉的内幕信息为依据,则甲和乙的交易行为是对等的。
⑧该规则也被译为披露或弃绝交易,公开或拒绝交易规则,公布消息否则禁止买卖规则。对该规则的进一步讨论和批评,可参见Donald C.Langevoort & G.MituGulati,The Muddled Duty to Disclose Under Rule 10b-5,57 Vand.L.Rev.(2004).
⑨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及1942年SEC依据该条制定的10b-5规则虽都以禁止证券欺诈为主要内容,但用语颇具弹性,留给执法机关充分的解释空间。发展至今,这两个条文已成为美国禁止内幕交易的基本法律依据。See Louis Loss & Joel Seligman,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5),pp.766-780,848-862.美国法上的这两个条文下文还有提及,以下简称Section 10b和Rule 10b-5。
⑩U.S.v.Teicher,987,F.2d 112,(2d Cir.1993).
(11)参见曾洋:《证券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页。
(12)参见曾洋:《证券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3)张子学:《邓军、曲丽内幕交易案》、《潘海深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4)(2008)天法刑初字第689号。
(15)(2003)深罗法刑初字第115号。
(16)《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北孚集团、秦少秋、倪锋、柳驰威)[2010]40号。
(17)《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四环药业金峰、余梅)[2009]4号。
(18)《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陈建良)证监罚字[2007]15号、《市场禁入决定书》证监禁入字[2007]6号。
(19)王长河:《陈建良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遗憾的是该案行政处罚文件过于简单,没有记录相应的论证和处罚理由,无法充分体现出这一“利用要件”及其存在的证明过程。
(20)“持有说”在Teicher案中被明确提出,See Supra note 11,U.S.v.Teicher,987,F.2d 112,(2d Cir.1993)。“持有说”、“知悉测试”、“知悉标准”与本文所称“知悉+交易”之内涵一致。而“利用测试”之内涵对应于本文的“知悉+利用”公式及“利用要件”。但美国法上这两个标准的使用并非确凿无疑,理论纷争亦仍在延续。
(21)Dirks v.SEC,463 U.S.646(1983).
(22)United States v.O'Hagan,521U.S.642(1997).
(23)SEC v.Texas Gulf Sulphur,401 F.2d(2d Cir.1968).
(24)SEC v.Downe,969 F.Supp.149(1997).
(25)SEC v.Ginsburg,362 F.3d 1292(7[th] Cir.2004).
(26)See Karen Schoen,Insider Trading:the "Possession Versus Use" Debate,14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9),pp.249-264.
(27)See M.Gillen,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 in Canada,11[th] Queen's Annual Business Law Symposium,15 Oct.2004,at 14-17.转引自[加]戴维·约翰斯顿、凯瑟琳·罗克韦尔(David Johnston & Kathleen Doyle Rockwell)著:《加拿大证券监管制度》(Canadian Securities Regulation),曾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369-370页。
(28)Corporations and Markets Advisory Committee(Australia),Insider Trading Report(Nov.2003):sec.3.8.Government response to Report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Fair Share for All Insider Trading in Australia,11 Oct.1990.
(29)See Karen Schoen,Insider Trading:the "Possession Versus Use" Debate,14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9),p.278.
(30)SEC v.Adler,137 F.3d 1325(11[th] Cir.1998).该案判决中的“知悉测试”和“利用测试”之含义分别对应于本文提出的“知悉+交易”和“知悉+利用”构成要件公式。
(31)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法律主管William McLucas的观点,See Phyllis Diamond,McLucas Hails O'Hagan Ruling,But says Issues over reach of theory Remain,29 Sec.reg.& L.Rep.,(1997),pp.1097-1098.转引自前引马其家:《英美法系内幕交易的认定证明标准及启示》,《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10月号,第7页。
(32)如2008年邓军、曲丽内幕交易案中,“邓军辩称,其买捷利股份的股票是基于看到技术上突破了,而不是因为搜索到了尽职调查人员的名字就买捷利股份的股票,二者有一定的巧合。曲丽也辩称自己没有利用内幕信息”(张子学:《邓军、曲丽内幕交易案》、《潘海深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页)。但是,执法者在该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此未有只言片语的反驳,显然是对难以证明的“利用要件”无可奈何地回避。
(33)事实上,不仅是对“利用内幕信息”的推定,“知悉内幕信息”也常被用推定的方法予以证明,可见在内幕交易的证明过程中推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多重推定的合理性如何,仍值得探讨。
(34)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35)裴苍龄:《再论推定》,《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1页。
(36)参见王雄飞:《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第181-182页。
(37)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李际滨、黄文峰)(2010)29号。
(38)SEC v.Texas Gulf Sulphur,401 F.2d(2d Cir.1968).
(39)SEC v.Downe,969 F.Supp.149(1997)、SEC v.Ginsburg,362 F.3d 1292(7[th] Cir.2004).
(40)SEC v.Adler,137 F.3d 1325(11[th] Cir.1998).
(41)事实推定是一个三段论推理过程,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方面构成,其中甲事实与乙事实之间的或然性联系(经验法则)是大前提,甲事实(基础事实)是小前提,乙事实(推定事实)是结论。(参见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其中的大前提应当符合科学性标准,三段论之事实推定方式才能有效成立,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8页。
(42)U.S.v.Causey,F.Supp.2d,2005 WL 3560632(S.D.Tex.),该案判决将Adler案中关于“利用要件”的证明方法总结表述为“Adler推定”。
(43)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
(44)褚福民:《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及其正当性质疑》,《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第680页、679页。
(45)See U.S.v.Smith,155 F.3d 1051,1066-1069(9[th] Cir.1998).
(46)褚福民:《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及其正当性质疑》,《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第682页。
(47)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卞建林:《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71页。
(48)褚福民:《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及其正当性质疑》,《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第678页。
(49)Sec.Ex.Act Rels.42,259,71 SEC Dock.732,745-748(1999)(建议稿);43,154,73 SEC Dock.3,19-22(2000)(通过稿)。本文研究发现,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该文件的相关解释存在误读,也缺乏整体解读。
(50)U.S.v.Causey,F.Supp.2d,2005 WL 3560632(S.D.Tex.)
(51)《证券法》第202条规定内幕交易的行政责任时,并没有规定该要件,采用的是客观标准。张子学:《邓军、曲丽内幕交易案》、《潘海深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页。
(52)参见彭冰:《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张育军、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三卷(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53)张子学:《邓军、曲丽内幕交易案》、《潘海深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页。
(54)例如,2002年美国第七巡回法院审理的SEC v.Ljpson案适用了10b5-1新规则。被告David E.Lipson知悉公司财务利空消息时以每股9美元出售365,000股公司股票,其后信息披露的当天,股票价格跌至每股6.50美元。Lipson声称出售股票的唯一理由是“遵守两年前制定的遗产计划”。但Posner法官认为:“(如果认可抗辩理由)是荒谬的,因为出售者可能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向儿子转移财务,另一种是避免遭受内幕信息显示其将遭受的损失。合法目的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使目的合法化。”See SEC v.Lipson,278 F.3d 656(7[th] Cir.2002).
(55)《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北孚集团、秦少秋、倪锋、柳驰威)[2010]40号。
(56)《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潘海深)[2008]12号。
(57)《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瞿湘)[2008]49号。
(58)《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陈建良)证监罚字[2007]15号、《市场禁入决定书》证监禁入字[2007]6号、王长河:《陈建良内幕交易案》,载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59)张苏:《对内幕交易罪争议要素的评释》,《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4期,第24页。
(60)内幕交易是否必然表现为异常交易?或者说其“异常”是相对于市场而言还是相当于该交易人本身而言?显然这是一个可质疑的问题。但这并非本文研究主旨,亦限于篇幅,故不作展开。
(61)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指出,这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抗辩权,防止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适用对象被不当扩大,故而借鉴成熟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采用列举表述加兜底条款的方式规定了不属于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的情形。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材料”,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yjdt/20120522135820.htm,访问时间:2013年9月23日。
(62)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