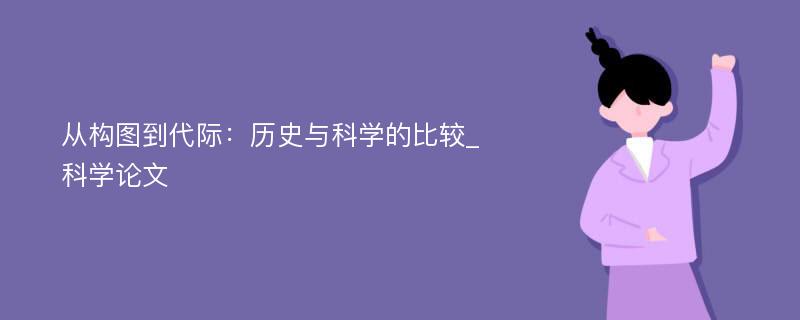
从构成到生成——历史与科学的一个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历史学与科学分属不同领域。科学自然是自然科学;历史在西方一般被认为是人文学科,在中国则是社会科学,都不属于自然科学。因而历史与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形态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也曾经有观念方法上的相互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外在的重新构造,发掘历史和科学在知识形态上的某些同构。
1 类比
如所有的基本概念一样,历史也没有一个人人认可的定义。但无论怎样定义,都无法逃避“过去”这个词,“过去”是历史的核心。以“过去”为出发点,历史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涵义:
(1)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
(2)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对过去事件的研究。
对于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也可以构造出对应的陈述:
(a)存在一个自然界;
(b)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对自然的研究。
对于命题(1),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可以将其改写为:
(1)存在一个过去。
这样,就构造了两对同构的命题,把历史和科学对应起来。前一对命题为:
(1)存在一个过去;
(a)存在一个自然界。
(1)和(a)实际上只是分别指出了历史和科学的研究对象,断言存在这个对象,可称之为存在命题。在存在命题的断言中,隐含着一种观念,即“过去”和“自然”都是已经存在的对象,这个存在与人的主观意识无关,所以是“客观的”对象。
后一对命题为:
(2)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对过去事件的研究。
(b)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对自然的研究。
这一对可称为描述命题。研究必然是人的研究,人的主观因素在此隐约出现。
把(2)进一步分解,关于过去的知识和对过去的研究主要包括:
(2.1)某些事件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刻,某一时刻某一空间的人究竟在干什么;
(2.2)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这些事件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与历史对应,可以同样对(b)做如下分解:
(b.1)自然中存在哪些事物,这些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分布;
(b.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然界,自然中的事物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2.1)和(b.1)的对应与(2.2)和(b.2)的对应是显然的。这种划分与人们一般心理大致相符。先获得(2.1)和(b.1),对于对象的描述——这个描述当然是越完整越好;然后是(2.2)和(b.2),根据这个描述获得关于对象的进一步知识——把握其规律。
在此,科学和历史的对应似乎有些失衡。一般认为,历史知识以(2.1)为主,以(2.2)为辅;而科学则以(b.2)为主,(b.1)为辅。但是,可以把(b.1)理解为博物学传统的科学,使它与(2.1)意义上的历史对应。
博物学传统的科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从各种生物获得它们的名字起,博物学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可以上溯到人类有语言之初。同样,自有人类活动开始,人类的历史也就开始了。简单地理解,博物学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自然界)进行收集、观察、记录;而历史学则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收集、考据、记录。在获得了对象的若干集合片段(2.1)和(b.1)之后,就开始了(2.2)和(b.2)——对这个集合进行研究:分类、整理,提取规律。
当然,这一种简单的假设,如果是搭积木,总是先把要用的积木块都找出来摆到桌子上,然后再搭建可能的形状。但是,构成“过去”和“自然”的积木块是否预先就已经存在了?
事实上,在把科学划分为(b.1)和(b.2)时,就已经无意识地对自然采取了一个本体实在论的看法,即假定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的客观的自然界。这种假定似乎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也是许多科学家潜在的观念。自然必然具有属于其自身的确切的稳定的特性,这才谈得上对它进行研究,获得关于它的知识。在古希腊人看来,“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含使它自己消灭的种子”[1]。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同时,人类对于自然的基本观点也逐渐地变化着。在牛顿物理学取得成功之后,构成论的机械论自然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构成论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由一些早已存在的东西造成的。事物的生成和毁灭,都是完全独立的元素相结合和分离的结果。”[2]在这种自然图景中,自然是一只巨大的钟表,人们可以通过对一个个钟表齿轮的认识得到关于自然的整体认识。构成论首先是实在论的,同时也是还原论的。既然能够把自然分解成各个部分,必然也能够把分解出来的各个部分组合成原来的整体。就是说,可以通过对部分的研究,获得对整体的认识。但这种分解不应该是无限度的,所以构成论也认为存在实体意义上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于是构成论也是原子论的。为了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分离和还原必定是惟一的,必然的。所以构成论也必然是决定论的。
这种构成论的自然观在历史学中也可以找到对应。
复述一下关于历史的命题(1):存在一个过去。这可以理解为,存在一个时间上的过去,在这个“过去”之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种叙述方法已经预先设定了一个从古至今的时间坐标,这个坐标上逐一标定着各个事件。把这个坐标在空间上展开,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排了所有事件的时空框架。有些事件人们确信曾经发生,比如武王伐纣,但是不知道把它安排在时空框架中的什么位置。这就需要(2),对过去进行研究,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
构成论在历史学中的表现,从实在论的意义上说,就是相信存在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确切的过去。也可以把这个完整的过去分解成许多部分,对各个部分逐一认识,再复合起来,就如同把一根根骨头化石拼接起来,得到一个关于过去的完整的骨架。进一步讲,人们还要通过这个骨架,复原出骨架主人的形象,得到对于过去的进一步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构成论者认定能够通过对过去的研究复原出确切的真实的过去,即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2 辉格
“辉格式的历史”是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对某种编史方法的批评。“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3]简而言之,辉格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把今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以今天的标准来评判过去。比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史,可算是典型的辉格史学。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重大变革。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网络,不可能存在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的简单因果联系。巴特菲尔德这样期望历史学家:“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更加详细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4]辉格式的历史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表明,绝对的反辉格史学也是不可能的。现在,人们基本承认,历史总是要有一定的辉格倾向。
从对辉格史的反对,到承认辉格倾向不可避免,与早期电影理论中的某些发展过程有些类似。巴特菲尔德理想中的历史是一个无穷大的数据库,里面储存着关于过去某一段时间的全部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全部客观准确,所有的细节都可以无穷地放大。这种观念与构成论自然观是一致的。电影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一些电影人曾认为,人类终于获得了一项绝对客观的观察事物的手段。克拉考尔(Sigfried Kracauer)就把自己的电影理论著作命名为《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在这种观念下,也曾有电影人对一个人的行为跟踪拍摄,把这个人的所有活动包括吃饭、睡觉、打哈欠的场面都拍摄下来[5]。这应该符合巴特菲尔德的理想,如果这部电影拍摄得无穷之长,就能够获得某个人完整的历史,一旦我们需要什么,就去查胶片。但即使如此,这个电影数据库也是不完整的。且不论其中不包括触觉和味觉信息,即使视听信息,也远非全息。同时,镜头也不可能绝对地“客观”。后期电影理论承认,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电影。即使是一部不需要剪辑的电影,其镜头的角度、景别也都隐含着拍摄者的主观色彩。
历史关注的是具体的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命运。既然无穷大的数据库不可能,在资料丰富时要进行筛选,就会涉及到筛选的标准。如同分类的标准一样,筛选的标准也是不可能客观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选择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在资料欠缺的时候,历史学家又要用自己的想象填充未完成的部分。至于如何填充,仍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理解。
对应于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设想,如果博物学也能获得一个无穷大的数据库,上面记录着各个地方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各种动植物在不同地方的生活习性,矿物在不同地方的表现形态。从这个数据库开展(b.2)的研究一定方便得多。但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最基本的博物学研究来自人的观察,这种观察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观察者的视觉模式。视觉并不是先天的。从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婴儿所看到的世界与成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只是婴儿不能辨认出所看到的东西。但是研究表明,在视觉模式形成之前,婴儿不是辨认不出来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根本看不到不认识的东西。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先天失明的盲人在成年以后通过手术恢复了视力,最初,他无法通过视觉来辨认他熟悉的事物,必须用手摸过之后才能确认[6]。这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念有许多相合之处。
所以,存在命题只是一个假设。
现在考察关于科学的描述命题(b.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然界,自然界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不妨认为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引发了自然哲学,对后一个问题的追索产生了数理传统的科学。其前提是,相信自然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的、可以被人认识的、并能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规律。数理传统的科学与实际的博物学传统的科学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也可以把数理科学视为博物学对于自然分类从定性到定量的延续。数理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也改变了人类自身。
以(1.1)意义的历史与(b.2)意义的科学相比较,当然会有很多差异。我们现在常说的科学与历史间的差异,也正是因为以二者不对应的部分进行比较。就此二者的比较而言,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研究类的性质,而历史则关注具体的事件以及事件中具体的生命个体。即使博物学,所关心的也是类。生物学家劳伦兹(Konrad Lorenz)养了许多穴鸟,他要从中发现的规律是关于所有这类穴鸟的,而不是关于特定的几只。当他在《所罗门王的指环》中用重墨描写他与其中几只穴鸟之间的感情时[7],他离开了科学,进入了历史。
那么,对于历史学,是否存在与(b.2)的对应?
即(2.2):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这些事件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历史是否存在如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是确切无疑的,找到了历史规律,对于这些事件为什么发生就有了解释。但是,这种强意义上的规律并不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可。根据吴国盛的观点,当把历史理解为在时空中展开的一系列事件时,单向的时间就暗示了在不同的空间中的事件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在时间上展开。所以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8]。其中“相同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弱一些的规律。无论强的规律还是弱的规律,都认为历史遵从某种确定的法则。
而在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看来,只有“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是有意义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他把以(2.1)为主要内容的史学贬为剪刀加糨糊的史学。他说,一个自然科学家可以不去考虑自然怎么想,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考虑历史事件中的人怎样想。所以,柯林武德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9]。
3 实体
量子力学诞生后,对于人类诸多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不再把科学当作客观的真理,而是当作对物质世界的一种描述方式。本体实在的假设被取消了,还原论和决定论都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同样,对于绝对真实的历史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可以获得。“在今天的美国大学中,谁要是还宣称他能知道‘真正真实的历史’,那他就将失去在大学教书的资格”[10]。
在量子力学思想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问题:“月亮在没有人看到它的时候,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对本体实在提出了怀疑。这个问题转换为历史问题就是:历史是否真的曾经存在?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观察到过去,如果我们不能断定月亮在没有看到的时候是否存在,那么我们也无法断定历史真的曾经存在过。物理学家惠勒(J.A.Wheeler)的观点更富有冲击性,他认为:“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已完备存在着的观念是错误的。‘过去’只是理论上的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过去’存在着,除非它现在被记录到”[11]。这种观念初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是,这却是惠勒根据他的延迟选择实验在1979年从物理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令人惊奇的是,此前40年,柯林武德也有类似的表述:“我们不应该回答过去怎样为人所知这个问题,却应该主张过去并不为人所知,只有现在才为人所知”[12]。在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的思想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平行。惠勒的思想和柯林武德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结论完全来自物理学本身。
惠勒接着说:“我们用怎样的量子设备置于现在这一点将会对我们所谓的‘过去’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影响”[13]。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物理学不再是关于自然的真理,而是关于自然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形象地说,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我们得到什么答案,与我们的提问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惠勒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延伸,甚至“过去”也是在我们现在的提问中产生的。同样,历史也成了人与过去的对话。柯林武德“自命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其解决并非是由于发现了新材料,而是由于重新考虑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14]。柯林武德认为,哲学史所展现的并不是对同一个原则问题的不同解答,而是对不同问题的回答。答案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问题本身发生了变化。
既然“过去”取决于现在的提问方式。那么“一切历史”就如克罗齐所言,成为“现代史”。于是在柯林武德看来,史学的水平取决于对话的深入程度,取决于对话者的提问水平。史学家必须不断地提问题,并自己给出回答。这样,史学家就使过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这一重演是以史学家本人的水平高低为其前提的,并且是通过把古代纳入今天的轨道进行的。因此,它并不是停留在古代水平上的重演,而是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15]。因此,“只有在历史学家以他自己心灵的全部能力和他全部的哲学和政治的知识都用之于所思考的问题时,这种重演才告完成”[16]。于是,史学从剪刀糨糊的工匠的工艺变成了大师的艺术。这种史学观对史学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工艺可以模仿,而艺术则不能。历史在此获得了个性。
柯林武德认为,这样通过在心灵中对过去的重演获得的历史具有一种自律性。自律性是指成为其自己的权威,而不需要其他的权威来证实自己。这时,历史学获得了一种整体性。如一粒种子,在不断的提问和回答中成长起来。这种历史与剪刀糨糊的拼贴不同,它不再是构成论的还原论的历史,而是整体生成的历史。这样一种历史与科学家惠勒所描述的历史又有某些同构之处,惠勒认为:
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整合体(grand synthesis),其全部时间中的一切以一个整体全盘端出。其历史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它不是一件事情跟随着另一件又另一件。而是一个整体(totality),其中“此时”之所发生赋予“彼时”之所发生以实在性,甚或决定彼时之所发生[17]。
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史学思想与科学(至少是物理学)思想都存在一条从还原构成论到整体生成论的发展线索,但是两者间的直接关联尚未发现。
4 后话
柯林武德把人类的经验或曰知识分为五大类: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哲学。各类知识中,至少宗教曾经在人类社会中占据过主导地位。而今天,站在这一位置的是科学。在科学与技术结成一体之后,人类拥有了非常高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相比之下,人类控制自身的能力弱得不成比例。就如同一个十四个月的婴儿挥舞一把锋利的刀子。这是人类的危险之所在。而拯救的力量,在柯林武德看来,将来自历史学。
柯林武德“特别强调20世纪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其中史学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可以方之于17世纪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教导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史学则有可能教导人类控制人类自身的行为”[18]。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柯林武德强调,需要对史学进行重建。因而“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19]。
柯林武德预言了20世纪史学和科学在另一个层面上可能的同构。这个预言显然没有实现。但预言的理由依然存在。科学及其技术已经使人类具有了毁灭自身的力量。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必将使这种毁灭力量表现出来。毫无疑问,人类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制约它。只是,这种力量是否如柯林武德的预言,由史学来承担,尚未见端倪。
收稿日期:200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