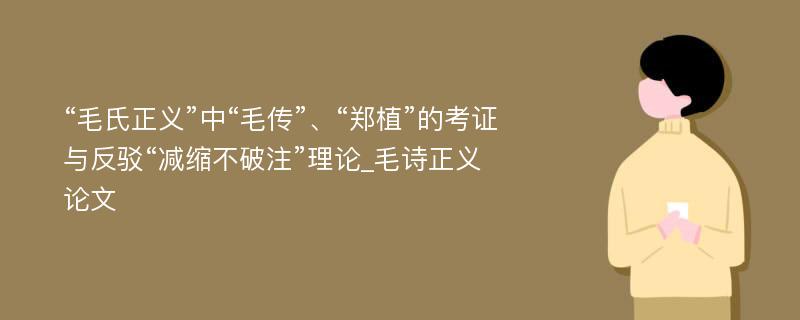
考论《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兼驳“疏不破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不破论文,批评论文,毛诗论文,毛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8)06-0012-04
奉太宗之命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以下省称“《正义》”),是以《诗》学史上最为权威的注本《毛传》、《郑笺》为底本作疏,成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著作。但自宋以后,学者多诟其墨守毛、郑成说,不敢有所逾越。本文按《正义》批评的内容分类考察,以见《正义》对权威注家批评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毛诗正义》批评所涉内容较多,为了彰显问题的特征性和层次感,我们拟将其分为文献批评、文学批评和经义批评,大致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文献批评
批评《郑笺》的引文错误。指毛、郑对文献的征引与古籍不相符合。如,《小雅·南有嘉鱼》云:“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笺》释“绥”云:“绥,安也。与嘉宾燕饮而安之。《乡饮酒》曰:‘宾以我安’。”据《正义》考证说:“案《乡饮酒》无‘以我安’之文,……则此文在《燕礼》矣”,并举例以证,《燕礼》云:“司正洗角觯,南面奠于中庭,……。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因此“言《乡饮酒》者,误也。定本亦误”。然后,又进一步分析致误的原因在于:“以《南陔》与《由庚》之笺皆《乡饮酒》、《燕礼》连言之,故学者加《乡饮酒》于上。后人知其不合两引,故略去《燕礼》焉。今本犹有言《燕礼》者。”此引文的错误由后来学者传抄所致,不在郑玄。但也有一些引文错误是郑玄本人所致。如《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笺》释“被”云:“《礼记》:主妇。”而《正义》考证文献说:“此‘主妇’,在《少牢》之经,笺云‘《礼记》曰’者,误也。”这样的例子很多,不烦多举。《正义》都是从考察文献出发,表现出客观严谨的态度。
批评毛、郑的训诂错误。指毛、郑对经文的解释或与古文献不符,或与语境不合。如,《传》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但是,《正义》考证《释山》云“石戴土谓之崔嵬”;孙炎也说所谓“崔嵬”是指“石山上有土者”,并且还说“土戴石为砠”。《正义》因此认为,“此及下传云‘石山戴土曰砠’,与《尔雅》正反者”,可能就是《传》的错误。我们再看与语境不合者。如,《周南·桃夭》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笺》:“老而无妻曰鳏。”鳏是指男子无妻。《笺》将“鳏”限于老者,义太狭隘。于是《正义》纠正说:“鳏寡之名,以老为称。其有不得及时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无鳏民’,谓年不过时,过则谓之鳏。”然后又证之以古代典籍。《释名·释亲属》:“无妻曰鳏。”《尚书·尧典》“有鳏在下曰虞舜”,《正义》云:“《王制》云:‘老而无妻曰鳏。’舜于是年未三十而谓之鳏者——鳏者无妻之名,不拘老少。”可见鳏并非特指老而无妻。从《桃夭》诗意及《诗序》来看,《序》中的“鳏民”,显然不是老而无妻的鳏夫,而是指超过婚龄仍未成亲的青年男子。郑玄误解了原意。《正义》指出,“鳏”只有与“寡”并提,才指的是“老而无妻”,《序》中的“鳏民”正是“不得及时为室家”的青年男子,直接纠正了郑玄的错误训释,表现了客观通达的训诂思想。
(二)文学批评
批评郑玄“不明诗作具有典型性”的错误。就《诗》的特征而言,经过魏晋以来文学经验的积累,《正义》的认识要比毛、郑前进一大步。在阐释过程中,《正义》对于毛、郑认识的局限也常常加以批评纠正。如,对诗的立意,《正义》表达了不同于郑玄的见解。《诗大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这是讨论风雅是如何产生的问题。《郑志》张逸问:“尝闻一人作诗,何谓?”郑玄答曰:“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于一人之本身。”也就是说,郑玄认为诗立意的方式是:
诗者一人之意 天下国家之意
在“诗言志”观念里,只有“诗”,没有“作诗者”。“作诗者”的情感意象,是在从孟子开始转换了的诗学主题里才逐渐成为问题的。因此说,较之前人,郑玄是用新视野看旧问题[3]P16,而《正义》则更进一步,它认为,照郑玄的说法,则“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这种方式就是以个人之意,强加给国家,这样的诗不具有典型意义。比如,《谷风》、《黄鸟》,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怨夫耳。《北门》、《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正义》使用两个未必,表明了对郑玄观点的断然否定。而《正义》认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即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然后形诸歌咏。这样诗的立意,便经过从国家到诗人,再从诗人到国家的两个双向思维路径,即:
作诗一人之意 天下国家之意
因此,《正义》认为,《谷风》、《黄鸟》、《北门》、《北山》之诗的典型意义在于:“但举其夫妇离绝,则知风俗败矣;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一人言之,一国皆悦”。其实,《正义》是想从诗的立意的角度,说明经义的客观权威性,但就是在经义阐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深触到诗产生的本质问题,远远超越了先儒。
批评郑玄对《诗经》比兴手法认识的不足。简言之,《正义》借“体用”的哲学思辨,将《诗经》六义分为三体三用,风雅颂是三种诗歌体裁,赋比兴是诗的三种表现手法。将郑玄时代比较模糊的认识明朗化。而且,对郑玄所谓“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关雎序》疏引郑玄《周礼》注)的比兴概念进行严肃批评,认为郑玄不敢直言,“有所嫌惧”,“嫌于媚谀”,从而用“美刺俱有比兴”纠正了郑玄的“比见今之失,兴见今之美”的偏颇观点;用“理自当然”的作文之体纠正了郑玄的“有所嫌惧”的错误认识,直接为当下直言切谏的政治和诗教张本,赋予比兴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有唐一代的诗文张扬了一面致用的旗帜。其文学和政治的意义自不待言。
(三)经义批评
引王肃为毛说,批评《毛传》的庸俗。《诗》学史上,有著名的郑、王之争,即,王肃以《毛传》为据处处与郑玄为敌,非其所是,是其所非,《毛诗正义》因此引王肃之说以为毛说。所谓庸俗者,指对《诗》的阐释非关义理,这是《正义》所要批评的内容之一。如:《小雅·甫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郑玄说《诗》,善于破字。《笺》云:“曾孙,谓成王也。攘读当为馕。馌、馕,馈也。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喜读为饎。饎,酒食也。”按郑玄的说法就是,成王出观农事,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为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馕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而王肃则另立新说,云:“曾孙来止,亲循畎亩劝稼穑也。农夫务事,使其妇子并馌馈也。然田畯之至,喜乐其事,教农以间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莱,尝其气旨土和美与否也。”《正义》因毛氏于诗无破字之理,不与郑同,便以王肃为毛说。王肃又以“妇人无阃外之事”来否定妇为成王之后。王肃说田畯看到农夫的老婆孩子带着饭菜来到田间,于是非常高兴云云,非关义理,是较为庸俗的。而郑玄说成王使世子知稼穑之艰难,立意高远,关涉王教。两相比较,显然,《正义》支持郑说,并反复批评王肃等说不合理:(1)根据《诗序》,郑玄之说与“伤今思古”的主旨相合。(2)根据语境,从整首诗的几章内容来看,从与《大田》卒章的关系来看,“不当以农人妇子辄厕其间”;而且,从句间的语法逻辑关系来看,上无农人之文,下即不得为农人妇子。仅就此端而言,王说则不通矣。(3)根据古礼,以王与后于田蚕之农事有外内之别,职司之义,来反驳王“妇人无阃外之事”的说法。以上三点,《正义》逐层说明王肃的错误,目的是对王教的张扬。《正义》云:“王者忧深思远,以世子者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故与之俱行,知稼穑之艰难,欲其重国用而爱黎民,保王业而全宗祀也。以子所亲,莫过于母,使之俱观辛勤,内相规谏,此圣贤明训,可与日月俱悬。”
《正义》为什么在这里如此强调王者使世子知稼穑之艰难呢?《正义》的话语里有潜在的时代因素,寄寓着初唐王朝的政治理念。因为唐太宗曾反复叮咛孔颖达和于右宁劝谏承干太子,使知稼穑之艰难。有史料为证,《四库全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十载:
帝谓志宁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盎之子姓艰难,耳目所未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4]。
孔颖达性格忠直,直言敢谏,曾多次面折承干太子,显然,《正义》所言正是太宗皇帝的反复叮咛嘱托;可以说,《正义》的立论完全是从唐太宗王教的现实出发,将极谏太子和贵族子弟的精神贯彻到《诗》教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正义》严厉批判王肃(实则批毛)的庸俗不合理,我们也因此更可见《正义》说《诗》的现实指向性。
别取新说,尤见批判精神。皮氏议孔疏之失,“不取异议,专宗一家”[1]P142,斯不然矣!《正义》有时也在毛、郑之外别取异说,而使新意叠出。如:《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云:“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云:“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毛、郑都将公子理解为男子,只不过阐发的经义不同。王肃申毛说:“豳君既修其政,又亲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归也。”如此理解,虽然有关教化,但是,好像与上文“女心伤悲”没有关联。而郑玄则理解为女之思嫁,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虽贵贱有异,感气则同,故与公子同有归嫁之意。虽然与上文联句而释,又参阴阳感气之说,但是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仍然难以捉摸。也许正考虑到毛、郑之说不谐,《正义》另取它说:
庄元年《公羊传》说筑玉姬之馆云:“于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是诸侯之女称公子也。
《正义》从《公羊传》的记载中,发掘出“公子”的新意,将公子视为女子,既别于传,又异于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在将此说至于毛、郑之后,却戛然而止,不再申说,或许《正义》认为“诸侯之女”的解释,更能圆通语意。但《正义》的阐释体例,只释经注,不释引文,亦不自我发挥,所以只得将新解寓于引文之中,聊备一说耳。《正义》对毛、郑的这种批评态度是极为含蓄的,也许是不经意的,但是对后人却影响极大,尤其是对于顾颉刚、余冠英等现代学者。清代学者全祖望批评《正义》说:“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汉、晋经师异同之说,删弃十九,令后世无所参考。愚尝谓《正义》出而经学隘。”(《全祖望集·唐孔陆两经师优劣论》)[6]P1532仅此而言,祖望之说未为定论。
以上我们考察了《正义》对权威《传》、《笺》所作的批评,举凡九类,大致分为文献、文学和经义三个方面,其所涉问题之多,内容之广,充分说明《正义》不仅尊重传统,而且亦具批判精神,而不是单纯地拘泥于传统,从而否定了《诗》学史上“疏不破注”的说法。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饶有兴味的启示——
《正义》的阐释原则具有多元性。“疏不破注”只是后人的界定,对于《正义》而言,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不是一个绝对严格的概念。导致“疏不破注”偏狭传统观念的原因有二个:第一,以偏概全,只看到主要方面,忽略次要方面。如一篇题为《〈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的文章[7]P48-53,从六个方面说明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其实这只是运用了不完全归纳法,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第二,相信权威,人云亦云,心中常常忽视文本的存在。对待研究的对象,我们应该通盘考察,综合分析,次要方面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往往与主要方面相辅而行,共同说明问题的本质;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次要方面有可能会转化为主要方面。陈广恩的《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8]P64-66,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认为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角度较新,立论较为客观。总之,抛开次要方面,我们有可能会失去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正义》对传统的批评立足客观。《正义》对于毛、郑的批评,绝非凿空之说,亦非标新立异,基本上是立足现实,或是根据大量的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证,或者是从文本语境和生活经验进行缜密的推理,从而纠正了毛、郑错误或片面的认识,丰富了经学思想。因此,这种批评是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经学健康、良性的发展,因为,在客观求是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经义更具有现实性和权威性。
《正义》的本质是经学的政治实践。《正义》虽然建立在诗的文本之上,它的本质却首先是经学的,从它的批判内容和精神,更能看出它的实践指向。《正义》对所选之注,基本上是回护、引申和发挥,但是当注出现基本的文献错误,影响到经典权威的时候;当注的思想庸俗、狭隘,服务于政治的力量削弱的时候,《正义》则要对注加以改造、修正、补充,甚至是批评,从而使经典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其中贯彻着皇帝和当权者的政教思想,寄寓着孔颖达等编撰者的政治理想。因此,经典起着陶铸君臣人格,规范人伦秩序的作用。
《正义》的批评表现了一定的文学进步。《正义》的本质虽然不是文学的,但是,它的经义必须附着在《诗经》文本之上。《正义》的文学进步是,相对于将经义与文本较为背离的毛、郑等以前的经学家而言,《正义》更注重经义与文本之间的联结点,因此,《正义》往往能够从文本出发,考虑到文本自身的特点,这时候,《诗序》基本上不再是唯一的阐释依据,诗的特点便凸现了出来。如上所论,诗来源于生活的问题,《正义》已经触及到诗的意象和典型性。《正义》发现诗意的典型性,诗情之所以能够感动大多数人,就是因为诗人之意是“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的。正因为诗意具有典型特征,所阐发的经义才更具有权威性。这对于唐代陈子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人的诗论和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启发[9]P73-76。又如,关于诗的作者问题,《正义》是想通过纠正《诗序》“国史说”的简单化判断,说明经义普遍性价值,客观上却揭示出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性特征,深化了对文本的认识。再如,《正义》对于郑玄“有所嫌惧”的比兴观的批评,要求作文之体理当自然,赋予比兴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有唐一代的诗文创作指明了方向。此外,通过批评毛郑对《采葛》诗意错误的理解,说明了解诗歌声韵的作用。《正义》的目的不在于张扬诗歌的形式主义文风,而是说明了形式对于表意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引导了唐代诗歌声律的健康发展。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正义》在阐释经义的过程中,正是基于对文本的尊重,不仅丰富发展了经典的政教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诗歌的文学本质,其贡献可谓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