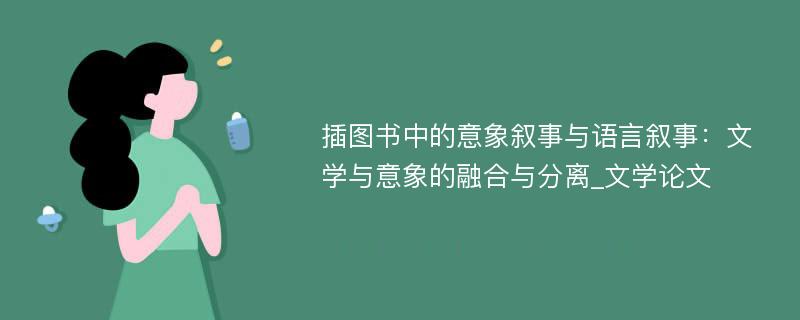
插图本中的图像叙事与语言叙事——文学与图像的融合与分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语言论文,插图本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像与文学的争论由来已久,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特别是数码、多媒体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及文学与图像互相融合产生的“超文本”形态,不仅给读者带来了全身心的审美感受,也为我们思考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对话以及它们与传统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新问题,同时也为图像与文学的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多理论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图像与文学之间的巨大张力,如海德格尔就认为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技术时代”,更是一个“图像的时代”。①罗兰·巴尔特也指出了这种由词语占据主导地位到形象占据主导地位的转变。②甚至有些理论家认为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如希利斯·米勒就担心文学的时代已近结束。③然而新时期图像与文学的密切结合并没有为我们理解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提供新的根据,特别是对如何理解目前广为流行的插图本中的语图关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插图本目前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它充分说明了一个艺术史的老问题:图像充分展示了语言所无法具有的功能,这是视觉艺术本身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的根本精神需求,甚至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插图本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史的老问题,不过由于今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审美观念的变化为插图本的流行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可能。插图本中图像与文本的关系首先是孰先孰后的问题。如《圣经》的语言文本是先于其他文本而在的,也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新约·约翰福音》1:1-2)这个根本原则导致了圣经传统中图像文本对语言文本的依附与对立,历史上圣经绘画的巨大成就与对圣像多次的破坏运动都是这种矛盾态度的直接表现。在神学家看来,《圣经》的各种插图或图示既是对《圣经》的解释,也是对《圣经》的背离。当然圣像的破坏也与《摩西十诫》中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仿佛什么形象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密切相关(《旧约·出埃及记》20:4-5)。佛像的产生也是一样,虽然造像与佛陀的基本理念是相违背的,但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使佛像得以产生。吴黎熙在《佛像解说》中说:“有什么能比给佛陀造像以代替其预期的权威,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法呢?”绘制明了易解的图像乃是宣传学说的内在需要,完美的艺术形象同样能充分展示佛教语言所竭力追求的固守自我、忍受一切、内外合一的大解脱者的精神形貌④。因为视觉信息与视觉愉快乃是人的内在需要,对图像的视觉感受与对外在世界的直觉感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语言较为高级也无法代替。理查德·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就认为语言对现实的“指称”(reference)更多的是“谈论关于”(talking about)⑤。波普尔也认为:“与探索真理相比,探索逼真性是更清楚,更现实的目标。”⑥虽然《摩西十诫》中规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但丁也在《神曲·天堂篇》借助俾德丽采之口说,凡人只能借助语言并仅凭感官来理解圣经,使上帝具有手足,因此他们的理解就降低一层⑦。但神以人的形象出现乃是因为人的感受力与理解力的局限,人必须借助这些可感知的形象才能更好地感受到神的存在及其意义。人很难从语言上感到上帝的存在,但可以从教堂的图画与雕塑中感受到。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希腊的前辈们在依据基督教学说拒斥《旧约》圣经对绘画的敌视时,已经运用了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在上帝的化身成人中看到了对可见现象的基本认可,并因此为艺术作品赢得了某种合法性。”⑧中国人在宣传基督教时也采用了插图的方式,如明万历二十二年刊《程氏墨苑》中根据利玛窦赠送的基督教绘画中复刻出的《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副绘画,都说明了中外共通的问题⑨。这也正是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包括意大利的乔托、德国的丢勒、法国的陀莱、英国的布莱克等为《圣经》插图的根本原因。不仅《圣经》,没有乔托《但丁在天堂》的插图,没有雕塑家波尔格萨尼制作的但丁半身像⑩,我们对但丁就没有什么图像上的印象,更不要说《神曲》中迷失在黑森林中的但丁、俾德丽采、维吉尔,阿刻隆的渡船、地狱判官迈诺斯、自杀者的森林等等了(11)。
笔者并不认为图像能够代替语言,也不认为语言可以代替图像,图像同语言一样有高低之分,并不是所有的图像像目前文学理论者所宣称的那样都是扁平无深度的,只要是熟悉古希腊艺术,甚至中西伟大艺术作品的人都不会认为所有的图像都是浅薄的,插图本也是一样。很多伟大的艺术大师,如丢勒为《圣经》所作的插图,特别是他的著名的《四使徒》更是显示出绘画所特有的对人的精神甚至灵魂的冲击力,有些是语言无法表达的(12)。霍尔拜因为马丁·路德所译《圣经》及伊拉斯谟《愚人颂》所作的插图,威廉·封·考尔巴哈(Wilhelm von Kaulbach)为歌德《列那狐》所作的形象拟人、栩栩如生的插图,马奈为爱伦坡的《乌鸦》所作的插图,艾里克·吉尔(Arthur Eric Rowton Gill)为《圣经·雅歌》所作的精美绝伦的插图,约翰·丹尼尔(John Tenniel)为《爱丽丝漫游奇景》所作的妙趣横生的插图,布歇为奥维德的《变形记》、薄伽丘的《十日谈》的插图,威廉·布莱克为《约伯记》及但丁、弥尔顿作品的插图,比尔兹莱(Aubrey Beardsley)为王尔德作品的插图,德拉克罗瓦为《浮士德》的插图,亚瑟·拉克姆(Arthur Rackam)为《彼得·潘》、《仲夏夜之梦》、《爱丽丝漫游奇景》、《尼伯龙根之歌》、《格林童话》等所作的插图,毕加索为巴尔扎克《玄妙的杰作》所作的插图,吉尔伯特为莎士比亚戏剧的插图,鲁迅收藏的陀莱为《圣经》、《神曲》、《唐吉柯德》、《十字军》所作的插图,杜拉克(Edmund Dulac)为《一千零一夜》、《鲁拜集》还有中国官场风俗所作的插图,罗伯特·吉宾斯(Robert Gibbings)为柏拉图的《斐得若》、福楼拜的《莎朗波》所作的黑白分明、突兀奇崛的插图等,都是插图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再如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为荷马史诗所作的插图,当荷马史诗描写到赫克托尔在出征前向安德洛玛克告别时,“一个女仆跟随在后面,怀中抱着像星星一样灿烂的幼儿。父亲对着幼儿安静地微笑,安德洛玛克却泪流满面,温和地握着他的手”(13)。弗拉克斯曼简洁单纯、质朴严谨的“轮廓线”插图准确表达了荷马史诗所特有的一种原始的美(14)。当我们想到插图时不能仅仅想到目前街上流行的一些简单的、粗制滥造的文化快餐,更应该想到这些伟大艺术家呕心沥血的艺术作品。有些理论家对比亚兹莱为王尔德《莎乐美》的插图提出异议,因为其插图中的很多细节与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并不一致,甚至增加了很多细节。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细节而过分责备比亚兹莱,因为拙劣的插图是对文本的依附与解释,而卓越的插图则是对文本的合作与超越,是两位艺术家为达到一个共同的审美理想而努力的结果。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插图珍藏本诗集《鲁拜集》正文插图共十幅,其中以男人、女人、酒为共同主题的有六幅,以男女谈情为主题的七幅,以男人独自饮酒为主题的三幅,男女骑马谈情无酒的一幅。从这些简单明了的插图就可准确看出《鲁拜集》的基本主题。正如编辑出版此诗集的美国诗人路易斯·安特迈耶所说:“它不仅是一部诗集,它已经成了一个口号,一个反叛的象征,一个有韵律的反抗,针对一切装模作样和僵化刻板。”(15)由此可见,插图与诗歌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存在,正如歌德所说:“德拉克洛瓦比我自己想得还好。”(16)这也是所有伟大插图画家所共同努力的方向,比亚兹莱在提到他给《朱文诺6号》的插图时也曾说:“我努力将它的翻译和插图做得一样优秀。”至于他为《莎乐美》所作的插图就使王尔德担心自己的文字沦为比亚兹莱插图的插图(17)。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先于Arthur Rackham,Edmund Dulac,甚至是Paul Woodroffe的插图,但这并不意味着莎士比亚的语言文本《暴风雨》就先验地超越于三位插图画家的图画文本之上,更不意味着读者在阅读时必然遵循着艺术品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决定欣赏轻重的次序。优秀的插图本把图画艺术与语言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追求真善美。圣格雷戈里说:“文学作品使得未开化者通过阅读而明事理。同样,绘画也能发挥这种作用。”波希格里芙在谈到著名的切法卢天主教堂时说:“当你看到这些巨大、恢弘的人物时,那种神圣的感觉依然近在咫尺,你仿佛被笼罩在一种庄严肃穆的神秘气氛中。你甚至想弯下腰来颂扬。”她在评价安吉利科的画时说:“安吉利科的画中透露着谦逊、亲切及虔诚。凝视这些虔诚的画可以让修士时时记住信仰的神圣性。”(18)绘画同样是一种视觉的警醒,它时刻提醒着观看者的心灵,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与归宿。因此傅雷认为伦勃朗的绘画能“使我们立刻远离现实而沉浸入艺术领域中”(19)。艺术家所表现的这种超凡脱俗把观者带入一种更伟大、更崇高的艺术境界,而这种艺术境界是所有伟大的艺术,包括文学、绘画与音乐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与绘画不过是一种使人不断超越自我的手段。
中国传统的图文一体的艺术也是如此,敦煌的佛经插图、北魏的摩崖造像(20)、北宋文人的诗画一体、明清时代的各种戏剧小说插图本,甚至鲁迅为自己的作品所精心策划的各种插图,齐白石受老舍之嘱为查慎行、赵秋谷、苏曼殊等人的诗句如“蛙声十里出山泉”、“手摘红樱献美人”、“几树寒梅映雪红”等所作画作早已经成为绘画史上伟大的艺术作品。(21)郑石岩在为蔡志忠的漫画《禅说》所作的序中说,蔡志忠的漫画是禅学的“象征式语言”,“最能引导一个人脱胎换骨的教育方法”(22)。我们并没有觉得阅读这些伟大的插图本会丧失我们理性的光辉,它们并不是酒酣耳热的产物,而是艺术家整个艺术生命的结晶。所谓“图像使人浅薄化”都是对这些伟大作品审美与理论意义的忽视。鲁迅写作《连环图画辩》、《连环图画琐谈》等反复讨论语言与插图之关系,可见其重要性(23)。郑振铎在1927年的《插图之话》和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指出了插图的现实意义,例如《红楼梦》第三回描写宝玉的外貌及穿戴,“束发嵌宝紫金冠”、“二龙抢珠金抹额”、“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但如果不借助图画的功能,今日的读者,即便当时的读者,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种服饰的贵族,也同样无法感受这种华美的服装与神采奕奕的贵族公子形象了。但读者却可以通过绘画本的《红楼梦》如清光绪间姚梅伯评本《石头记》中的插图来体会到。同样,如果没有陈老莲所作《屈子行吟图》中屈原清瘦颀长、沉吟傲岸在湖畔行吟的形象,今日的我们也很难想象到屈原的大致形貌(24)。
但插图本中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图像与语言的融合还是同一疆场上的纷争,它们在这场诗画时分时合的同路旅行中最终给作者、读者带来什么不同的审美感受呢?思考这个问题,莱辛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是无法回避的一部重要著作。莱辛曾得到历史上很多伟大理论家的称赞:康德曾出于对莱辛的尊重而反对人把他与莱辛相提并论(25),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一文中曾说马克思几乎每天都阅读莱辛与歌德的作品,马克思也在他的《自白》里把莱辛列为最喜爱的散文作家(26),歌德则曾在他的自传《诗与真》中谈到莱辛对他的深刻影响,并为自己因为年轻人特有的自负不愿去亲近莱辛而抱憾终生(27)。《拉奥孔》研究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图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媒介与语言的根本不同。首先莱辛对诗画艺术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区分。他在《拉奥孔》的一开始就说:“诗画无论从摹仿的对象来看,还是从摹仿的方式来看,却都有区别。”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当时的批评家对诗画区别的否认。莱辛认为:“时间上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绘画所采用的符号是在空间中存在的,自然的;而诗所用的符号却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人为的。”“绘画运用在空间中的形状和颜色。诗运用在时间中明确发出的声音。前者是自然的符号,后者是人为的符号。”由此来看,莱辛并没否定绘画艺术的成就,他主要是强调二者的区别,所以他说:“我所提出的艺术家们摹仿了诗人的假说并没有贬低了艺术家们。毋宁说,这种摹仿更足以显出艺术家们的智慧。他们追随诗人,却丝毫没有被诗人引入迷途。他们用了一个蓝本,但是在把这个蓝本从一种艺术转移到另一种艺术的过程中,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进行独立思考。他们的独立思考就表现在改变蓝本方面,这就证明了他们在雕刻艺术里和诗人在诗的艺术里是同样伟大的。”莱辛在对伟大的文学作品与伟大的绘画(雕塑)进行对比时主要是为了揭示二者的差别及各自的特点,并非完全在强调诗的优越性,并认为诗在任何时候都优于绘画。这也是莱辛清醒客观的地方。所以他认为绘画应该描绘“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这样便可避免空间艺术的局限,因为这一时刻“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这都是绘画的空间性特点决定的。他举出哈勒《阿尔卑斯山》中对花草的描绘:“描绘出来的,但是不能产生任何逼真的幻觉。我不敢说,凡是没有见过这些花草的人们从这幅图画里简直不能形成什么意向。”这不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先后承继性不适于描述物体的同时并存性,而是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象征性的符号,语言描述的东西无法在读者的头脑里还原为逼真的整体。这也就是语言的哈姆莱特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图画的哈姆莱特却不会产生任何的差别的原因。所以莱辛说历史学家玛拿赛斯在他的历史书中描写海伦时,他说:“如果有一千个人读这段诗,他们不就会想象出一千个不同的海伦吗?”不仅历史学家如此,即使伟大的诗人阿里奥斯陀所描写的他的心上人、维吉尔描写的“绝美的狄多”也是如此,因此莱辛说如果维吉尔被责问,他就会这样回答:“画不出他的美,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只怪我这门艺术有它的界限;应该称赞我谨守了这种界限。”所以他称赞荷马没有直接描写海伦的美,而是描写海伦美所产生的效果,因为在莱辛看来荷马明白语言相对于绘画所具有的界限。所以莱辛说:“宙克西斯画过一幅海伦像,而且有勇气把荷马描述惊羡的元老们招认所感到的情感的那些名句题在画下面。诗与画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竞赛。胜负还不能判定,双方都值得受最高奖。”在莱辛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要明确二者的差别,而不是要泯灭二者的界限而任意妄为。如果诗人欲摹仿画家,或者画家摹仿诗人,都是对对方领域的侵犯。最后他得出结论:“我认为一门艺术的使命只能是对这门艺术是特别适宜而且惟一适宜的东西,而不是其他艺术也能做得一样好、如果不是做得更好的东西。我发现普鲁塔克有一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谁若是用一把钥匙去劈柴而用斧头去开门,他就不但把这两种工具都弄坏,而且自己也失去了这两种工具的用处。’”因此在莱辛看来,最为根本的就是每个艺术形式都必须遵循自身的艺术规律,而不能越俎代庖,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如果艺术家不遵循艺术本身的特性及规律,忽视艺术媒介的特性以及它所必有的局限和要求,诗人和画家比赛描绘事物,而画家和诗人比赛叙述故事,那二者都将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敌手。他在给尼柯莱的一封信中说:“我只不过才开始研究诗和绘画的一个差别,这个差别起于它们所用符号的差别,一种符号在时间中存在,另一种符号在空间中存在。因此,绘画和诗都有两种,高级的和低级的。”莱辛关于诗画特性的区分已是理论界的常识,但笔者在此重提莱辛的基本观点只是要申明莱辛区分二者的根本特性并不是如朱光潜所认为“《拉奥孔》虽然是诗画并列,而其中一切论点都在说明诗的优越性”,他只是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对我们理解插图本中语言与图像的互异性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那就是:插图本乃两种艺术共同驰骋的疆场。当我们看到有些理论家对莱辛的指责时,就会想到莱辛对他的论敌温克尔曼的尊重,他说:“温克尔曼一个人举起了历史的火炬,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跟在他后面去进行思辨。”他认为温克尔曼的写作有“无限渊博的学问和对艺术的深广而精微的知识”,此外还有“高尚的信心与尽全力去探讨首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仿佛采取故意疏忽的态度”,他甚至把自己指出温克尔曼的一些具体错误当做“吹毛求疵”。(28)莱辛对论敌温克尔曼的尊重与他对诗画不同艺术特点的尊重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尊重发挥差异而不是取消,甚至是等级化差异。所以,玛丽·盖塞在《文学与艺术》一文中认为,“在大部分现AI写作作和绘画当中,莱辛讨论过的审美感觉原理仍然是适用的”(29)。某些现代小说家在采用新的叙述形式时充分发挥了小说的空间感觉的原理,但小说叙述形式的空间化仍与绘画的视觉形式不同,因为这些小说家仍然是借助语言来加以想象完成的。莱辛并没有绝对化二者的差异,正如汝信所指出的莱辛看到了二者区别的相对性,由于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因此莱辛还对两种,甚至是多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进行了理论的探讨,他认为把多种美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一种综合的效果,如他在《汉堡剧评》中就讨论了关于演员的艺术,认为演员的艺术乃是诗与画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甚至更接近于绘画。(30)莱辛对戏剧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电影作为图画与语言两种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现实意义。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体”的观点,《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韩干马十四匹》中“苏子作诗如见画”、《韩干马》中“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等都是诗画一体论的具体表述。其他如邹一桂《小山画谱》中“善诗者诗中有画,善画者画中有诗”(31),贺贻孙《诗筏》中“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32),王国维关于元曲的境界说与不隔说等都是此种理论的直接反应。然而诗画一体主要是指诗画的通感,也就是诗画在读者的内心所产生的意象与心理感受,这与插图本中诗画的共文与互文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它们是一种艺术形式所产生的两种艺术效果。然而正如阮阅《诗话总龟》中所说的“顾长康善画而不能诗,杜子美善作诗而不能画”(33),要完全达到诗画一体也只有诗画双能才行。这种诗画一体观念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表达了苏轼诗画平等的观念,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就准确地表达了文与可画竹子与轮扁斫轮及庖丁解牛一样都达到了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34)这种观念与他本人作为一个艺术家所特有的创作体验与审美感受是不可分割的,很难想象一个把诗歌的语言艺术放在绘画艺术之上的人会有这种结论。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苏轼对人性的根本理解:语言与图像的关联乃是人自身需要的确证。孟子所谓“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性也”。(35)《庄子》中盗跖所谓“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36)。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反复申明的“目欲”(37),都强调了眼睛的审美需要,《周易》更是阐明了“目见”乃是人认识世界之开始,《系辞上》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期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即用具体的卦象来表达对事物本性的认识,但语言在表达对自然万物深刻精准的把握时却常常“言不达意”。《易经·系辞上传》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38)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神思篇》讲:“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9)由此可见,中国古人也同样认为“象”的意义是不可取代的。当然中国传统诗画深厚的哲学底蕴及对价值超越性的直接追求,导致了苏东坡《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就是宗白华所说的“中国画违背了‘画是眼睛的艺术’之原始意义。‘色彩的音乐’在中国画久已衰落。”(40)陈师曾也说:“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41)但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解放与安息精神的作用仍然是一种绘画视觉艺术,而不是一种语言艺术。所以,从事古代文学理论的人往往从中国古代的诗画一体观念来反驳莱辛的《拉奥孔》,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就指出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标准的分歧这个历史事实。(42)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则明确表达了时间艺术高于空间艺术的观点。(43)在中西诗画的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史实往往容易忽略,那就是中西文学史中不同文体的发展有很大不同,中国古代文学史有强大的抒情传统,以诗歌取胜,特别是短诗,宏大叙事诗的缺失已成为文学史的常识,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一开始就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44)虽然明清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多被中国传统的诗画理论所忽视。西方文学则有着强大的叙事传统。中国古代的诗画一体观念正是以中国古代抒情诗,特别是较短的抒情诗为文学依据的,而莱辛的诗画观则是以西方强大的叙事传统为基本论述背景的,这是中西诗画观念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用诗画一体观来分析解读“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可谓一语中的,但在《红楼梦》这样的巨著前,这种传统的诗画观念就很难发挥它的效用了,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忽视这个文学史史实无论用莱辛的观点来解释中国诗画还是用中国的理论来解释西方的文学传统都显得方枘圆凿。当然,传统的诗画一体观念还有着诗画本是空间性的哲学观念作为理论支撑。其实诗词的空间性与绘画的空间性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空间感,它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是内视性空间感在读者脑中构成意境的审美过程。王昌龄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45)诗人用语言把经验的感受借助想象产生了心中的图像,而这些图像都是模糊不清的,它仅仅存在于诗人自己的心中,另一个人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去直接观赏,但画家的图像就可直接目睹。语言的图像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物质化存在,而是一种茵加登所说的“图式化外观”,一种由读者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内在形象。(46)从摹仿的角度看,语言的描述并不能代替绘画,孟超在《金瓶梅人物》中曾以强烈的个人感情对潘金莲进行了介绍与评价,但潘金莲的长相与神态到底如何还必须借助张光宇的绘画,虽然这两幅绘画是否符合《金瓶梅》的描写倒是另一个问题。(47)语言与绘画各自无论有怎样的优势,都无法互相代替。艺术虽然划分为语言和绘画艺术,但正如贝尔所说的:“在艺术之中,唯一重要的区别就是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之别。”(48)
总之,插图本中的语言与图像乃是根源于人的不同的感官,它们对人同样重要,我们必须以一种平等的精神来尊重这种不同艺术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差异,而不是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开始就强调了这种“对感觉的喜爱”是所有人的本性(49),对绘画的喜爱就根源于人的视觉。黑格尔说:“绘画所应采用的主要是可以通过外在形状来表现的东西”,绘画同样能“描绘人物性格,灵魂和内心世界”,画家的优点就是“他能描绘出一个具体情境的最充分的个别特殊细节,他能把现实事物的形状摆在目前,使人一眼就把一切都看清楚”。(50)虽然黑格尔最后仍然得出“诗比任何其它艺术的创作方式都要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因此,对艺术的科学研究似应从诗开始”的结论(51),但他对绘画特点的精彩分析告诉我们,图画相对于诗歌与音乐来说有它自身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是音乐与诗歌都无法替代的。诗歌能传达作者内在情感的无比自由及无比丰富的包容性是绘画所难以企及的,但在表达事物的外在形象方面,在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方面,语言又往往逊于绘画了。即使像电影这种完美地把画面连接在一起的艺术也无法像诗歌与小说那样自由表达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诗歌虽然具有强烈的绘画性,也就是描述性,但这种形象性与绘画的形象性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诗中鲜艳明媚的春天与宁静清冷的夜晚和真正的春天与夏夜不同,正如巴什拉所说:“诗人的形象是以语言说出的形象,而不是我们眼睛看见的形象。”(52)萨特在《恶心》中关于“星期五”那段对自己脸是“立体的月球,世界的地质学地形图”的描述(53),葛里叶在《橡皮》中众口皆碑的关于西红柿切面的描述(54),还有《伊利亚特》第十八卷中关于火神赫菲斯托斯为阿基琉斯制造的铠甲与盾牌的详细描述(55),都无法与绘画的脸、盾牌与西红柿切面相提并论,语言的造型能力与绘画相比更加需要读者的介入与配合,所以亚里士多德告诫文学家既要表现一种逻辑力量,又要有一个形象的感染力量,“使事物活现在眼前”(56)。但正如莱辛所说:“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描述事物所产生的“幻觉”再逼真都和画家的图像属于不同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画家与诗人一样不仅仅在追求照抄自然,而是追求理想,正如阿瑞提指出的,古希腊阿芙罗底特之所以“是女性美的典范”就在于她“更多是体现了对于女神的观念而不是对于实际生活里的女子的观念”。(57)所以威勒克在《文学原理》中说:“莱辛很可能是对的,他批评阿里奥斯托对许多女性美的描述缺乏视觉上的效果(虽然未必缺乏诗的效果)。”(58)语言无论从表达最本质的人的内在感受,还是在表达最高的真理都具有它的局限性。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画家与诗人一样都无法表达真理,因为“摹仿与真实体隔得很远”,否则艺术家“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59)。科林伍德就通过对国家概念的分析说明了语言的含混性。(60)所以伟大的艺术家都会超越语言的束缚,正如潘诺夫斯基指出的,丢勒与不懂希腊文的伟大诗人能超越译者来全面掌握索福克勒斯的著作。(61)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因此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仍然是一种语图完美结合的插图式文本,目前插图本的流行乃是艺术发展与人的内在需要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多媒体的发展,电影的发展更是插图本发展的更高级形式。虽然艺术本身的等级从未停止过争论,丹纳这种有着古典价值观的理论家自然认为艺术的等级是明显的,而克罗齐却认为艺术根本就没有等级(62),因此韦勒克评价克罗齐“把所有的美学问题都集中在直觉的行动上”(63),康德虽然在《判断力批判》中说“任何通过概念来规定什么是美的客观鉴赏规则都是不可能有的”,但他又认为鉴赏判断中必然存在着“共通感的理念”,最后同黑格尔一样认为“在一切美的艺术中,诗艺保持着至高无上的等级”。(64)无论这些伟大理论家对艺术的等级怎样判定,我们总不能认为一个普通的文学作品可以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或者一幅普通的绘画与《蒙娜丽莎》相比,虽然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克罗齐所谓审美者的内在感受。因此关于图画与艺术的争论的本质不是文学与绘画孰优孰劣,而是文学本身有优有劣,绘画本身有优有劣。从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标准来看,无论是图画还是诗都能反映真理,追求理想,但都无法达到完美状态。洪堡特说人类的现实“并非时时处处都与理想相符”,但人类的“文字作品、艺术作品和积极进取的行为意图中的精神,极其纯真、完整和协调地描述了人类高度自由地发展的可能范围”,这幅“理想化的图景”乃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所共同呈现出的本质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基本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艺术可以单独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65)语言必须与其他伟大的艺术一起为完成人类完美的自我塑造做出贡献。这其中电影作为图像与语言完美结合的综合艺术,也可说是更高级的语图一体作品,虽然它自身也有高低之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如巴赞所说银幕形象乃是“造型结构和时间艺术中的完美组合”(66)。德勒兹也说:“电影采用一种画面自动运动,甚至一种自动时间化。”“电影总是叙述画面的运动。”(67)关于这种“总体艺术”海德格尔则认为它会成为“民众的一个节庆与宗教”(68)。虽然我们在电影中也必须像德拉克洛瓦所说的那样,“凡是给眼睛预备的东西,就应当去看;为耳朵预备的东西,就应当去听”(69)。总之,尊重差异是我们能够欣赏不同艺术作品的首要前提,而插图本,包括电影则为我们提供了同时欣赏不同艺术的可能。
注释:
①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
②Rolan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in Susan Sontag,ed.,A Barthe Read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pp.204~205.
③王逢振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④赫尔穆特·吴黎熙:《佛像解说》,李雪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3页。
⑤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0~293页。
⑥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⑦但丁:《神曲·天堂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⑧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⑨任继愈主编:《中国版本——插图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⑩但丁:《神曲·炼狱篇》,插图一《但丁半身像》,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但丁:《神曲·地狱篇》,插图1~36,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12)丢勒:《版画插图丢勒游记》,彭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13)(55)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438~442页。
(14)(16)余凤高编:《插图中的世界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6、76页。
(15)莪默·伽亚谟:《鲁拜集》,郭沫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17)比亚兹莱:《最后的通信》,张恒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43、255页。
(18)波希格里芙:《基督教美术之旅》,彭燕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24、47~48页。
(19)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1~152页。
(20)徐小蛮:《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0页。
(21)齐良迟主编:《齐白石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6页。
(22)蔡志忠编绘:《漫画佛学思想》(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0~151页。
(23)《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4)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25)《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87页。
(27)歌德:《诗与真》,李咸菊译,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0页。
(28)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171、181~182、40、93、112~118、97~98、202、205、223、148、164、168页。
(29)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4页。
(30)汝信、夏森:《西方美学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105页。
(31)《画论丛刊》(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791页。
(32)《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33)阮阅:《诗话总龟》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34)《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6页。
(35)《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3页。
(3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9页。
(37)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19页。
(38)黄寿祺:《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526页。
(39)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3页。
(4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112页。
(41)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42)参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517页。
(43)钱锺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页。
(4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
(46)茵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6页。
(47)孟超著:《金瓶梅人物》,张光宇画,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48)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46页。
(4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50)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2、289~290页。
(5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52)加斯东·巴拉什:《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5页。
(53)柳鸣九编:《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152页。
(54)葛里叶:《橡皮》,林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166页。
(56)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4页。
(57)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页。
(58)(6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2、137页。
(59)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
(60)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61)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
(62)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248页。
(64)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4、172页。
(6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43页。
(66)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67)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7、69页。
(68)海德格尔:《尼采》(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
(69)《德拉克洛瓦日记》,李嘉熙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