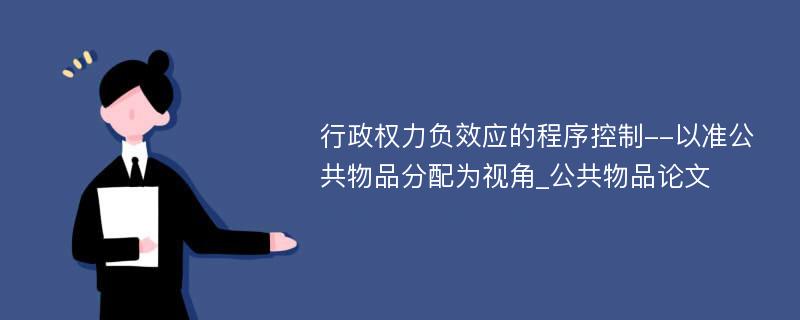
行政权力负效应的程序控制——以准公共物品分配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效应论文,视角论文,行政权力论文,分配论文,物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准公共物品的提出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公共物品的分析是其重要内容。其代表学者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具有不可分割性,即非排他性,而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则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关于公共物品的标准,早在1968年,布坎南就对萨缪尔森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认为俱乐部形式的存在能够通过一种收取费用的机制排除部分公共成员的参与。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公寓中共同使用一定数量的衣架,人们会想方设法的占用尽可能多的衣架,甚至只是为了占用衣架,而悬挂衣物。这就出现了,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浪费,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资源的稀缺是先天性的而不是由于浪费而导致的稀缺,换句话说,浪费并非稀缺的原因,而是稀缺的结果。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公共场地的占用,远远超过自己的使用能力范围,有时候为了避免抢夺而引发的争端,就采取了收费形式,导致了公共物品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出现。由于这些物品的排他与竞争,社会成员就不可能平等的享有,那么如何合理分配对行政权力的掌控提出了挑战。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现实,把行政权力的掌控者完全看作是“政治人”是不合适,也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正如西蒙所说,他们同样也只具有“有限理性”的社会中的一员,面对相对稀缺的准公共物品,他们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获得权力是防止被他人掠夺的最可靠方法。”[1](P263)由于准公共物品的特殊性质和权力掌控者的特殊心理,不可避免的使行政权力产生诸多负效应,这就是我们第2部分要论述的:行政权力的负效应。
二、行政权力的负效应
在讨论行政权力负效应之前,我们必须先给出行政权力的界定,它的定义,有过各种学说:汉密尔顿与杰弗逊的三权分立说;[2]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3](P10)还有议行合一,组织权力等学说,但无论如何理解行政权力,它都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总会出现不能有效行使其治理功能的状况,必然产生行政权力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权力争斗
由于准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使得对于准公共物品的分配权显得至关重要。而谁掌握分配权,如何进行分配,便成为权力博弈的重心,当这种博弈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很可能出现了畸形的模式,往往表现为分配者把行使公共职权当成是一种实现权力欲望的手段。当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存在于一个组织环境中,形成了公共部门的组织氛围,权力争斗就开始蔓延开来,并愈演愈烈。这已经明显的反映在行政人员中,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所抱有的政治理想,只不过是使其职业和职位逐步特殊化,为此,他们工作的重心不是通过实现公共部门的公共利益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在权力体系中勾心斗角,极力扩大所能触及的范围,以便占有更多的价值,获得更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受到本身能力和环境的限制,这种不择手段而获得的权力是勉强而为之的,往往不能胜任,又进一步加深了权力的负效应。
(二)权力的扩张与滥用
如果说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为行政权力的负效应提供了物质刺激,那么权力的扩张性则是行政权力负效应产生的主观动因。换句话说,准公共物品正是遇上了“权力”这个催化剂,才促使一系列行政负效应的产生,甚至加速行政负效应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P154)由于这种心理的作怪,权力不断扩张,终于出现了越界。不仅在权力使用上表现出不能胜任,在支配权力的着眼点上,也放在了尽可能的扩展、占用更多的公共权力资源,而忽略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即便有所关心,也只是次要关心,即摆在较为次要的地位,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低作为。
(三)权力特殊化
我们退一步假设,公共部门人员他们安守本分,不在行政序列中积极攀爬,也不处心积虑的扩张自己的权力行使范围,他们只是把所有关心放在自己所在职位上,那么又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为了能够在不损人的情况下利己,他们极有可能强化自己的权力,尤其对于准公共物品这种有利可图的物化政治资源,只要稍加规定,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独自掌控分配准公共物品的权力,久而久之,这种权力日益特殊化,最后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特权化。当然,这种特权化在不少情况下,并不是主观蓄意的。由于在行政层级结构中,为了保证整个体系的有序与规范,对于处理准公共物品的权力,必然由一些特定的人来行使,在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人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缺乏监督和规范的情况下,出现权力特殊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面对分配准公共物品中出现的行政权力的负效应,我们已经有了大体的框架。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这种负效应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则尝试从行政程序方面进行解释。
三、行政程序的法律保障
我们仍然要从根本的说起,翻开《法学词典》,程序法是“为保证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制定的诉讼程序的法律”。[5](P914)一般说来,行政程序具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实现的总合。行政程序一旦被法律所规范,即成为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法律上的程序权力义务,具有规范性、强制性,行政机关必须履行法定的程序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由于行政程序是设计好的法律规范,它就更侧重于对行政主体科以义务,赋予行政相对人以权力。更重要的是,在设计行政程序时,行政主体主要充当的是程序义务人的角色,行政相对人就相对的成为程序权利人。在这个控权和维权过程中,行政主体得到了控制,具体而言,行政主体权力受到了控制。可以说,行政程序在控权上体现了明显的法律保障作用。
(一)行政程序在资源公正配置中的作用
论及公正正义,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罗尔斯,按照他的观点,把“蛋糕做大”固然重要,但更应注意程序的公正。因为通过行政程序的公正可以获得行政结果的公正,即使结果不公正,但由于行政程序公正也能使法律正义得到实现。尤其面对准公共物品与权力之间的纠葛,程序原则是在两者权衡中实现公正配置资源的最佳模式:要排除偏见,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要体现公平,就应当让当事人申辩。随着政府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积极干预,行政权也迅速膨胀,权力的特殊化,使得不公平配置资源的机率大大增加,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合法的程序去规范,行政主体就很可能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恣意、滥用行政权力,使社会中资源的分配有失公允,同时也侵害了社会中个体的权利。而由于行政程序的存在,并且我们假定的前提是这种行政程序的合理合法的,行政机关在配置公共资源时,特别是配置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时,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在做出影响公民权利或者义务的具体决定时,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维护行政管理的权威,保证权力的公正行使,否则与法不容。
另外,准公共物品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过程中,很容易由于形式上的不公,引发公众与公共部门的矛盾,而程序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调解的作用。它能够使行政相对人和公众相信一个行政决定的事实基础是真实的,从而消除对行政决定的疑虑和抵触;退一步讲,如果相对人得知他被不公正行政决定所冤屈,做出与他有利害关系的行政决定并不根据可靠的事实,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裁决,但行政程序也已经给了他充分的自卫机会(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这种自卫敦促行政机关必须作出充分的公正努力,以保护该相对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仍然会给与行政机关理解,淡化与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反之,倘若程序本身是不公正的,即便查明的证据事实与客观事实吻合,而且行政决定也适用法律,相对人仍然可以怀疑行政决定的不公正。这在当今政府治理中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城市拆迁问题,各种行政费用征收问题,行政审批问题……可见,行政程序的不公正容易引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频繁出现政府与公众的纠纷,而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够合理公正的配置资源,培育并发展和谐的社会秩序。
(二)行政程序对实体法在控权上的补充
在合理调整准公共物品分配权的过程中,实体法做出了诸多法律控制,但由于实体法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尤其体现在降低行政权力负效应上的局限性,要求由程序法来做出补充。从程序法的词典解释上可以看出,实体法的内容是程序法的动因,程序法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实体法内容的实现,也就是说,程序法为实体法提供了工具。我们在分析权力负效应的部分已经得出,行政权力的行使最终离不开人的因素,这种特性导致了它在对待准公共物品特殊性的时候,即便不出现严重的违法问题,也极有可能产生法律的瑕疵,为了尽量减少这种行政人员的主观意志,弥补行政主体在施行实体法过程中出现的负效应,我们必须强调程序法:由法律为行政主体设定轨道,规范行使行政权力的环节。具体而言,当实体法是“不良之法”的时候,正当性程序能自动的、本能的纠正或削弱它的“恶性”,使之变为“良性”而作用于个案;当实体法本身是良法时,程序能自然的、稳定的保证其良法的性质而融入个案,实现正当的法律目标,合理分配准公共资源。比如当行政主体在行政许可、行政征收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寻求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行政程序的信息公开制度,诸如听证制度,使得行政主体通过各种实体法作用于行政客体的时候,必须接受程序法的控制,面对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也是为何近来政府频频举行水电费,门票价,车票价等价格听证会的原因。
当然,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有一个正当与否的问题,实体法规定的内容的确有赖于公正的程序法的实施,但我们绝不可因此而过分看重程序法,也就是说,公证的程序只是产生公正结果的必要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辅助性的,即辅助实体法功能的实现;在例外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填补性的,即在没有相应实体法适用于个案时,允许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遵循程序法的规定造法。所以,我们强调程序法的原因是基于准公共物品的存在,实体法无法提供足够有效的规范降低行政权力在运行中的负效应,而程序法恰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在很多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三)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作用
以上所谈的“公正配置资源”和“对实体法的补充”都是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讨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但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约束力,是被动的达到消极控制的效果。对于准公共物品,既然它是公共物品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受用主体应该是公民,实现分配的公正合理性的根本带动力在于民众,掌握它科学分配的主动权也应握于受用主体,这才是从本质上降低行政权力负效应的长久之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可以有各种途径,但都不得回避其中有关程序的内容,不能忽视行政程序在民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
行政权力的负效用之所以能泛滥并深化,与它所拥有的行政工具等一系列强大的行政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面对着这强势力量,个体公民似乎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公民有着能与权力抗衡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更多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影响范围和重要性都要比行政权力远远大的多。这种公共权力在公民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以个人的民主参与来保障公民自身的权利,这一系列的民主参与实质反映的就是行政程序的参与作用。不仅程序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呼吁和保证民众的参与,其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就是民众的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法律的优化选择,使准公共物品的配置不仅公正合法,并且科学合理,最终实现分配结果对行政相对人有利,也反过来使行政主体获益,从源头上降低了行政权力的负效应。这种控制行政权力的所采取的视角反映了现代行政程序设计的普遍趋势,通过扩大参与来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目的,它弱化甚至改变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客体地位,而扮演行政程序中积极参与的角色。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选举,民主谏言,村民自治(仍把村一级看作政府组织)等,都在分配准公共物品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效用,可以说“参与原则的主要优点是要确保政府尊重被统治者的权利和福利。”[6]因为有了参与,才使行政相对人能够在程序过程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使行政主体的包括配置准公共物品在内的各种行政行为在法定范围内有所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