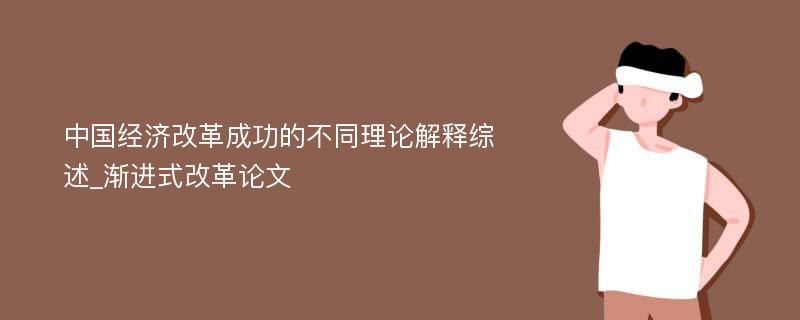
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不同理论解释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中国改革的成功为“中国之迷”,(注:诺兰:《中国后毛泽东主义政治经济:一个迷》,《对政治经济的贡献》,1993年12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说明。近几年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成功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文献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本文拟对各种解释作一综述。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内部条件和后发优势
以新古典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和内部条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渐进主义发挥了特别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允许足够的经济自由,从而最好地利用了中国的结构。他认为中国的成功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的结构状况与前苏东国家不同。改革之初,中国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大约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8%左右,70%的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是自由化过程中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过渡的典型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常的经济发展比结构调整要容易。大量不享有国家补贴、急盼流动的剩余劳动力为新的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如果中国的国有部门就业比重不是18%,而是像波兰、苏联那样是80%、90%,则中国的改革也不好办;二是改革之初中国的金融相对稳定,没有严重的外债。(注:萨克斯、胡永泰:《中国、东欧、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因素》,《经济政策》,1994年4月。)
世界银行把中国获得改革成功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一旦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 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 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同时,当放松对小公司的控制后,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很容易取得优势。(注: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丛书:《九十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第4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马丁·雷瑟认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应归于有利的内部环境,即中国在非常稳定的形势下进入80年代,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结构较接近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高度工业化的东欧,中国政府的政治权威没有被破坏,反而使得改革的主张容易接受。(注:马丁·雷瑟:《谁该吸取教训?社会主义中国和可比较的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共产主义经济和经济转变》,1995年2月。)
钱颖一等人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于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 中国改革以前是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即“M”型结构),在“M”型组织中,基层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这种结构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市场活动,刺激了市场取向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注: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0期。)
中国改革成功还有一个因素是后发优势。根据发展水平趋同论,落后经济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栗树和把“后起者”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起点(不是指决定因素)。
有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以上提到的初始条件、内部条件和发后优势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樊纲认为被压抑的非国有部门和落后优势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条件。(注:樊纲:《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宇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有利的初始条件有一定的关系,但改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觉的行为,是各社会集团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初始条件只是改革的一种外部环境,它不可能决定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也不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在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改革成败的关键还在于改革道路本身合理与否以及改革者的组织协调能力。好的初始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改革的成功,而不利的初始条件也不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而且初始条件也是相对的,还要看人们如何利用和使用这些初始条件。(注: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军认为,对于改革本身来说,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外生因素,而外生因素不会成为影响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它会与一些内在因素相互作用。(注: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西方经济学界,诺顿、(注:诺顿:《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从改革到增长》,法国巴黎发展中心OECD,1994。)麦金农(注:麦金农:《社会主义经济渐进还是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世界银行年会1993年关于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会议。)等经济学家反对萨克斯等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乃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
(二)中国改革成功是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是策略运用的成功
这种观点把渐进式道路作为改革的外生变量,政府选择的战略是外生的。林毅夫、蔡昉、李周指出,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内生出“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诺顿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它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把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概括为:双轨制的运用,经营绩效指标从数量型转为效益型,计划逐步向市场转化,最初的宏观稳定,宏观波动的不断持续对经济的长期市场化助了一臂之力,私人储蓄的增加使储蓄和投资维持较高的水平。(注:诺顿:《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从改革到增长》,法国巴黎发展中心OECD,1994。)
很多经济学家对价格双轨制给予足够重视。价格双轨制是代表一种既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入市场体制的折衷,通过“变大震荡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轨也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成为可能。麦金农认为,由于在改革初期阶段,中国在国有部门实行了价格双轨制,使得中国的改革避免了“通胀税”,而这个价格双轨制的做法也应该在其他过渡经济中被采纳。(注:麦金农:《社会主义经济渐进还是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世界银行年会1993年关于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会议。)“双轨制”最初出现在价格领域,后来事实上应用于改革的许多领域。“双轨制过渡”,可以视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式,即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首先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新体制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加大,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全面过渡。所以“双轨制”改革,人们又称“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相当于经济上讲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注:盛洪:《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
张宇认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道路,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它具有许多优点,如:体制外发展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动力,从体制外入手改革显然比体制内获得突破容易些;在不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发展非国有经济,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国民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促动,减少改革的阻力,避免“休克疗法”的经济后果。(注: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军对“双轨制”作了深入研究,并将其模型化、 数学化。 (注: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有些经济学家则从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美国的德怀特·帕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东南亚一样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农业改革的成就,实行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建立了经济特区,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调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加强了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另一方面市场因素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注:德怀特·帕金斯:《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吗?》,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版。)
(三)中国改革是内生的并从改革成本等方面入手的“渐进式改革”
樊纲认为,任何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一个“外生”的、由战略或政策明智程度所决定的政府行为,而是一国经济中“内生”的社会过程,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关系;政府行为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不过是经济与社会体系中一个内生的、特殊的利益主体,抽象地看改革方式并无优劣之分。经济改革中存在着两种成本,即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是“激进程度”的增函数,不同条件下改革方式的选择不同。在中国特有的初始条件下,选择渐进式改革更合适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初始条件内生出渐进式改革方式。(注: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0期。)
张宇不同意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激进程度”的减函数,他认为这个结论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渐进式改革同样也有利于降低实施成本,原因是:(1)在“试错”中学习,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 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2 )渐进式改革避免了信息和组织资源不必要的破坏和浪费,降低了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3 )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信息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人所掌握的,因而分步骤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能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改革收益。(注: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姜洪从渐进改革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来讨论这种方式给中国改革带来的成功。他认为市场经济十分需要稳定的秩序,而渐进式改革相对来说能保持稳定;渐进改革有利于培育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注:姜洪:《经济渐进改革的合理性》,选自《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渐进式改革”的提法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异议。吴敬琏认为,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中国的改革方式体现在中国改革的战略方针上,而改革的战略方针先是体制外改革,后转到改革国有经济体制本身。中国的改革战略不是渐进主义的,而是非常激进的。例如两年内实现了农村承包制,“五年价格闯关”等。(注: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承先从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出发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注: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晓西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与激进相结合,“渐进”是中国改革诸多特点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特点,他认为区别中国改革与苏东改革,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主导的改革道路,苏东走的是政治主导改革道路。从本质上讲,中国的道路是东亚模式,而苏东则是没有成功先例的独特的苏东模式。(注:李晓西:《渐进与激进的结合: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改革的道路》,选自《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孙来祥则认为:“大跨跃”式改革并不代表失败和混乱。(如越南改革);“渐进式改革”并不必然成功。(如50年代开始改革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俄罗斯虽然宣称进行“休克疗法”,但并未真正实施。总之,对复杂的由多种合力共同作用促成的社会变革的抽象和归纳必须严肃、认真和忠诚于历史。(注:孙来祥:《对一种“社会共识”的质疑》,《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
(四)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对经济理论的挑战
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追求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上还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是指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政府拥有大部分或全部生产方式,但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西方典型市场经济的四个特征:私有制、完备的法制、崇尚个人主义、多党制,中国经济体制却包含着: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共存、半法制化、崇尚集体利益和一党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证明,这四个方面并不意味着没有效率,相反,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富有一定的效率,这给现代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注:格里高利·周:《中国经济体制挑战经济理论》,《美国经济评论》1997年5月;伊特维尔、米尔盖特、纽曼主编:《经济学词典》、 伦敦迈克米兰,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