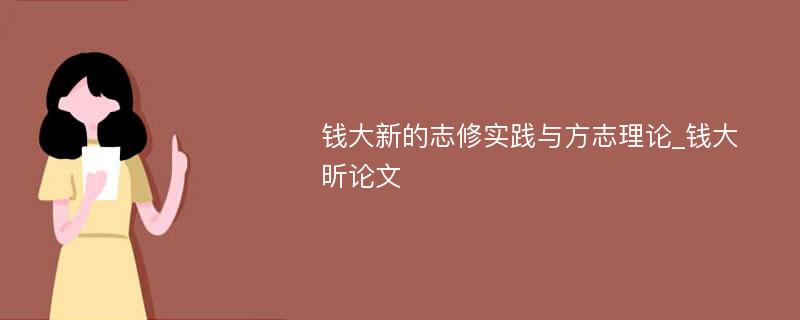
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论文,钱大昕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乾嘉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编修地方志形成热潮,我国古代方志学理论趋于鼎盛。钱大昕身处这一时期,参与过志书的修撰,评论过志书,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方志学理论,与以戴震为首的地理派(亦称旧派)和以章学诚为首的历史派(亦称新派)在方志的性质、方志的编撰等等方面的看法主张均有所不同,独树一帜,卓然一家,很多见解在今天的修志活动中,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钱大昕的方志学说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他的方志学说时,决不能脱离开他的史学思想。只有和他的史学思想相联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他方志学说的精髓。
钱大昕有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乾隆二十一年,与纪昀一起奉旨修《热河志》,馆阁中有“南钱北纪之目”。①乾隆三十六年,充《一统志》纂修官,重修《一统志》,并撰有《与一统志馆同事书》,说明自己对修志的一些见解。乾隆五十二年,鄞县令钱维乔延请钱大昕为《鄞县志》总纂,修撰《鄞县志》三十卷,“是志考核精当,体例尽善”。②嘉庆六年,长兴县令邢澍延请钱大昕与其弟钱大昭合修《长兴县志》,体例由钱大昕拟定。除了亲自参与修撰地方志外,钱大昕还在《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及其它著作中,对宋、元、明各代各种类型的方志约35种进行了评论,对这些方志的版本、卷数、撰者、刊刻流传情况、内容、编撰的优劣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评论与他的修志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方志学说。
钱大昕的方志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方志的性质——“为一方之证信”,“足备一方之文献”
方志的性质是方志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方志的起源、方志的作用等许多问题。当时戴震与章学诚在这一间题上辩论激烈。戴震认为方志为“地理之书”,应详古今地理沿革,所谓“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③轻视文献。章学诚则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史”,所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④强调文献的重要,但有轻视地理沿革的倾向。对此,钱大昕提出了自己对方志性质的看法,即方志“为一方之征信”,“足备一方之文献”。⑤他曾说:“志之为言识也。《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其志之权舆乎。”⑥钱大昕追潮方志起源,说明方志是对一地认识的记载,包括历史、地理、政事、风土等内容,是综合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并征而有信的载体。
对于方志中的地理沿革与史事叙述,钱大昕都是极为重视的。他认为方志于一方之地理沿革变化,应该了如指掌。他辨黄浦非以春申君得名,⑦辨鄞县非以秦始皇神将王鄞而得名,实以盛产赤堇而得名;辨小江湖非西湖,甬桥非甬水桥,⑧等等,俱皆精审。他在《养新录》卷二十中指出“吴郡志沿革之误”,他对韩浚所修《嘉定县志》忽视舆地,错谬百出极为不满,亲自调查清楚,一一驳正,足见他对志书所载地理沿革变化的重视。钱氏谙熟于地理沿革,凡所举正,言皆中的,而且,他认为志书记载地理沿革,会对史书起到补充作用,他在评论《舆地纪胜》时曾说:“此书所载,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统之旧,然史志于南渡事多阙略,此所载宝庆以前沿革,详瞻分明,裨益于史事者不少”。⑨认为地理沿革有益于史事。
同时,钱大昕也十分重视志书中史事的叙述,他认为要以编撰国史的态度编撰志书,修志要“以列传为重”。⑩从他对历代所修志书及历代所修《鄞县志》的辩证与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同意章学诚“志属信史,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这一见解的。他在修《鄞县志》时所作的三十条辩证中,绝大多数属于史事及历史人物的考证,如《王修非鄮令》、《朱文公未尝至鄞》、《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等等。他在评《江西通志》时,指出此志《选举门》“载元时进士题名,皆诞妄不足信”,原因就是“志所采者多出于家乘墓志,凡曾应乡举者,皆冒进士之名,而修志者不能别择也”,“是并《元史》,全未寓目”,(11)对于史事不究心,造成了重大错误。
钱大昕之所以重地理沿革又重历代史事及人物,都是基于他方志“为一方之征信”这一思想基础的,但他又不是方志理论中地理派与历史派的折衷,他更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在“一方之征信”这一基础上,“备一方之文献”,占有最充分的资料,留下最可信的资料,既重古籍,又重采访,力争志书传世。不载空言,翔实可靠,具体而微,使一方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资料尽数网罗于志书之中,钱大昕对方志性质的见解,已使方志越出了“图经”的概念,又使方志不同于“历史”的概念。他重视方志对文献的保存及征信,是和他“史者,纪实之书也”(12)的史学思想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方志的作用——“志无论小大,皆道之所在”
对于地方志的作用问题,当时的人们都提出了不少见解。钱大昕认为“志无论小大,皆道之所在”,(13)这里的“道”是“资治之道”和“教化之道”。钱大昕把志书看作官宦,特别是地方官治政的必读之书,他批评地方官“视其官如传舍,公事以吏为师,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噤不能出声”,对所辖州郡疆域、风土民情、物产资源,一无所知,又不求助于方志,“反訾为迂疏不切事”,这样的地方官,是不会造福一方的。(14)志书体现资治的思想,为地方官吏提供进行善政的依据,是钱大昕的一贯思想。他赞扬张受先刊修《太仓州志》“于地方利病,剀切言之,洵非率尔操觚”。(15)还引用《论语》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的话,认为人们无论贤愚,都应认识到方志的资治作用。他在修《鄞县志》时,也突出这一思想,他不满于闻性道所修《鄞县志》只有郡治、县境两图,增加了水利、学官、海防等图,指出“水利,关系民生利病;学官,为人士之观瞻;海防,为军政之枢要。……今皆图而列之,俾观者了如指掌”。而且“叙述水利,较之旧志为详”。(16)凡此种种,体现了他志书关系国计民生、有益于地方致治的主张。
三、方志的取材——“博观约取”
资料是修志工作的基础,未曾修志,资料先行。“古人作志,必先聚书,准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17)对于志书的取材,钱大昕提出了“博观约取”的方志取材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是在研究了众多前人修志的成败之处后产生的。他曾说:“宋《乾道新安志》、《嘉泰会稽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皆详瞻有法,其纪一邑者若高似孙之《剡录》、杨潜之《云间志》,亦皆文质彬彬,足备一方之文献。明之武功、朝邑诸志,专以简胜,未免为空疏藏拙之地矣。四明文献甲于两浙,若网罗太广,恐卷帙纷繁,又有疥骆驼之诮。博观约取,此中颇有苦心焉”。(18)细绎之,钱大昕的“博观约取”,实际上是想编撰详而不繁的方志。
“博观约取”是修志的良法。“博观”就是广泛征集材料,巨细无遗。历代正史,地理旧志、诗集文集、稗官小说、公文案牍、金石碑刻、家传志状、口碑传说等等,皆在收集之列。钱大昕的修志“博观”思想与他“史家不可以不博闻”,(19)“历来史家之患,在于不博”(20)的史学思想是一致的。他撰“《鄞县志》”,“博稽载籍,参以采访,赋役营伍,征诸吏牍,人物事迹,核诸乡评”,“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或引旧志,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21)收集资料不可谓不富。
广泛搜集来的资料,并非巨细无遗地尽数写进志书,其间有一个逐步筛选的过程,即“约取”。“约取”就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加工处理,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资料进行严密考订,去伪存真;二是剪裁资料,做到“文减事增”,详而不繁。钱大昕注意对史料真伪的考订,这和他的历史考据学思想又是一致的。无论是史还是志,他都力争做到史料字字皆准,事事皆确。他非常崇陈耆卿的话,“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洵得著书之体,而为后代法者矣”。(22)对于志书好采家传,溢美家世乡贤,钱大昕是反对的。他在《鄞县志·凡例》中指出此志的编纂原则时,就说:“古人事迹以正史为凭,而稍汰采家传之事无实据者”,“若旧阙而今增,则必引据史传及名人撰述文集,信而可征者,不敢徇一家之私乘,以滋后世之惑也”。对于里巷传说资料,钱大昕认为更应小心鉴别,《宝庆四明志》载管辂墓在鄞县西四十里圣女山,闻性道《鄞县志》载朱熹曾到鄞县等等,钱大昕经过考订,认为这些都是“委巷无稽之谈”,作志者所不足采。对资料进行严密考订,去伪存真,只是“约取”的第一步,第二步则要去粗取精,剪裁资料,吸取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能“卷帙纷繁”,又不能“空疏藏拙”,使志书变成一只“疥骆驼”。在钱大昕看来,“文减事增”,详而不繁,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思想内容,是志书“约取”的理想境界。
钱大昕“博观约取”的方志取材思想,把“博”与“约”,“多”与“精”辩证地统一起来,凡由此途而出,志书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成为不刊之书,为后人取法,同时也是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修志工作的具体表现。
四、方志的体例——“叙述有法,繁简适中”
修志须知志书体例,对此,钱大昕提出“叙述有法,繁简适中”(23)的志书体例思想,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志书体裁、结构、门类设置及文字叙述的看法。
钱大昕主张志书体例要有创新,这种创新要能反映一地的特色,并便于表述出来。他拟《长兴县志》体例二十九门,附类八,于疆域、风俗、特产三门,例严事详。疆域下附形胜,因邑地处扼要;风俗重养蚕俗礼;物产特详叙土著。又删旧帝王一门,改列于人物之前,大变旧志体例。书后附杂识一门,兼及考证;而又另立辩证一门,义例分明。钱大昕还特别提倡志书增加图表,认为“志之有图,如人有眉目”。(24)对于通都大邑、兴废攸系之地,也主张加大篇幅,采用变体。如他在《跋景定建康志》中说:“建康思陵驻跸之所,守臣例兼行宫留守,故首列《留都录》四卷。又六朝南唐都会之地,兴废攸系,宋世列为大藩,南渡尤称重镇,故特为年表十卷,经纬其事,此义例之善者”。(25)
对于志书所引资料,钱大昕主张注明出处,集文献之大成,以凭征信。他在《鄞县志·凡例》中指出,所引资料,“于各条下注出书名,庶无攘善之嫌,亦无杜撰之诮,或略加隐括,则曰据、或曰采、或曰参用,要无失乎古人之本意也”,对于公文案牍,“亦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钱大昕重视文献,在志书体例上主张注出文献出处,为后来修志者效法。
五、对志家的要求——“志乘寓史法,不私其亲”
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修志人员素质的高低,钱大昕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提出了自己对志家的要求。
其一,志家要能据事直书,不私其亲,不■上。钱大昕提倡“志乘寓史法”,主张以修撰史书的直书精神修撰志书。对那些私亲■上的志家,钱氏进行了无情的讥讽,梅应发、刘锡修《开庆四明续志》阿谀地方官吴潜,几乎把一部地方志写成了吴家的家谱,极尽阿谀之能事,钱大昕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吴氏一家之书,非志乘之体矣”。(26)他还狠狠批评了一些当世修志者,“近世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矣”。(27)这样修成的志书,是不会有什么经国养民的价值的。
其二,志家要明于掌故,特别要精于舆地、官制、氏族之学。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舆地、官制、氏族是史家所必备的三种最基本修养,所谓“予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8)“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9)他同样用这一标准要求修志人员。谢幼度本来是征西将军桓豁的司马,而《剡录》删去“桓豁司马”四字,结果成了“谢幼度为征西将军”。钱大昕指出,这就是志家“未通于前代官制”而致误。(30)江西的瑞州,宋代本名筠州,至南宋理宗朝始改今名,而《江西通志》编纂者不谙历史地理,将辽、金的河北瑞州(邢台)的刘秉忠录入通志《人物门》,闹了笑话。钱大昕指出:“志家不谙地理,不校时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岂不令人喷饭满案乎!”(31)在钱大昕看来,志家除具有高尚的史德,直书史事外,还要有丰富的知识修养。
六、关于方志人物立传的思想
历代方志,均重视人物立传,钱大昕也同样如此,而且,他在这方面的见解是有清一代其他方志学家所比不上的。
其一,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变黑为白。钱大昕说:“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32)“若一人之身,瑕瑜不掩,则当节而取之,倘任情爱憎,以黑为白,岂惟公论难掩,亦恐鬼责莫逃”。(33)主张方志立传与国史要有差别,有褒无贬,借以褒扬乡贤。但有褒无贬决不是变乱黑白,志书中没有记载的丑行,可于国史见之,钱大昕赞同袁桷《四明志》的做法:“袁伯长《四明志》于史同叔(弥远)但叙其历官,而云事具国史”。史弥远以奸臣擅权,危害朝政,罪不胜书,国史自有记载,志书省去其恶行,决不是掩盖其罪责,而是史志参看,发挥志书褒扬乡贤的作用。
其二,人物传不立标目,不以儒林、文苑示尊卑,只立人物一门,以时间为次排列。钱大昕在《鄞县志局与同事书》中说:“史家之例,以列传为重,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创道学之名,欲以尊异程朱诸人。后来无可充道学者,而无识之辈竞以儒林为荣”,结果因某人当不当入儒林而争端纷起,致使有些儒林传难孚公议。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他是一直反对史书多立名目的,贯彻到志书的修撰上,也是如此。他主张志书列传人物,“总题之曰人物,但以时代为次,不分优劣,既遵古式,又息争端,有尚友古人之识者,自能别其孰为大贤,孰为小贤也”。(34)他立人物不标目,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光绪《鄞县志·凡例》说:“钱志人物传不立标目,此例最善”。按时代先后排列,有助于知人论世,这种人物立传的方法,对今天编修方志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其三,志书记人物,一律以本地籍贯为准。他说:““夫舆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长是邦、游钓所在,俾后世闻其风者,兴高山景行之思。至若魏晋以降,士大夫以门第相尚,王必太原、琅邪,李则陇西、赵郡,谢称陈郡,裴号河东,虽去其乡国更数十世,犹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学,无关于地理。而后之志州郡者,昧于疆域,滥收乡贤之数,甚可笑也”。(35)钱氏之言,乃有威而发,当时作志书者,为褒扬乡贤,多援引先祖,遥遥华胄,芜滥不堪,弊端丛生。钱氏对于人物籍贯处理,务必以生长游钓之邦为主,不及其氏族之远久者,这是正确的。他批评闻性道所修《鄞县志》以张知白入宋贤传,就是犯了这种错误。张知白是沧州清池人,历官从未至两浙,居鄞县的是张知白的后人张籲,张籲与张知白之间不知经过了几世,而闻性道“以后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闹出了笑话。(36)
其四,名宦事迹,与正史互见。钱大昕提出,名宦大吏,“但叙其在伍事迹,若立朝本末,自见正史,毋庸9缕”。(37)志书只记地方官在一地的事迹,至于其一生事迹首尾,当见正史。这样就使志书与正史相配,避免了志书的繁芜。
其五,不为活人立传,以示盖棺论定。他说:“人品定论,必在身后,名宦人物见存者,例不立传”。(38)这是因为人死之后,其一生活动都已结束,是非较易确定。诚然,人死以后,人们还会有不同的评论,有时甚至会因某种原因而几经反复,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人物的事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永远无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盖棺才能论定。活着的人是无法论定的,因为活人的生活道路一直在改变,好坏总在变化,人生的道路既然还未走完,过早地给他们下结论是不恰当的。钱大昕的这一思想一直为后来修志者继承。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的方志学理论是清代方志学中的一朵奇葩,自立门户,俨然一家,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可惜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人不揣浅陋,表而出之,以告慰这位二百年前的大学者的亡灵,并希望人们能进一步深入发掘他方志学思想的精华,使我国古代方志学理论更加发扬光大。
(致谢:本文得到吕友仁先生指数,谨致谢忱。)
注释:
①《竹订居士年谱》
②光绪庚辰程其珏修《嘉定县志》卷二五《艺文志二·地理类》
③④章学诚《文史通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⑤(16)(17)(18)(21)(24)(33)(37)(38)《鄞县志·凡例》
⑥(13)(24)《潜研堂文集》卷二四《风阳县志序》
⑦(25)(26)(30)(32)分别见《潜研堂文集》卷二九的《跋云间志》、《跋景定建康志》、《跋开庆四明续志》、《跋剡录》《跋新安志》
⑧(36)《潜研堂文集》卷十九或钱大昕修《鄞县志》卷三0《辩证》
⑨(15)(22)(23)分别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的《舆地纪胜》《太仓州志》《赤城志》《琴川志》
⑩(34)《潜研堂文集》卷三五《鄞县志局与同事书》
(11)(31)《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江西通志》
(12)《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二》
(19)《二十二史考异》卷五0《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
(20)《潜研堂文集》卷一八《记疏璃厂李公墓铭》
(27)《潜研堂文集》卷二九《跋会稽志》
(28)《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二十四史同姓名录》
(29)《二十二史考异》卷四0《北史·外戚传》
(35)《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一统志馆同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