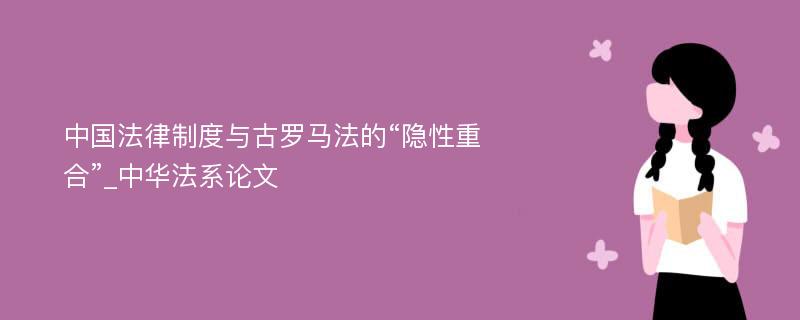
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法之“暗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系论文,中华论文,古代论文,罗马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11)04-0046-09
中国古代很早就与西方有过密切的往来,在古代西方的文献中,经常出现中国的名字。据西方学者研究:“从横跨中亚的商道上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确切知识,已包含在公元前6或7世纪成书的普洛柯奈苏斯人亚里斯特亚士(Aristeas of Procounesus)所著的《阿里马斯比亚》(Arimaspea)《独目篇》之中了。”[1]1公元2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中,曾根据马利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个片段,提到一位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努斯(Maes Titianus)从幼发拉底河到位于中亚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过赛里斯国,他“只不过派遣自己手下的一批人到那里去过罢了”[2]21。东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廷人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记述了哲斯丁皇帝在位时,“波斯人某,尝居赛里斯国。归回时,藏蚕子于行路杖中,后携至拜占廷。”
中国古代文献对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情况也有很多记述。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最早记述了罗马人来到中国之事。唐代杜佑的《通典·边防九》,也记述了安息国王向汉武帝“献黎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由此可知,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就一直没有中断。
众所周知,欧洲是古代罗马法的发源地,东亚是中华法系的诞生地。历史上东西方两大法系是否有过接触和交流,一直是东西方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早在1885年,德国学者夏德(Hirth F)把中国史籍中有关大秦和拂菻(隋唐以后指东罗马帝国)的记载辑录并翻译成书,名为《中国与罗马东部地区》(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20世纪初,法国学者戈岱斯(George Coedès)编辑出版了《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对古代希腊拉丁作家有关中国、印度的资料进行了汇纂。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注意对中国史料的研究,1996年,罗马大学东方学丛刊第15卷出版了《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China Sources,by Leslie D D and Gardiner K H J,Roma 1996),可以说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交往的力作。
既然东西方学者都认同中国与古罗马在历史上有过密切的交往,那么历史上东西方两大法系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是否有过接触、交流和碰撞呢?如果有交流和碰撞,古代中国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西方的罗马法呢?带着这一困惑和疑虑,笔者试图从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葡萄沟(Bulayiq)的一座废寺中,发现了大批用叙利亚文、波斯文和粟特文书写的古代文献,“它们包括《新约圣经》选文集、圣书诗赞、赞美诗、祈祷文、圣徒传记、箴言、布道书及注释书等,大部分文献是译自叙利亚文本,也有一些是粟特人自己编纂的”[3]。这说明在公元7世纪以前,东罗马帝国的文献就曾传入到中国内地。
古代西方的文献典籍中,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记载,如朗格卢瓦(Langlois)所译的《希腊历史片段》第5卷“赛里斯人的法律”中有如下描述:“赛里斯人有一些法律,禁止他们杀生,私通和崇拜偶像。所以,在赛里斯的所有地区,既没有偶像,也没有妓女;既没有杀人犯,也没有被杀者”[2]58-59。由西方古代文献对中国法律的记述可知至少在唐代以前东西方两大法系就有了相互了解、交流和借鉴的可能。
一、中国古代文献关于罗马法的记述
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4],也是迄今为止对后世产生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律体系。关于罗马法起讫的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分歧,有些学者以《十二表法》和优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和西罗马帝国灭亡作为罗马法的起讫时间。[5]还有学者认为:“罗马法者,自罗马建国伊始,至优士丁尼(Justinianus)去位,即自西历纪元前753年,至纪元后565年,罗马所有之法制也。”[6]英国学者巴里·尼古拉斯指出:“在东罗马帝国,直到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之前,罗马法的历史还没有中断。”[7]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中国文献最早记述古罗马政治法律制度的史籍是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其对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有如下记载:“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在东晋袁宏所著的《后汉纪》卷15《孝殇皇帝纪》中,也对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了如下描述:“大秦地方数千,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种植、树蚕桑。国[王]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百盖[小车],出入击鼓……王所治城周环百余里。王有五宫,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宫听事,止宿;明日复至一宫,五日一遍复还。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民欲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会乃议事。王无常人,国中有灾异,风雨不时,辄放去之,而更求贤人以为王,[受放]者终无怨。”袁宏《后汉纪》记述古代罗马皇帝坐车裁判的情况,在德国学者特奥多尔·蒙森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审判日’(dies fasti),君王登上审判所的‘法官坛’(tribunal),坐在‘车座’(sella curulis)上审判案件或发布命令(ius):他的校尉在他两旁,被告或两方(rei)站在他面前”[8]。
南北朝时期,古罗马商人、传教士来华的情况屡见于中国史籍文献之中。据《洛阳伽蓝记》卷3记述:“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
既然很多大秦人来华,也就为古代中国了解罗马法律提供了可能。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魏书·西域传》的记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古罗马的情况。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在位时,曾对帝国的地域组织进行改组,“戴克里先根据他的四头统治体制创设了四位大区长官。把整个领土划分为四个大区(高卢、意大利、伊里尼和东部)的作法由君士坦丁加以实现并且逐渐确定下来”[9]。
唐朝是中国对外交往颇为繁荣的时期。有唐一代,从贞观十七年至天宝元年,东罗马帝国的使团曾7次来唐,这足以说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唐代文献对东罗马帝国的政治法律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据《旧唐书》卷198《拂菻传》记载,东罗马帝国“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鹅,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余户,南临大海。……风俗,男子翦发,披帔而右袒,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
唐代杜环的《经行记》一书,记载了东罗马时期的星期制度:“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诸国路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①书中提到东罗马帝国的星期制度,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情。星期制度最早源于古代的巴比伦王国,公元4世纪初期,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命令,星期制度成为古代罗马帝国的法定作息制度。
两宋时期,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了解更加深入。在《诸蕃进贡令式》16卷中,宋朝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东罗马帝国进贡的程式。《宋史·拂菻国传》对东罗马帝国的风俗习惯、政治法律制度也有如下记述:“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两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
元、明之际,东罗马帝国逐渐衰落,所控制的地理范围逐渐缩小,包括小亚细亚的西北角、色雷斯、马其顿、爱琴海北部的一些岛屿和伯罗奔尼撒的若干据点。[10]但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及欧洲大陆的交往并没有因此中止。元朝时期,甚至有拜占庭人在中央政府任职。据《元史·爱薛传》记载:“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明朝建国后,拜占庭帝国已经衰微。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存续了将近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在古代西方的文献典籍中,也有对中华法系的描述。生活于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西方学者巴尔德萨纳(Bardesana)对汉朝的法律有过如下描述:“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里,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2]57公元7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陶格斯国记》中,也对北朝至隋代的法律情况作了如下记述:“陶格斯国主,号泰山,犹言上帝之子也。国内宁谧,无乱事,因权威皆由国君一家世袭,不容争辩,崇拜偶像,法律严明,持正不阿。其人生活有节制而合于理智。物产丰富,善于经营,多有金银财帛。然国家法律,严禁男子衣附金饰”[11]。古代西方文献对中国古代法律的记述,拉近了东西方两大法系之间的距离,从而证明历史上东西方两大法系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于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动态环境之中。
二、关于古代罗马法传入中国的路径问题
中国古代文献对罗马法的记述表明古代罗马法的一些规则在历史上曾东传至中国,并对中华法系产生了影响。地处西方的罗马法系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中国的呢?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伴随着中国与古代西方陆路和海路两条通道的开辟,罗马法也通过这两条通道逐步传入中国内地。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陆路通道又称为丝绸之路,它东起中国的洛阳、西安,向西穿越西域、中亚、西亚一直通往欧洲的罗马。中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就已经开始了。据英国学者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公元前5世纪,蒙古的黄金已经贩运到了欧洲塞种(西徐亚),而且有一个希腊旅行家曾沿着这条商路深入到准噶尔大门以东,并听到过一些关于中国和太平洋的情况。”[2]25自汉武帝派张骞开通西域后,大批东西方的商旅、使团都通过这条陆路通道来往于东西方之间。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一条商业通道,也是一条法律文化交流的通道。来往于东西方的商旅、使团在从事贸易和外交往来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对方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法律规范。如公元7世纪前半叶,泰奥菲拉克特在其《历史》一书中就清楚地记载了隋朝的政治法律情况:“这一民族崇拜偶像,其法律是公正的,生活中充满着智慧。他们有一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习惯,即禁止男子佩戴金首饰,尽管他们在从事贸易方面具有极大的规模和便利,使他们掌握了大量的金银。桃花石以一条江为界。从前,这条江将隔岸遥遥相望的两大民族分隔开了”[2]105。
中国与古代罗马海上的交往也很早就已开始。西方文献关于罗马帝国与东方海路交通的记载始见希腊佚名作家《厄里特里亚航海记》(Periplus of Erythraen Sea),该书提到了红海、阿曼海乃至印度洋。东汉、三国时期,已有罗马商人经过海上商道来华。据英国学者赫德逊研究,在公元1世纪末,罗马商人走得更远了。西海岸各港口仍旧是绝大部分罗马船舶航行的终点,但少数船只绕过科摩林角,从柯罗曼德尔海岸再次利用季风横越孟加拉湾,最后绕过马来半岛,古罗马商人就发现了一条直抵中国的全海运路线。[1]44中国学者林梅村的研究证明了赫德逊的观点,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的罗马方物。[12]
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笔者认为,古代罗马法传入中国的路径大致有5种。
其一,古代罗马官方使团来华的传入。中国古代很早就与古罗马有过往来,罗马使团历史上也多次来华从事交往。中国古代文献最早提到古罗马使节来华的是范晔《后汉书》。永和十二年(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②。关于“蒙奇”、“兜勒”究竟所指何国,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中国学者林梅村认为,东汉永和十二年,罗马的商团已经到达了东汉的都城洛阳。[12]此后不久,汉桓帝延熹九年,另一支罗马使团又来到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麻诃斯添雷斯安拖尼诺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于公元161年即位,在162-165年间东征安息国,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归于罗马版图,安息此前与汉朝有过往来,故罗马使者能够于汉延熹九年到达中国。
唐宋之际,中国文献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③。关于拂菻王波力多究竟是指何人,目前东西方学者尚有不同意见,但此次罗马使节来唐还是十分可信的。唐睿宗景云二年(708年),拂菻国献方物。④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⑤
北宋以后,中国与东罗马帝国的交往更加频繁。北宋元丰四年十月,拂菻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珍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宋哲宗元祐六年,拂菻国接连派出两批使者,北宋皇帝“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⑥。
古代罗马的使团频繁来华,罗马法也就有了传入中国的可能。中国古代各政权都建立了庞大的外交机构,如唐代的鸿胪寺是中央专职的外交部门,尚书省礼部的主客司、中书省的四方馆与通事舍人、门下省的典仪符宝郎等机构也负责外交礼仪方面的事务。[13]鸿胪寺、尚书省等部门设有专门的翻译人员,其重要职责就是准确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和法律制度。唐代法律规定:“诸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14]7
其二,古代东西方的商旅、游客和民间艺人等频繁往来于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直接或间接地把罗马法的一些规则传入中国。中国与西方的商贸往来由来已久。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西方的商队通过丝绸之路这一陆路通道往返于东西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Florus)的《史记》记载:“其余世界,不属罗马帝政所治者,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盛强,见罗马人而生敬心……不独此也,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中国学者张星烺认为:“佛罗鲁斯所记中国使节,恐为商贩或个人旅行家抵罗马京城者,断非汉之朝廷所遣。”[15]
古代东西方商人来往于罗马和中国之间从事贸易,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也可得到证实。200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东魏时期的茹茹公主墓内发现了两枚罗马时期的金币,两枚金币分别铸造于公元491-518年和518-527年,而茹茹公主去世的时间是公元550年,距金币铸造的时间相隔20多年,罗马金币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流入中国,充分印证了东魏与东罗马帝国往来的频繁。
从两汉时期开始,先后有许多古罗马艺人来到中国。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这是中国文献见到的最早罗马艺人来华的记录。大秦艺人的名字后来经常出现于唐人的笔记小说中。据《出录异记》记载:“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氏。”⑦从两汉至唐宋之际,许多东西方的商旅、民间艺人往来于亚欧之间,为古代中国了解罗马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开辟了又一交流渠道。
其三,古代西方的传教士为了传播宗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在把宗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罗马法的一些规则带到了中国,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罗马法的传播者之一。关于西方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笔者认为,至少在北魏时期或者更早,基督教就有可能传到了中国。在北魏的都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尽天地之西垂。纺绩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⑧。唐朝时期,东罗马的传教士已来到唐朝传教,据《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天宝元年五月,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这是东罗马帝国向唐朝派遣的官方基督教使者。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徒人数很多,唐武宗会昌年间的毁佛运动,被还俗的僧人“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⑨,这一数字说明唐朝境内的基督教徒还是很多的。
其四,古代罗马的一些文献典籍、民间故事在历史上也曾传到过中国,其中也涉及了一些罗马法的内容。语言文字、书籍绘画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拂菻的图画。[16]据唐代裴孝源《唐人说荟·贞观公私画史》记载:“拂菻国人物器样二卷,鬼神样二卷。外国杂售二卷。右六卷,西域僧迦佛陀画,并得杨素家。”另据《南宋馆阁录续录》卷3记载:“捕鱼图四,盘车图一,朱陈嫁娶图一,拂菻人物一。”拂菻人物,绘制的当然是东罗马时期的人物图。北宋的《宣和画谱》卷3记载了王商绘有拂菻风俗图、拂菻妇女图、拂菻仕女图。唐宋文人对东罗马帝国时期的风俗人物有如此细微的了解,证明当时双方的文化交流已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
20世纪初,在中国西北敦煌的藏经洞,发现了一批用汉文和粟特文书写的古代基督教支派景教的文献。此外,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葡萄沟的废寺中也发现了大批用伊朗文和突厥文书写的景教文献,这些文献包括P3847号《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等基督教经典。[17]东罗马帝国基督教经典的传入,也会对当时中国的法律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五,地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中亚和西亚诸国,对于传播东西方两大法系也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两汉至唐宋之际,生活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匈奴、大月氏、突厥族、粟特等少数民族与罗马帝国的交往十分频繁。北朝时期,突厥帝国甚至与东罗马帝国签订了同盟条约。
古代的安息(后称波斯)地处西亚,与罗马帝国接壤,其宗教信仰、交易习惯都深受古罗马的影响。唐代杜佑的《通典》卷139记述了东罗马帝国与安息经常从事贸易的情况:“大秦,一名犁靬,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大批的波斯商人在西边与罗马商人进行贸易,向东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境内经商。关于波斯商人在华经商的盛况,可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颁布的敕节文窥见一斑:“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⑩。大批的波斯商人从事东西方贸易,对于传播东西方的法律文化也会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从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伴随着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古代罗马与中国的往来就一直没有中断。罗马使团的频繁出访,中国、古罗马、中亚和西亚商人经常往来于东西方之间,基督教徒的东来传教,都为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路径。尤其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都设立专门的外事管理机构,注重对西方诸国风土人情、政治法律、山川河流等情况的搜集整理,为古代中国详细了解罗马法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三、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法之“暗合”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古代罗马与中国政治制度有相似之处。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大秦)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11)《魏书·西域传》也记载:“(大秦)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既然古代罗马与中国的衣服车旗制度有相似之处,那么古代罗马法与中华法系两者之间有没有过交流呢?虽然现存的古代文献没有明确记述,但是罗马法系与中华法系的许多规定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也无人给出明确的解释。有鉴于此,笔者姑且使用“暗合”一词,以此来表达东西方两大法系“暗合”的奇特现象。
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法“暗合”之处很多,若把这些“暗合”的现象加以详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是基于偶然的巧合而出现的双方立法相同或相似的现象;第二种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法律原理而出现立法相同或相似的现象;第三种是由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而形成的“暗合”现象。目前因文献资料匮乏,还很难对上述3种“暗合”进行明确区分。但笔者认为,双方法律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暗合”现象应占有很大的比重。
(一)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婚姻法之“暗合”
中国古代的婚姻法与罗马法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由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婚姻法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在一些具体的立法细节上,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古代罗马法禁止官员在任职期间娶管辖地的女性为妻,保罗《论判决》第2编记述:“在某一行省执行公务的人不得娶有本省籍贯的女性或者居住在本省的女性为妻,但是这不意味着禁止他们订婚。不过,如果男方离开行省公职后,女方不愿缔结婚姻,则只要她归还所得的订婚赠物,便不再受该订婚的约束。”保罗《论解答》第7编记载:“我认为,在某一行省履行公务的人娶了本省内的女性为妻违反了皇帝的谕令。但是,放弃其公职后,若还同意与这一女性结婚,婚姻有效。”[18]39中国古代的法典唐令《户令》也有几乎相同的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14]162比较上述两条条文可见,唐宋时期的婚姻法与罗马法的规定是相通的。
中国古代法律规定,如果男女双方订立婚约,三年内男方家无故不娶,女方可以解除婚约,亦不用返还聘财。如南宋时期的法律规定:“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12)上述规定在罗马法中亦能找到相类似的条款,公元9年颁布的《帕披亚·波拜亚法》规定,“订婚后两年内未婚的,其婚约失效”[19]183。公元259年,“瓦莱里亚诺皇帝和卡里埃努皇帝及瓦莱里亚诺太子致保莉娜”中说道:“若你的女儿等待她的在国外逗留的未婚夫,超过三年而不再想等待时,她可以同其他人结婚。因为这一婚姻的希望是渺茫的。她不能蹉跎出嫁的好时光”[18]29。显然,罗马法中该项法律规定与唐宋时期的立法宗旨是相同的。
早期的罗马法规定,嫁奁是妻对夫的赠与,婚姻解除后,丈夫并无返还之义务,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国初期,丈夫单方面休妻的情况并不多见。到优帝一世时,对于嫁奁返还制度进行了改革,才确保妻子在婚姻解除后能够收回嫁奁。[19]215巴比尼亚诺《论解答》第4编说:“如果嫁资之物被估价,随着婚姻的解除,应将其返还给妻子,在这种情况下要申明数额,且不能订立出售契约。”[18]89罗马法中的该项规定在中国汉唐时期的法典都能找到对应项,据《礼记·杂记下》郑玄注引“(汉)律:弃妻,畀所赍”,即归还从娘家带来的嫁妆。
(二)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物权法之“暗合”
古代罗马法中关于埋藏物的规定,与中华法系几乎完全相同。《法学阶梯》第2卷记述:“某人在自己的地方发现的财宝,被尊为神的阿德里亚奴斯遵循自然平衡,把它授予发现人。如果它是某人在圣地或安魂地偶然发现的,他作出了同样的规定。但如果它是某人在并非致力于这一业务,而是出于以外的情况下在他人的地方发现的,他将一半授予土地的所有人。”中国古代的法典《唐律疏议》、《宋刑统》等文献皆有几乎相同的规定,凡于自家土地内发现的埋藏物,归土地所有人所有;“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13)。
罗马法中有关于冲积土地的规定,“河流通过淤积增加于你的土地的土壤,根据万民法,为你取得”;“如果河流的强力卷走了你土地的某一部分,并把它赶到了邻人的土地,显然它仍然是你的。当然,如果时间长了,它已固定在邻人的土地上,它随身带过去的树木已扎根在该土地上,从这时起,它被认为已由邻人的土地取得”。[20]中国古代的法典也有类似的条款:“诸田为水所冲,不循旧流而有新出地,给被冲之家(可辨田主姓名者,自依退复田法),虽在它县,亦如之。”(14)中华法系的该项规定,与上述罗马法第一款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罗马法中有关于遗失物的规定:若不是出于本人意愿而遗弃的物品,财产所有人并未丧失所有权。如遗失物,乃所有人不小心丢失的物,他虽然不再占有,但并未放弃所有权的意思。漂流物、沉没物的性质与遗失物类似,它们不是以所有人的意志而丧失,有机会有可能时所有人仍要寻回这些物件。[19]319中国古代关于遗失物的立法精神与罗马法相同,都采取了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的原则。《唐律疏议》卷27“得阑遗物”条:“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对于拾得人不返还所有人遗失物的行为,唐律的处罚标准是比照坐赃罪处罚。
(三)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债法之“暗合”
关于古代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之比较,已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古代的契约法对古罗马法有“显见的承袭和吸收”[21]。笔者认为,罗马法中关于契约、债的分类、债的构成、债的履行等方面规定,皆与中华法系有暗合之处。
古罗马法和中华法系都对借贷契约的利率作了限制。中国古代的借贷契约禁止回利为本,严禁一本一利。唐令《杂令》规定:“诸以粟麦出举,还为麦粟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又不得回利为本。”以公私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若官物及公廨,本利停讫,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余本生利如初,不得更过一倍”。[14]789
古代罗马法对借贷契约的利息也有明确规定。早期罗马人习惯于自然经济的传统,借贷一般是为了消费,支付利息不是借用人必尽的义务。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法对于借贷的利息才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十二表法》首先规定了借贷的最高利率,利息不得超过1/12,公元前347年,改为最高不得超过1/24。公元前342年,《格努西亚法》又明令禁止借债取息。到了法学昌明时期,罗马法规定,到期未付的利息累计与原本金相等时,即停止生息,贯彻“一本一利”的原则,优士丁尼制定的法典规定:“我们不允许利息的限额超过原限额的两倍”[22]。罗马法还禁止复利,“当事人不得约定将未到期的利息滚入原本金再生利息,纵使当事人有此约定亦不生法律效力”[19]691。罗马法与中华法系关于借贷利息的规定,完全相同。
古代罗马法禁止债权人未经法官的批准占有债务人的财物。卡里斯特拉杜斯《论审判》第5卷说:“债权人如果起诉其债务人,应该通过承审员的判决来主张他所认为的债务人对其欠下的债务。如果没有经过批准而占据其债务人的物品,马尔科皇帝规定他们将失去其债权。”[23]139中国古代关于债的履行的规定和罗马法的立法精神是相通的,法律在注重保护债权人权利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债务人的利益。《唐律疏议》卷26“负债强牵财物”条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疏议曰: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
(四)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刑法之“暗合”
中国古代刑法与古代罗马法中的许多罪名基本相同。罗马法有私度城关的罪名,据彭波尼《各种片段引述》第2卷记述:“侵犯城墙的人应判死刑,就像靠移动梯子或用其他任何方式越过城墙的人一样。对罗马市民来说,除非通过城门,否则不得出城,因为用其他方式出城是敌对行为并且是可憎的”[24]。在中国古代的法典中,也有类似的条款:“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越官府廨垣及坊市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15)。
古代罗马法有禁止夜间集会的条款:“城市里的夜间集会,不得有任何借口,无论是欢乐或是宗教的原因,甚至就是出于公益也不行。”[25]中国古代的法典中也有禁止夜间出行的规定。《唐律疏议》卷26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罗马法中的《阿奎利亚法》有设置陷阱致人损伤的规定:“为捕捉熊设置陷阱的人,因其在人经过的路上设置陷阱而导致某物跌落其中并由此造成损害,那么他要依《阿奎利亚法》负责。”[26]中国古代法典也有相类似的条款:“有人施机枪及穿坑阱,不在山泽拟捕禽兽者,合杖一百”;“其深山、迥泽及有猛兽犯暴之处,而施作者,听。仍立标识。不立者,笞四十”。“若立标识,仍有杀伤,此由行人自犯,施机枪、坑阱者不坐。”(16)
(五)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诉讼审判制度之“暗合”
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与罗马法也有很多“暗合”之处。古代罗马法中已出现了回避制度,法官不得受理与自己及亲属有关的案件。[19]929乌尔比安《论告示》第3编:“执法的人不应当对自己行使司法权,也不应当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解放自由人或其他属于他自己的人行使司法权。”[27]20中国古代的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司法官员的回避制度。唐代《狱官令》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佐、国官于府主亦同。”[28]
古代罗马法对民事诉讼的时间作了限制,法官于听讼日(dies fastus)办案,节假日不受理诉讼案件。古时每9日一市(nundinae),集市之日,视为节日,不得听讼。加上会议日和其他节日,实际上一年的听讼日仅约40日。公元前3世纪80年代,《霍尔滕西亚法》为了便利郊区居民进行诉讼,规定嗣后集市日不作节日计。[19]929中国古代也有节假日不办公、不听讼的传统。唐宋时期的《狱官令》规定:“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14]1427
中国古代有在农忙季节中止民事诉讼活动的传统,《宋刑统》卷13《户婚律》“臣等参详”条:“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如未毕,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断遣,不拘上件月日之限。”而在古罗马的审判制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乌尔比安《论一切法庭》第4编:“马尔库皇帝在谕令中说道:在收割和收获时节,不得强迫对手出席审判,因为正在从事农田作业的人不应被强迫出庭。”[27]38
罗马法中禁止奴隶控告主人。乌尔比安《法学阶梯》第2卷记载:“在任何情况下,奴隶都不得针对其主人提起诉讼。因为毫无疑问,根据市民法以及根据裁判官法或公诉程序,他们不被承认有提起诉讼的权利。”[23]169中国古代至少从秦律开始,就严禁奴婢告发主人。如秦律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29]唐宋律典也严禁奴婢控告主人:“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17)
罗马法对于正在怀孕妇女执行刑罚的办法,也与中国古代相同。《唐律疏议》卷30“妇人怀孕犯死罪”条规定:“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中国古代严禁对怀孕的妇女进行刑讯,“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18)。古代罗马法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4卷记述:“要对处于怀孕中的妇女执行刑罚的,必须推迟到其分娩之后进行。我也知道还遵守这样的做法,即只要妇女怀孕,也不得对其进行拷问。”[23]289
(六)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其他法律之“暗合”
中国古代和古罗马皆设有邮驿,笔者认为,古代罗马和中国古代邮驿的管理法律制度有许多共同之处。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公元46-125年)在记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时这样写道:“他所修的道路都是笔直而无分歧的,路面铺砌石头,路基是压紧的沙堆。凹陷的地方都填平,一切横断的河流或峡谷上都架桥,路两旁的高度都相应地平衡,所以这工程的外貌到处都显得和谐美观。此外他将每条道路都以‘里’来度量了(罗马的‘里’比八个富浪略少),并且在路旁树立石碑以标志里程。”[30]
古代罗马的邮驿制度与古代中国极为相似,中国古代很早就设有邮驿制度,据《唐令拾遗补·厩牧令第二十五》记载:“诸道须置驿者,每卅里置一驿,若地势险阻,及无水草之处,随缘置之”,每驿设驿长一人,负责驿站的管理。为了便于管理、维修和行人辨认,唐代在交通道路上每隔五里设置一个里程碑,即“里隔柱”。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中有如下记载:“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里隔柱”类似于现代公路上的里程标识,它的设立对于计算道路里程,辨认道路方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罗马法严禁地方行政长官经商,莫德斯丁《学说汇纂》第10编:“皇帝在宪令中指出:行省长官及其随从在所辖省内不得经商、不得进行金钱的消费借贷或海运借款。”[22]79中国古代的法典也有相类似的条款,若“官人于所部交易,断契有数,仍有欠物,违契不还,五十日以下,依《杂律》科‘负债违契不偿’之罪”。“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19)北宋《天圣令·杂令》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于部内置庄园店宅,又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请占田宅、营造邸店碾硙,与百姓争利;虽非亲属、宾客,但因官人形式请受造立者,悉在禁限。”[31]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很早就对地处亚欧大陆西端的罗马给予了密切关注,中国古代的正史文献大都设有关于古代罗马(大秦、拂菻)的列传,记录了古罗马时期的风俗习惯、政治法律制度等情况。历代政府为了准确地了解外国的信息,还设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负责搜集外国的信息,翻译外交方面的文书。每当外国使团和商旅来华,外交官员亲赴馆驿向使臣当面了解该国政治法律和风土人情,并将其记录在册。中国历代正史文献所记述的古代罗马政治法律方面资料,有些是当时来华的罗马使团、商旅的亲口陈述;有些是与罗马帝国相邻的各国使节、商旅的所见所闻。若将其与现存的古代罗马法律典籍相对比,大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法律内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对罗马法的记述材料来源基本可靠,记载的法律内容也是较为真实的。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从两汉至唐宋之际,开放的中国与古代西方有众多的交流渠道。尤其是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华帝国与古罗马帝国通过海路和陆路这两条通道保持密切的文化贸易往来。东西方两大帝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大批的商旅和游客、传教士,成为传播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的重要媒介;地处两大帝国之间的波斯、中亚诸国也为传播东西方法律文化起到了中介和桥梁作用。历史上中国与古代罗马虽然相隔甚远,但法律文化交流的路径却十分通畅,尤其是彼此双方都十分迫切希望了解对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这也为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和可能。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古代东西方文献典籍都有对彼此双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等情况的介绍,这应该就是彼此双方交流的结果。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东西方的学者尚未找到古代罗马法典或法学著作传入中国的直接证据,也没有发现中国古代法典传到西方的材料。但从两大法系诸多的“暗合”来看,这种现象绝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上东西方两大法系之间交流的结果。尽管这两种法律文化的交流是悄然无息的,然而却是自然而然和实实在在的,否则也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暗合”之处。从宋代以后,走向没落的明清帝国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断了与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律制度处于封闭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华法系的发展,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入总结和反思。
注释:
①参见:《通典》卷193“边防九”。
②参见:《后汉书》卷4“和帝本纪”。
③参见:《旧唐书》卷198。
④参见:《册府元龟》卷970。
⑤参见:《册府元龟》卷971。
⑥参见:《宋史》卷490。
⑦参见:《太平广记》卷284。
⑧参见: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卷4。
⑨参见:《新唐书》卷52“食货志”。
⑩参见:《宋刑统》卷12。
(11)参见:《三国志》卷30“魏书”。
(12)参见:《明公书判清明集》卷9“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
(13)参见:《唐律疏议》卷27。
(14)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9“农桑门”。
(15)参见:《宋刑统》卷8。
(16)参见:《唐律疏议》卷26。
(17)参见:《唐律疏议》卷24。
(18)参见:《宋刑统》卷30。
(19)参见:《唐律疏议》卷11。
标签:中华法系论文; 古罗马论文; 罗马法论文; 罗马市论文; 张骞通西域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汉朝论文; 罗马帝国论文; 法律论文; 大秦论文; 外国法制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