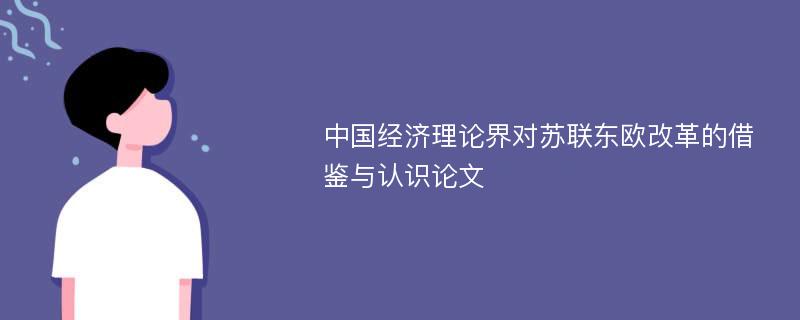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与认识*
谢志刚
[摘 要] 20世纪中后期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两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在相关领域回顾较多关注于改革实践,而对理论发展方面讨论较少。本研究着重于思想和理论视角,首先回顾中国对苏联东欧改革考察借鉴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经济理论界与决策层在此阶段的紧密联系;其次,分析指出对中国理论界影响较大的东欧改革理论是围绕着“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展开的;最后总结在此借鉴过程之中中国经济理论界如何引入“实证范式”“制度分析”等内容,并初步讨论了中国理论层面的改革滞后于实际经济改革的一些可能原因。
[关键词] 苏联东欧改革 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学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了拓展研究视野和方法范式的“理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和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早期决策层与理论界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考察研究以及交流,主要是对各种改革实践模式的经验学习和研究借鉴;其二则是以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等人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的系统引入,包括相关学者与中国学界的交流访问、著作的引入等。从实证方法的初步引入到制度研究的兴起,对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经济学从“苏联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型。
一、对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酝酿时期,决策层意识到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① 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一分册,2014年内部版,第33 页。 由此,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兴起了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的对象“既包括苏联、东欧,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② 姚依林:《同心协力做好经济改革的调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学习考察的内容也逐渐从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相对表层的因素逐渐深入到对经济体制层面的探索。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研究范围较广泛,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苏联等,但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改革上。这三个国家被认为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市场派”、“计划派”和“中间派”三种改革基本取向。③ 刘艳、王涛:《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考察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引入水稻先进种植技术提高单产。保加利亚的水稻种植是采取直播的方式进行,一般栽培品种选择135天成熟品种,田间管理粗放,单产较低,直接导致近几年水稻栽培面积减少。保加利亚公司针对这一情况,从国内聘请专业团队,引入了中国自主研发大棚育苗技术、旱育秧技术、水稻插秧机等机械设备,将中国的35个水稻品种在225亩水田进行了实验,通过育秧、机插秧等技术,使水稻生长期延长30-50天,极大地提高了水稻单产,吸引了周边众多农场主的参观交流,为下一步组建以保加利亚公司为龙头、其他农场主为联盟的产业创新团队,扩大水稻种植,树立中国企业水稻自主品牌奠定了基础。
(一)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改革的考察
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和学习于中国理论界和决策层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曾一度是中国的主要参照模式。如雷颐所指出的,“南共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却不容低估”,南斯拉夫改革的“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解魅”,这甚至“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① 雷颐:《“国有”与“全民所有”之辨——改革初期南共思想的影响》,《中国中小企业》2013年第11期。
1977年8月铁托访华,中南两国关系升温。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全面考察其政治、经济制度。考察团报告指出,“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②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4-55页。 这样的意见让中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认识上迈进了一大步。出于改革探索起步阶段的谨慎,这一时期中国对于东欧的出访和考察多是为了扩展视野和比较分析。以当时视角来看,南斯拉夫的改革属于较为激进型的,而罗马尼亚的改革模式则较为保守,因而此阶段的考察主要是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联合对比考察。
会计内部监督工作是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的会计内部监督工作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会计内部监督很容易受单位领导人员影响,有时候出现我们所说的“专权”问题,会计内部监督工作无法形成严密的牵制关系,出现票据管理漏洞,很多人员利用这些漏洞贪污,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1978年11月至1979年1月,宦乡、孙冶方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访问。经过考察比较,中国考察团总结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两国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有明显的区别,南斯拉夫比较强调自治,而罗马尼亚比较重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考察团注意到,“在南经济学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长期来是一个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并意识到类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又如何理解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改革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考察》,《世界经济》1979年第7期。 考察报告指出,“这就是意味着在计划控制下的商品交换,也意味着为消费而生产,生产者要为消费者服务的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销(市场)定产,而不是以产定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1979)。 这显然已经表达了某种初步的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当然,由于“过去在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是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提的,认为‘市场’就是意味着无计划和自发势力,一谈到‘市场’就联想到‘自由’市场”,因此考察报告并未明确指出市场的地位或者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而是相对含混地指出,“只要我们把供、产、销的问题合理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1979)。
锡克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家,而且“曾任捷克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设计了捷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一九六八年四月任捷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领导经济改革”,⑥ [捷克]奥塔·锡克:《奥塔·锡克教授谈经济体制改革》,《农村金融研究》1981年第12期。 具有丰富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1981年初,锡克的著作《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被中国期刊《苏东问题研究》介绍到国内,其重点在于对苏联斯大林的政治体制的批判。① 蔡慧梅:《苏联官僚统治的实质——〈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一书简介》,《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1期。 1981年,锡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苏州作了七场学术报告,人们对他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柳红,2010,第290页)。锡克介绍了价格改革的思想,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仿捷克以前的做法,采取“先调后放”的手段,利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价格。在此次座谈之后,国务院成立了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并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他们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1982年7月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锡克本人虽然没有参会,但他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是东欧专家的重要代表。② 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锡克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联系,“1986年,奥塔·锡克教授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附寄了他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的一篇近作”,③ 柴野编译:《奥塔·锡克教授谈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 第1期。 希望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借鉴。1982年,锡克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等在中国被翻译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对于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考察报告特别指出:“南经济研究工作开展得是相当生动活泼的。我们在访问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地各抒己见,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他们发表自己的著作,维护自己的观点。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是因为南领导人认为这些不同意见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是有好处的,是允许的,因此对这种争论不是横加干预,而是鼓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1979)。考察报告的意见显然与改革决策层思想解放的思路具有一致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经济理论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股重要的改革驱动力,与这种强调容忍不同意见、鼓励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倾向是分不开的。
(二)对匈牙利改革的考察
南斯拉夫改革的市场化倾向较为强烈,并且放弃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实行自治制度,这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而言是难以接受和效仿的。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的改革则较为保守,显得改革力度不够。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相比较,匈牙利将计划和市场结合得比较好,改革较为稳妥而且深入,因此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的借鉴对象。
中国与匈牙利在理论层面的交流不断深入。1983年5月至6月,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织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考察。③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资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54期。 1983年10月至11月,以“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匈牙利党中央委员、科学院经济所顾问涅尔什·雷热为团长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应邀回访,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考察与交流。访华期间,涅尔什·雷热和霍尔瓦特·拉约什等人做了改革专题报告和座谈,并发表了对中国改革的咨询意见,在中国理论界激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讨论。④ 李淑华、孟传德、李峻:《匈牙利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看法》,《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第4期。
1979年底,于光远、刘国光、苏绍智、黄海、陈国焱等人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回国后,于光远等人在不同场合详细地介绍了匈牙利改革情况及其新经济体制特点,产生了较大影响。匈牙利自1968年开始实行 “新经济体制”,其特点在于,首先是对中央计划的放松,“在计划制度方面,取消了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改由企业自己制定计划”;其次是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用贸易制度代替由中央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的制度和官方分配产品的办法”;① 刘国光:《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12年的评价》,原题《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刘国光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50页。 最后,在组织制度方面,宏观经济过程的管理权牢固地掌握在国家的中央机构手中,微观过程的管理权则保持在经营机构一级。考察之后,中国理论界总结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区别在于:第一,匈牙利强调同时发展两种公有制经济,即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而南斯拉夫强调必须把国有制经济改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第二,匈牙利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是倒退到私有制经济、废弃国家计划,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南斯拉夫则较早放弃了国家计划。② 苏绍智、黄海、陈国焱:《匈牙利现行经济体制的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 年第68 期。
血源性职业暴露为影响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的重要因素,而急诊科不仅经常接触急危重症患者,且医务人员要求动作迅速,使急诊科医务人员发生锐器伤等血源性职业暴露风险更高[4]。虽然我国卫生部颁布一系列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方案,但职业暴露在医务人员中仍时常发生[5]。故本研究对我院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急诊医务人员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防护对策,以降低临床职业暴露发生率,保证医务人员职业安全。
对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考察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为了给1987年、1988年制定改革方案提供借鉴,国家体改委认为有必要对匈牙利、南斯拉夫再做一次综合考察。1986年5月,以高尚全为团长的中青年学者考察团再次对两国展开深入考察,考察重点是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考察报告总结了多方面认识,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 提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实行多元化工资管理制度,给企业以选择权;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加强法制;加强市场组织、协调和市场监督;在改革中承认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党政企分工;重视对改革的宣传;等等。针对当时中国改革面临的如价格改革等迫切问题,考察报告强调:“市场的形成是相当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将改革本身理想化”。⑥ 吴敬琏:《80年代经济改革的回忆与反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3-295页。
早在1979年7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的刘国光就在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座谈会上介绍了布鲁斯的相关理论和思想,① 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另一位所长董辅礽则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交流时与布鲁斯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特别交流,并邀请布鲁斯来华讲学。② 董辅礽:《怎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记与牛津大学布鲁斯教授的一次谈话》,《经济管理》1979年第11期。 1979年底,布鲁斯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授其经济模式理论,并就中国改革的问题与中国经济学者展开讨论。经济所学者赵人伟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提出了诸多代表性问题,如“社会主义模式”、“计划与市场”、“企业自主权”等。与布鲁斯的讨论的主要论点随后被赵人伟整理并报送到中央主要机构以及各学术单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③ 赵人伟:《布鲁斯谈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9期。 布鲁斯以流亡者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宦乡等人会谈并交流改革意见,且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的接见,这充分展现了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将“计划”与“市场”视为对立。如皮尔森所总结,“对于大多数传统主义者来说,市场产生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终止的地方”,“这毫无疑问是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理解,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却从来不曾这样泾渭分明”。② [英]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姜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市场社会主义正是代表着这种来自实践的观察和理论思考,同时也是夹缝之中生长的“弱小的、有时并不明显的理论传统,它十分明确地尝试要建立一种从整体上来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理论家的著作”(皮尔森,1999,第99页)。“兰格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中央计划经济可以依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使用“试错法”等方法找到一般均衡价格,从而实现对市场的模拟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苏联东欧改革思想和理论的引入
(一)市场社会主义与兰格模式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对苏联东欧改革实践的考察和学习还带有试探性的谨慎,考察关注重点更多在于解决问题的实践性和实用性,那么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则进入到较为系统地引入相关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的阶段,从而在改革理论系统化方面深入了一步。
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最先对社会主义关于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设想的可行性作出严密经济学论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家”。①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这里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除了帕累托、巴罗尼等先驱人物之外,主要指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中“市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奥斯卡·兰格等人。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较为充分且系统,这里有对外考察交流经验积累的因素,也有理论界对于改革问题和理论研究深入的原因。特别是1979年以于光远、刘国光为代表的团队对匈牙利经济体制的考察,既有对改革现实问题和经验的研究总结,也有对改革和经济体制一般理论的思考,为之后的对外考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对匈牙利改革的考察就具体政策建议作用而言,对决策层的影响也很大,其改革经验常常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话题,一些具体的政策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如于光远等人的考察报告提出,匈牙利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集各方面力量研究和制定改革方案,这很快为中国改革所仿效。1980年中国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对经济学的西方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阵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欧国家的一些改革就曾经直接地受到兰格模式的影响,而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相关思想和理论的借鉴则是通过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间接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东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访问活动莫过于前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③ 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到80年代中期,早已蜚声海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也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中国理论界的“科尔奈热”。皮尔森在总结“新市场社会主义”时也指出:“许多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都是东欧的经济学家”,“包括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皮尔森,1999,第101页)。中国经济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研究布鲁斯、奥塔·锡克和科尔奈等的改革理论的热潮。
(二)布鲁斯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e)沿着兰格的基本思路区分了“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变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的传统思想,进而提出了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分权模式。布鲁斯认为,区分“经济制度”有三个主要标准:“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由它们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3.由它们产生的产品分配的原则”。④ [波兰]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周亮勋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如果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结成彼此合作的关系,个人参与分配的产品份额由劳动决定,那么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之相反,便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可以而且必然采取不同的模式。
布鲁斯将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根本性的宏观经济决策,它们通常应当由中央一级直接作出”;第二类是“在收入已定的情况下关于个人消费结构的决策,关于职业选择和劳动岗位的决策,它们通常应当由分散的并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最后是“其他的决策”(布鲁斯,1984,第65页)。在此基础上,布鲁斯考察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分为前面所提到的四种类型:(1)“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该模式三个层次的决策都是集中化的。(2)集权模式,第一、二层次决策集中化,第三个层次决策在原则上分散化。(3)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其中第二、三层次决策分散化。(4)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三个层次决策均为分散化的模式。按照布鲁斯的划分,“苏联模式”就是“集权模式”的典型,而他倡导的是第三类,即“分权模式”。
按装SSAS后,船舶在海上一旦发生或确定将要发生保安事件,就可以立即启动报警按钮(启动后不发光,不发声,并且其在船上的位置除了船长、SSO外其他人均不被知道),缔约国港口或主管机关一旦收到该信号后会立即派就近的海军或其他海上反控组织前往救援。
布鲁斯此后还多次来华访问交流。1982年7月参加了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杭州莫干山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也被称为“莫干山会议”。1985年来华参加了“巴山轮会议”。1992年参加了由体改委和联合国经济部举办的经济机制转换国际研讨会。布鲁斯长期流亡英国并任教于牛津大学,因此也把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介绍到了中国。例如布鲁斯介绍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以及“买方市场”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很快被中国经济界接受并展开应用分析(林重庚,2008,第31页)。
(三)奥塔·锡克
奥塔·锡克(Ota Sik)是倡导以“市场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家。④ [美]法斯费尔德:《奥塔·锡克论经济民主和人道主义》,张宇燕译,《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9期。 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1965)中,他基于“兰格模式”,更进一步从利益角度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锡克认为,兰格模式没有触及“社会主义劳动和经济利益的内在矛盾性”这个问题的实质。⑤ [捷克]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王锡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市场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仅是因为在技术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还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利益矛盾。锡克还从信息出发,论证了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在信息收集、传输和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信息的不完备性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社会性质,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利用市场,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加,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还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转化的矛盾。由此,锡克又从信息出发,论证了市场的必要性。他在著作《第三条道路》(1972)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
(2)计算网格 ui|i=1,2,…,2d的矢量坐标,记为c0-gi,c0 为SU={u1,u2,…,u2d}中网格的公共顶点,根据各网格的矢量坐标计算网格滑动的方向矢量
(4)压缩空气潮湿。 广宁轨枕预制场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广东天气潮湿,由空压机输出的压缩空气含水分较大,空压机经多次使用后水分在输送管道内积留易堵塞气阀,使得压缩空气不能自由流动,气缸内进气量不同导致气囊顶升不同步,从而导致轨枕挡肩裂纹出现。
24 V电压经过两个电容滤除高频成分后接入2脚,EN使能后芯片开始工作,BOOT口输出电压经电感电容滤除纹波之后脚到达输出端,此时FB通过外设电路中的R39、R40分得一个输入电压,反馈给芯片.FB脚内部是一个误差运放其参考电压为0.8 V.如果FB获得的反馈电压低于0.8 V时,芯片提高输出电压,FB获得的反馈电压也随之升高,直至达到0.8 V时,整个芯片开始稳定工作,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如果FB获得的反馈电压高于0.8 V,芯片降低输出电压,FB获得的反馈电压也随之降低,直到0.8 V时,整个芯片开始稳定工作,输出电压稳定.根据公式:
(四)科尔奈
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建立在他的“非均衡”或者说“反均衡”分析框架之上。他认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依据的兰格模式不研究非价格信号,无法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使企业预算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标模式。
科尔奈将对企业的约束分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三种类型。从约束类型来看,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受需求约束更明显,属于需求约束型体制,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受资源约束程度更强,属于资源约束型体制。科尔奈独具匠心地提出,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而社会主义企业则处于“软预算约束”之中。④ [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企业独立承担生产管理的风险,承受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己决策生产的行为后果,企业对于投入品的需求是优先的。与之相反,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属于软预算约束类型,企业的商品价格由中央计划机构制定,外部资金投资、税收和信贷制度都是软的,国家提供无偿拨款。科尔奈指出,在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的双重作用下,价格机制的作用程度取决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度。高度集中体制下软化的企业预算约束造成社会产品和资源的长期短缺,而短缺是一种非价格信号,不能通过均衡价格来克服。杜绝短缺的途径只能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使传统的半货币化的经济向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制过渡。
早在1981年,吴敬琏就于国际会议中接触到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并产生强烈共鸣。此后国内学界开始研究科尔奈的思想和理论,《短缺经济学》的译稿甚至在1986年正式引入出版的前两年就在学界广为流传。1985年科尔奈受邀访问中国,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举办的国有企业改革会议。1985年9月,中国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邀请了布鲁斯、科尔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等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介绍了其改革目标模式的观点。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这两种协调机制又分别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 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科尔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B 作为目标模式。⑤ 赵人伟:《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年第6期。 “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尔奈的思想和理论能够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反响,既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关,也与科尔奈本人深厚的学术造诣、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分不开。在这个时期,“不但中国有科尔奈热,而且国际上也有科尔奈热”(赵人伟,2009)。根据赵人伟的回忆,国外有学者曾经评论道:“大陆经济学界有人把科尔奈抬得太高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科尔奈怎么能和马克思比呢?”(赵人伟,2009,第186页)科尔奈对于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对苏联东欧改革的思想借鉴与反思
对于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有学者认为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并不成功,对于中国改革的借鉴作用不大。如胡鞍钢认为,“实际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思路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经验和理论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成功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相对他们而言还是‘先行一步’”。① 胡鞍钢:《邓小平与中囯对外开放》,《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 较多观点则认为苏联东欧改革对于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安志文认为,“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② 安志文:《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文世芳总结认为,“国外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曾经走过弯路,这对中国改革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文世芳:《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述评》,《甘肃理论学刊》2016年第2期。 刘艳、王涛等人更为具体地分析了苏联东欧考察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作用,认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解”;第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第三,“丰富了中国改革理论的思想资源”;第四,“促进了有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形成”。④ 刘艳、王涛:《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考察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其中:l1+l5=450 mm,且选定 l1=300 mm,l5=150 mm,根据整个装置的长度和一般家庭使用的座便器的尺寸选定l2一个合适的值为700 mm.
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理论界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实证范式、制度范式等方面的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如林重庚指出,“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林重庚,2008,第31页)。章玉贵认为,制度范式特别是制度比较范式的引入,“解放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模式的迷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引进中国以后,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⑤ 章玉贵:《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1978—2005)》,《财经研究》2007年第2期。 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如何相结合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学界的问题之一”,赵人伟(2009)认为虽然存在着“实证非实证”的争议,但科尔奈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无疑是颇具启发的。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产生了巨大反差。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先是无法突破旧体制的硬壳”,“后是改革失去控制”,而“通过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渡,没有产生社会失控和经济下滑,并且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只有中国”。⑥ 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2页。 在改革实践方面,中国以“后发者”身份实现了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赶超”和“跨越”。然而需要看到,无论是在改革理论层面还是在一般理论层面,中国经济学界的进展显然滞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甚至在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一般理论的深入和创新发展甚至仍然不能与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当时的国际影响力相匹敌。这是值得中国经济理论界反思的。正如夏斌在非正式文献之中所指出的,“迄今对形成‘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中国改革的总结大多数都是“经验性总结”,而“纯理论性文章”较少。① 夏斌:《一个经济学人对理论创新的思考》,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742.html,2019年3月31日。
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认识借鉴过程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中国改革理论落后于中国改革实践,这首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倾向有关,即重视“实干”胜过“书本”,重视“实用知识”而轻视“形而上学”的一般逻辑和知识体系。其次,还可能存在作为“落后国家”急于“赶超”的战略导向带来的短期效应与制度性约束。最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与决策层的紧密关联,一方面使得中国改革能够得到经济理论直接有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可能也造成了经济学界的学术独立性不足。这特别反映在改革初期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阶段,理论界与决策层具有相当的身份重叠,许多参与考察的学者本身也是决策层或者具有相当的决策影响力。这固然有助于经济理论的应用和高效地解决改革的实际问题,但也造成了经济理论界普遍重视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轻视甚至忽视一般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创新。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有顾准、孙冶方等人在“价值理论”、“计划与市场”等方面做一般理论创新尝试。1978年宦乡、孙冶方等人组成的考察团在同南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等座谈时,南斯拉夫方面“不识庐山真面目”,特别提到,“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柳红,2010,第287页)。这个“小插曲”也生动地表明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是一直在理论研究上处于跟随者地位的。
苏联东欧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借鉴,对于中国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具有双重涵义。其一是通过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经验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多样性”,打破了此前有关价值、市场与计划等诸多问题的讨论禁区,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积极参与解决此类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二是诸如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等东欧经济学者的一般性理论和思想的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认识到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前提之下,仍然可以有较为一般化和较为完整的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和视角,如科尔奈的“短期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在一般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思想解放”,甚至是“启蒙”。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总结和创新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无疑有待更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中图分类号〕 F0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10-0108-08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成”、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社会学研究”(14AZD1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100836)。
责任编辑:张 超
标签:苏联东欧改革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