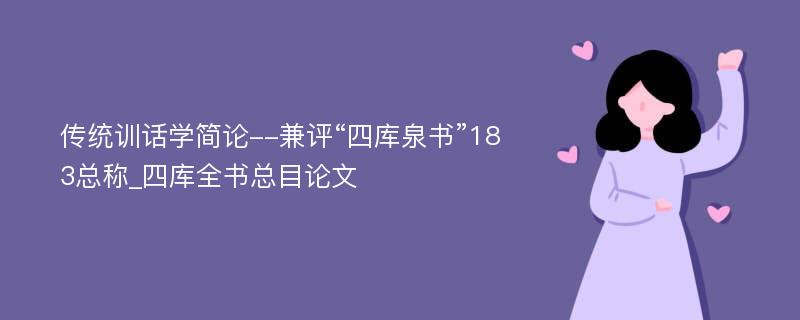
言简意赅的传统训诂学小结——评《四库全书总目#183;经部总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部论文,总目论文,言简意赅论文,小结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勾勒出长期作为经学附庸的传统训诂学迂回发展的轨迹,其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表现为:不是简单地以朝代更迭而是通过学科内部“六变”的发展实际划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阶段;揭露传统训诂学“拘、杂、悍、党、肆、琐”等流弊,具有针对性;倡导“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学风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传统训诂学 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总叙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以下简称《总叙》)以仅五百余字的篇幅论述自汉迄清的经学,实际上它勾勒出传统训诂学迂回发展的轨迹,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得失,特别是一些影响深广的流弊,给予中肯的批评,同时阐明训诂学应坚持的学风与方法。《总叙》称得起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传统训诂学小结。一些当代训诂学专著不仅引用《总叙》,而且给予相当的评价,并不是偶然的。
一
《总叙》开宗明义:“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显然它所论述的不是“经”本身,而是“诂”经的学问。把经学与训诂联在一起并不牵强,本文把较为系统论述经学的《总叙》视为传统训诂学小结,也是合乎实际的。
其一,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经学的空前昌盛。然而产生于先秦的儒家经典到汉代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已障碍重重。于是读经必须先通训诂,著名的经学家大都同时是训诂专家。如为人称道的“五经无双许叔重”,正是以《说文解字》名世的许慎。解经促成传统训诂学的大发展,但同时也使之具有经学的附庸的地位。虽然历代都有训诂学者力图从注释对象、范围等方面冲破经学羁绊,摆脱训诂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然而一直到传统训诂学进入鼎盛时期的清代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观念看,清代卓有成就的训诂大师们直言不讳:“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顾炎武),“夫穷经者,必通训诂”(钱大昕),“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重乎得音”(段玉裁),“小学明而经学明”(玉念孙)……;从实践看,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编辑的《皇清经解续编》共收清人经部传注157家、389部、2727卷。从中可见,清代传注训诂的重点无疑仍在经部,训诂学者们仍在为解经付出大量心血。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儒家经典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当然也不难能否认其中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总叙》清楚地认识到儒家经典的“如日中天”的地位。尽管传统训诂学不局限于解经,但“诂经之说”确实是它的贯彻始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论述经学自然同时也是在论述传统训诂学。
其二,《总叙》虽只有五百余字,却多处直接而明确地论及训诂的内容。除将经学概括为“诂经之说”外,还有“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一字音训动辄数百言”等提法。这进一步说明《总叙》并非间接地涉及训诂问题,而是直接地自觉地把传统训诂学当作论证的对象。
其三,《总叙》曰:“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尽管“小学”是附于经学之末的,却足以说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的撰述者是将“小学”纳入经学之中的。《四库总目》进而明确指出训诂是“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经部·小学类一》)。这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说明将《总叙》视为传统训诂学小结并非牵强附会。
二
《总叙》的核心内容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彼,学凡六变”,通过论述这“六变”,阐明传统训诂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传统训诂学在先秦尚属萌芽状态,至汉代进入形成阶段,一大批训诂学者与训诂专著的出现即为醒目的标帜。《总叙》以汉代为开端,阐述训诂的发展是有见地的。另外,《总叙》不是简单地按朝代更迭划分训诂发展的阶段,而是着眼于“六变”所反映的学科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这种学术见解也不能忽视。
第一阶段。《总序》曰:“其初,专门授受,递相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汉代经学家对本经进行说解的主要方式是师生传授,特点为专治一经且师说各别,于是十分讲究“师法”。事实上师法之外还有“家法”。如:《易》的传授同出于田何,而后又分为施、孟、梁丘三家;《书》的传授同出于伏胜,而后又分为欧阳及大、小夏侯三家。师法也好,家法也好,都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说,代代相传,谨遵家法,不与别家相通。更为复杂的是,秦火之后,“古文经”陆续发现,又造成古文经师与今文经师分门别户、相互攻讦,甚至相视若仇。应该说《总叙》所述符合事实。更难得的是,《总叙》一方面以“其学笃实谨严”,充分肯定了素称“朴学”的“汉学”,讲究无征不信,另一方面又尖锐指出“其弊也拘”。所谓“拘”指的即是受师法、家法等门户之见的制约,不敢创新,不求发展。实践证明《总述》击中了要害,只有冲破“拘”才可能促进训诂学科的发展,有所建树。如东汉末年的训诂大师郑玄正是由于摆脱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敢于消除门户之见,才做到学无常师,集今文经、古文经的大成,融汇诸家之长,遍注群经且成绩斐然,创建了为人誉为“郑学”的新学派。《总叙》这段论述堪称少而精。
第二阶段。《总叙》曰:“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这一阶段由三国魏到北宋跨度较大。王弼、王肃均系魏人。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经典,鼓吹与汉学大相径庭的“玄学”,王肃则另创“王学”,与号称集汉代经学大成的“郑学”分庭抗礼。在他们所持“异议”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汉儒治经形成的格局。到了唐代,孔颖达、贾公彦坚持以先儒的一家之说为主,力求“疏不破注”;而啖助、赵匡则“其论多异先儒”,注《春秋》多“攻驳三传之言”(引自《四库总目·经部·春秋类一》)。两相对照正是典型的“或信或疑”。北宋的孙复、刘敞进一步发展疑古学风,治《春秋》迭出新意。但二人亦有不同,孙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乎尽废三传”,而刘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引文出处同上)显然,孔、贾与啖、赵、孙、刘,甚至孙、刘之间都是“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对成说敢于质疑,勇于各抒己见,对学术活动来说是正常的。正应通过不同见解的阐述与争辩,使学术得以发展。《总叙》能客观地、审慎地肯定“各自论说,不相统摄”,体现一种进步的学术思想。不过,《总叙》同时指出的这一阶段的流弊“杂”,涵义却不甚明确。堆砌、杂糅,不能以观点统帅材料,自然是治学之弊;然而,如果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标准去追求所谓的纯而又纯,不允许任何的“离经叛道”,就不足为训了。不可讳言,《总目》从本质上看,衡量是非的标准是封建的正统思想。《总叙》揭露的六弊中,“杂”似乎是最为模糊而无力的。
第三阶段。《总叙》曰:“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经学到宋代发展为程朱理学,一反汉儒侧重名物训诂的治经途径,改为阐释义理为主。表现在学风上为勇于独立思考,敢于摆脱旧说、创发新义,这使传统训诂学进入不同凡响的变革时期。《总叙》以籍贯“洛闽”指代的程颐、朱熹是宋学的代表人物,而特别应提到的是朱熹。他通训诂但不墨守旧说,对旧说做到择善而从,同时又敢出新意,以期对经文加以合理的解释。例如《四库总目》对他的《中庸章句》的评价为:“不从郑(玄)注而实较郑注精密”,“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宋学在训诂方面往往为人所诟病,而《总叙》却肯定“其学务别是非”,堪称公允之论。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反映在训诂上有主观武断的缺点,甚至“强经就我”。另一理学大师陆九渊就毫不掩饰地声称“六经皆我注脚”。《总叙》对这种学风冠以“悍”字,既准确又传神,同时还列举了王柏、吴澄之所为以揭露其弊。王柏有《书疑》、《诗疑》,俱为排斥汉儒之著作。《四库总目·诗类存目一》评《诗疑》曰:“《书疑》虽颇有窜乱而未敢删削经文,此书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删削之”,接着举出粗暴删削之处多起。《四库总目·经部·书类二》评吴澄《书纂言》云:“颠倒错简皆以意自为,且不明言所以改窜之故。”王、吴治经之“悍”已到不讲道理的地步。
第四阶段。《总叙》曰:“学派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却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这里又论及宋末至明初传统训诂学发展中的党同伐异的问题。治学上的“见异不迁”要具体分析。坚持科学真理,不为哗众取宠之论所惑,不为耸人听闻之说所动,是令人赞许的严肃态度;对足以修正自己错误、令自己水平得以提高之论,则应勇于择善而从、见异而迁。不以是非为标准,一味维护本学派的“声誉”与“权威”,就构成“其弊也党”了。《总叙》列举的二例都很典型。朱熹《论语集注》解释《公冶长》篇之“琏瑚”时沿用东汉包咸的“夏曰瑚、商曰琏”之说。此说与《礼记·明堂位》的“夏后氏之四连,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说法不符,显然有误。元人张存中的《四书通证》是一部相当严肃的著作,《四库总目》称赞它“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但对一代宗师朱熹的错误却不敢引《礼记》以证其误。《四库总目》指出这样做“不免有所回护”,而“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另一例谈及上述的王柏删改《诗经》一事,元人许谦对这种做法有所怀疑,而另一元人吴师道竟公然包庇王柏,责难许谦。原因何在呢?《四库总目·经部·诗类存目一》一语道破:“后人乃以王柏尝师事何基,基师黄干,干师朱子,相距不过三传,遂并此书亦莫敢异议。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议也。”这段话对“其弊也党”揭露得可谓具体而深刻。
第五阶段。《总叙》曰:“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辩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这一阶段的王守仁是个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重要人物。他对抗的不是传统的汉学,而是宋初以来“主持太过”、备受偏袒的程朱理学。针对朱熹的“外心以求理”,提出“格物致知,自求于心”;针对宋儒的“知先行后”,提出“知行合一”、“知行并进”。自明中叶后,王守仁的学说影响甚大,形成又一“王学”。这一学派在“各抒心得”之中暴露出“肆”的弊病。所谓“肆”是指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空谈臆断、胡言乱语。典型的表现为王守仁末流的以狂禅解经。禅宗不立文字,主张顿悟,而狂禅则更发展为空疏而诞妄,鼓吹“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满街皆是圣人”之类的奇谈怪论,而且妄改古书成风。有识之士对王学末流深恶痛绝。《总叙》对这一阶段的论述是切实的。
第六阶段。《总叙》曰:“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辄数百万言之类)。”清初学者顾炎武等对王学末派给予大力抨击:“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对其怪诞不经的学风更是全面否定。他们倡导把经学建立在对古音、古义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清代的“朴学”。继而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加以发扬光大。他们重视旧注但不墨守,勇于创发,实事求是,使清代“朴学”不是简单地重复“许郑之学”,而是力求体现朴素的历史观念、使用比较科学方法的新朴学。其学风上的明显特点是不盲从旧说,但也不妄立新说。凡立说必有据,甚至“例不十,法不立”,这就是《总叙》所肯定的“其学征实不诬”。为立说有据必然要重视考据,但走向极端则又出现为考据而考据,不加分析地搜罗堆砌材料的问题,即《总叙》所批评的“琐”的弊病。《总叙》不仅说古,而且敢于论今,特别是敢于揭露“国初”时弊,应予肯定。或以为清代是中国训诂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于训诂理论及训诂方法上皆卓有成就,殊不满足《总叙》所概括的“征实不诬”四字。《总叙》限于篇幅,固难免挂漏,但还应当看到《四库全书》成于乾隆47年(1782年),虽然当时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以及戴震的《转语二十章序》(写成于1747年)等著述已完成,甚至戴震所校《方言》已为《四库全书》所采录,但一些更为重要的训诂专著尚未问世。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成书于乾隆50年(1785年),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完成于乾隆60年(1795年),至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完成时间已是嘉庆12年(1807年)。这样,《总叙》只能就“国初诸家”而论,人们不便对其苛求了。
总的看,《总叙》所勾勒的传统训诂学发展的轨迹是清晰的,所指出的其学风上的“拘、杂、悍、党、肆、琐”等六弊也确实都是存在的。但“六弊”的说法还有失于严密和全面。其一,“拘”与“党”、“悍”与“肆”、“杂”与“琐”都紧密相关,很难截然分开。其二,“六弊”多为历代相沿的流弊,很难划归某一阶段所专有。例如“琐”本与作为训诂对象的儒家经典本身的“博而寡要”有关,清代固然有“一字音训动辄数百言”的繁琐之弊,但比起汉代秦恭说《尚书》的“尧典”二字竟用十余万言,又相差甚远了。其三,概括不全,有所偏颇。如上所述,汉代训诂之弊只言“拘”不言“琐”当然不全面;又如清代训诂不容忽视的厚古薄今之弊未能言及则更不够全面。这些应视为《总叙》的不足与缺陷。
《总叙》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有独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其一,应当承认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势必对学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总叙》或限于篇幅,或不便明言,在这方面未能涉及,自是不足之处,但《总叙》不简单地以朝代更迭而是侧重学科内部发展的实际来划分训诂发展阶段,又令人耳目一新。它科学地揭示出某一学派或作为学派标帜的学风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渐变的,而不是随改朝换代而突变的,很有说服力。尤应肯定的是它含蓄地肯定了敢于变革为学科带来的生命力,同时揭示了一旦形成学阀、抱残守缺,就又走向反面。其二,对某一发展阶段的训诂学,力求指出其优长与流弊共存的两重性,从中可见学术是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其三,一般都认为训诂在元、明两代处于衰落时期,多不屑深入评论,而《总叙》却认真地列举实例加以剖析,留下了一些可贵的材料与见解。总之,《总叙》确实存在给人以有益启示的理论价值。
《总叙》所概括的传统训诂学的“拘、杂、悍、党、肆、琐”的流弊,尽管不是训诂学所专有,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并顽固地阻碍这一学科的进步。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乾嘉时期的小学家们取得不少超越前人的突破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针对上述流弊,自觉地追求不“凿空”,不“墨守”,“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阮元语)的好学风,不失为重要原因。这又体现《总叙》对训诂发展的实践价值。
《总叙》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还充分体现在论述传统训诂学发展的结语上。《总叙》曰:“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自出现习谈性理的宋学后,便与讲究训诂考证、无征不信的汉学势同水火。宋学斥汉学的训诂与名物考证为“玩物丧志”,汉学则讥宋学为“恃胸臆断”。事实上,一方长于训诂,一方长于说理。取长补短则能有力促进学术之发展,壁垒森严则造成偏颇而使学术难以健康地发展。这一问题到被誉为小学鼎盛时期的乾嘉时代也没能根本解决。一些训诂大师们也往往以反对宋学为己任,言论未免偏激过头。如“宋人则恃胸臆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戴震),“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如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释经典”(钱大昕)等,都有极大的片面性,导致清代的汉学、宋学之争仍不得平息。《总叙》可贵之处在于不为偏见所左右。既肯定汉学的“具有根底”,反对“以浅陋轻之”,又肯定宋学的“具有精微”,反对“以空疏薄之”,可谓公允之论。当代著名训诂学家郭在贻先生认为“这才是全面的看法”(《训诂学》 189页)。有清一代除汉学、宋学之争外,作为小学正宗的顾炎武一系也分为以保守汉人学说为主而兼及小学的吴派和以长于小学,将音韵、文字、训诂作为治经手段的皖派。如何对待不同学派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总叙》的下文:“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就显得更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了。而《总叙》接着提出的“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的评论古籍的原则,正是以上述的对不同学派的公允评价和对门户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四库总目》按此原则进行的评书实践应该说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总叙》所以起到传统训诂学小结的作用,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四库总目》的编纂者中有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训诂名家,更不乏熟读经史有学术见解的文人。第二,《四库总目》对浩瀚的包括经部在内的古籍逐部认真地加以剖析、评介,尽管它有“钦定”的烙印,但“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鲁迅语),从而奠定了《总叙》对传统训诂学做出的较为切实概括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