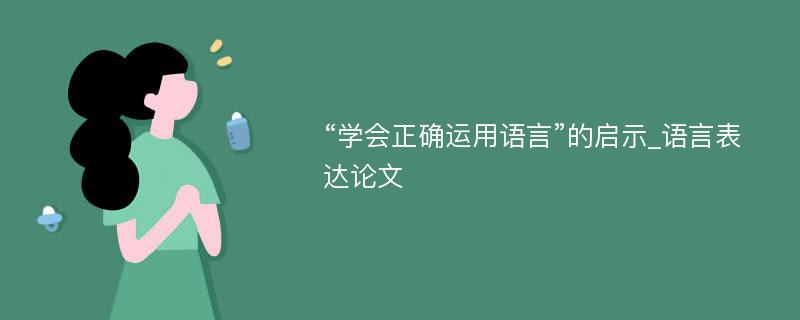
“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得论文,启示论文,正确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前言部分有如下表述: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这段文字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包括三个并列分句,前两个分句用了分号,最后一个用了句号。这就表明,“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后面两个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领属关系。也就是说课标认为语文课程起码有这样三个任务。我一直不同意这样的解读,而认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等,应是渗透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过程之中的;或者说“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等可由且应由“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带动起来,而不是在此过程之外的添加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其间要用两个分号而不用逗号呢?标点的使用是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是最基本的部分;显然,此处的分号、逗号绝不是随意乱用的,而是课标制定者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这于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关系实在太大了。然而,语文课程的任务远不止于此。这段文字的第二句,由“不可替代”四字提示全体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课程还应自觉承担“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任务,而这段文字第三句中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则是呼应并强调了前两句中三个“为……打下基础”,“继承和弘扬……”与两个“增强”。 上面所引的课标文字是其前言中的一部分,而关于语文课程的任务应看下面的部分: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 文字表述确实有了变化,但内容则是完全一致的——“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是与“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并列的任务,其实就是“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的概括而已。 不得不说,课标加给语文课程的任务实在太重、太多、太全了!我以为,新一代的人文教育是包括家庭、学校在内的整个社会共同的任务,不是单靠学校,更不是单靠语文一门课程所能担负得了的。 近日重温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有如醍醐灌顶,特别是身处当前语文教育的严重雾霾之中,顿时觉得眼前晴空万里。 社论开宗明义,毫不含糊地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不就是让学生“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吗?“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不就是我们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吗?“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表达何等简洁、明确,真正能把我们设置语文课程的缘由,能把语文课程的任务、内容、目的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可谓掷地有声! “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九个字也让我们看见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以我之见,上引课标文字,留下第一句中的第一分句“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即可,其余全在可删之列。因为这句话就是“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从课程理论角度的表达,能够引导语文教师全心全意地把力气用在刀口上,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不言而喻,苦功要下在学好语言上,再者,下苦功一定要有时间上的保证。反观现在,中小学语文课的课时越来越少,加给语文教学的任务却越来越多,学生的语文水平从整体上看呈下降趋势是必然结果;而后来的教师就是原先没有在语文上下过多少苦功的学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语文水平整体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我曾在《漫话语文品质之三: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1]一文引用过一位老师《爱莲说》的教学方案,其中“目标确定的依据”第一条就写道: 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 ①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分析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②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③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这位老师对课标足够尊重,但也因此导致目标繁杂,过于重视分析、概括,过于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而教学时间只有1课时。如此这般,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吗?我曾经建议这位老师把教学目标简化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初步读懂课文语句的意思,对课文语言简练之美、生动形象之美有所感受,能正确、流畅地朗读课文,并当堂背诵出来。”我们的课标得学一学《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精神,在规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时,把分散、延伸出去的收回来,把增多、加码的减去,把不多的宝贵时间真正用于“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以期真正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目前,这种在语文教学中把过多时间用于思想、品德教育的现象相当严重,十分普遍。有一篇文章义正词严地指出: 语文教学当然要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目标,但这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根本的目标”。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其根本目标是育人,它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而不能局限于认知和技能。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在育人上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因为其课文内容有着最丰富的精神营养,理当在教学中用这些营养滋补学生。[2] 如此说来,“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就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了?不可否认,教育必须育人;但是,不同的课程可以并且应该依据自身独特的角度、独特的内涵、独特的优势各自发挥育人的作用,具体的课程标准应从“独特”上做文章。如果每门课程的课标都只是强调“育人”这一“根本目标”,而不以自己这门课程有别于旁的课程的“独当之任”为本课程的根本目标,势必就会导致在教学实践中把不少时间花在本课程“独当之任”外的各门课程共同的根本目标上,从而影响各门课程完成自己的“独当之任”,甚至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达不到起码的及格(指水平而非分数)要求。这样的“育人”能说是成功的吗? 我们再来看《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全文自始至终紧扣“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一中心展开,却并没有扯到要把语言用得正确立场就必须坚定、思想就必须正确等上面去,而主要在遣词造句、文理通顺等方面做足文章。“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当然和政治相关,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如开头的“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结尾的“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仅此而已。如果一定要在语言使用与政治思想、立场观点的关系上做文章,那么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这个主题就说不清楚,更不可能说得透彻。这篇社论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主题说清楚讲透彻,正如语文这门课程就是要完成“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这一“独当之任”一样,语文与政治、品德等的关系当然也不必回避,但一般就应像这篇社论一样点到为止。 课标制定者的良苦用心,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绝不否定语文和三“观”、两“感”、两“力”、两“发展”、两“传统”,还有“个性”“人格”等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想要否定也是徒劳。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语文之中,语文的“读写听说”之中,就有三“观”、两“感”、两“力”等;另一方面,倘若真正明白了语言之所以要这样用才正确,那样用就走样甚至错误,三“观”、两“感”、两“力”等也就在其中了,换言之,后者是渗透于前者之中的,而不是游离其外的。其中第二个方面必须稍稍展开论述,因为这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从生成过程看,课文和所有的言语作品一样,其内容和形式是同时成就的,既不是内容决定形式,也不是形式决定内容,而是一定的内容生成于一定的形式,一定的形式实现一定的内容。朱光潜指出:“日常会话往往都是即时完成的,即边说边想。我们的思想在自发地涌现,直接走到舌端。我们并不是先形成一个概念,然后再找字词表达这个概念。当我们表现出犹豫的时候,我们表面是在调整语言,但是实际也在同时调整思想。有时我们做出改正,但是被改正的就是伴随表达的思想。意义随着表达的不同而改变。”“如果语言出了毛病,那是因为思想出了毛病。”“表达总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精确表达出来。”[3] 从生成结果看,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难解难分。两者天然地统一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没有谁。我这里说是“两者”,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即一篇言语作品本身。言语作品绝对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加之和,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形式而单独存在的内容,也不存在可以脱离内容而单独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共生共灭的。所谓两者,只是指我们去看言语作品的人在自己的脑子里(也就是说不是在客观上)从不同的侧面去关注同一篇作品的不同结果。有的人侧重“说什么”的内容,有的人侧重“怎么说”的形式。当然,实际上关注“怎么说”离不开“说什么”,反过来也一样。《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侧重的就是怎么使用语言,而不是应当用语言说些什么,以真正达到倡导“把语言用得正确”的目的。语文教学在关注、研究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同时,也就在引导学生感知、品味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等,在我们关注、研究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的同时,把它所表达的一切抛在一旁不加理睬是不可思议的,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语文教师致力于启发学生学习课文如何“把语言用得正确”,实际上同时也就是在引导学生感悟蕴含其中的三“观”、两“感”、两“力”等;当然我们有时也会着眼课文的内容,直接就其内容进行必要的阐释、发挥,但往往点到为止,不会“以他乡作故乡”。从总体看,语文课程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课文如何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它与人文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叶圣陶曾一再说:“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4]而在我看来,本文开头所引的课标表述恰恰犯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的毛病,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把语文教学、语文教师不必要的过重负担给减下来,在“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的康庄大道上轻装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