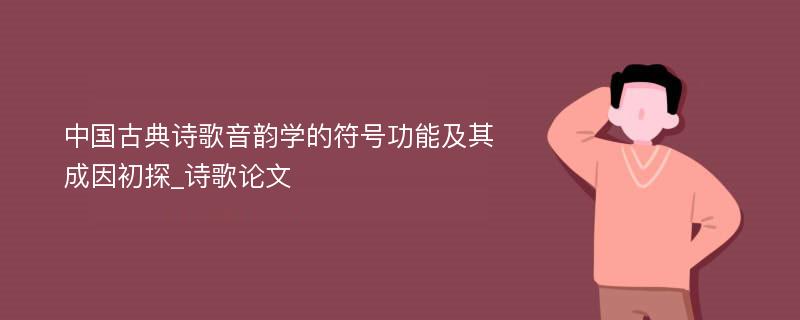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及其成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论文,成因论文,中国古典论文,诗歌论文,象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3)01-0101-06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的形成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古典诗歌所凭借的符号体系——汉语言文字,既具有单音节为主和形、音、义统一的特点,又具有四声的特性。它们既为构建诗歌整齐的句式和对仗、押韵提供了便利条件,又使句内音节和句间对应音节的和谐搭配成为可能。它使人们在诵读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回环往复、整齐而铿锵的优美节奏与朗朗上口、和谐悦耳的韵律美。然而在我看来,这只是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形成的浅层原因;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的形成还有隐含其中的深层原因,即词语的发音特征与词语所指称的对象(客观事物)的自然音韵之间具有一种象拟的关系。这不仅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一种“天籁”般音韵美的特征,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的内涵获得更为丰富的认识;而且它还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的另外一重功能,即人们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即使脱离诗歌语词概念意义的导引,仅凭这些语词在诵读时的音韵特征,就可以获得对全诗或个别诗句的情感韵味的总体把握。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
一、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
对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古人虽未对其所以然者作出理论阐述,但其敏锐的感受捕捉能力远胜于今人。他们对音韵声响在诗歌曲赋创作和诵读中的重要性,发表过大量格言式的感想。而明清学者对此感受最为深切,所论也最为精当:“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1](P414)诗之所以能以“声”为“用”,就因为“声”不仅是诗人刻意经营令人悦耳的格律要素,而且是影射着诗意的音义结合体。所以,“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是“作词第一吃紧义也”[1](P164);所以“昔朱子谓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下工夫。匪独退子,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自然”。[2]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最鲜明直接地表现在对自然界和生活中各种音响效果的描绘表现方面,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双声叠韵词、叠音词的大量使用。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诗经》)、“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杜甫《兵车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中私语”(自居易《琵琵行》)、“寒生更点当当里”(杨万里)。李重华《贞一斋诗话》曾对诗词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词作过总结性的评论:“匠门业师问余:‘唐人作诗,何取于双声叠韵,能指出好处否?’余曰:‘以余所见,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连,取其宛转。”[3]李氏所言“铿锵”与“宛转”类词语在诗中的功能作用只限于音韵的和谐悦耳。其实,双声叠韵词、叠音词的音韵,除了具有和谐悦耳的功能以外,还因其直接表现了描写对象的声响特征——拟声,使读者可以越过语词的概念意义仅凭其语音就获得了对诗句全部或局部意蕴的理解。这种拟声达意的表现方式在后来以口语的大量运用见长的元曲中,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上为人们所熟知,故不赘言。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远非限于对拟声词的频繁运用,即使诗歌中一般语言的音韵也几乎都具有象征的功能,举凡情景物象、人物情态、情感意蕴,几乎无不从诗歌语言的音韵中投射出来。
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一节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先看“昔”、“今”两个时间副词。“昔”发音时气流从从合并的两齿之间向外流出,且带拖延音,与“昔”之过去或历史的悠长历久之义相吻合;“今”由短而清的前鼻音发出,且气流驻留于口腔而不外延,恰似“今”之现在时和短暂的意义。再看“往”、“来”两个动词。“往”发音时口型由嘬而微闭再张开,气息随之一拥而出,似门由闭而开,人从屋内走出离去;“来”发音时口型预先张开,舌尖离开上颚而下落,并稍稍往后(回)抽动,恰似将门打开,人从门外走进屋内。再看“杨柳”两个名词。“杨”发音洪亮且用上声,正如杨树高大挺拔的形象;“柳”发音清澈宛转细腻,正如垂柳的柔条细枝。至于“依依”、“霏霏”,前者发音时舌尖紧抵合并的双齿,气息往外流而受阻,只能发出细细的声音,好象互相依恋,不得不离,但感情难舍的情形;后者发音时由上齿抵下唇继而在气息的暴破中抬升,发出虚而飘的声音,正如细雨迷朦、雪花飞扬的情形。这里,不仅“我”往昔离开和今日归来的不同情态、不同的环境气氛、不同的心情,在音韵上获得了奇妙的象征,甚至象时间这样的抽象概念也赋予了恰如其意的音韵特征。
岳飞的《满江红》更是一首用词音综合象征人物情态、环境特点甚至抽象情感的优秀词作:“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词中直接表现人物情感意志的语词如“怒”、“壮怀”、“恨”的词音都从喉咙深处流出,伴随一定程度的胸腔共鸣,与忧愁悲愤的情感寓藏并发自心灵深处之情之意相符;“激烈”突出情感的强烈,故发音时气息虽有双齿的合并抗阻,但仍然用力挤出;“空悲切”之“悲”,发音轻弱而短促,正如人因悲痛而几乎说不出话来。“潇潇雨歇”中“潇潇”状风雨交加,“歇”音微而短,状事物的运动渐渐停息。由“潇潇”而“歇”的词音流动,使人感受到风雨交加到渐渐停息的过程。而最能表征词音象征功能的是表现人物情态动作的语词音韵。如读“冲”时,气流从口中用力喷出,使人感到怒气冲天,仿佛要把帽子都掀掉。人凭依时的身体重量主要靠地面支撑,对凭依之物只是稍稍依偎,故“凭”音轻盈。“抬”、“仰”是向上的动作,且要克服一定的下沉阻力,所以音量宏大,声调上扬。“望”的视野辽阔,故发音时口型大,口腔内空无阻拦。总之,通过对以上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音韵的诵读体会,不仅使我们对诗人所处的骤雨初歇后的亭台环境、凭栏远望仰天长啸的情态形象、以及重愁叠恨悲愤交加的浓郁情感,获得了一般意义上的更深刻的体会;而且因诵读伴随气息、口腔、喉咙、胸腔、面部表情等多种生理体能上的运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诵读的过程就是对作者创作时的特定时空背景、他的一喜一怒、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乃至他的心跳、呼吸、哽咽等内在细微的情感涌动所作的身临其境的重新体验。这种体验之深刻、真切,对读者心灵的震撼力量,是诗歌词语一般概念意义所引起的联想体验所无法比似的。
在更多的古代诗歌中,不仅语词的音韵特征恰如其分地投射出对应语词所表征的情境物象和情感意蕴,而且往往由众多语词的音韵共同形成一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音韵旋律,从而对整个作品或局部作品所表现的整体情境物象和感情意蕴起到有力的烘托作用。如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写春江月夜景色的诗句:“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是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这里描写的是在春天一个浩月当空的夜晚,辽阔空旷又处处鲜花野草、白沙流霜的江岸在月光下宁静、空灵、朦胧、优美而令人神往的境界。仔细品读就会发觉,不仅“江”、“绕”、“月”、“照”、“霰”、“空”、“流”、“霜”、“飞”、“沙”、“天”等词音风格几乎都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特征相吻合,而且作为韵尾的“甸”、“霰”、“飞”、“见”以及句中“林”、“皆”、“里”、“流”、“觉”、“汀”、“纤”等词音因都具有发音轻巧、细微、空灵的特点,从而形成鲜明而统一的音韵风格,构成了该段诗韵的主旋律,与诗所描写的宁静、空灵、朦胧、优美的意境浑然一致。司马相如《上林赋》这样写八条水道混流而下的壮丽景象:“赴隘峡之口,触穹石,激堆碕,沸乎暴怒,汹涌澎激,沸宓汩,偪泌偪节,横流逆折,转腾敝冽。”连续运用双唇爆破音,以气息受阻爆破象征江水受阻之激沸,摄人心魄。[4]
在一首诗中,组织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共同隐喻一种情思或特定的情景,这在韵脚的选择安排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由此我们发现,对韵脚的选择安排,决不仅仅是为了音韵的和谐悦耳,而且还有使韵脚的词音具有象征不同情感意蕴和诗体风格的功能。例如唐代诗人崔灏抒发思乡怀古愁情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幕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其中“楼”、“悠”、“洲”、“愁”等韵语就都具有词音悠长徐缓和厚重深沉的特点,与作者抒发的绵绵幽情和对人事沧桑的沉重感慨情愫是如此的吻合。然而杜甫以欣喜心情写下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所用的韵语就洪亮而奔放:“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其中“裳”、“狂”、“乡”、“阳”发音时气流通畅、粗旺,词音洪亮、辽阔、有力,从而使作者听到喜讯后的兴奋、豪迈、澎湃之激情得以充分地烘托。
在同一首诗中(尤其是篇幅较长的诗),古人经常采用换韵的手法。为什么要换韵呢?显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追求音韵在变化中求得更高境界的和谐,而且也在于通过音韵的转换更好地象征感情的跌宕起伏。例如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歌》开头两句:“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前两句用圆润之韵,与儿女私情的意韵相协调。后两句情绪一变为激昂,韵脚也还以阳刚之韵:“划然变轩昂,猛士赴战场。”再如上引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全诗四句一换韵,由平而仄,由仄而平,回环不已,令人情虽流水,荡气回肠,吟哦不已: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是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频频换韵,形成推波助澜之势,象征着感情的曲折与回荡。
这种基于词音、韵脚特征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具有不同风格的音韵旋律,与音乐中的不同调式和曲式具有相似的风格和功能。有的洪亮、强劲、欢快,如音乐中的C大调,适宜于象征诗人激昂、奋发、达观的思想情感(如上引《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有的舒缓、沉郁、幽深,如音乐中的小调,适宜于象征思古的幽情和缠绵悱恻的情思(如上引《黄鹤楼》);有的轻柔、细微、空灵,如音乐中的小夜曲,适宜于象征清新、明丽的环境和诗人恬淡的情趣(可以王维《山居秋瞑》为例体会);有的雄浑、开阔、悠长,如音乐中的交响曲,适宜于象征阔大的气象或迷朦深远的境界(可以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为例体会)。
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以这种音义同构的音律形象,声情并茂地单发诗意的。这就使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符号系统的汉语具有了双重的表意功能:既通过语言的一般概念意义写物抒情,又通过词音的象征功能隐喻对象的情景意韵特征,使人对诗意的把握领会既可以通过词语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转换想像而获得,又可以通过对词语音韵的直接感知而获得。由此也导致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一种双重形象性的特征。通常所谓诗歌的形象性,是指由诗歌语词的一般概念意义所引起的内隐于读者大脑中的视觉形象。但因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兼具象征情景物象的功能,所以,由付诸听觉的词音自然也会引起人们对特定情景物象、表情神态和诗情画意的联想、体验,所以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在赋予中国古典诗歌更多的意韵和音乐美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一种实实在在的音乐形象美的特质,从而使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性获得双重途径或双重意义上的体验、把握。这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独具的民族特质。
二、诗歌音韵象征功能之成因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是由汉语词音的人文理据性,也即汉语的生成机制——象声表意——所预设铸就的。
而我国现代语言学界对汉语词音的理据性研究恰恰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关于语言约定俗成理论的影响所致。[5]其实,正象汉字采取了象形表意的生成机制一样,汉语特有的语音特征也不是偶然任意创制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文理据性。
对汉语词音的理据性最早予以关注的是公元一世纪左右刘熙的《释名》。刘熙释名的一个基本方法是选择一个同音同义的字进行解释,如“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时成也。”“冬,终也,物终成也。”“金,禁也,气刚毅能禁制物也。”“木,冒也,华叶自覆冒也。”“水,准也,准平物也。”[6](P203)刘熙的释名法内隐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凡字音相同或相近则字义也相同或相近。由此开启了后代中国训诂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声训法。但不管刘熙的释名还是后代的声训,都是对汉语音义同构这一固有现象的训诂应用,而没有阐明音同为什么会导致义同的道理。宋代的王圣美可能是明确提出汉语的词音具有表意作用的第一人,他说:“古之字皆从右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着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7]但他只注意到形声字的音义同构现象,也未对音义之间的因果联系作出说明。清代学者对其中的奥妙始予以重视,象王念孙、钱大昕、段玉裁、黄侃、张炳麟等人都在“因声寻义”方面进行了大量考证研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而尤以章炳麟的意见最为明了透彻:“语言不冯(凭)虚起,呼马为马,呼牛为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何以言‘鹊’?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雀’?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此皆以音为表也。”[4](P67)现代国学底蕴深厚的学者如吕叔湘、杨树达、王力等人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的理据性作了进一步拓展性的研究。但总体上看,对汉语音与义的内在复杂关系仍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更多的人至多把汉语的理据性局限于拟声词或形声词的狭隘范围内审视,[6](P256)以至目前为止汉语词音的理据性仍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下面,我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词音的理据问题作一较全面的阐述(注:鉴于该问题在本文中的从属性,故仅阐明其概要,不便象专论那样展开论证。),以期揭示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形成的终极原因。
仔细分析汉语的词音特征就会发现;汉语的生成机制与汉字的生成机制如出一辙,都是我们的祖先“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的认识成果,都是以不脱离具体对象为特征的具象思维的产物。所不同的是,汉字用类似于事物的外形特征的视觉符号为能指形式来表征所指,而汉语用类似于事物的自然音响的听觉符号为能指形式来指称对象。借鉴汉字的生成法叫象形表意,我们姑且将汉语的生成法叫象声表意。汉语的象声表意法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从总体而言,可以分为直接象声表意法与间接象声表意法两类。
(一)直接象声表意法
所谓直接象声表意法,是指通过模拟事物的声音特征而获得指称事物及其意义的语音符号的语言生成机制。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来考察。
1.对自然界和人事界各种音响现象的语言指称
自然界和人事界各种音响现象是最适宜于用象声表意法为其命名的。以具象思维为能事的汉族先民为这类现象命名时,几乎是必然地选择了顺应自然、“以声象声”的方法。于是汉语中便产生了大量的拟声词。而且由于一切声音现象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同一频率的连续鸣响,为了使拟声更加逼真,这类拟声词大多以叠音词或双声叠韵词的形式出现。如睢鸠之“关关”、水之“汩汩”、雷声之“隆隆”、秋雨之“滴嗒”等。其它如“咚咚”、“锵锵”、“嗡嗡”、“哇哇”、“扑嗵”、“轰隆”、“嗄吧”、“叮叮当当”、“悉悉簌簌”、“毕毕剥剥”、“叽哩咕噜”、“劈哩啪啪”、“叽哩哇啦”……过去我们认为,双声、叠韵和叠音词的运用是《诗经》作者在表现方法上的创新;其实,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早已存在于汉语中,只要诗歌以汉语为媒介,这种诗歌就必然会表现出频用双声、叠韵和叠音词的特点。
2.对人类感叹行为的语言指称
感叹既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又是一种伴随着语音现象的行为表现,所以对感叹行为的语言命名,也非常适宜用以声拟声的方法。但它与表示自然事物声音现象的拟声词又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表示自然事物声音的拟声词,其语音形式多少经过了一定的概括提炼、加工改造,它们与自然事物的声响虽然相似,但毕竟不完全相同。而感叹词的语音形式与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原始的慨叹感喟声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汉语的感叹词就是对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的感叹的“录音”复制。第二、表示自然事物声音现象的拟声词是纯粹的以声象声,即它除了指称声音现象外无任何意味。而感叹词除了指称感叹声外,还指称着人的一种感叹行为;从更深的层次看,它们还分别指称着人的各种心理特征,表现着主体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对人事物象所作的伦理的、审美的、认知的多重价值判断。因为很明显,无论是“噫”、“呀”、“啊”、“嗨”、“哇”、还是“唉”、“嗯”、“噢”、“嘿”、“吁”……无论是从信息发出者看,还是从信息接受者看,人们关注的都不是这些语音形式本身和感叹行为对象,而是隐藏于感叹行为背后的某种情感、意向。感叹词因直接以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叹声为语音符号来传达感叹所系的情感意向,所以,在所有汉语词汇中,感叹词的表意最具有直接性的特点,以至于人们通常根本意识不到它们作为符号媒介的中介性,而径直将其作为所指对象来感知体味。
3.对具有声音属性的事物的语言指标
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方面的,即以物理属性而言,就有形状、颜色、质地、声音、重量、气味等方面。但汉族先民即使用语言为非声音现象的事物命名时,同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事物的声音属性,即通过模拟事物的声音特征来指称整个事物。这是用类似于修辞学上的借喻手段来生成语言的方法。例如,“火”之读音如野火“呼呼”之声,“萧”之读音如风吹篙叶之声,“粟”之读音如果实裂开之声,“金”之读音如敲击金属之声,“虎”之读音如虎咆哮之声,玩具“叮当”如其叮玲当郎之声,等等。如果说前两类拟声字采取了与所指称对象的声音特征相近或相同的语音形式的话,那么这类拟声字只是采取了与所指称对象的声音特征大体相近的语音形式,表现了汉语的语音形式开始向抽象化、概括化的间接象声表意法发展的趋势。
(二)间接象声表意法
正象所有的汉字不可能都用象形造字法生成一样,由于客观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的纷繁复杂性,完全基于直接模拟客体音响和主体音响的以声寄意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如有些事物虽有声音属性,但其音响具有多种形态,难以用单一恒定的语音形式名之;有些事物虽具有物质实体,但通常以无声的状态存在;尤其是一些抽象事物纯粹不具备象声表意的音响条件。但即便如此,汉族先民在用语言表达对世界的认识时,仍执拗地通过各种曲折途径为事物及其意义的命名寻找不同的物音理据,从而使象声表意法几乎成了所有汉语词汇生成的普遍法则。下面根据命名对象的不同特点,分两类情况予以考察。
1.被命名对象虽有声音属性,但音响形态多样化,难以用一种恒定的语音形式模拟。对于这类对象,一般通过发音时特定的口形或气流在口腔中的不同运动方式来模拟事物的运动状态,以此实现对事物的指称。如“气”指一种轻盈地运动着的东西,发音时用自然的口形让气流从口中轻轻溢出;“打”指强有力的动作,故发音也较用力,且声音洪亮;“杀”的动作结果是尸首分离,发音时上下牙齿由合而分开,口形由小变大;“吐”指食物由口喷出,故用有力的爆破音;“升”指由低到高的运动,故发音时舌头由低而抬高;“降”指由高落下的快速运动,故发音时舌尖由上颚而快速落到下颚;“天”上“地”下,故“天”之发音气流有飘升之感觉,而“地”之发音有气流急速下沉之感觉。此外如“关”、“团”、“出”、“入”、“砍”、“割”、“尘”、“来”、“去”、“宰”、“锯”、“开”、“合”、“哭”、“笑”、“吵”、“闹”、“撕”、“展”、“奋”、“藏”、“判”、“飞”、“插”、“唱”等等,都是通过特定的发声方式模拟事物的运动特征以指称对象的。这种命名方式涉及的对象或者是具有运动属性的事物(名词对象),或者是事物的运动状态本身(动词对象)。显然,这类对象最为纷繁多样,因此在汉语中由这种命名法产生的词汇也最为丰富。
2.因发音会引起嘴部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所以,特定的发音方式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表情;而且发音方式不同,音调的风格也迥然相异。正是通过特定的发音方式与表情神态和音调风格的结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属性和一些非实体性现象也能通过象声表意的方法予以命名,这是汉语的象声表意方式最为曲尽其妙之处。如“愁”隐藏于心灵深处,人之有愁,则表情呆滞,眉头紧缩。而愁音正是发自喉头深处,且发音时表情恰如罹愁之态。“乐”意为心喜,其发音轻松且呈喜笑颜开之表情。“涩”为舌头感到不光滑且有刺激味,故发音时舌尖抵齿,气流受阻而不顺畅。“阳”刚而“阴”柔,故“阳”之音调雄壮嘹亮,而“阴”之音调轻柔晦暗。“好”意为欣赏赞许,故发音时伴随欣喜之表情,且声音洪亮。“恶”为厌弃否定,故发音时一脸苦相,且音调呜咽。“慢”发音用带拖音特征的声母"M",“快”发音用带急促爆破特征的声母"K",故“慢”、“快”发音恰如其义。另外如“大”、“小”、“多”、“少”、“方”、“圆”、“粗”、“细”、“正”、“反”、“轻”“重”、“饱”、“饿”、“动”、“静”、“胖”、“瘦”、“凸”、“凹”、“团”、“粘”等等表示事物抽象属性的词,只要仔细分析,都可以从它们的发音方式及其伴随的面部表情和音调的风格特征里找到它们恰如其音的意义踪迹。
三、汉语音韵与诗歌音韵的内在关联性
汉语象声表意的生成机制决定了汉语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色。第一,它使汉语语音系统具有了一种浓郁鲜明的自然音韵美。关于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的内涵,过去我们仅仅理解为人们在诵读时感受到那种回环往复、整齐而铿锵的优美节奏与朗朗上口、和谐悦耳的韵律美;论其形成原因,则直接归结为押韵、平仄、双声、叠韵及整齐的节奏等因素的动用安排,间接归结为汉语的单音节和四声特点。从以上分析看出,其实,即使汉语的单音节和四声特点也不过是构成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的浅层原因,因为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追问:汉语为什么会具有单音节和四声特性呢?显然,其原因正由于一音象征一物的汉语命名机制。至于汉语四声,固然有协调语调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与同声同韵的搭配组合,孳乳出更多的可以相互区别的语音代码来,从而影射具有不同特征、情状的外物对象。可见,汉语象声表意的生成机制才是汉语诗歌音韵美及其象征功能形成的终极原因。
第二,汉语象声表意的生成机制同时也决定了汉语表意的形象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在印欧语系的各民族语言中,一种音响形式一旦成为语音符号,就会被高度抽象、发生严重的变形,所以,它完全摆脱了事物原始鲜活的声响特征。这个语音符号之所以能指称事物及其意义,是由于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人为的联想关系,而非直接从符号的语音特征就可以看出或听出所指涉的事物及其意义来,其语音形式充分体现出符号的中间性的特征。汉语的语音形式虽然也经过抽象、变形,但万变不离其“宗”,人们由其符号的语音特征仍然可以觉察到事物及其意义的原始、鲜活的形态特征和属性。以至于我们稍加夸张就可以说,汉语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体系,而且也是事物及其意义本身。当然,汉语的语音形式作为符号的中间性的特征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大大地弱化了;而与此同时,汉语表意的形象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却被高度强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之所以能将特定情影物象、表情神态、诗情画意象征得惟妙惟肖,正是基于汉语表意的直接性和形象性而获得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汉语象声表意的生成机制不仅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和自然音韵美的特征,而且对以汉语为媒介的所有体裁的中国文学都程度不同地赋予了相同的特征,因为“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是带着模子的色彩和线条”。[8]只是由于诗歌在早期与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诗歌本质上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汉语的音韵元素故能自然吸纳、顺势利用,其音韵美的特征显得异常突出罢了。
收稿日期12002-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