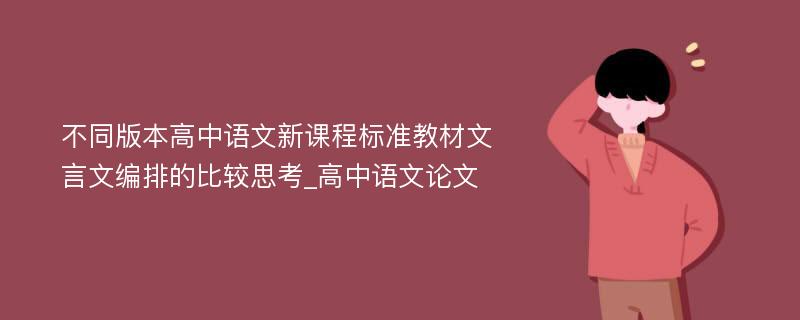
不同版本高中语文新课标教材文言文编排的比较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新课标论文,高中语文论文,教材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言文教学是高中语文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编排情况进行研究,是考察文言文教学问题的一个有效视角。为了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把握,笔者有意识地搜集了七种版本的新教材,针对这些教材在文言单元与课文编排方式上的异同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寻找到相对合理的编排模式,同时对高中文言文教学改革有所启迪。本文所考察的七种新课标教材为:人教新版(袁行霈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人民版(童庆炳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语文版(史习江、张万彬主编,语文出版社2006年版),苏教版(丁帆、杨九俊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粤教版(陈佳民、柯汉琳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鲁人版(谢冕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沪教版(王荣生、倪文尖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除了上述7种新教材之间的横向比较外,还引入人教1998年版、2000年版两种老教材作纵向的考察和分析。
据笔者考察,7种语文教材中,文言课文的编排体例,大体呈现为两种大的类型:
(一)文言文与现代文(语体文)混合编组型,苏教版、人民版与鲁人版即属此类。这些版本的教材均采用以人文主题为纲来组合课文的方式,比如将《劝学》、《师说》与《获得教养的途径》(外国散文作品)三篇课文合在一起组成“获得教养的途径”这一专题(苏教版必修一);将《石钟山记》与《再别康桥》(现代新诗)、《听听那冷雨》(现代散文)三篇课文组合在一起构成“体悟山水神韵”单元(鲁人版必修一);将《项脊轩志》与《〈呐喊〉自序》(现代散文)、《再别康桥》(现代新诗)、《葡萄的精灵》(现代散文)四篇课文组合在一起构成“往事悠悠”单元(人民版必修一)。
(二)文言文单独编组型,人教版、语文版、粤教版、沪教版这四种教材属于此类。这一类型事实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型:一是文言语体与文体结合型,像人教版、粤教版这两种。比如《兰亭集序》、《赤壁赋》、《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游褒禅山记》四篇文言文组合为“古代山水游记类散文”单元(人教版必修一);《孔孟两章》、《劝学》、《过秦论》、《师说》四篇文言文组合为“古代优秀的议论文”单元(粤教版必修四)。二是文言语体与人文主题结合型,像语文版、沪教版这两种。比如《鸿门宴》、《淝水之战》、《段太尉逸事状》、《崔杼弑其君》四篇文言文组合为“大江东去”(古代历史英雄人物)单元(语文版必修二);《宫之奇谏假道》、《荆轲刺秦王》、《鸿门宴》、《赤壁之战》四篇文言文组合成“古代战争与英雄精神”单元(沪教版必修二)。
在对各版教材的文言文编排情况作一番粗略的梳理之后,接下去我们要围绕这一问题作一个相对细致的审视和思考。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以前,无论是私塾还是新学堂,所谓的语文教学一律是文言教学,包括读与写两个方面。随着白话地位的确立与提升,渐渐地,中小学校的白话教学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文言教学也依然受到重视(尤其是初中与高中阶段)。当时所编写的各种语文教材,都实行文言与白话混合编排的做法,并实行“退着走”的方式,即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白话内容逐渐减少,文言内容逐渐增多。新中国建立之后,小学基本上没有文言学习的要求;初中到高中,随着年级的提高,文言文学习的分量渐次加大,难度也逐渐加大,要求当然也相应提高。从教材编写来讲,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基本上都采用叶圣陶先生所谓“雨夹雪”的文白混编形式,这可以说是汉语文教材的一种常态。不过,对于文白混编方式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20世纪40年代,浦江清先生就提出:“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所以他主张“把中学国文从混合的课程变成分析的课程;把现代语教育,和古文学教育分开来,成为两种课程”。[1]60年代,吕叔湘先生也认为:“现行的教材编法和课时安排都还不能符合要求。教材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插花着排列的。”他主张,“学习文言应有一定的系统”。[2]60年代就进行文言文教学改革实践的北京景山学校,则从文言文教学实践入手进行探索,并最终得出这样的经验结论:学比不学好;早学比晚学好;集中学比分散学好;文白分开学比混合学好;以诵读为主比以讲知识为主好。[3]
对于文白混教的方式,叶圣陶先生本人的态度也是处在变化过程中的。从20世纪20年代的赞成、倡导并力行之,到新时期,叶老又主张文言要集中编、集中学,坚信“教文言文和教现代文当然有共同之点,也必然有教文言文的特殊之点”[4]。“文白教材混编混教,混淆了两种教学各自的侧重点,削弱了文言教学的根基。……(文言与白话)二者的特点和难点不同,学习的起点也不同,不宜放进一个教学层次,纳入同一条教学路子,否则就会违反各自的教学规律。硬是要混在一起,尤其是把文言作品纳入现代实用文的框子,按单元编排,很难充分照顾到文言教学的特殊性。”[5]笔者以为,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建国以来一统天下的人教版统编教材多年沿用所谓的“雨夹雪”、“插花着排列”的文白混编方式(人教1998年版教材可为代表),即每册教材共7个单元,专门的文言文单元有2个(第六册例外,只有一个)。其单元编排方式是文言文单元作为每一册的最后两个单元。这样的编排方式,符合文言“集中学习”的原则,有其合理性。人教新版与粤教版这两种教材基本上延续了人教旧版统编教材的体例。
而另外5种新课标教材则与此不同,其共同特征是,单元组合以人文话题为依据。在文言文单元、课文的编排方面,它们的区别在于:语文版、沪教版是同时考虑“文言”语体特征及人文话题这两个因素进行组合编排;而苏教版、人民版与鲁人版采用的是文言文与现代文(语体文)完全混合编组型(同一单元内兼有文言文和现代文),这种混合,较之原先的“雨夹雪”、“插花着排列”的混编方式,其“混合”程度来得更为彻底(我们不妨称之为“满天星式”)。
我们认为,这样的编排方式(尤其是文言白话完全混合型),对于文言文教学的消极作用极为明显。
我们都知道,当前通行的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都属于文选型教材,都是由相互之间在内容上没有必然联系的若干篇文章组成的。这些文章,原本并不是作为教材课文来写作的,而是作为一种社会阅读客体存在的。根据李海林先生的看法,这些课文都具有“原生价值”。这些文章一旦进入语文教材,其价值就发生了变化。它们原本所有的传播信息的“原生价值”仍然得以保留,同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价值,即“教学价值”。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对某一篇课文的教学价值,除有一个在其原生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教学价值的发掘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对其具体的教学价值进行“定位”的问题:它们有许多教学价值,可是在这一个具体的教学点上,我们应该选用哪一点教学价值呢?[6]——这是教学实施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如王荣生先生所言:“一篇篇的‘范文’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既不能从‘范文’中剥离也不能使之独立,因而往往也就没有客观而确定的连接点能将两篇‘范文’内在地贯穿起来。也就是说,作为课程内容的选文,从本质上讲,是圆满自足而各自为政的,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多数是人为的外在标准,甚至主要是编排者的创意或对某种编辑效果的追求。”[7]
因此,具体的某一个文言文本,一旦被吸纳到教材体系当中作为一篇课文,它就必然地体现着教材编者对于这一文本的教学价值的“定位”。比如同样的一篇《鸿门宴》,它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教材当中,其原生价值无疑是相同的;可是,在不同的位置(教材、单元)中,其教学价值的表现却千差万别:它可以是“古代记叙散文”(人教新版必修二),也可以是秦汉文学作品(人教2000版第二册);可以是历史英雄题材散文(语文版必修二),可以是古代战争题材散文(沪教版必修二),也可以是“透视人世百相”的文本(鲁人版必修二);当然也可以是单纯的“文言文”(粤教版必修五,苏教版必修三)。
在“教教材”观念的支配下,不折不扣地“贯彻编辑意图”是每个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想而知,教材编者的“创意”与主观意图,将会怎样直接地影响甚至左右着教师的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行为。在“用教材教”的观念下,课文与教材仅仅是作为教学的素材而存在,语文教师的教学行为,就是借助“教材内容”来生成“教学内容”,“它既包括在教学中对现成教材内容的沿用,也包括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重构’——处理、加工、改编乃至增删、更换。”[8]我们当然支持、鼓励语文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构”,不过,不容否认,即便在“用教材教”理念指引下,语文教材编者的主观意图及语文教材内容对于教学的制约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比如对于《鸿门宴》一文,面对由《鸿门宴》与《林黛玉进贾府》这两个文本组成的“透视人世百相”单元,使用鲁人版教材的教师,除了顺应教材(编者)的倾向,自然地将教学重心放在引导学生透过文本去认识鸿门宴及林黛玉眼里的“众生相”之外,有多少人会同时有意地着眼于其“记叙散文”及“文言文”的特征呢?而执教粤教版教材的教师,估计也基本上将精力都放在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等文言现象上,而不太可能去太多关注“透视人世百相”这一维度。
更不要说,影响教师教学的,不唯课文的组合与单元名目,还有与之配套的、直接表明编者意图的“单元导引”文字及课后练习设计,它们对于教师与教学的导向及制约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比如,我们来看同样包括《鸿门宴》等文言文本的四种教材的单元导引文字:
汉魏晋是我国散文迅速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出现。……学习这个单元,要把握课文的思想内容,着重了解贾谊对秦王朝迅速灭亡原因的分析和司马迁在《鸿门宴》中对项羽悲剧性格的揭示。在朗读和背诵的过程中,注意掌握有关的文言词语和句式。
——人教2000版第二册第五单元“两汉魏晋文学”
这个单元学习古代记叙散文。这些文章或记政治、外交的风云变幻,或记杰出人物的嘉言懿行,都是千古流传的叙事名篇。学习这个单元,既可以从中领略古人的才华和品德,又可以欣赏和借鉴叙事的艺术。文言叙事特有一种简洁之美,学习时要反复朗读,悉心体会。还要学习提要钩玄的阅读方法,学会抓住关键词语,概述文章的叙事脉络,做到纲举目张,化繁为简,提高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
——人教新版必修二第三单元“古代记叙散文”
本单元四篇课文都与战争有关,课文中的人物充分地体现了传统的英雄精神。《宫之奇谏假道》描述了幕后英雄的智慧,《荆轲刺秦王》展示了失败英雄的豪情,《鸿门宴》让我们感受英雄的性格与命运,《赤壁之战》引我们思考英雄对历史的影响。
英雄崇拜,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情结。让我们循着英雄们渐远的足迹,进入历史深处。
——沪教版必修二第四单元“古代战争、英雄散文”
阅读文言文,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还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语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形成较大的古今差异,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困难。但只要潜心其中,由流溯源,就一定能觅得学习文言文的津梁,汲取古代经典的智慧。
——苏教版必修三第四专题“寻觅文言津梁”
从这四段话中我们可以分别提取出四个关键词:文学,叙事,英雄,文言。遵循这样的单元要求(教材编者意图)来实施教学,同样面对《鸿门宴》这一文本,其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学重点的确定是明显不同的。
至此,我们就要提出疑问了:在教学《鸿门宴》这一古代文本时,按照上述苏教版教材编者的要求,无疑应该以“文言”为教学重心(哪怕不是全部围绕“文言”,至少也须重点着眼于“文言”),那么,其他几种教材的《鸿门宴》教学,除了分别强调“文学”、“叙事”、“英雄”(或着眼于文体,或着眼于题材)之外,还要同时关注“文言”这一维度吗?如果要关注,那么,应该关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在教学时如何处理“文言”教学内容与“叙事”教学等其他内容的权重呢?
事实上,教材给教学造成的麻烦,使用教材的一线教师们已经有切身体会了。江苏无锡的徐忠宪老师以“文言文教学的彻骨之痛”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揭示了苏教版教材对于文言文教学造成的伤害:“笔者和江苏省全体高一语文教师使用苏教版课本进行语文新课改已经整整一年了。反思这一年新教材使用效果,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斗胆说一句:苏教版新课本给高中文言文教学造成了彻骨之痛。”而“文白混编,忽视文言文教学的特殊规律”正是其“三痛”之第一痛。他认为,苏教版“文白混编”格局导致学生的文言文学习零碎而不成系统,形成重课文思想情感而轻语言文字的课本定势。[9]
耐人寻味的是,苏教版教材编者自身对上述问题其实也是早有警觉的。教材编者之一黄厚江先生曾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新课标教材的特点与教学》一文中告诫大家(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和以前的单一的文体组元不同,这套教材是以人文主题为统领进行组元。但在教学过程中,绝不可着眼于人文主题进行教学,更不可把人文主题的解读作为教学的内容,否则就背离了语文课程的基本要求。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立足于语文学习,必须把语文学科三维目标的具体内涵体现在教学过程之中。……整个教学活动都必须坚持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为目的。文本资源的利用,也不可局限于专题的人文主题和板块的专题,要尽可能充分发挥文本的价值。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绝不可放弃文言文教学的基本任务,进行架空的人文主题解读,而应该在文言文的阅读过程中探讨有关问题。[10]
就现代语体文教学而言,较之实行多年的人教旧版统编教材的以文章文体为统领进行组元的方式,笔者以为,采用“以人文主题为统领进行组元”有其更大的合理性。可是,像苏教版(还有人民版、鲁人版)这样,不考虑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目的及教学规律的差异,不加区别地将这种组元原则贯彻到文言课文身上,是缺乏理据的,对于教学实践的干扰作用也是无法否认的。教材编者关于“以语言为核心”、以文言文教学为“基本任务”的初衷,与其教材编写的实际可以说是相背离的;在现有的教材格局下,“放弃文言文教学的基本任务,进行架空的人文主题解读”的所谓“文言文教学”,几成当下文言文教学的正统与常态。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追求现代语体文同文言文完全“融合”的苏教版教材,在其教材体系中专门设置了一个纯粹的文言文专题“寻觅文言津梁”(必修三),这是苏教版必修五册教材中唯一的“文言文”单元。为什么要安排这个专题呢?《语文教学参考书》(必修三)“专题内涵解说”中,编者专门指出:“本专题为落实这一要求而专门编排,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文言文基本特点和阅读文言文的基本规律,引导学生把握文言文学习的重点,掌握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法,提高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我们不禁要设问:学生单单凭借这样一个专题(寥寥6篇文言文)的集中学习,就真的能如教材编者所愿,可以“让学生了解文言文基本特点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基本规律”,并最终顺利达成“觅得学习文言文的津梁”的目标吗?
说到文言文阅读教学的数量问题,如王力先生所说:“学古汉语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念三五十篇古文,一二百首唐诗。宁可少些,但要学得精些。”[11]王力先生提出的最低要求是“三五十篇”,似乎与我们这些新教材的文言文篇目数量比较接近了(如果加上初中的,那就更充足了)。可是,像苏教版教材那样,虽然文言课文总数达到了24篇,可是,除了“寻觅文言津梁”专题中的6篇算是正经八百的“文言文阅读”教学之外,零星散布于各册教材各个专题的“古代作品”(文言文),能归入文言文教学范围内吗?何不索性将文言课文从那些混合专题中分离出来,专门设置文言文教学专题以利于真正开展有针对性的文言文阅读教学呢?——这样做,未必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笔者看来,若不囿于现实因素,专门编写文言课本甚至单独设置“文言阅读”课程,应是更适宜更彻底的解决办法),但毕竟也是改变现状的一种思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