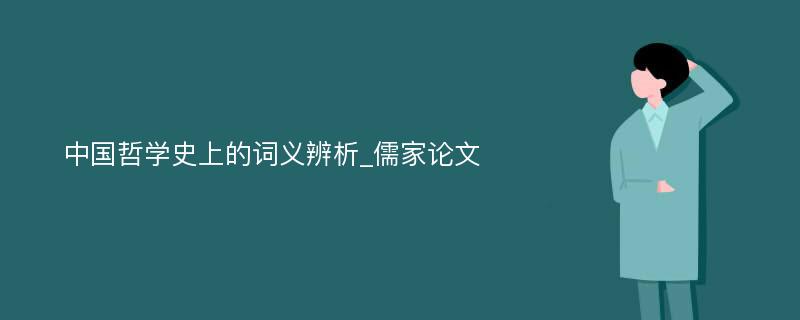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言与意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言意之辨就是讨论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大体上说,言意之辨源于先秦,盛于魏晋,终于明清,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一
春秋战国时期,天与道、神与人、性与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已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人们在表达这些感受和思考时,发现许多内心世界的感受不能用语言表现出来。孔子最早揭示了语言和思想的矛盾,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系辞上》)在他看来,天道性命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予欲无言”。(《论语·阳货》)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言不尽意”的观点。庄子把语言、思想和事物的关系分为三种:“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说明了这三者的不完全对应性。庄子认为如果说出不可言说的道,那就不是它自身了。“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知北游》)而且“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庄子·则阳》)庄子认为人们即使知道了语言文字,也未必能理解其中的思想,所以重要的不是得言,而是得意。“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而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天道》)怎样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庄子不同于孔子的“无言”和老子的“不言”,他开辟了一条超越语言把握道的途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庄子首唱“得意忘言”,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观、人生观、认识论和审美观,以及后世的言意之辨。
二
言意之辨在魏晋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方法论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取得了统治地位。两汉经学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传授、整理和注释儒家经典,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谶纬迷信,把儒家的经典神秘化、宗教化。经学大兴章句训诂之学,注经解字,索隐发微,“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成为繁琐哲学。经学恪守“师法”、“家法”,成为人们思想的禁锢,阻碍精神的自由发展。随着汉王朝的覆灭,思辨的、理性的玄学开始取代繁琐的、迂腐的经学。玄学否定经学的思想武器就是“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说。
汉魏时期,许多文人学士如蒋济、钟会、傅嘏就评论人物、辩论才性已经提出了言不尽意的思想。比较深入的争论是在荀粲兄弟间进行的,实际上反映了玄学和经学的冲突。争论之一是如何看待儒家的典籍。“粲诸兄并以儒术议论,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三国志·魏书》)荀粲看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书籍来理解前人思想的障碍。人们研读六经,得到的并不是先圣的本意,因此,应该对儒家经典持一种批判态度,而不应盲从。荀粲这一思想来源于庄子,“古之人与其不可传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表明他自觉地运用道家的思想做为批判的工具。争论之二是语言能不能表达深奥微妙的思想。“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因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三国志·魏书》)荀粲认为先圣即使在著述六经时,也没能把“理之微者”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这样,汉儒皓首穷经,在六经章句中寻找微言大义,自然是牵强附会,强加于前人的。但荀粲把“象外之意”难以用语言表达看成是根本无法表达,这就割裂了语言和思想的联系,走到了极端。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虽然“好老氏,通辩能言,”(《三国志·魏书》)但他家世代儒业,本人深受儒学的熏陶,加之处于历史的交替期,经学的势力和影响还有相当地位。这使他不可能象荀粲那样,公然斥六经为糠秕,用“废言”的方法否定经学,也没有力量用“立言”的方法提出自己独立的理论,大畅玄风。王弼的方法是“得意忘言。他以老解孔,以庄注易,以道释儒,目的是从六经中得出新的结论,完全不必拘泥于书本字句。“得意忘言”说为扫除汉代象数之学,开一代正始玄风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王弼首先承认言、意、象的依存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周易略例·明象》)由于认识的目的是明象得意,在认识过程中就存在着言与象、象与意的矛盾。“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同上)从玄学重本经末的思想出发,只能舍末而求本。“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同上)既然得意可以忘象,得象可以忘言,所谓经典的权威地位也就自然动摇了。如果严守经典辞句,只知训诂注释,而不知其本义,就更显得没有意义,是舍本求末了。王弼用“得意忘言”说对汉儒经训的繁琐哲学进行了批判,指责他们“一失其原,巧斯见矣。”(同上)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方法论的批判意义。
继庄子之后,王弼又唱“得意忘言”,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提倡思想的自由发展,造就新的学风和文风,促进人的内心世界的觉醒,形成尚通脱、好玄远的魏晋风骨,起了关键的作用。但王弼的“得意忘言”说是建立在语言和思想的分裂前提上的,这就从理论上潜藏着走向不要语言、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可能。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言意之辨。向秀、郭象作《庄子注》,进一步发挥了庄子的直觉主义认识特征。认为“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庄子注·知北游》)就是“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庄子注·齐物论》)玄学家的观点各有差异,但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就是力图超越语言表达思想的障碍,求得思想驰骋的更广阔空间。玄学的言意观构成这一时期言意之辨的主流。
需要提到的是,在阮籍、嵇康等竹林贤士那里,“言不尽意”论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写照。阮籍“本有济世志”,但“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也。”(《阮籍集》卷下)当时“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后人常鄙薄阮籍不如嵇康敢于直言,在司马氏的专制下明哲保身,但遍观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种被扭曲了的人格、被压抑了的精神的内心痛苦。“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嵇康处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残酷、尖锐的时代,即使隐居不仕也不能逃避司马氏政权的迫害,生命毫无保障。身不能超脱便只有心的超脱,“方将观大鹏于南溪,又何忧人间之委曲!”(《嵇康集·卜疑集》)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通过追求玄远的人生理想境界得到安慰和忘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爷处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钱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嵇康集·赠秀才入军诗》)在忘言中达到对理想人生的体验。从人生哲学角度阐发“言不尽意”,自然就减弱了言意之辨的哲学认识论、方法论意义。
魏晋时期“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言尽意论》)只有欧阳建“以为不然”,不甘“雷同”,存心“违众”,作《言尽意论》,自成一家之言,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言意之辨的深化。
欧阳建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唯物的名实观出发论证言意关系。“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同上)欧阳建强调言和意的统一性,语言对于表达和交流思想的重要作用。欧阳建还认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同上)指出了语言不断丰富和变化的性质可以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欧阳建用名实关系类比言意关系,没有看到言意关系的特殊性质,这就内在地承认了语言和思想是外在的联系,以及没有语言的思维是可能的。他用“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同上)的比喻说明语言对思想的依附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理解。欧阳建没有直接回答玄学家提出的“理之微者”、“象外之意”、无形无名的本体、玄之又玄的道能否用语言完全表达的问题,这就很难对“言不尽意”论做出全面、深刻的批判。
三
从东晋开始,言意之辨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文学艺术受“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方法的启发,在艺术创作和审美观中,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画外之景,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特色。另一条是佛教哲学继玄学之余音,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运用于佛学的阐发。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直到东晋才广泛流行,除了社会原因之外,佛学方法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原因。早期佛教的译经和讲解多采用“格义”方法,即用中国传统的名词概念去比附佛经的名词概念。这种方法类似于经学,不利于佛学的传播。东晋佛教徒以道安和支道林为代表,反对“格义”,不拘泥于佛教字句,提倡会通,用玄学对待儒经的态度对待佛经,由此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兴起。
道安开始从事佛教活动时,“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高僧传·释道安传》)道安在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佛经时,力图解决言和意的矛盾,使译文尽可能表达佛学的本义,并且能更好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他提出了翻译过程的“五失本”和“三不易”。“五失本”是如何使译文不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和词句,通过“失本”而得意;“三不易”揭示了翻译中言与意的三种矛盾。一是言和意随着时间发展出现的矛盾。“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二是出言者与会意者的矛盾。“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同上)三是传言者与出言者的矛盾,即翻译者不容易把作者的思想很好地转述出来。尽管道安这里讲的是翻译理论,但实际上说明了语言和思想的矛盾不仅是主体自身的表达问题,而且是在主体之间的交流问题。由于道安在佛学的传播中不执著于文句,旨在融贯大义,使他取得了一定成就。“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
支道林在讲解注释佛经时,受“得意忘言”说启发,表现出革新精神。“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高僧传·支遁传》)支道林因此名噪一时,对于玄学和佛学的合流起了重要作用。佛教哲学接受玄学方法并不仅仅为了佛经翻译,更重要的在于宣扬佛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支道林从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认为“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诡世,岂意者所测?”(《广弘明集》卷一五)对于这种不可言说,难以意测的神秘世界,他的方法是“寄言得理”,“苟慎理以应动,则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畅所以言。理冥则言废,忘觉则智全。”(《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支道林在这里不是承认语言的工具作用。
僧肇不仅是“秦人解空第一者”(鸠摩罗什语),在中国佛教史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在言意之辨上,也是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的佛学论文和经注,在阐述般若空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也提出了他的言意观。由于僧肇不是从翻译理论提出问题,而是作为认识论出现的,这就使他的言意观比道安和支道林等人富有哲学色彩。由于名僧比名士在形式上远离社会和人生的现实,这就使他的思想比玄学家更具有思辨深度。
僧肇以他的“不真”故“空”的本体论为基础,从各个角度论述了语言的界限。他认为,这个“至虚无生”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可言说的。“无相之体,同真际,等法性,言所不能及,意所不能思,越图度之境,过称量之域。”(《维摩经注·见阿门佛品》)佛教的真理“真谛”,也是超然于名称概念之外。“真谛独静于名教之外,见曰文言之能辩哉?”(《不真空论》)作为佛的到达涅盘之彼岸的最高智慧“般若”,也是常人不能用语言理解和把握的。“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般遗民书》)甚至佛经自身,其宗旨也是言琼不能企及的。“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是穷微尽化,妙绝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象所测;道越之空,非二乘所议。”(《注维摩诘经序》)僧肇认为语言本身和“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的世界一样,也是不可规定的。“有无既废,则心无影响;影响既沦,则言象莫测。”(《答刘遗民书》)所以说了许多也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可以说僧肇是最彻底的“言不尽意”论者。
僧肇并不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认识世界的界限,他的认识论是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般若无言,而无所不言。“无有文字是真解脱也”。(《维摩经注·弟子品》)通过宗教的神秘直观,“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般若无知论》)僧肇规定了许多语言的界限,可是他自己又在不断打破这个界限。他解释为了启蒙冥冥众生,还是要借助语言的工具。“玄旨非言不传,释迦所以致教。”(《长阿含经序》)“然群生长寝,非言莫晓;道不孤远,弘之由人。”(《注维摩诘经序》)但是对圣人来说,这种语言又等于无言。“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圣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般若无知论》)僧肇全面论证了“言不尽意”论,再向前发展就是废除一切语言文字,不经过语言而“明心见性”。这是经过晋宋时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论,最终在唐代的禅宗慧能那里完成的。
佛教从汉至唐数百年的时间,翻译的佛经及其注疏浩如烟海。中国僧人的佛典撰述也有数千卷,而且文辞艰深晦涩,已经成为经院哲学。任何佛教徒即使耗尽终生,也难以穷尽佛典,更难领会其教义法理。这样,教人成佛的佛经却成为成佛的障碍,想从尘世解脱却不能从书本中解脱。在佛教睚身的发展面临危机时,出身贫苦、没有文化的慧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开辟成佛的新途径,完成了佛教的转向。这就是“以心传心”,“不假文字”,把依靠佛教的经典转向相信内心的顿悟。既不坐禅,也不念经,把包括佛家经典在内的一切语言文字形式统统抛弃。
慧能的“不假文字”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认为佛以及佛经,并不是外在于人心存在的,而是人心中自有的。“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校释》三一)经书文字的本源还是在人心之内,“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坛经校释》三○)懂得了这个关系,加上众生皆是佛,与其念经成佛,不如顿悟成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同上)慧能主张“立无念为宗”,完全隔绝内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也就取消了语言的媒介作用。由于佛法存在于个人心中,顿悟就完全是独特的个体感受和直观领悟,不需要也不可能运用语言。也就是“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坛经校释》二八)“得意忘言”说还承认语言作为认识的工具、途径和条件,而“不假文字”论则完全取消了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为了回答禅宗的经典《坛经》本身就用了文字的诘难,后期禅宗说:“此经非文字也,达磨单传直指之指也。”“坛经非文字,乃祖意佛心”。(《坛经校释》附录)语言和思想在他们看来没有区别,完全合一了。言意之辨从语言和思想的矛盾发端,这种矛盾在认识中的绝对化的结局就是泯灭二者的一切差别,消融为一体的蒙昧主义。
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依靠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来推行佛教改革,他们想完全摆脱语言的束缚,最后却没有摆脱自己的语言的束缚;唐代“不立文字”的禅宗,到了宋代之后却变为“不离文字”的禅宗;反对佛经的教条,自己也变成了最僵化的教条。后人王起隆在重刻原本坛经时写道:“祖师言句,一字不容增减。”“后人增一字为增益谤,减一字为减损谤,紊一字为戏论谤,背一字为胡违谤。”(《坛经校释》附录)这些都说明“不假文字”是行不通的,是人类文化的倒退。
四
宋明理学的兴起,出现了理一元论。理学家批判佛、道、玄以空、无为世界本体的理论,认为理虽然是观念性的,但并不是虚空,而是实有其理,因而是可以认识、可以表达的。邵雍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象数学出发,论述了言与意的统一生,批判了禅宗“不假文字”的方法论。邵雍认为,“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言著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谓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指出了禅宗的言意观的根本特征正在于“舍筌蹄而求鱼兔”。欧阳修也对“言不尽意”论进行了批评,他在《系辞说》中写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欧阳修充分肯定了语言文字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继承性的重要作用,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是言语和文字、语言和思想矛盾的次要方面。
中国哲学史上对言意之辨做出总结的是王夫之,他的言意观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可能达到的高度。王夫之主要是通过对先秦儒家经典义理的阐发来表述他的言意观的。
对于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予欲无言”的一段话,历来都有不同的解释。王弼认为这是崇本息末,防止象外之意被言教所埋没。王夫之也承认孔子的“予欲无言”是“意义自是广远深至”,但很多人并没有“在夫子发言之本旨上理会”,“只向子贡转语中求意旨”。王夫之认为孔子看到了确实有言不尽意的可能性,“言之不足以尽道者,唯其为形而下者也。……虽天理流行于其中,而于以察理也,愈有得筌蹄而失鱼兔之忧。”所以孔子述而不作,“未尝取其心所得者见之言也。”王夫之是得言失意之忧,王弼是立言湮意之虑,这一点他们没有根本区别。但王夫之不认为孔子无言是为了证明以虚无为本,教化为末,而是认为孔子有很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用“默成”的方式推行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思想。孔子“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见道之大,非可言说为功;而抑见道之切,诚有其德,斯诚有其道,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王夫之把儒家的“言不尽意”论和道家、玄学、佛家的“言不尽意”论区分子开来,认为孔子的“无言”有很强的实践意义。“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说也,非释氏‘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之说也,圣人所以‘自强不息’,‘显诸仁,藏诸用’,‘洗心而退藏于密’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王夫之虽然承认“力有所不逮,而言者本不能尽意者也”,但他与道、玄、佛的区别在于解决矛盾的途径不同。后者是“得意忘言”,王夫之是“有微言以明道”。为了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王夫之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故有微言以明道。”说明了认识对象不同,对使用的语言也有不同要求,而且随着认识的深化,也会创造出表现这种发展的语言。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运用这种“微言”来表达“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思想,就会“微言绝而大道隐”。王夫之指出有两种不正确的思维方式,分别由道家和佛家所代表。一种是道家“以为分析而各一之者,谓阴阳不可稍有所畸胜,阴归于阴,阳归于阳,而道在其中,则于阴于阳而皆非道,而道且游于其虚,于是而老氏之说起矣。”由于道家只强调分析,把阴阳分割开来使道成为虚无,因此就无法用“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微言”来表述世界的存在及规律。另一种是佛家“以为抟聚而合之一者,谓阴阳皆偶合者也,同即异,总即别,成即毁,而道函其外。则以阴以阳而皆非道,而道统为摄,于是而释氏之说起矣。”佛家只强调综合,抹杀阴和阳的差别,结果和道家殊途同归,由不能以“微言之明道”走向“得意忘言”的方法论,“此微言所以绝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五章》)王夫之从思想方法分析佛道两家“忘言”说的根源,把佛家与道家的“得意忘言”说做了区分,使对言意之辨的总结又深入了一步。
王夫之在言意之辨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周易外传·系辞上、下传》中提出了“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即言、象、意、道四者统一的理论。王夫之把语言、思想和实在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解决道器、象道关系,回答言意关系,综合考察名实、本末、言意之辨。王夫之首先证明“天下无象外之道”,因此“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吉凶悔吝,舍象而无所征”,没有卦象,就无法表现和说明道。由于道不能脱离象而存在,“得意忘象”就没有实现的条件。王夫之进而对王弼的“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这对于反对汉儒的拘泥象数、牵强附会、繁琐哲学具有积极作用,但王弼把言意关系比做蹄和兔、筌和鱼的关系是不正确的。王夫之用道器关系说明言意关系,道和器“统之乎一形,非以相致何容相舍乎?”这种统一,他更强调的是“无其器则无其道”,说明了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语言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比欧阳建的认识大大地前进了。王弼以至于庄子的比喻的不合理性在于“筌蹄一器也,鱼兔一器也,两器不相为通,故可以相致而可以相舍。”“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筌以获鱼兔,亦可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他们这种比喻本身就把语言看成是对于思想可有可无的东西。王夫之还用象与言的统一,批判“得象忘言”的方法论,指出:“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得兔之理,舍象而别有得《易》之涂邪?或夫言以明象,相得以彰,以拟筌蹄,有相似者。而象所由得,言因未可忘已。”
王夫之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从认识的目的看语言和思想的密切联系。“鱼自游于水,兔自窟于山,筌不设而鱼非其鱼,蹄不设而兔非其兔。非其鱼兔,则道在天下而不即人心,于己为长物,而何以云‘得象’、‘得意’哉?故言末可忘,而奚况于象。”所谓“忘言”,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因此,语言在认识过程中有关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类对于世界及其规律的反映和掌握。“言所自出,因体因气,因动因心,因物因理,道抑因言而生。则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而奚以忘邪!”而玄学的方法论对于批判经学的教条是有益的,但离真理越来越远,“‘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以辨虞翻之固陋则可矣,而于道则愈远矣。”从老庄、王弼到佛教,他们的言意观的错误根本在于“弃民彝,绝物理”,违背了人类认识和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样,王夫之在对以往各家观点的批判中完成了对于言意之辨的总结。
标签:儒家论文; 王夫之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佛教论文; 佛经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