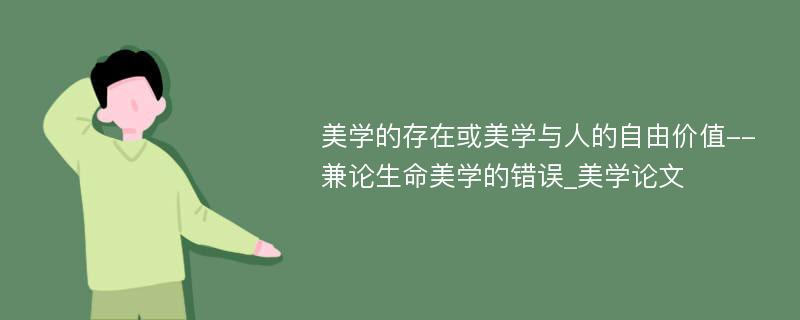
美学之存在或审美与人的自由价值——兼论生命美学的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与人论文,价值论文,生命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3-0059-04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断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美学不是哲学,但美学的研究又离不开哲学,因而无论是哲学或是美学对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人的自我存在的研究。同时,只有将人置于现实的多样化实践活动中进行考察,审美活动中人的自我才是具体的自我,自我超越和人的自由也才有实在的价值内涵。
哲学之思: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西方哲学对人的研究自柏拉图以后就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在近代哲学中这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遭遇到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反动,并形成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同时科学主义哲学(理性)也使自中世纪后由哲学和神学携手建立的世界秩序日渐崩溃。黑格尔虽欲用思辨哲学调和形而上学与科学精神的对立,但由于没能彻底摆脱本体论和知识论范畴,最终进入“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之中。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则形成了对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强烈攻势,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历史地看,尼采“上帝之死”论的出现则最具振聋发聩的意义。关于尼采“上帝之死”的基本内涵,海德格尔进行过最为深刻的阐释,认为“这个神是从柏拉图哲学以来的东西,所以是指一般的超感性世界、广义的彼岸世界、‘真’的世界、形而上学的世界。根据他的解释,‘上帝之死’是意味柏拉图哲学的终了,以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欧洲形而上学的结束。这是彼岸与此岸、真世界与假世界对立思想的终止”。[1](P20)因此,尼采高喊“上帝死了”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应有的全面性、完整性、丰富性、自主性和人的感性生动性。也就是说,“上帝之死”意味着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成了价值的自主评判者,他能规定是非善恶,能辨别真假好坏,人会在自己把握自己自由的过程中获得生命价值的永恒。
关于人的片面性发展的问题,席勒早就在《美育书简》中分析认为,近代社会中人的人格出现了严重分裂的状况,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的一个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因此他呼吁要通过更高的教育即美育来恢复被破坏了的“自然(本性)的完整性”。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得到更充分的表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2](P77)由此可见,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不仅是指人的活动是自觉而自由的活动,而且是指以丰富、全面和完整的人格特性所体现的整体性。还应看到,人不仅在实践性的对象化活动中来确认自身,而且也只有在对象化的活动中才能实现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等的平衡和协调。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审美活动就具有了突出的实践性特征。
文艺复兴、狂飙突进、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科学的发展对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性、神学理性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当现代哲学思潮、文艺思潮成为不可抵挡的汹涌潮流时,尼采就意识到“上帝死了”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查拉图斯特拉的话如此呼唤:“兄弟们,要不断提升你们的心灵!同时别忘了脚!你们这些优秀的舞蹈者,将脚举高,最好是能站立于自己的头上!”[1](P324)尼采所呼唤的正是精神与肉体、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就是要超越形而上学的理性世界。他认为,人应是超越理性束缚和神性统治的人,也应是能超越自身的“超人”,这样的超人,“就是那大海”,就是能覆盖“一切的轻蔑与鄙视”的人,[1](P5)从而是完满的、健全的、自主的、自由的人,也是充满生机的和富有独特个性的人。
《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深刻的“道”之追问使任何哲学的深层总是隐含着形而上的意义,因此无论怎样看待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总难以完全绕开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等等问题,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无论是知识论、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反叛,还是思辨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调和,或者是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都难以完全脱开形而上的方式。
哲学是人及与人相关世界的哲学,美学是人及与人的审美活动相关的美学,因而它们共同的目的就是使人能够成为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具体生动的人和自主自由的人。但是形象地说,哲学犹似一位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固执辨析世界之“真”的思考者,而美学则是一位在现实与未来的交叉处描述世界之“美”的想象者。然而,生命美学论者在提出美学的“真正的追问方式应该是‘人之所是’的问题之后,又说美学“并不追问人是‘什么’,而是追问人之所‘是’,并不追问人的确定的肖像,而是追问人的最为宽广的可能性,并不追问人的现实属性,而是追问人的无法确指的实现可能,或者说,它并不追问什么存在着,而是追问怎样存在着,并不追问‘有’,而是追问‘无’”。[3](P270-271)而追问“人之所是”就是追问“人之为人”,“也就是追问自由之为自由”,人的自由在于“在把握必然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自我超越”,人的特征“在于不可穷尽,无穷无尽,他没有任何的本质,是零、无、否、X”。[3](P273-275)这种哲学式的追问本该有思维转换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它忽视了这样一些基本前提:即没有人的现实确定性,亦无人的宽广可能性;没有人的“存在”,亦无人的“怎样存在”;没有人之“有”,人之“无”亦无从谈起;没有人的本质,也就无所谓人的自我超越。因此这样的追问无疑是一种对人的“不可知论”式的追问。
人的本性是对自由的追求,但人的现实生存条件的有限性,使人无法完全实现这种自由;或者说,人在现实性上是自觉但不自由的,人在可能性上既是自觉的也是自由的。美学所要追问的就是人以怎样的方式成为自觉且自由的人,成为实现自己本质的人,成为全面完整的人。美学要追问人的自由,但不以牺牲对人之为人的现实本质的探求为代价;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的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有着密切关联性,但不一般地把审美活动同实践活动划上等号,而是把审美活动视作人为实现其自由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精神)实践活动。这样人的自我超越才有具体的现实基础,因而才可把审美活动看作是真正属人的活动,是人的自由的一种体现。
美学之思:生活与艺术的审美创造
朱光潜在谈到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时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4](P146)所以朱光潜认为人生应是艺术的生活,而只有艺术的生活与人生的艺术化两方面的完满结合,才能使人把自己的生命史当作一件作品来创造,才能实现高尚人格理想的建立。[5](P228)可见,艺术是审美的,生活也是审美的;艺术需要创造,生活也同样需要创造;艺术的审美创造着理想的精神和心灵家园,生活的审美创造着美好的生活和生存境界。生活的审美是对具体、实在、真切生活的一种艺术化创造和欣赏,即人把自己的现实生命当作艺术品进行创造;艺术的审美则是一种在直觉、想象、情感的世界中进行的创造,即人把自己的精神自由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进行创造和欣赏。全面而本质地看,人类的任何创造都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能动而主观的活动,也是在与对象的关系中确认自身、超越自身的主体性活动,人只有在这样的活动中,才有情感的摇荡、想象的活跃和灵感的激动,也才有直觉的发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那么人进行艺术创造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黑格尔说:“自然界事物只是直接的,一次的,而人作为心灵却复现他自己,因为他首先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其次他还为自己而存在,观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只有通过这种自为的存在,人才是心灵。人以两种方式获得这种对自己的意识:第一是以认识的方式……其次,人还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分,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当他一方面把凡是存在的东西在内心里化成‘为他自己的’(自己可以认识的),另一方面也把这‘自为的存在’实现于外在世界,因而就在这种自我复现中,把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东西,为自己也为旁人,化成观照和认识的对象时,他就满足了上述那种心灵自由的需要。”[6](P38-40)在黑格尔那里,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自然物的方式而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能思考的,他能认识并观照自身,以心灵的方式存在;人创造艺术的原因就在于既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于自己的世界转化成在意识里可以观照、可以认识的对象,从而也把自己观照、认识到的一切转化成心灵的东西,并最终通过这种心灵化的改造复现自身,满足追求自由的需要。“这就是说,人的生活是人的自我创造或自我实现。他能够通过实践的活动去改变外在事物,消除外在事物与人的对立,使人的目的、他的内心生活以至他自己的性格都在外在世界获得实现,从而使人成为自由的主体”,“艺术创造的产生,根源于人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力求要通过他的自我创造去消除外部世界与人的对立,使人的自由在外部世界获得实现,或者说使外部世界成为人这个和自然物不同的‘自我’的‘复现’。”[7](P131)
人的所有特性,人的一切需要的满足,人的一切丰富性的展示,人的生命的完满性和整体性的实现,必然地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本出发点的,审美活动中人的自由价值也因此才是具体化的。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人对对象的创造活动,或者说离开了人的主体性活动,就谈不上审美,谈不上美学,更谈不上人的自由。
然而生命美学论者在否定整个20世纪的中国美学,否定人的审美活动的实践性本质,否定“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等基础上,提出所谓审美就是人的一种“自我确证、自我超越、自我发现、自我塑造的‘非对象化’活动”,其实质就是在美学“虚无主义”的架构范畴中完成对中国已有美学研究的反动,因而也是一种抽空了人的所有具体性、现实性、本质性的美学妄想。“20世纪美学已经陷入绝境,面临的出路只能是或者死亡,或者转型。为此我要大声疾呼:根本的转换来自方法,只有走出主客二分,中国的美学才有希望。我们已经延误了100年,现在我们必须迷途知返,接着胡塞尔、海德格尔讲,接着庄子、禅宗讲。不如此,我们就无法成功地走出美学的误区。”[3](P43)这里的错误就是意欲采取君临一切、鄙视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化态度,割断美学研究的历史经线,用偏执狂的方式建立自己空虚的美学宫殿。
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确实走过不少弯路,出现过一定的失误,但80年代以后基本恢复了美学本体,走上了美学研究的人文正轨。但在生命美学论者看来,这样的研究存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失误,总而言之,所有一切都陷入绝境、应属“死亡”之列。可是,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生命美学论内部存在着未能解决的逻辑悖论: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美学研究是在制造“文字障”,“用‘文字障’蒙蔽生命、蒙蔽自己”,“取代生命、取代自己”,或“干脆生息于‘文字障’之中,让‘文字障’成为生命、成为自己”,即“抽干生命的血,剔除生命的肉,把他钉在死的美学体系、美学范畴、美学著作及论文十字架上,使之成为不食人间烟火而又高高在上的标本”,因而,中国的美学“在令人触目惊心的失误中挣扎着、扭曲着、沉沦着”,且走上了一条“美学体系、美学教材的虚假繁荣”之路,“生命在这虚假的繁荣中被可怜地冰僵”[3](P32-34);另一方面,自己却又在著述、论文中大量设置“文字障”(如套用、生造一些晦涩术语,或使用绕口令式的语句)。一方面他自豪地说自己“日夜与中国的《山海经》、《庄子》、《古诗十九首》、魏晋玄学……曹雪芹、王国维、鲁迅”等等,和“西方的《圣经》、奥古斯丁、雨果、荷尔德林、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进行“对话”,并“期望从上述美学历史谱系、精神资源的‘一线血脉’中寻找一条重新理解美学与美学历史并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3](P408);另一方面却不允许他人进行这样的“对话”,否则就被视作是“对于美学体系、美学范畴、美学论著及论文的盲目推崇”,是“在字里行间、在范畴体系、在著作等身中‘审美’”。[3](P32)生命美学论者置自己的逻辑悖论于不顾,又摒弃了现实中具体、实在的生命本质,却要实现什么思维方式的转换,即实现审美观念从二元对立到“多极互补”的转换,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审美故我在”的转换,最终实现美学研究的总体转换,即用艰涩、绕口的“文字障”将有血有肉的、有情欲的、活生生的生命体在“抽干血”、“剔除肉”之后转换成虚无缥缈的“零、无、否、X”,这难道不是借“生命美学”之名而行践踏生命之实?或许面对如此干瘪的生命躯体和抽象的生命概念,生命美学论者就可以骄傲地向人类宣称:“瞧,这就是美!”
境界之思:美学的诗性居所
艺术通过境界的创造提升艺术的品位,生活通过境界的创造提升生存的质量。艺术境界也好,生活境界也好,都需要由人这个万物之灵在具体活动中的想象性创造;而且,这个境界是美学的一个诗性居所,美学在这样的居所中能获取生存的养分,生命的动力,也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怎样理解人就成为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关键。
卡西尔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8](P87)卡西尔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建立起关于人的观念基础,因此关于人就有着具体的内涵,即“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同时,在卡西尔看来,人的本性就是在“劳作”即活动中实现的自由,而艺术活动是人的本性之所以能得到展现的具体“劳作”方式之一,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艺术的审美境界,正是在艺术“劳作”这一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
宗白华说,空灵和充实是艺术境界的两元,空灵是静照的结果,而“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但他认为,艺术境界的“空”并非是真正的“空”,而是包蕴着“人生的广大、深邃”亦即充实,能使人“体验生命里最深的矛盾、广大的复杂的纠纷”,给人“启示一个悲壮而丰实的宇宙”,[9](P161-163)即“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9](P150)。
宗白华认为美离不开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但以主观、心灵为美的根源,而艺术境界是人在静照万物时由心灵创造的、又蕴蓄着深刻生命意义的充实。这实际是唯物的、辩证的生命哲学在美学观上的表现。我们并不否认哲学研究上形而上学的意义,但我们不主张用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去看待人,而生命美学恰恰以这种原则审视人,即在否认人的丰富具体的实践活动、割断人的主观心灵与世间万相的联系、将人从复杂多样的现实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前提下去看待人。这样,人就成为抽空了血肉的皮囊,人的生命及其自由、人的原初“人性”也就成为空洞的概念。生命美学论者认为,审美境界非他,而是“远离了客体世界,甚至远离了主体世界”的“第三性质”的世界,“是审美活动在对自由生命的定向、追问、清理和创设中不断建立起来的一个理想的世界”,这是“一个原初、本真的世界”。[3](P50-51)由于先验地设定了生命就是绝对的“空无”,否定了现实生命的真正“充实”,否定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因此这样的境界只是靠生涩、奇异的语言装点而成的豪华理论门面。在这种境界中,因没了实在的生命,也没了主体对生命的创造,因而石头仍是原样的石头,草木仍是原样的草木,更可悲的是人的生命也类同于石头和草木。美学不会寄宿于如此荒凉的郊野!若按生命美学对艺术境界的界定,美学就会失去诗性的家园,美学的生命会被肢解成僵硬的碎片而任由抛洒;人的生命自由亦会被驱逐在生命体之外而飘泊流浪,也只好向“生命美学”的繁华理论街市乞求怪异、玄奥的语言装饰。
王国维指出:“诗人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10](P102)他的意思是,就主体性而言,诗人会从主观上以符合自身的内在需求为前提去能动地审视、观照对象;而从主体体验的角度来看,主体须进入对象世界,将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以达到物我两忘、浑然如一之境。这与他所提出的诗人对宇宙人生既“须出乎其外”又“须入乎其中”之要求是一致的。也即人在自身的审美活动中,一方面要和客体对象融通为一,潜心体味,另一方面,又要从主观心理上与对象保持距离,冷静又是能动地把握、改造对象,使其符合自己的审美愿望或期待。所以,即使非常重视人的原初性、强调审美经验的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也认为,一部艺术品意义的产生应有三个条件,一是“作品自身不要像手淫那样从自身上获得满足,作品多少要参照世界”,二是作品整体的“各要素自身也是要有意义的”,第三是要有人进行“创造性的阅读”。在他看来,“意义产生在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因为世界只有在人的目光或人的实践的自然之光中才得到阐明。没有设想,就还是没有对象,反过来……没有对象就没有主体,更没有主体之间的对话”。[11](P148-150)美向我们说话,是说美及美的世界作为对象在向主体说话,审美主体须用心灵去谛听、去创造,才会显示出生命的自由价值。但生命美学论者丢弃了审美活动中主体对世界的参照,终止了对对象的创造性阅读,只追求一种“自淫”性的自我满足,因而审美境界就是空洞的世界,审美活动就不是真正属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审美的生命自由。
我们应牢记生命美学论者准备追随的海德格尔的一段话:“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12](P15)生命美学论者是否应该反省自己存在的方式背离了“最本己的意图”?
[收稿日期]2003-10-24
标签:美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