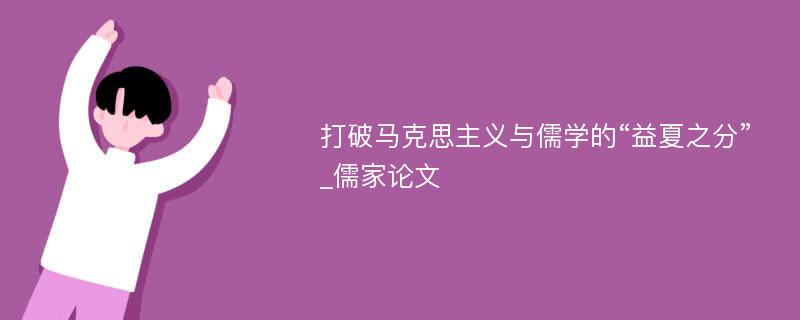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夷夏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持“夷夏之辨”的观点,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澄清,就根本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先后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和现代所奉持的指导思想。儒学产生于先秦,在汉代上升为国家的和民族的指导思想(“国家的”与“民族的”当有区别,但我想,能成为“国家的”必有其民族的一定基础,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当然,如果失去了其民族的基础,现实的就将成为不合理的)。魏晋以后虽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但由宋至清,儒学或新儒学仍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的危亡和文化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逐渐深入人心,并且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华相结合,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1949年后指导中华民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
儒学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是适应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况而使自身的理论形态不断演变的。先秦儒学的最高成就是确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价值观,而在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政治的变革等方面存在着“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陷。儒学在汉代之所以能取得“独尊”的地位,是由于汉儒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由魏晋至隋唐,“儒门淡薄”,反映了儒学理论体系比较粗糙而不够精微的缺陷。宋代新儒学排斥释、老,复兴儒学,实也大量吸收了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由秦到清,中国历史治乱更迭,尤其是宋亡于元,明亡于清,暴露了由法家所建立而被儒家所认可(或儒家欲变革而终未取得成就)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土地私有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宋明道学的理论形态也有重心性而轻实务的缺陷。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反思和批判,说明儒学在当时正面临着自汉以来所未有的一种转型,但清代的文化专制使这一转型没有完成。鸦片战争以后,如同山东六国未能抵御强秦的坚甲利兵,中国文化也不能抵御西方列国的船坚炮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实现现代化;而欲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实行改革和转型。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儒学自身的缺陷,儒学没有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有其历史的和文化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有着契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也与儒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着契合的关系。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又不断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过程。走西方的道路,一是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没有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等等,没有被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所认同。马克思主义不是像佛教、基督教那样由传教士传到中国来的,也不是先由下层民众逐渐传播开来的,而是由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转型而自己选择的。李大钊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要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东西方优秀文化创造性综合的一个中介,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我认为,中华民族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初衷,决不能忘记。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文化输入,一次是佛教的输入,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文化的输入。佛教的输入,有老庄、玄学作为其文化土壤,满足了中世纪需要有一定的宗教情绪和宗教生活的社会文化要求。但佛教的出世取向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有矛盾的,这一出世取向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虽曾有繁盛之势,但终被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所遏制。它一方面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禅宗为主要代表的佛教各宗派,另一方面其一部分精华被宋明新儒学所吸收。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夏之辨”而排佛者,而这一排佛终归是揭示儒佛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和佛教过度发展对社会生活的不利影响。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宋明新儒学之排佛,一是讲公私之辨即价值观的冲突,二是讲“本天”与“本心”之别即哲学本体论的冲突,而不提或很少提“夷夏之辨”。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风云际会中,也有以“夷夏之辨”而拒斥西学者。但历史昭示人们:中西文化际会不仅是中西之争,而且是古今之争;拒斥西学不仅是思想文化上的保守或门户之见,而且其拒斥的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前程。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精华相结合,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由于它指导中华民族完成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除台湾省外)的任务,遂在1949年后成为国家的和民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发展,如何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并且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些都是文化发展和创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有成功和正确之处,也有失误和严重失误之处。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现代阐释,可以引发人们进行反思并且吸取其教益。然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也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以“本心”拒斥“唯物”,二是以“夷夏之辨”排斥马克思主义。就前一点而言,“本心”之说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的思维方式;就后一点而言,“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落后的、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两点是相互矛盾的,“吾儒本天,释氏本心”,既吸取外来佛教的思维方式,又以“夷夏之辨”排斥马克思主义,岂能说不矛盾?
“吾儒本天”,用现代哲学术语说,就是客观实在论。我认为,儒家的入世和道德取向能在中国古代居于主流地位,中国文化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在中世纪走入宗教之一途,是以“吾儒本天”的哲学观念为其理论支持的。程朱之“本天”是本之于“理”,即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合理的、道德的;张载之“本天”是本之于“气”,即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然后再说这个世界是合理的、道德的。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新理学”、“新心学”,而没有“新气学”。“新理学”是本之于程朱理学而综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实在论的思想;“新心学”是本之于佛教唯识论和陆王心学而综合了黑格尔、康德等人的思想。就气学的线索说,张载之后,其气本论被纳入“伊洛渊源”;明中期以后,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和戴震等人的思想可谓“气学的复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有此说),亦可谓“新气学”。在中国近代,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中也有气学的因素。在中国现代,何独没有“新气学”?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气学在现代已不能新,若新就只能是现代物理学或人体科学等等;从另一意义上说,气学在现代也能新,若新就只能是“新唯物论”。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30—40年代,推崇“(横)渠(船)山”之学、颜李之学,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这两方面无疑是相互贯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也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气论或气学讲的,亦可谓是“新气学,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流衍、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本心”与“唯物”之争,可谓张载与佛教之争,罗钦顺、王夫之与陆王之争的一种现代形态,而不可以“夷夏之辨”简单、武断地对待之。
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应该是实事求是地对儒学进行分析,继承和发展儒学在现代仍有价值的合理因素。儒学的核心思想即其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内容,如入世的价值取向,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人本或民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经世济民、重视民生日用的价值取向,强调君子自强和民族自强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无疑是需要肯定和继承发扬的内容。应该说,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不肯定这些方面,就是自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即唯物史观具有儒学所不具有或与儒学的道德绝对主义相冲突的内容。我认为,中国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哲学内容,就是唯物史观把儒家的绝对的道德本体转变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上层建筑(应该指出,所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非如一幢幢的楼房那样是分离断裂的,而是社会发展长河中的“连续统”)。道德是社会生活需要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不断积淀,社会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因而首先也具有继承性和弃旧开新的创造性。儒家之“礼”继承了周代之“礼”,然而周代之“礼”是强调“礼别异”、“礼明分”,儒家之“礼”则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一种创造;儒家之“德”继承了周代之“德”,然而周代之“德”是畏天之威、祈天永命而“敬德保民”,是礼乐的行为规范和仪典形式,儒家之“德”则强调“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更是一种创造。儒家把其继承和创造的“仁”“礼”道德(汉代以后主要是“三纲五常”)逐渐发展为社会的本体和宇宙的本体(宋明道学是如此),这在中国古代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人际关系曾经起了积极作用,但其泛道德论的理论形态不利于科技和经济等因素的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儒学的道德之“体”如果不改变,不还原为社会之“用”,那么在这一“体”的笼罩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根本无从可能(“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昭示了这一点)。在西方文化的诸种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明确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是儒学的道德之“体”转变为社会之“用”的转型;只有这样,原来在儒学的道德之“体”笼罩下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因素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变革,我们也才能够去分析儒家的道德中哪些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哪些是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仅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就是无可取代的。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发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也将发展于中国。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研究,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进行双向反思和互动的问题。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做出使其更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有利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结合的调整。而且,这种指导应该是出于理论的自觉、自愿而又有百家争鸣的指导。对以其他方法研究儒学,也应该做出细致的分析,肯定其合理的学术地位。“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应该具有这种开放的胸襟和容纳百川的恢弘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