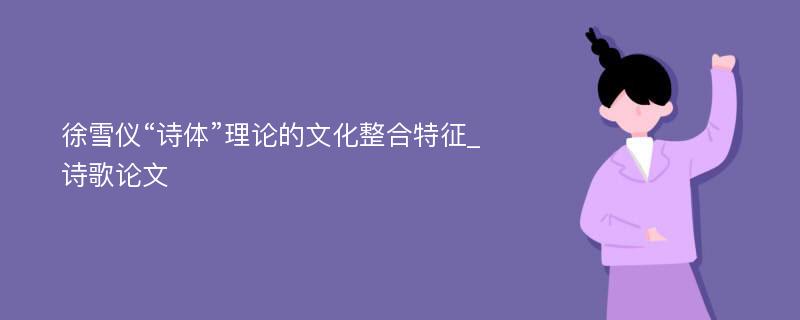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体论文,文化论文,许学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4)03-0131-07
一、许氏论“诗体”的特征: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明末诗论家许学夷穷毕生精力写成诗论著作《诗源辩体》,其所谓“辩体”,主要是从体裁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辨析历代诗歌文本的不同特点和诗歌发展衍变的轨迹,这固然汲取了七子派“格调”论的理论精华,更重要的是,他的“诗体”论吸收了公安、竟陵等派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七子及末五子等格调派单纯以体格声调论诗的弊端,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使其诗学思想具有文化整合的意义。许氏于话语组合牵出体制问题。其论体制,从分类学上有四体:“正体”;“圣体”;反之则为“变体”;正变兼得为“神体”。
其所谓“正体”,除指称各代某种诗体的规范外,特指合乎“雅正”之诗[1]:
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委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卷一第三则)(注:引自许学夷《诗源辩体》,下文凡引此书,在文中注明卷数、则数,不再加尾注。)
可见,他对“正体”诗的看法在本文层面上,有四个因素的规定:一是在审美意蕴上偏于历史内容,“出乎性情之正”,与《诗序》“治世之音”相同,认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无邪”传统。二是话语结构层面的“言委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此指语言节奏上的音律和谐所造就的雍容典雅的气度。而这一切,许氏归结为艺术手段的运用:“盖托物引类,则葩藻自生,非用意为之也。”(卷一第四则)三是审美形象上的“得于声气之和”。他认识到,诗歌本文的形象层面应以“不落言筌,曲而隐也”为上,或寄意于咏叹之余,或意全隐而不露,或反言以见意,或似怨而实否,或似好而实恶,或似谑而实刺。凡此,“含蓄固其本体”,“正在委婉优柔,反复动人也”(卷一第十则)。在相异的形象意义之间,一如多声部音乐,“和而不同”,相值相取,能有声外之韵。故其以为“风人之诗,其性情、声气、体制、文采、音节,靡不兼善”。这类诗歌本文的统领特征是“性情之正”而又本乎天成。
而既得“雅正”,又有“性情之真”者,为“正体”的亚品种。这类诗,以汉魏诗歌为代表,妙处在融化无迹,但这不等于“天成”,却有“天成之妙”。其体制特征,要更丰富些。首先是在审美意蕴上,一方面与国风有关联:“汉魏五言,源于国风。”(卷三第二则)或在话语层面,以委婉优圆,“于国风为近”(卷三第四则);但另一方面,又“本乎情之真,未必本乎情之正”。其次是在话语层面,一为其体委婉而语悠圆,气格自在(卷三第七则);二为声响色泽,无迹可求(卷三第一四则)。虽其中有“格不同而语同,语不同而意同者实多”,亦有“意思重复,词语质野,字句难训”之什,但古诗“在篇不在句”,在此,正见其天成之妙。(卷三第八、九则)再次是“一倡三叹,有遗音矣”(卷三第一五则)。三是在审美形象上,“托物兴寄,体制玲珑”,浑然天成,而无作用之迹。由于这类诗歌体制“本乎情兴”(卷三第三则),是感物而动,不是预先思索的结果,具有无意性,故其在本质上是“本乎情之真”,而非“本乎情之正”(卷三第五则)。因此,它上承风诗之正,下启“圣体”审美上的“兴象”特点。
许学夷论“圣体”,以盛唐诸公(注:此处“盛唐诸公”指李杜之外的盛唐诸家。据《诗源辩体》。)之诗为经典代表。《诗源辩体》卷十四第二则云:
初唐沈宋二公古、律之诗,再进而为开元、天宝间高、岑、王、孟诸公。高、岑才力既大,而造诣实高,兴趣实远。故其五、七言古,调多就纯,语皆就畅,而气象风格始备(七言古,初唐止言风格,至此而气象兼备),为唐人古诗正宗。五七言律,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多入于圣矣。
可见,盛唐“圣体”在话语层面和形象层面的特征与“正体”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唐人“变于六朝”,“以调纯气畅为主”,故而在“体”、“语”方面则是“浑圆”、“活泼”,生气勃勃。(卷十五第四则)在卷十七第四一则,言盛唐诸公“得风人之致”,而“汉魏亦本于国风”。可见,从风诗至汉魏至唐,始终有相承之处,但“正体”与“圣体”的“体”、语之别,在话语和形象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体现在话语的审美意蕴上,由于“才力”、“造诣”的进入,其即事、即景之作皆缘情而生;在形象层面上出现了更为丰富的意蕴,即出现了“兴趣”、“气象”等具有唐代特征性的审美形象;与意蕴丰富相生的是“调纯语畅”、“语多活泼”、“体多浑圆”等新的话语特征的形成,造就了“气象风格始备”、“兼备”、“自在”的“入圣”之诗。把丰富多变意蕴整合成上述话语特征,需要不凡的素质。“圣”在古代,指对某一事物或技艺,无所不通、不能,并深刻把握,它是“通”、“达”的境界,故而能笼天地于形内而“融化无迹”[2]。这表现在诗歌形象的生成上,是“神会兴到,一扫而成”,而“体制声调靡不合于天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卷十六第十七、十八则)。故声韵和平,调自高雅。“入圣”的“融化无迹”表现在诗歌接受上,则是“血气方刚时未易窥其妙境”(卷十七第三零则)。可见入圣的“才力”和“造诣”与形象上的“兴趣”有密切关系,它们之间是“化机流行,在在而是”(卷十七第三一则),融入体格、声调、兴象与风神,而“兴象、风神无方可执”(卷十七第三二则),只能靠体验,领会悟入“神情”遂能有得。其原因在于“入圣”之诗,“兴趣极远,虽未尝骋才华、炫葩藻,而冲融浑涵,得之有余”(卷十七第四三则)。
在许学夷看来,随着诗歌活动的发展,“圣体”入情到一定程度,就会“入于神”而变为“神体”。《诗源辩体》卷十八第一则云:
开元天宝间,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进而为李杜二公。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诣极高,意兴极远(李主兴,杜主意)。故其五七言古,体多变化,语多奇伟,而气象风格大备,多入于神矣。严沧浪云:“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尽寡也。”
关于李杜“变而入神”,我已撰文论述。[3]从许氏分开二公与盛唐诸公的标准看,表面上他用了一系列副词,与盛唐诸公诗歌本文各层面的才力、造诣、兴趣、体、语、气象等相比,李杜在各方面已达极至,其中的丰富性、变化性也无以复加,其归之于李杜“识通变之道”,故而李杜高于他人在于“变”的才能。这样,“变而入神”既需要促进诗歌发展的伟大素质,更需要主体驾驭诗歌生成的各种因素并使之融会而入自然的造化之功。对“变而入神”,许学夷有理性的认识。一方面,李杜之“变”遵守各类诗体基本规范,全面吸收又别裁伪体,集了大成。另一方面,转益多师,遵照美的发展规律,创新了一代诗歌风貌。其创新的突出之处,在对“变”的处理与把握。许氏论述了“入神”的条件或共性特点。
“入神”的第一个条件是集大成或全面总结历代诗歌话语的优长。“李杜五言古,正与歌行相匹”(卷十八第六则),而“五言古,七言歌行,其源流不同,境界各异。五言古源于国风,其体贵正;七言歌行本乎离骚,其体尚奇”(卷十八第四则)。李杜有承传可见一斑。他们的五言古,既宗国风,又宗离骚,使其五言古在不同诗体碰撞间吸收了歌行的错综阖辟、自然超逸之势,在“变”中形成了新的诗体风貌。二是要“体纯”,形成高度成熟的诗体。诗歌体式的成熟,是各种文化因素(包括语言、主体各因素)的天然融合,蕴藉遥深,并显示出外在的形式与内在心性的和谐一致。许氏言“李杜二公于唐体为纯”,“体”多指“语体”和由话语秩序特征生成的格调,这与创作主体的艺术才能相关(见卷十八第一零则),这种才力倘若极大,就善于处理变化不测的各种诗歌语体和形式因素,达于“体纯”。
许氏从“语体”发展史角度,论述了“入神”诗体的话语系统导致“神境”的诞生。“神境”的生成意味主体造诣不惟人力与意志,是以天才之“兴”,达于自然而又独造的结果。无论豪放、沉着,语皆自出机杼,调纯气畅,“奇幻不穷”又“含蓄无量”(卷十八第二一则)。可见,诗之“神体”,表明主体面对自身与对象,无论有多少变量因素,皆能变化灵异,使之浑然一体,不着痕迹,古人所谓难以句摘者,皆指此。
二、发展论意识与整合文化的意图
许学夷诗分三体,既有诗歌发展论的意识,也有在其中整合文化的意图。他提出的三体,着眼于诗歌流变角度,从某种意义上又含有“大文本层次理论”的色彩。诗体经过唐人尤其是发展到李杜的“神体”,其中已经集合了各种诗体的优长,“神体”在本文层次的不同层面,已分别有正体、圣体、神体的规定性,这样,其话语蕴藉就包含多样文化审美意义。随着对本文层次的考察的深入,许氏发现了“神体”中多姿多彩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品质。
许氏发现,从正体、圣体到神体是变化着的,这说明他具有强烈的关于诗体的演变意识。《辩体》卷二第十五则云:
或问:“汉魏诗与李杜孰优劣?”曰:“汉魏五言,深于寄兴,盖风人之亚也;若李杜五言古,以所向如意为能,乃词人才子之诗,非汉魏比也。
卷三第十六则云:
汉魏古诗、盛唐律诗,其妙处皆无迹可求。但汉魏无迹,本乎天成;而盛唐无迹,乃造诣而入也。
上述两则,在比较汉魏与盛唐相同诗体的同时,指出唐人以才力、造诣入诗,才力、造诣这些新的文化因素进入,丰富了原有诗体规范的蕴涵,改变了诗体话语的特征。因此,他认为,新的文化活动因素的进入,是诗体发展的动因之一,诗歌的发展就是反复地利用诗体规范,又不断打破原有诗体规范而优化、发展、消亡着,这是规律使然。《辩体》卷十二第二则云:
五言自汉魏流至陈隋,日益趋下,至武德贞观,尚沿其流,永徽以后,王、杨、卢、骆则承其流而渐进矣。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此五言之六变也。转进至沈宋五言律。
可见,许氏论三体,不仅为了划分诗体区别,而用意在流变。不仅在诗体流变,而是认为在诗体发展至成熟的颠峰阶段,该诗体就会集大成,从而形成本文层面上的丰富性特点。根据上引,在诗体走向“圣体”的过程中,新的文化活动因素如“才力”、“造诣”进入诗体,在吸收原有五言诗优长的基础上,形成初唐五言新的诗体,在形象层面体现出“气象”、“风格”。在许氏看来,一是扬弃与继承:“律句则自齐梁始,其来既远,故至此而纯美。”二是“理势之自然,无足为异。”(卷十三第一二则)“理势”即规律。可见他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已达到较高的自觉程度,凡此种种,至李杜“入神”,道理一样,在“神体”,是吸收了“正体”、“圣体”的诗体优长,在扬弃了对于诗体发展无意义的诗体因素的基础上,加上新的文化活动的主客体因素的进入,丰富并优化了此前诗体的审美蕴涵,使之在本文层面上既集了大成,又变化多端,诗歌本文的各层面融化无迹,达到“入神”的境界。
“入神”已达颠峰阶段,这时,这种诗体最为成熟,后世再难发展,必将促使新诗体的生成。成熟的“诗体”,其本文蕴涵了前此一切诗体的诗性因素,故而其本文层面也包孕前此诗体中的“三才万象”。就“神体”而言,它的本文层面,有“正体”、“圣体”及“神体”的一切审美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李杜“神体”具备了大文本色彩。
诗体流变至“入神”境界,其间的文化变迁起着重要作用。许学夷以为是“正变”运动的结果。因此,其对正变运动的文化语境和诗体发展、变迁的关系,亦有留意之处,他的这一做法,带有明显的寻找文化整合的意图。
在许学夷,三体各有文化价值和审美品质,现在的问题是,文化整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许学夷的上述观点进行现代阐释,我以为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因为文化在历史中流动,构成“文化的传递”。但“就其基本的形态而言,它们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各个层面上的‘文化的对话’所组成的‘文化接触链’。一般说来,由文化的纵向性的‘对话’所组成的‘接触链’,我们称为‘文化的继承’;由文化的横向性的‘对话’所组成的‘接触链’,我们称为‘文化的交流’,它们都是‘文化的传递’的具体形态,……而更多的是以立体的形态进行的,从而构成了‘文化的传递’的复杂而生动的形态”[4]。就诗体文化而言,它在传递过程中,原有诗体的本体性价值,已经后人描述,成为描述的诗体,不再等于原有诗体的事实本身,在“描述诗体”的层面上,诗体的原有规范被作了“不正确的理解”,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各种不同的“理解”,使得诗体价值和功能具有多重性和开放性,当一定时代诗学活动者使这一理解后的描述性诗体与当时当地的文化语境对话时,原有的诗体“描述性形态”进入新的时代语境,形成新的诗歌范型。可见,经过描述的诗体新的价值和新的审美功能不断融合,改变了原有诗体的审美形态,表现为诗体的重构。这样,旧诗体的审美价值与功能不断消融在新诗体的重构中,从而在诗体变迁中不自觉地形成了历代文化的整合。许学夷的诗学意图,不是到此为止,他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在诗体文化传递研究中,论证文化整合的依据,他借用儒学的亲和力与“和”的生生之力力图融合历代审美文化,使诗学理论来一次全面的总结,提升中国古代诗学的学术水平,同时建构他的以“入神”为标志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三、许氏文化整合方法论与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许学夷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和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这得益于他对各种文化特征的充分而均衡的洞察,非率尔操觚者所能窥及。[5]许学夷诗学思想形态形成于明末清初,当时经过宋明理学,儒学在艰难寻求着中国超越性的一体性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其本身在文化传递过程中表现出不同方向和不同深度的发展或变异,因此,儒学振兴不在外在于它的文化威胁,而在于其自身的生命力。在诗学领域,儒家诗学至明末清初经过一千余年而发展下去,就只有一方面保持它固有的政教或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寻求超越,使儒家诗学的审美化走向成熟。这一方法鲜明地体现在许学夷的诗体理论中。
许学夷的“文化身份”或者“本体论的信仰”是儒家文化。当时的儒学振兴语境与他的生存状态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许氏已认识到“文化身份”的重要性。面对明末清初新的文化语境,儒家诗学感召力形成的现实条件无疑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他分析了当时审美文化的各种现实因素,并以自身的文化身份判定当时文化的质态,决定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古代文化中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成儒家文化诗学的感召力。当时各种诗学文化上的主义流派林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颇为热闹的一个时期,……异说纷呈,各种文体的理论批评都有较大进展”[6]。对于中国历代文学思想,明代诗论家几乎都有涉猎,只不过在文化传递过程中根据时代语境有所发展和变异,至中晚明时期,形成了诗学文化的多元格局。从大的方面说,当时自由情感的审美文化已流行了一百多年,成为明代文化的传统,但另一方面,现实情境的变化使审美化的自由不能解决任何人生的现实问题。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生成于明末诗学思想融合时期。不同的是,他改变了王世懋等人的不自觉融合为有目的、有理性的自觉整合。其论先秦至明代诗歌创作、历代选集和诗论著作,清人恽毓龄言其“集诗学之大成”,这一说法一般限于诗体美学领域,尚未有文化诗学层面的意义。今天看来,恽氏的话可作新的阐释,许学夷以正统儒家“中和”观,吸纳了明代释道之学和王学的文化智慧,以之为学术视野,扬弃、吸收并超越中国古代诗学,为历代文学批评作总结,形成新的文化诗学。
也就是说,许学夷的整合既包括文化范式的整合与认同,也在艺术理想层面进行了超越,其中有观念内容的文化艺术设想,又有理想艺术感性范式的实现途径,体现着理论设想与诗学实践的统一。
在诗学文化范式的整合或认同方面,许氏的文化胸怀较为广阔。除认同传统儒家文化外,据明代恽应翼《许伯清传》记载,“晚年栖心物外,萧然一室,窗外古石峻嶒,花竹交映,中设维摩像,颜曰‘维摩室’。每风雨幽寂,则明灯下帏,焚香宴坐,曰:‘吾于释氏,聊借以谴妄心,非欲求生西方,转来世也。’尝言:‘儒者莫先于穷理。释氏、庄、列多夸辞寓言,而庄列产于中土,人知其为夸寓,释氏起于西域,人以夸寓为真,终使笼罩后世,无能自脱,此贪痴之患也。’”恽氏与许学夷为知己,此言当可信。由此,见出其广泛吸纳多元文化的同时,有扬弃与超越,其价值取向的基本尺度是儒家人生哲学,他以面向现实与人生的态度,吸收庄、释之学,弥补儒家和王学之不足,其晚年逍遥的同时,又借佛禅之境,以遣妄心,而于三教之理会通之处,获得营养,辟创人生的审美境界。他不再抓“言志”或“缘情”某一极,而是根据一个诗人或一个时代诗学活动本身的特征,以自身的多元文化造诣与识见面对历代文学活动。其所谓“见”就是一种立足多元历史文化的态度,其所谓“识”,乃是面对多元文化时自己的取向,这一取向对社会人生具有有益的意义。可见,“识”不仅是一种素质,还是对历史发展本质的把握能力,它需要“理论家的勇气”。《诗源辩体》卷三十四第三则云:
学者闻见广博,则识见精深,苟能于三百篇而下,一一参究,并取前人议论一一绎,则正变自分、高下自见矣。今之学者,闻予数贬古人,辄相诋訾,虽其质性之庸,亦是其闻见不广故也。譬之学书者,识见不广,偶见一帖可意,遂终身笃好,不复向上寻觅,便是井蛙夏虫耳。试于古篆、秦隶而下一一究心,则知古人干品万汇,高下不齐,一肢半体,未足以概其全也。
这不仅体现在许氏的文化胸怀上,也正是立足于对历史文化的多元和精深的识见,在诗学方法上,才不至于隔靴搔痒,而是针对对象的自身特性,在“情”“意”二者之间整体把握。《辩体》卷三十四第六则云:
学汉魏而不读三百篇,犹木之无根;学唐人而不读汉魏,犹枝之无干;乃至后生初学,专读近代之诗,并不识唐诗面目,此犹花叶之无枝,将朝荣而夕萎矣。
中国诗歌这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仅得一枝一蔓,以为全体,历代多数诗评家都有这一缺陷,故其“数贬古人”,即使一人之作,亦有“好丑”之别,今天看来,却是切中肯綮、实事求是之说。于此可见,“识见”在审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有了“识见”,就不为任何大家所恐,能以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尺度整体把握历代诗歌,衡量诗歌高下。他一方面对审美文化中缺乏活力的因素进行扬弃,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抓住一极或一点而不及其他,只会导致发展机能萎缩,这体现了他对历代艺术理想层面的超越,并在艺术观念内容方面提出了设想,在理想艺术范式实现的途径方面也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辩体》卷三十四第二一则云:
学者于诗,或欲为六朝,晚唐,其失为卑;为锦囊、西昆,其失为偏;又有但争一字之巧、一句之奇,以新耳目,初不知有六朝、晚唐,亦不知有锦囊、西昆也,则其失为野矣。或曰:“汉魏、初、盛自不必学,六朝、晚唐、锦囊、西昆,亦已有之,不若因时趋变,足快一时耳。”予曰:子不见器用与冠服乎?三岁而更新,十岁而易制,再更再易,而新者复故矣。大历诸公,而律始变焉,元和、开成、唐末,而又变焉,至宋,而又再变焉,再变之后,而神奇复化为臭腐矣。然后之论律诗者,宗初、盛唐耶?宗大历、元和、开成、唐末耶?宗宋人耶?故作者但能神情融洽,出自胸臆,观者自能鼓舞,固不必创新立异以为高耳。譬之于人,须眉口鼻皆同,而风神意态不一,岂必须眉变相,口鼻异生,始为绝类乎?试以予说求之,其惑自祛矣。
在上述所引及《诗源辩体》卷三十四部分中,许氏对其艺术观念、艺术理想及其在艺术实践层面,对艺术理想的实现途径,进行了集中论述,其总结意识与超越整合意图,稍加体会,便可了然。其去“古惟独造”,提倡“我则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卷三十四第十九则)。首先,在创作的本质追求上,是“神情融洽,出自胸臆”,而非刻意求新求奇求“变”。今天看来,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家,其审美心理结构中已包孕时代的文化审美精神,以这样的精神结构与审美心理自能形成自己的艺术观念;去创造时,能“神情融洽,出自胸臆”,自能创出新的境界。再实践层面,既能符合个体的艺术观,又能暗合艺术的理想范型,这在历史层面,就能包孕某一艺术范型在发展中的优秀成分,这些成分由于天然组合,趋于丰富完美,达于艺术范式的理想境地:“须眉口鼻皆同,而丰神意态不一。”故“不必创新立异以为高”。其次,许氏以为单纯追新逐异,抓住一极任意发展,既不能扬弃艺术活动中落后的因素,亦不能在多种艺术活动素质中相摩相荡,相值相取,“因时趋变”,“变而入神”。反而走入奇异之境:“为卑”、“为野”,“神奇复化为臭腐”。以人喻之,则“须眉变相,口鼻异生,始为绝类”,“绝类”是发展机能萎缩的表现,缺乏生气与活力,会导致某种艺术形式的消亡。若整个艺术活动如此,亦能导致艺术活动的消亡。于此见出,第一,许氏对审美文化整合,以及借助整合,以期出现新的充满生机的审美文化范式的努力,得到了艺术发展史的支持。他在艺术观念领域,从内容到形式的设想,在艺术理想层面,以艺术实践活动中的感性范式变化,支持他的设想,抛开诗学方法不说,其诗学思想中对审美文化范式的整合,在艺术理想问题上得到了印证。第二,许氏对文化的价值与审美品质是有取舍的,取舍的标准是尊重艺术活动发展的需要。许氏对历代诗学思想的总结,目的是寻找艺术发展或“正变”交替中的动因。艺术能否发展,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质的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言而喻。
〔收稿日期〕2003-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