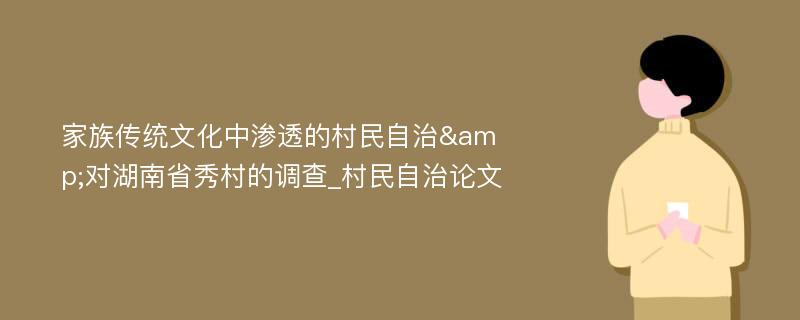
浸润在家族传统文化中的村民自治——湖南省秀村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省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村民自治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在长期共同生活和世代繁衍中,家庭不断扩大,形成为一个由若干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所组成的家族。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社会。中国的不少村庄就是以姓氏命名的。由于家族通过血缘关系将若干家庭联结在一起,并内在地产生出家族社会权力,因此这一权力一经产生,必然会深深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之中。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将其称之为支配乡村社会的长老权力。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由于家族传统的悠远,家族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更突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族权视为束缚中国农民的四大权力之一。1949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但家族传统文化并没有很快消声匿迹,而是随着实行家庭承包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有所复萌。继家庭承包之后崛起的农村基层新的治理形式——村民自治,必然会受到家族传统文化的浸润。通过对湖南省秀村的调查,便可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一、秀村历史沿革与家族传统变迁
秀村位于湘北洞庭湖畔一个大垸子的中间。该村现有耕地1792亩,其中水田1337亩,旱地80亩、水面100亩, 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农耕村落。1995年,全村有283户,1051人,男性562人,女性489人, 均为单一的汉民族。
秀村历史上是一个移民村落。明朝洪武年间“江西填湖”时,秀村始祖孙公率领全家从千里之外的江西吉安一带,经南岳衡山迁徙到湘北洞庭湖畔,随后围湖造田,休养生息,逐渐形成一个家族村落孙家岭,即今天的秀村。由于孙氏家族兴盛,其子孙向外扩散。秀村也因此成为湘北地区孙氏家族的活动中心,受家族传统文化影响甚深。1949年前,秀村一直存在完整的家族组织,由族长、族正、各房系和各支派首领组成家族董事会,行使对本家族治理的最高权力。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主持祭祀、修谱、管理族产,制定和执行族规等。与该地区其他家族相比,孙氏家族以其盛大的修谱活动和强悍的家族武装著称于湘北。因为前者可以显示家族的强盛并成为家族的纽带,后者则可以维护和扩大家族的利益和影响。严密的家族组织体和强有力的家族武装,使秀村的治理具有高度的家族自治性。任何国家权力的统治和渗透都需要经过家族体系发生作用。即使保、甲长也必须对族中长老礼让三分,大小事务都得向族长咨询,取得族长同意、认可和支持后才能实施。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家族自由的并存,并以家族自治为主导,构成秀村治理的重要特点。
1949年后,秀村的家族及家族权力受到削弱和打击。土地改革时期,随着对封建势力的打击,秀村进行了没收族田、拆毁祠庙、烧毁族谱、斗争族长等运动。为削弱孙氏家族势力,土改工作队将孙家岭一分为三,分别归为三个乡管理。土地改革后,秀村被纳入到集体化过程中。1958年,秀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大队,其建制范围一直延续到现在。1983年由大队改为村。土地改革使秀村的家族势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在这之后,家族传统长期被视之为封建残余而受到批判和清理。1971年,孙氏家族的祖庙被拆毁,标志着家族组织体系的彻底消亡。自此,秀村一直不再存在组织形态的家族活动。
秀村的家族组织体系虽然趋于瓦解,但家族传统文化影响不可能随之很快消除。特别是家族赖以存在的姓氏家族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1949年前,秀村所有村民都姓孙,没有杂姓。1949年后,张、李等姓氏家族陆续迁入,孙氏家族的单一性不复存在。但是,历经40多年,孙姓仍是该村的大姓,在283户家庭中,孙姓有229户,占总户数的80.92%。
1980年代以后,秀村的家族传统文化逐渐复萌。首先,秀村的家族传统主要是依靠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加以限制的。1980年代以后,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紧张的意识形态控制得以松弛。传统的丧葬礼仪习俗首先复兴。这一习俗是一种追颂先人,且有严格血缘差序格局的活动。其后果将会强化村民的血缘关系和“自家人”意识。村民们开始普遍以姓氏辈份相互称呼,流行多年的“同志”一词用得愈来愈少。其次,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分户经营。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一家一户的村民需要寻求社会帮助,其主要对象就是被视之为“自家人”的本姓氏家族成员。这无形中又增强了村民们家族意识。第三,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需求扩大,希望通过姓氏家族关系满足社会交往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家族传统文化迅速扩张,并以一定组织形式加以表达。1991年,湘北数县的20多名孙氏后裔到秀村认祖归宗,进行家族联谊活动。为适应家族联谊和扩大家族影响需要,1995年,在孙氏老人的组织下,召开了湘北70多名孙氏族人参加的族人代表会议,并成立了修建祖庙领导小组和祭祖筹备委员会,分别准备建庙和祭祖活动。其经费主要来自于收取丁口费和族人自动捐款。
尽管秀村的家族传统迅速复萌,但没有,也不可能回复到1949年之前。原因一是经过数十年的变迁,传统的一整套家族组织体系受到破坏。二是家族力量的扩大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为此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秀村所在地区的报纸曾多次发表文章,指出大规模的祭祖浪费人力、财力,增加农民负担,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由此秀村的祖庙修建便很难大张旗鼓地进行。三是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个人观念在意识形态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甚至取代家族意识。这在年轻一代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秀村的家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要是中老年人,一些中青年人只是以一种应付的心理参与。因此,在秀村,只有家族传统文化及活动,而没有正式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权力。但即使如此,秀村受家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仍较大。秀村的孙氏家族还准备在2000年以前启动大规模的修谱活动。
二、家族传统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村民依据法律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村民在参与村落公共事务活动中,必然会受其自我意识的支配。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由上而下的法律意识尚相当薄弱,内生于社区的家族传统文化却深深浸润在心理意识之中,并会自觉不自觉影响其自治行为。
1983年,随着政社分离和乡镇政府的建立,秀村由生产大队改为村。但在1983到1987年,村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87年,根据政府指示,秀村村民委员会正式挂牌,村党组织也得以改组和加强。村组织的任务有所增多,如调解纠纷和发展企业等。
1987年《村组法》颁布后,1989年12月,湖南省制定并通过《村组法》实施办法。1990年初,随着自上而下贯彻实施《村组法》及有关精神,秀村人开始了解《村组法》及相关知识。1991年初,秀村进行了《村组法》颁布后的第一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选举以等额方式进行,由村民直接投票。但这之后,村民委会干部更换十分频繁。1995年初,秀村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政府的直接指导下,采取差额直接选举。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年龄较轻,积极性较高,做了一些被认为是“真正代表了村民利益的事”,受到村民的好评。通过村委会的选举,村委会组织得以健全,并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从总体上看,秀村的村民自治是在国家有关法律和政府指导的轨道上运作。但在村民自治运作的一些环节中,也受到家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由于秀村的大多数村民都姓孙,1949年后主要村干部也大多数姓孙。但在1980年代前,干部主要以上级任命的方式产生,干部和村民的阶级意识大大高于“自家人”的家族意识。1980年代以后,随着家族传统文化的复萌,干部和村民的家族意识都得以强化,并渗透到村干部的产生过程中。1991年后的村委会干部先后有7人。其中有5人属于孙氏家族。另外2人中,有1人虽然是外姓,但属于孙氏家族体系的人,另1 人为妇女主任。这意味着村干部要当选,必须得到占村民大多数的本家族的人认可。这种情况在村干部候选人提名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秀村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候选人通过三种渠道提名。一是上届干部为当然候选人,二是上级领导直接指定,三是由各村民小组推荐候选人。1991年是等额选举,候选人即可顺利成为村干部。各村民小组从本小组和本家族房派利益出发,尽可能将本组和本家族房派的人推荐为候选人。孙氏家族共有五房。在原村委会干部中,五房的人最多。村干部候选人推荐时,五房推出3人,其他四房联合推出3人。即使如此,其他四房推出的候选人中也有2人被否定。 由于上级对村民小组长的人选影响较小,其组长人选的推举更容易受到家族房派的影响。大多数村民小组长同时是家族房派首领。第三村民小组由2房和3房村民共同组成。两房组成一个生产队(小组)达30年之久。但该队一直存在2 个队长(组长)。推举组长时,两房派都希望本房派人当选,最后只能维持2 个组长并存的局面。
在村委会正式投票选举中,“自家人”、“本房人”的家族房派意识也在无形中发挥作用。1995年实行差额选举。在投票过程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将选票投给本家本派人,希望本房派的人当选为村干部,以期在分配计划生育指标、下派任务等方面给予一定照顾。更多的人虽然没有这种利益冲动,但仍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投本家人的票。有的村民难以在能力和本家族人之间进行选择,只好弃权。
由于村干部要经过村民选举产生,家族意识势必会影响干部的管理行为。干部在管理活动中也要考虑事实上存在的家族关系和影响。这在村民纠纷的调解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家族房派依靠姓氏血缘关系形成内部的凝聚力,同时对家族房派之外具有排他性。分户经营使各户的矛盾和纠纷增多,而家族意识又使这种矛盾和纠纷趋于复杂化,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干部在调解矛盾和纠纷时难免有“投鼠忌器”的心理,尽量避免干预。计划生育是农村工作的难点之一。在秀村,村干部每年都要请镇干部下来做工作。因为计划生育直接关系到传宗接代,最容易得罪族人。孙姓二房和四房间曾为责任田界限纠纷发生矛盾和冲突。由于此事涉及到村民小组间的关系,村支书和村治保主任出面调解,但当事人双方均认为没有为自己说话而不理会村干部。
作为村正式公共组织代表的村干部在村的治理活动中要考虑家族问题,主要是因为家族通过姓氏血缘关系网络将众多村民联结在一起,干部本身也置于这一网络之中,不能不受其左右。80年代以后,尽管秀村的家族传统影响迅速扩大,但尚没有形成与村正式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这除了正式组织后面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作支撑外,主要是秀村的家族首领已接受现代文明,与国家政权力量有一定的“亲和性”。但是家族传统一经恢复,便会受到家族利益的驱动,从而寻求正式组织的支持。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本家族的人推举为干部,并使其受家族传统网络的影响。同时,家族首领大多是本村德高望重且有一定政治经验的老人,对于年龄轻、辈份小的村组干部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秀村的家族主要是通过影响干部的公共管理行为来实现其利益要求。由此,家族在一定程度上与干部具有一种合作关系。
首先,家族首领作为村民代表将一定的权力让渡给村干部。自1981年后,秀村除选举之外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实际行使村民会议的权力。它由以下人员组成:(1)全体党员;(2)在职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3)各村民小组长;(4)一般村民代表,主要是家族各房、派、系中廉明公正、德高望重的首领。根据有关法规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大会闭会期间村内最高权力机构,且定期召开会议,以讨论决定村内重大事务。但在秀村,村民代表会议一般是前三部分人参与,成为村民干部会议。作为村民代表的家族首领很少参加会议,更没有发挥独立作用影响村落公共管理的意识,从而在事实上将属于自己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力让渡给村干部。当选村民代表只是正式权力赋予家族首领的一种荣誉性称号。
其次,家族首领作为本家族的老人和能人,在调解本村社会纠纷和维持本村利益方面可以起到村干部难以起到的作用。在历史上,由家族老人调解纠纷便成为传统。近10余年来,若涉及到分家析产、兄弟纷争、叔侄矛盾等“自家人”的事情,一般都由本家族的权威老人出面加以调解,村民很少找村干部,村干部也很少主动过问。因为“自家人”的事情在“自家人”内解决更容易为当事者双方接受。即使对于一些必须由村干部出面解决的重大纷争也往往邀请家族权威老人协助做工作。1993年,第三村民小组因为一块责任田而起纷争。该小组主要是由孙氏家族二房和三房的族人组成,80年代中期便因责任田的调整有过纠纷。1995年是责任田15年承包期到期和重新调整之年。两房村民为责任田的肥瘠问题相互争吵,矛盾有扩大趋势。最后由村干部出面,并邀请孙氏家族权威老人参与,与双方代表协商后才妥善解决。
家族力量与正式权力的合作,一方面协助村干部做了一些工作,对于村民有效的自我管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这种合作中无形地使正式权力的公共权威性有所消蚀。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村干部制定了公共性的村规民约,但没有能有效地贯彻执行,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条文村干部自己也不能执行。如村规民约第13条规定:“凡组织或者参与宗族活动,挑起宗族矛盾,对组织者每次罚款50—200元, 对参与者每次罚款20—100元。”但大部分村干部都参与了1995 年的祭祖联宗活动,且未受到处罚。
三、有关思考与看法
从秀村的调查情况看,家族传统文化有其古老悠远的历史和深厚广阔的社会土壤。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现象还会存在,并会渗透到以大众参与为特征的村民自治进程之中。
秀村家族变迁的状况表明,当今的家族影响和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与1949年前的情况已大不一样。首先,家族影响毕竟是传统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家族传统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秀村年轻一代的家族意识远不如老人的事实便是明证。其次,家族影响只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权力。它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国家正式权力的允许和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程度。当今的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程度还相当高,这就意味着家族权力不可能取得国家认可和社会承认的合法性。在秀村,村干部在公开场合从不愿承认家族在村落治理中的影响。由秀村所在镇统一制定的村规民约明确规定不能参加宗族活动。当家族力量与村正式组织发生冲突时,国家力量便予以介入和干预。所以,当今的家族很难构成完整严密的组织性力量,只是作为一种传统化而存在,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也有限度。
但是,对此影响也不可忽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性力量。特别是家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人文基。它植根于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之中,并会支配人们的政治社会行为。这种情况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表现得尤其突出。一是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意味着国家权力收至乡镇,在乡镇以下的村落由村民群众自治。尽管村干部在一定意义上要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但他们毕竟生活在村民之中。村干部的产生和其公共管理行为都不能不受到家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二,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管理。村正式权力的运作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家族的影响,特别是在调解社会纠纷方面,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使权力的公共权威性受到侵蚀。其三,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家族传统文化有可能将本家族的人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性力量,并以其力量与正式权力抗衡。当村民仅仅只是将自己视为某一家族房派之中的族民,而不是国家法律认可的公民时,村民自治就有可能变为族民自治。
考虑到家族传统文化的长期性、广泛性,对于其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应该十分慎重对待。家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可能依靠简单的政治运动加以消除。在调解一般家庭和村民间的纠纷等方面,它对于村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家族毕竟具有排他性。其发展有可能损害依据现代国家法律精神运作的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进程中,通过强化国家法律意识和正式组织的公共权威性,可以使家族传统文化受到必要的节制。特别是要通过国家权力支撑下的公共权威组织的作用,有效抑制家族力量对村民自治过程的渗透。在家族传统力量较大的地方,实行村民自治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社会背景,从而采用相应措施,以防止村民自治蜕变为族民自治。
(此报告是笔者拟定提纲后约请孙龙进行实地调查,并在其提供的调查材料基础上写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