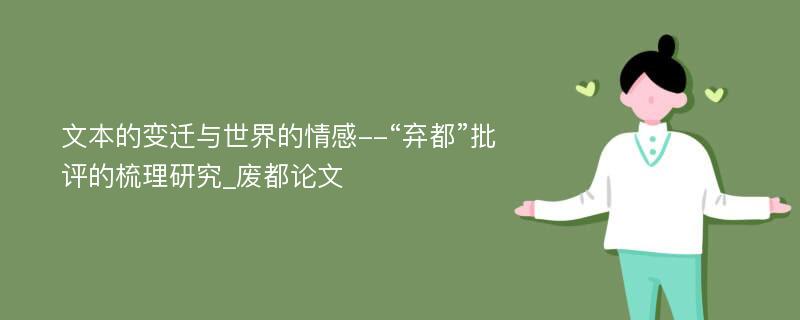
文变染乎世情——“《废都》批判”整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情论文,废都论文,文变染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以“商州系列”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贾平凹写出了自己第一部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废都》,由《十月》杂志全文刊载,同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后记”中,贾平凹称其“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然而,又如他所言,书出版之后就和作者完全脱节。之后,围绕《废都》的评论成为1993年最为热闹的文化事件,赞之者誉之为“好书”、“奇书”,毁之者称之为“黄书”、“黑书”。对一部作品竟然出现如此迥异的评价,这些充满矛盾和分歧的文学批评也折射出转型期知识界波涛暗涌的动荡与哗变。此后,在新闻媒体、书商的助势之下,批评《废都》的文章纷纷结集出版①,对其否定性批判终成压倒之势,这也导致《废都》在出版半年之后被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以“淫秽色情”、“低级庸俗”下文收缴。可以说,《废都》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时成为知识界的“公敌”,遭到很多文章的严厉批评、否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废都》批判进行整理。韦勒克告诉我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批评规范”②,时过境迁之后,《废都》作为“重放的鲜花”③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当年一些激烈批判《废都》的学者也做出反思。因此,本文的整理主要限于1993年6月《废都》出版到1994年1月被禁,从中找寻文学转轨的历史脉络。
一、多重《废都》滋味
在《废都》批判的风潮中,国内一线学者、批评家几乎全部卷入,新闻界、学术界、出版界等概未能免。然而,“在‘《废都》热’——《废都》的阅读与评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于《废都》的二度写作——两种完全不同的‘《废都》滋味’。一种是庄之蝶的同代人对《废都》感伤的抚摸,一种是晚生代对它的愤怒的呵斥,以至认作是‘一部嫖妓小说’”④。巴赫金认为,“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⑤。一本小说多重阅读,其所衡量的尺度或文学批评成规存在何种差异和分歧,还原其批评话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转型期作为文学事件的《废都》所裹挟的理论紧张。
最早发出声音、并极力推崇《废都》的是陕西评论界。1992年,在痛失杜鹏程、路遥、邹志安之后,陕西文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废都》的出版及相伴随其间的“陕军东征”提供了重振旗鼓的机会。因此,在《废都》还未出版的1993年初,王新民和孙见喜就拟发征稿信,向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文朋书友征集有关贾平凹创作尤其是《废都》的文章,先后编辑出版了《贾平凹与〈废都〉》、《多色贾平凹》、《废都啊,废都》。他们也最早对《废都》表示力赞:“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废都》是第一部完满实现了向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回归的作品,所谓的《红楼梦》味儿即由此出。贾平凹用《废都》向现行的一套文艺理论和阅读习惯挑战。这部小说将传统的创作实践抛弃甚远,这是中国小说回归自我的第一声响雷。”“《废都》是继《围城》之后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杰作。这是贾平凹的里程碑,标志着平凹进入自己艺术创造的巅峰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极具开拓性的一部小说。”⑥
贾平凹的好友白烨,西北大学的校友王富仁,评论家雷达、学者温儒敏等等更多地给予作品理解和同情,称其为“真实的心灵刻画”和“世情小说”。他们认为:“这种自剖魂灵的勇气构成了作品的最大内力与魅力。因为不再做作、不再雕饰、作品在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上也打通了原有的界限,可读性与可思性也就融为了一炉。人们从朴茂中读出了深邃,从轻松中读出了沉重,从而借助《废都》这面多棱镜反观自我、认识环境和思索人生。”⑦“《废都》属于世情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有极密切的血缘,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汇,化合的功夫之到家,令人惊叹,可说得《金瓶》、《红楼》之神韵。其叙述语言流畅、练达、素朴、自然。”⑧“贾平凹的《废都》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所形成的人文景观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或者说,是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去体验当今历史转型期的文化混乱,表现现代人生命困厄与欲望。”⑨
相比较之前的赞赏或理解,更多的声音是不满和讨伐,并将大批判的号角声吹向每一个角落。这些文章散见于《废都滋味》、《废都废谁》、《失足的贾平凹》等等。在这种批判浪潮中,青年批评家、北大博士们尤为愤慨:他们集中批判了《废都》的媚俗、颓废、性描写等等:“贾平凹披着‘严肃文学’的战袍,骑着西北的小母牛,领着一群放浪形骸的现代西门庆和风情万种欲火中烧的美妙妇人,款款而来,向人们倾诉世纪末最大的性欲神话,令广大读者如醉如痴,如梦如歌。”⑩“赤裸裸的性描写,绝少生命意识、历史含量和社会容量,而仅仅是一种床笫之乐的实录;那种生理上的快乐和肉体上的展览使这种实录堕落到某种色情的程度。”(11)“《废都》既不能撞响衰朽者的丧钟,又不能奏鸣新生者的号角,它所勾画的是一帮无价值、又不创造价值的零余者的幻生与幻灭。”(12)“我完全有理由把《废都》看作是一部‘嫖妓’小说。与那些不入流的黄色淫乱作品相比,不同的是《废都》经过了‘严肃文学’的包装,它在技巧和结构上更圆熟,并且出自于名家之手罢了。”(13)
女性批评家们也对作品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废都》是一个赤裸裸的白日梦,是一个在社会和性方面都受到压抑的男性所寻求的心理补偿。”“女人在《废都》中,是舒适生活的保姆,是发泄性欲的工具,是铺平仕途的基石,是抒展个性的渠道,是创作灵感的源泉,是毁灭男人的祸根,唯独不是‘人’,她们的人性早已被物性淹没了。”“其他不论,单就妇女观来说,今天的贾平凹竟比数百年前的汤显祖、曹雪芹还要落后一大截。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还要写这样的评论文章,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悲哀,中国妇女的耻辱。”(14)
虽然贾平凹在《废都》扉页写下“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但这些批评话语仍给作家带来极大困扰,他不无伤感地说:“在《废都》以前,我在文坛上属于比较干净的人和纯洁的作家,突然一夜之间变成阴暗的人和流氓作家。”(15)萨义德说过:“当代的批判意识,就处于两个可怕而又相互联系的吸引批评关注的权力所代表的诱惑之间。一个是批评家们(由于出生、民族、专业而)在嫡庶性上与之紧密联系的文化,另一个是(由于社会的和政治的信念,经济的和历史的境况,自愿的努力和赋予意志的慎重而)在隶属性上所获得的一种方法或者体系。”(16)两种看待《废都》的方式,更多源于批评家立场和视角的不同。
在对《废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一方看来,庄之蝶就是贾平凹的影子,庄之蝶的名人之累是贾平凹真实的心灵写照。“作为与贾平凹交往甚密、相知甚深的朋友”,白烨“联想到《废都》里的某些情节和场景,更知《废都》里的种种描写确有其扎实而可靠的生活依据”,“他在作品里发抒了观感,宣泄了情绪,似乎在精神上超越了现实,但说到底,那也是面对苦闷现状的一种审美补偿,是寻求个人生活的整体平衡的文学努力”(17)。王富仁以“曾在西安生活过三四年的”亲历者身份来体味《废都》,认为相比较以前穿着“文学的衣服”而言,“《废都》里说话的贾平凹才更像真的贾平凹,《废都》所营造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庄之蝶以自己的方式返回这个世界,他只有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才能获得属于人的真实的东西”(18)。这说明,一个本色的写作年代在与精英文化的疏离和对抗中业已来临。每个人都抛去了自己的精神假面,而开始以其本来的面目进入写作。
相比较之后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话语,同情和理解的声音显然被批判者的愤怒压低。而在批判《废都》的理论话语中,对其“媚俗”、“性描写”、女性观的非议显得过多流于表面。在《废都》出版的1993年,通俗文学热早已吹遍大江南北,琼瑶、三毛、席慕容、汪国真等人的作品早已风行一时,王朔的畅销小说甚至得到王蒙的赞赏和支持。女性主义的抗拒性阅读策略已然降落,注重寻求中国本土的女性精神资源和现代传统。仅就中国当代纯文学来讲,张贤亮、王安忆等人的创作已经对性本能、欲望做了不少探讨。即便和《废都》同时出版的《白鹿原》,也充斥着不少性描写。为什么仅仅是《废都》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论和非议?伴随着1994年1月《废都》被禁,争议戛然而止,这些批判话语背后的深层焦虑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打开历史尘封、找寻更多的历史沉积,也成为文学史研究者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二、激进批判的身份焦虑
《文艺争鸣》杂志在1993年第1期发表了《王朔自白》,其中“关于知识分子”一节,也许是迄今为止当代文坛上唯一的“痞子教训知识分子”的奇文。“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然丧失了。”“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恐怕将来难有一席之地。”(19)贾平凹在《废都》创作问答中回应“有人说庄之蝶像‘多余的人’”的话题时,说:“我想了想,有这么个味儿。”“庄之蝶是废都里一奋斗者、追求者、觉悟者、牺牲者。他活得最自在,恰恰又最累,又最尴尬,他一直想有作为,但最后却无作为,一直想适应,却无法适应。”(20)书中,“苦闷的庄之蝶、冲撞的庄之蝶、觉悟的庄之蝶”为权贵服务,给假农药做宣传,谋取友人字画珍品,对于自己要写的长篇小说却自始至终并未动笔。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完全沦落为“废都”中的“多余人”,“只好靠对女人和性的无穷的追逐来证实自身”,沉醉于“一蝶四花”的美梦中,终至中风倒下。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我写小说是为我自个,要活人,要闹口饭吃”(21)的“一点正经没有”“痞子文学”作家王朔和“处事没从流俗走,立身敢于古人争”,“严肃、纯情、真挚、笃重”(22)的“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贾平凹在知识分子“找不到位置”的“隐秘心态”看法形成了同构,这的确让以知识分子、精英、启蒙者身份自居的批评家们难以接受,于是他们惊愕地喊出“贾平凹怎么啦”,“这是贾平凹的作品吗这是贾平凹写的吗?!贾平凹怎么也写起黑书黄书来了,贾平凹是不是没钱花了,用黄与黑来获得王朔式的商业成功。这不是堕落吗?贾平凹这样的作家都如此堕落如此义无反顾走向金钱,那么中国的作家还能有几个让人有信心呢?”(23)
1992年到1993年,是文人“下海”频发的两年,也是知识分子身份转变和精神大颓败的两年。以王朔为核心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集结了三十名中青年作家,其中有海岩、莫言、魏人、朱晓平、刘恒等等;济南的“天马创作室”有苗长水、周大新、刘照如、于爱香、陈志斌等,刚刚成立便接手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作家群体华丽转身,迈向影视最强音,而“纯文学”则日益凋零,在此背景下,“多次表示无意下海”、“除了写作不会别的”的贾平凹的意义更为凸显。“从《满月儿》发表至今,在1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贾平凹的创作可以说是基本上一直是在刚健、庄尚、淳真和优雅的道路上前进的。”“汪曾祺曾把他称为‘鬼才作家’,孙犁则把他比作‘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濛濛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孙犁还说,‘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24)“他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满月儿》,预示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由揭露‘伤痕’向正面写实的过渡;他发表于1984年间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和后来的《浮躁》,有力地促进了‘改革文学’向现实生活深处的掘进和发展;他发表于1982年的《卧虎说》最早发出了文学‘寻根’的审美信息,此后又以‘商州’系列作品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主将。”(25)正如王富仁所说:“在中国文学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各种潮流,很多作家倏忽而来转瞬即逝的时候,贾平凹却几乎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器重。至少我所接触的很多文学评论家,是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的。”(26)
早在90年代初由王朔领衔编剧的《渴望》,在对传统色彩极浓的市民道德极度赞扬的同时,剧中作为批判和谴责对象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激起了一批文化人的反感。此后,王朔屡屡在作品中调侃知识分子,也引发了知识界的集体围攻。而《废都》中的庄之蝶似乎恰好印证着王朔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有意建构。“在‘新时期’的‘现代性’话语中,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代言者’的角色。《废都》中有关庄之蝶如何受崇敬的表述,似乎就是对这种旧梦的不停的重温。”它在描述了庄之蝶的高雅脱俗之后,却又写了在市长和黄厂长等人面前的局促尴尬,那一串串“□□□□”更是不堪入目。于是,批判者们愤怒地指出,《废都》批判的“问题不在于贾平凹现在写出了《废都》,而在于他曾经写出了像《鸡窝洼的人家》那样触动我们心灵的作品”(27)。“问题在于,曾被寄予厚望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所发生的当代逆转,那些曾以五四新文化传人自命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最艰难的关头临阵‘反水’,这么顺当地就抛掉了‘为人生’和‘为艺术’的旗帜,而将‘传厚黑之奇’的‘黑幕’,‘言床笫男女之欲’的言情,以及‘专以雕琢为工,而连篇累牍无其命意者’之骈文熔为一炉,从而成就一部‘旷世之作’《废都》。”(28)
由此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群体愤慨围剿《废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庄之蝶=贾平凹=知识分子。王朔的媚俗、调侃只是一种痞子式的“一点正经没有”,而作为严肃作家,贾平凹的问题则上升到知识分子身份的层面。因此,他们不无伤感地说:“连我们时代‘最后一位大师’都无力修复‘纯文学’(美文)的历史,它最终不得不变成对古籍、禁书、淫书的拼贴,那么,‘纯文学’的破败确实是无可挽回了。一个虔诚的文化守灵人,却又不得不高唱纵欲者之歌,以此来祭奠经典文化的死亡和招徕街头书摊的匆匆过客——这本身就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观。”(29)
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激烈批判《废都》的陈晓明也曾对此现象做出反思:
平心而论,他(贾平凹)有历史的敏感性,九十年代初的要害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八十年代终结的后遗症。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仅茫然无措,也处于失语的困扰中。王朔的调侃替代了知识分子话语真空,但却替代不了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还是处于那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对王朔进行了集体的围攻。知识分子的话语以毫无历史方向感的形式第一次获得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表达,王朔不幸成为杂语喧哗的对象。失语后的复活没有别的方式,只有强烈的批判性,矫枉必须过正,下一个对象是贾平凹,他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知识分子重新出场较量的对象。(30)
诚然,如王蒙所言:“‘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几个基本点上其实常常是一致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31)自70年代末期以来,处于边缘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了短暂的“回光返照”的机缘。整个80年代基本上由知识分子引领着一拨又一拨的文化潮流,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与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成了思想文化主要的言说者与阐释者,他们又一次体验了大众启蒙者、代言人的豪情或悲壮。即便在市场经济袭来,“范导者身份的失效”、“下课的钟声已然敲响”的1993年,知识分子仍然试图用“人文精神论争”来“设计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32)。在这种知识体系和认知背景下,批评家们对贾平凹的新作《废都》的种种纠葛充满不解,知识分子庄之蝶从“启蒙者”到“多余人”身份的转化,作品没有了贾平凹早期的清新、刚健,成为一本“颓废”小说;宣传、策划完全背离精英圈子,跑步进入市场轨道;那一串串“□□□□”更像是对《金瓶梅》的东施效颦。
萨义德说:“没有任何阅读、释义的行为是纯粹中性的,不受‘污染’的;在不同的程度上,每一个读者和文本都是理论立场的产物,当然这立场可能是很含蓄而且是无意识的。”(33)批评家们痛心疾首地呼喊:“王朔对灵魂清醒的毁坏反使我们觉出一点生机,只有像贾平凹这样对灵魂不自觉的(因而也是真正的)弃绝才使我们感到幻灭。”(34)因此“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由知识分子出面操持的对文化的阉割和对文化的减价处理,比王朔的主动向精英文化进攻贻害更大”(35)。在批判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批评家仍是用80年代“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以启蒙者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大众代言人的道德规范来界定贾平凹和《废都》。佛克马、蚁布思关于身份和成规的概念告诉我们:“成规这一概念预设了一群对他行为的期待相同的人。因此,一种成规是一个明确的或彼此心照不宣的协议,这两种协议本可能是不同的,但人们认为它们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每个或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被期待的是什么。”(36)而贾平凹显然打破了80年代的文学成规,在强调文化抵抗的关键时刻,贾平凹却走到了文化抵抗的反面,这是他招致绝大多数批评家反感的主要原因。因此,《废都》中颓废的庄之蝶“多余人”身份塑造只能迎来对它有着不同成规期许的批评家们愤怒的呵斥。
三、在90年代的门槛上
有学者提出:“‘《废都》批判’像一座被废弃于当代文学史深处的矿址,它牵涉的复杂问题可能至今都没有得到启发性的解释。它被认为是80年代文学终结和90年代文学兴起之标志,当代文学从此从意识形态轨道向市场经济轨道彻底转轨。因此,‘《废都》批判’很大程度上成为俯瞰当代文学转型的另一窗口。”(37)在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以决绝的姿态抵抗世俗文化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分裂,彰显出进入90年代的不同方式。在对王朔和《废都》的批判风潮中,依然有着王蒙《躲避崇高》中对王朔的赞赏和王富仁为脱去“文学衣服”的真实贾平凹叫好。与之同时,持80年代纯文学知识谱系的批评家们对《废都》愤怒的批判已经彰显作品完全脱离了80年代的文学轨道,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甚至可以说,站在90年代门槛上的《废都》所遭遇“大批判”使它一时间成为各种矛盾的“集结号”,它是“严肃作家”的纯文学作品,却遭遇到市场的极力热捧;它是作家“在四十岁的觉悟”,“唯有心灵真实”、“安妥破碎的灵魂”的作品,却被批评界冠以“颓废”、“堕落”、“缺乏理由的人生幻灭感”;它承袭明清世情小说,却被抨击为“对明清文学的皮毛仿制”;它写知识分子的无所皈依,却被讽为《废都》中的“多余人”、“《花花公子》的中国兄弟”(38)……一本书的出版在短时间内集结了十三本书的诠释和争论,四十万字的言说迎来数倍的批判话语。可以说,它所汇聚的矛盾,它所引发的争论事件,实际上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学面临的困局,也是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重新出场的标志性事件。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发表使社会经济运作体制的大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于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情绪浓云般笼罩在这个群体的心头。后来成功策划“布老虎丛书”的安波舜辛酸地回忆:“1992年,也就是‘布老虎’出生的前一年,文学跌进了最低谷,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几乎就意味着赔钱。我当时正在创作一部书写少年时期成长经历的长篇小说,每天晚上写得泪流满面。可是想想,写完之后怎么样?谁给出?出了以后谁会看?当时不光我,我周围的许多作家,包括著名的先锋作家马原、洪峰他们都很沮丧。”(39)即便自称“比一般作家日子好过一些”,“字画还能卖点钱”的“知名作家”贾平凹也坦言:“现在的作家太穷,稿费太低,我并不奢望靠写稿发大财,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太低,实在不公,生计问题解决不了,难以保证好的创作。言义的是君子,言利的也是君子。”(40)
对于贾平凹,如他自己所言,作为作家,书写出了交给出版社就不再管了。而作为《废都》责任编辑的田珍颖则需要找到更好地适应90年代的生存方式:“文学要不要包装?文学要不要推销?我们在面对经济大潮时,似乎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编辑,面对我们的潜心写作的作家们,我常产生一种苍凉感和一种忿忿不平。因此我愿为我担任责任编辑的作品,努力宣传——倘若我们必须同避‘包装’、‘推销’之类的词,用‘宣传’二字,总是体面的吧!”“面对市场经济的庞大声势,向社会宣传文学,是一个文学编辑应具有的竞争的能耐。”(41)因此,《废都》的宣传策划所贯穿媒体时代的“注意力经济”,也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强烈不满:“先是一则捕风捉影的消息称,《废都》稿酬高达一百万元。消息一传出,全国几乎所有文摘版面八方呼应、竞相转发。”(42)“书未见,推销却已经使这本书变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这无疑使惯用‘雅’文学为自己定位的贾平凹彻底地进入市场。这一方面巩固了贾平凹那些风格诡异的散文在文化消费的市场上打出的名声,另一方面,则以一种越轨的、打破以禁忌的传闻极大地拓展了贾平凹的市场效应。于是,在《废都》尚未出版时,它的成功就已被肯定了。……这的确是一件极其成功的推销的范例。”(43)
在批评家们痛心疾首地呼喊“《废都》作为世纪末面对历史的又一次绝望的写作冒险,宣告了中国知识分子由世纪初的文化冒险家,到世纪末的文化掘墓人的必然转化;宣告了中国文学由文化写作,经政治写作向市场写作的全盘倒戈”(44)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社会转轨的现实。当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文学急剧市场化的背景之下,80年代的文化地图已然失效,90年代并未按照80年代的预设发展,启蒙话语已经告终,新的媒体制度悄然兴起,而批评界显然对此缺乏准备,仓促上阵。一方面是批评界重寻人文精神,倡导启蒙主义的理想激情;另一方面是文学界的不断溃败,连自称“我是农民”的贾平凹也在性描写中宣泄颓废和虚无。于是,批评界在那个“红尘滚滚的年代”,对消费时代的文学投降主义倾向表达出极大的不满,对《废都》的批判就显得更为激进。
虽然批评家们对“严肃作家”贾平凹与市场的无缝对接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和谴责,我们却无法忽视短短几个月内十余本《废都》批判书籍密集问世背后潜在的市场力量。曾撰文批判《废都》的方位如此回顾《废都滋味》出笼的过程:
当时召集这次座谈会的两位出版社的编辑说出他们商业色彩极浓的目的后,是一片静场。应邀出席这次座谈会的除了我这个下了海的人以外,其余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学博士。还有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当时我有点担心,担心哪位博士会突然耍起清高的脾气,拒绝参加这种商业目的极为明确的讨论和写作,那样大家都会很难堪的。接着就发生了让我吃惊的事情:刚才还在对贾平凹先生为推销自己的作品使用“广告”手段持极为激烈的轻蔑态度的朋友并没有做出让我担心的清高举动,而是在一阵极短的静默之后就很自然地投入对写作这样一本《废都》批评集子的结构安排、名字选定和市场策划的讨论之中……(45)
与之同时,伴随着市场时代媒体批评和书商势力的日益庞大,对《废都》的批判显然并不只发生在知识分子内部。在《废都》批判的话语中就包含着大众话语,有书摊主“这书有点黄”、“就这东西人爱看”,有学生家长“□□□□全是一口口陷阱”,有普通职员“写那个,老是删去多少字,看着不舒服,要写就写,不写拉倒,何必这样吊胃口”(46),有退休老干部“扫黄的人干嘛去了”的大声质问,大学生“让贾平凹进牛棚”(47)的强烈呼吁……如是看来,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上说,《废都》可以算作是当代文学走向大众、走向传媒、走向民间社会的一个较早的成功样板。王晓明在《精神废墟的标记——漫谈〈废都〉现象》中提出:“不但是一位作家创作一部小说来描写‘废都’,而且这部小说使许多文学出版机构、大众传播、读者乃至文学评论家都一齐陷入了‘废都’式的喧哗,甚至作家的描写本身,也反过来证明他自己正是‘废都’中的居民,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自我映证更令人震惊呢?”此后,即便还有张汝伦宁愿《活在历史中》的理想情怀和诗性表达,我们也不得不用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作为90年代的“发声”:
一年来,市场经济劲猛冲击中国社会。社会问题性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变化剧烈,改变着读者,也改变着文学。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作家面临的压力也不同了。
一切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作家们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48)
“《废都》批判”的主体指向是它的媚俗、迎合市场大众的堕落,批评家们一方面在哀叹《废都》的轰动效应所彰显的“商业文化的得逞和人文精神的没落”,一方面却以十三本书密集面世的方式对其狂轰滥炸,这的确极其矛盾。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文学界对《废都》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多是肯定其文学价值和在文化转轨中的独特意义。《文心雕龙》讲“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9),《废都》批判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就是站在90年代门槛上的知识分子因所追寻的理想主义无法成为可行的现实操作方案,在彷徨中升腾起迷惘、虚无、茫然无措的心绪,不知该往何处去成为其内心的隐忧,而《废都》却真正赤裸裸地写出了中国文人的那种颓败、虚无和绝望感,因而迅即成为众声喧哗的对象。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写到:“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50)可以说,《废都》作为媒体时代的经典个案,它以飞蛾扑火般的凄美照亮了90年代的多彩斑斓,它告诉在门外徘徊不前的知识分子,纯文学经过包装亦有市场,于是催生了“布老虎系列丛书”;它以令人咋舌的销量宣告长篇小说亦能热销,改变了新时期之后“中短篇热”的状况;它使作家和出版者认识到文学也具有大众传播的潜力,文学也有可能摆脱困境;它使得更多的“精神贵族”脱下了“文学衣服”、抛却了“精神假面”,重新出发……然而,在迈还是不迈过这道门槛的挣扎和纷扰之中,《废都》却成为一个时代情绪和历史话语的聚集目标,成为知识分子重新出发的牺牲品。在《废都》批判的风潮中,媒体、出版社、批评家、流言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共同演绎了这个盛大的文学事件。
注释:
①包括以下著作:王新民选编《多色贾平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纵横》编辑部编《贾平凹与〈废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江心主编《〈废都〉之谜》,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井频、孙见喜:《奇才·鬼才·怪才贾平凹》,西安出版社1993年版;先知、先实选编《废都啊,废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黄海舟编《废都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肖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多维编《废都滋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十月编选《沸沸扬扬话〈废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陈辽主编《〈废都〉及〈废都〉热》,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庐阳:《贾平凹怎么啦——被删的6986字背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刘斌、王玲主编《失足的贾平凹》,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星明编著《贾平凹谜中谜》,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③孟繁华认为:“《废都》再版对贾平凹个人来说,也是一朵重放的鲜花。”(见王辙《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④旷新年:《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⑤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⑥孙见喜整理《陕西部分专家评价〈废都〉的主要观点》,《废都啊,废都》,第45—46页。
⑦蔡葵、雷达、白烨:《废都三人谈》,《废都废谁》,第135页。
⑧文波整理《说长道短论〈废都〉——京都评论家八人谈》,《废都废谁》,第131页。
⑨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网扰》,《废都废谁》,第217页。
⑩陈晓明:《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废都滋味》,第24页。
(11)尹昌龙:《媚俗而且自娱——谈〈废都〉》,《废都废谁》,第241—242页。
(12)田秉锷:《〈废都〉与当代文学精神滑坡》,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13)孟繁华:《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失足的贾平凹》,第49页。
(14)刘红林:《“人”的失落——〈废都〉妇女观简论》,《〈废都〉与“〈废都〉热”》,第154页。
(15)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 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6)(33)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页,第5页。
(17)白烨:《走红的受难者——贾平凹与〈废都〉琐记》,《废都废谁》,第87页。
(18)王富仁:《〈废都〉漫议》,《废都废谁》,第212页。
(19)《王朔自白》,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20)贾平凹、王新民:《废都创作问答》,《废都啊,废都》,第7页。
(21)王朔:《我和我的小说》,载《文艺学习》1988年第2期。
(22)(24)艾斐:《〈废都〉现象与贾平凹的文学道路》,载《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23)《北京文化界人士谈〈废都〉:〈废都〉与废墟》,《废都废谁》,第137—138页。
(25)白烨:《多色贾平凹》,载《时代文学》1998年第4期。
(26)王富仁:《〈废都〉漫议》,《废都废谁》,第210页。
(27)(34)李书磊:《压根就没有灵魂》,《废都滋味》,第2页,第2页。
(28)(35)(44)韩毓海:《除了脱裤子无险可冒》,《废都滋味》,第53页,第62页,第50页。
(29)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0)陈晓明:《穿过本土,越过“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见贾平凹《废都》(代序),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1)王蒙:《躲避崇高》,载《读书》1993年第1期。
(32)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载《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36)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37)程光炜:《当代文学60年通说》,载《文艺争鸣》2009年10期。
(38)孟繁华:《贾平凹借了谁的光》,《废都滋味》,第92—99页。
(39)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40)《贾平凹答记者问》,《废都废谁》,第26页。
(41)《〈废都〉责编田珍颖答记者问》,《废都啊,废都》,第16—17页。
(42)程德培:《莫非批评界也被“批租”》,载《新民晚报》1993年8月12日。
(43)易毅:《〈废都〉:皇帝的新衣》,载《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45)方位:《〈废都〉真的都“废”吗》,《〈废都〉滋味》,第166页。
(46)《京城八月:街谈巷议说〈废都〉》,《废都废谁》,第115页。
(47)《让贾平凹进牛棚——一场关于〈废都〉的论战》,《废都废谁》,第280页。
(48)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载《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49)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50)贾平凹:《废都·后记》,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标签:废都论文; 贾平凹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读书论文; 纯文学论文; 王朔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