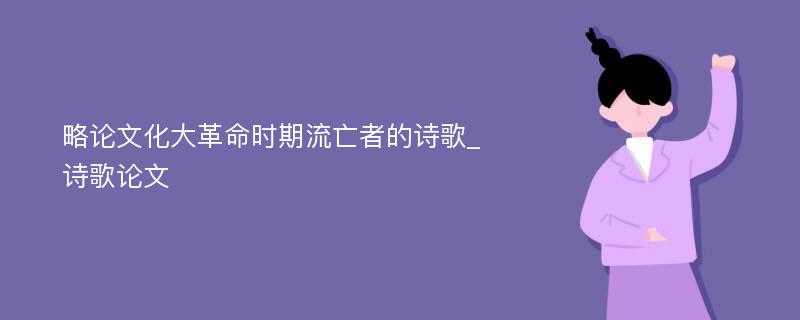
“文革”时期流放者诗歌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诗歌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爆发后,整个文坛受到犁庭扫院式的清洗。大批诗人被揪斗批判、抄家监禁,一部分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而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后来或者被关进牛棚和监狱成为囚徒,或者被驱逐到“五·七”干校、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些“积习难改”的囚徒和被放逐者是缪斯真正的信徒,他们在前途难测,甚至是生死未卜的恶劣环境中,仍然抓住有限的“缝隙”,冒着“罪加一等”的危险,继续进行诗歌创作活动。驱动着这些身处逆境的诗人从事创作的动力是什么呢?不止一位诗人谈起过他们是如何把诗歌写作当作苦难人生中的精神支撑的。诗人曾卓回忆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时说,他是“通过诗来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因而减轻了自己的痛苦”;同时,他也“通过诗来反映了内心的自我斗争”,“高扬起自己内在的力量,从而支持自己不致倒下,不致失去对未来的信念”(注:曾卓:《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见《曾卓文集》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418页。)。胡风在狱中创作了数千首旧体诗,他的妻子梅志认为“他在狱中这十年就是靠自己创作这些诗篇温暖自身,才没有被独身牢房的孤独击垮”(注:梅志:《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0页。)。为叙述方便,姑且把由这些囚徒和被放逐者创作的诗作统称为流放者诗歌。流放者诗歌与知青诗歌共同构筑起了文革时期的“地下诗坛”。
文革时期流放者诗人的构成较为复杂。他们中有因1955年“胡风集团”案而罹难的牛汉、绿原、曾卓等诗人;有1957年“反右”运动而致祸的穆旦、唐湜、公刘、流沙河、周良沛、胡昭等诗人;有那些长期在诗坛受排挤的“不合时宜者”蔡其矫、公木、陈敬容等诗人;还有以郭小川、何其芳、臧克家等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在文革中后期被流放到干校后,创作了一部分能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默许”的诗作;此外,黄翔和陈明远等青年诗人在年龄序列上与上述中、老年诗人不属一个层次,但他们同样具有遭放逐而坚持地下诗歌创作的经历。
流放者诗人在监狱、牛棚、干校中进行着特殊的写作。流放者诗人的上述创作空间与红卫兵诗人的创作空间——广场、街头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从整体社会环境中分割出来的特定空间,后者是全民式的社会空间;在前一空间进行的写作大多是秘密进行的,而在后一空间进行的创作无疑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在公共空间里诗人用公共话语、社会话语进行写作,在监狱、牛棚、干校等空间中诗人基本上用个体话语、私人话语进行写作(也有少数诗人仍用公共话语写作)。
如果说在广场、街头等公共空间展开的红卫兵诗歌的抒情姿态是大喊大叫,那么在监狱、牛棚、干校进行的流放者诗歌的抒情姿态则是独白。相比较而言,在国家出版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总得时时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写作符合当时的政治美学原则,考虑自己的作品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读者;流放者诗人大多把诗歌当成苦难生存境遇下的精神支撑,他们写诗一般都没考虑拿去发表,没必要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个别诗人除外),他们写诗是给自己或一二友人看的,不必考虑读者的欣赏趣味。这种不看官方和读者脸色的创作对于流放者诗人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尽管当时他们有形的躯体是不自由的),从而使个人化的诗歌写作得以恢复和生存。
1975年9月6日,穆旦在一封致他的“诗歌学徒”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不过,你另一句话也说得很对,就是你在写它时‘没有别人在旁边看着我的感觉’。这‘感觉’成为现在作者的很大问题,他身兼两职,既要凭感受来写作,又要根据外面的条条来审核和改动自己的感受,结果他大为折衷,胆子很小,笔锋不畅,化真为假,口是心非。这种作品我们不会认为是好作品,尽管非常正确合格,但不动人。”(注: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穆旦作品卷),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23-224页。)穆旦信中所言的有没有别人“在旁边看着我”的感觉,成为个人化写作和非个人化写作的分水岭。
非个人化写作采取“合唱”式的抒情姿态,而个人化诗歌写作的基本抒情姿态是“独白”。在大地上四处漂泊的青年诗人黄翔说:“我徘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独白于生与死之中,思想像一线淡淡的光芒。”(注: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写于1968-1969年的诗论),见《黄翔作品集》(打印稿),第462页。)“囚徒”曾卓回忆自己狱中的创作时写道:“我常常努力排开一切烦恼和杂念,像困兽一样在小房内徘徊,或是坐在矫凳上望向高窗外的蓝天,深夜躺在木床上面对天花板上昏黄的灯光,喃喃自语。”(注:曾卓:《生命炼狱边的小花》,出处同①,第380页。)老诗人公木则从另一角度来描述流放者诗人们的“独白”抒情姿势。他说,自1958年以后,自己就不曾真正写过诗,因为“附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注:见《公木诗选·后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就是说,在“反右”运动以后,权力话语加紧了对诗人的控制,诗人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不顾事实地表现假、大、空的东西,或大胆地抒发真实的感受。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公木在文革中不愿加入粉饰、美化现实的“合唱”队,但也不能公开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只好用“自语”或“耳语”的方式悄悄地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自语”和“耳语”其实是一回事,“自语”,即是诗人的嘴以自己的耳朵为倾听对象的喃喃自语。
黄翔以一首题为《独唱》的诗,艺术地描绘了在那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里,流放者诗人孤寂地进行“独白”的抒情姿态: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惟一听众
是沉寂(注:见《黄翔作品集》(打印稿),第30页。)
在远离尘嚣的深谷里,一条瀑布孤独地歌唱着,它的情感绝不为世人而敞开,“高山流水”不再是人们的知音,它惟一的知音是像死一般寂静的沉默。在这首诗中,诗人写出了自己拒绝加入众多诗人喋喋不休、聒噪不止的“合唱队”的孤傲姿势。当然,并非所有拒绝“合唱”的诗人都会采取黄翔式的、斩断与外界一切联系的抒情立场(其实,黄翔本人也不能完全做到与世隔绝,下文再论)。拒绝“合唱”与关注民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尤其在我们这个拥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度里,诗人很少能够让自己对现实闭上双眼。文革时期的许多流放者诗人在自己屡遭厄运的恶劣环境里,仍对百姓满怀着深切的关爱。老诗人蔡其矫在文革后期的《祈求》一诗中唱道:
我祈求炎夏有风,冬日少雨;
我祈求花开有红有紫;
我祈求爱情不受讥笑
跌倒有人扶持
……(注:见《蔡其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93页。)
祈祷,同样也是一种“独白”。这是一位富有人间情怀的“大爱者”在歌吟,他的“祈祷”绝对有别于那些“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粉饰人间苦痛之作的“甜蜜”歌唱。
并非所有的流放者诗人都坚持用“独白”姿态歌唱,这就如同国家出版物上的诗人李瑛,有时也能唱出点个人的心声。郭小川、臧克家、何其芳等为数不多的诗人虽屡遭放逐,却仍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干校或其他流放地遥遥地应和着文革公开诗坛的“合唱”。面对一块由登山队员从珠穆朗玛峰带回的4亿年前的古老化石——“海百合”,老诗人臧克家抒写道:
今天山峰连着山峰,/当年浪波推着浪波,/我手捏一块小小化石,/鉴赏四亿年前“海百合”。
谁说“天不变”,谁说?/“珠穆朗玛峰”就是证人一个。/谁说“道不变”,谁说?/请看过去的农奴、我们的登山英雄——潘多!(注:臧克家:《四亿年前“海百合”》,见《臧克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第2版,第327页。)
在此,诗人以珠峰上的海洋化石“海百合”和登山女英雄潘多,论证“沧海桑田”的“变”之理,并对“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传统天道观进行批判。此诗作于1975年9月,可视做为诗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种积极表态。
何其芳在长诗《我梦见》的后部写道:“我的梦使我不快,/是它无情地指出:/在战场上我没有战绩,/靠阶级弟兄们援助。/除了对革命踏实,/服从党的统帅,/我没有什么建树,/却不少失误和挫败……”(注:蓝棣之编《何其芳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84页。)看来,诗人是以写检讨书的姿态来写作,如果这些文字不是以分行的形式出现,人们完全可能把它们视做一份上呈的“交待材料”(其文体特征是“自打耳光”)。一位曾写过“谁的流吩的黑睛像牧女的铃声/呼唤着驯羊群,我可怜的心?”(《季候病》)这样纯粹抒情诗的诗人,竟会唱出如此干涩、局促、苍白的歌声,的确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至于郭小川,他原来是共和国“合唱队”的领唱歌手;文革时期,他的唱歌权力基本上被剥夺,但仍以“时兴”的唱腔写出了20多首符合“流行”时尚的歌,因而得以发表《万里长江横渡》等少数诗作。郭小川的干校诗作在当时曾传诵一时,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江南林区三唱”组诗(仿60年代初的《林区三唱》而作),仍遵循着他本人50年代开辟而具有广泛影响的路子——景物描写加直接抒情议论,其中的第二首《欢乐歌》与文革公开诗坛上的“政治韵文”似无太大差别:
社会帝国主义,/撞的是丧钟;/美帝国主义,/发的是悲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呵,/响的是欢乐的歌声!
美国帝国主义,/得的是绝症!/社会帝国主义,/是死前在发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呵,/有的是欢乐的面容!(注:见《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第1版,第301页。)
郭小川作于文革后期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的确堪称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动人之作,其动人的力量来自于诗人对战士坚贞不屈性格的塑造,至于在诗艺上,这两首诗仍用写景加抒情、议论的写作模式。值得重提的是,郭小川写作这两首诗时,多少受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以致诗中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掠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注: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出处同上,第383页。),和“磨快刀吧,要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跟上工农兵的队伍吧,用金笔剥开敌人的画皮层层”(注:郭小川:《秋歌》,出处同(11),第387页。)这样的诗行。
摘引郭小川这些诗行,意在表明:文革时期的地下诗坛与公开诗坛并非完全隔绝,在某些地下诗作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力是明显存在的。这并不是说郭小川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事实上,他同那些把写诗纯粹当作仕进之工具的文人有着质的区别。郭小川无疑是一名有人格、有操守的当代诗人,他的诗作最为感人的恐怕是其理想主义精神。
当然,表现理想主义也不宜于过于直白,宣言毕竟不是诗。一些优秀的地下诗人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探索,譬如老诗人牛汉曾写过《反刍》这一反映干校生活的诗,作品写抒情主人公“我”与一头母牛共同在树荫下歇晌,母牛的反刍引动了“我”的情思:
我反刍的
不是鲜嫩的青草
而是荆棘
我的生命
酿造出的
是苦咸的血液
甜蜜的理想的奶汁。
血液的奶汁
一滴,一滴
哺育着
我饥渴的生活
和瘦弱的小诗(注:见《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94页。)
诗作笼罩着一层理想的光晕,它的理想主义精神乃是经由“反刍”这一新奇的意象来表现的。并非直抒胸臆,也不是以那些用滥了的意象(如青松、红梅)来传达,另外,“反刍”也是对流放者诗人在逆境中仍执著地追求诗艺之探索精神的诗性写照;从某种程度上说,“反刍”还是一种特殊的抒情姿态:在苦难(荆棘在胃)中,以鲜血灌溉着瘦弱的小诗,诗人成了一只口吐鲜血而歌唱的荆棘鸟。这种“一步一滴血”的写作,堪称是现代式的“苦吟”。
在监狱、牛棚、干校,写诗属于非法行为,“笔和死罪是联系在一起的呵”(注:公刘:《仙人掌·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212页。)。恶劣的创作环境迫使诗人们采取了种种奇特的秘密写作方式。诗人公刘回忆文革时期的写作时说,自己当年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创作:一是把诗句埋在心底若干年,一是“用某种只有本人读得懂的方式‘压缩’在一片烂纸上若干年,若待着得见天日的机会”(注:公刘:《仙人掌·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212页。)。公刘这两种秘密写作方法也曾为其他许多流放者诗人所采用。诗人曾卓被关进监狱之初曾拿那些写材料的纸写诗,但不久,这些诗连同纸笔被没收,并受到“如果再犯就要受到惩罚”的警告。他只好换用口吟的方式进行创作,“其中不少在念一念后,抒发过感情就放弃了,但有的在反复地默念,不断地推敲后就形成了诗,在记忆中保留了下来”(注:曾卓:《生命炼狱边的小花》,出处同①,第380页。)。
青年诗人陈明远的诗《封存》记录下他当时的写作方式:“我走了,无声无息/只留下这几本诗集——/……抚摸这一串串密码,/封存你的记忆!/这是我整个生命里,/唯一留下的东西。”(注:陈明远:《劫后诗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09-110页。)诗人在牛棚中用拼音、密码,用种种只有他本人才能看懂和复原的符号进行写作。
青年诗人流沙河也谈及自己被关在派出所后院中的秘密写诗情况:“我在心头写诗。定稿在脑子里,怕出去就忘了,我用我发明的缩语偷写在香烟盒纸背面,藏入衣袋。其中就有十三年后发表出来的《故国九咏》的几首。”(注: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1月第1版,第264页。)
这种口吟默记的写作方式一旦形成习惯,便难以改掉:
聂鲁达伤心地讲过/有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改不了许多悲伤的习惯——/……他想写的诗/总忘记写在稿纸上/多少年/他没有笔没有纸/每一抒情/只默默地/封记在心里/我认识这个诗人(注:见《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01-102页。)
这是牛汉的诗作《改不掉的习惯》。这种没有纸笔,以心灵为底板的抒写方式在文革时期的监狱、牛棚中甚为常见,因此,牛汉觉得自己与“这个诗人”很熟悉:他是牛汉的友人胡风、绿原,他是牛汉所见过或听说过的被囚禁的无数个诗人,他也是牛汉本人。牛汉在题为《在深夜……》一诗中写道:
有时候/在深夜/平静的黑暗中/我用手指/使劲地在胸膛上/写着,划着/一些不留痕迹的/思念和愿望/不成句/不成行/象形的字/一笔勾成的图像/一个,一个/沉重的,火辣辣的/久久地在胸肌上燃烧/我觉得它们/透过坚硬的弧形肋骨/一直落在跳动的心上/是无法投寄的信/是结绳记事年代的日记/是古洞穴壁上的图腾/是一粒粒发胀的诗人的种子。(注:见《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5-76页。)
这是多么奇特的写作方式!诗人以手为笔,以胸膛为稿纸,挥写着他对苦难人生的体验。没有切身的体验,没有在黑暗的中国从事过这种极为“原始”的写作,诗人是根本写不出这种沉甸甸、火辣辣,给人以“肿胀”感的诗行来的。牛汉的这首诗是对文革时期干校诗歌写作状态力透纸背的描绘,它形象地揭示了生命永存、诗火不灭的艺术哲理。
诗人周良沛的写诗方式同样令人为之惊叹:在长期的监禁中,诗人通过“谈心”与一位看守结为朋友,这位看守给诗人提供写诗用的纸笔。诗人充分利用这位看守的值班时间来写作,而监狱每次搞突袭搜查之前,这位友善的看守便会提前发出通知,使诗人能及时收藏或转移诗稿。然而,诗人只听过这位好心人的声音,并未见他的面孔,更不知道他的名字。诗人动情地回忆道:“先后我过了三年多这样的日子,是在不见阳光的黑牢里的日子。那是人世最黑暗的地方,我却从这个人的心灵看到人世最灿烂的光辉。人心是不会死的,我们的人民多好啊!”(注:周良沛:《铁窗集·自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3月香港第1版。)
在漫漫长夜里,诗歌之火一直点燃着。有无数的中国百姓像这位无名的看守一样默默地做着传递诗歌薪火的伟大工作,他们与诗人一道保藏、传播着秘密状态下写成的诗篇,开辟了一条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地下诗歌流通渠道,建立起了一个范围无边的读者群体。
在文网森严的时代,人们想尽种种“绝招”来传播地下文学,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诗歌作品,原因是:“非法”传播地下文学的方法都很原始——不外乎口口相传和手抄两种途径,诗歌的篇幅相对较短,部分作品还押韵,因此,比小说和剧本更容易背诵和传抄;诗歌比其他文体能更精粹地表现现实,深谙此道的苏联地下文学大师布罗茨基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诗歌可以对付现实,方法是将现实浓缩为一种可以摸触到的东西,一种否则便不能为心灵所保存的东西。”(注:约·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见《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广州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367页。)
正如布罗茨基所言,文革时期流放者所作的诗歌通常具有高度浓缩,又能为心灵直接抚摸到的特性,诗人绿原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偷偷向他的诗友牛汉背诵的短诗《我的一生》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将钻进隧道里去
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
我又将在洞口昏倒
等“光”把我拍醒
我钻的隧道是人生
我到的洞口是坟墓
我等的“光”却是平凡。(注:见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第73页。)
在生死交界地带,“我”坚卓地追寻着光明,这是对沉沦于黑暗之中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凝炼的艺术写照。值得注意的是绿原把这首默记于心中的短诗背诵给牛汉听的口口相传方式,除了与诗友共同品味欣赏新作这一层动机外,不能排除这是诗人在特殊环境里所采取的储藏、传播诗歌的特殊方式。在斯大林政治高压时代,苏联杰出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便采用过类似的方式,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人因为写了几行诗而“永远地失踪”,因此,她不敢用纸笔记下自己的情思,“只能由作者和其他几个人记在脑中,……每过一段时间,她便同某一个人会面,请他或她轻声朗诵这一或那一片断,这就是她的仓储方式”(注:约·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见《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广州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366页。)。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这首被公认为20世纪表现苦难和对苦难的坚承母题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便是通过这种方式保存下来。
诗人唐湜在文革黑暗年AI写作下的不少诗稿也通过分存在几位“豪爽的年轻朋友”处而得以保留下来(注:参阅唐湜《泪瀑·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富于传奇色彩的藏诗事件何止一、二个,不过,流沙河诗作被保存的故事恐怕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1966年秋天,戴着“右派”荆冠的流沙河凭借7封情书和7首情诗(除了已发表的《情诗六首》,还有一首《故乡吟》)赢得了女青年何洁的爱情。婚后,何洁一直珍藏着这些她心爱的诗稿,躲过了大小12次抄家风波。她先是把诗稿团成一卷,藏在贴身的内衣里;次年生下孩子后,又把诗稿放入婴儿的襁褓内。后来,她一度把诗稿藏到成都一友人家,又觉不妥而带回家。随着抄家一次比一次“深入细致”,她两次下决心想把诗稿烧毁,但最终还是下不了手,便托人将它们带到千里迢迢之外的贵阳友人家保存。后来形势有变,何洁取回诗稿,把它夹在两片层板之间,送到苏轼故乡的一位女知青手中,托她代管(注:参阅何洁《怨情雁飞向人间》,出处同(19),第58-59页。)。
诗人黄翔也像流沙河之妻何洁一样采用过影视作品中地下工作者藏匿秘密文件的方法。他作于文革时期的长诗《火神交响曲》直斥黑暗的专制统治,一经被查抄,他便可能有掉脑袋的危险。黄翔想了种种点子,最终把诗稿藏入蜡烛内(注:见《火神交响曲》,登载于民办刊物《启蒙丛刊》创刊号“编后记”的有关介绍。)。
流放者诗歌的秘密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社会上公开地被广大的读者接受和阅读,而只能是在朋友、熟人的小圈子内传阅。据有关材料介绍,诗人黄翔经常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手举火炬(蜡烛),向青年诗友们大声朗诵《火神交响曲》等鞭挞封建专制统治的诗篇,在友人心中掀起阵阵情感的狂风暴雨(注:见《火神交响曲》,登载于民办刊物《启蒙丛刊》创刊号“编后记”的有关介绍。)。这种小规模沙龙式的聚会是当时地下诗歌的基本传阅方式,不过,在文革时期也出现了大规模地传抄、阅读地下诗歌的事件,其中《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事件牵动了数十万计读者的心。文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手抄的、复写的、油印的、铅印的各种版本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10多首系中科院声学研究所青年科技人员陈明远的作品,陈明远为了消除误会,贴出“重要声明”,指出事实真相,结果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分子”,受尽种种折磨和非人待遇(注:参阅路丁《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4-15页。)。
具有“异端”色彩的地下诗歌除了在传抄过程中能够出现在民间的手抄本、汕印或铅印本上外,根本不可能在国家出版物上发表、出版(郭小川、臧克家等诗人以“合唱”姿态创作的少数作品是例外)。当时的报刊和出版社都被当作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而牢牢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任何诗作在面世之前都要经过反复的审查和“消毒”,这就断绝了地下诗歌发表和出版的机会。
当然,那些从事地下诗歌创作的诗人本来也可以办地下刊物来登载自己的作品。可是,在中国当时极为严格的新闻、出版管制条件下,创办地下刊物比登天还难。更由于那些从事地下诗歌写作的诗人政治地位都岌岌可危,个人偷偷写诗就已是冒险之举,如若抱团办地下刊物,那无异于组织“反革命团体”,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与中国文革同一时期的苏联、东欧地下文学却纷纷能得以发表。尽管六、七十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日益升级,但东、西欧贸易、文化、旅游交往却一直未中断。苏联许多地下文学作品常被偷偷带到西方国家发表、出版,接着,又偷偷被带回国内,由为数不少的地下刊物翻印出版。像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罗茨基的大量诗歌便是先在国外发表、出版,然后再传回苏联印行传布的(注:参阅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2章“萨米兹达特”:地下刊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文革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对立关系业已形成,虽然相互之间仍保持一定限度的交往,但似乎没有一个从事地下文学创作的中国作家敢像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托人带到西方发表。因此,从内外环境来看,文革地下诗歌都不具备浮出地表,在出版物上刊载、出版的机会。
由于写出的作品难以得到社会承认,甚至还会招来灾祸,一些流放者诗人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流放地秘密地写着诗,又无可奈何地销毁用自己心血凝成的精神产品,诗人牛汉的《蝴蝶梦》表现的就是地下诗歌的那种诞生伴随着夭折的“不幸”处境:
那些年
多半在静静的黎明
我默默地写着诗
又默默地撕了
撕成小小的小小的碎片
(谁也无法把它复原)
一首诗变成数不清的蝴蝶
每一只都带有一点诗的斑纹
(谁也无法把它破译)
它们乘着风
翩翩地飞到了远方(注:见《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95页。)
这是一声为诗歌的死亡而举行的悲壮祭奠,诗人特意用括号标示出的两句诗“谁也无法把它复原”和“谁也无法把它破译”,既有嵇康临刑前弹完一曲《广陵散》而直呼“绝矣”的沉痛,也有黛玉命绝前焚毁诗稿的无限凄凉。不过,诗的后半部写出了诗人的自我告慰:那撕成碎片的诗篇具有了生命力,它们的亡魂附在蝴蝶上,飞向艺术的天国,去寻找它们最终的栖息地。相信像牛汉这样有过焚诗经历的流放者诗人决不止一二人,我们后人也难以估算到底有多少优秀的地下诗篇就这样化为灰烬。
另一些流放者诗人似乎对自己作品未来的命运更乐观一些,他们执著地认定自己的诗篇总有“出头之日”。诗人黄翔在他文革时期写的诗论中自信地宣称:“唱歌的人死了,歌声也就停止了,但诗的歌永远不死。”他似乎指着自己的诗作对假想的读者说:“这里有属于未来的种子,只有白痴才看不见它。”(注: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写于1968-1969年的诗论),见《黄翔作品集》(打印稿),第481-482页。)在20世纪上半叶,屡遭不幸的“白俄”流亡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首《寄语百年之后的你》,写出了她对自己诗作后世命运的乐观期待:“在我亡故后的一个世纪,/你来到世上,——/现在我为你而执笔/畅叙必死者的衷肠。”(注:见《温柔的幻影——茨维塔耶娃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74页。)诗人的预言已提前实现,在自杀而亡(1941年)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位生前备受当局迫害和读者冷落的诗人已经拥有了大批读者知音,并被世界诗坛公认为自古希腊萨福以来最杰出的女诗人之一。
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青年诗人陈明远也唱出了茨维塔耶娃式的“未来之歌”。1976年的一个秋夜,诗人在地震棚里为他的诗集《地下诗草》写作了跋诗《唯一的梦》,诗的结尾一节是这样的:
绞架、断头台、火刑堆,
都抹不去坚定的笑容!
我将消逝。但这地下诗草
会永远被世人传颂!
无论映照着萤火虫、
皓月、冰雪、启明星,
直到朝阳升起欢庆的灯笼,
那是我永生的梦
——唯一的梦(注:陈明远:《劫后诗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76页。)
需要补充的是,文革地下诗篇在当时却也有时被当作“反面教材”,获得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脸”的机会,这可算是一种特殊的发表方式。诗人曾卓回忆说,他偷偷写的诗篇“在一个一千多人的大会场上被宣读了,不过,那是插在揭露我的‘罪行’的大批判当中,作为不肯低头‘认罪’、‘梦想翻天’的‘罪证’的。当时我被‘驾着飞机’站在台上。听到那些诗竟然能公之于众,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注:曾卓:《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见《曾卓文集》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418页。)诗人周良沛也有相似的经历:“我因‘死不认罪’,常被揪到台子上批斗,有时也把我的‘黑诗’抄在饭堂的大字报上‘示众’。可是,每当夜间见人秉烛边抄那些诗边说‘真黑真黑’时,我却为别人替我提供了发表阵地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注:周良沛:《铁窗集·自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3月香港第1版。)
噩梦般的文革终于在1976年10月画上了休止符,在那之后的三四年里,大批被放逐的诗人纷纷回归诗坛,他们一方面唱出了时代的新赞歌,另一方面开始整理、出版那些在黑暗的岁月里写下的地下诗篇。值得称赞的是,绝大多数诗人都能依据历史主义的态度,尽量保留地下诗篇的本来面目来发表和出版,即使对个别诗篇作一定的润色,也会专门作出说明。在这方面,牛汉、唐湜等老诗人所作的努力更加令人感佩,正是他们的“实录”精神,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见到地下诗歌的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