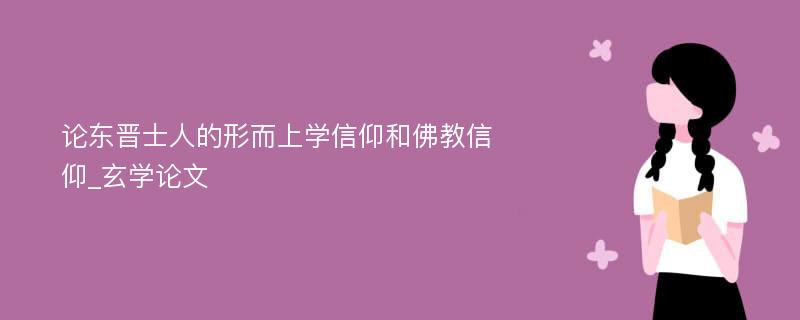
论东晋士族的玄学信仰与佛教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佛教论文,玄学论文,东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1—0090—07
汉晋之际,中国士大夫在思想信仰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道自任的道不再仅仅是圣人之道,还有玄道和佛道。东晋时期,政在士族,祭在司马。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从人生实践入手,研究士族的玄学信仰和佛教信仰之关系,对于理解两晋南北朝的学术与思想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众所周知,魏晋玄学所依据的基本典籍是“三玄”:《易》、《老子》和《庄子》。而三玄在玄学不同的时期,各自所具有的地位不同。玄学的第一阶段即正始时期,《庄子》没有地位,所重的典籍是《老子》和《周易》。玄学的第二阶段即竹林时期以后,直到东晋时期,《庄子》占有核心地位,《老子》、《周易》的地位逐渐淡化。从学术的转型和哲学思想的兴起来看,第一时期的王弼、何晏之学,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地位当然十分重要。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有真信仰者即能见诸于行事的人,还是竹林名士。所以,研究玄学之为信仰,核心的典籍还是《庄子》。《庄子》在魏晋名士中的地位,如同《六经》在礼法之士中的地位,那是思想的源泉,情感的归依,行为的准则,地位是很高很高的。
从信仰来看,玄学有个根本问题,即天之徒与人之徒的分别。这一个分别,前人不辨,今略申论如下。《庄子·人间世》: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人善之,蕲乎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
天之徒,以天为师,与自然同类。在天面前,自己与天子都是天之子,本性上相同,地位上平等,就不需要对外说什么了。人之徒,以人为师,与人同类。人有亲亲尊尊之别,每个人都尽人臣人子的礼节,我能不这样做吗?作为天之徒,是从人的本性上界定的,具体体现在内在的心灵和思想之中。作为人之徒,是从社会关系上界定的,具体表现在外在的行为和言事之中。天道与人道相对立,本性与形迹相对立,内直与外曲相对立,是庄子的基本观点。儒家礼教,仅仅体现在形迹之中,它不讲人的本性,它没有给人的心灵留下生长的空间。人的本性在哪里呢?在自然之中。人的心灵生长的空间在哪里呢?《庄子》认为在六合之外即方外。因此,《庄子》又有方外、方内之分。所谓方内方外,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文化上的概念。所谓方内,就是生活在依照礼教而建立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之内,受礼教之束缚,即郭象《庄子注》所说的“桎梏于内者”;所谓方外,就是不受礼教的束缚,摆脱了世俗社会的桎梏,游离于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之外的人。方外之人的重要特征是,与造物者(道)为友伴,神游于尘世之外,逍遥于自然之境,故好生而乐死。方外在哪里呢?在现实社会之中,这样的方外只能存在于远离群落的山林之中,自先秦以至魏,莫不如此。然而,两晋之际,士族当权,他们不愿隐于山林,依照王羲之的说法,那样太苦,受不了。他们更愿隐于朝廷。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间,这是他们的理想。用东晋名士孙绰的话说,就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其理论基础就是郭象的“游外而宏内”理论:
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1]《庄子·大宗师注》
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也。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以为天下也。[1]《庄子·大宗师注》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1]《庄子·大宗师注》
所谓方外,本来只存于二处:一是山林之中,二是心灵之处。此二者都是世俗权力不能干涉的地方。在这里,人是自由的。然而,没有政治空间和经济保障的“方外”,并不能使心灵得到自由的生长,所谓天之徒,只是一种思想情怀而已,在实践中,那些能够称于方外之宾的人就是独身一个的隐士。独身一人,远离村落与文明,不是创造心灵生长的空间,而是从根本处扼杀了心灵生长的可能。所以,过着独身隐士生活的“天之徒”不是什么真的天之徒,更没有什么逍遥自在的生活,而是真实的“天之奴”,被大自然的一切所奴役,比动物还苦。因此,方外不能离开方内,郭象“游外以宏内”的观点是言之成理的。然而正确的理论与正确的实践是两回事。在礼教文化之内,对原有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不做任何改变,是完全不可能实现“方外”与“方内”的结合,而只会导致方外与方内的相害。人生问题没有解决,政治责任也丧失了,朝廷的玄学权贵是要负责任的。要在方内为心灵的自由生长与自在生活建立一个空间——方外,必须有四个支持体系:一是文化上即价值理论体系的支持;二是教育的支持,要使方外观念深入民心并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三是政治上的支持,要有独立于王权的政治空间、思想空间、信仰空间、学术空间、言论空间;四是经济上的支持,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人在社会之中,是做不了自己的主宰的。一言之,心灵的生长,应有文化空间、教育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四者缺一不可。并且,这种空间的建立,绝不仅仅依靠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变革,而是有许多因缘凑泊的结果。其中,存在能够自主的各种力量的生长至关重要。没有制度上的探索,没有自治力量的生长,仅仅作为一种思潮,“方外”能建立起来吗?中国自古没有思想自由和心灵自由生长的空间,两晋士大夫没有好好探索,是有责任的。当然,在那种种族冲突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东晋南朝士族最后自己也被陈霸先给夷灭殆尽,也怪不得他们。历史没有给士族以机会,没有给中国文化以机会,那就寄望于未来吧。
从人生的根本问题——生死问题来看,《庄子》把生死看成天道自然生化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礼教所视的家族血统延续的一个环节。以道观之,生与死都是生化之道的表现,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生不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就叫齐生死。生死与道同体,与化同体,这是庄子关于生死问题的基本观点。在这个观点中,生死问题与祖先无关、与地神无关、与天帝无关,生死问题只与道有关。这就割断了家族的连续性和血统上的关联性,突出了生命的个体性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断裂性。强调生命的个体性与血缘上的断裂性,是思想的进步。魏晋玄学将这个思想推到极致。郭象说:
死生宛转,与化为一,犹乃忘其所知于当今,岂待所未知而豫忧者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时哉,未化而死,焉知己死之后哉!故无所避就而与化俱往也。[1]《庄子·大宗师注》
夫死生犹觉梦耳,今梦自以为觉,则无以明觉之非梦也。苟无以明觉之非梦,则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觉梦,未知所在,当其所遇,无不自得,何为在此而忧彼哉![1]《庄子·大宗师注》
生与死,都是与化同体的。生生死死、宛转循环是天道的规律。人们不明生死,犹如不辨醒与梦,梦时不知自己在做梦,醒时又焉知自己是醒着呢?郭象进而说: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1]《庄子·齐物论注》
郭象明确地否定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观点,不仅断绝了人生与祖先、天地之神的关联,而且进而也否定生死之外有一个超然的主宰。他认为盗(或言自然),就是在生死之中,离生死之化而别无道立。这个观点有点像熊十力所谓的即体即用,实际上是以用为体,倒果为因。他说:
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1]《庄子·大宗师注》
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1]《庄子·天地注》
郭象认为,生是自生自得,相因而独化,不资于任何其他主宰。不需要对上帝、地神、祖先感恩,我不欠他们什么,也不要感谢道,离我之外别无什么独立的道。道不离我,我即自然。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不仅把个体突出出来,而且强调个体的自主性、自足性。自生自死,自了生死,不依外物,自做主宰,是郭象“独化”说的真正内涵。
郭象在否定家族的血统连续性和道的关联性,强调个体的“独化”性的同时,又突出强调个体之间在本性上的差别性。这就是性分理论。不同类的事物,有不同的本性。同类的事物,又有各自不同的本性。人也如此。人与异类相比,人有人的本性;人与人相比,各自的本性又不同。尧与许由都是人,但各自本性不同,但逍遥为一。各得其性,并根据自己的本性,“适性”、“任性”、“尽性”而不“伤性”、“残性”,就是逍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性,并培养自己的本性,发扬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那就是自由。人与人的本性不同,但自由是相同的,这就是郭象所谓的:“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庄子·逍遥游注》
陈寅恪说:“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2] 大多数学者赞同陈先生的看法,认为玄学到了向秀、郭象就终结了。东晋一朝的玄学没有什么发展。从学术上和思想上看,这是对的。但在信仰上,东晋一朝才是玄学真正的黄金时期。东晋名士礼玄双修,此一点唐长孺早有所指。不反礼教,主张自然与名教同,是其一大特点。正因于此,才是东晋士族思想信仰上成熟的标志,这一点在王导、庾亮、庾冰等人身上有集中反映。不反政治,就是装饰,无论如何说不通。还有人认为,东晋玄学与佛教合流。这个观点也要仔细分析。东晋前期,即王导、庾亮死之前,玄是玄,佛是佛,并没有合流。玄佛合流是在东晋的中后期,地点有二,一是建康,二是会稽。至于其他地方如襄阳、庐山等,并未有玄佛合流的事实。玄学作为个体信仰,它的存在,不仅东晋有之,而且,整个东晋南朝260余年的历史,都是存在的。这一点,是基本的事实。
二
佛教是外来文化,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性。佛教分析人生问题有二条:一是生死流转,二是寂静还灭。前者是生死烦恼,后者是涅槃解脱。二者有一个统一的基础,那就是十二支缘起:此生则彼生,则是生死流转,三世轮回,苦海无边;此灭则彼灭,则是涅槃解脱,脱离三界,修证胜果。缘起理论在论证生死流转的同时,也为还灭解脱开了方便法门。所以,生死与还灭,统一的基础都在缘起理论上。
依大乘之见,四谛中的灭谛,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四谛只是对小智所说的方便法门。若论根本,就要说二转依。一着眼于能,一着眼于所,内而身心,外而事相,皆能舍染而趋净。《瑜伽师地论》以境、行、果统摄,由境起行,由行证果,一以舍染趋净为根本。其实,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印度佛教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舍染趋净。染净是根本,迷悟只是资粮。这一点,不能动摇与淆乱。
然而,佛教是外来文化,在中国没有固有的生存空间。它惟一的、不可选择的生长空间只能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空间。否则,就不可能生根、发芽。佛教作为一种个体信仰性质的宗教,它在中国生存的空间是玄学开辟的,因而与玄学具有共生性。我们在考察东晋士族的信仰之后,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信仰佛教的出家与在家士族,绝大多数是出儒入玄的士族,而非传统的礼法士族。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礼法士族有公开、虔诚信仰佛教的行为,惟一例外的蔡谟,也仅仅是晚年舍宅为寺而已,并未有其他的证据,其早年一直是公开反对佛教的。
玄学名士由玄入佛,决非为佛教而佛教,为信仰而信仰,而是因为个体的人生问题玄学解决不了。吕徵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许里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都谈到同一个问题,即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本文试从士族的人生问题入手,做点申论,以明东晋佛学在人生问题上的基本走向和基本特点。
东晋末期的僧叡法师在《喻疑》中对汉晋佛学发展的一般线索与问题作了一次回顾与总结,值得我们参考。在这篇文章中,僧叡有几个观点是很重要的。一是关于汉晋佛学的发展。他认为汉末以至西晋,中土出家人很少,做的工作无非是“撰集诸经”,并用格义的方法作一些解说。这说明,中国佛教徒并未开始对佛教义理展开研究。真正的研究开始于西晋末年,至东晋罗什来华则大兴。从西晋末年至东晋末年的中国佛教,最受重视的是三部经:《般若》、《法华》、《涅槃》。他们认为这三部经是显示过神验,从信仰来说,完全可靠。二是《般若》、《法华》、《涅槃》三经有一个关系。《般若》是遣虚妄,《法华》是明究竟,《涅槃》是讲实化,三者合,则法门完备。三是说,从《般若》到《法华》,从《法华》到《涅槃》,东晋佛学的流行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其中核心问题是:“谁是作佛的主体或承担者?”正是这个问题才使佛学由《般若》而《法华》终而《涅槃》。一言之,是佛教修行实践中的问题推动了东晋佛学的发展。四是说,罗什不谈佛性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涅槃经》,如果看到了,他对佛性问题也不会有什么疑义。根据上述四点提示,本文讨论以下三个问题:1.玄学在实践上遇到哪些困境,使士大夫选择了佛教来解决?2.《般若》、《法华》、《涅槃》三经在东晋时期所遇到的实践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中国新出现的,还是印度原有的?与玄学有什么关系?3.罗什对法身的理解为什么与慧远有分歧?
综观中国本土文化的礼教与玄学,在实践上的核心问题不是印度的染净问题。中国人没有染净的观念,即使理论上可以理解,但在实践上并没有舍染取净的困境和问题,因而对染净之分野并未有真切之体会,这就注定了中国士大夫佛教决不会以染净为核心。外来的、异质的文化之所以被接受,必定是为本土文化所培育的心灵所具有的问题而服务,不可能制造一个虚假的问题强加给士大夫。当然,有二种情况是可能的:一是帮助士大夫发现原本存在但未意识到的问题;二是在解决原有问题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么,礼教和玄学在实践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二者的核心问题是人与道的关系问题。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3]《论语·卫灵公》闻道、谋道、体道、悟道、证道、行道、弘道、尊道、重道,必要的时候还要以身殉道,凡此均为士大夫一生的责任和使命。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不仅在思想上对道要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还要在情感上热爱道,进而在实践上和境界上与道合一,获得一种审美的体验(乐)。这是不容易的。儒者所信服的礼教,其道是有具体内容的,即生生之道、资生通运之道。儒者与道的关系也很具体:一是人与天的关系,二是人与地的关系,三是人与鬼(先王或祖宗)的关系,此三者皆有资生养育之功。那么,怎样才能与道合一呢?首先要有仁爱之心,其次要承担养生送死的责任,并且由近及远,最终能承担天下苍生养生送死的责任,那么,就参赞了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同德、与生化之道同体了。一个人,力量很小,怎么可能承担天下苍生的资养之职呢?很简单,凭借文化的力量,通过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来完成,因为文化的力量是无边的。说白了,儒者所谓的修齐治平,落实在人生实践上,就一条:做圣人之徒,行圣人之道,弘圣人之教而已。
礼教存在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上,故其理论要点就是人禽之辨。它不承认文明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更加抹杀个体在本性上的差异性,反而突出血统性、政治性和疆域性,具有一切古典文明共同的缺憾。
玄学作为礼教的异端,既有同根的一面,又有批判的一面。就文化的同根性来说,玄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人与道的关系问题,并且这个道也是天地生化之道,只是仅有自然无为的性质,而无人间的内容。在玄学的人与道的关系中,没有人与天帝、地神、人鬼的关系,没有养生送死的责任,更没有血统性、政治性、疆域性和排他性。玄学的道是普世的。就批判的一面来说,玄学认为礼教是尘垢、是囹圄、是桎梏、是残生伤性的束缚。礼教彰人之形迹,而暗人之本性。它强调人与人的本性是不同的,与化同体,任性逍遥才是人生的目的。在政治上,主张不治而自治,无为而无不为,落到实处就是放弃政治责任。
反礼教是容易的,在行为上放荡就行了。放弃政治责任也是容易的,只要不做官就行,即使做了官,也可以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然而,反礼教并不意味就从礼教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谁都明白,异端就在正统之中,鲁迅所谓魏晋反礼教的名士骨子里是信礼教的论点,一点也不错。在实践上,真正摆脱礼教的束缚,是需要新文化新制度的建设,这一点很不容易。另外,与化同体,任性逍遥,从理论上可以说得通。但在实践上怎样实现呢?综观名士的实践,一是任情而为,比如裸体、饮酒、好色、丧服吃肉、集体淫乱等等,然而这是禽兽之径,并非逍遥之途。若此就是任性逍遥,那禽兽是最逍遥的了。这不是文明不如野蛮、人不如禽兽吗?显然不是。二是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有点像禅定。然而禅定是由观引导的,其结果是会生出智慧。庄子的“心斋”断断是没有智慧的,它的结果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一片漆黑,那不就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怎么个“与化同体,任性逍遥”呢?郭象说,物有真性,人有真我。这很好。但在实践中,怎样认识这个真性或真我呢?他没说,因为不知道。所以,玄学仅仅在理论上有突破,在修行实践和制度建设上,根本就没有探索。而已经传入数百年之久的佛教有理论纲领,有修行实践,有僧团制度,又是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礼教的外来文化,满足了士族打破礼教束缚、确立个体信仰、追求人生自由的需要。由玄入佛,就是士族信仰的大势所趋了。
人与道的关系问题在人生实践上的意义有三个:一是寻找生死的依据。在玄学那里,道是生的依据,也是死的依据。明道即是要明白生死之理。玄学家所谓的本无,即以“无”为生死之本,所以生死皆与道同体,与化同体,是天道生化的环节。二是认识自己的本性。玄学认为本性由命注定,命不同,性分就不同。因而人与人之间的本性是有差别的。要适性逍遥,首先就必须认识自己的本性。本性来源于道,是道在不同事物、不同人身上的体现。只是性分不同罢了,即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三是理想人格。儒玄二家关于圣人的内涵不同,但标准是相同的:即圣人是道的化身、道与圣人是合一。确立圣人的意义在于,圣人是道在人间的直接证据。若人间无圣人,道离人高不可及,道的真伪,谁能分得清呢。汤用彤说:“汉魏以来关于圣人理想讨论有二大问题:(1)圣是否可成;(2)圣如何可以至。而当时中国学术之二大传统立说大体不同,中国传统(谢论所谓孔氏)谓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印度传统(谢氏所谓释氏)圣人可学亦可至。”[4] 其实在印度佛教中,佛并不是中国式的理想人格,佛可学可至,与中国文化中作为崇拜和祭祀对象的圣人是否可学可至,完全是两回事。圣人理想,是纯粹的中国问题。圣人不可学不可至,那要立圣人干什么?原因是,圣人是人祭祀的对象,信从的对象,侍奉的对象,敬畏的对象,效法的对象。有了圣人,人生就有了方向。所以,圣人,在中国,是人生实践的旗帜和方向。打圣人的旗,走圣人的路,这个问题很重要。
总之,人与道的关系在人生实践上必然要归结于明理见性与圣人理想两个核心问题。前者是人生的依据,后者是人生的方向。这是中国士大夫最重要的人生问题。
三
印度佛教没有这两个问题,印度佛教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明因缘,分染净。生死流转是染,涅槃寂静是净。然生死与还灭,皆依据于缘起。所以明因缘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缘起理论和染净之分,从理论上士族可以理解这个理论的大意,但在实践上,并不是把这两者作为核心问题来解决,而是把这两个理论视为明理见性的工具和塑造新的圣人理想(佛)的材料。这一点,在东晋佛学中有突出的体现。僧叡《小品经序》:
《般若波罗蜜经》者,穷理尽性之格言,菩萨成佛之弘轨也。[5]《出三藏记集》卷8
僧叡《大品经序》:
非心故以不住为宗,非待故以无照为本。本以无照,则凝知于化始;宗以非心,则忘功于行地。[5]《出三藏记集》卷8
僧叡《法华经后序》:
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5]《出三藏记集》卷8
僧叡《大智度论序》:
夫万有本于生生,而生生者无生;变化兆于物始,而始始者无始。然则无生无始,物之性也。[5]《出三藏记集》卷10
道安《安般注序》:
夫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何难也![5]《出三藏记集》卷6
道安《大十二门经序》:
淫有之息,要在明乎万形之未始有,百化之逆旅也。[5]《出三藏记集》卷6
道安《道行经序》:
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5]《出三藏记集》卷7
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般若波罗蜜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首,以法身为宗。[5]《出三藏记集》卷7
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抄序》:
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5]《出三藏记集》卷8
齐万物于空同,明诸佛之始有,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阶,趣无生之径路。[5]《出三藏记集》卷8
夫物之资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与本,万理之源矣。[5]《出三藏记集》卷8
僧肇《般若无知论》:
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
夫圣人功高二仪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弥昏。岂曰木石瞽其怀,其于无知而已哉!
是以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
生灭者,生灭心也。圣人无心,生灭焉?然非无心,但是无心心耳。又非不应,但是不应应耳。是以圣人应会之道,则信若四时之质,直以虚无为体,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灭也。[6]《肇论》
般若理论在印度有三个要点:一是大悲心,二是解空相慧,三是菩萨行。怎么到了中国,这三个问题都淡去了,人们关注的是“有无本末”及其“空、寂、真如、法性、法身”等问题呢?很显然,东晋士族把“空、寂、法性、真如、法身”看成是万有的根据,它们在实践中的地位就等同于中国文化中的道。然而,印度佛教并非如此,诸法实相,不是根本。它在观行中的作用,仅仅是增上缘而已,根本之处还在转依,即染净境界依上。《般若经》说,不依俗谛,则第一义谛难立。《成唯识论》说,不明依他起之幻,则难成就圆成实性。大乘空有二宗、二谛三性之说,把俗谛和依他起性(相当于俗谛)看成是各自理论的肝髓。而东晋佛学却把真谛等同于道,视为认识与实践的根本,实在是一种颠倒。很显然,之所以产生这种颠倒,是因为没有把缘起与染净问题作为核心,而是把人与道的关系问题视为核心。走的路子,还是重在认识,即明理见性,其禅定实践也最终归之于悟道(体寂),这就十分偏颇了。悟道只是能,趣净才是所。所,才是印度佛教的方向与道路。而东晋佛学却把重点放在能上。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由于东晋佛学把探求万有的本质、真性、究竟视为自己的任务,而般若学从因缘空到当体空一空到底,只能“遣有”,而不能满足人们寻求生死根据,心性真我的需要,所以《法华》、《涅槃》应时而盛起。按照僧叡的观点,《法华》的贡献在于“明究竟”,什么是“究竟”呢?就是“诸法实相”与“十如是”理论。《涅槃》的贡献是讲“佛有真我”,解决了一个成佛的依据与主体问题。其实,《法华》的“诸法实相”是佛的境界,只有成具佛的智慧与功德,才能做到“三界互具”、“一念三千”。并非三界诸法本来如此。《涅槃》说佛性,只是因义、界义、清净义。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从因义和当有义来说。心性清净与烦恼不同类,但依据还是缘起理论。不谈缘起,根本就无法分辨染净,此所以缘起理论为佛学之基石也。然而,东晋佛学,却把“诸法实相”视为究竟之实有,把“佛性”视为法身之实有,按照印度佛教的教义,这都是错的。原因还是一条,即中国玄学的思维在作怪。《大乘大义章》是东晋佛学的重要著作,它反映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原则区别。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等人在系统地比较了罗什与慧远在佛学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之后,得出结论说:
“佛”作为法身,是否是真实的存在?与此有关,众生是否皆有佛性?这是当时佛教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在鸠摩罗什与其门徒之间,也有反复讨论。鸠摩罗什的哲学是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实体存在的,他的方法论又使他从不坚持任何肯定的意见,所以他始终不置可否,但倾向则是否定的。僧叡设想鸠摩罗什会因闻得《大般泥洹经》的说法,“便当如白日其胸襟”云云,其实正是僧叡自己的心情。[7]467
在宗教观念上承认“神”的永存,在现实世界肯定有作为事物本质的“物质”实有,以及作为现象变化的因素“生”的真实,是慧远佛教哲学的三大支点,也是有别于鸠摩罗什的最基本的方面。这些特点的形式,固然有佛教内部的派别原因,如他晚年所信奉的主要是说一切有部和犊子部的阿毗昙学,使他难于理解鸠摩罗什所传的中观学说,但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更加立足于中国土地的社会基础,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外来的思想。[7]700
我认为,上述观点十分精辟、正确。慧远把“神”视为不灭,把“四大”视为“实有法”以区别于“因缘法”,把“法性”视为万有的真实本性与依据,把菩萨法身也视为实有等理论,其目的就是要为生死找依据,为作佛找依据。其所谓的“神”是生死轮回的依据,“法身”是解脱作佛的依据,“四大”、“法性”,是万有的本原,其功能相当于传统文化的“道”,所以,完全可以说,东晋佛学,从道安到慧远,都是为解决士族的人生问题而服务。这个人生问题是人与道的关系,为中国所独有。我们说,中国佛教的根子在中国,内容有多方面,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自东晋佛法初盛,佛教就是为中国人自己的人生实践服务。当然,中国佛教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仅仅是士族固有的人生问题,还包括由此而引生的诸多相关问题,如僧祐《弘明集》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多说了。
总之,东晋佛学在人生问题上,所打的旗、所走的路、所解决的问题、所重视的修持方法,都具有中国士族所固有的特色,而与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拉开了距离。
收稿日期:2004—10—25
标签:玄学论文; 佛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东晋论文; 唐僧论文; 出三藏记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庄子论文; 般若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佛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