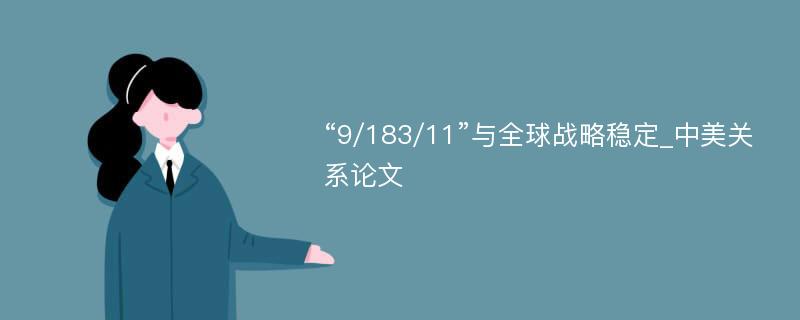
“9#183;11”与全球战略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在此期间,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及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恐怖主义无疑是对人类进步的一种反动,必然遭到世界各国的唾弃和反击;但同时还应看到,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也在根本上凸显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及其深刻的矛盾,标志着美国霸权已经发展到某种极限,不仅改变了美国主要的安全关注,还动摇着原有的国际战略关系框架,直接冲击着原有的全球战略稳定,并从反面影响乃至推动达成了一种新的全球战略平衡。
一、体系的深刻矛盾
长期以来,全球战略稳定一直属于“国家中心”模式,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主要角色是国家,二是主权国家承认并遵守主要的国际规则。但“9·11”恐怖袭击开始改变了这种模式,因为恐怖主义以非国家形式出现,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和恐怖主义进一步泛滥带来了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改变,从而在实际上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恐怖主义威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出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恩格斯曾经说过:“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①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结果越来越难以预料。从历史上看,只要物质世界的不确定性过大,一些人甚至会退向宗教原教旨主义。②
在本源上,当前的国际体系以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为经济基础。不幸的是,资本扩张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给各国带来普遍的发展机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达与落后、富裕与贫穷、优越与绝望之间的强烈反差。由此而来世界仍然得不到安宁,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也更加分散、更加广泛。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与发展机会有限之间的矛盾是当代国际政治根深蒂固的症结所在,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紧密相关,甚至有时会以极端的方式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激化程度。没有相关国家内部的社会进步,没有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没有高超的战略智慧,就难以消除国际安全领域潜在的巨大风险。
恐怖主义活动及恐怖网络的广泛存在说明,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聚集了复杂程度和深刻程度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全球政治进程中的边缘化力量甚至在对立和绝望中走向极端,追求模糊的非现实目标,用非理性手段与强者对抗。对于他们,甚至结果都已经不那么重要。恐怖主义的猖獗和美国以保证自身“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反恐战争进入国际政治的前台,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各种深层矛盾激化的结果,世界也由此变得更不安定。
二、强权也会失效
然而,美国显然误读了“9·11”的战略涵义。恐怖袭击标志着美国霸权已经扩展到某种极限,标志着原有国际体系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和利益倾斜,处于某种临界状态。事实证明,“9·11”不仅改变了美国主要的安全关注,还动摇着原有的国际战略关系框架。多年的反恐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资源,并严重损害了美国霸权的信誉,甚至欧洲一些国家也不得不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就像自然厌恶真空一样,国际体系厌恶不受约束的权力。”③
恐怖主义力量大多存在于地缘政治的“灰色地带”,往往也位于不同文明的断层线上,因而在中亚、中东、东欧、非洲、东南亚等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正是在这样的灰色地带,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根深蒂固并在近年日趋猖獗,成为国家力量和强权失效的地方,甚至成为权力的“黑洞”。如何避免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失效,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难题,没有战略上的耐心和信心,没有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于过于相信冷战后具有的强势,美国显示出明显的战略自负,其塑造世界的愿望十分强烈。上台伊始,小布什更是强调“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挫败敌人将其意志强加于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和友邦的任何企图”。这种愿望在“9·11”事件后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在反恐的旗帜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反恐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些地区的强权干涉涂抹上了更“合理”的色彩。“‘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霸权的鼓吹者创造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带动起整个国家的人民。而入侵伊拉克则使美国进入了盛衰循环的消涨过程中远离均衡的状态。”④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的艰难经历说明,即使拥有再强大的权力,也有其运用的范围和界限,超出了这个范围和界限就难免力不从心,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权力使用过度。何况直至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抵抗仍在继续,短期内仍然难以消除。可以认为,即使在安全领域,美国也存在着某种弱点。以极端势力的恐怖网络或体系为例,美国对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的打击不能不说迅速、猛烈而有效,但是由于在从北非到南亚、东南亚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基地”组织生存的土壤,目前恐怖分子在这些地区仍然维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极端势力已对国际安全构成了灾难性威胁,恐怖活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恐怖分子已组成了复杂的网络,打掉一个结点,其他的结点还会照常运行。
反恐战争极大耗散了美国的权力,甚至2008年以来美国遇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也与之存在密切联系。反恐战争拖累了美国经济,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来,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相辅相成,并共同构成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石,如今美国却难以左右逢源。
金融危机使持续平稳增长近30年的美欧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应对危机做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一些积极效果,但经济发展中一些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债务负担反而不断加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进入2011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元疲软,房地产市场下滑,国家债务迅速攀升,到2011年8月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接近危机前的2倍。2011年8月6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负面,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及欧洲经济的乱局不仅使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蒙上更深阴影,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和中国国家安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等西方国家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困难,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甚至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而实际应属于经济模式乃至其霸权体系遭遇的深刻危机,意味着金融扩张也发展到了某种极限。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美国总统里根先后上台,为摆脱石油危机的影响和经济滞胀的困境,美英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崇尚自由竞争。这一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在美欧内部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向大资本积聚。到2008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风险积累发酵,金融扩张与金融监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必要平衡被打破。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金融危机迅速在全球范围蔓延开来。在根本上,金融危机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应。当金融资本将盈利的目标扩展至社会最贫穷群体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模式已发展到某种极限,危机的爆发已不可避免。而当前西方空前的债务困局说明,美欧以金融资本扩张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危机后并未得到有效和必要的调整及修正,经济运行中一些结构性矛盾仍在进一步积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不能排除再次发生衰退的可能,若如此,国际体系将面临重大冲击和动荡。
美国的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难以挽回霸权的衰落,不可能为全球战略稳定提供根本保障,甚至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富裕与贫困、利益垄断与分散需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引起新的动荡。只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总体进步和国家间利益联系的日趋增强,大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持续不断的局部性动荡由此成为国际体系自身调节的一种常态。从这一角度理解恐怖主义,可得出多一些的启示。
三、可控的动荡?
怎样收拾反恐战争的残局,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重要议题。2011年5月19日,奥巴马更是发表了中东政策演讲,推出“中东新政”,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实施扶持计划,鼓励中东北非的民众通过“和平方式”推翻“专制政权”,把推动这一地区的“政治改革”确定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最优先议程”。奥巴马“中东新政”出台的背景主要有三个:一是“9·11”后美国反恐战争历经10年,并早已显出疲态,“中东新政”成为奥巴马上台后政策调整的深化发展。二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变局中已经摸索出一套有效方法,尝到了甜头,有进一步拓展的冲动。三是受成功“猎杀拉丹”的鼓舞。
“中东新政”的提出意味着美国战略的重大调整,代表着以反恐为主线的中东政策的结束,可被看作一种可以称为“超越控制”战略的开始。这种战略与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实施的“超越遏制”战略有许多相类似之处。美国在与苏联的紧张对峙中并没有得到多少便宜,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变战略,利用国际形势的缓和,发挥美国的相对优势,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手段,用“和平演变”的方式从外部推动了苏东剧变,改变和动摇了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最后“不战而胜”。老布什政府更是把这种战略称为“超越遏制”。奥巴马“中东新政”也是新形势下针对中东地区的“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战略。即通过若即若离的挑动、施压、利诱和“软战争”等方式对大中东实施战略管理和战略控制。
“超越控制”属于一种比较高级的战略,较好地适应了中东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中东具有特殊的地缘地位并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世界政治的众多矛盾在中东地区聚集,资源争夺、领土边界冲突、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发展困境、强权干涉、宗教争端等交汇在一起,解决起来难而又难,其中几乎任何一个问题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世界主要力量都在这里拥有重大利益。中东发生动荡是正常现象,不出现问题却是奇怪的事情,犹如地球上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区域。美国对于这样一个地区,必然要加强控制和管理,否则其霸权将无从谈起。所以,“中东新政”就是要强化美国的控制。当然,中东的动荡不能消除,但如果能够把动荡维持在大体可控状态,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就会进一步加深,“可控的动荡”符合美国的利益。
如果控制得当,中东不仅不是拖累,通过中东反而可以撬动全球政治。实际在中东北非变局中,美国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对美国的需求更加明显;欧洲受动荡的影响和冲击最直接,在接受难民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意大利就抱怨其他欧盟国家过于自私;而中国在北非的利益也遭受严重损失,在利比亚的经营成果几乎一夜之间被“清零”。通过控制中东,美国企图坐收牵制欧洲、挤压俄罗斯、限制中国之利,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先机。击毙拉丹,美国收获了成功,也使巴基斯坦和南亚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表面看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分歧增加,实际上对美国的依赖将有增无减。
“中东新政”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战略,由于注重软力量的使用和“超越控制”,美国可以避免深陷其中。如果能够维持“可控的动荡”,美国的战略优势就可以更多地发挥出来。“中东新政”的出台,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筹划具有比较强的纠错能力。反恐战略实施近10年才作出调整,时间确实不短,但毕竟得以改变。回想越南战争,美国也打了十几年,陷入泥潭。然而经过多年争论,最后美国还是撤了军,并且随后就改变了对苏战略,通过“缓和”从外部推动了苏东剧变。亦即,美国的大战略筹划有其自身特点,即使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毕竟能够修正。只是,中东地区的利益关系过于复杂,矛盾错综交织,未来局势演变不可能完全按照某一种力量的战略设计而展开,即使美国也没有消化整个中东的政治经济资源。现代史上,中东一些国家的政权更替就多次出现不符合美国意愿的情况。单凭美国自己的力量,不可能维持中东的稳定。
四、混沌中谋求稳定
“9·11”以来,国际力量结构及相应机制一直处于较为明显的动态变化之中。国际角色不断涌现,国际安全议题持续增加,国家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金融危机及其美欧经济困局更加剧了这样的混沌态势。⑤国际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演进。上述背景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不仅强化了国际机制的作用,呼唤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同时也要求强化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有效促进全球战略稳定。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制度供应不足之间存在的矛盾,⑥而这种矛盾正是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在比较混沌的国际体系中理清和维护必要的秩序,建立和强化新的战略稳定,已经成为大国不可回避的责任。
实际上,到目前大国关系已经和正在发生较大变化,竞争不掩合作,主要国家只有以更宽阔视野来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以美俄关系为例。俄格军事冲突给俄罗斯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但其积极意义却在其后逐渐显现出来:美国确认并开始尊重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以此为基础,两国出现关系稳定和战略接近倾向。2009年9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放弃东欧反导计划,把原本计划建在波兰、捷克等地的导弹防御系统转移到其他地方。尽管奥巴马政府极力淡化俄罗斯因素的影响,宣称使美放弃原反导计划是基于最新技术和威胁评估,但这一重要决定无疑为美俄关系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改善扫除了一大障碍,也有利于美国在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争取俄罗斯的支持。
美国放弃东欧反导计划不仅是美俄在欧洲地区攻防的具体结果,而且在深层次上更是全球政治背景深刻变化的必然反映。历史上,欧洲大国角逐带有浓重的地缘争夺色彩,地缘分界线像手风琴一样推来推去。冷战结束后,北约保留了下来,并不断吸收新成员向东扩展边界,美国进而计划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这自然引起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紧张,一退再退的俄罗斯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在南奥塞梯发起坚决反击并在反导问题上毫不妥协。
挤压别国生存空间在本质上属于“零和游戏”这一传统思维的惯性延伸。美国收手尽管晚了一些,但放弃东欧反导计划无论如何都属于一种进步,避免了美俄之间的紧张对抗,为加强协调提供了重要条件,欧洲安全也就有了更好的保障。而东欧国家更可以松口气了,如果由此得以摆脱大国争夺的沉重阴影,实在值得庆幸。在今天,直接的地缘扩张和占领已经不合时宜,东欧国家更有条件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东欧毕竟是东欧人的东欧,而欧洲也毕竟是欧洲人的欧洲,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总是需要这里的人民自己来承担,美国不可能长期超越欧陆之上。美国的政策调整最好不是权宜之计,改变过度经营东欧的政策不应在其他地区或用变通方式寻求补偿,地缘对抗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果真如此,传统地缘政治在这里就发生了积极改变,称其为拐点也不为过。
中美关系也是如此。美国对外政策的霸权逻辑将长期作用于中美关系,由此也强化了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人由此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发生的规律将再次应验到中美两国关系中去。中美冲突的危险当然存在,但远不是不可避免。因为中美之间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竞争与合作并存,不能将中美关系的未来简单归于某种宿命。进行更多积极的沟通与协调,不仅有利于中国,对美国也有益处。
达成中美关系基本稳定与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积极调整,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不可或缺的两项基本目标。仅有关系稳定,没有美国对华政策的逐步调整,将意味着中国在如何运用不断增长的实力,或在适应国际关系新变化方面出现了偏差和问题,变成了单向妥协。这反而会导致问题与矛盾的积累,使中美走向冲突,不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发现和充分利用能够约束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极端发展的积极因素,是中美两国战略家和政治家共同的任务,这将有利于化解中美未来可能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使中美关系沿着积极轨道发展,从而塑造中美关系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3、334页。
②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③Kenneth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00,p.28.
④[美]乔治·索罗斯著,燕清等译:《美国的霸权泡沫——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5页。
⑤有研究更进一步,提出无极世界的判断。参阅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
⑥参见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现代国际关系》庆典特刊,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