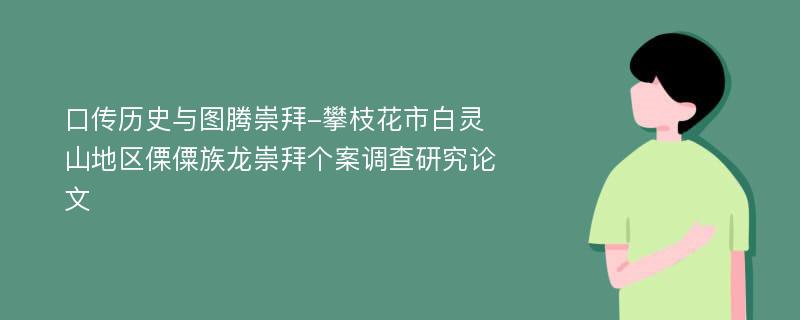
·金沙江文化研究·
口传历史与图腾崇拜 ——攀枝花市白灵山地区傈僳族龙崇拜个案调查研究
李生军
(攀枝花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 文化自信的建立,其前提是必须要有文化,没有民族文化,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所以要调查、研究,通过细致的工作,理清民族文化的根源和现实的存况。傈僳族是氐羌的一支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没有文字,傈僳族的历史文化依靠口口相传得以延续。在傈僳族的口传的故事或祭祀经中,可以很清晰地解读出傈僳族有着祖先崇拜、葫芦崇拜等信息,而傈僳族祖先崇拜和葫芦崇拜,其本质就是龙图腾崇拜。白灵山地区及其周边地域傈僳族的葫芦笙文化、祭龙习俗、以及无处不在的“龙迹”等是傈僳族龙图腾崇拜的精神创造及民族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白灵山;傈僳族;口传历史;葫芦崇拜;龙图腾
中华民族的初民在依靠自然、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龙”图腾,“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龙”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是具有超自然的神性且能支配和主宰本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灵物,“它在中国人的意念中不单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的客体,也是一个与人类异形同质、甚至可以自由转化的精灵;龙可化人、人可化龙的设定,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中国人自我神话的实践。”[1]2龙,随着中华初民的迁徙而不断与其他图腾文化融合,不断完善,不断被赋予新的神性。查海遗址中出土的两块龙纹陶片及大型堆塑龙,经测定形成时间为8000年。从堆塑龙摆放的位置来看,龙是作为神物被当地初民祭祀和供奉的,表明这里的初民在800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创造了龙图腾,有了崇龙的习俗[2]。从我国各地出土的大量龙形器物、雕塑、绘画、木刻等实物和民间关于龙的传说等文化遗产来看,中华民族的龙崇拜很早就广泛存在于各地的中华初民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龙图腾的创造、再构、不断赋予新内涵的文化史。不管文化怎样多元,在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文化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龙文化。是龙,把生活在不同地域内的,不同文化生境中的中华子孙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精神图腾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由于各自所处的山川江河、地形地貌、与之相伴的动物植物等自然环境的不同,龙呈现出不同的神职和存在方式。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很多民族没有创造文字或丢失了文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往往隐藏于民族服饰、生产生活用具、口口相传的故事或祭祀经等口传历史之中,民族口传历史与文字记录的历史同等重要,有时甚至重于文字记录。本文拟从傈僳族口传历史入手,追寻攀枝花市白灵山地区傈僳族龙崇拜的根源,并对当地及周边存在的龙文化现象进行调查研究。
第一,水利部将以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为依据,考虑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用水结构与发展规划,将《意见》确定的全国水资源管理红线指标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实施考核的依据。
本文所谓“百灵山地区”,是指地处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境内的、与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等交界,以白灵山为中心的傈僳族人生活的地域范围。
根据楚雄州、怒江州等地傈僳族的《祭祀经》、《创世纪》的记载,结合攀枝花境内傈僳族“呢扒”(东巴先生)的口述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百灵山地区为傈僳族先民迁徙走廊重要的节点”的判断。这里所谓的“节点”,是指白灵山地区是傈僳族重要的生息地之一。白灵山地区的傈僳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因为“走不动,不想走了”而留下来世居本地的傈僳族,如盐边县国胜乡民胜村转龙沟一带的傈僳族,这样的傈僳族主要集中在白灵山腹心地带;其二,来自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一带的傈僳族,如盐边县箐河乡岩门村的蚩姓傈僳族人,这部分傈僳族人是十六世纪丽江傈僳族人不堪木姓土司的重压而迁徙到此地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傈僳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研究成果显示,这次傈僳族迁徙是一次大迁徙,大部分到了云南省怒江一带,部分到了今天的攀枝花境内;其三,来自永北(今天云南省永胜县、华坪县一带)的傈僳族人,如盐边县红果乡三滩村的傈僳族。这部分傈僳族应该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永北公母寨傈僳族人唐贵等发动的“驱逐汉族地主,夺回夷人土地”起义被镇压后,迁居而来的傈僳族。这次迁徙也是一次傈僳族大迁徙,大部分也去了怒江州一带。
(1)学校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双休日定为校本感恩互动节,为期两天。各个班级要求父母至少一人到校参加活动。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强化亲子互动,唱孝亲尊师等感恩歌曲,为父母洗脚,助推爱的流动,通过活动促进孩子的知恩报恩,融洽亲子关系,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
百灵山地区傈僳族的崇龙文化现象具有“祖源性”的特点。所谓“祖源性”,是指傈僳族今天的龙图腾崇拜,根源在于其祖先的龙图腾崇拜,这种继承祖先的图腾崇拜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民族经历的各种磨难而消失,而是顽强地在白灵山地区及周边地域内以各种方式留存下来了。
一、傈僳族祭祀经与龙图腾
在茶碗上加盖的创新设计,优化了单独碗、盏、杯的品饮功能。防尘保温之外;捏拿碗盖于碗中轻重刮拨,调节茶汤浓淡;饮茶时不揭盖,将其微调成半张半合之态,茶汤徐徐入口,碗内茶叶阻于盖沿处,同时盖径小于碗径,盖入碗内,品饮倾斜时也免于滑落;碗盖起落之间,茶汤若隐若现,相较无盖碗盏一览无余,更添属于国人的一份起承转合之韵律。
傈僳族先民在迁徙过程中,用口传的方式记录了本民族历史和文化。各种信息汇集,可以理出民族历史的脉络:傈僳族是炎黄子孙,是古羌的一支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是“龙”族后代。尽管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在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民族的根和魂一直没有改变。
二、傈僳族口传创世史诗与龙崇拜
(一)傈僳族口传创世史诗与的葫芦崇拜
傈僳族是一个没有文字或者说丢失了文字的民族(傈僳族创世史诗里描述傈僳族曾经拥有文字),其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全部靠口传,特别是阴传先生“呢扒”(傈僳语,又称“东巴先生”)口传的创世史诗和各种祭祀经,更是研究傈僳族族源、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源。因为没有文字,呢扒在背诵这些信息量巨大的创世史诗和各种祭祀经时要向祖先发誓,确保不增加或减少一个音,全部是按照祖先传下来的原版复制。当然,为了保持它的神性必须得蒙上神秘的色彩——所有内容都是祖先有灵,附着在呢扒身上通过呢扒来传递本民族的信息,这个过程在金沙江流域特别是百灵山地区称为阴传。阴传在百灵山区不仅仅只有呢扒,还有傈僳族医药。生活在百灵山南侧盐边县箐河乡岩门村的贺正德、蚩银清等是当地有影响的呢扒,攀枝花民族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团队在走访两位老人的时候,专门了解了他们口中傈僳族的创世史诗,两位老人的描述与我们在怒江等地收集到的傈僳族创世传说是一致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天上有了日与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江河,人类开始繁衍了。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有了发明创造,学会了很多生存的技巧,创造了语言和文字。后来,家庭牢固了,生活安定了,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外,还有了很多的剩余。生活富足了,人们就有了贪欲,出现了高低不平等,分配不均匀,出现了不公。人类的这种现象让天公、地袛心里很不痛快,为了惩罚人类,降下了上到天边,远达地角的滔天洪水。人类都要死光了,人种面临断绝,只剩下了兄妹二人,钻进葫芦里藏身避难,洪水退去后,葫芦降落在平地上。兄妹俩从葫芦里出来,看到的是遍地死尸,除了兄妹二人,看不到其他人的存在。为了不让人类灭绝,必须繁衍后代,于是,把梳子和手镯分成两半,兄妹各拿一半,哥哥往北,妹妹往南,分别去寻找人。当哥哥头发花白,妹妹眼角起了皱纹,兄妹会合在山谷中心,拿出梳子和手镯又合在了一起。哥哥对妹妹说,因为找不到人,只好兄妹婚配成亲。妹妹认为,能不能成亲,那要看天公地袛的意思。于是,妹妹在地上支起麻团做靶子,让哥哥用箭射麻团,如果箭射破麻团心,穿过麻团腰,那就说明婚配牢固,哥哥搭手一箭射出,正中麻团心穿麻团腰而过;妹妹又让哥哥箭射针眼,如果箭穿针眼,说明将来家庭稳定,哥哥射出一箭,射穿了针眼;妹妹认为兄妹婚配繁衍人类是大事,草率马虎不得,还需继续确认是否是天意,于是将一副磨盘的上一扇放在山头上,下一扇放在山下洗痳池边,如果两扇磨盘能合拢,说明是天公地袛的神意要兄妹俩婚配,结果磨盘滚动下上下两扇合上了。最后,兄妹俩在经过重重考验后婚配结合在了一起。成亲后,生下九男七女,开始了人类的繁衍。
很多少数民族创世史诗都有类似的描述:早年人类经历了洪水灾难,面临灭绝,葫芦救下一男一女而繁衍成了现在的人类。葫芦崇拜广泛存在于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之中,彝学家杨甫旺认为葫芦崇拜就是母体崇拜。
(二)傈僳族创世史诗中的兄妹就是汉籍传说中的伏羲女娲
关于伏羲氏、女娲与葫芦的联系,田秉锷《龙图腾——中华龙文化的源流》引闻一多教授《伏羲考》有这样的论述:伏羲,又作包羲,因古时候“包”同“匏”,“羲”同“瓠”,所以伏羲就是匏瓠,匏瓠就是葫芦的意思;女娲,又称女希、匏娲,同音转义为女伏羲、女匏瓠,意思就是女葫芦,也就是说伏羲、女娲是与葫芦同名同意的,“揭示了古已存在的‘葫芦图腾’。”[1]43如果说中华初民创造了龙图腾,而伏羲氏、女娲则是把中华民族塑造成“龙族”的始祖。《潜夫论·五德志》曰:“大人迹出龙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德木,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3]关于伏羲氏“以龙纪官”,《纲鉴易知录》综合了各个时期多个版本的文献资料,作了详细的归纳性表述,伏羲氏所封的各级官员中,封朱襄、昊英、大庭、浑沌、阴康、栗陆等为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分别负责造书契、造甲历、治屋庐、驱民害、治田里、导水源,又封春、夏、秋、冬、中五官分别为青龙氏(苍龙)、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可见伏羲帝崇龙、敬龙。而闻一多《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从人首蛇身神、二龙传说、图腾的演变、龙图腾的优势地位等对伏羲氏、女娲奠定的华夏“龙”图腾的“人文存在”作了定性的论述,故田秉锷称太昊伏羲氏为华夏第一龙。综上,伏羲、女娲本身就是葫芦,他们奠定了“龙”图腾的人文存在,所以葫芦图腾也是龙图腾,葫芦崇拜就是龙崇拜。
伏羲氏、女娲出现于各种典籍的记载中始于战国时期,而后多个文献典籍、著述等有了关于他们关系的记载或描述。《潜夫论·五德志》对伏羲氏和女娲有这样的记载:“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5]伏羲为三皇之一。《路史后记》二引《风俗通》:“女娲,伏西(羲)之妹。”也有说伏羲和女娲是夫妻的,如《钧天舞》“高皇迈道,端拱无为。化怀硬鬻,乒赋句骊。礼尊封禅,乐盛来仪。合位蜗后,同称伏羲。”这里以伏羲女娲比唐高宗武则天的夫妇关系[6]。卢仝《与马异结交诗》:“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7]可见伏羲和女娲为夫妻关系的说法是存在的。
闻一多教授关于伏羲氏与女娲的关系问题可以归纳为:伏羲和女蜗是以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8]。在论述他们关系是,闻一多引用了芮逸夫研究成果,列举了二十余则多个地域、多个民族关于洪水来了,只有兄妹二人得救,兄妹结为夫妻,遂为人类始祖的民间故事或传说,得出了“故事中的兄妹即汉籍中的伏羲女娲”的结论[9]。傈僳族的口传创世史诗,记录了葫芦救兄妹于洪水,兄妹结合而繁衍人类的血缘婚的历史存在,这与闻一多关于伏羲氏与女娲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同样地,傈僳族创世史诗中的兄妹,就是汉籍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
(三)葫芦崇拜就是龙崇拜
根据闻一多先生《伏羲考》的著述,伏羲氏和女娲都是葫芦的意思。而葫芦崇拜,就是龙崇拜。
兄妹结合为夫妻的血缘婚,可以追溯到太昊伏羲氏和女娲的关系问题。
傈僳族是氐羌的一支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形成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傈僳族祭祀经《祭葫芦神》详细叙述了傈僳族迁徙及形成的过程:傈僳族先民来自辉煌的古羌王朝,那时有坚固的城池,有金科玉律,后来长年的纷争和战争的消耗,使得古羌王朝崩塌了。为了保住自己的根,九个族长商量决定由西向南迁徙,并留下了以后认祖归宗的联络暗号。在南迁过程中,又遇到能征善战的戈几人的阻击,死伤了不少人。为躲避阻击和追兵,他们顺着雅砻江、岷江,沿着崎岖的高山岩路,一路迁徙,到了今天的雅安一带,终于安定下来,过了一段和平安定的生活。在《祭葫芦神》中,有这样的描述:“氐羌留雅安,氐羌出傈僳。”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雅安定居的日子里,氐羌的一支就演化成了古傈僳族人。后来,雅安一带人增多了,古傈僳族人安定的生活受到冲击,于是不得不再次迁徙。这次迁徙时从雅安出发,分为三部,一部到了怒江,一部到了澜沧江,一部到了金沙江,今天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大部分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傈僳族祭祀经所述与龙图腾的关系可以从闻一多教授的理论中理出。
三、白灵山地区及周边傈僳族龙文化现象调查研究
龙图腾文化不仅存在于傈僳族民族的口传历史之中,在多元文化的今天,白灵山地区及其周边的傈僳族人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原始的龙崇拜文化习俗。民间吹葫芦笙、跳葫芦笙舞、祭龙等遗风,正是傈僳族人生活中龙图腾崇拜的文化表现。
(一)吹葫芦笙、跳葫芦笙舞的本质是龙崇拜
傈僳族的葫芦崇拜早已融入了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傈僳族人擅长吹葫芦笙,跳葫芦笙舞。
奥斯本检核表法由美国著名创造工程学家创新技法之父A·F奥斯本提出,是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需要创造发明的对象,以提问表格的形式,列出9个方面的有关问题,即如能否他用、能否借用、能否改变、能否扩大、能否缩小、能否代用、能否调整、能否颠倒、能否组合,然后逐一进行审核讨论,以促进创新活动深入进行的一种创新技法。运用该创新技法的核心是检核思考。在检核思考时,可将每一条检核项目视为单独一种技法使用,也可结合其他检核项目或者其他创新技法共同使用,并按照创造性思考方式进行深度思考,还需对各种设想进行可行性检验和综合评价,尽可能检核思考出有价值可操作的创造性设想。
各种各样,密集分布在白灵山地区及周边地域的“龙迹”,是傈僳族人寄情山水,表达愿望的精神创造。感恩龙、崇拜龙,就是敬畏祖先和神灵、感恩自然、祈求和谐与美好的精神寄托,是傈僳族民族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灵山一带关于葫芦笙的来历的传说更像一部傈僳族迁徙的史诗:很久以前,有五弟兄分别去寻找能安身立命的理想场所。深知再聚不易的五弟兄,制作了能代表他们共同情感的乐器——葫芦笙,以便以后在吹起葫芦笙,就能想到家人及远方的兄弟。笙斗为一天然葫芦,葫芦底部开有五孔,葫芦体上装五根笙苗(赤竹制成),每根笙苗上有一黄竹片制成的簧片。葫芦代表母亲,五根笙苗代表一母所生的五弟兄,笙苗长短各不相同,最长的代表老大,其余的按照长短分别代表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五根笙苗中,最高苗(大哥)不开窗子,其余四根苗全开窗。最高苗为主音管,其余四根苗为副管。在主音管的上方,有一小葫芦,用作扩音,小葫芦挖掉部分,剩余部分镂空刻成人的笑脸。每根笙苗发出不同的声音,葫芦笙斗的五孔与任一笙苗形成不同的音组合,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对话。笙苗之间相互配合也可发出和谐的和声,表达兄弟之间和睦。后来,五个兄弟分别到了米易、德昌、盐源、盐边、华坪,并在那里繁衍生息。
在傈僳族的创世传说中,从葫芦里走出来的俩兄妹婚配后繁衍的后代分别是汉族、傈僳族等兄弟民族。葫芦笙起源传说中分别去了不同地方一母所生的兄弟,与创世传说中俩兄妹婚配繁衍的后代是兄弟民族的描述,是同质事件的不同表述。葫芦笙是傈僳族创世传说的物化表现,而创世传说是葫芦笙起源传说的根和源,葫芦笙与葫芦笙舞承载的是傈僳族的母体崇拜,表现为葫芦崇拜,其本质就是龙崇拜。
(二)祭龙习俗
在傈僳族的多个祭祀经中均重复传递出一个信息:傈僳族人的祖先就是古羌人,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对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动物等的原始自然崇拜。白灵山地区傈僳族人每月初一、十五要烧豆瓣香(当地称谓,就是本地的树香)祭祖先,过年时,树香要从大年三十烧到正月初七。这个只信祖先不信神的民族,却把祭祀白龙神和祭祀药王菩萨作为重大的民俗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要祭祀白龙神、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要祭祀药王菩萨,生活在盐边县箐河乡丁家弯、刘家沟一带的傈僳族人还要在每年十月再祭祀高山白龙神。
白灵山地区及周边傈僳族对龙的崇拜同时还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拜中,在他们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地域中,处处有“龙迹”,以龙命名的地名随处可见。位于百灵山南侧的民胜村,是典型的傈僳族村,在本村三组有一山势形似头朝下、身体盘旋正在喝水的龙,故地名为转龙,这条沟为转龙沟。盐边县箐河乡六村名岩龙村,因岔河有一岩子上有一石头形似龙而得名,岔河石龙,已被雷击断裂了,部分掉在了河里。盐边县鱼门镇有一傈僳族村民小组,名龙洞弯组,组里半山腰有一长年流出泉水的山洞,当地傈僳族人称其为龙洞,龙洞流出的泉水保障着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之所以称其为龙洞,含有感恩的意思。在白灵山及其周边地域内,有多处龙洞、龙泉、龙潭等以龙命名的洞穴或水源。白灵山系有一东西走向的山脉名龙头山,龙头山地跨盐边县红宝、共和、鱤鱼等乡镇,从白灵山延伸到雅砻江边,是傈僳族人世代挖药、采野生蜂蜜和其他山珍的天然场所。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所在地为龙舟山,而龙舟山是近现代的称谓,以前的文献资料记载为龙肘山,龙舟山在白马镇半山腰有一长年流水的天然溶洞名龙潭龙洞(前些年改名为颛顼龙洞)。在白灵山地区及其周边还有多处以龙命名的“龙山”。此外,还有如仁和区布德镇的回龙湾、云南丽江地区华坪县的石龙坝等等,都显示出傈僳族人曾经生活过地方或迁徙走廊上的各种“龙迹”。
(三)无处不在的“龙迹”
在傈僳族民族记忆的深处,祖先创造了龙图腾,以龙为民族的精神,祭祀祖先也是祭龙。药王菩萨,即神龙氏,也就是炎帝,炎帝是真龙,祭药王菩萨就是祭龙。祭祀祖先、白龙神和药王菩萨是傈僳族人祈求祖先保佑、祈求和感谢神灵佑护的精神创造,是傈僳族人龙崇拜的仪式体现。
傈僳族人能歌善舞,舞蹈更是他们表达喜悦情绪的重要方式,在婚礼进行中、丰收日子里、喜庆场合下、农闲聚会时,傈僳族人必跳舞,跳舞必有伴奏乐器——葫芦笙。今天,在白灵山地区及其周边仍有吹奏葫芦笙的好手。白灵山南麓盐边县箐河乡丁家湾社的贺国友、丁国文、贺国祥等就是傈僳族葫芦笙的代表性传承人,是当地傈僳族民间跳葫芦笙舞的重要伴奏者。在周边,盐边县红果乡的三滩傈僳族村、盐边县鱤鱼乡的东风村等民间均有葫芦笙演奏技艺的传承人,东风村还发现了葫芦笙六重奏的传承。
四、结语
闻一多教授《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中《龙图腾的优势地位》详细评述了华夏文化的源头就是龙文化:“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起初都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也许因受东方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的压迫,一部分向北迁徒的,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移的。”“我们的文化究以龙图腾团族(下简称龙族)的诸夏为基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3]黄帝和炎帝是华夏部落联盟领袖,同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夏民族就是龙族。《祭葫芦神》:“你是阿考总,你是阿近美”,阿考总、阿近美是傈僳族语,意思是“你是炎黄子孙”[4]。同时,《祭葫芦神》很明确地表述了今天的傈僳族是古羌的一支演化而来,大禹为古羌人,《史记》:“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大禹为龙族后代,故古羌的图腾无可争议地是“龙”。傈僳族源自古羌人,是炎黄子孙,由此可见,傈僳族的龙崇拜源于祖先的龙崇拜,龙图腾是傈僳族人固有的图腾文化。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及傈僳族的龙图腾崇拜,其目的在于要建立本土民族文化自信,为政府制定相关文化自信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为百灵山地区傈僳族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文化依据。文化自信的建立,其前提是必须要有文化,没有民族文化,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所以要调查、研究,通过细致的工作,理清民族文化的根源和现实的存况。众所周知,傈僳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尽管今天有一些傈僳族学者在编写傈僳族通用文字,但现阶段还并没有完全普及使用。一些有价值的傈僳族文化基本掌握在“呢扒”(东巴先生)的记忆中,这些文化信息,在以前闭塞的环境中,一代代口口相传,保持初态。而如今,这些文化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如果不及时记录,很有可能会在现代强大的外来文化交融中走样或丢失。比如傈僳族的祭祀活动或祭祀经、创世传说等,往往饱含丰富的民族信息和强大民族密码,如果丢失,那就丢掉了民族的“根”和“魂”,忘记了历史,丢掉了文化,何来的民族文化自信呢?
阿强将信将疑,他打开防盗门,在门外找信封。这时,正好有人牵了一条大狼狗上楼,那狗见到阿强家门开着,突然窜了进去,那个牵狗的男人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同志,你进去把狗赶出来吧。”
而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正好能补救这一弊端。《药》这篇小说可以采用比较文学的很多种方法进行解读。限于篇幅,我这里仅从影响研究的层面,谈几点教学思路。
对白灵山地区傈僳族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相关各部门都相当重视,成果也很丰富,抢救、传承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基于某一个文化现象进行单一的,简单的项目传承的问题,对于项目本身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缺乏认识,往往是为了传承而传承,脱离民族背景地传承,结果是花了大力气,努了足够的力,收效甚微甚至事与愿违。
就目前的阴道分娩接产情况来看,采用的常规方法,接产人员利用手掌向上的推力,尽量的在产妇分娩过程中胎儿在阴道下降的过程中进行适度的托举,使得胎儿能够缓慢的下降,尽量的减弱胎儿对会阴的冲击力度,来减弱胎儿对产妇会阴造成的损伤[5]。采用常规的保护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的上减弱分娩时对会阴的损伤,但是在进行操作时,接产人员的手掌的力量和胎儿下降的合力会给会阴带来很大的的压力,容易在接产时造成会阴的水肿和充血[6]。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会阴的表面会变得更加脆弱,损伤程度可能会加重[7]。因此为了寻找一种更加适合的会阴保护方法,我院对一年来在我院阴道分娩的产妇进行了本次的研究。
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关键是挖掘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这就要透过一些文化现象研究其文化本质、理清其文化根源,才能抓住有价值的民族文化,才谈得上文化的融合,才能把外来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相关部门应与相关的语言学专家、热爱本土傈僳族文化的学者、本土立志让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为民族发展服务的傈僳族兄弟姐妹等一起,从傈僳族“呢扒”口传历史入手,抢救记录、深入研究本土傈僳族历史及文化。
在此,也呼吁广大专家学者在研究藏彝羌文化走廊有关历史文化时,应给予傈僳族文化足够的重视,以保证民族迁徙走廊上文化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参考文献
[1]田秉锷.龙图腾——中华龙文化的源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吉成名.查海龙纹陶体和龙形堆塑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3).
[3]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张自强,杨宗译.傈僳族祭祀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5]郭超.四库全书精华·子部:卷2[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19.
[6]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9:100.
[7]孟二冬.韩孟诗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620.
[8]陈均.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闻一多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190.
[9]闻一多.神话与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History Passed down by Word of Mouth and Totem Worship ——A Case Study on Lisu People’s Worship of Dragon Totem in Bailing Mountain Area of
Panzhihua LI Shengjun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Sichua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relies on the existence of cultures. The ab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s results in the abse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fore, meticulou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are required in sorting out the origins and practical situations of ethnic cultures. Lisu ethnic group is a branch of the Diqiang nationalit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migration, owing to the absence of written language, historical culture of Lisu people was passed down by word of mouth.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oral stories and sacrificial scriptures of Lisu people, ancestor worship and gourd worship can be found and interpreted explicitly, practically worships of ancestors and gourd are equivalent to the worship of dragon totem. In Bailing Mountain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Lisu’s gourd and Sheng culture, dragon sacrifice custom, and the ubiquitous “dragon trac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Lisu people’s ethnic characteristic and spiritual creation of dragon totem worship.
Keywords :Bailing Mountain; Lisu ethnic group; history passed down by word of mouth; gourd worship; dragon totem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63( 2019) 03-0008-06
DOI: 10. 13773/ j. cnki. 51-1637/ z. 2019. 03. 002
收稿日期: 2019-03-02
基金项目: 本文为攀枝花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市级课题“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攀枝花百灵山地区傈僳族崇龙文化研究”(201801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生军(1969—),男,四川遂宁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