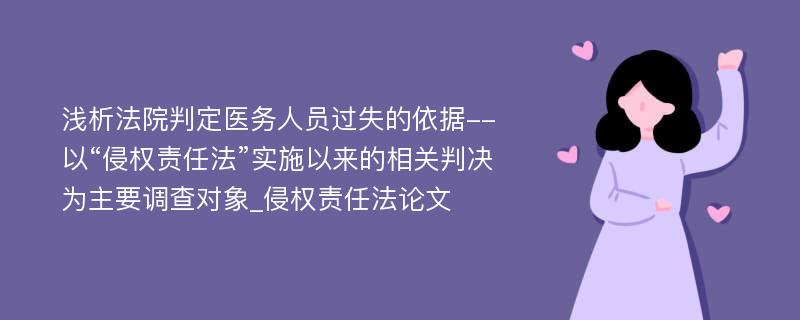
法院对医务人员过失判断依据之辨析——以《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相关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务人员论文,过失论文,判决论文,法院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2.16 一、问题的提出 综观《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的判决,在判断医务人员过失的具体依据方面,法院一般会适用第55条的“说明义务”、第57条的“当时医疗水平”、第58条第1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第58条第2、3项的“病历资料相关瑕疵”。在适用第54条一般规定时,“医疗常规”也常常见诸相关判决之中。除此之外,医疗纠纷案件的专业性也使得法官会倚重于医疗鉴定意见,特别是鉴定意见中的过失鉴定。 在这些依据中,需要辨析的是医疗水平、医疗常规、鉴定意见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因为实践中对它们的适用多有偏差,往往使得过失在实践中的结果与理论中的预设相左。而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实践中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忽视或者误解,比如过失判断标准是否有一致的具体内容可循,违反规范是否必然属过失,过失判断是价值性抑或事实性等等。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依据进行辨析,考察它们能否承担判断医务人员过失的任务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此确定它们的真正作用并准确适用。 目前,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纯理论的讨论或国外案例的介绍,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缺乏关注,因此所做出的研究成果难以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已近5年之久,法院在判断医务人员过失方面已积累了很多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只有加强此类研究,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这些考虑,本文主要考察《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的相关司法判决,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此类问题的可行性建议。 二、判断依据(1):医疗水平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了一个具体的判断依据,即医疗水平。如果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属过失。适用该依据能否准确判断医务人员的过失?这需要通过对其具体内容的考察方能确定。由于条文中“当时的医疗水平”这一表述较为抽象,也没有进一步的具体界定,因此需要在适用第57条的相关案件判决中考察其内容。在可参考的判例中,笔者择其典型予以解析。 (一)医疗水平的确定与当事医方的客观情况 “宗某与某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法院认为,判断未确诊右侧耻骨上支骨折的行为是否属医疗过失,应与医疗机构的级别及其他条件相联系。被告属乡镇医院,受医疗条件、资质等限制,无法据患者骨盆DR摄片(数字式X线摄片)发现右侧耻骨上支异常。且被告已嘱原告转诊上级医院,原告于当天转市某医院就诊,并未延误。因此,被告已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2)溧民初字第3077号民事判决)。 “王某等与郑州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被告对原告母亲施行了腰椎后路切开复位椎管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病人被诊断出双侧股神经损伤,系手术中造成的。后患者无法恢复,遂自杀。法院认为,作为医务人员,有义务具备同一或相似地区在相同条件下从业医务人员所应具有的学识和技术,有义务保持同一或相似地区在相同条件下从业医务人员在相同病例中的注意使用相应技术,有义务在实施技术或应用学识时保持合理的智慧并做出最佳判断。被告作为三级综合医院,应具备同一地区的医疗水准,但在手术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致患者损伤。同时对原告实施的手术也并非最先进的,而是最传统的。尽管最传统的手术方式并未被废止,但在降低手术风险、治愈病患方面最先进的手术方式更有效果。因此被告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1)管民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 上述案件说明了医疗水平的确定与当事医方的客观情况有关。第一个案件的被告是乡镇卫生院,法院对医疗水平的判断以乡镇医院这一级别为基准,由于这类医院限于设备、条件等因素都无法诊治出该案的病情,因此认定已经超出当时医疗水平而判定被告不具有过失。第二个案件的被告是三级综合医院,法院判断时的参照对象也就锁定在该地区三级综合类医院这一级别,认为这类医院具备实施病患手术的相应设备和医务人员,可以完成上述手术,然而该案的医务人员却造成患者双侧股神经损伤的损害后果。因此,法院认定未达到当时医疗水平而判断被告具有过失。 从上述判决可以看出,法院在适用医疗水平时对当事医方的情况进行了考量。根据当事医方所具有的级别、资质、所属地区等客观因素,把同一地区、同等级别的医院、同类资质的医务人员作为参照对象,将其视为医疗水平的代表。当事医方的诊疗结果达到或者优于该参照对象所达到的结果,方能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如果当事医方在诊疗活动中产生了损害,而作为参照的同类医务人员却能够避免类似损害的发生,那么即存在过失。① 需指出的是,医方所具有的级别、资质等情况指的是“医疗水平”层面的情况,而非“医学水平”层面的情况。在不少判决中,法院适用第57条时没有使用法条中的“医疗水平”,而是使用了“医学水平”,这显然是混淆了两者的差别②:后者是指医学学科在学术研究上的理论水平,其诊疗方法仅处于试验阶段,没有经过确定性的验证,在临床中并没有达成共识。而前者则是指在医学水平之下、临床实践中所达到的水平,其诊疗方法被一般的同科医生所认识,在临床医学界经过广泛运用而获得共识,具有临床适用的可能性。对于两者的差别,我国司法判决尚无实例对此作出明确区分性说明。③不过,上海市高级法院《医疗过失赔偿纠纷案件办案指南》在第3条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判断时依据的是具体医疗行为发生时“临床医学实践中的医疗水准”,而非医学水平。④ 另外,还需考虑新型诊疗方法的问题。如果与当事医方处于同等区域、具有相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掌握了某种新型诊疗方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稳定的适用性,使得病患足以期待当事医方具有该新型疗法的知识,那么,无论该诊疗方法实际上在当事医方是否固定地施行,该诊疗方法即被视为属于当时医疗水平的范围之内。在上述第二个案件中,被告医院和医生对实施先进手术可能并无足够的经验,但是这不妨碍医疗水平的确立。正如审判法院所言,他们“有义务具备同一地区或相似地区在相同条件下从业的医务人员所应具有的学识和技术”,并针对病患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的诊疗方法。在该案中,最先进的手术方法更适合病患的利益,而当事医方却选择了最传统的方法,因此未能达到医疗水平。 (二)医疗水平的确定与诊疗当时的具体情况 “杨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原告之子在被告医院洗胃时死亡。法院认为在对患儿洗胃时,应尽到较成年人更高的诊疗注意义务,对患儿采取左侧卧位,尽量避免患儿误吸液体,防止急性肺水肿或窒息。但被告未采取左侧卧位,而将其平卧,头向右侧,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⑤ “邹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医生认为患者语塞、声嘶症状是脑梗死所致并据此治疗。后患者语塞好转,但声嘶未缓解,导致病情延误。法院认为,虽脑梗死伴有声嘶,但喉癌的症状也是声嘶。尽管“一元论”和“多考虑常见病”等原则可解释患者症状,但考虑患者是老年人,往往多病因并存,医生诊断时应先排除预后不良的疾病和对机体有显著影响并可致死致残的疾病,如恶性肿瘤。根据临床表现确定可疑诊断后,再用排除法作鉴别诊断。据此可认定医生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⑥ “王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原告之子受伤至被告医院就诊,医生未对伤口分析而简单认为是普通摔伤,未做出正确诊断,致患儿因狂犬病发作而死。法院认为医生应对伤口作分析,即患儿摔倒时,头顶枕部不可能四点同时着地造成四处头皮裂伤;若是摔伤,头皮应是擦伤或因皮下淤血起包;根据患儿体重、身高及行走速度,若是摔倒,不可能产生如此大撞击力以至于头皮四处裂伤。同时,若是摔倒,颅骨及颅内必有损伤,但头颅无畸形且颅内未见出血征象。结合患者家属所述的“被狗追”情节,患儿外伤应是狗致伤,而非摔伤。医生未基于常识作分析,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因此,被告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而存在过错。⑦ “陆某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法院认为,血管腔内介入手术需盲视下在股动脉处穿刺,可致术后进行性渗血,造成假性动脉瘤而再次手术,所以该手术需与患者谈话,详细、明确地告知风险及术后预防措施。然而该案医师虽对患者及家属作了谈话,但其内容过于格式化,解释不够详尽,使他们对并发症的发生只存于概念性理解,对并发症的演进过程无从认知,以致患者在术后发生渗血形成假性动脉瘤的过程中医患交流与衔接不足,造成并发症且未能及时控制,因此被告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而存在过错。⑧ 此类判决说明了医疗水平的确定与诊疗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在第一个案件中,患者是幼儿,针对患儿的特别情况,同类医生会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采取区别于成年人而符合儿童生理结构的洗胃术。在第二个案件中,患者是有多病体质的老年人,医生一般都会考虑其特殊情况,通过仔细排除各种可能,鉴别出真正的病因,而不会以“一元论”和“多考虑常见病”等原则性方法进行简单判断。第三个案件针对病症的具体情况,依据医生的基本常识,都会根据伤口的情况分析出具体病因,并采取适当的诊治措施,而不会不加甄别地简单处理。第四个案件针对诊疗手段的特殊性,凡实施该手术的医生都应当根据手术的特点详尽地解释说明风险,而不应格式化地交谈。在这四个案件中,被告医务人员都忽视了个案的具体情况,没有审慎地进行具体诊断,采取了不符合具体情况的通用方法,而作为参照对象的与当事医方同等级别和资质的医务人员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审慎地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准确判断,从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当事医方具有过失。 从此类判决可以看出,医疗水平的确定还需要考虑诊疗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病患的体质、病情的特征、诊疗手段的特殊性等。在确定了与当事医方具有相当性的比较对象之后,应当注意,作为参照对象的同类医方所尽到的注意义务在内容上并非完全一致,且没有统一的模式可遵循,而是应依据诊疗当时的具体情况,以最符合病患利益为原则,合理谨慎地作出诊断和治疗。那么,当事医方也应当与其比较对象一样,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反应,唯需遵守的是勤谨地尽到注意义务。 不过,在实践中,很多判决往往忽视了以个案的具体性去确定医疗水平而是以具有一般适用性的医疗常规来确定医疗水平。对此,我们可以看一则案例: “吴某与某医院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吴某之子因发热、抽搐、意识障碍等症状到被告医院就诊,但被告未查明病因,最终病情恶化而死亡。死因鉴定为结核性脑膜炎、支气管肺炎伴左心衰竭。法院认为,原告吴某仅以患儿脑脊液检查的两项结果即“葡萄糖和氯化物下降”为依据,就认为可确诊结核性脑膜炎,依据不足,因为根据医学教材《儿科学(第7版)》,结核性脑膜炎“最可靠的诊断依据是脑脊液中查见结核杆菌”,脑脊液结核菌培养“是诊断结脑可靠的依据”,而在被告对患儿所做的脑脊液检查中未找到该细菌。因此被告未作出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符合当时医疗水平,依据第57条的规定并不存在医疗过错。⑨ 在该案中,法院所依据的《儿科学》是讲授在儿童疾病临床中已形成惯例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通用著作,它描述的是对儿童病症的通常表现形式及其一般性的治疗方法,大多数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都会对其进行参考,属于医疗常规。其中,该书所指出的“脑脊液中查见结核杆菌是最可靠的诊断依据”,仅仅是叙述了一般的、常见的情况。这里“最可靠的诊断依据”并没有排除所有的诊断依据,在具体个案中完全可能存在特殊的情况,即依据其他因素也有可能诊断结核性脑膜炎。虽然不能如原告所主张的仅以患儿脑脊液检查的两项结果即“葡萄糖和氯化物下降”为依据就予以确诊,但在排除该病情的存在方面,也应当全部排查完所有可能的情况之后,方能确定该病人未患有结核性脑膜炎。该案被告仅以对患者做了脑脊液检查未找到该细菌为由断定不存在上述病情,显然只考虑了一般情况,并没有尽到审慎地全面分析个案病情的注意义务,而对病情进行审慎分析的注意义务是同类医生能够尽到的。 该案法院在判定是否符合医疗水平时依据的是作为医疗常规的医学教材,认为医学教材中记载的通常诊断方法就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显然,这里并没有将医疗水平与医疗常规区分开来。关于两者的关系,我国法学理论上鲜有辨析,而在涉及两者的判决中,也鲜见明确的阐释。对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相关判例。 原告7岁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在做腰椎穿刺及麻醉后开始手术,医师要求每5分钟做一次血压测量。手术中,原告休克,被告终止手术进行急救。后虽抢救成功,但原告无法恢复意识成为植物人。被告在诉讼中抗辩称,根据当时的惯例,血压为每5分钟测量一次。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被告不负过失责任。但最高法院否认了被告的抗辩,废弃了原审判决,认为医疗水平是医生注意义务的标准,应根据病情具体判断,与医生从事的医疗常规未必一致。医生依据医疗常规记载的一般情况和方法所进行的医疗行为,不能都认为业已尽到医疗水平的注意义务。⑩ 在该案中,日本最高法院明确区分了医疗水平与医疗常规。对于医疗水平的判断强调其具体性,即医生要根据具体病情尽到勤谨注意义务,而没有僵化的、刻板的标准。法官应当参酌个案的背景,合理决定医生应负的诊疗义务水平。而医疗常规是关于一般情况下医生做出常规反映的标准,具有一般性、普适性,它不能针对特殊情况做出具体指导。因此,根据医疗常规无须进行某种诊疗方法或检查,但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情形认为医生应当实施该项治疗方法或检查义务,那么当医生违反此项义务时,就属于不符合医疗水平的要求。 从前述吴某的判决来看,在适用第57条时,将“医疗水平”等同于“医疗常规中确定的水平”。其混淆的原因大多源于对“通常”的理解。虽然医疗水平和医疗常规都有对“通常”的强调,但是因所指对象不同,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前者所说的通常是“医生通常应尽到的注意义务”,比如前述王某等诉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同等级别的医生通常都会仔细分析病情,审慎地做出相应地诊疗。而后者的通常则是“对病情通常情况的描述以及通常情况的诊疗措施”,比如前述吴某与某医院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儿科学》对结核性脑膜炎一般症状通常诊断的说明,但并没有完全列举所有情况下可能的情况。 总之,确定医疗水平必须要考察个案的具体性。对医疗水平的判断不能按统一内容的标准后,单纯地判断医生是否违背此标准,而应当依据具体情况进行个案分析。由此,对于医疗水平的认定就表现出动态化特征。虽然这种动态化的判断方法因没有统一标准而具有非确定性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有碍于法律的安定,但是在无法具体、明确的情况中,法律规则保持一定的弹性,符合过失案件的动态性特质,也利于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 (三)“当时的医疗水平”即理性人标准的具体适用 综合上述两类判决来看,“当时的医疗水平”作为我国法院评判当事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的依据,对其确定既与被评判者的级别、资质等情况有关,又与诊疗病患时所针对的病情等具体情况有关,总之是通过与当事医方同类的医务人员在处理相同或类似个案时的行为进行比较,去确定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当时的合理期待,以促使其尽同类医务人员通常所尽的注意义务。 从判断方式来看,实践中所适用的“医疗水平”与理论中的理性人标准是一致的。所谓“理性人”,是法律涤除了不同人在智力、性格等方面的差别而拟制出来的具有一般见识和能力的普通人。在专业领域,该拟制人具体化为本职业中合格且具有合理谨慎的从业人员。他们无需展示过于高超的专业技巧,只需尽其所属群体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即可[1]。如果行为人的职业行为导致了损害,而与该行为人从事相同职业的人依据共同具有的技术和知识在类同的情况下却可以避免损害的发生,那么该行为人即具有过失。由此可以看出,理性人标准也是通过确定与当事人相当的参照对象,看其在同样情况下的具体反应,从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的。因此,医疗水平依据在判断方式上与理性人标准是吻合的。 除此之外,实践中医疗水平的确定并非如同医疗常规那样是对某种医疗事实的纯粹描述,而是在个案中,法官设定一个参照对象,该参照对象的拟制既从医方的自身情况出发,又对病患的具体病情及其合理期待观察,通过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确定医方应尽的注意义务。这样一来,既不会苛求医方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也不会使患方因医方怠于对病情的谨慎注意而受损害。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水平”代表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因此,该依据一方面具有法律的价值判断性质,法官可以据此对医方的行为做出是否符合法律价值的判断;另一方面又具有法律的价值引导性质,通过该标准的适用可以引导医方遵从法律的价值取向。理性人标准的属性也是如此,即以拟制的理性人确定法律的价值评判准则并以此引导当事人的行为。因此,从本质属性上来看,两者也是一致的。 综上比对来看,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医疗水平依据是理性人标准在医疗案件中的具体适用。对此,我国学者也主张将“当时的医疗水平”视为合理的专家标准或者合理医师标准[2]。由于理性人标准在理论上视为判断过失的有力工具甚至是通说标准[3],因此医疗水平依据在正确适用的前提下也当然能够对医务人员的过失做出准确判断。该依据的适用对于法官在法律上裁判涉及医学方面的案件有重大意义,即通过设定具有法律价值的参照对象,将当事医方与之比较,确定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从而判定是否存在过失,这样使得法官可以利用自身熟知的法律知识进行裁决,避免法官在医疗案件审理中因不懂专业而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 三、判断依据(2):医疗常规 在《侵权责任法》的条文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医疗常规”,但如前所述,有些法院在适用第57条时会以医疗常规来确定医疗水平,间接影响过失的判断。除此之外,在单独适用第54条一般规定时,法院常常会直接依据医疗常规来判断医务人员的过失。不仅如此,在案件的审理中,病人常常以诊疗活动不合常规为由主张权利,而被告也常常以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进行抗辩。在鉴定机构的鉴定中,是否符合医疗常规也是必备的考察对象。于是,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案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诊疗活动是否符合医疗常规。(11)在此,本文针对直接适用医疗常规的判决,对医疗常规能否准确判断医务人员的过失再作辨析。 医疗常规是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形成的通用惯例,为医务人员的广泛参考。它通常表现为对病症一般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描述。如前述“吴某与某医院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儿科学》一书在实践中为众多医务人员参考,其中对儿童病症诊断的著述即可构成医疗常规。依据医疗常规来判断医务人员的过失,主要是通过将医务人员的行为与医疗常规进行比较,如果当事医方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那么即为无过失,否则即属过失。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将专业领域的理性人标准替换为医疗常规中的通常规定,即依照通常的情况诊断病情,依照一般的方法来治疗病患。这里的问题是,两者可否进行替换? 对此,我们先看两则案例: “王某等诉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患者因酒后头晕、恶心分别于4点、14点至被告医院就诊,均未诊断出原因,仅做简单处理。对病人的疼痛并未重视,仅以年纪轻、疼痛是正常为由予以忽视。该患者于20点因重度甲醇中毒死亡。在法院采纳的鉴定意见中指出,医方处理符合医疗常规,目前医院的常规检验项目无法检出甲醇中毒。在没有诊断出甲醇中毒致死问题上,法院以符合医疗常规为由没有确认被告存在过错。(12) 依据医疗常规,以一般的检验项目无法检查出甲醇中毒。但是,在现今的医疗条件下,对甲醇中毒的检验并非难事,可以通过相关症状以及特别项目的检验确诊。在该案中,仅以医疗常规判定医方不存在过失并不妥当。因为尽管依据常规无法检出甲醇中毒,但是当患者两次因同一原因就诊时,理性医生通常就不会简单地以常规检验进行检查,而是会根据患者喝酒以及是否可能喝到假酒等情形进一步问诊并进行特别检查。即使该医院没有相关设备无法检测,从第一次就诊至死亡的16个小时里,完全可以进行转诊,但是从诊疗过程来看,当事医方没有做出这些行为,因此当属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而存在过失。 “毛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周某高处坠落致瘫,被送往被告医院。医生实施颈椎体骨折次全切除减压、钛网植骨、前路钢板内固定术。术后患者出现呼吸不畅、意识障碍,于是医生再行右侧侧脑室钻孔引流术。术后患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后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鉴定意见认为诊疗常规中未规定对颈椎手术需进行预防性抗凝治疗,因此对患者术后不使用抗凝剂并无过错。法院采纳了鉴定意见。(13) 在该案中,尽管医疗常规未规定对颈椎手术需进行抗凝治疗,但是并不能因此确定对患者不用抗凝剂并无过失。因为是否需用抗凝剂,理性医务人员会根据患者手术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审慎地予以判断。如果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需要使用,且这样能够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害,那么就会使用。医疗常规仅仅规定了一般情况下无需使用抗凝治疗,而无法预见各种特殊的情况。因此,该案中仅以医疗常规未规定为由判定被告无过失并不妥当。 上述案例都显示出了依据医疗常规来判定过失的欠妥当性。在这些情况中,将理性人标准中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尽的义务替换为医疗常规中的规定,对病患严重不利。当然,诊疗行为是一项复杂的专业性活动,医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职业经验对病症及其诊疗方法进行裁量。基于这种裁量选择了医疗方法中通常的一种后导致医疗结果不理想的,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然而,医务人员裁量权的行使不应是不受约束的,即使选择了通用的诊疗方法或者通常的注意事项并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具体病情不能适用该通常方法时,或者具体个案要求应特别注意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裁量及选择通常方式时就应当审慎,否则会违背医务人员应有的注意义务。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有情况来看,大多倾向于只要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即判定不存在过失。不过,在少数的判决中,还是有些法院注意到了医疗常规的局限性,并未因医务人员的行为与医疗常规相符而判定其不存在过失,比如: “张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丁某入被告医院治疗,在诊疗中左大脑严重脑梗,最终死亡。被告辩称,其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医疗过错。法院认为,被告在对丁某行主动脉瓣置换术后,按常规进行了华法林抗凝治疗,用法用量都符合要求,并严格进行了抗凝监测。尽管按常规对死者的诊疗无明显过错,但存在对死者特殊体质及个体差异并未尽到谨慎注意及预防义务的过错,调整抗凝用药过于保守以致脑梗塞。因此,被告存在过错。(14) 在该案中,法院强调了对死者特殊体质及个体差异的谨慎注意及预防义务,这是理性医务人员所能达到的程度,而当事医方却没有达到,尽管其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但仍判定其具有过失。这实际上是以理性医务人员标准否定了以医疗常规对过失的判定。 除此之外,在前述“邹某等诉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当事医方所遵循的“一元论”和“多考虑常见病”等原则也是医疗常规,但法院指出应当考虑患者是老年人,往往是多种病因和疾病并存,医生在诊断时要首先排除预后不良和对机体有显著影响并可致死、致残的疾病,如恶性肿瘤。根据临床表现确定可疑诊断后,再用排除法作鉴别诊断。这同样也是以理性医务人员标准排除医疗常规判定过失的做法。 在国外的判例中,对于医疗常规判定过失的局限性以及不能替代理性人标准也有明确的认识。除了前述日本判例之外,我们还可以看一则美国的案例: “Helling诉Carey案”。原告24岁时由被告做了眼睛检查,7年后再检查时发现患青光眼。经查原告患病已10年,但无明显症状。原告主张被告因当年未查出而具有过失。被告则抗辩,40岁以下的人青光眼的患病率低于25万分之一,因此眼科医疗常规确立青光眼检查只对40岁以上的人进行。那么,未对原告做检查符合医疗常规而无过错。原审法院判定原告败诉。但上诉法院却认为,医疗常规不足以作为医生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应根据具体情况酌定。对于40岁以下病人做青光眼检查,即使患病率极低,与眼科医生职业惯例不和,但法院仍有义务宣示该检查属医生义务,应列为例行检查项目,使所有人享受同等保护,以避免低年龄者遭受青光眼损害。并且此项检查仅为简单的眼压检查,安全且便宜。因此就法律而言,没有进行检查,被告具有过失。(15) 在该案中,上诉法院指出,尽管医疗常规中有因40岁以下人患青光眼的概率极低这一事实而确立不做眼检的惯例,但就极个别特殊情况的可能发生、患青光眼这一后果的严重性以及检查成本的便宜性等情况综合考虑,理性医务人员仍会对低概率事件做出应对,即在眼检时做眼压检查,以防罹患青光眼。这其实是运用理性人标准否定原审法院以医疗常规判定过失的做法。在该案之后,美国法院重申对医生行为的过失判断应回归到一般认定标准,即以理性医生的注意程度为准在个案中做出判断,放弃了以医疗常规作为判定医生行为过失与否的标准[4]。 综合上述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实践中倾向性意见的不足在于没有注意到理性人标准与医疗常规所确定的注意程度的差异。理性人标准注重要求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具备与其他同级别医生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具有的注意程度,这种注意程度需要医务人员对个案情况的特殊性尽到审慎对待、具体诊断的义务。而医疗常规则不同,它仅仅对病症通常情况以及一般治疗方法进行描述,而没有也不可能对千差万别的个案情况完全列明,以此为医务人员的注意标准只需以病症的通常现象进行诊断,并以一般的方法进行治疗,无需考虑个案的特殊性,比如病症的紧急性、病患体质的特殊性等。然而,医疗行为的个体性、特殊性等性质决定了医务人员要考察个案的具体情况,应当根据个案的特殊性确定合适的诊疗方法。即使所患疾病属于同类型,也不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治疗方法。另外,现代医疗讲求对病人意愿的尊重,也就是说通过向病人充分说明诊疗方法的优势与风险,由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选择。而且,病患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好坏以及个人的偏好等原因也会导致诊疗方法存在巨大差异[5]。因此,医务人员不能将医疗常规中所规定的通常病症的诊断方法以及一般性的治疗方法无差别地应用到不同的个案当中。医疗问题的个案性特征决定了医疗常规的规定无法独立解决临床问题,必须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对于医务人员过失的判断也就不能完全依据医疗常规所确定的注意程度而进行。 除此之外,医疗常规是医务人员之间的行业惯例,它可以作为医务人员在临床实务中的操作指南,在法律上判断过失时也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依据,但是如果将它绝对化,完全依据它来判定过失,那就存在疑问了。一方面,法院完全依据医疗常规判断过失实际上是源于对医学专业的不了解,对医务人员产生过度的信赖。然而,医务人员也有自利性或者职业上的偏好,他们所形成的惯例非常可能存在有利于自身的偏向性,以此作为裁判案件特别是衡量医患双方利益纠纷的依据显属不当[4]909-969。另一方面,以医疗常规替换理性人标准实际上是让医务人员自己设定法律上的行为标准。由此,法官在法律层面的价值判断被医务人员的行业规定所取代。在此标准之下,法院所需做的工作并非判断医务人员应该从事怎样的医疗行为,而是判断被告行为是否符合医疗专业的惯例。换言之,将规范性质的判断,交由医学专业人员决定。这样实质上就是使医疗专业的惯例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医务人员在医疗常规的保护下,即使医疗人员构成过失,被害人仍无法请求赔偿。这样使得医生更容易固守旧有的医疗惯例而不思勤谨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 总之,医疗常规描述的是医生通常实际所适用的临床操作指南,而并非规定理性医生“当为”的医疗行为标准。完全以医疗常规来判断过失,无疑降低了医务人员应有的注意义务,因此它不能作为判断过失的全然性标准,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之一。倘若某医疗常规本身并不合理,其适用不能使得医务人员尽职尽责,或者该常规在具体个案的适用中可能产生临床风险,那么法院理应宣示对其排除适用。 四、判断依据(3):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导致患者损害的,推定具有过失。基于此,“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就成为了司法实践中判断医务人员过失的依据。对于该依据的适用,司法实践中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诊疗活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就推定为过失,且没有反证的可能。从各地法院的判决情况来看,鲜有例外。 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侵权责任法》颁行之前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中。比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赔偿纠纷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皖高法[2004]11号)第12条规定“有证据证明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直接认定其存在过失:明显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再比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赣高法[2009]210号)第37条规定“医方……具有其他明显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的医疗行为的,应认定为有过失。” 这种态度也与理论乃至立法中的一种观点相符合。该观点认为,第58条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失,属于不允许被告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推定。区别于第85、88、90条的许可被推定人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推定。严格地来说,第58条的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实际上是立法者预先作出的直接认定,而非假定,其法律效力等同于“视为”,即法律的直接认定,不允许被告推翻此项认定。法院一经审理查明案件存在法定情形,即应认定被告有过失,并驳回被告关于不存在过失的主张[6]。 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诊疗规范中,是有关于医务人员基本义务的规定,因此,在判断过失时对其予以参照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将此绝对化,作为全然决定性标准判定过失的存在,这就值得商榷了。以诊疗实务中常见的诊疗规范为例(16),在临床中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医务人员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了适合该个案的诊疗方法,但是却不符合诊疗规范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上述观点必然被判定为过失,而且在目前的司法判决中也尚未发现有违反诊疗规范而通过其他事实证明不存在过错的先例。 对于此类情况,美国的司法判例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Lowry诉Hendry Mayo Newhall Memorial Hospital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医生在使用高级心脏维持器时,使用两种药物,增加心脏跳动频率,违反了美国心脏协会建立的诊疗规范。被告抗辩称,基于个案的临床判断,若严格遵守心脏协会的诊疗规范,则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医生的违规行为有利于患者病情的治疗,因此诊疗规范可以不予遵守。该案法院判决被告胜诉,认为诊疗规范与案件本身事实相比较,并非更具说服力。(17)“在Denton Regional Medical Centre诉Lacroix案”中,法院同样指出,判断医生的过失,诊疗规范并非绝对标准。除此之外,还需考量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审查。(18)在美国判例中,医生没有完全遵守诊疗规范时,法院并没有因此判定被告具有过失。反之,医生遵守诊疗规范时,法院也没有确定地认为医生不存在过失。也就是说,是否遵守诊疗规范并不必然对应于过失的存在与否[7]。 之所以将是否遵守诊疗规范与过失判定进行区分,理论缘由与医疗常规类同:诊疗规范是医疗专家集体制定的,针对多数共同临床医疗行为的操作指南。这类规范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特征。而医疗行为具有个体性、特殊性,需要医生的个案判断。这类规范无法针对个别病情予以具体指导,仅可以作为医生在诊疗活动中的参考,而无法替代医生针对具体情况的临床判断。如果将诊疗规范作为判断医疗过失的绝对标准,会使得对患者的诊疗活动“教条化”,使得医方无需根据具体病情进行审慎判断,而例行公事式地予以敷衍,以逃避法律的审查,这样对患者的治疗不利。除此之外,即使诊疗规范可以用来个案指导,但其中立性和正确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医患双方并非利益的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激烈的冲突。这种情况很可能影响到诊疗规范的制定。在此类规范的制定过程中,参与起草的医务人员,颁布的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医疗类利益团体的影响而有所偏向,从而导致了对组织分散的病患方保护不够充分。同时,由于该类规范制定者的信息不足、政策分析不合理、制定者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时过境迁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这类规范本身所确定的行为标准存在不合理之处[8]。因此,在具体个案中,司法者不应不加分辨地一概以诊疗规范等为标准认定过失与否,而应当对这类规范在个案适用中的合理性进行具体审查。 综上,本文认为,在我国司法判决中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作为全然性决定性标准,在法理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弊端。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只能作为判断医疗过失的重要证据。因此,对于第58条的推定,宜采通常的理解:即使可以证明医务人员的诊疗活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但是如果医务人员能够证明其采取的诊疗手段是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所能采取的最合适的方法,即可推翻此推定。 五、判断依据(4):鉴定意见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由于涉及医疗方面的专业问题,法官需要借助医疗专家的意见方能判定过失,因此,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成为法院判断医务人员过失的重要依据,在很多时候甚至成为主要判断依据。(19)不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也并不必然以鉴定意见为依据做出过失判定:有的情况是鉴定意见本身存在问题,法院不予采纳(20);有的情况是法院不同意鉴定意见的判断,而自行判定是否存在过失(21);还有的情况则是因当事人放弃鉴定或者无法进行鉴定,由法院自行判定是否存在过失(22)。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法院判断医务人员过失时相较于其他类型案件会倚重于鉴定意见,但并没有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唯一依据,而仅仅是一种证据。在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中,也都强调了它的证据性质。比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24条规定“医疗鉴定结论经法庭质证确认后,具有证据效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与医疗过失鉴定结论均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最终依据,应由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的规定进行认定。” 鉴定意见被定位为证据,那么它应当是对涉案医疗事实的描述,包括医务人员诊疗行为的过程、病症的样态、病患的情况、诊断治疗方法等等,而不应涉及价值性法律评判,即对涉案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进行判断。然而,作为法律价值评判结果的过失,却成为绝大多数鉴定意见的必备鉴定项目。同时,从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来看,法院也有意将医务人员的过失判断交由鉴定机构做出。(23)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践中对于过失判断属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以及判定机构的确定仍待澄清。 对过失的判定必须以事实为前提,但是案件事实的核定与过失的判定却并非一回事。前者是对客观世界的探知,而后者则是客观事实与在法律上为了达到某种价值目标所确定的标准进行比对的结果。在医疗方面,涉及病症、诊疗方法等事实问题是依照医学的专业方法确定的,而对于医务人员过失的认定则应当探知在案件发生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对于这种合理性的判断,法官必须拟制出一个具有法律价值取向的参照体系进行比较,即一个合理谨慎的同行处在当事人的位置上该怎样去做。两者的区别说明了过失并非单纯的客观事实,对其的认定也不是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而是一种具有价值评价性质的法律判断,它不能随着案件事实的核定而自然得出。对于过失的评判属于法律判断也是由于过失在民法中的功能所决定的。在民法中,过失作为归责基础直接与不利的法律效果联系在一起。如果认定当事人具有过失,那么该当事人即负不利的侵权责任;与此相反,侵权损害的事实却并不直接与不利的法律效果相连。在事实得到核定之后,过失判定的任务即为说明当事人的行为在案件当时环境中是正当的抑或不正当的,从而为法律责任的认定铺平道路。因此,案件事实只是过失判定中的一部分论据而已[9]。 过失判定由医疗鉴定机构做出,其准确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从它们的判断依据来看,大多以医疗常规、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诊疗规范为依据判定过失存在与否。如前所述,这类依据并不能作为判定医务人员过失的全然性标准。另一方面,在医疗案件中使用鉴定意见是为了以医疗鉴定机构的专业知识来弥补法官的知识欠缺;法官所欠缺的是关涉医疗的技术性知识,即关于病患的病情以及诊疗活动是什么的知识,而并不欠缺关涉法律价值评判的知识,即医务人员应当如何做才是合理的知识。对医务人员过失的判定就是确定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那么其标准的设定就需要通晓法律价值取向的法官来完成,而医疗鉴定机构显然不能胜任;因此,以医疗鉴定机构来做过失鉴定是以其之短而为越俎代庖之事。 基于此,在实践中应明确鉴定意见的证据性质,即它是医疗专家依据自身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对案件的事实问题所做的技术分析和解释,应当将鉴定的内容限定在对涉及医疗专业性问题的核实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尽可能地说明案件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在明确鉴定意见的作用的基础上,对于医务人员过失的判定则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之内。即使鉴定意见就医务人员是否有过失发表意见,但医务人员是否具有过失最终还是应由法院综合种种证据来判断,不应受鉴定意见中结论的拘束。 六、判断医务人员过失之综合考量 由于医疗案件的专业性,在判断医务人员过失时,为了避免因医疗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导致误判,法官往往倚重于医疗常规、诊疗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即使是医疗水平这种需要法官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断的依据,在很多判决中其具体判断的特性也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内容一致的通用标准。除此之外,法官在大多数案件中还将判断过失的重任让渡给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医疗鉴定机构,依据鉴定意见中的过失鉴定来判定过失。从前文的论述来看,实践中的这种倾向已经偏离了公平公正的价值目标,依据这种方法往往造成个案中过失存否的误判。 实际上,上述依据都是判断医务人员过失与否的可靠依据,应当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妥当适用: 对于医疗常规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来说,首先应考虑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是否与它们相符。如果不相符合,则推定其具有过失。反之,则无过失。其次,允许当事人举证证明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患者诊疗当时的具体情况,即以患者诊疗当时的具体利益为准,判断诊疗行为遵守或违反医疗常规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时是否合理,以此肯定或推翻前述推定。不得仅以是否符合医疗常规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为准,全然肯定或否定过失。 对于鉴定意见来说,其主要作用在于鉴定关涉诊疗活动的技术性事项,包括医疗常规、诊疗规范等专业问题的解释;确定诊疗行为是否与之相符;鉴定不符合常规、规范的诊疗行为是否有利于在当时情形下对患者病症的诊疗;等等。总之,鉴定意见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作为法官最终判定过失存否的素材,而不能做出过失的鉴定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法官的判断。 对于医疗水平的标准来说,由于它是理性人标准在医疗专业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对其适用应符合理论中理性的专业人员标准的判断方法。 首先,应当根据当事医方的客观情况确定参照对象。专业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技能会影响到他预见危险及避免损害的能力。同时,该专业人员所处的环境等因素比如仪器、设备、辅助人员等会影响其到知识与技能的发挥[10]。因此,判定专业人员过失时应当考虑这些客观因素,将从事同类职业、具有同类资质、处于同类环境的人确定为参照对象。比如,骨科主任医师的参照对象应是同科别、同等资质的医师。青海某地二等乙级医院副主任医师的参照对象只能是同一或类似地区的同级别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而不能是上海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前述例举的“宗某与某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王某与郑州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即依此确定。 其次,应当根据诊疗当时的个案具体情况确定参照对象的行为模式。由于医务人员的诊疗活动以其自身的知识性、经验性判断为主,需根据诊疗当时的情况自由裁量,因此其行为并无内容绝对一致的模式可循,只能在个案中具体确定。但是,自由裁量并非不受任何约束,法律对此所设定的限制是行为的合理性,即以维护病患的利益为宗旨,合理谨慎地履行注意义务。这里的合理性是抽象的,在具体案件中应参酌两大方面综合确定: 一方面是患者自身的具体情况。在对病患诊断和治疗时,要考虑其年龄、性别、身高、体重、体质等个体情况,根据这些具体情况诊断病情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如前述“邹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在诊断病情时应考虑老人的多病体质。“王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医生在分析伤口时应考虑患儿的体重、身高。“杨某等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医生应考虑到儿童的特殊性,选择与成年人不同而适合儿童的治疗方法。另外,还要考虑患者自己的选择,即患者出于自身的经济能力、疼痛的承受能力等考虑选择治疗方法。那么,合理的诊疗行为也应当尊重患者的选择。 另一方面是诊疗行为的具体情况。这方面应主要斟酌五个因素:1.诊疗行为的风险:诊疗行为本身的风险有大小之分,在可选择的诊疗方式中,应根据前述患者的具体情况尽量选择风险较小的方案。2.诊疗行为的收效:如果实施的某诊疗行为越能有效地治愈病患,则该行为就越合理。3.诊疗行为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治愈疾病在同样前提下的花费越低,该诊疗行为就越合理。4.发病的概率:如果没有或没有正确实施某诊疗行为所导致的病患发病的概率越高,那么医务人员就越可能存在过失。5.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如果没有或没有正确实施某诊疗行为导致病患所生病症越严重,那么医务人员就越可能存在过失。 当然,在实际的个案中,对这五个要素的考虑一般不会单独进行,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综合权衡。比如前述的“Helling诉Carey案”中法院最终确定医生的行为属于过失就是对上述五个要素做了综合的权衡:被告没有对原告眼睛进行眼压例检导致了罹患青光眼这一后果,与简单眼压例检的成本相比,差异巨大。尽管原告作为40岁以下的人发病概率极低,但以便宜无风险的眼压检查以及有效防止发病这一收益相比,进行例检是有必要的。总之,当病人有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时,即使医疗常规因该概率的微小而没有规定,但法院仍应宣示医生的义务,尤其在该损害后果可以简单且便宜地予以避免时。 我国法院在个案中对上述因素进行衡量以确定过失的先例也不少。比如“宗某与某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官对于转诊问题的考虑就体现了成本与损害后果严重性的综合考量。医生及时告知转诊所花费的成本极少,但如果没有告知转诊,病人因延误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却是严重的。因而,如果被告医生没有告知转诊,那么即属过失。再比如“陆某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血管腔内介入手术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但能有效治愈患者疾病,因此应采用该手术的方法。在此情况下,为了尽量降低风险,应当详细对病患告知术后的并发症并采取预防措施,这种术前告知所需成本与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相比是极其低微的,应当进行详细地告知,然而医生却未尽该义务,因此存在过失。还有在“王某等与郑州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传统手术方式所存在的风险较之先进手术的风险更大,而可能产生的收益却较小,因此应选择后者,而医生却适用了前者,因未达到医疗水平而具有过失。 最后,在确定了参照对象及其个案确定的行为模式的基础之上,将当事医方的诊疗行为与其相比,如果前者达到甚至优于后者,那么即判定无过失,否则即属过失。 另外需指出的是,对于医疗水平依据的理解不能狭隘,它不仅仅是指医疗技术的先进或落后,更是指医务人员能否在个案中尽到参照对象能尽到的注意义务,与参照对象处于同水平,这才是法条中“当时的医疗水平”的准确范围。因此,第55条规定的说明义务也是与当时医疗水平相符的诊疗义务的一种。如果不能正确履行,那么也属存在过失。 医疗是一门依靠医务人员的知识、经验在个案中作出裁量判断的技艺,无统一模式可循。这就决定了对医务人员过失的判断不仅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和医疗常规中的通用性规定,更要由法官考察个案的具体情况,包括当事医方的客观情况,患者自身的特殊情况,斟酌诊疗行为的风险、收益、成本、发病的概率以及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只有综合妥当地衡量上述各种因素,方能准确判断医务人员的过失,实现个案的正义。 ①从《侵权责任法》第57条的起草背景来看,对医方情况的考虑与理论中的观点甚至立法意图相悖。在《侵权责任法》第2、3稿草案中,该条均为两款。其中第2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对此,有人认为设置该款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在许多案件中医疗机构均可以当地医疗水平低于当时医疗水平作为抗辩理由,否定诊疗活动中存在过失,最终使受损害的患者不能获得赔偿。于是该款被删除。(参见:梁慧星.论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J].法商研究,2010,(6).)但是,该观点并未被司法机关采纳。对于“医疗水平”的考量,除了反映在上述具体案件之中外,还体现在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中。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10年7月1日)第1条规定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应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未尽到该注意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应认定医疗机构有过失。认定医疗机构有无违反注意义务,应适当考虑医疗机构的资质、医务人员的知识、技能等相应专业、资质及地区差异等因素。 ②比如: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0)穗番法民一初字第2656号民事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464号民事判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0)静民一(民)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4)静民一(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乌中民五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0)嘉南民初字第2311号民事判决。 ③对此,我们可以参看日本的判例:“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案”。早产儿出生后需在人工给氧的温箱中生活一段时期,当时许多早产儿在温箱中产生了视网膜病变,后发现与氧气浓度较大有关。当时并无有效治疗方法。医学界提出了“光凝固疗法”,但临床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没有定论。该案中的早产儿在保温箱中发生视网膜病变,仅给予酸素治疗,而没有采取“光凝固疗法”治疗,后病情恶化而双目失明。日本法院认为,医生未能对当时已存在的“光凝固疗法”及相关资讯向家属说明,其违反义务、延迟转院的行为具有过失。该判决在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光凝固疗法”在当时尚未确立为有效治疗方法,法院判决无疑是以当时医学发展的“医学水平”作为过失认定基础,对医方显属苛刻。后来,日本法院修正了标准,在高山日赤医院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判决中废弃了医学水平的标准,指出在“光凝固疗法”的安全性及疗效未经确立前,医生的义务应以“诊疗当时临床医学实践上的医疗水准”为标准。(参见:陈聪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之过失判定[J].政大法学评论,2012,(127).) ④尽管该文件的发布早于《侵权责任法》,但现在依旧有效,在审判实践中仍具有指导作用。 ⑤参见: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2011)绥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 ⑥参见: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13)安民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 ⑦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2)六民初字第695号民事判决。 ⑧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1028号民事判决。 ⑨参见: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南市民一终字第182号民事判决。 ⑩参见:平成8年1月23日判决。民集50卷1号,第1页;判时1571号,第57页。(转引自:陈聪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之过失判定[J].政大法学评论,2012,(127).) (11)参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1324号民事判决,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2013)吉民初字第44号民事裁判,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3)贺八民一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 (12)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43753号民事判决。 (13)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衢民终字第679号民事判决。 (14)参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3)历民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 (15)参见:Helling v.Carey,519 2D 981(Wash.1974). (16)需说明的是,医疗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医方当为性和禁止性义务的一般性规定,在诊疗活动中较之诊疗规范,其具体指导意义很小。诊疗规范是由卫生部门或者医学团体依据专业知识形成的作为临床实际应用的实务操作规范。比如中华医学会的《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因其内容具有很强的技术指导性,医务人员在临床中可用以具体参考。因此,诊疗规范在实践中应用最多,而体现的问题也最为突出。本文以诊疗规范为例说明所存在的问题。另外,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制性规范的行为不能直接判定过失的理由,已有学者从法理角度作了阐释:其原因在于这类规范和侵权法的目标存在区别,两者评价标准并不一致。公法与私法上的行为的可接受性必须严格区分,公法的规制性规范在引入私法时必须对其进行筛选和甄别。私法的行为标准应具有独立性,侵权法本身必须在考虑个案事实的前提下完成过失的判断。法官在此应具有独立评价的空间,即使法官最终认为违反这类法律规范构成过失,这也是法官评价之后的结果,而非违反规制性规范的直接结果。如果认为违反规制性规范就一定构成过失,法官必须受此约束,这无异于排除了法官在此过程中独立的评价空间,扭曲了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的合理关系。正因为如此,违反规制性规范并不能直接认定为过失,并不应使得对方当事人不能举证推翻此种认定。否则,无异于让规制性规范中所确定的行为义务标准优于过失判定时的注意义务标准。司法者自主评价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参见:朱虎.规制性规范违反与过失判定[J].中外法学,2011,(6).) (17)参见:Lowry v.Hendry Mayo Newhall Memorial Hospital 229Cal 620(1986). (18)参见:Denton Regional Medical Centre v.Lacroix 947 SW 2D941(Tex.Appeal 1997). (19)比如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一(民)初字第2973号民事判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6423号民事判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3)松民一(民)初字第8050号民事判决中都倚重了鉴定意见。有法院指出“由于医疗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法院确定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的主要判断来自于医学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再比如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3)沙法民初字第02987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指出“关于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医疗过错与原告所诉的后果间有无因果关系,因涉及专门医学知识,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手段和丰富的临床实践,超越普通人的经验、学识,法院只能借助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作为判断基础。” (20)比如在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张中民三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指出,鉴定意见一方面确认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疾病较为少见,患儿入院早期病情不典型,被告在诊断方面存在一定客观难度,且李某入院时病情已十分严重,治疗效果难以评价,预后差;另一方面作出被告的诊疗行为具有过失,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其鉴定结论与结论依据所作的分析之间存在矛盾。因而,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 (21)比如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院(2010)徐民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中,尽管医学会鉴定结论为“医方没有过失”,但法院仍然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对胎盘早剥的认识不足,新生儿出生后抢救不力等缺陷,因此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 (22)比如在沅陵县法院(2012)沅民一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12)宛民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西峡县人民法院(2012)西民一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中,都因原告拒绝鉴定或放弃鉴定等原因导致无法进行医疗鉴定,法院在这些情况下没有鉴定意见可以参考,因此自行做出“过失判断”,即被告在医疗活动中,应该具有高度的注意,对患者应尽到高度的谨慎和关心义务,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 (23)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通知》第3条规定,“委托医疗损害鉴定,应要求鉴定机构在鉴定意见中对医疗行为有无过失、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一并做出明确认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要求鉴定机构对涉案医疗行为有无过失、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及伤残等级作出明确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7条规定:对下列医疗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双方有权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无过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医疗损害的鉴定,由受托鉴定机构对医疗行为有无过失、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等进行鉴定,损害后果依据伤残等级标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