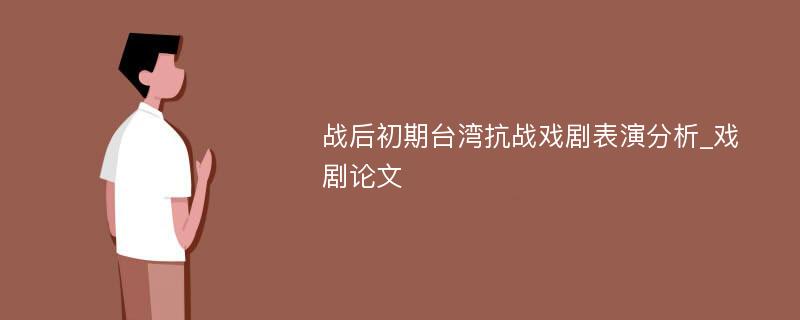
战后初期抗战戏剧在台湾的演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初期论文,戏剧论文,演出论文,在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15)06-0050-14 抗战时期戏剧是非常时期的戏剧,展现在戏剧创作目的的高度集中、演剧创作队伍的急速扩大、戏剧形式内容的蓬勃开展、演出范围的无所不在等面向上,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黄金时代。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回归中国,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对新生台湾为达去殖民化之文化重建目的,此后四年的战后初期,透过来台的职业话剧团、军中演剧队、外省业余剧团及教师、学生,当时超过40位大陆知名剧作家的70部以上的剧作被引介来台演出,其中即包含相当数量的抗战戏剧作品。 抗战戏剧就广义来说,可谓抗战时期的戏剧,泛指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期间所有的话剧创作演出;而狭义概念,则指创作以戏剧为文化武器,担负抗战救国任务,以宣传、教育、动员为目的,举凡与抗战相关之歌颂与敌人英勇斗争、歌颂爱国/历史英雄、歌颂战时正面进步人物、借历史故事以古喻今/激励人心、反映时局生活问题、强调军民合作、呼吁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与国内黑暗势力斗争、描绘敌后斗争及敌伪丑态等题材皆属之。本文以狭义的抗战戏剧进行论述,广泛运用台湾战后11份报纸材料以探讨此“彼时彼地”色彩至为明显的抗战戏剧,在台湾战后四年间被搬演的情形为何?对于中国文化与国语尚待学习熟悉,且战时经验迥然相异甚至对立的“此时此地”的台湾人而言,其接受度又为何?不同类型内容的抗战戏剧在台湾的接受度可有差异?在1949年底两岸隔绝后,在新的剧本荒年代里抗战戏剧可有新的面貌得到延续及影响?以上皆为值得研究却又是长期为学界忽视的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厘清解决,将对台湾戏剧史、两岸戏剧交流史及中国话剧史研究有所帮助。 二、战后初期抗战戏剧在台演出史略(1945-1949) 1945年至1949年战后初期的四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因台湾的地方政府组织改组、大陆局势的骤变及台湾情势的变化,仍对中国剧作在台湾的演出实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下即以省署时期(1945.10.25-1947.5.16)、省府时期(1947.5.16-1948.12)及“戡乱”时期(1949.1-1949.12)①等三个历史段落,对抗战戏剧在台湾的搬演进行观察。 1.省署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台湾结束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回归中国,在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前几天,自宁波移防台湾的陆军第70军抵达基隆,该军政治部为庆祝台湾光复后首次元旦,1946年1月1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三个独幕剧《军用列车》《半斤八两》及《红色马》,②这是光复后第一次中国剧作在台湾上演的记录,其中严恭、石炎创作的《军用列车》(1940)为抗战戏剧剧目。[1](P.108) 为介绍祖国文化、沟通军民情感、充实军中文化及社会宣传,第70军政治部自沪、杭一带征聘男女艺术人才来台组织话剧宣传队。4月下旬,在台北市中山堂公演抗战名剧陶熊的《反间谍》(1941)[2](P.112)、陈铨的《野玫瑰》(1941)及徐霖昌的《密支那风云》(1945)等三出戏,以“慰问台胞及招待各界”。③一直到12月底奉令移防回返大陆徐州,70军政治部在台的一年零两个月期间,还在全省各地演出吴铁翼的抗战四幕喜剧《河山春晓》(1945)、熊佛西的独幕剧《艺术家》及王光乃的独幕剧《群魔》(1940)等剧。④ 1946年整年,除了70军政治部剧宣队演出《军用列车》《反间谍》《野玫瑰》《密支那风云》等抗战戏剧外,尚有以驻台外省记者组成之业余话剧团体台北市外勤记者联谊会,联合外省业余剧团青年艺术剧社,于11月初在台北共同公演曹禺名剧《雷雨》,这是曹禺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演出;[3](PP.40-41)另由复员到台湾的原福建实验小剧团部分演员结合本地剧人所组成的实验小剧团,于12月中旬在台北演出改译自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名剧《守财奴》,当时分国语、闽南语两组演出,获得了鼓励同时发展国语话剧和闽南语话剧者的支持。⑤而台中民众教育馆为普及国语运动率先组织的戏剧研究会,也曾于12月下旬演出吴天(方君逸)的五幕剧《四姐妹》,免费招待各界民众。⑥ 负责战后文化宣传工作的省署宣传委员会⑦为推行国语、倡导话剧运动,特别邀请抗战时期知名的新中国剧社来台公演,这是祖国第一个具高知名度的职业话剧团体来到台湾,又因为有知名戏剧前辈欧阳予倩随行,所以引起了报纸媒体极大的关注。1946年12月31日至次年1月6日开演第一档戏《郑成功》,这出戏是阿英(魏如晦)在上海孤岛时期创作的南明史剧之一《海国英雄》(1940),这次来台演出特别由改编者“齐怀远”增加了一段荷兰人受降的结尾并改剧名为《郑成功》,导演为欧阳予倩,严恭饰郑成功,促成此行功劳甚巨的名演员蓝兰(蓝馥清)则饰郑成功夫人董氏一角。这是战后台湾首次以南明史实借古喻今的抗战戏剧演出。 1947年元旦,台南市民众教育馆实验剧团在台南市延平戏院演出了宋之的、老舍合著的抗战名剧《国家至上》(1940),此为战后台湾南部第一次大规模的国语话剧演出。演员皆为台南各机关公务员,而观众中除了外省籍公务人员之外,大部分皆为本省民众。⑧而为筹募台南地震救济金,1月中旬该团再于台南市全成戏院演出同一剧目。此出强调汉回不同民族应化解误会、共同抗敌的戏,或因有益于本外省人间隔阂的化解,或因其情节富戏剧性,很快为台湾本地职业新剧团移植以闽南语演出,该年已有国声剧团演出同名剧目。[4](P.205)1月22日农历新正,有台东业余剧社于台东剧场演出陈铨的《野玫瑰》。 2月中旬,另有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奋斗剧团特请本省导演,以闽南语排练中国新剧前辈朱双云的《平壤孤忠》(1940),并演于台北市新世界戏院。⑨该剧敷演19世纪末日军侵略朝鲜,兵临平壤,城内清军总兵左宝贵御敌牺牲事。以闽南语演出的方式引介此改良京剧剧作,在国语尚未普及的当时台湾别具意义。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件⑩爆发前,1月初尚有话剧研究会在省立台湾师范学院大礼堂演出曹禺名作《日出》;(11)1月下旬,三民主义青年团基隆筹备处所属基隆青年剧团于高砂剧场演出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12)2月15日戏剧节当日,则可见台东民众教育馆演出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的一夜》;(13)而新中国剧社亦在演出吴祖光的《牛郎织女》、曹禺的《日出》和欧阳予倩的《桃花扇》之后,因该事件而终止中南部的巡演及留台推动剧运的计划,4月分三批回返上海。[5](PP.219,238,241) 综观省署时期台湾的抗战戏剧搬演,主要以普及国语、增进对祖国的认识了解、沟通军民情感为演出目的,演出团体则以军中演剧队为主,地方民教馆附设剧团、外省业余剧团、中国职业话剧团的演出为次。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一剧因题材与台湾关系最为密切,加上新中国剧社为省署邀请来台,代表中国职业话剧在演出、制作水平的示范,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而《野玫瑰》一剧也因剧情巧妙融合战争、谍报、爱情、道德等通俗剧元素而较易为观众接受,因而有较高的搬演率。另外,以闽南语演出《国家至上》《平壤孤忠》等抗战戏剧,便利台湾民众在无语言障碍的条件下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话剧的尝试,也已踏出可贵的一步。 2.省府时期 “一·二八”事件之后,台湾剧界沉寂数月。7月底,“国防部新闻局”军中演剧第三队奉“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之命调派来台,7月31日率先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了宋之的的抗战名剧《新县长》(《刑》,1940)。(14)演剧三队为台湾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筹募基金,10月下旬续于同一地点演出了夏衍、宋之的、于伶于抗战时合写的《草木皆兵》(1944)。(15)之后至1948年底,演剧三队还演过阿英的《明末遗恨》(即《碧血花》,1938)等抗战戏剧。(16) “二·二八”事件后移防台湾的青年军第205师新青年剧团在1947年10月下旬于台北市中山堂演出于伶的历史剧《大明英烈传》(1940),(17)该剧后成为该团巡演之常演剧目。而为“宣扬祖国文化、沟通省内外感情、推行国语运动”,台湾糖业有限公司邀请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旅行剧团来台演出,这是战后第二个受邀来台的中国职业话剧团体。自11月9日在台北市中山堂第一档演出杨村彬的《清宫外史》(1944)开始,该团在台巡演的7个月间,尚演出顾一樵的《岳飞》(1939)(18)及袁俊(张骏祥)的《万世师表》(1943)等抗战戏剧。[6](PP.128-129)该团于1948年5月回返上海,有国立剧专毕业的演员崔小萍、金姬镏留台发展。 1947年12月,台湾南部屏东一地的话剧演出不断,除了青年军第205师新青年剧团演出于伶的《大明英烈传》外,省立屏东农校也演出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1942),而屏东中学为庆祝两周年校庆亦于下旬在屏东剧场演出《反间谍》一剧。(19) 1948年1月中旬,青年军第205师新青年剧团在台南演出《结婚进行曲》。4月下旬,则有本地职业新剧团“民声”,演出改编自陈铨《野玫瑰》的电影《天字第一号》之闽南语新剧。(20) 7月11日北一女中自治会得留台话剧演员崔小萍指导,在该校礼堂演出吴祖光的《少年游》(1943)[7](PP.178-179),该剧写北平沦陷之后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以及知识分子思想脉动。8月底,崔小萍再为北一女中自治会执导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并演于该校礼堂。 为庆祝第三届台湾光复节,台湾省政府于10-12月举办盛大的台湾省博览会,其中游艺部分计有职业、业余、学校剧团于台北市中山堂多场的话剧演出。其中演出抗战戏剧者有受邀来台的南京国立剧专剧团演出吴祖光的《文天祥》(《正气歌》,1940),以及台湾大学演出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1943)。[8](PP.364-365) 此期台湾的抗战戏剧搬演,以歌颂历史英雄、借古喻今的历史剧比例最高,如《明末遗恨》《大明英烈传》《岳飞》《文天祥》等;歌颂抗战时期正面人物及描绘敌伪抗日情形居次,前者如《新县长》《万世师表》,后者如《少年游》《草木皆兵》。较特别的是,随着1946年底改编自陈铨抗战锄奸戏《野玫瑰》的上海电影《天字第一号》来台上映并引起轰动后,1948年本地新剧团随即改编为闽南语话剧作品演出。 3.“戡乱”时期 因国共内战日炽,1949年2月15日第六届戏剧节是战后以来庆祝活动最冷清的一届,两个演出剧目中有省立台湾师范学院人间剧社演出沈浮的《金玉满堂》(1944)与抗战有关。(21)3-4月,有演剧三队分别在台北市中山堂、台中戏院、台南全成戏院演出常演剧目阿英的《明末遗恨》。(22) 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政治局势丕变,大批外省人士陆续撤退来台,其中的话剧爱好者开始在台组织起业余话剧团,下半年外省业余话剧团的数量激增。7月下旬,由上海勘建剧队在台改组的勘建剧团于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陈铨的《野玫瑰》。(23)8-9月,空军高炮六团铁花业余剧社分别在嘉义中山堂、朴子东和戏院演出抗战谍报剧《八十八号间谍》,(24)此实为《反间谍》之异名,取剧中主角白先生之间谍编号为八十八号之故。8月中旬,由甫成立的业余成功剧团联合5月才从上海迁台之中国制片厂演员田琛、黄曼等,于台北市中山堂演出徐昌霖的《密支那风云》。(25) 9月1日,有本地职业新剧团“新天华”以闽南语演出改编自电影《天字第一号》的同名闽南语话剧。[4](P.246)9月中旬,有业余实验剧团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杨村彬的《清宫外史》第一部《光绪亲政记》,并有台声国乐队现场伴奏。(26)10月中旬,则有演剧三队于台北市中山堂演出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1941)。(27)另在25日有第99军政工队在花莲中华戏院演出陈铨的《野玫瑰》。 继8月演出《密支那风云》之后,11月中旬,成功剧团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了第二档戏——周彦的四幕古装剧《桃花扇》(即《秣陵风雨》,1944),因该剧宣扬民族气节,崇尚忠烈,而为媒体肯定,演出时且有高子铭、孙培章、陈效毅、黄兰英等四位国乐名家伴奏。(28)而12月中旬,有基隆业余实干剧团请胡杰导演陈白尘的抗战剧《群魔乱舞》(《魔窟》,1938),预定24日在基隆高砂戏院公演。(29) 此期台湾的抗战戏剧演出,以军中剧队、外省业余话剧团为演出主力,数量虽有减少,但以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及间谍锄奸戏占其大宗,前者如《明末遗恨》《忠王李秀成》《桃花扇》,后者则有《野玫瑰》《八十八号间谍》。而此年因政局变化、“四·六”事件(30)等因素导致岛内思想钳制加剧,以及剧本、演出的审查及“反动”书刊的查禁,(31)1949年下半年此类剧作家的作品多已无法在台湾演出。 三、此时此地的悖逆 据可考资料,战后初期抗战戏剧在台湾的演出计有23部,数量占战后初期在台湾演出之中国剧作的三分之一。(32)若依题材内容区分:(一)描写抗战中之进步正面者:《国家至上》《新县长》(《刑》)、《河山春晓》;(二)描写历史故事以冀激励人心者:《明末遗恨》《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海国英雄》《平壤孤忠》《大明英列传》;(三)以历史讽喻现实者:《桃花扇》《忠王李秀成》《清宫外史》:(四)直接描写抗战者:《密支那风云》《军用列车》;(五)描写敌后人民与敌伪斗争者:《少年游》;(六)描写敌伪间谍活动:《草木皆兵》《野玫瑰》《反间谍》;(七)描写敌后汉奸丑态者:《群魔乱舞》;(八)描写大后方严惩奸商者:《金玉满堂》;(九)描写大后方艰苦自守者:《重庆二十四小时》《万世师表》;(十)描写大后方揭发社会不合理者:《结婚进行曲》。其中以历史故事借古喻今、激励人心的剧目比例最高,几为二分之一。而除了《军用列车》为独幕剧外,余者皆为多幕剧。 若采田进于《抗战八年来的戏剧创作》一文中以1941年为界(33)来区分抗战戏剧创作的前后期,战后初期台湾演出的抗战戏剧,前后期作品各占一半。而其中绝大多数仅是由单一剧团演出过一次而已,演出比例最高的是有7个剧团(其中两个是本地的闽南语新剧团)演出的《野玫瑰》,有3个剧团演出的《结婚进行曲》,有两个剧团演出的则有《反间谍》《密支那风云》和《清宫外史》。 1.成功的文化斗争武器与失败的文化宣传利器 在战后初期四年中,抗战戏剧集中压缩在台搬演,此具明显“彼时彼地”特色的演出,对“此时此地”的台湾本地人及外省人而言具有何种意义?以及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针对抗战戏剧在不同时空的演出意义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一解此问。 抗战戏剧因时代而生而荣。作为最有力的文化斗争武器,戏剧在抗战期间,无论在宣传、教育及动员上皆起着积极的作用,并在相当程度上担负了抗战救亡的任务,从而成为一代人的共同情感记忆,无论是剧人队伍、观众数量,以及剧本创作及演出的质与量上都有突出的发展,因而造就了话剧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 而此戏剧工具论在抗战时期的成功作用,随即影响了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时的文化教育思维。亦即当时的文化主管单位,为使甫脱离日本殖民的台湾人能尽早认识祖国文化、学习国语,国语话剧于是成为彼时文化施政“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之文化重建的利器。一时间,自“五四”至抗战时期二十多年间中国话剧发展的成果——超过40位剧作家的70部以上的作品迅速地集中压缩在此四年间于台湾呈现,23部抗战戏剧作品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台湾现身。 严格说来,这些抗战戏剧作品大部分是彼时知名剧作家的佳作,在大后方及上海也多有不错的演出实绩及观众反映。像刘念渠就肯定《群魔乱舞》是抗战剧本中能避免并克服公式化倾向而有典型创造的好作品;[9](P.55)洪深也曾说过,若要他推荐10部必看的抗战剧本,《国家至上》《忠王李秀成》将名列其中;[10](PP.133-134)而演出200多场的《文天祥》,更是上海孤岛、沦陷时期公演场次仅次于《秋海棠》者。[11](P.295)可是,当时这些优秀的抗战剧作对于中国文化及国语尚待熟悉、祖国认同还待培养的台湾百姓而言,其接受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抗战戏剧的演出内容,也因与台湾人的生活、历史经验差距过大,而有着先天上的缺憾。台湾戏剧前辈吕诉上即曾在《台湾电影戏剧史》一书中谈到演剧三队演出宋之的《新县长》,因剧本内容涉及大后方的兵役、食粮问题,与台湾观众的生活经验差距过大,因而上座率并不高的情形: 剧情里虽然充分表露民族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意识,演出中表现一种“力”加强光明而战胜黑暗的剧旨。演出效果,该队是以重于宣传的意义来演这出戏,但时也地也,生活习惯各有距离,无法大量地吸引多数观众。[8](P.352) 也因台湾人并无抗战的共同经验及情境的了解,难以产生剧作该有的情感共鸣及宣传效果,于是,少数观赏抗战戏剧演出的本省观众仅能将焦点集中在艺术呈现的批评上。吕诉上在提到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旅行剧团演出的《岳飞》时,他即完全聚焦于演出的艺术评论: 导演单顾到舞台的地位和某些结尾部分小段情感的玩弄,而忽略了布景道具和暗转的配合,那些笨重不灵的道具和景片妨碍了迅速的搬移,而超过了暗转可能的紧张的时间,且剧本近似平剧小白的台词,演出也“架子化”了。[8](P.356) 他在看完该团的《万世师表》之后,也只留下对演员要饰演两代人精湛演技的印象。[8](P.361) 当然,当时所有的抗战戏剧演出也不是没有成功之例,像新中国剧社来台演出的第一个剧目《郑成功》,即因其题材与台湾关系密切,且能因时地制宜修改剧本而为观众欢迎,当时并有《和平日报》《中华日报》《自强报》等三家报纸刊出该剧的演出特辑。[12](PP.58-60)导演欧阳予倩就曾提及此剧在台湾演出的意义: 郑成功这个戏,在台湾上演,是有它深切的意义的,尤其在光复台湾的今日。……他(阿英)写作的时候,是在抗战当中,写作的地方是在敌伪控制下的上海,所谓为着“此时此地”,而今演出的时和地完全不同,便把剧本的名称改为“郑成功”,剧中的场面也有些更变。[13] 由台南民教馆实验剧团演出的《国家至上》则为另一成功之例。虽然仅演出三场,但因观众以台湾人为主,加上剧本之民族团结剧旨能与本外省人情感融合、加深对祖国认同、化解隔阂、国家至上等现实问题进行呼应,此具备此时此地演出意义是其成功之因: 《国家至上》这次搬上台湾的舞台来演出,是有着深切的意义的,在目前沟通本外省人情感的融洽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事实上在本省光复初期,为了语言上的隔阂,以及一些不法官吏的贪污行为,因而引起台胞的反感……把抗战史实中政治斗争最艰巨最悲壮的一页,在舞台上再现,使台胞认识祖国的伟大,与民族性的倔强,以及粉碎法西斯匪徒及其走狗们的挑拨离间的阴谋。……让《国家至上》作为沟通本外省人感情的桥梁,使台胞对祖国加深认识。(34) 战后初期台湾“国语”剧坛的观众其实是以来台的外省籍观众为主,因为他们甫经历过艰苦的抗战生活,加上对抗战戏剧相对熟悉,战后初期来台演出的抗战戏剧对他们而言是相对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但剧作因时地改变后现实意义的转变或扞格,他们也格外敏感。一署名“雪青”的外省观众,投书报端批评了“国立”剧专剧团的《文天祥》未能反映现实的问题: 时代的转变,生活环境的转变,现实教训了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也完全转变了。……因之“时间”格杀了《文天祥》这戏,过去热血奔放,情绪激动,现在看来,因现实使这“热情”泄了气,已鼓不起观众的共鸣,且在一般头脑冷静的人们眼中,觉得这是对现实一个难堪的讽刺。(35) 演剧三队演出的《明末遗恨》,原是阿英在上海孤岛时期的创作,以古人故事警示今人为目的,但战后初期在台湾的演出,因未能实时与现实呼应而招致讥讽:“虽然它在抗战时期在沦陷的孤岛上曾经风极一时,可是时代的巨轮已经把它压在历史的背面,今日再出现,未免有点老生常谈。”(36) 2.从抗战到“戡乱’的挪移 1949年,随着内战局势的丕变,反内战声浪延伸至岛内,并且台北校园发生“四·六”事件,国民党当局对于台湾不分省内外人士的思想钳制也越来越紧,反映在戏剧方面的是加强了剧本及演出审查的力度与范围,并陆续公告查禁剧本名单,明显“左”倾及已响应中共号召的剧作家的作品此时都无法搬演,这对国语剧界直接造成的影响是剧本荒现象。当许多剧本开始因作者问题而无法演出,抗战戏剧的内容又不合“戡乱”需求,而此时若还演出喜剧、闹剧更与时局现实距离过远,于是,开始有了鼓励写作“戡乱”剧及改编抗战剧内容为“戡乱”剧的呼吁。(37) 而部分仍能演出的抗战戏剧,也因观众/创作者观点诠释及侧重的转移,使其有了新的时代面貌与意义而续存于台湾。如周彦写于1944年的《桃花扇》是有感于坚持气节是最终得以战胜的关键而创作,当时他在《我怎样写〈桃花扇〉》一文中即有明确的表达。[14](P.3)可是,时空改变,1949年11月成功剧团在台演出该剧时已是“戡乱”正炽的时候,自然观众在观赏时所抨击的对象会转移至已/拟响应中共号召的人身上,《桃花扇》于此时又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其宣扬气节,崇尚忠烈之剧情更为该剧最正确之主题;于此时上演正可给予……迎头一大棒喝!(38) 而徐昌霖创作于抗战胜利前夕的《密支那风云》,原采中国远征军联合英美克复密支那史实,1949年8月成功剧团在台演出该剧时,观众也自动将抗日大后方的“后方”密支那挪移至“戡乱”的“后方”台湾,并肯定导演王珏对该剧重新诠释的用心: 我对“成功”这次选择了《密》剧,又在今日演出,诚然有它丰富的、现实的意识存在。一个好的导演,是能在古旧的剧本中,发掘出新的意识,亦等于将一面封尘的镜子拂净后,看到了鲜新的影子。是的,“没有安定合理的后方怎么能够打胜仗!”(39) 当编剧人才补充未及,“戡乱”剧本写作尚少,根据旧本略加改编,把抗战意识改为“反共”意识并更改剧名是当时解决剧本荒的方法之一,1950年就曾出现改编自陈白尘《群魔乱舞》的“戡乱”讽刺话剧《百丑图》,改编自陈白尘《岁寒图》的《岁寒知松柏》,以及改编自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的《台北一昼夜》等。 3.选择性的接受:《野玫瑰》与《国家至上》 战后初期台湾的抗战戏剧演出,数量并不算少,但真正对台湾人有所影响的实则不多。主要原因是当时台湾人的戏剧娱乐主要在戏曲及新剧,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演剧传统又因故中断,所以,抗战戏剧的演出人员和观众群几为来台及在台的外省籍人士,对大多数的台湾本地人而言,抗战戏剧其实并未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 日据中期以来,台湾知识分子借演剧关怀社会、批判时政的传统,在战后一年里短暂闪耀后旋即中断[15](PP.83-87),仅剩商业通俗取向的职业新剧团于台湾各地戏院巡演,而陈铨的《野玫瑰》,即因曲折的剧情中巧妙融合战争、谍报、爱情、道德等通俗剧元素,而为本地职业新剧团移植改编并以闽南语演出,成为战后初期抗战戏剧中最为台湾民众所熟知者。其实,本地职业新剧团的演出并非直接受到来台话剧团体演出《野玫瑰》的影响,而是间接改编自1946年底轰动上海,由屠光启导演、欧阳莎菲主演,改编自《野玫瑰》的电影《天字第一号》,1964年又因台湾谍报电影《天字第一号》(40)及其后续四集的拍摄及卖座而又再度造成台湾的“野玫瑰”热潮。 西南联大教授陈铨在1941年创作的《野玫瑰》,避开了抗战初期间谍戏、汉奸戏中十个汉奸九个脓包、没有灵魂的傀儡这样公式化的处理,尽管因为他笔下的汉奸北京伪政委会主席王立民被描绘成一个有才智、坚强意志的人而招致批评,甚至在1943年引发该剧是“裹了糖衣的毒药”、裹藏“战国派”思想的论争。[16](PP.186-192)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曾有的学术、党派之争自然不敌该剧通俗、具市场价值的商业卖点及潜力,由屠光启的电影、台湾职业新剧团的演出及台湾电影《天字第一号》的成功及影响即可证明。台湾谍报电影《天字第一号》的导演是外省剧人张英,他在回忆录中即曾谈到他偏爱《野玫瑰》之因: 我先后为不同的剧团和学校,导演过不下二十多次。该剧不但剧情的结构好,引人入胜,而且亲情、爱情与国家至上的抗日锄奸与冲突,显现了人性的光辉,并非左派所批评的宣传法西斯主义。[17](P.22) 从大陆话剧团体来台多次演出《野玫瑰》,到台湾职业新剧团演出闽南语新剧《天字第一号》,再到国语、闽南语两版的电影《天字第一号》所掀起的谍报片风潮,我们可以说《野玫瑰》是所有战后初期在台湾演出的抗战戏剧中,唯一留下深刻及持续影响的作品。 另外,宋之的、老舍的《国家至上》,虽然仅在1946年由台南民教馆实验剧团以推行国语为目的演过三场,但后来该剧却是以“国语练习教材”持续影响台湾的国语教育,成为抗战戏剧在台作用遗绪的另一例。 战后台湾的国语推行始自1946年4月成立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与老舍颇有私谊的何容,或因二人关系及何容对老舍剧作有一定的了解,在其后来升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委期间,曾选《国家至上》剧本当作国语练习教材,1978年在他创办的《国语日报》社,又再次亲自校订编印了全文注音的《国家至上》剧本,以为《国语日报》社语文中心国语教师教学之用。[18](PP.156-160)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本教材的阅读范围,但以《国语日报》社及其语文中心在彼时对国语推行上的重要影响,当有不少学习者得以在戒严时期(1949年5月至1987年7月)的台湾一睹难以得见的抗战戏剧剧本。 抗战戏剧在战后初期的台湾,因介绍祖国文化、学习国语中文、沟通军民情感、推动台湾剧运的需要而引进,四年间共计有欧阳予倩、老舍、宋之的、陈白尘、吴祖光、杨村彬、张骏祥、夏衍、于伶、陈铨、阿英、徐昌霖、沈浮、严恭、石炎、吴铁翼、陶熊、顾一樵、朱双云、周彦等20位剧作家的23部作品在台湾演出。 这些深具“彼时彼地”色彩的抗战戏剧作品,对于欠缺共同历史生活经验、文化语言尚有隔阂、民族认同尚待凝聚的台湾人而言,缺乏“此时此地”思考的演出是较难被接受的,以致观赏者过大比例集中在台湾的外省籍人士,完全达不到原来被当成文化宣传利器的目的。 1949年因“戡乱”需要,许多抗战戏剧因作者政治立场问题而无法在台湾演出,得以演出者也必须敏锐地呼应现实而对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与重新诠释。来年,两岸局势底定,因剧本荒之故,抗战戏剧除了《野玫瑰》《密支那风云》《桃花扇》《结婚进行曲》《文天祥》等旧本重演之外,另有根据旧本略加改编,把抗战意识改为“反共抗俄”意识并更改剧名的情形。[8](P.95)另,未曾在台湾演过,来台剧人张英于抗战胜利初期所写的抗战戏剧《春到人间》,也曾于1950年以《恼人春色》之名演出。(41) 1951年起台湾剧运进入“反共抗俄剧”时期,随着剧作家、剧作越来越多,抗战戏剧几已不见演出,至此,《野玫瑰》以《天字第一号》等影剧作品形式持续为台湾人喜爱,并掀起了一阵谍报片风潮,《国家至上》也因被编作国语教材而能为台湾人持续认识。 抗战戏剧在战后四年集中压缩于台湾演出,时间虽短,但影响不小,对于中国优秀剧作的在台展示、两岸隔绝后外省青年剧作家写作思维的影响、话剧演员队伍的建立等,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尤其是在两岸隔绝半个多世纪之后,两岸戏剧交流史研究还未见明显成绩之时,此时对于抗战戏剧在战后初期台湾演出的回顾与分析,当有助于戏剧学界进一步的合作与议题开拓。 ①此分期概念参考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台湾新剧发展史》。 ②《民报》,1946年1月7日。 ③《民报》,1946年3月28日。 ④《自强报》,1946年12月31日;《民报》,1946年10月14日。 ⑤《和平日报》,1946年12月19日。 ⑥《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9日。 ⑦关于该会的讨论,可参阅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9)》(台北:麦田出版,2007年)一书第三章“传媒统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 ⑧《中华日报》,1947年1月4日。 ⑨《国声报》,1947年2月13日;《台湾新生报》,1947年2月11日。 ⑩1947年2月27日因查缉私烟失当而引发的台湾民变,其根本原因为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诸多不当措施所累积的民怨所导致,后随着军队来台镇压,加上绥靖、清乡,终使“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的政治禁忌及之后岛内省籍摩擦的重要源头。 (11)《和平日报》,1946年12月20日;《国声报》,1947年1月6日。 (12)《民报》,1947年1月20日。 (13)《中华日报》,1947年1月20日。 (14)《台湾新生报》,1948年1月1日。 (15)《全民日报》,1947年10月16日;《和平日报》,1947年10月20日。 (16)《华报》,1948年3月8日。 (17)《全民日报》,1947年10月26日;《和平日报》,1947年10月28日。 (18)顾一樵之《岳飞》原作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有自印单行本行世。1939年底顾一樵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戏剧学校演出而改写此剧,并于来年4月首次搬上舞台(导演杨村彬),因改写扩充幅度颇大,现实针对性更为强烈,且此时为首次舞台搬演,故仍将此戏列入本文之狭义抗战戏剧之列。 (19)《民声日报》,1948年1月4日。 (20)庄曙绮:《台湾战后四年(1945-1949)现代戏剧的发展概况》,第246页。改编自陈铨《野玫瑰》的电影《天字第一号》,1946年底由中电三厂出品,编导屠光启,主演欧阳莎菲。 (21)《和平日报》,1949年2月26日。 (22)《天南日报》,1949年3月21日。 (23)《“中央日报”》,1949年7月25日。 (24)《“中央日报”》,1949年9月6日。 (25)《华报》,1949年8月22日。 (26)《“中央日报”》,1949年9月20日;《华报》,1949年9月18日。 (27)《华报》,1949年10月13日。 (28)《华报》,1949年10月28日;《华报》,1949年11月6日。 (29)《华报》,1949年12月12日。 (30)1949年4月6日军警大规模逮捕省立台湾师范学院及台湾大学宿舍学生的镇压行动。一般认为,“四·六”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滥觞。 (31)台湾地方当局于1949年11月公布需查禁的“反动”书刊,其中戏剧音乐类包括沈浮《戏剧手册》,师陀、柯灵《夜店》,陈白尘《结婚进行曲》,宋之的《新歌选集》,文庞选《话剧选》,郭沫若《南冠草》《屈原》《棠棣之花》《虎符》,贺敬之《白毛女》,马思聪《祖国大合唱》,郑君里《角色的诞生》,洪谟、潘孑农《裙带风》,董林肯《表》等。 (32)徐亚湘:《战后初期中国剧作在台演出实践探析》。 (33)田进的说法是:“我拿一九四一年春来做分界线,不仅由于那是抗战期中的一个转折点,即以剧运本身来说,战地演剧的减退,后方大都市营业演剧的兴起,戏剧审查的加严,市侩主义的勃发,都是从这一年开始,或从这一年种下根苗的。”转引自洪深:《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第137页。 (34)《中华日报》,1947年1月17日。 (35)《公论报》,1948年11月14日。 (36)《天南日报》,1949年3月25日。 (37)《华报》,1949年8月26日。 (38)《华报》,1949年10月28日 (39)《华报》,1949年8月21日。 (40)1964年台湾万寿影业出品的谍报电影《天字第一号》,同时发行国语、闽南语两版,导演张英,编剧杜云之,主演柯俊雄、柳青、白虹等。 (41)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第371页;林黛嫚:《李行的本事》(三民书局,2009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