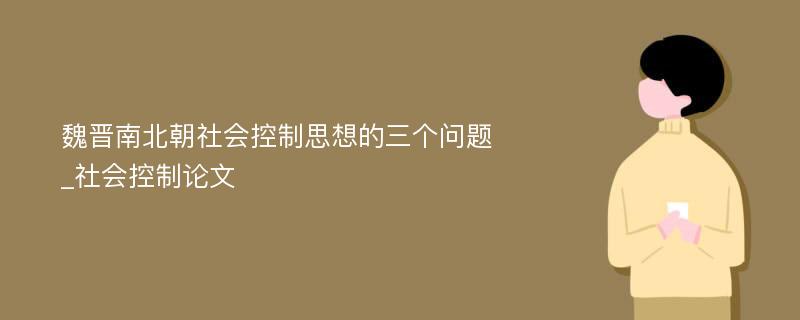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社会控制思想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04)06-0030-06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其复杂的社会现状和众多的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由于魏晋南北朝社会结构和社会环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政治、思想上权威真空的存在,使得人们提出的社会控制方案形形色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控制思想必将加深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特征的认识,同时拓展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一、对统治阶级的不道行为加以匡正和制裁的主张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各民族先后建立过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政权,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多则数十年,少则仅数年。同时,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据大略统计,这一时期共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约五百余次[1](P7),战争和动乱主要根源于统治阶级的极度腐朽和内部的纷争。战争和动乱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形成的正常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时代被打乱;封建统治者各种丑恶现象纷纷展示于这一时期;各种人间悲剧集中上演于这一时期。因此,制止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纷争,就成为有识之士提出社会控制方案的主要目的。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思想解放浪潮的高涨,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固有伦理道德观念,因而在提出社会控制方案时,往往会大胆地涉及一些思想禁区。基于当时统治者之昏庸无道给社会带来无穷灾祸的现实,一些士人勇敢地提出对统治阶级的不道行为加以匡正和制裁的社会控制主张。
1.“上息欲”
“上息欲”,即统治者停止纵欲。这是西晋人傅玄针对统治阶级的腐败而提出的匡正主张。傅玄生活的西晋社会,呈至上而下的腐败风气。开国皇帝司马炎荒淫无道,后宫将近万人;士族官僚则奢侈成性,夸豪斗富,胡作非为。为匡正世风,清明社会秩序,傅玄提出了社会控制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上息欲”。傅玄看到当时国君贪欲无度,引起上行下效,“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傅子·检商贾》,载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华书局本),这种无节制的欲望已经达到任何东西都无法填满其欲壑的程度。傅玄认为,财物是有限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统治者不“息欲”的话,社会动乱,国家败亡就在所难免。要想社会安定,秩序正常,唯一的办法就是“上息欲”。只有统治者抑制、停止自己的贪欲,社会风气才会质朴。傅玄的社会控制思想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所以,它虽然切中时弊,但注定不会被统治者所采纳。
2.“废昏立明”
废昏立明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我调节、自我整合和自我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这个观念早已有之,但它在魏晋南北时期的社会控制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汉末以至南朝,政坛上不断上演着异姓废立和同姓废立的闹剧,它不仅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不断冲击着谶纬神学宣称的“君权神授”论,于是思想界产生了以东晋人鲍敬言为代表的激进的“无君论”思潮。但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君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对统治阶级内部秩序进行有效的控制,通过强力干预和制止内部混乱和矛盾,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废昏立明”就成为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社会控制思想。南朝沈约通过其所著《宋书》史论,对此作了集中的论述。
作为统治阶级集团的主要成员,沈约看到并反感“昏君”们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于是极力主张“废昏立明”。沈约认为,自三皇五帝以来的改朝换代史,就是一部废昏立明史,废昏立明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程序。基于这种思想,沈约激烈抨击东晋末年腐败的政治,盛赞宋武帝刘裕乘“晋道弥昏”之机而建宋朝之举,说这一废除昏君之义举,功劳超越前代那些楷模。(《宋书》卷三《武帝纪下论》)同样,沈约也强烈谴责刘宋历代昏暴之君。依沈约之见,如果国君昏暴,其行为超越了地主阶级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引起社会剧烈冲突,使社会秩序混乱,带来统治危机时,统治阶级理应废昏立明,以避免人民造反推翻暴君或社会动乱无序时给整个地主阶级利益造成更大的危害,从而尽快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常态。
从整体上看,昏君的统治给人民带来加倍的苦难,对社会进步造成严重的阻碍,因而“废昏立明”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这种观念凸现于南朝,也是时人习惯了自晋室南迁以来“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政治格局的缘故,(《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王弘传论》)它是东晋门阀轮流执政和南朝国君废立更替频繁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这一时期为解决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地主阶级进行社会整合和控制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运作方式。
二、开明和具有远见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理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交织的时代。这一时期,北方、西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氐、羌、羯、鲜卑、乌丸、高车、柔然等,他们大都散居于汉族政权周边,过着游牧部落生活。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各地豪强纷纷招引边境各少数族人民内迁,以弥补兵源和劳动人手的不足。同时,边境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举族内迁,由此形成这一时期“华戎杂错”的局面。汉族封建政权及豪强地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奴役和剥削,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之间的种种差异和隔阂,致使民族矛盾十分复杂尖锐。西晋灭亡前后,一些少数民族豪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十六国政权时期,民族压迫和歧视十分普遍,而被压迫民族又总是联合起来反抗压迫民族的野蛮残暴统治。此外,南北政权双方又都自诩正统,互相攻伐,战争的民族特性十分明显。
民族斗争只是中国古代民族问题的一个方面。民族问题的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即是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主题是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实现封建化,这在习惯上被称为汉化。到南北朝末期,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已基本一致,民族融合得以实现,其产物就是隋唐时期的新汉族及辉煌的隋唐文明。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交织的形势不能不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用什么眼光去看待如此壮观的民族迁徙、民族斗争、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等纷繁的社会变迁景象;用什么手段去对民族关系如此复杂的社会进行整合和控制,这些都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控制思想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西晋末年,江统在《徙戎论》中,基于“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见解,曾建议朝廷以迁徙关中氐、羌族人民回归故土的办法,解决因华戎杂居共处后带来的社会问题。(《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但永嘉之乱、西晋灭亡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行不通。因此,后世极少有如江统那样来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了。随着这一时期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看法已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相当普遍,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呼声开始高涨,这不仅在南北朝双方频繁的通使活动、经济交往中可以看出,而且也普遍地体现在时人的观念中。
首先,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既成事实,主张缓解南北政权的矛盾。如梁武帝就认为梁与东魏和好,在一些事情上不必斤斤计较,区分彼此。(《北史》卷四十七《阳尼附阳斐传》)北魏荆州刺史李崇为避免“边人失和”,曾向孝文帝建议将抓获来的南齐人送还。(《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沈约则更为细致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以羁縻和防御为主,而非战争。在《宋书·朱龄石毛修之傅弘之传论》中,沈约指出:自晋室南渡后,中国南北分裂的局势就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南北政权各有其行政区域。所以对待异族政权最好是采取“羁縻”的方式,距险闭关,以抵御其寇暴。在《郑鲜之裴松之何承天传论》中,沈约进一步认为,治边之术不在攻伐,而在于修好边塞的防御工事,谨慎地守卫险要之地,这样才能“禁暴止奸,养威攘寇”。
其次,反对民族仇杀,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惟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孝文帝更是强调推诚心以待异族。他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齐纪》八)南朝齐崔庆远曾对孝文帝说:“和亲则二国交欢,生民蒙福;否则二国交恶,生民涂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六)沈约也主张对少数民族施行仁政,避免滥杀无辜。(《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论》)以上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及少数民族对民族关系的新看法,它是这一时期具有进步意义和时代特色的社会控制思想,也是即将到来的南北大统一时代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从玄、佛、道思想的角度为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出谋划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利益集团大分化和大改组,社会人口空前大流动,民族关系空前大变动等等社会现象,无不冲击着思想文化领域,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汉文化同域外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给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吹进强劲的新风。而社会的无序状态、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又给思想领域留下一大片空白,刺激着形形色色社会思想的产生和裂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无序的社会应如何整合?怎样有效地实施社会控制手段?理想的社会应是什么模式?这些问题在困扰和刺激着社会各阶层人士,促使他们去关心、思索、探讨、研究和论证,结果是儒学在艰难中恢复和发展,其伦理济世之学仍是这个社会的精神支柱;魏晋玄学异军突起,其宇宙本原之学使“天人之际”这一古老的命题得到了本体论的发挥;佛教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它的融入使中国传统思想平添几多思辩色彩;道教通过改革增加了活力,蔚然成为独树一帜的本土宗教。此外,刘劭的《人物志》、钟会的《四本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鲁褒的《钱神论》、裴頠的《崇有论》、杨泉的《物理论》、鲍敬言的《无君论》、范缜的《神灭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各种思想和学术风云际会,互相激荡,又与儒、玄、佛、道交相辉映,从而使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思想呈多元、异彩的景观。
1.名教之治还是顺其自然?
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潮的主流是魏晋玄学,而“名教自然之辨”则是魏晋玄学的主题之一。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审视,这一主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手段问题。怎样对这一时期混乱无序的社会进行控制和整合?如何使封建社会呈正常运行状态?是以儒家名教为治呢,还是奉行道家之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这成为当时社会整合和控制方案不可避免的话题。
其一,何晏、王弼倡言“名教本于自然”。
魏晋南北朝社会问题中最突出的是纲常名教的社会地位受到怀疑和挑战。自儒学定于独尊以来,统治者无不以名教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儒者也无不“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故而名教的社会地位本不成什么问题。然而黄巾起义以后,东汉瓦解,儒学独尊的地位被动摇,名教已难起到维系统治秩序的作用了。要继续以纲常名教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就必须用新的理论为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作新的论证,而魏晋玄学的兴起恰恰迎合了这个时代的要求。在探索新思想的过程中,曹魏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何晏、王弼抛弃两汉哲学的神学目的论的思维模式,以思辩的方法研究关于物质世界的本体问题,从而建立了“贵无论”玄学。其“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成者也”(《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而作为“万有”之一分子的“名教”,当然也是本于“无”,也即本于“道”,本于“自然”了。这样,何、王就在“以无为本”的“贵无论”基础上,阐述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名教本于自然。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调和儒道,明确了既不抛弃名教,又要坚持“贵无”原则。名教与自然在原则上一致起来,名教的尊崇地位得到重新证明。何、王之以“名教本于自然”论为儒家正统进行辩护,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何晏、王弼活动于司马氏与曹魏争权夺利斗争白热化之际。此时,司马氏不臣之心路人尽知。作为曹魏新贵,他们竭力要维护君权,伸张名教。他们觉察到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曹魏的皇权十分堪忧,他们必须为曹魏皇权的合理性作出论证。首先,他们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合理的。论据是,认“有生于无”的根本法则出发,既然“自然”或“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那么,由此而形成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他们认为君主专权具有合理性。论据是,“无”是天地万物唯一的本源,即是说,是“一”造就、制约和统率着万物。万物虽众,但可以执一以统御之,这就叫做“执一统万”。以“执一统万”之道来考察社会,社会人民众多,君主只有一人,众与君的关系即“一”和“万”、或“一”和“多”、“众”和“寡”的关系。按照“执一统万”的法则,“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参见王弼:《老子注》第32章、《老子指略》、《周易略例·明象》)君主是人世间的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是“至寡”,是“一”,因而能够治众。所以君主专制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如果让司马氏集团的势力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曹魏君权覆灭。而名教恰恰强调君臣名分,伦常秩序,特别有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和稳定。所以曹爽集团的玄学家们还得借助名教的尊严来规范司马氏的不臣之心,进而实施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其二,嵇康、阮籍高倡“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阮籍处于易代前后的魏晋之交。他们将“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一变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推进这一演变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沿思维发展的规律探寻,何、王提出的“名教本于自然”这一理论本身就以自然为主、为本,名教为次、为末,即肯定了自然高于名教,强调了不忘根本。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正始之音中“名教本于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司马氏出身经学世家,自诩以名教治天下,动辄引经据典翦除政敌,屠戮异己,这就使其宣扬的名教显得那么虚伪。于是,在嵇、阮心目中,名教与自然水火不容,再也不能融为一体了。嵇康借《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自己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心迹。他自陈性情疏悚傲散,与礼法相悖,又因研读了老庄学说,使这种放逸的性情更加浓烈,故“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根本无意步入仕途。接下来,他用尖锐的言辞陈述自己有“必不堪者七”,即不愿遵守礼法,蔑视虚伪名教;“甚不可者二”,即“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和“刚肠嫉恶,轻肆自言,遇事便发”。这实际上是公开反对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号以篡曹的行径。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取天下的,周公以辅佐大臣身份而秉国政,孔子盛赞行禅让的尧舜,这些都是司马氏在改朝换代时所寻找的先圣范例和根据,故嵇康加以强烈的鄙薄和坚决的否定。在《答难养生论》、《太师箴》、《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等文中,嵇康把无为、自然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义无反顾地抛弃名教,高倡自然,并以生命为代价与司马氏的名教抗争,书写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悲壮篇章。阮籍则对虚伪的礼法之士予以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抨击,说这些官爵利禄齐全,自鸣得意,有所谓“高致”美行的“士君子”,如同“群虱死于裈之中而不能出”。他甚至比嵇康更激进地提出“君臣礼法致乱”论,认为无君无臣时,天下安定;有君有臣时,暴虐兴起,这是人类最大的灾难。礼法是“君子”用来束缚下民、愚弄百姓的东西,是“天下之贱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传》)这无疑是对名教的核心——君臣名分的彻底否定。
其三,郭象论证“名教即自然”。
西晋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东汉以来旧世家的统治得以恢复,门阀制度开始确立并日趋巩固。世家大族通过“九品中正制”获得了世代做官的政治特权;通过“户调式”又获得占田、荫族、荫客方面的特权。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寄生的本质和世家大族奢侈豪华的传统所致,西晋社会风气从一开始就十分败坏,官场处处溃烂,士风日益沦丧,完全没有新王朝应有的进取和活力。然而腐败的现实政治却极需纲常名教来维护,而名教的社会地位在经历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论的冲击后,必须重新得到证明并加以定格,这样,郭象的玄学应时而生。
郭象继承和发展了向秀《庄子注》的思想。他从“独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万物都是自然产生,没有什么真宰使之然。无不能生有,物各自生。无论以自然为本还是以名教为本,都不符合万物独化的法则。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引伸出“名教即自然”的命题。将此论推而广之,“有为”即是“无为”,“山林”即是“庙堂”,“外王”即是“内圣”,“周孔”即是“老庄”。这样,名教与自然完全合流。肯定名教之治即是自然之理,论证名教之治的天然合理性的理论在门阀制度业已确立的西晋是适时的、实用的,它为世家大族既占据高位、享受特权,又要附庸风雅、标榜清高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因为按照郭象的理论,门阀世族虽然过着世俗的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是清高绝俗的。他们身虽处庙堂之上,而心却在山林之中。名教即是自然。名教中自有乐地,逍遥放达不必超越礼法,背离传统;适情任性勿须隐逸山林,远离世务。“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岂有背俗而用我哉!”(郭象《庄子·逍遥游注》)郭象就这样用明显有悖于《庄子》原文观点的方法,凭借他那高超的哲学思辩能力,完成了关于名教的社会地位的哲学论证,结束了“名教自然之辩”。至此,玄学家以儒道结合,实施社会控制的方案遂完整出台。
2.佛、道二教的社会控制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佛、道盛行。二教从宗教理论的角度阐明了其社会控制思想,一方面,欲匡正统治者的残酷好杀行为,保护僧俗士众,为佛教的发展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为统治者进行社会控制出谋划策,以求获得统治阶级的亲睐,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西域僧人佛图澄看到十六国时期的汉统治者刘聪父子、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等以残暴好杀为能事,甚至连出家人也多受其害的情况,为制止统治者的暴虐行径,往往以佛教慈悲、报应等教义来感化统治者,以求保护僧俗,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石勒当政时,他劝石勒行德政。石虎询问什么是佛法,佛图澄说:佛法不杀。石虎问他,自己是天下之主,如果不用刑杀就不能安定天下,现在已经违背了佛法戒杀的教义,还能获得幸福吗?佛图澄说:帝王事佛,主要表现为对佛法的恭敬、顺从,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而已。至于那些凶愚无赖之人,是难以改变其本性的。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绝不可以肆意暴虐,滥杀无辜。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是倾尽财物服事佛法,也不能解除殃祸。佛图澄的这番告诫,石虎虽然不可能全部顺从执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的暴虐(《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
东晋高僧道安从佛教的人生观出发,认为当时社会和人生苦难,根源于人类具有贪淫、嗔恚、愚痴三个特性,但是人们却浑然不知自己的处境,不知道由于贪、嗔、痴所引来的并不是嬉乐,而是苦难和祸殃。如果不冲破“贪囹”、“恚圄”、“痴城”的禁锢,就不能杜绝社会问题的产生。由此,他提出了具有佛教特色的社会控制方案。他认为,如何根除人之贪淫呢,可以用禅观的方法,教贪色的人把美貌女子,从她的青春一直想到老丑以至死后的尸体,化为骷髅、残骨,这样一来,色淫之心就会消失。如何根除人之嗔恚呢,可以教人生起慈、悲、喜、舍四心。慈者,与众生共乐;悲者,欲救济众生之苦;喜者,见众生离苦而庆悦;舍者,无亲无疏平等相待。这样一来,社会冲突就会消泯于无形。如何根除人的愚痴呢,可以用“四空”之法对症治之。四空是佛教十二门禅中的四定。因为愚痴把世界看成实在,所以,要破除愚痴,就要做到“四定”:第一,空无边处定,即去掉一切物质现象之想,把心集中在无边的虚无境界。第二,识无边处定,即去掉了“空”想,把心集中在内识上。第三,无所有处定,即去掉了“识”想,把心集中在无所有处。第四,非想非非想处定,即没有了晋通人的心思,其所思所想已与佛教理念一致。通过四定的修养,即可达到无苦无乐、心思寂静的状态,愚痴之心也就化解于无形之中,一切社会冲突和人生苦难也将不复存在。(《十二门经序》)
此外,佛教还宣扬“因果报应”、“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说教,其最终目的虽然是让人类脱离世俗社会,达到“涅槃寂静”的境界,但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佛教的社会控制思想是适用的,它可以被利用来解释当时社会极不合理的现状,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作论证;也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去统治、麻醉和欺骗人民,使其忍受现实痛苦,恪守封建社会道德规范,俯首听凭统治者奴役和摆布,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控制的现实目的。南北朝学者颜之推曾在《颜氏家训·归心》中,谈到佛教这种强大的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他宣扬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能够起到教化民俗的作用。刘宋时何尚之也对宋文帝说,如果百家之乡有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厚谨慎。千室之邑有百人修“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正见),则百人温和厚道。若佛教教义之传播遍于天下,那么编户齐民千万人中就会产生仁人百万了。人们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那么天下就不会再用刑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皇帝即可坐致太平。(《弘明集》卷十一《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这就把统治者对佛教有助于社会控制的看法准确地表述出来。
道教主要借助神仙的力量来进行社会控制,这最为典型的反映在东晋道教徒葛洪的思想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不少人认为通过服用药物或养生之术可以长生,但对不死成仙多持怀疑态度,有的人甚至根本不信世上有神仙。葛洪则认为神仙是存在的,只是人的感觉器官不够灵敏和感觉经验有限的缘故,不能判断神仙的有无。其实,神仙的威力无穷,它对社会和人类具有非凡的、无限的控制能力。他列举了种种社会问题,如憎恶好杀,口是心非,犯上作乱,知恩不报,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室,害人之身,夺人之位,取人之爱,掳掠致富,不公不平,凌孤暴寡,不敬师长,败人苗稼,损人器物,短斤少两,以伪杂真,诸如此类恶行,说凡犯以上一事,就是一罪。神仙中的“司命道人”控制着人的性命,它会根据人所犯罪程度的轻重对其生死寿夭施加影响,即“小者夺算”和“大者夺纪”。人若要想长生不死,就既不能有“恶心”,更不能有“恶迹”。葛洪正是针对人类好生恶死的本性,想通过他所构造的法力无边的神仙的力量,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规范,以求收到社会控制的实效。[2](P252-253)
以上三题仅仅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控制思想中的三个比较独特的方面。事实上,礼乐教化和刑法这两个封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传统手段仍然被普遍地提倡和使用于这一时期。通过礼乐教化可对社会进行积极性控制,引导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化解社会冲突;运用刑法可对社会进行消极性控制,制裁越轨者,使人不敢轻易逾越社会规范。礼乐教化和这种强大而全面的社会控制功能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不能忽视的。因此,即便是思想多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激进者如阮籍、嵇康、鲍敬言等,对于礼乐教化和刑法也并非是真正的友对,这是我们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控制思想时要注意到的。
收稿日期:2004-10-21
标签:社会控制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宋书论文; 郭象论文; 佛教论文; 傅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