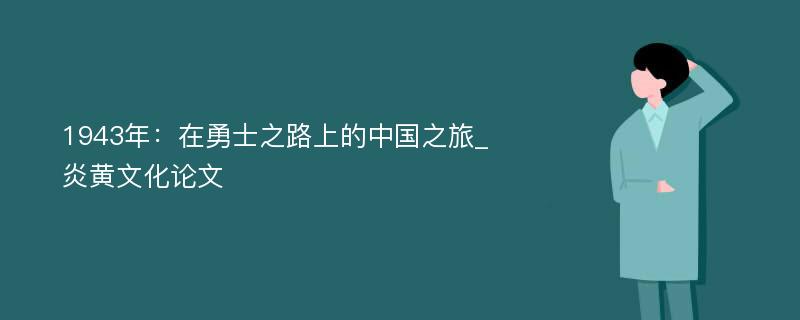
1943: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中国论文,小路论文,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无疑是给中国以最直接、最大影响的一位。他通过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和新村运动的倡导表现出来的和平主义精神和人类主义精神,经周氏兄弟的介绍和宣传广泛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如此,其新村理想还直接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新中国作为毛泽东的缔造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形的新村。总体看来,实笃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出从文学到思想、再到社会实践的综合性特征。
不过,除了1936年4月底去欧洲旅行途中在上海临时上岸与鲁迅、崔万秋、内山完造诸人会面之外,实笃的中国之旅只有一次,这就是1943年4月的中国旅行。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实笃已经由大正时代的和平主义者、人类主义者转变为“大东亚战争”的支持者。这种转变始自1937年前后①。就在开始中国之旅前一年的1942年5月,实笃出版了支持战争的代表作之一《大东亚战争私感》②,当月26日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实笃又被委任为戏剧文学部部长。不久,1943年4月实笃是作为官方派遣的日本文化使节团团员前往南京参加伪中日文化协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个人前往北中国和“满州国”以及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旅行。这样,作为一个曾经以和平主义思想·人类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日本作家,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阐明自己的战争观念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旨在以武者小路实笃的这次中国之旅为中心,探讨同一时期实笃的战争观与中国观这两个具有内在相关性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引文皆为引者翻译,“支那”一词为历史概念,从中国人的自称变为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有个历史过程,为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这里原文照录。
一 背景、过程与身份
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崇拜西洋、蔑视中国的时代,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武者小路实笃从1910年代开始却对中国怀有深切的关心,憧憬中国,希望到中国旅行。1938年4月他在题为《支那旅行的梦》一文中说:“什么时候能够一个人从容地在支那国内旅行,希望那样的日子到来。也许那是一个梦,不能变成现实,但支那的自然之美和人工之美是我崇敬的对象之一。”“不管怎样说,支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多有亲近感的国家,是那样令人憧憬之地”③。这种亲近感的形成一方面与《一个青年的梦》和新村运动在中国获得了众多知音有关,同时也与1936年在欧洲旅行的过程中曾经品味“黄种人屈辱感”有关。
实笃在表达这种渴望五年之后的1943年4月前往南京参加会议,“中国旅行的梦”终于变为现实。
伪中日文化协会作为汪伪政府的附属文化组织,是由褚民谊提议、于1939年在南京成立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文化部部长伊东隆治亦为核心成员之一。该组织名为“文化协会”,实际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身为发起人、并在该组织成立之后担任理事长的褚民谊是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常务理事中的江亢虎和陈群亦同样是汪伪政府的核心人物——江为考试院院长,陈为内政部部长。1943年4月第二届所谓“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申报》发表的“社评”也明确指出这一点:“老实说,现在的中日文化协会,政府人员多于民间文化人。”④该组织的文化人会员之中,则多有留日派。以樊仲云和张资平为例,樊为伪中央大学校长,张资平1941年担任该组织出版部部长和机关刊物《中日文化月刊》主编,二人均曾留学日本。巧合的是,二人均曾翻译实笃的作品⑤。这种人员构成的基本状况,表明了“中日文化协会”的非文化性和御用性。1941年开始发行的《中日文化月刊》,亦合逻辑地成为汪伪政府的御用刊物。汪精卫1943年的“元旦训词”《今年新国民运动之重点》,即同样被第三卷第一期《中日文化月刊》作为“特载”刊发。
1942年4月1—3日,伪中日文化协会曾在汉口举办第一届所谓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于整整一年之后的1943年4月1—3日在南京召开,一方面是按例行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配合汪伪政府所谓“国府还都三周年”的纪念活动。日本政府为了表示支持,向大会派遣了由十四位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界的名流组成的文化使节团,实笃即为团员之一。作为日本官方派遣的使节团团员前往南京出席汪伪政府的文化会议,意味着实笃这位二十年前的人类主义、和平主义作家完全被纳入了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关系之中,客观上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合作者。
不过,实笃的中国之行开始得并不顺利。使节团一行3月30日从九州岛北端的博多乘飞机飞往上海,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但是,实笃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发烧、痢疾无法按计划行动,独自留在了上海。休息、作画、购物,两天之后的4月2日下午才独自乘火车去南京。到火车站迎接的人把他送到讨论会会场“建国堂”的时候,讨论会已经在进行之中。根据会议记录,实笃仅做了如下简短的发言:
到上海后因身体不适,迟到南京,很为抱歉。此次来京,恐没有多少贡献,刚才听到各位高论极有意义。这个问题一时不能解决,要以后时行讨论。谈到此种政治经济问题,本人对日本并无贡献,对于中国当亦无贡献,如何能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孔子说,“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不能解决,恐千百年后更不易解决。本人是小说家,是一个空想家,对于新秩序的建设,希望中日两国共同合力迈进。我常想,一个人的生命如何使能不死。东洋思想是以生命为主,以之来建设将来的新秩序,一定可以成功的。⑥
4月3日上午是闭幕式,下午实笃应邀前往伪中央大学发表讲演,并于当晚应邀到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演。两次讲演的题目均为《东洋文化的一个特色》。在讲演中,他以中国南宋画家梁楷的作品为例,阐明东洋文化的优异之处,进而批判西洋人对东洋的轻视,说:“我并不是否定西洋文化,而是希望对于其最优秀者怀有无限的敬意,但是对于蔑视东洋文化者感到愤怒。尤其是对于在人种的意义上蔑视东洋人的无知者,同时感到可悲,产生憎恶之情。我们完全没有遭受侮辱的理由。在精神的深刻、宏大、美丽方面,恰恰是我们,拥有许多理应教导他们的地方。”⑦文化使节团团长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1878—1962),实笃仅仅是团员中的一位。他受到这样的重视,无疑与其曾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过巨大影响有关。在伪中央大学的讲演显然是樊仲云安排的。在4月4日下午的“挥毫会”(会议内容之一部分)上,实笃又当众挥毫,画梅花一幅⑧。身为日本人画梅花而不是画樱花或者其他什么花,大概是因为他理解梅花在中国人这里所具有的文化含义。
4月5日,实笃乘火车离开南京北上,开始了真正的中国旅行。途中先后停留徐州、兖州、曲阜、天津,最后到达北平。从北平去了大同,三天之后回到北平,应邀到伪北京大学讲演。4月18日上午参加庸报社主办的座谈会并与周作人见面,午后到厚士职业指导所参观,然后到八道湾周家拜访⑨。次日即离开北平前往伪满州国首都“新京”(长春)。自“新京”纵贯朝鲜半岛到达釜山,从釜山回到日本本土当在四月底、五月初。
在这次旅行中,实笃的身份呈现出二重性——作为官方派遣的文化使节团团员,同时作为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小说家。这种身份的二重性在南京会议上的简短发言中已经显现出来。所谓“尧舜都不能解决,恐千百年后更不易解决”,就是作为官派使节为日本的入侵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灾难开脱。因为这种发言是针对广东代表林朝晖的观点而发。在实笃发言之前,林朝晖针对日方代表谷口吉彦宣扬的“东方的灭私奉公主义”,指出中国民众认为战争影响了生活,强调“衣食足而知礼节,最先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日本是思想支配环境,而在中国是环境支配思想。”林朝晖与谷口吉彦的对立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私”与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公”的对立。面对这种对立,实笃用隐晦的表达否定了林朝晖对中国人生存问题的强调。不过,与此同时实笃又说:“谈到此种政治经济问题,本人对日本并无贡献”,“本人是小说家,是一个空想家”。在回到日本之后撰写的《支那归来(二)》一文中他明言:“在南京的大会上,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他人所期待着的那种期待。所以没有必要在会上发表了不起的意见,而且不过是一个陪衬演员式的装饰品,但对此也并无特别的想法。”此类发言意味着“使节团团员”这种公的身份并没有完全遮蔽实笃个人性的身份——即作家和文化人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伪中央大学和广播电台谈论文化问题,即成为确认自己文化人身份的一种方式。离开南京、北上旅游开始之后,实笃的行为具有了更多的个人性。文化人身份的自觉性规定着其旅行的内容。旅途中实笃特意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曲阜的孔庙(在兖州下车即为参观孔庙),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去孔庙是为了看孔子的墓、表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敬意⑩,去大同则是为了看佛像。这样,实笃的个人旅游成为“半儒半释”的“文化旅游”。在北平停留期间,其身份的二重性又一次表现出来。一方面,在庸报社主办的座谈会上,他声称“自从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我们日本文艺界同人,一致认为非彻底战胜英美不可,所以没有一个不努力从事活动。我本人也自以为是很努力在工作的。”但发言时间(包括讲客套话的时间和译者张我军的翻译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分钟。而与此同时,他在伪北京大学讲演的题目却是《作家的修养》,讲了两个小时,并在讲演之后表示“自从到中国旅行以来,今天的谈话最痛快”(11)。
二 中国认识与军营体验
对于武者小路实笃来说,第一次中国旅行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返回日本前后,即1943年4月至8月,他先后发表了六篇与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文章(12)。遗憾的是六篇文章均未收入小学馆十八卷本《武者小路实笃全集》(1987—1991年出版)。从这些文章中能够发现,实笃通过这次旅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实际感受,对中国怀有更大的善意。与1936年在欧洲旅行时黄种人的孤独感和屈辱感触发了他对于“祖国之可贵”(13)的认知完全相反,实笃在南京的会议上“没有来到异国的感觉”(14)。不仅如此,在《支那归来(二)》中他一再强调日本从中国蒙受的“恩”,说:“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大量摄取了支那文化,这是应当十分表示感谢的。”“从前就曾经感觉到,未曾意识到自己并不那样了解支那人。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自己人从支那蒙受了许多恩惠,有一种想报恩的感觉。”与此同时,他直接、尖锐地否定了日本人的“卑劣”,说:“拿出一元就想获得一元的报酬,拿出十元就想获得十元的报酬,好像是为了获得报酬而行动。那给我以卑劣之感。我希望日本人丢掉那种心态。”结合战争中日本政府对言论界的严密控制来看,能够发现实笃的此类发言所包含的政治批判意义。用“卑劣”的态度、怀着“获得报酬”的目的对待本应是“报恩”对象的中国——这可以看作实笃对同一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一种理解和描述。
不过,亲近感与报恩感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实笃通过这次旅游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文化隔膜。旅游结束、刚刚返回日本的5月3日下午,在东京帝国饭店召开的使节团归国报告会上,实笃直言:“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日本文化不被尊重。他们嘴上姑且说日本文化很精彩之类,内心里好象是觉得日本文化远不及中国文化。”(15)在随后撰写的游记中他又说:“在直接交谈中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对于日本文化这种东西支那人依然没有理解并且表示轻视。”“在这一点上,今后日本人有必要广泛地促使中国人反省,让他们知道日本文化中尚有更多、更优秀之物”(16)。“与支那人谈话,能感觉到什么地方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在发言”(17)。这种隔膜甚至体现在他与老友周作人的关系之中。实笃来中国开会、旅行之前周作人曾经去信劝阻。几乎是与南京的会议召开的同时周作人也往南方旅行,但二人并未安排见面,而似乎是互相回避着。实笃到达北京、参加庸报座谈会的时候,二人才匆匆见面。不仅如此,与实笃同行的哲学教授谷川徹三在南京会议上对周作人思想提出了批评,周作人得知之后大为不满。本来,1930年代中期之后实笃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是“东洋—西洋”的对立,中国和日本都被他纳入“东洋”之中,“西洋”对“东洋”的压迫构成了他支持“大东亚战争”的理由。现在,在他通过中国之旅发现了存在于“东洋”内部的“中国”对“日本”的轻蔑(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卑劣”)之后,其“大东亚战争”观就有了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
实笃是在中日战争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到沦陷区(日本占领区)旅行,因此他在切身感受中国的同时无法回避对于战争的感受。事实上,旅途中的日军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晚年完成的回忆录《一个男人》中,实笃依然记得在中国乘火车时看到的情景:“在南京我是一个人旅游。战后在火车中看到美国兵的时候,我就想起当时在中国的火车旅行。我们是免票乘坐火车一等车厢,但日本军人比我们还要耀武扬威。看到一个日本兵在车厢里旁若无人的态度,我感到羞耻。——如果再稍微收敛一点的话怎样呢?我因同为日本人而感到羞耻。我想,中国人看到那样子会更加不快。”(18)在将置身中国的日本兵与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士兵进行类比的时候,这种类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着对于日军行为“占领”本质的认知。这种认知显然不仅仅属于晚年的实笃,而且属于1943年在中国旅行的实笃。
旅途中更密切地接触侵华日军是在到达兖州的时候。到达兖州之前与军队方面取得了联系,所以实笃受到驻扎兖州的日军的欢迎,投宿军营,并且是由军车送往曲阜参观,当日往返。在战争状态下,一位知名作家作为侵略国的国民乘坐军车参拜敌国的文化圣地,这构成了战争年代一道讽刺性的文化风景。这道风景之中,包含着中日两国之间国家关系(交战国的矛盾性)与文化关系(儒教文化圈的同一性)的背离。前往曲阜参拜的前一天晚上,几位年轻的日军军官要听实笃讲话,来到实笃的房间。当晚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记录,但战争的话题应当是难以回避的。因为当时中日战争正在继续,谈话的一方是军人,而且,1938年4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激战、消灭约两万名日军的台儿庄战役的激战地就在兖州旁边。在实笃的《支那归来》中,涉及当晚的内容只有如下短短的几行:
在那里的下榻处发生了这样的事。五、六位中尉或少尉级别的人说是要听我讲话,到来的时候看到火盆里有一只小蝎子在爬,便用火筷子给压死了。不过,那种时候会有蝎子,我觉得稍微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想,要是别把那只蝎子压死、装在瓶子里带回来就好了。
这种表述中包含着对于生命的悲悯。对于曾为反战作家、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生命的尊严与平等的实笃来说,这种悲悯显然并非仅仅是指向死于火筷子之下的小蝎子。当晚实笃是否曾与年轻的日军军官们谈及战争、死亡等问题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但当晚的实笃具有自觉的生命意识是一个事实。结合刚刚结束的南京会议上中国代表对于中国人“生存”问题的强调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来看,实笃的这种生命意识显然是与南京会议上所说的“东洋思想是以生命为主”处于同一延长线上。
总体看来,《支那归来》与《支那归来(二)》这两篇游记中包含着自觉的生命意识、对中国的“恩”的强调以及对日本人的“卑劣”的否定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的互动有可能成为实笃重新认识“日中战争”之本质、重新认识中日关系的起点。这种可能性在随后创作的《三笑》中又一次表现出来。
三 《三笑》中的“中国”
1943年9月,即中国之旅结束四个月之后,实笃创作了赞美“大东亚战争”、鼓舞日本国民斗志的五幕剧《三笑》。“三笑”是取其与“三胜”的谐音(在日语中这两个词的发音完全相同),“三胜”的意思就是日军在陆战、海战、空战中均取得胜利。在剧本中,实笃借剧中人野村广次(盲诗人)的口发出呼唤:“亚细亚的民族哟!/合而为一/互爱/互助/创造一个大国/成为世界的栋梁!/建造和平的殿堂/谁都不能侮辱你/谁都仰慕你/的殿堂!”剧本10月7日在东京帝国剧场举行第一次公演,演出持续至11月间,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944年10月剧本由小山书店出版单行本。
一目了然的是,《三笑》的创作意味着实笃并没有因为中国之旅改变其支持战争的立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角色在《三笑》中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
“三胜”向“三笑”的转换,是借用中国典籍《庐山记》中“虎溪三笑”的典故。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法师送客以不过寺前虎溪为约,因过溪则虎啸。大雅堂以此为题材绘有《虎溪三笑图》。在《三笑》的第三幕,驼背画家野中英次与盲诗人野村广次将“东洋的魅力”概括为“无止境的快乐与纯真”,就是举《虎溪三笑图》为例。不仅如此,《三笑》公演之后实笃撰写了剧评《观艺文座的〈三笑〉》,剧评在新村机关刊物《马铃薯》(1941年5月创刊)1943年12月号上发表的时候,实笃不仅将《虎溪三笑图》印在这一期《马铃薯》的封面上,并且撰写短文进行解说。这样,本来是表现儒释道之和谐的“三笑”故事在实笃这里被赋予了“东洋”的意义。在剧本《三笑》中,“三笑”的典故之外,鉴真和尚也成为驼背画家野中英次鼓励盲诗人野村广次的根据,所谓“眼睛对于人来说实在是重要的,但尽管如此,失去了眼睛尚能表达精彩的感觉,令人吃惊。”
现代中国在《三笑》中是通过剧中人西岛次郎(身份为小说家)登场的。同样是在第三幕,西岛本应与画家野中一起到诗人野村家里去,但将要出门时有中国客人来访,洽谈翻译西岛作品的事(这种情节的虚构显然是基于实笃本人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的事实),西岛说来自中国的客人是必须接待的。谈及此事,野村议论道:“今后有必要与支那友好相处。那比什么都好!如果亚细亚各国互相理解、携手并进的话,天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希望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看到那一天。”对待中国的这种友善态度与剧本对美国人的刻骨仇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三笑》中,六十岁的驼背画家野中英次无力上前线,便诅咒美军,希望用自己的诅咒杀死美军。盲诗人野村广次也说:“如果剖腹自杀能够使美英灭亡的话,我想日本会出现许多剖腹的人吧。”小说家西岛次郎的儿子、立志参加日本陆军的西岛胜造,甚至对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出警告。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实笃曾经是战争支持者。一方面,他认为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拯救落后的中国,另一方面,他将中国看作应当受到惩罚的“东洋的叛徒”,赞扬汪精卫而批判蒋介石,并且期待着蒋介石“悔改”(19)。但是,在1943年创作的《三笑》中,这种对中日战争的支持消失了(或曰被回避了)。相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被从日本与英美的关系之中分离出来。这种情形的发生,应当与其通过中国旅行对中国“恩”的认知、对日本“卑劣”的发现有关。
日本战败不久的1946年3月,武者小路实笃因为曾经支持侵略战争而受到“公职追放”(开除公职)的处分,直到五年之后的1951年8月“追放令”才解除。不过,法律裁决不应掩盖实笃自身的复杂性。实笃由大正时代的和平主义者、人类主义者向昭和前期的战争支持者的转变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内容和情感内容。不言而喻,这种转变鲜明地打着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记,成为实笃确认自己“日本国民”这一身份的形式,但与此同时,转变本身也折射出了近代以来西洋与东亚、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复杂关系。19世纪以来欧美列强以殖民者的身份对东亚的大规模入侵是一个历史事实,19、20世纪之交日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胜利又被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作为鼓吹“黄祸论”的重要根据。“黄祸论”并非仅仅是针对日本而言,而是将中国和日本一视同仁。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实笃的“支持战争”具有了必然性。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实笃战争观的分裂即显现出来。唯一的一次中国旅行促使他将日中战争从日本对英美的战争中分离出来,并且通过这种分离达到了对日本的有限批判和对中国价值的肯定。这是武者小路实笃与林房雄(1903—1975)、佐藤春夫(1892—1964)等同样支持“大东亚战争”的日本作家的不同之处。但是,悲剧在于,在当时的背景上实笃的战争观无法获得现实性。历史事实是,“黄祸”首先是发生在黄种人内部——即发生在东亚社会内部。日本与英美作战不是为了将东亚国家从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而是为了使自己变为新的殖民统治者。与此同时,恰恰是美国成了中国抵抗日本入侵的同盟国,中国是借助美国的力量提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中战争从“大东亚战争”的分离完全是一个虚构,实笃对中国的善意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中无法获得现实性的意义。实笃将自己称之为“空想家”,这种自我认识不幸地成为事实。
注释:
①关于这种转变,日本学者大津山国夫在小学馆版《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十四卷的“解说”中举实笃《日本人的使命之一》(发表于《改造》1937年8月号)一文为例进行了论述。
②短论集,河出书房1942年5月20日初版。
③原载1938年5月1日《日本评论》13卷6号,引自《武者小路实笃全集》十五卷36页。小学馆版。后同。
④1943年4月1日《申报》第二版。
⑤张资平翻译的《不幸的男子》收入翻译短篇小说集《压迫》,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部1928年出版。樊仲云翻译的《桃色女郎》和《某日的事》分别发表于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15卷第6期、8月10日同刊15卷第8期。
⑥见《中日文化月刊》第3卷2、3、4期合刊。1943年4月出版。
⑦该讲演稿在实笃归国之后发表于《马铃薯》昭和十八年(1943)六月号。同年六月一日出版。
⑧4月5日《申报》有消息,题为《京文化团体茶会招待出席文协会代表》,副标题为《褚部长蔡大使当面挥毫武者小路实笃画梅花一枝》。
⑨这一天的行程见于周作人的日记。据周作人日记手稿。
⑩实笃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专文论述的问题。发起新村运动之前的1910年代中期实笃就曾认真阅读《论语》,1933年出版了《论语私感》(岩波书店),1941年又出版了《孔子》(讲谈社)。
(11)参阅以斋(张我军)《武者小路实笃印象记》。载《艺文》1943年8月号。张我军曾在实笃到达北京之际前往车站迎接,并在庸报的座谈会上担任翻译。
(12)这六篇文章分别是:1.《和谐的空气——回顾中日文化大会》,《朝日新闻》1943年4月21日;2.《支那旅行归来》,《改造》第25卷第6期,1943年6月1日出版;3.《东洋文化的一个特色》(讲演稿),《马铃薯》1943年6月号;4.《支那旅行》,《日本评论》1943年7月号;5.《支那归来》,《马铃薯》1943年7月号;6.《支那归来(二)》,《马铃薯》1943年8月号。下文出自这六篇文章的引文只标篇名。
(13)关于实笃在欧洲旅游时体验的黄种人屈辱感,可参阅其随笔集《湖畔的画商》。甲鸟书林1940年出版。
(14)《和谐的空气——回顾中日文化大会》。
(15)见1943年5月4日《朝日新闻》第三版的报道。
(16)《支那归来》。
(17)《支那归来(二)》。
(18)《一个男人》191章。《武者小路全集》第十七卷267页。
(19)参阅《支那事变》和《战争》二文。二文均发表于1938年1月1日《日本评论》第13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