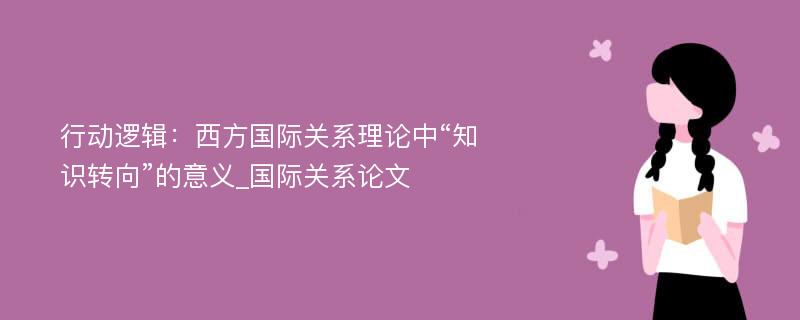
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逻辑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际行为体行动的逻辑。过去50多年里,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讨论的是实在性原因因素。以美国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试图发现一个单一的、最重要的因变量,用以解释国家行动的原因,比如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主流理论之间的论争往往集中在哪一个单一原因因素更具解释力,实证研究也多是验证这些变量中哪一个更符合客观事实。但是,如果从这些具体变量上升到知识概念,就会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实在性因素背后的知识结构是什么?知识和行动之间是否有着重要的关联?什么样的知识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上述问题指向一个不同于主流理论整体思路的研究议程。而这一研究议程表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经历了几十年对实在性行动原因的讨论之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即转向对知识和行动关系的关注。虽然这一转折还没有广泛应用于对具体国际事务和政策的研究,西方学者还没有意识到知识和行动的关系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所谓“他文化”以及“他文化”理论创新问题,但理论层面的讨论已经显示出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空间。从表象性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走向背景性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从理性主导走向实践本体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走向,也是最近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转向,笔者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的这种以知识为核心、讨论知识与行动关系的研究议程和辩论焦点称之为“知识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是探讨何种知识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力,而这将直接导向理论的文化建构问题。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种行动逻辑
行动逻辑指的是行动的原因机制。国际关系研究对于行动逻辑的论述受到美国三大主流理论的影响。三大主流理论之所以成为不同的理论流派,主要是因为每一流派都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单一的行动原因: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而建构主义则强调国际规范。近年来,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兴起,提出了不同的行动逻辑,使得国际关系研究从实在性要素转向知识性要素,从一种知识的一统天下走向对多元知识的重视。这种趋势就隐含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几种主要逻辑,即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建构主义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①和实践理论的实践性逻辑(logic of practicality)的发展进程之中。
(一)理性主义理论与结果性逻辑:利益决定行动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尤其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大,两种理论遵循的均是结果性逻辑。结果性逻辑的基本内涵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利益权衡。行为体是理性人,在面临决策情景时,能够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将手段和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理性地选取那些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目的的手段,即成本效益比最好的方式,并采取行动。但两种理论在什么因素决定行为体利益权衡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核心变量。
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选择”,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权力结构或曰实力分布是决定利益权衡的主要动因,亦即结构决定行动。美国学者华尔兹借鉴现代物理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系统提出了简约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现实,比如,华尔兹本人就认为两极更加趋于稳定,多极则更加趋于动荡,因为两极的确定性成分高,便于国家进行准确的理性权衡。②这种将体系内实力分布的状态与国家行动联系起来的做法,是理性因果论的典型代表,实力这种显见要素决定了行动者的利益权衡,因此也就决定了行动者采取什么行动。比如新现实主义框架内的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当国际体系中顶端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亦即当挑战国实力接近霸权国实力的时候,处于权力顶端的国家最容易采取战争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守成霸权国担心的是最强有力的崛起国的挑战,而崛起的挑战国也会认为自己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位置,甚至是霸主或准霸主地位。实力越是接近,权衡越是容易出现误差。双方根据各自的力量以及力量对比,认为或是误认为可以战胜对方,所以,发生战争的几率相当高。而当霸权国与挑战国实力有着明显差距的时候,国家采取战争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因为霸权国和挑战国都是理性行为体,都知道存在明显的权力差距,霸权国没有必要使用战争这种代价最高的工具,而挑战国明知若战必败,也自然不会使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选择”,认为国际制度决定利益权衡,亦即制度决定行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国家需要获得利益,获得利益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新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领军学者基欧汉一方面接受现实主义这一前提假定,另一方面则提出了以制度为核心的行动逻辑观,指出国际制度可以克服无政府性、促成国家采取合作行动这一论断。④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无法保障的: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裁判机构,国家为了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很容易采取欺骗行为,诱使对方采取合作行动,而自己采取不合作行动。各方均以此种理性进行权衡,结果只能是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之中,双方都无法获得最大的共同利益。新自由制度主义明确提出了国际制度这一变量,认为国际制度是解决这种困境的最好办法,因为国际制度为利益权衡提供了确定性很高的依据。交往双方依据国际制度行动,就会加大信息透明,减少交易成本,使合作成为可能。国家的理性权衡也很明显,如果依照国际制度办事,就会在交往中通过合作获得绝对收益;如果不依照国际制度办事,则会受到惩罚。即便不是即时的惩罚也可能会获得某种即时的收益,在其他领域和未来的交往中也会像信誉不佳的公司一样,给自己蒙上不可逃避的“未来阴影”,难以实现重大和长远利益。作为一个理性人,国家会以整体、长远思考进行权衡,为获得自我最大利益而遵守国际制度并且需要国际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加大获取利益的确定性。⑤
到目前为止,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行为逻辑,行动者采取什么行动主要来自利益权衡,决定利益权衡的或是体系结构或是国际制度。这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阐释的基本逻辑,也深刻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政策领域。
(二)建构主义理论与适当性逻辑:规范塑造行动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最后十年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选择”,国际体系文化范畴内的重要变量“国际规范”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议程。对于建构主义而言,行动逻辑是适当性逻辑。所谓适当性逻辑,就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对行动是否合乎社会规范的思考,亦即规范决定行动。虽然西方主流建构主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包括身份、认同、规范、文化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最成熟的研究议程是国际规范研究。建构主义认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会认同现有的规范结构和规则体系,采取与自我身份相符合的行动。长此以往,行动者会内化这些规范,从盲目服从,到学习内化,再到自觉服从。⑥温特讨论了国际体系的三种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身份是敌人,行动者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暴力的手段达到目的,因为霍布斯丛林的规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洛克文化中,竞争合作成为基本规范。国家是竞争对手,竞争包含了冲突与合作,但消灭对方已经不是目的,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是洛克文化的基本规范,所以,国家的适当行为是通过竞争与合作寻求发展。而在康德文化中,国家的身份是朋友,非暴力成为基本规范,一切暴力手段都不应当存在也不会存在,因为暴力不是朋友身份应该采取的行动。⑦当然,即便是内化,也是一个理性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其然到知其然再到不问其然的过程。⑧
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研究具体地反映了这种思路。⑨西方主流理论对规范传播的研究多是基于“好规范”假定,或者说是“好规范偏见”,即假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规范是“好”的,是可以促进国际生活向更加文明、更加先进的方向发展的。另外,这类研究还有一个隐含假定,即国际体系中落后的国家需要学习和内化这些“好规范”,以便使自己也进入文明社会的先进国家行列。⑩换言之,这类“好规范”提供了适当性行为的基本标准。一旦国际组织教会了后起国家或是后起国家学会了这类规范,他们的行为就具有合规范性;一旦这些国家内化了规范,他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就有了基本的依据:符合规范的就做,不符合规范的不做。行动是否符合规范成为是否采取行动的主要动因。
建构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国际规范研究以及适当性逻辑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研究议题。虽然也有学者批判“好规范偏见”,但规范研究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议程,而且在国际关系的政策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国际组织对规范传播力度的加大,跨国行为体对规范生产、传播和普及的高度重视等等。
(三)实践理论与实践性逻辑:实践引导行动
实践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之后不仅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最具活力的理论取向。(11)实践理论取向在国际关系领域最初显现于世纪之交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中,包括伊曼纽尔·阿德勒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和巴奈特主编的《安全共同体》。但当时的研究仍是在建构主义框架中进行的,研究议程也主要围绕建构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展开。2002年,国际关系理论期刊《千禧年》(Millennium)出版专辑,讨论了杜威对社会理论的影响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实用主义转向”,为实践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具有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使其开始脱离对建构主义的依附,导向了以实践为理论硬核的研究路径。(12)201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伊曼纽尔·阿德勒和麦吉尔大学的文森特·波略特主编的文集《国际实践》对实践理论做出了系统论述,成为这一理论系统化的标志性著作。(13)
实践理论突出的是“实践选择”,亦即实践引导行动。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实践性逻辑认为,实践活动本身是行动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实践理论学者对实践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实践是适当行动的实施。更加具体地说,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行动,这类行动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当性,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性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这类行动在物质世界中发生,也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14)在国际领域的实践活动也就被定义为“与世界政治相关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动”。(15)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规范思考使然,而是他们每时每日的实践活动使然。这种实践,就是与行动者资质相符合的日常行动。换言之,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都会发生作用,但两种因素的作用是在实践活动中结合产生并发挥出来的,物质和理念因素通过实践促成了行动。实践是物质和理念之间的桥梁,没有实践,物质不能产生意义,理念也无法成为行动。(16)
国际关系中的实践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将知识要素突显出来,使物质和理念因素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与知识类型密切联系在一起。行动者的知识是通过长期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亦即实践定义中的背景性知识,正是这一要素推动行动者采取某一种行动而非另外一种行动。比如安全共同体,这种非暴力的国际社会群体形态,不像制度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国际制度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个合作的约束性制度框架之中;也不像建构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好规范的产生、传播、内化使共同体成员完全放弃使用武力。实践性逻辑认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是共同体成员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共有知识和相互默契,使他们不会将使用武力作为一种行动选项加以考虑,也不会认为其他成员会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换言之,他们在处理彼此关系的实践活动中,自然而然地诉诸外交手段。(17)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日常实践互动中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实践活动。行动者也会进行理性的思考,但理性思考不会也不可能超出他们日常实践的范畴。
在实践中直接驱动行动的是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行动者对自己如何进行某种博弈的直觉把握,当行动者遭遇一个社会境域的时候,过去的经验就会被激活,呈现于现在,并自动地告诉行动者应该怎样去做。也就是说,行动者往往不是经过缜密的理性思考和理性设计之后才采取行动,而是更多地依靠过去的经验,瞬间将这些经验集中到当下的决策情景上面,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实践意识既不是单纯的结构性因素,也不是单纯的个体性概念,实践意识的形成是外部性内化和内部性外化的辩证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境域这一外部因素被摄入行动者个体的习性之中,同时,行动者个体习性这一内部因素被投射到社会境域中。在这种交集中产生了认识、判断、决定和行动。
实践性逻辑与结果性逻辑或适当性逻辑有着根本的不同。结果性逻辑的基本假定是行动者会采取收益最大的行动;适当性逻辑的基本假定是行动者会采取符合主导社会规范的行动;而实践性逻辑则是行动者会依照实践的经验采取某种行动。所以,结果性逻辑表述的是对目的手段反思后的行动,适当性逻辑表述的是对身份规范反思后的行动,而实践性逻辑则是未经反思的、由实践“自然而然”促成的行动,是从实践经验中自然流淌出来的。(18)即便行动者似乎是经过认真思考和理性权衡之后采取行动,这种思考和权衡也无法超越行动者实践活动的范畴。比如对待同样的事件,东方人和西方人所做的“理性”决定可能截然不同。简言之,现在所遇情景,激活内在习性,促成未来行动,整个过程是弱意识的自然反映,这就是实践性逻辑。
二、西方国际关系的知识转向:从表象性知识到背景性知识
上述有关“行动逻辑”的三种理论模式,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在讨论什么要素构成了行动的原因。但是,如果超越这些具体原因机制的范畴,就会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经历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后,出现了实践理论。这个过程使得理论构建一步一步地从理性思维转向人们的日常实践,从超然理论转向行动者作为社会人活动和习性的理论,即从表象性知识转向背景性知识。而这种知识转向才是新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深层意义所在。
(一)表象性知识与背景性知识
知识可以被分为表象性和背景性两类,(19)而对上述两类知识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行动逻辑的解读,也构成了知识转向的主要内容。表象性知识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型知识论观点,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表象性知识是人通过大脑的反思产生的知识,是思维和分析的结果,是强意识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统知识。(20)所谓表象,就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规律。所以,表象性知识被视为人通过理性思考之后对真实世界的真实写照,是普适性知识,是通则和规律。表象性知识不是来自具体的情景、不以具体地域和文化的经历为基础,而是来自理性人对世界的客观观察、抽象思维和真实再现。从定义上讲,表象性知识就具有普遍意义,不以地域环境文化等具体地方性要素为转移。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寻求普适性通则的做法,就是受表象性知识影响的集中体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象性知识的主导地位主要来自笛卡尔的二元主义以及因之产生的理性主义传统。(21)二元主义本体论的核心是二元分离,认为世界是由两种存在形态构成的,一种是“物体(things)”,一种是“思想(thoughts)”。前者指观察者所观察的对象,后者是观察者对所观察对象的理性抽象,所生产的知识也就是对客观世界、尤其是客观世界规律的重现。根据这种观点,世界分为现实的世界和知识的世界。知识的世界是由表象性知识所构成的。(22)正是人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分离、思想与物体的二元分离,以及人的灵魂或心智被赋予的超然能力,使得知识的性质被赋予重要的特征:知识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才能被生产出来,客观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反思才能再现出来。这种思想在知识生产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人以其超然能力进行抽象分析和思维,才能够生产出普适性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也必然是反思性和充满能动作用的。
与表象性知识不同,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背景性知识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的自然沉淀积累。背景性知识具有与表象性知识不同的特点。(23)首先,背景性知识是地方性的、具体的、自下而上的。由于行动者的行动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发生,背景性知识必然是地方性的,是在具体经历和实践中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人脑通过抽象思维产生的高度普适性知识。其次,背景性知识是弱意识的、高自发性的。也就是说,行动者在获取这类知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自然习得而来。第三,这种知识是弹性的,变化的。表象性知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寻求确定性,是发现通则性的恒定规律,确立探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背景性知识则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知识。由于它的获取是在具体的、地方的场景之中,所以,它也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情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24)
在国际关系领域,背景性知识的重要意义是由实践理论学者明确提出来的。实践理论借鉴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区分了表象性和背景性两类知识。实践理论从一开始就在研究中突出了背景性知识。2008年波略特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的学理性论文《实践性逻辑:一种安全共同体的实践理论》,不但区分了两类知识,而且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表象性知识的话语霸权地位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波略特指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注重反思性和有意识的知识(reflexive and conscious knowledge),忽视背景性和无以言明的知识(background and inarticulate know-how),这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根深蒂固的“表象偏见(representational bias)”。在批判表象偏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25)其后,阿德勒和波略特在《国际实践》中明确使用了“背景性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的概念,用以指代与表象性知识不同的知识类别。(26)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将知识的重心从表象性转移到背景性知识,并以背景性知识为行动逻辑的根本机制。
(二)知识与行动:行动逻辑的核心问题
根据上述知识的分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行动逻辑的论争便转换为:行动的主要驱动力是表象性知识还是背景性知识?这是知识转向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行动逻辑的核心问题。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在假定是表象性知识引发并促成行动。依据纳什均衡,理性驱动了行动,博弈双方都希望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最终只能达成一种次优结果。奥尔森也认为:当行动者是“理性人”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选取搭便车的行动,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收益。(27)现实主义将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认为权力的大小可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利益,权力计算直接涉及利益的权衡。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试图通过国际制度来解决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行为以便利合作,这被视为该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贡献。(28)新兴的实践理论转而强调背景性知识,明确指出背景性知识是促成行动的主要原因。关于背景性知识促成行动的重要意义,可以追溯到韦伯、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和图尔明及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布迪厄关于习性(habitus)的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习性是“持久的、可传输的性情体系,它每时每刻将过去的经历和行动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认知、判断、行动的坐标,使人们得以应对千差万别的情景”(29)。根据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当习性和场域互动时会产生一种引导行动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潜移默化所把握的明示或是潜在的游戏规则。实践理论继承了这一传统,强调行动者从自身在社会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不同于表象性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使得行动者能够自动地、不假思索地应对自己面临的情景、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是一种对事物前反思性的、潜意识的把握,是行动者通过长期浸沁于社会世界而从中获取的、无以言明的知识。
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表象性知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行动逻辑一直是围绕表象性知识范畴内的实在性因素设置研究议程。在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发展过程中,知识作为重要的因素却一直没有受到研究人员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由于理论界的思考被限定在表象性知识范畴之内,致使研究人员内化了表象性知识,自然而然地就范于理性思维定势,总是在表象性知识划定的边界之内寻找具体的原因因素,而对知识本身的性质及其对行动产生的作用不做任何质疑。从20世纪70—80年代兴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社会建构主义,再到新近发展起来的实践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表现出一个新的发展轨迹:对社会性、实践性、地方性的理论探索已经冲击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边界,也突破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理性思维定势。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行动逻辑”的研究正在从关注利益、制度、规范等可言明、可界定、甚至可量化的表象性知识范畴中的概念转向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无以言明的背景性知识。当对行动逻辑基本机制的认识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思路的变迁随即悄然发生。
三、知识转向与“他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转向已经发生,从目前的研究议程和理论形态上来看,实践理论学者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开始在主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但还没有形成像主流理论那样成熟的研究议程。而且,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存在,在学理上可以严格区别,在实际运作中却往往难以分离开来。况且背景性知识本身也充满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只注重背景性知识和适当行动的实施难以解释重大的体系转型和国际社会变化,也难以解释所谓的非适当行动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意义。(30)
因此,以背景知识为行动基本驱动的实践理论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发现了另外一个原因因素,而在于这种理论发展取向开拓了非主流、非西方理论创新的合法性空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中,20世纪70年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性主义理论所表现的是行动逻辑的单一性、理论的一统性和知识的一元性。建构主义的出现部分地挑战了这种话语主导,开始强调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并提出了国际社会多元无政府文化的观点。实践理论的兴起表现出来的趋势是加大了对背景知识的强调力度,弱化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理性和不确定性等核心假定。知识转向从对知识的不同认知思考行动逻辑,虽然西方学者论辩的焦点仍然是哪种要素构成了行动逻辑的核心机制,但非西方学者看到的则是多元理论发展的广阔空间。在表象性知识的一统天地中,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实践经验如何、思维方式如何,所有理论构建必须在表象性知识规定的边界之内进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也是以表象性知识为普适性标准的。背景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多元本质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论构建和形式的合理性。因此,知识转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自文化”中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提出深刻挑战,也因之释放了“他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潜在能量。知识转向的深层意义正在于此。
(一)自文化、他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在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自文化”指西方主流文化,“他文化”则指非主流、非西方的文化。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所以恰恰可以形象地反映国际关系主流学界的思维定势。(31)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自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是以理性本体论为思维基础、以西方实践和经验为基础、以表象性知识为话语主导的理论构建。自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规定了理论构建的基本途径和理论评判的正统标准,因之成为束缚“他文化”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的桎梏。
理性本体论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坚实硬核。理性本体论以二元分离为本体论依据。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分离,知识超然于经验和实践之上,是对客观世界的表象。知识生产者与客观世界也是分离的,知识生产者可以独立地、客观地、理性地观察和分析世界,所以这样生产出来的知识也就是价值无涉的,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根据这样的观点,无论行动者来自何种背景、何种性别、何种民族,他们的行动逻辑是一样的,比如理性被认定为共性,是任何行动的基本逻辑。并且,这样的行动逻辑可以通过客观数据加以验证。正像自然科学的实验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重复多少次都只能得出一个结果一样,其他任何因素都是没有意义的。新现实主义遵循物质主义,坚持物质第一的本体论,强调物质是独立的,本身就具有意义。建构主义遵循理念主义,坚持理念第一的本体论,强调一切意义来自主体间互动,物质性因素的意义被降低到最小程度。但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以二元主义为基本依据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范畴内的概念,只不过强调的方面不同而已。(32)
根据理性本体论的话语体系,他文化的思想和知识都要统合到理性的边界之内,也都要归依到理性的话语权力框架之中。否则,就不能被视为理论和知识。西方历史,或者说西方的实践和经验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基本依据,并且,这种历史、实践和经验以西方主流社会为主导。纵观西方国际关系史研究,近现代国际关系往往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但此前出现的其他国际体系或类国际体系的历史则被排除在外,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或是东亚的朝贡体系。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知识历史来看,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英国学者卡尔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以欧洲经验为主要背景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奠基著作、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也是以欧洲历史为主要依据。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以理论为先导,例证部分主要则是参照了西方国际体系的多极和美苏冷战时期的两极,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主要使用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为经验事实。(33)
由于表象性知识被不加质疑地视为唯一的知识类别,处于表象性知识边界之内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以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成为普适性的理论并被如此地加以接受。其他地方性的历史,他文化中的实践,也就只能具有一种地位,即作为“客观”证据,验证这些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与事实的吻合程度。由于当今社会科学主流普遍接受“演绎”的原则,以理论为出发点,自上而下地进行科学验证,所以他文化中的实践经验首先就被框定在主流理论提出的假设范畴之内,无论如何,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这些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普适性和强势话语地位,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长期处于一种常规科学状态,难以产生革命性的进步。
(二)自文化内部他者的理论反叛
国际关系的知识转向为释放他文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由于实践被赋予本体优先的地位,被视为行动最重要的原因,心物二分的理性本体论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表象性知识的霸权地位开始动摇。在以背景知识为基本依据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经验人”和“实践者”代替了表象性知识中的“理性人”或是“超验人”。换言之,人作为社会的、经验的主体,其思维和行为是不能与其生活的世界以及在世界中的活动分离的。将背景性知识视为行动最重要的原因从更加根本的层面否定了表象性知识是唯一知识的垄断话语,表明在不同历史文化社会中的实践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不同的理论取向。自文化和他文化的概念虽然主要是指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但即便在西方文化之中,非主流文化体也往往被视为他者。自文化内部的他者群体从理论上思考他们与自文化主流的差异,在理论上挑战了主流理论的话语霸权。
产生于西方社会内部的女性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西方为当然的、具有统一知识、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社会,所以,从来不会将某一社会群体当作行动逻辑的主体。女性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了这种以男性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化方式,提出了基于女性经验和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身为女人,我的亲身经历是什么?女性主义理论学者扎尔维斯基在讨论科索沃战争的时候说,在战争中女人和男人的经历是不同的,因而对战争的解读也就不同。(34)这是一种基于实践进行思考的方式。从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女性国际关系理论是以背景性知识为行动的基本依据,是以女性作为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身份这一特殊经历入手的。女性的经验实践和男性具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处于社会边缘和压抑的基本状态、女性作为社会人的集体经历和记忆等背景性知识使得女性的行为不同于男性行为。(35)而女性的历史经历和实践活动,受到表象性知识的压抑和掩盖,不可能被理性主导的表象性知识所“表象”或是“再现”。只有从女性的经验和实践入手思考行动的逻辑,才能构建符合事实的理论。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理论反叛。但也正是这类理论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多元知识话语搭建了一个创新的平台。
一旦表象性知识的话语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一旦实践成为促成行动的主要原因,人们就会从更多的方面思考行动的原因,从更多的角度审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表明,即便在所谓的自文化内部,不同的次文化体也会提出新的理论,诠释行动的逻辑。
(三)超越自文化的他文化理论创新
知识转向更为重要的意义是释放了他文化的理论创造意义,为多元理论生产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只有在完全意义上的他文化中才能真正实现。他文化作为一种实践和共同体形式,反映的是不同的历史和实践活动。不同文化和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经历和日常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就会具有很大的差异。同时,实践的不同又会导致行动原因机制的不同,在更深的层面上,还会导致生产不同的知识和建构不同的理论。
表象性知识范畴内的行动逻辑势必导向所谓的普适性理论,即表象性理论在任何地域文化场景之中都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行动者的行动。这为国际关系中有关“行动逻辑”的表象性知识解释建立了神坛。所有基于地域文化情景的行动及其背后的动因都被排斥在主导话语之外。其结果是,自上而下的知识意识和理论建构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由于这些理论是表象性知识,是普适性通则,所以,只有在这种思维框架之中才能形成理论,才能进行知识的再生产,也才能发现推动行动者行动的主导原因,也就是说只有在现有的“普适性”理论框架内才能生产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发现新的行动逻辑。
实践理论在深层意义上对表象性知识包含的文化话语霸权提出了挑战,指出表象性知识只是一类知识,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关注的只有这一类知识,所以表现出非正常的“表象性知识偏见”。正因如此,无论是工具理性的结果性逻辑还是规范理性的适当性逻辑,都难以解释非表象性的实践活动。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国际关系领域的表象性知识偏见只不过反映了现代知识界对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崇拜。“现代科学的进步就是远离实践性知识,走向正式的、抽象的表象性知识”的过程。(36)如果这种崇拜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出现,并且形成一种话语暴力,那么,无论行动者的文化背景如何,都会像化学元素一样在相同条件下表现出相同的行动,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也只有一条,其他解释和路径也就因之成为没有科学根据的臆想或是幻觉。(37)
背景性知识以及背景性知识促成行动的逻辑是自下而上的理论。它首先考虑的是行动者自身所处的具体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中长期实践的重要意义,势必将地域文化视为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实践是行动中的文化。(38)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象体系,形成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理论。(39)所以,针对美国学者阿龙·弗莱伯格(Aaron Freidberg)提出今日之东亚即昨日之欧洲的说法,韩裔学者康灿雄明确地指出:“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用欧洲的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而不用亚洲的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呢?”他表示:“我越是研究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越是将亚洲的过去与亚洲的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我就越感到饶有兴趣。”(40)康灿雄所强调的正是基于非西方历史的实践经验所蕴含的理论和知识资源。
近年来,与实践理论同时出现了一批试图使用“他文化”实践资源实现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并引起广泛注意。以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均势理论为例。均势理论认为,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崛起会导致体系的不稳定,为了维护体系稳定,其他国家会采取结盟和制衡的战略。但康灿雄发现,在东亚历史上,均势理论所表述的、欧洲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结盟和制衡现象并没有发生,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联合起来抗衡中国,形成均势,而是出现与中国合作的现象。正因为如此,1300-1900年间亚洲的战争明显少于欧洲。这不是均势理论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在不断的互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偏好和行为方式。(41)也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使得康灿雄通过使用亚洲的历史和实践活动,提出了一个与均势理论不同的国际体系理论观点,用以解释“儒家长和平”现象。
一位华裔学者许田波也有着相似的设计思路。她发现,均势理论对欧洲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却是不适用的。她提出,制衡这个均势理论的核心概念适用于欧洲却不适用于中国。(42)中国先秦时代与欧洲的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却产生了不相似的结果:欧洲最后产生了以个体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中国则出现了大一统的国家;欧洲产生了各方制衡的格局,而中国则产生了统一的秦帝国。(43)显然,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当时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战略选择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解释。
许田波和康灿雄的研究理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研究是从局部实践活动开始的,因此都有一个含蓄的预设:理论从局部的经验和实践中产生,在历史和文化中得以建构。不同文化中的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实践形态和生活方式,一种实践场域中产生的理论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另外一种实践场域中的行为。不同的实践导向不同的行动。
以实践为行动基本动力的理论暗含着一个重要的道理:文化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根据地域和其他自然原因出现了游牧、农耕和商业等几条主要脉络。彼得·卡赞斯坦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也讨论了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六种主要文明形态,强调了多元传统与多元实践对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44)如果从背景性知识的观点加以审视,不同文明的实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实践活动对国家形成以及国家作为一种集体组织的行动逻辑是否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有着何种重要影响?这样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本身就是文化共同体实践活动的建构,是经验的长期积淀和反复激活,是来自实践者的身体力行。如果行动的原因不是理性主导的表象性知识,而是寓于日常实践的背景性知识,那么,理论发展的根源也就在于地域文化的实在土壤之中,而不是超然理性的非凡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理论都是基于具体的、地方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脱离具体经验和实践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基于他文化的行动逻辑理论一方面会在挑战理性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发展创新,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理性话语迎接挑战、对行动的理性要素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知识转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背景性知识为行动基本原因的思想对非西方、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思考和理论建设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可以看出,颠覆心物二分的本体论,挑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为各种文化提供创造性解释行动逻辑的可能,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挑战表象性知识的地位为背景性知识开拓了活动的空间,为非表象性知识争取了应有的话语权。而这样的颠覆和挑战,将为更加多元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更加关注实践的行动逻辑提供发展的平台,尤其是为所谓的他文化理论发展开拓合法性空间。
回顾国际关系领域几十年的论战,不外乎存在两种辩论。一种是具体内容和观点的辩论,比如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另一种是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论争,比如美国强实证性的行为主义学派和欧洲弱实证主义的英国学派等等。但这些论辩,对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而言,并没有真正涉及所谓的他文化问题,都是在自文化中展现理论话语,加强自文化的话语地位。而知识转向却必然蕴含了一个道理:他文化作为不同的实践和经验共同体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创新的可能和必然。这是知识转向最具意义的一点,也是现在西方强调实践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深层意义。
因此,知识转向不仅是一种自下而上地解释行动的逻辑,也是一种释放他者和他文化的逻辑。无论这个他者是女性,是异己,是非西方的行为体,是自文化边界之外的行动者,他们的历史、经历、实践、话语都是知识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上看,知识转向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旦所谓的他文化经验和实践得以释放,就会为理论创建,尤其是关于行动逻辑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提供多种多样的营养成分,使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人类知识生产的过程在多元的交流和冲撞中释放出强有力的原创能量。
①关于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参见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943-969; Robert Nalbandov,"Battle of Two Logics:Appropriateness and Consequentiality in Russian Interventions in Georgia,"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No.1,2009,pp.20-36.
②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参见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④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San Francisco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9.
⑥Jeffrey T.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2005,pp.801-826; Alexandra Gheciu,"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2005,pp.973-1012; 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39-275.
⑦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⑧参见Jeffrey T.Checkel,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应指出的是,虽然建构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价值理性思维,但建构主义强调规范内化,内化后的规范往往成为行动者不假思索的行动导向。因此,较之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已经弱化了理性权衡的假定。
⑨关于规范理论研究成果,参见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召颖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Edward Keene,"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erarchy:British Treaty-Making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2,2007,pp.311-339; Mark L.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actions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Policies,or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2007,pp.145-179; Ryder McKeown,"Norm Regress:US Revisionism and the Slow Death of the Torture N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1,2009,pp.5-25.
⑩参见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参见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纳、埃克·冯·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另参见Emanuel Adler,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5; Emanuel Adler,"The Spread of Security Communities:Communities of Practice,Self-Restraint,and NATO's Post-Cold War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2,2008,pp.195-230;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2)参见Millennium,Vol.31,No.3,2002.
(13)参见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4)(15)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Theory,Vol.3,No.1,2011,pp.1-36.
(16)Vincent Pouliot,"The Materials of Practice:Nuclear Warheads,Rhetorical Commonplaces and Committee Meetings in Russian-Atlantic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5,No.3,2010,pp.294-311.
(17)伊曼纽尔·阿德勒:《欧洲文明:实践共同体视角》,彼得·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101页;Emanuel Adler,"The Spread of Security Communities:Communities of Practice,Self-Restraint,and the NATO's Post-Cold War Transformation," pp.195-230; Emanuel Adler and Patricia Greve,"When Security Community Meets Balance of Power:Overlapping Regional Mechanism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Supplement S1,2009,pp.59-84; 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No.2,2008,pp.257-288.
(18)最近出现的习惯性逻辑则更加强调行动的自发性和无意识。参见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2010,pp.539-561.
(19)(20)参见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p.257-288,260.
(21)C.Robert Mesle,Process-Relational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 to Alfred North Whitehead,West Conshohocken,Pennsylvania: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2008,pp.20-30;参见Victor Lowe,Understanding Whitehead,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6.
(22)Patrick Thaddeus Jackson,"Foregrounding Ontology:Dualism,Monism,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No.1,2008,pp.129-153.
(23)参见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p.257-288.还需注意的是,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是认识论范畴的现代性概念,前者指人的感官对客观事物的印象,反映了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后者指在感性知识基础之上的推理判断,反映了事物的规律和内在联系。感性知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理性知识则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两者在实践中统一起来。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是知识论范畴的概念,前者指来自理性思考的抽象知识,后者指来自实践活动的经验知识,两者没有高低阶段之分。与实践密切相关的主要是背景性知识,故亦称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或是非言明知识(tacit knowledge)。
(24)参见Friedrich Kratochwil,"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p.43-48.
(25)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p.260-271.
(26)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6.
(27)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8)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29)转引自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272.
(30)参见Raymond D.Duvall and Arjun Chowdhury,"Practices of Theory,"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p.335-354.
(31)“自文化”与“他文化”的概念基于后殖民理论对“自我”和“他者”的论述。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揭示了西方自我界定的“主体性”与非西方殖民地的“非主体性”,亦即“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从本源上决定了自文化的主导地位和对他文化的排斥,也决定了两者之间是非包容性的冲突性关系。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2)参见Vincent Pouliot,"The Materials of Practice:Nuclear Warheads,Rhetorical Commonplaces and Committee Meetings in Russian-Atlantic Relations," pp.294-311.
(33)参见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等。
(34)Keith L.Shimko,International Relations:Perspectives and Controversies,Boston:Cengage-Wadsworth,2010,pp.51-52.
(35)参见Rumki Basu,ed.,International Politics:Concepts,Theories and Issues,California and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2,pp.221-247.另外,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知识产品,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 Millennium,Vol.18,No.2,1989,pp.245-253; V.Spike Peterson,ed.,Gendered States:Feminist(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1992;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 Postmodern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6)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260.
(37)典型的是华尔兹批评经典现实主义的说法,即经典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些想法,而不是科学的理论。参见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1990,pp.21-37.
(38)Ann Swidler,"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1,No.2,1986,pp.273-286.转引自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ractices: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14.
(39)“理论即实践”的观点是对理论的一种定义,否定了只有理性活动才是理论建构的途径。这种观点认为,理论是生活方式,是生活形式,是我们每日每时所做的事情(What we all do every day,all the time)。这个观点是实践本体的基本内涵,认为构成理论的不是物质性因素,也不是单纯的主体间话语,而是把理念和物质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活动。根据这个观点,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种族都能够以自身实践为基准进行理论化活动。理论即实践的观点在欧洲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时间较早,当美国主流建构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欧洲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讨论了。但由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当时欧洲学者的讨论并没有进入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参见Marysia Zalewski,"'All These Theories Yet the Bodies Keep Piling Up':Theory,Theorists,Theorizing," 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6-351.
(40)David Chan-oong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xi.
(41)参见David Chan-oong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
(42)参见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43)Victoria Tin-bor Hui,"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sights from Comparing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1,2004,pp.175-205.
(44)参见彼得·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第74-101页。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