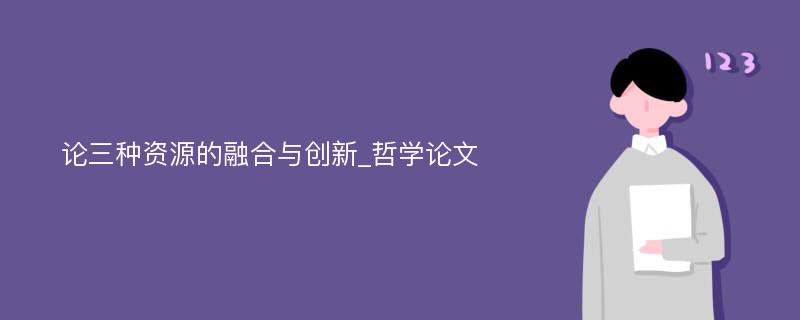
论三种资源的会通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1-0085-06
“中国哲学”是一种现代学术话语。把“中国”和“哲学”两个词关联在一起,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一大贡献。所谓现代中国哲学,可以说就是中国固有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三种资源的会通与创新。“会通”是一种态势,“创新”是一个目标。在建构“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老一辈哲学家取得了理论思维成果,也留下了经验教训。如何吸收他们的理论思维成果和经验教训,是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本文对此话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学科意识的自觉
“中国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建立在哲学学科意识自觉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并没有这样的基础。中国固有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样,都属于包罗万象的学问,被视为“一切学之学”。西方哲学家在17世纪中叶突破了这种观念,实现了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把哲学定位为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的学问,使哲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到20世纪初叶,中国哲学家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也实行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思维成果。
蔡元培是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他对哲学的理解颇具代表性,表明对哲学的学科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把哲学理解为“综合之学”,而是理解为各门学科分化出去之后的独立学科。他在《简易哲学纲要》写道:
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哪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①
在这里,蔡元培表达了一种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他认为,在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不断深化的思考方式。哲学研究应该突出问题意识,体现怀疑精神。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眼光,契合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他强调,哲学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是僵化的教条。现代哲学同古代哲学的区别在于,不再受到宗教的限制,甚至具有取而代之的功能。他叫做以美育代宗教。概括而言,蔡元培关于哲学学科的看法,有三个要点:第一,哲学是关于认识论的学问,应当诉诸理性,讲究逻辑证明,不能建立在“圣言量”上面,不能以引证代替论证。第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提出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理论。第三,哲学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帮助人们树立一种指导人生实践的价值理念。基于这种认识,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创办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哲学系。
同蔡元培一样,冯友兰也认为,讲哲学不能诉诸直觉,必须诉诸理性。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说:“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至于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二是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三是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②
最早表述哲学学科自觉意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瞿秋白。1923年,他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讲授《社会哲学概论》。他在讲义中指出,最初的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③他明确地指出,各门科学纷纷独立之后,作为学科的哲学便只成为“求宇宙根底的功夫”,也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以上三位哲学家的哲学信仰不一样,但在哲学观上却存在着共识,都认识到哲学乃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这种共识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已经突破古代哲学的框架,跨入现代哲学的论域。由于中国哲学家对于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比西方哲学家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西方哲学这样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误认为“标准”的哲学形态,过分看重中西哲学的共性,而忽略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他们在突破中国固有哲学的局限的时候,也疏离了本民族的优良精神传统,陷入单数哲学观的误区,没有充分意识到哲学形态的民族性和多元性。对于这种单数哲学观,也有人提出质疑,表示认同复数哲学观。金岳霖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坦言:“我很赞成冯先生的话,哲学根本是说出一种道理的道理。但我的意见似乎趋于极端,我以为哲学是说出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这个道理冯先生已经说过。但何以又要成见呢?哲学中的见,其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的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者暂时不能证明与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他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这不是哲学的特殊情形,无论甚么学问,无论甚么思想都有,其所以如此者就是论理学不让我们丢圈子。”④讲哲学就是讲道理,当然应该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不过,要想对结论做出完全充分的论证,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任何一种哲学结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论断,难以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找到充分的理由,难以达成所有人的共识。哲学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假设或信仰的色彩,故而金岳霖称之为“成见”。“成见”与“道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复数,而后者是单数。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1927年,他在《儒家哲学》一书中写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⑤很可惜,金岳霖和梁启超的复数哲学观并未引起哲学界的重视,也没有改变单数哲学观占主流的情形。
二、三种资源的外在会通
中国现代哲学家取得的第二项重大的理论思维成果,就是致力于三种哲学思想资源的会通,力求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单数哲学观的限制,他们对中国哲学的民族性认识不足,未超出“外在会通”的层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选择的路向不同,前者以“意欲调和持中”为基本特征,后者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基本特征,然而他却不否认中西哲学之间有可沟通性。他发现,“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⑥。他把儒学同生命哲学加以会通,找到了开启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路径。他的会通以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为前提,属于一种外在的会通方式。
冯友兰从单数哲学观出发,运用新实在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取得的成绩是写出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他在该书的《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史所讲的内容,就是“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者名之者也”。同梁漱溟一样,他也努力寻找中西哲学的相似点共同点,未超出“外在会通”的范围。从今天的视角看,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冯著旧版《中国哲学史》有傍依西方哲学之嫌,但他毕竟从哲学学科自觉意识出发,对中国固有哲学做了比较系统的处理,把中国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起来。我们不必苛求前辈,因为他们在起步阶段,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研究水平长久没有得到提升,不能归咎于前辈,而应当归咎于我们自己。冯友兰撰写完《中国哲学史》之后,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哲学史家,开始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1939年开始,他陆续出版“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在“贞元六书”中,《新理学》是关于宇宙论或世界观的专著,《新原人》是关于人生论或人生观的专著。关于知识论,他没有写出系统的专著。他创建的新理学体系,“外在会通”的特征也颇为明显。其中使用的主要范畴理、气、道体、大全等等,取自中国传统哲学,而“共相单独存在”的观念则取自新实在论。
贺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也在努力寻找中西哲学的相似点,力求把二者会通在一起。他信奉单数哲学观,认为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合贯通,去发扬光大”。⑦中国哲学虽有儒、道、墨三家,亦可归结为唯心、唯物两派;西方哲学虽有唯心、唯物两派,亦可归结为儒、道、墨三种类型。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完全可以会通。他创立的新心学体系,也是“外在会通”的产物,一面承接中国陆王的学脉,一面承接鲁一士“绝对唯心主义”理念。
金岳霖虽不认同单数哲学观,但在会通中西哲学方式上,同上述哲学家大体一致,也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写出《论道》一书。道既是金岳霖本体论学说的出发点,又是归结点。他从道出发,抽象出能的范畴,又从能导出式的范畴,最后又把二者都囊括到道之中,从而形成“道-能-式-道”的架构。道是金岳霖本体论思想的核心。他说:“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式那样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实。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象宇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⑧在金岳霖那里,道是中国哲学的“旧瓶”,可是其中装的“新酒”却来自西方的新实在论,仍未超出“外在会通”的范围。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对金氏“旧瓶装新酒”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中国哲学并不是“旧瓶”,也无需装什么西洋的“新酒”。
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加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很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暂时还来不及考虑这种新哲学如何同中国固有哲学如何会通的问题,把更多精力放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考量上。毛泽东形象地把马克思主义喻为“矢”,主张“有的放矢”,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但还未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运用大量的中国文化史上的资料,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还在《时》一文中引用庄子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等名句,用以说明主观认识的局限性,可以看出中国固有哲学曾对他接受和理解唯物史观发生了潜在的影响,但他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取得许多成果,如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侯外庐著《中国思想史》,但也没有考虑如何用中国固有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毛泽东把中国固有哲学中的某些思想材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提出“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命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示呈现出中国特色,但也不能算是两种资源的有机结合。总的来看,两种资源尚处在相互外在的情形,未达到“内在会通”的程度。
三、“哲学”与“中国”的疏离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建构,迈出的第一步是“外在会通”,接下来的第二步本该是“内在会通”,可是这一步竟迟迟没有迈出,反而蹈入“哲学”与“中国”的疏离,切断了二者之间的关联。1949年以后,在“左”的思潮主导下,复数哲学观无人敢讲,单数哲学观成为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唯一模式。不过,这种唯一可以讲的哲学,并不是冯友兰心目中的“道理”,而是来自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原理”。在“哲学是单数”的视域中,“中国哲学”的概念没有存在空间,只容许讲“某种哲学在中国”,不容许讲“中国自己的哲学”。
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流行开来以后,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只能唯“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仿佛世界上只有一种哲学,就是苏联哲学教科书讲的那种哲学。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掌控了话语权,讲哲学只允许用一种声音,不容许出现不同的说法;只容许认同单数的哲学观,不容许认同复数的哲学观;只容许讲普遍性,不容许讲特殊性。在这样的语境中,哲学家独立的哲学思考能力被限制住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哲学”意识的失落。
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哲学的讲法被单一化、简单化,一律归结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研讨,把这个问题认定为适用于任何哲学的“基本问题”。至于为什么说是“哲学基本问题”,教科书并未做出充分的论证,只是引证恩格斯的一段话为理论依据。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的确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说法。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恩格斯的说法,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做教条主义的理解。我们不能忽略恩格斯同时说的另一句话:“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⑨引用者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是在西方哲学语境中讲的,指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指人类的全部哲学。恩格斯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哲学,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埃及哲学、印度哲学等,不会贸然下一个“全部哲学”的断语。从形式上看,恩格斯似乎做了全称判断,实际上则是特称判断,特指德国古典哲学或者西方哲学。因此,从恩格斯的论断中,不能得出“物质与精神关系的问题适用于任何哲学”的结论。如果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对恩格斯的误解,并站不住脚的。
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哲学基本问题”公式化、普遍化,不否认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否认不同的民族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恩格斯只是以西方哲学史为例说明他的论断,并没有论及其他民族哲学史的情况。他特别提到,思维对存在的地位的问题,在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具体地表现为精神与自然界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在这里,恩格斯谈的显然是西方中世纪哲学的特殊性,并不是整个人类中世纪哲学的普遍性。如果不顾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具体情形、具体特点,把恩格斯的具体分析简单地套用到其他民族的哲学史上,无疑有违于恩格斯的本意,并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哲学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上帝创世论的思想影响很大。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哲学家们才把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来思考。世界是从来就有的?还是上帝创造的?这是西方人才会有的一种困惑,是在基督教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中才会提出的问题。中国古人从来没有上帝创世说的观念,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创世说的传说,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但只是小说家言,不能作为一种非常严肃的学术观点拿到台面上。我们不能用看待西方近代哲学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固有哲学。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任何哲学必须讨论的基本问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讨论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中,没有单独使用“存在”这个西方哲学常用的范畴,另外创立了“社会存在”这样一个新范畴。所谓“社会存在”,是指属于人的存在,并非指与人毫无关系的客观世界本身。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泛泛而谈“存在决定意识”。其实,“客观世界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无限性,并不能成为人认识的对象。人只能以客观世界的部分为认识的对象,得出具体的结论,而无法以客观世界整体为认识对象,因为人自己就在“客观世界”之中,无法与之对象化。人不可能站在“客观世界”之外,因而无法对“客观世界是什么”做出判断。换句话说,对于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人无法给出答案,无法达成共识。马克思指出,自己创立的新哲学,同以往的西方哲学有原则区别:以往的哲学以“解释世界”为宗旨,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追问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恐怕仍旧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话语,显然有违于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初衷。
当“哲学”与“中国”的关联被切断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成为三个各自独立的二级学科。讲西方哲学史,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用不着讲“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讲教科书就够了,也用不着讲“中国”;至于讲中国哲学史,其实并不讲“中国固有哲学”,只讲“中国思想材料”,以便为“哲学原理”提供例证。在这种语境中,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丧失了创新能力,患上了失语症,不能做思想家,只能做宣传家,跟着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亦步亦趋。
四、内在会通与创新诉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和“哲学”再次被关联起来,迈入“内在会通”发展阶段,表达出强烈的创新诉求,失落已久的“中国哲学”意识开始复苏了。这在高清海、冯契、冯友兰三位当代著名哲学家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突破单数哲学观的藩篱,重申哲学的多元性,提出关于哲学的新见解,并且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固有哲学的“内在会通”。“内在会通”的诉求在于,不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清海教授较早对苏联教科书的讲法表示怀疑。我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生期间,他多次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当只有苏联教科书这样一种表述方式,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不能被教科书的讲法捆住手脚,而应当大胆探索,找到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讲法。他认为,苏联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用一个“和”字联系在一起,已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不可能再讲成“一整块钢铁”。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只讲物不讲人的倾向,他提出批评,强调哲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而应当是属人的客观世界。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同苏联哲学教科书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有当代中国哲学家的独到见解。他不再照着苏联哲学教科书讲,而是按照中国哲学家的理解,接着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冯契教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体现出两点意向:一是化理论为方法,二是化理论为德性。他大胆地把“德性”这一中国固有哲学范畴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法中。“化理论为德性”的具体内涵,就是培育“平民化自由人格”理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冯契心目中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就是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新人。按照他的理解,“共产主义事业正像马克思说的要‘由于人’和‘为了人’。这个事业要通过新人来建设,而且这种建设是为了使人成为新人。培养人,让人能够真正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一个头等的大事。我们搞共产主义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人成为新人”。⑩冯契的人格理念既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也是接着中国固有哲学讲的,并且把这两种思想资源融会贯通。中国固有哲学特别重视人格问题,冯契继承了这个传统,同时又超越了这个传统,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找到了新的讲法。在中国固有哲学的人格理念中,儒家推崇圣人,强调人的道德素质;道家推崇真人,强调人的精神境界。这两种人格理念的共同缺陷是缺少发展的观念,对人的能力素质重视不够,因而很难塑造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冯契着眼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需求,把传统人格理念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新人格的理论设计。这种新人格既有很高的道德素质,也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还有很强的能力素质。总之,新人格是全面发展的平民,不是古人所憧憬的单向度的圣人。
冯友兰教授在晚年坦言,自己虽然曾经上过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理论骗子的当,但决不因此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郑重声明:“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定二度重写中国哲学史。“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他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西方哲学历来讲论的自然现象学。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11)按照这种说法,不应该再把哲学视为解释世界的“物学”,而应当视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人学”。如果把哲学视为“物学”,尚可归结为“一”,因为人类住在同一个地球之上;而把哲学视为“人学”,由于反思的主体各不相同,就只能归结为“多”了。按照冯先生的这种新哲学观,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物。这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看法是一致的。至于哲学的功用,他认为应当有两个:“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关于第一点作用,恩格斯已经谈到,冯先生表示完全同意。至于第二点作用,则是中国哲学家才会有的独到见解。在西方哲学家的眼里,哲学起于好奇,同人的精神境界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中国哲学家才会如是观。冯先生认同中国的精神传统,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12)由此来看,冯先生的新哲学观葆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上三位中国当代哲学家的讲法,不再受苏联教科书的限制,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识度,指示出“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天不假以时日,他们未来得及完全实现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未竟之志,难道不应该由我们来完成吗?
注释:
①《蔡元培哲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页。
③黄美珍等编:《上海大学史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所引文字见《附录》。
⑤《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⑥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153页。
⑦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7页。
⑧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⑩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1)(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第27页。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冯友兰论文; 恩格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史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金岳霖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